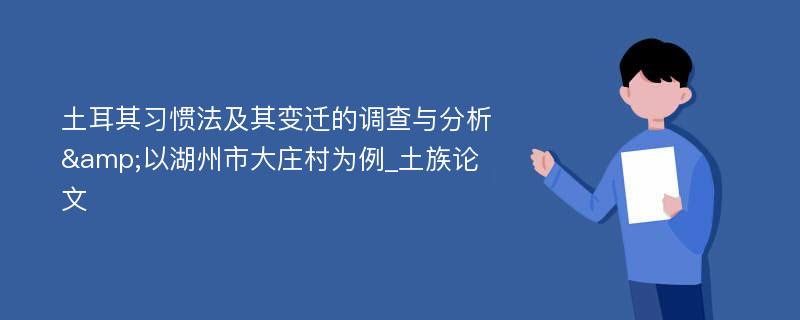
关于土族习惯法及其变迁的调查与分析——以互助县大庄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族论文,习惯法论文,为例论文,庄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47(2005)01-0020-05
大庄土族习惯法是大庄村村民长期口耳相传,世代相袭,逐渐被村民整体加以确认,并成为普遍遵循的习惯准则,是调节村民之间某些关系的社会规范。长期以来,土族习惯法曾在维护社会稳定、缓和村民矛盾、保护村落生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深刻变迁。2003年7—8月间,笔者参与了云南大学211工程重点科研课题——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活动,对大庄土族历史上和现存的习惯法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篇调查报告,希望有助于开展土族习惯法的研究。
一、大庄村历史上的习惯法
我们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和对大庄村籍省的民委老干部董思源和村老支书胡宗显、村民刁忠、东才让的访谈得知,旧时大庄村习惯法主要表现在调节纠纷,财产继承,处理奸情、命案,保护庄稼等方面。
1、家庭财产的继承。
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庄村每个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一切财产,他人不得侵犯。关于财产继承,一般是在家的儿子继承财产,外嫁的女儿无财产继承权。若有几个儿子,每人各占一份。分割财产时多由家长(一般为父母)来支配;若兄弟众多,同居一家时不能和睦相处,由家族中的长辈会同他们的父母主持分家,一般长子和幼子可以多得一些财产。父母不在世时,则由家族中的长辈会同兄弟们公平分配,最普遍的情况是长兄可分得上房,其余房屋按次序分给其他兄弟们。若家中有女无子,经家族长者们同意后可招外姓男子,但在招赘时必须改为女方姓,这样才能成为本家族成员,其地位如同儿子,有权继承家中财产。如家族亲属中有侄子愿意过继为子,则让女儿出嫁,让继子继承家产。过继儿子或招赘女婿,都须事先征得血亲关系亲近的家族长者同意,才可让其子去过继或入赘。如绝嗣,则由家族长者按其遗嘱分配家产;若无遗嘱,其家产一部分布施给寺院,一部分由家族最近亲的各户继承。
2、土地占有及处理。
(1)土司、寺院等所属土地租赁及交换。20世纪30年代前,大庄村约1200亩土地属于杂思朵的李土司,约100亩属于民和县老鸦峡莲花台寺属地,还有30亩公地属于全村所有,由大庄村庙官、老者们管理。大庄村大部分贫苦村民每年租种这些田地,向他们交纳租粮和各种捐款,并服各种劳役,承担兵役等。虽然没有任何禁止租种者离开土地的规定,但因土地附有兵税,租种者难以转让或退租。土司所属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但土司有权同其他土司或私人交换土地,并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土司所属的荒地,私人开垦时,必须向土司请准。民国以后,改土归流,大庄村民只交粮给县府大仓,不再给土司纳粮。
(2)私人土地、房屋等财产买卖、典借。私人所拥有的土地、房屋等财产,若主人因故买卖、典借,家族中各户有优先购买、典当的权利。家族内无人购买、典当时方可向外处理,但仍需征得家族长者的同意。买卖、典当要请保人订立契约;若无人识字不能订立文字契约,则用石片或骨板碎成两半,买卖双方各执一半,以作凭证。有识字人时,订立契约。典当契约一般书写两份,买卖契约则写一张。典当地没有定期赎回的说法,何时有钱何时可以赎回,故一般字约上都写着:“有钱当日抽约,无钱长年耕种”。土地买卖成交后,买方除拿出地价外,还须另外拿出三份钱,一份给中介人,一份给写约人,一份给卖房的亲房(即卖方家族长者),因为买卖契约上还须有卖方的亲房人画押才算有效。这三份数额多少不定,一般是中介人和亲房人所得相等,写约人是中介人之一倍。此外,买方还得另备酒饭招待一次。
3、土司对属民的司法管辖。实行土司制度时,土司对所属大庄村和外村土族村民的统治较严。在土司制度下,土族属民按村庄大小、人户贫富,分为五班或四班,一切杂役、供应费用,都按班份来负担。大庄村、姚马三庄为四班制。对盗窃、打架、伤人等行为,土司可设公堂处理。土司审理诉讼时,公堂两侧,侍立衙役,设有皮鞭、板子、绳索等刑具。案件中有被处以拘留者,则在空房里囚禁;有被处以打罚者,则受皮鞭、板子痛打;有被罚款的,其所交罚款多拨付村庙,作为修理费用。土司裁定的民刑事案件,均存档管理,土族村民对其无权过问。奸情案件一般由土司的夫人处理。重大案件,转交县府解决。
4、村民内部纠纷的调解和处理。
(1)一般纠纷的调节。大庄村村民间一般纠纷包括家庭不和睦、邻里不团结或村民间因生产、生活、债务等发生的争吵和斗殴。发生此类事情,大庄村村民多采用民间习惯法调解。一般情况下,家庭或家族内的纠纷由家长或家族长者调解和处理。属于不同家族的村民间发生纠纷打架,则请村上有声望的老人出面调解。经调解后,理亏的一方须向对方赔情,轻者携酒一两瓶到对方家中互相喝一杯,表示和好,谓之“拿酒上门”。情节较重者,除携酒一两瓶外,酒瓶上尚须搭盖一块哈达或一条毛红(宽五寸、长丈余的红布)。情节特别严重者,须“拉羊搭红”,即拉一只背上搭有红布的羊,外加两瓶酒。
(2)伤害案和命案的调解。如打伤了人,请村上有声望的老者或各家族中长辈出面调解,同时要“拉马搭缎,说理赔情”,即拉一匹马,上搭一匹绸缎,跟随老者去受害人家登门叩头认罪。如打死了人,必须赔命价。命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但命价很高,常致凶手倾家荡产。赔过命价,凶手不会再受任何处分,所以当地有“罚了不打,打了不罚”之说。如案件不能了结,死者的亲属聚到凶手家中任意拆毁房屋、器具,牵拉牲畜,长期居住在凶手家中,由其供给肉食油面,何时了结,何时才离开,这种做法叫做“吃人命”。
(3)奸情的处理。若勾引他人妻子而被其夫发现,通常由地方老者调解。其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拿酒搭红出钱上门赔礼;另一种是干脆由其夫将妻子转让给对方,其代价一般为一大石或二大石麦子,并立字据为凭。采用这种办法,其夫最受人蔑视,妻子也会被人叫做“活剩己”(意为坏蛋,活得只剩下自己)。转让字约不得在家里写,更不能到别人的田地、宅院里写。村民们认为在谁家的地边上写这种字约,谁家的田地里就不会长出庄稼。必须到离村庄较远的荒郊野地去写,用破笔、破桌子、破砚台,写完丢弃;同时,必须付给代书人很高的价钱。
5、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
举行村庙祭祀、保护庄稼是旧时大庄村民管理村内公共事务的重要事项。当庄稼出苗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大庄村全体成年男性村民聚集在本村村庙内点灯、煨桑,向大殿内的神佛顶礼膜拜,并对大庄村地方保护神龙王进行祭祀,以求庄稼获得丰收。然后由众人商议村内村庙祭祀、保护庄稼等公共事务,并制定和修改与之相关的护青、祭祀制度,要求村内全体成员遵守,若有违反,给予处罚。负责管理这些事务的人员分别是每三年由众村民推选出的庙官和老者、每年按家户轮流的“特日其”(即青苗头)。护青制度比较固定,大部分逐渐成为大庄的习惯法。如从保护青苗之日起,不许打架斗殴;禁止在田间地头及护坡上放牧;举丧不许号哭,禁止砍树、拆房等。如有违者,老者、青苗头们可以根据情节给予劝告、罚款、罚粮、罚工等处罚,若不服,则加重处罚。
二、现村内秩序的维护和纠纷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行政司法等各种权力的深入,大庄村基层组织建设日趋完善,传统的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庄村护青等制度基本上被废弃。改革开放后,一部分旧有的习俗和管理方式被恢复。随着近几年基层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国家司法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深入,大庄村整个村内秩序维护和纠纷处理呈现多元化趋向。
1、护青苗期间庙官、老者等对庄稼的管理。
1982年,大庄村村民们自动恢复了旧时的护青苗制度。护青会现由1名庙官、1名光涅、5名老者和6名特日其组成,又称广福寺(大庄村佛寺名)寺管会。庙官是平时管理大庄村广福寺内的收入开支和安排村内护青活动的主事。庙官要从全村年龄较长、德高望重并熟悉各种宗教仪式的人中选出,每隔3年,由“龙王”直接选定。老者也是三年一选,由大庄村下属的每个自然村选出,他们平时负责广福寺内香火、钱物的管理,在村内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并制定护青协议。特日其多为办事干练的青壮年男子担任,任期为1年,由每户村民轮流担任。在护青期间每天有老者、特日其在田间地头巡逻保护青苗。护青期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举行“插牌”仪式开始,九月初九举行“谢降”(即拆牌)活动后结束。护青(也叫插牌)期间,村内不许砍树、不许拆房,不许村民之间吵架和斗殴,不许村民在田间地头放牧牲畜。如谁违抗,便由庙官、老者、特日其处理,轻者劝说、警告,重则罚款、罚粮,罚款数额一般为20—60元不等,罚粮数额一般为50—60斤。由于老者大都由村内辈份较高、年龄较大、经验丰富、办事公正的人担任,在大庄村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再加上护青苗活动是维护整个村落整体利益,所以对违犯者所进行的处罚都能顺利执行。
2、家长、族长对家庭、家族事务的处理。
大庄村内某个家族或家庭中出现分家产、接纳家族新成员、惩罚触犯家规的成员等重大事务时,仍保持旧有的一些习俗,即由本家族德高望重、年长辈高的长者们召集家族内各户家长协商决定。例如某村民家中,儿子们长大成了家,父母想让他们各立门户,这时由家中老人主持分家,并请家族中的长辈到场,说明分家的情况及对财产分配的理由等。一般情况下长子分家单过,父母随同幼子在老房居住。对于财产的分割,家里老人说了算,家里承包的耕地一般按人口分。如某家招赘,家长也要请本家族中的长者到场,说明招赘理由,入赘女婿将原姓改为女方姓或承诺入赘后生男孩跟女方姓后,长者们代表整个家族将其视为本家族成员,进行一些如孝敬父母、夫妻和睦等方面的教导。遇老人过寿、看病或去世等大事,费用由儿子们分摊,如果儿子们彼此推脱,会遭村人谴责和族内长者的质问。此外,遇家族中谁家有婚丧嫁娶,便由族中长者们商议人选主持,安排族中成员帮忙。
3、大庄村村规民约的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庄村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即习惯法)在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曾起过较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大庄村村民制定的村规民约,其性质与大庄村旧习惯法完全不同。随着时代发展,村民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不断补充着新的内容,成为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维护大庄村整体利益、村落秩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庄村的村规民约共十条:(一)努力学习雷锋、朱伯儒、张海迪等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共产主义思想,说话和气,礼貌待人,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做到:不吵嘴,不虐待老人。(二)提倡种草种树,美化环境,勤洗勤扫,讲究卫生,保证做到人有厕所,禽畜有圈,院内门外经常打扫,保持清洁。(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全村的文化程度和思想水平,做到不聚众玩赌,不酗酒闹事,不干损人利己的事情,违者酌情罚款或予以适当的惩处。(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区分正当的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动。对那些坑害群众,直接破坏生产、干涉教育的巫神、法拉等要加以制止,屡教不改者要罚款或按有关规定处理。(五)坚决贯彻执行婚姻法和计划生育,大力宣传和提倡晚婚、晚育、晚生、优生,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坚决克服重男轻女,扼杀女婴的现象,违者一经查出按规定惩处。(六)维护集体利益,加强护青、护林制度、管好畜禽,不得在禁区放牧、割草,违者分别给予下列处罚:1、在禁区内放牧大牲畜,每头每次罚款伍元,猪每头每次罚款两元,鸡每只每次罚款伍角,当场兑现,不得拖延时间,拖得越长越要加重罚款。2、小孩摘穗头、豆角等,一经发现,每支穗头罚款一角,每只豆角罚款五分。3、在禁区割草者,每平方米罚款一元。4、在庄稼地里走捷路者,每人每次罚款五角。5、偷砍树木者,除追回原物外,罚原物价值的两倍。(七)遵守社会公德,提倡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的新风尚。严禁在公共场所乱吵乱嚷,说脏话,破坏公共秩序。(八)教育孩子不玩火(特别是在冬季),一经发现,每人每次罚款两元,并责令其家长当场兑现,拖者加倍。(九)提倡劳动致富,勤俭持家,互相帮助,共同富裕,发展多种经营,保证完成国家的派购、征购任务。(十)人人争当五好个人,户户争当五好家庭,让文明礼貌之花开遍大庄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庄村的村规民约共七条:(一)遵守社会公德,提倡助人为乐,团结友爱,说话和气,礼貌待人,不聚众玩赌,不酗酒闹事,不干损人利己的事情。(二)维护集体利益,加强护青、护林制度。管好家禽家畜,不得在林子里、塄坎上放牧,大牲畜全部围养,羊只不准上塄坎,违者大牲畜白天偷放罚款10元或罚粮100斤,晚上偷放罚款20元或罚粮100斤,羊只上塄坎、进树林、苗围每只罚款1元。(三)保护水利设施、公路桥梁、田间道路,不准在田间路上乱取土挖坑,社员用土在自承包地里或有土坊的地方去挖。(四)爱护广播线路、高压线路,禁止偷电,使用电炉子和瓦数大的灯泡,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教育小孩不得玩火(特别在冬季),不准剥树皮、折树苗,如发现折树苗、剥树皮的均罚款1元。(六)为了搞好社会秩序,改变村风,今后村里社员发生纠纷由村委干部进行调解处理,每调解一次当事人交纳调解费5元。(七)人人争当五好个人,户户争当五好家庭,让文明礼貌之花开遍大庄村。)其内容绝大多数和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相一致,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促进作用,部分内容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紧密联系。它的执行既不是靠村委会干部的个人权威,也不是靠国家强制力量予以保障,而是靠大庄村村民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其中不但含有“护青”条例,而且涉及大庄村的方方面面: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提倡建立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倡导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等社会主义新风尚等。但同时它作为大庄村村民共识的反映和村民利益的表达,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每一条规定并不总是与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甚至有少部分内容与国家现行法律相抵触,比如随意进行罚款等,对村民行为的规范缺乏正面的善意的引导。
三、国家制定法与土族习惯法的关系
1、历史上中央和地方成文法的更替对土族习惯法的影响。
大庄村土族的先民最早可追溯到吐谷浑、羌族的党项,突厥族的沙陀。(注: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61.)史书记载,“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注: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树洛干“轻徭薄赋,信赏必罚,吐谷浑复兴”。(注: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还有“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窒商人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死;他犯则征物以赎”,(注: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亦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 (注: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可见,吐谷浑时已有赋税法、刑法和罚处财物之法。大庄土族先民自然难以脱离其法律体系。自公元663年吐谷浑为吐蕃王朝兼并后,互助地区一度处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吐蕃在占领区设置“茹本”、“通颊”及昂锁等行政机构和管理者外,还相应颁布推行《法律二十一条》。其内容为:杀人者偿命、争斗者罚款;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8倍;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谎言者割断舌或发誓;虔信佛、法、僧三宝;孝顺父母,报父母恩;尊敬高德,以德报德;敦睦亲族,敬事长上;勿与贤者贵胄相争;出言忠信;学习佛法,了解其义礼;要信因果,忍耐痛苦,顺应不幸;帮助邻里,勿作侵害;如期还债;饮酒有度,具羞耻之心;斗要公平,不用伪度量衡;不生嫉妒之心,与众和睦;不听妇言,自作主张;语言谨慎,说话温和;如果是非难明,当对神祗发誓。(注:白廷举.土族习惯法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3).)这些法律的推行,对土族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庄村的许多习惯法都与这些法律相吻合,从中可以窥见吐蕃成文法的遗留痕迹。土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自元代开始,延至20世纪30年代。土司既是中央王朝统一法制的维护者,又是土族习惯法的执行者。在土司制度下,土族地区土司衙门土规土律,必定以土族习惯法为主要内容。但封建王朝制定、颁布的成文法令也起一定的作用。如明末藏巴汗制定了《十六法》、清朝政府曾先后制定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青海番夷成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理蕃院则例》及《蕃例条款》等。这些成文法先后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从而使大庄村土族习惯法深受多元法文化的影响。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明令彻销土司一案”,下令废除土司制度,土族地区延袭六、七百年的土司制度被正式废除,一部分土司变或村长、区长,大部分土司变成了世俗地主。1938年马步芳正式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编制保甲制度,原有红牌、乡老制度逐渐废止。每户人家都被贴上临时门牌,还被清查了户口,登记了壮丁,强迫村民订立保甲连坐公约。(注:主要内容为: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决不违抗,如有来人立即禀报甲长,决不暗通匪特,隐藏奸细,若有违犯者要立即呈报,若有隐匿不报者,各户均受最严厉的连坐处分。)自从实行保甲制以后,开始受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典》、《惩治贼匪暂行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禁烟法》等成文法约束和影响。但习惯法在大庄土族村民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2、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下的土族习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颁布并执行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法律文件,都成为大庄村土族群众遵守执行的成文法。但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部分习惯仍然与国家法律发生着冲突。其一:在财产继承、婚姻家庭等方面多以旧有的习俗为准。在大庄村土族村民中虽然多次宣传了《继承法》和《婚姻法》,但效果不明显。现今大庄村土族村民分割家庭财产和继承遗产时仍将出嫁外村的女儿不包括在内。除非家中无儿子,女儿不出嫁实行招赘。同样被招赘到外村的儿子也无权享有其原家庭财产分割权。此外,如果男方早逝,其妻可以改嫁,但子女和家中财产不得带走,只能带走嫁妆。作为绝户,房屋等财产归堂兄弟。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早婚现象较为普遍。可喜地是,目前大庄村村民不像过去以举行婚礼作为婚姻成立的标志,结婚时领结婚证成为大庄村村民认可婚姻成立的普遍共识。其二:在重大经济交往中普遍运用国家法律。大庄村村民之间有时会因为临时的困难向他人借钱、借物,这种借贷一般是口头约定,有钱、有物时立即归还,如有能力还债而拖欠会受到村内舆论的谴责,在全村人中失去信任。重大经济交往或承包土地、森林、荒地等活动大都通过公证等形式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双方在签订这些合同时,许多合同格式不规范,出现价款和酬金欠斟酌,违约责任规定欠具体,标的不明和数量不清等问题。还有的村民不按手印和印章,或合同签订方随便委托一人去县公证处办理有关事宜。因此合同、公证程序不是那么严格。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国家成文法在大庄村的地位逐步上升,传统的禁忌和习惯法地位逐步下降。目前,成文法倍受重视,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点。然而,土族村落传统的习惯法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某些方面,仍发挥着国家成文法难以替代的作用。可以看出,目前调整土族村民社会行为的规范大致有三个来源,即全国统一性法律、自治地方法规与单行条例、民族习惯法。三者的关系是:全国统一性法律在土族地区具有普遍使用性和最高权威意义,同时通过委任或准许方式给予土族自治地方制定条例并实施的部分自主权,通过准许方式给土族习惯法以部分自主。土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和规定基本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同时依照国家制定法,结合土族地区实际存在的习惯法,确立并实施自己的法律规则。土族习惯法实际上在土族地区作为土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存在,在最广泛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收稿日期]2004-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