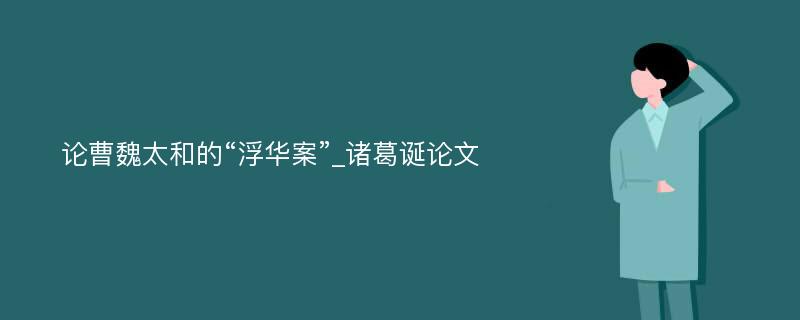
论曹魏太和“浮华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和论文,浮华论文,曹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间,一些刚刚步入仕途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品评人物、清谈名理,风靡于上流社会的青年知识群体中。这在朝中当权的建安老臣眼里,无疑属于危害社会稳定而应当取缔的非法结社活动,按当时的罪名叫作“浮华交会”或“浮华朋党”,因此最终导致了镇压这种活动的“太和浮华案”发生。其实,这次“浮华交会”风潮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魏晋玄学思潮即将到来的前兆,正始之音的序曲。遗憾的是,学术界一直未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对揭示曹魏前期社会政治势力的变化、士人文化心态的动向与正始玄学思潮形成的内在联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早在魏明帝刚刚登上帝位的太和初年(公元227年), 青年知识分子互相交游清谈的风气就已见端倪。“(荀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1〕有些学者认为,文中“善名理”的傅嘏与“尚玄远”的荀粲之间的争论是礼法之士与玄学家的争论。这种看法很难成立。《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转载上述事件时,称傅嘏为“善言虚胜。”可见,名理与虚胜含义相似,都指用形名方法探求事物的道理,即有形事物中的“道”,而荀粲的“尚玄远”大概是喜欢研究天地之外的“道”,总之,两人并无根本不同,仅是认识角度有差异。正因为双方“宗致”相同,所以裴徽才能调合双方观点,“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我俱畅。”〔2〕达成一致见解,最终成了思想上的好朋友。 荀粲和裴徽都是著名的玄学人物,对他们的思想事迹,后面还要涉及。在太和时期,这种交游清谈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还不是他们,而是何晏、夏侯玄、邓飏。
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
,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傅嘏传》注引《傅子》。
从《傅子》以上评述看,何晏、邓飏和夏侯玄三位活跃人物的特点和作用各不相同。何晏似乎以思想家形象出现,以其突出的“材辩”——对人材问题的雄辩而驰名于思想界。邓飏善于联系交际,打通各种人事关系,“好交通、合徒党。”夏侯玄则以其人格的内在力量居于“宗主”地位。对照他们后来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傅子》的说法尽管带有贬意,但基本上是可信的。
何晏本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后随母尹氏入魏宫,成为曹操宠爱的养子。由于何晏与曹丕之间关系紧张,所以于曹丕在位的黄初时代未被录用。曹丕死后,何晏的境遇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仅仅从“无所事任”的处境变为“冗官”——大概因为与沛王曹林的妹妹金乡公主结婚而被封为关内侯,并加上了“驸马都尉”这个当时皇亲国戚一般都能得到的闲散虚职。如果说魏明帝有时也欣赏何晏才干的话,那么也只是让他陪同游宴,为吾皇的丰功伟绩吟诗作赋以歌功颂德。例如,何晏就曾遵命为新建的景福殿作赋,为曹叡粉饰太平。虽然何晏在该赋中也借机躲躲闪闪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要求实施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但这观点除了现代研究者们由之而发现何晏此时的玄学思想萌芽之外,在当时朝中没有引起什么思想波澜。在历史记载中,除文赋之外,何晏引起魏明帝注意的并不是其思想见解,而是其漂亮的仪表。“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3〕很明显, 何晏的地位只是一个文学侍从或名为“驸马都尉”的高级文化倡优。
对于一个年仅二十多岁的普通青年来说,魏明帝赐与的政治待遇也不能算太低,但何晏出身魏王室,又是个才华横溢并且有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所以这种境遇与他的期望值之间则有天渊之别。在何晏的主观感觉中,此时的他与被打入冷宫的曹丕时代相比,也只能算从第十八层地狱升入第十七层而已。当时,在何晏的朋友中和他一样自认为受到魏明帝不公正待遇的青年官员,有曾“为尚书郎,除洛阳令, 坐事免”〔4〕,被一度罢官的邓飏,还有著名的青年士人领袖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出身于为曹魏帝国的创建而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的夏侯氏家族。他的族祖父夏侯淳、从祖父夏侯渊,都是著名的军事将领;父亲夏侯尚,与曹丕私交甚密,位至征南将军。夏侯氏家族不仅是军事世家,同时也有良好的文化传统。黄初六年(公元226年), 夏侯尚去世,年仅17岁的夏侯玄继承父亲的爵位,太和初年便“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5〕自曹丕时开始,散骑黄门侍郎多由杰出的青年才子充任,作为高层次政治人材的锻炼、储备机构。“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6〕曹丕曾专门下诏解释散骑侍郎的政治意义“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7〕但是有时皇亲国戚中平庸之辈依靠裙带关系也会进入散骑显职,这往往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曹丕时,有位叫孟康的官员靠郭皇后的关系居该职,被时人所讥笑,“号为阿九。”〔8〕夏侯玄太和初任散骑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魏明帝所宠爱的毛皇后出身于低贱的“典虞车工”家庭,其弟毛曾愚笨而粗俗,却借皇后势力跻入散骑侍郎行列,与夏侯玄“朗朗如日月入怀”〔9〕的高贵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 时人谓‘蒹葭倚玉树。’”〔10〕蒹葭,即芦苇。时人况且如此,夏侯玄本人当然更不满,这位以气量弘大著称的人物也失去了自制力,愤愤之色溢于言表。“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11〕
何晏、夏侯玄、邓飏等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物结合在一起,成为洛阳上层青年士人交游清谈活动的活跃人物。当时,尽管直接遭受政府当权派贬抑的青年官员并非多数,但像何晏、夏侯玄之类自我感觉怀才不遇的政治心态在青年士人中却不是孤立现象。这时一大批出身豪门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士人正步入仕途,在洛阳中央政府任职,他们的才华、个人期望与实际可能有一定差距。同时在这些青年人中萌生的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又使他们看不起父辈名法治国的政绩,而那些建安功臣们正年富力强地位于政府各种要职。魏明帝曹叡此时虽然也是20余岁的青年,但他是个守成之君,通过依靠父辈的建安老臣来维持已形成的政治格局。在这种形势下,京师洛阳的上层青年知识分子中萌发了一种新风气。这些青年士人是一些人格独立性较强的新派人物,他们并不像传统官僚机器中的“零件”那样在各自的部位老老实实地听天由命,而是自发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游、建立政治关系网络;品评人物,形成自己的人材舆论;探讨社会政治和宇宙人生哲理,以渲泻过盛的思想能量。这种活动对青年士人的巨大吸引力,一方面来自新思想的感召,但更重要的却是其人物品评内容。作为荐举制选官制度的人材依据,汉魏之际人物品评活动十分活跃,来自“民间”的人材清议舆论所形成的声价,直接影响着未来的仕途通塞。而引起清议注意的最佳方法,是加入人物品评中心,结交人材鉴识权威。如果在人物批评活动中获得“知人”美名,意义更为重大,因为,有了“知人”能力,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活动的资格。从史书记载看,汉魏之际的重要政治家大都被认为有这种政治资本。比如曹操、荀彧、荀攸、诸葛亮等人都以“知人”闻名。所以一旦被舆论界定为“知人”,则声价倍增,而参与人物品评活动则是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途径。例如夏侯玄、何晏的朋友李丰早在黄初时期,“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12〕以至声名远扬至孙吴。另外,何晏等人也非守株待兔,而是四处伸出触角,十分积极地与一切有才能的青年名士交朋友,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游离于这个团体之外,据说只有傅嘏例外:
(何晏、夏侯玄、邓飏)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
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虚
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
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
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
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
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
昵之乎?”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傅嘏传》注引《傅子》。《傅子》的作者傅玄,是傅嘏的从弟,二人在正始时期都是何晏的政敌,高平陵政变后又都是司马氏的死党,所以历代史家都怀疑《傅子》的上段文字的真实性,认为是傅玄用了曲笔故意贬低何晏、夏侯玄,以烘托傅嘏的知人之明。如裴松之在《三国志·傅嘏传》中注引了《傅子》的这段文字后即指出其不可信,认为傅嘏不可能知道“夏侯之必危……《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13〕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其力作《世说新语·笺疏·识鉴第七》中,旁证博引写了二千余字的考辨文章,以何劭《荀粲传》为据,指出:“观其载荀粲评论夏侯玄与傅嘏之言,一则曰子等,再则曰子等,是必三人觌面之所谈也。夫促膝抵掌,相与论心,其交情之密可知。嘏之答粲,第谓识为功名之本,而不言己与玄志局不同。是于粲之所评,固已默许之矣。其意气之相合,又可知也。而谓玄欲求交,而嘏不许,此矫诬之言,但欲以欺天下后世,而无如同时之何劭已载笔而从其后。何也?盖玄与司马氏之死党,而玄则司马师之仇敌也。二人之交,遂始合而终睽。抑或玄败之后,嘏始讳之,饰为此言以自解免。傅玄著书,为其从兄门户计,又从而傅会之耳。”〔14〕
先贤的考辨,实属不刊之论,但是退一步讲,即使《傅子》所言是事实,也可证明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士人十分愿意与何晏、夏侯玄交往。正因为傅嘏的行为不合常情,所以才引起荀粲的诧异“犹怪之”。
二
何晏、夏侯玄等人的交游清谈,直接影响了政府的选官活动,引起了习惯于“一元化”社会控制的统治者惶恐不安。汉末党锢之祸还记忆犹新,殷鉴不远。于是作为当权派的魏初名士集团本能地作出了反应,建安老臣董昭首先出场,上书魏明帝,要求予以严厉制裁:
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
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
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
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
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
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
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
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
,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
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
,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魏明帝对董昭的建议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下诏要求严办“浮华”案。“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15〕关于这次案件发生的时间,史料记载有所差异。据董昭本传记载,其上疏一事发生在太和六年之后,魏明帝下诏也应在此年之后。但是《资治通鉴》却将此事系于太和四年下面,这是不对的。不错,魏明帝是于太和四年发表过一道反“浮华”的诏书,其内容如下:
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
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
高弟(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细观诏书内容,则不难发现其主旨是要求知识分子以儒学为本,加强对六经的学习,对浮华现象发出警告。这与充满了逮捕、禁锢等严厉制裁措施的“浮华案“显然不是一回事。再者,时间上也与其它史料所载不同。《魏略》说,李胜因此案被“禁锢数岁,帝崩,曹爽辅政,胜为洛阳令。”〔16〕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距魏明帝逝世的景初三年(公元239年),相距整十年,《魏略》不可能将十年记载为“数岁”。 那么,它发生在哪一年呢?《三国志·魏书·卷十四·董昭传》将上疏一事置于太和六年董昭任司徒一职后:“六年,拜真。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董昭任司徒的时间为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七月, 青龙四年(公元236年)五月死于该职位上。不能否认, 浮华案也有发生在青龙年间的可能性。例如景福殿于太和六年九月落成,何晏受魏明帝之命写了《景福殿赋》,可见浮华案只能在其作赋之后发生。又如史书明确记载毕轨因浮华案与何晏、邓飏等人一起罢了官“皆抑黜之”。〔17〕至少青龙元年,他仍任并州刺史,与鲜卑轲比能作战。〔18〕然而毕轨系皇亲,与明帝交情较深,不排除被特殊对待的可能性,所以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妨仍将案发生时间暂定为太和六年,并作如下合理推测:“浮华交会”之风由来已久,魏明帝太和四年曾下诏,力图以崇尚儒术来遏制这股风潮,没有收效,因而于太和六年,在董昭的建议下断然采取了镇压措施。史料中有关这一事件内容方面的记载比较简略,最详细的一条资料如下: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
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
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
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注引《世语》《资治通鉴》引上段文字时,“玄、畴”为“玄等”,指夏侯玄等人;“诞、备”为“诞辈”指诸葛诞等辈,文义较通。此句大意是说,他们在互相品题时,将夏侯玄等四人称为“四聪”,将诸葛诞等八人称为“八达”。聪,指聪明;达,指通达;豫,指参与,分属三个人材层次。四聪最高,八达次之,三豫仅具参与资格。这种品评方法是汉末以来经常使用的,容易产生较强的人材舆论。“三豫”属于随从,因父辈权势而参与,可以不预考虑,那么,这个号称“四聪、八达”集团究竟由哪些人组成呢?除上文列举的夏侯玄、诸葛诞之外,《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也提供了一个名单:“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综合一下,可整理出如下核心人物: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七人。熟悉曹魏历史者一眼即可看出,这些人物亦是正始时期曹爽政治改制集团的主要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也是司马懿高平陵政变时作为曹爽死党而屠杀的目标。显而易见,这个组织在太和时期就已经形成,它构成了后来正始名士的政治核心。
除上述“四聪八达”的核心人物外,其他有据可查的在太和时期即参与其活动的青年名士还有荀粲、裴徽、李丰、刘陶等人。傅嘏、司马师此时大概也介入了这类活动,政治利益使他们产生分歧,是后来的变化。在此,我们将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浮华案发的历史瞬间定格,考查这时上述人物的年龄、职务及家族历史和父兄官职,请看下表:
姓名 字 生卒年太和时职务 东汉家世 父兄名及在曹魏官职
何晏 平叔
?—249驸马骑都尉 祖父大将军何进养父曹操
夏侯玄
太初
209—254 羽林监父夏侯尚、征南将军
诸葛诞
公休 ?
尚书诸葛丰后代
邓飏
玄茂
?—249中书郎
丁谧 彦靖
?—249度支郎中毕轨
父丁斐、典军校尉
毕轨 昭先
?—249黄门郎 李胜
父毕子礼、典农校尉
李胜 公昭
?—249
父李休、太守
刘熙 汉王室后代 父刘放、中书监
孙密 父孙资、中书令
卫烈
祖父卫兹
汉末名士
裴徽文季 世为著姓
父裴茂、封列候
兄裴潜、尚书令
荀粲奉倩
曾祖父荀淑父荀彧,尚书令
李丰 安国?—254 给事中 父李义、卫尉
刘陶 季治?—255汉王室后代父刘晔、大鸿胪
傅嘏 兰石209—255司空掾祖父傅睿 父傅充、黄门侍郎
东汉太守
司马师
子元208—255 世为二千石 父司马懿、大将军
据上表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如下情况:
其一,他们的年龄约30岁左右。一般在20——30岁之间。夏侯玄和傅嘏时年23岁,司马师24岁。其他人物的年龄已难详考,但从各种迹象看,相互间差距不会太大。
其二,浮华案时,这些人物均在洛阳,有些人于中央机关任职。其中无明确任职记载者,并非闲散人员,按一般惯例,亦应在职,只是史书未做记载。
其三,汉末家世多样化。有些人物为东汉以来的名门,如世为著姓的裴徽、诸葛诞、傅嘏、司马师、邓飏、荀粲、刘熙、刘陶等。家世史籍无载者,大概属父辈在汉末动乱中随曹操征战而白手起家的暴发户。如夏侯玄、丁谧、孙密、李丰、李胜等人。不过其共同点都是十分明显的,即这些人的父兄辈都是曹魏帝国的新贵。这种由汉末士人与土豪融合而成的曹魏新贵,才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的真正开先河者,其子弟彼此之间在社会身份和文化上已相互认同,共同的阅历和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使他们于太和时期走到了一起,融为一体。
面对贵族青年士人的结社现象和保守派大臣的抗议,魏明帝本来决心严办一次“浮华案”,下令逮捕了李胜等人。“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聪)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19〕很明显,由于该案涉及人太多,而且这些人的父辈都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魏明帝感到很棘手,只得释放了李胜,再将案中的李胜、何晏、邓飏等人免官禁锢,匆匆收场。
在浮华案结束后的明帝青龙、景初时期,尽管史籍上已不见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活动,但其影响似乎并未消除,魏明帝对此可谓念念不忘。直至青龙四年卢毓出任吏部尚书时,曹叡仍下诏提醒要抵制“浮华”分子造成人才舆论。“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其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20〕卢毓向曹叡建议,应建立考试制度来检验人才,这是对付浮华舆论的最好办法。曹叡接受了卢毓的建议,下令刘邵起草《考课法》以遏制“浮华交会”的潜在威胁。但是,《考课法》于一年后出台不久,就随魏明帝的个人生命的结束而一同夭折了。直至魏明帝离开人世,他一直没有松懈对“浮华”风死灰复燃的警惕。然而这是徒劳的。在魏明帝死后不久的正始年间,当年的浮华分子卷土重来并控制了政府,以著名的正始名士再现于历史舞台。
三
太和浮华之风实质上是魏晋玄学思潮的萌动,尽管这时它还很不成熟,但是那些士族社会的思想先驱们已经通过他们的活动向社会昭示了新思潮的即将到来。他们的人格行为、清谈名理和文章诗赋无一不闪烁着玄理的光耀。
正始名士在当时和后世最受崇拜的人物是夏侯玄。早在太和时期,他的名声就不同凡响。荀粲说:“夏侯太初一时之杰。”〔21〕正始时期,更是“盛有名势。”〔22〕在正始六年司空赵俨的送葬会上,“宾客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23〕即使在高平陵政变之后的嘉平六年,夏侯玄东窗事发被捕入狱必死无疑时,负责审讯夏侯玄的钟毓、钟会兄弟还向他表示敬意。当时,夏侯玄拒不“认罪”,而其罪名早已“钦定”,廷尉钟毓不忍用刑索取口供,便亲自连夜替他写了一份供词,“流涕以示玄,玄视,颔之而已。”〔24〕钟毓的弟弟钟会企图利用这个机会与夏侯玄交朋友,被正色拒绝。夏侯玄死后,其声望更是与日俱增,成为晋朝士大夫心中的楷模。
夏侯玄获得如此盛誉,似乎很费解。论文采和理论贡献,他不如何晏、王弼;论事功政绩,他不如司马氏兄弟。除在武官选举方面知人善任外,并无它长,而且又是骆谷之役的败军之将。那么,他成功的奥秘在哪里呢?从各种史书赞誉的焦点看,是他人格的内在力量,如“玄格量弘济”〔25〕,“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26〕“风格高朗,弘辩博畅。”〔27〕那么,透过上述抽象的赞美词汇,其高贵人格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应当说,是一种不为外物所累的博大气量,达到了超越生死的境界。请看以下为玄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两个具体事例:
其一,“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28〕
其二,“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29〕
引起魏晋士族知识分子肃然起敬的并不仅仅是上述风度举止等外在表象,而是这些表象中所蕴含的那种无声的巨大精神力量。冲锋陷阵易,猝然临之而不惊难;慷慨悲歌就义易,而面临死亡脸不变色心不跳难。夏侯玄所表现的,正是这种不被外物所累置生死于度外的物我两忘之境。这种境界是魏晋玄学家所可望而不可及的,留在了他们的理论幻想中,如王弼的“应物而无累于物”〔30〕,郭象的“玄同彼我,以死生为寤寐”〔31〕,支道林的“物物而不物于物”〔32〕,其归一也。
从历史实际看,夏侯玄尽管威望很高,但似乎是名义上的领袖,而实际的智囊人物或思想家,却非何晏莫属,何晏是这个新派名士集团的灵魂。正因为他的这种潜在的巨大作用,所以正始名士的对立面,从魏明帝到司马氏以及尔后的礼法之士都将其作为主要攻击对象。汉魏之际最重要的时代课题是人才问题,何晏杰出的“材辩”说明了他的理论家地位。关于他于太和时“以材辩显于贵戚间”,即在贵族青年中从事人物品评活动的具体事例,史书仅存一条:
初,夏侯玄,何晏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
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何晏品评人物所用典故出自《易·系辞上》,原文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态;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显然,何晏对夏侯玄和司马师的评语都甚高,韩康伯对“深”和“几”的注释为“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33〕都接近通玄体道的境界,但仍不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神才达到了与“道”合一的境界。何晏大意是说:夏侯玄思想深刻,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司马师洞察隐微,明能见机,所以能完成天下的事功。而何晏自己则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从总体上看,何晏品评人物的显著特征是注意人的内在气质和精神,尤其是以人们的认识能力“识”体悟“道”的水平为人材高低的标准,而不甚注意外在形迹及具体事功。这种人材标准,在荀粲那里也有类似表现。荀粲“常谓(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 ’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34〕很明显,在荀粲看来,人间再伟大的功业也不过是无限宇宙中有限的一物而已,而人类的智慧“识”,既决定有形有限事功的成败,又可与无形无限的宇宙大道为一体,因此,“识”的意义最大。
上述人物品评活动以及新的人材品评标准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太和时期正在萌动的玄学新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融儒、道,调合名教与自然,注重形而上哲理探索的新思潮,此时正以人物品评为中心,以清谈论辩为学术交流形式,向政治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拓展。遗憾的是,能揭示这一时期玄学思潮萌芽状态的思想资料太少了。对现存何晏、夏侯玄等人的著作,很难分清哪些是太和早期,哪些是正始晚期的。目前,能反映太和时期玄学家的思想状况的资料,只有荀粲关于《易经》言意之辩的高论和何晏的《景福殿赋》。
荀粲是著名的颍川荀氏家族成员。他经常发表怪论,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对儒家六经的直接批判,引起诸位兄弟的震惊、不满和反击。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
《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上述辩论肯定发生于太和时期,因为荀粲太和初(227 年)与傅嘏清谈时已成年,他死时28岁,未活到正始时代,所以其激烈言论大概发表于太和六年浮华案发之前。荀粲的话大意为:六经是关于治国方面的书籍,圣人没有在其中讨论人性与天道之类玄远的哲理,因为宇宙根本的大道,是超言绝象,无法用言象表述的。尽管荀粲并没有否定六经在政治人事方面表达了圣人之意,但他毕竟将六经视为“圣人之糠秕”,表现了激进青年士人反传统态度和准备创建新哲学的冲动。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变动时期,总会出现一些貌似激烈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意义恰如鲁迅所言:在中国进行改革,主张必须激烈,欲开窗户则宣布拆屋顶,才能使保守派接受开窗户的建议。其实,这类激烈人物的骨子里却往往是旧传统的忠实奴隶。荀粲本人就是典型之一。比如,礼教宣扬妇女价值在于“四德”,而荀粲大唱反调,说:“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35〕并娶了曹洪的漂亮女儿。但荀粲实际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妻子生病高热,他冬天于室外冻透身体再上床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后,他“不哭而神伤”。前来吊丧的傅嘏开导他:“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36〕这位自称好色而实际感情专一的口头革新家,因“痛悼不能已,岁余亦亡,时年二十九”〔37〕,“是以获讥于世。”〔38〕连几百年后的南朝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讥笑荀粲因丧妻而悲痛身亡,无庄子丧妇鼓缶而歌的胸怀,以此证明玄学家言行不一。
与荀粲的激烈言论相比,何晏显得平和得多。也许与自幼寄人篱下有关,何晏公开阐述政治哲学观点时比较谨慎。他于太和六年作遵命文学《景福殿赋》,在歌颂象征曹叡盛大帝业的景福殿之宏伟壮丽的主旋律中,时时出现几个乐句的玄学不协合伴奏。
其一,何晏首先将魏明帝美化为玄学思想中集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君主。“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上则崇稽古之弘道,下则阐长世之善经。”〔39〕此句大意为:曹魏帝国传至明帝时,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了,原因在于明帝政策既顺应宇宙变化的自然规律,又符合人类的自然本性;既继承了古代圣王的治国大法,又为后世树立榜样。总之,明帝有为的礼教法术都是与自然之道相一致的。余敦康先生认为:“这就是后来玄学家所服膺的名教本于自然思想的最早表述。”〔40〕所言极是。
其二,在回忆景福殿的修建原因及过程后,文章进入了对宫殿建筑装饰的描述。在介绍各个建筑部分时,只要有可能,何晏都借题发挥,不时地插入政论。例如在介绍宫室壁画功能时说:“钦先王之允塞,悦重华之无为。命共工使作缋,明五彩之彰施。图象古昔,以当箴规。”重华即传说中无为而治的圣王虞舜,按五德终始说,舜与曹魏同为土德,故当时格外受曹氏尊重。共工指画工,缋通“绘”,指绘画。很明显,何晏于献媚中借机表述自己君主无为的玄学思想。
其三,在文章的结束处,何晏首先表达了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是:“家怀克让之风,人康哉之诗,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近似老子笔下“其政闷闷,其民淳淳”〔41〕的社会。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上德,也可以称为“朴”,也是下文的“太素”——天地人刚刚形成的淳朴状态。但是,要达到这种无为之境,必须进行政治改良,“招中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通之繁乱,反民情于太素。”这些观点,十几年后部分转化为正始改制的内容〔42〕。
太和时期玄学思潮的萌动是无可置疑的。虽然此时它还很幼稚,以致看不到系统的理论体系,然而,时代思潮的兴起犹如自然界的浪潮,它往往开始于一个微弱的浪花,但它将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变成惊天动地的思想巨澜。
注释:
〔1〕 《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2〕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3〕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4〕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
〔5〕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
〔6〕 《三国志·魏书·卷十六·杜恕传》注引《魏略》。
〔7〕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四·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8〕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9〕 《三国志·魏书·卷十六·杜恕传》注引《魏略》。
〔10〕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11〕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
〔12〕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13〕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傅嘏传》裴松之案。
〔14〕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识鉴第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6页。
〔15〕 《三国志·魏书·卷十四·董昭传》。
〔16〕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
〔17〕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
〔18〕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19〕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
〔20〕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二·卢毓传》。
〔21〕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傅嘏传》注引《傅子》。
〔22〕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文章叙录》。
〔23〕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
〔24〕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注引《世语》。
〔25〕〔29〕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
〔26〕 《晋书·卷九十二,袁宏传》引袁宏《三国名臣颂》。
〔27〕 《世说新语·方正第五》注引《魏氏春秋》。
〔28〕 《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30〕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31〕 郭象:《庄子注·德充符》。
〔32〕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注引支道林《逍遥游》。
〔33〕 《王弼集校释·附韩康伯系辞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1页。
〔34〕 《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注引《荀粲别传》。
〔35〕 《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注引《荀粲别传》。
〔36〕〔37〕 《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38〕 《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
〔38〕 《文选·何晏〈景福殿赋〉》。
〔39〕 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80页。
〔40〕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 页。
〔41〕 拙作《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