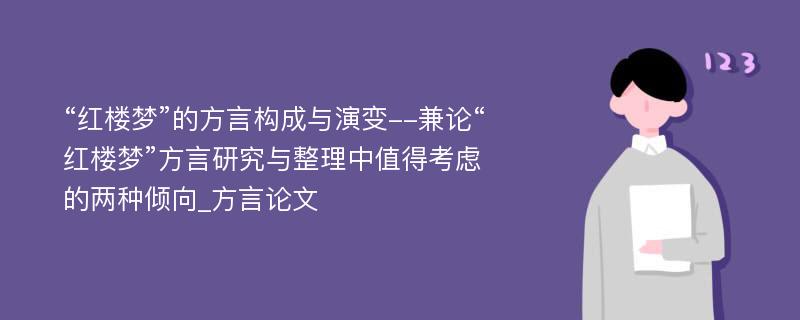
《红楼梦》的方言构成及其演变——兼谈《红楼梦》方言研究与校勘中两种值得思考的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方言论文,两种论文,倾向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09)02-0099-08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中最具“官话京腔”的典范之作。这部被誉为“万古不磨”的罕世奇书,不仅为中国近代汉语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语言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方面也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鲜活的方言例证。
从《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上看,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只是作者为完成这部小说的“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索时,又会发现《红楼梦》中的方言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地域色彩。这种特别的词汇、特定的语法结构、特殊的语言音调,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味外味”,构成了另一种具有独特性的语言艺术世界。
《红楼梦》语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方言,这个事实许多读者和专门的研究家早有深切的感受。清人周春在他的《〈红楼梦〉评例》中就曾说道:读《红楼梦》要“通官话京腔”。①近人齐如山也说:《红楼梦》中的方言土语有“特别的意味,特别的地方性。”[1]但他们的评说大都局限在小说中的“北京话”上,对“北京话”之外的其它方言则少有涉及。仔细阅读《红楼梦》,我发现这部小说中方言构成不仅有其复杂性,而且存在一个过去为不少研究者所忽略地演变过程。笔者有感于此,不揣鄙陋,愿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向诸位学界先进请益。
一、早期抄本《红楼梦》中方言构成的考察
要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如何构成,最直接也相对可靠地考察根据应该是早期抄本《红楼梦》。从上世纪20年代胡适意外购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略称“甲戌本”)开始,今天大家可以读到的抄本已达12种之多。这些珍贵的抄本年代虽然有先有后,保存的回数有多有少,但经过“专家”们的鉴定和广泛的讨论,大体上可以认定它们是曹雪芹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后的“稿本”过录本或是再过录本,基本上保留了原“稿本”的面貌。
当我们一本一本地读完这12种早期抄本《红楼梦》之后,对《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而全面的印象:
(一)18世纪中叶,即《红楼梦》诞生时期,北京话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基本上趋于成熟。这一时期北京话中的方言除了北京地区原有的方言之外,它还吸收了周边地区(例如冀东话、唐山话)和大批移民的语言。据《明实录》、《明史》等文献记载,自明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仅山西一省向北京移民就不下七次,每次约在万户左右,在北京“大兴县东部和顺义县西北部有大同兴营、屯留营、河津营、上下黎城营、潞城营、霍州营、忻州营、更县营、东西绛州营、稷山营、蒲州营、红铜(即洪洞)营”[2]。这些移民将本地区的语言带到了北京,融入北京话之中。因此,在《红楼梦》的语言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流行于冀鲁地区较为冷僻的方言“讨愧”(第30回),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出今日绛州人的常用口语“角口”(第9回)、“不卯”(第21回)、“生像儿”(第39回)。大多数北方人说“口角”,绛州人则说“角口”。其他如“强梆子”(第59回)等等,都是绛州人的口头语②。
(二)自公元1644年清王朝定鼎北京之后,顺康时期的北京话呈现出一个“满语式汉语”的阶段。这种满语式语言现象至雍正朝中期和乾隆朝,逐渐消失,只存痕迹。到嘉庆道光朝连“痕迹”亦难以找到了。道光朝以后,北京话已进入了现代北京话的时代。从《红楼梦》早期抄本看,前80回中保留满语式汉语还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例如:“……罢了”(第3回)、“看承”(第6回)、“行当儿”(第6回)、“白……呢罢”(第6回)、“巴不得”(第14回)、“苏州去的昭儿”(第14回)、“忽刺巴儿”(第16回)、“……罢呦”(第32回)、“把莺儿不理”(第35回)、“肯劝”(第74回),等等。除了北京话中的“满语式”语言外,《红楼梦》中还直接保留了“满语”,诸如“小厮”(第2回)、“嬷嬷”(第3回又写作嫫嫫)、“混唚”(第7回)、“丧谤”(第35回)、“作死”(第52回)、“捞梢”(第37回)、“捞嘴”(第76回)、“妞妞”(第92回)、“克什”(第118回),等等[3]。
(三)《红楼梦》中有相当多的方言是来自辽东三省,特别是沈阳话(又称盛京话)对清代北京话影响很大。“清初满人入关,将内城划为旗人居住,汉人只许住在外城。因此,八旗汉族成员的沈阳话首先进入北京内城,而外城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明代北京话。入关日久,沈阳话渐渐与明代北京话融和。入关的满人开始学的是沈阳话,这就对沈阳话进一步(再一次)发生了满语的影响。”《红楼梦》中有许多方言来自沈阳话,例如“响快”(见第6回)、“一顿把”(见第28回)、“走水”(见第39回)、“下作黄子”(见第40回)、“上脸”(见第40回)、“老货”(见第53回)、“亲香”(见第54回),等等③如果我们将齐如山编的《北京土话》、陈刚编的《北京方言词典》、傅民等编《北京话词语》与徐皓光、张大鸣编的《简明东北方言词典》[4-6]对照研究,就会清楚地发现北京方言与东北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红楼梦》语言中是否有南方“方言”,有多少南方“方言”和哪几种南方“方言”,一直是读者和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三个值得思考并希望做出解答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中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红楼梦》一书中不只使用了大量的北京方言,而且还用了数量可观的吴语词汇”[7]。在文章中他还列举了上百条例子,明白指出是吴语词汇,用以支持他的论点。稍后有几位学者发表文章,就《红楼梦》中的南方“方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8-11]。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京于平在她的《论<红楼梦>语言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论曹雪芹的江南情结》[12-13]二文中对南方话作了梳理和分析。
综合以上诸家提供的信息,对照早期抄本《红楼梦》的语言描写实际,我们可以认定在《红楼梦》的语言世界中存在有南方多个地区的语言词汇,其中包括曹家曾经生活过的苏州、南京、扬州及相近的镇江等地方语言。例如《红楼梦》中写到的吴语有“高乐”(第2回)、“劳什子”(第3回,“什”吴语读“杂”)、“嗄”(第22回)、“事物”(第27回)、“气退一退”(第27回)、“扚”“热闹”(第59回)、“人客”(第64回)、“事体”(第67回)、“豁啷”(第74回),等等。又如南京话有“才亦”(第6回)、“唧唧”(第6回)、“瘦巧”(第7回)、“轻狂”(第8回)、“矼”(第16回)、“促狭”(第21回)、“姑娘”(第39回)、“强”(第40回)、“浇头”(第61回)、“宾住”(第70回)等[12-13]④。与以上两地相比,扬州话词汇显示比南京话要多,宣建人《红楼梦杂记》一文中选列了103条[14]。王世华在《<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一文中将扬州话与南京话合称“下江官话”,所列也有百余条之多。但他们所列的词汇中有不少词汇在“北京方言”和“绛州方言”乃至“东北方言”工具书中所列的方言词汇重复不少,诸如“褡裢”(第1回)、“打谅”(第3回,又作打量)“大阵仗”(第7回)、“狼犺”(第8回)“靸鞋”(第20回)、“促狭”(第21回)、“嚼舌根”(第38回)、“仗腰”(第45回)、“小月”(第55回)、“捞梢”(第73回)、“撒村”(第75回)、“歇晌”(第81回)、“嗷嘈”(第90回)、“洑上水”(第100回),等等。尽管有个别词汇写法有区别(如“嗷嘈”又写作“懊糟”,但词意相同),所以我认为这些词汇似乎是许多地区“共有”的语言。对这些“共有”语言究竟属于那一地区,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斟酌。但无论如何,通过以上几方面材料汇聚之后,我们对《红楼梦》方言构成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了解证明了早期抄本《红楼梦》的一条脂批的说法:“按此书中若干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前照饮食诸类,皆东西南北兼用……亦南北相兼而用无疑矣。”(《己卯本》第39回)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即王世华《红楼梦语言的色彩》[8-11]一文中提出《红楼梦》中的某些诗词和个别词汇的音韵问题。例如,第5回“……今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好大雪之‘雪’……”王文认为“雪、薛,中古音均为心纽薛韵,但开合不同;北京人‘入派三声’后,二字同声韵而不同调。南京话二字完全同音,以此构成谐音双关。”同回秦可卿判词中的“情”与“秦”二字谐音相关,王文认为“‘情’‘秦’在古音和今北京音中均不同韵,下江官话中[in]、[iη]不分,此二字扬州、南京话中韵母读为[iη],完全同音,由于同样原因,‘宁’与‘淫’叶韵。”又如,第41回写“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王文认为:“‘牛’和刘姥姥之‘刘’谐音双关。‘牛、刘’古音与今北京音韵不同声,古音分别为疑母、来母;今北京音分别为[n]、[l]。扬州话中,[n]、[l]相混,‘牛、刘’是同音字。”同类例子还见于林黛玉写的《秋窗风雨夕》、《桃花行》,都是从音韵角度做出解读。故王文认为:“作者写林黛玉出此语,固可见林黛玉的敏捷、尖刻,同时也正表明这位原籍姑苏但长于扬州的小姐虽已进京,但仍未改乡音。”我认为作者注意到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王文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大家在《红楼梦》方言构成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词汇”的梳理,而且还要注意方言的音韵和语法构成的研究。倘能如此,文章得出的某种结论就可能会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二、早期抄本《红楼梦》中方言演变的轨迹
在早期抄本《红楼梦》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小说作者在锤炼方言方面纯熟的艺术技巧——“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而且还发现作者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对小说中的方言词语也作了“增删”。特别是从作者的“增删”中,令人感觉到某种“规律”性,似乎表明作者在“披阅”和“增删”中有了某些新的思考。
(一)尽管《红楼梦》作者将宁荣二府安排在“京都”,但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却大都来自江南,使读者有一种“秦淮旧梦忆繁华”之感。小说第33回写宝玉挨打时,贾母风风火火赶到,对贾政的“笞挞”甚为愤怒,其中说到:“……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到南京去!”第97回写宝玉与薛宝钗成婚大事,凤姐与王夫人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咱们南边规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第106回借贾母之口说道:“只是咱们的规矩还是南京的礼儿”从这三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知道贾家原在“南京”。尽管现如今人在“京都”,但他们家的“规矩”还是“南京的礼儿”。由此,似乎可以想象《红楼梦》的“原稿”中所用的南方词汇量较多一些,这应该是情理中事。但是,随着作者由江南回到北京日久,对北京话更熟悉,所以在“披阅”、“增删”时开始减少南方词汇,以此淡化作者家世背景的印象。这里聊举数例,以供大家参考⑤。
例一,甲戌本第6回写刘姥姥去荣国府告贷之前,其女儿刘氏说道:“只你这样嘴脸也怎么好到他们门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门上人也未必肯去通报。”己卯、庚辰、舒序、梦稿、卞藏等本相同,而戚序、甲辰本则删去南方话“先不先”三个字,或改为“只怕他那”。同回又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事,待从凤姐处出来后,周瑞家的责怪刘姥姥一口一个“侄儿”。她说:“便是亲侄儿,也要说和柔些。”“和柔”是江南话,确切地说是南京话,己卯、庚辰、舒序、梦稿、卞藏诸本均改为北方话“和软”。
例二,甲戌本第7回出现“台矶”“台矶石”,但在己卯、庚辰、舒序、梦稿、卞藏本中作“台阶”,或作“台坡”(可能为“堦”字之误)。“台矶”与“台矶石”亦为南京话,“台阶”则为北方话。
例三,甲戌本第7回写贾蓉应王熙凤的要求,将秦钟带进屋子,是一个小后生,凤姐眼中“较宝玉瘦巧些”,列藏、戚序、舒序、卞藏本同甲戌本。“瘦巧”是南京话,而己卯、庚辰、甲辰等本作“瘦些”,变成了北方话。
例四,甲戌本第7回写焦大醉骂,其中一句是“你们这把子的杂种忘八羔子们”。舒序、戚序、列藏、甲辰本同甲戌本,而己卯、庚辰、卞藏本则改为“这一把”“这一把子”。所谓“这把子”是苏北方言,意为“这一帮”。
例五,甲戌本第8回,写黛玉到薛姨妈房内,丫鬟送个手炉来,黛玉借题发挥讽刺宝玉,说“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手炉来……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轻狂”二字为南京话,己卯、庚辰、舒序、卞藏本均改为北方话“狂惯了”。
例六,甲戌、己卯、庚辰、舒序、列藏诸本第16回写王熙凤与平儿对话中有:“原来你这蹄子肏鬼”一句,其中“肏鬼”本为南方话,戚序本改为“调鬼”,甲辰、梦稿本改为“闹鬼”。同回,赵嬷嬷来到贾琏凤姐屋子,甲戌、己卯、庚辰、舒序、梦稿、列藏、戚序诸本中写凤姐道:“嬷嬷狠咬不动那个,到没的矼了他的牙。”“矼”字为南方话,甲辰本改为“没的到吃了他的牙”,程甲、程乙本改为“咯了他的牙”。“咯了”是典型的北方话。
例七,甲戌、庚辰、舒序、戚序本第26回开头即说“宝玉养了三十三天后,不但身体强壮亦且连脸上疮痕平服,仍回大观园去。”句中“平服”原是吴语,意为痊愈复原。列藏、甲辰、程甲本改为“平复”。
例八,蒙府、戚序、列藏、甲辰等本第69回写秋桐哭骂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嚼舌根”(亦见于71回)一句中的“嚼舌根”原吴语,庚辰本改为北方话“咬舌根”。同回写贾琏“只得开了尤氏箱柜,去拿自己的梯已。及开了箱柜,一滴无存。”而在戚序、甲辰、程甲本则改吴语“一滴”为北方话“一点”。
这八个例子,只是现存12种早期抄本《红楼梦》“去”南方话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此类例子还可以列出一些。我们细心观察这八个例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印象:一是“去”南方话并非从程伟元、高鹗二人整理120回本《红楼梦》开始,因为没有人能说明上述所列抄本中的改文都是出于程高之手,也无证据说明所有12种抄本都是程高指使什么人抄录的;二是不能排除个别词汇是因误抄而造成的,但大多数改文分布在各个抄本上,而各抄本所据底本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些改文只能是原底本中的文字,而不大可能都是“误抄”。
(二)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生于苏州长于扬州,后来她虽然进了贾府,但她“终不脱南边人的话”(见87回探春语)。细读小说中有关林黛玉的描写,我们发现林黛玉的生活习惯及所作诗词的音韵,总不脱乡音乡情的影响。《葬花诗》充分运用吴语微而婉,尚亮尚节奏的特点,以花喻人,以花喻美,以花象征生命。其中一句“而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写出林黛玉对乡音乡情的真性情。我们从早期抄本《红楼梦》中很难找到关于林黛玉的语言乃至对她的描写文字有改南为北的痕迹,似乎说明作者或“增删”者都有意保持林黛玉“南方”闺秀的形象。
总之,从前面所举的八例来看,甲戌、己卯、舒序本“去”南方话较少,庚辰本开始“去”南方话逐渐增多,梦稿本、甲辰本已接近程甲本。程乙本虽然保留了个别的南方话(如扬州话“没得”等),但从第61回将南方的“浇头”改为北京的“飘马儿”⑥例证看,整理者在“去”南方话上也下了一番工夫。清人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说:“书中多用俗谚巧语,皆地道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15]的断语,显然不符合《红楼梦》语言(特别是方言)构成的事实。
三、《红楼梦》方言研究与校勘中两种值得思考的倾向。
《红楼梦》方言构成及其演变的研究,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和新的思考。我毫不怀疑,这个研究对整个小说研究的深入会起到一种新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这一课题研究中所发生的一些令人忧虑和反思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近三十年来《红楼梦》语言研究成果上看,《红楼梦》中的方言研究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提高研究的水平。这不仅仅因为目前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数量远远不及其它课题,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如其它课题系统和全面。特别是近几年来所见到的《红楼梦》方言“研究”中表现出一种与社会上刮起的抢名人拉古人的风气搅和在一起的倾向——即把曹雪芹和《红楼梦》同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是炫耀历史文化悠久联系在一起。例如某位作者从《红楼梦》语言中“发掘”出一些“绛州口语”,竟然得出结论说“《红楼梦》生活语言是用绛州口语写成的”,小说中的“绛云轩”就是“绛人喧”。他在书中列举了“肏攮”一词,说“肏攮”就是吃东西。“肏,全国普遍读作‘操’,唯绛州读作——‘日’。这也是绛州的一个常用口语。”除了这个“肏攮”特例外,作者还举出“乏了”“妥了”“款段”“靸着鞋”“敁敠”“撺掇”“淡话”“籰子”“破费”“不卯”“牙碜”“搜寻”“铺排”“吆喝”,等等。最后,作者根据一位约生于“同治末年”的老人口传说曹雪芹曾在家败回京后去了绛州生活过七八年,“使他领略了这块古老土地上淳朴的风土人情,尤其是继承了当地群众多方面的词汇和口语,并运用到《红楼梦》的生活语言里,从而使众多人物,各自具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使叙述语言也更加有艺术表现力。”⑦其实,作者所说“肏攮”是绛州独有的方言并不准确。以我有限的知识来看,“肏攮”一词山东方言、吴语方言中也有。如“肏”读“日”,山东话就读作“日”,吴语中也有“日娘贼”一类的词汇。至于其它各例,北京方言(如北京早从明代就有绛州营,绛州话早已融入北京方言之中)、山东方言、河北方言、东北方言也都有,并非是清代时绛州人独有的语言。
另一个例子是前几年一位学人发表的《〈红楼梦〉中的湖南方言考辨》一文[16-17],作者在列举了“大量”湘方言之后指出《红楼梦》“作者并不是曹雪芹,而是一位有在湖南长期生活经历的人士”写的,曹雪芹只是“在原始之作者的基础上,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艺术加工”而已。很明显,湘方言的“发现”只是用来“剥夺”曹雪芹著作权的工具。于是出现了另一位学人发表了《〈红楼梦〉与江淮语言——兼评“湘方言”说》[18],作者从《西游记》、《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金瓶梅》、《绿野仙踪》、《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诸书中找出大量词语进行比较,说明某些所谓“湘方言”早在这些小说中已出现过了。作者最后总结道: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在民族交融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方言词汇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着,有的为其他方言区的人所接受,有的演变为共同语,还有一部分则在方言区的口语中沉淀下来,因此,方言与方言、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最大的差异主要还是表现在语音上。就方言语汇而言,一旦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时,地域特征往往不能阻碍不同方言的读者对其加以研读理解,因此判断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词汇,应基于这样的原则:
一、少为乃至不为共同语所使用;
二、本方言区使用频率较高,但不具排他性。
我很同意上述的见解。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首先要把这部小说的诞生放在18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并在空间上把当时北京的语言文化发展大背景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野之
内;其次是要把《红楼梦》作者家世环境和个人经历考虑在其中;再次,在考虑到方言形成的地域性同时,必须注意到方言也有“流动”性的事实,这其中包括移民在方言的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2]15-53。某些《红楼梦》方言研究著述之所以难以让人信服,在众多的原因之中,除了忽略语言的流动性,更主要在于作者过多地注意“方言”词汇的选择和说明,而缺乏对“方言”的形成历史及其音韵、语法结构的综合研究。
(二)在《红楼梦》走进大众、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红楼梦》的校订与注释是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但由于这部小说是“未完成”稿,流传至今的早期抄本多达12种,故各抄本之间、抄本与刻印本之间存在相当的文字差异,所以给今日的校订注释乃至翻译都带来一定的困难。近50年来,随着早期抄本的陆续发现,版本研究、成书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为文本的校订注释和翻译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从近年来新出版的多种校订注释本的质量上看,校订注释两个方面都吸收了当代的研究成果,学术品位明显地有了提升,这一点应该予以肯定。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影响下,在“红楼夺目红”的躁动中,《红楼梦》的校订注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其一,由于某些校订者对抄本《红楼梦》中方言构成、演变不甚熟悉,盲目改动原底本中的方言土语。
例一,庚辰本第6回刘姥姥说:“他们家的二小姐(指王熙凤)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有人提出汉语中从来没有“响快”这个词汇,作家也无需要作此创造,认为“响快”是“爽快”之误。但事实上“响快”一词是东北、华北两地的方言,已收入方言词书之中。
例二,庚辰本第28回、第36回都出现了“一顿把”这个方言,有的校订者不知“一顿把”是华北、东北流行的方言,硬是将“把”字改为“扒”,失去这句方言的原意。
例三,庚辰本第28回,“宝玉听见湘云也有这件东西(指金麒麟)……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飘人”这里的“飘”字读piāo;有的校订本改为“瞟”,读piǎo,斜着眼睛看之意。这个“飘”字十分传神且有几分亲切感,至今东北、华北一带还用这个“飘”字。
例四,庚辰本第30回有“话说林黛玉与宝玉角口后,也自后悔。”这句话中的“角口”二字确实较为冷僻。但作者用此方言并没有错,因为在今山西绛州方言中仍然存在。同回有“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一句,有人认为“讨愧”是“惭愧”之误。其实原文不误,所谓“讨愧”即是惭愧,今日冀鲁方言词汇中仍保留。如说有什么证据的话,《醒世姻缘传》第79回就有“讨愧”二字。
例五,庚辰本第54回贾母接受王夫人的建议,率众人搬到“暖阁”去,说“大家坐在一处挤着,又亲香,又暖和。”这里的“亲香”与亲热相近,但有程度的差别。今在东北、华北地区仍然用此二字,故不应该改为“亲热”,底本用“亲香”二字没错。
例六,庚辰本第74回凤姐说“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句,这是满语式的一句话,所谓“肯……”意为常常、老是,惯于。在幽燕语中也常有。有人认为“肯”字应是“恳”字之误,用“肯”字不通,显然是不太了解“肯”的另一种用法。
类似的擅改方言之例数量较多,不一一细列。
其二,《红楼梦》抄本中所用的一些词汇早已为戏曲小说所用,已成“熟语”。但有些校订者凭着感觉走,只要自己感觉“不顺”或是见其他抄本中有另一种写法,即断定底本为错误,其实是一种轻率的判断。
例一,庚辰本第17回有“贾政听了,沉思一回”句,《红楼梦》中用“一回”二字很多。有人认为“一回”是“一会”之音近而误。事实上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已用过“一回”或“一回儿”,这只要读一读《金瓶梅》第13回、第58回就可以明白了。
例二,庚辰本第19回有袭人说“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几年”句,这里的“伏侍”二字屡见于《红楼梦》抄本之中。校订本是否要一律改为现代通用的“服侍”还可以再研究,但说“伏侍”用“错”了则恐怕用词太重了。“伏侍”二字并不冷僻罕见,《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中就用“伏侍”二字:“小人愿伏侍小娘子前去。”
例三,庚辰本第24回写贾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虽然是泼皮无赖,却因人而使,颇颇有义侠之名。”这里“颇颇”二字是重叠形容词,如同《红楼梦》常见的“巴巴的”“特特的”“直直的”等。元代石德玉《曲江池》:“从幼儿教他读书,颇颇有些学问。”又,《醒世恒言》:“生意顺留,颇颇得过。”有人认为“颇颇”二字不通,应删去一个“颇”,说“颇有义侠之名”才对。我则以为作者用“颇颇”二字不错,大可不必删去一个“颇”字。
例四,庚辰本第26回中有“因老爷叫,也顾不得别的,疾忙回来穿衣服。”句,其中“疾忙”二字意为快快、急急之解,见于《五代史平话·梁史》卷上,亦见于《西游记》22回,戏曲《宦门子弟错立身》第4出。校者认为“疾忙”是庚辰本抄错,应作“急忙”。敝意以为,“疾忙”既是不错,似不必改。
例五,庚辰本第62回有“倏然不见了湘云,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响,使人各处去找,那里找得着。”此句中“影响”二字,有人认为所指什么令人费解。依我所见《夷坚丙志》(卷12)、《刘志远诸宫调》(二),《警世通言》(卷五)诸书内均有“影响”二字,意谓消息、音讯。倘能稍加探讨,就不会有“费解”之疑。
例六,庚辰本第69回有贾琏“只得开了尤氏箱柜,去拿自己的梯己。及开了箱,一滴无存。”句中“一滴”,又作“一的的”,本属吴语,意为“一点点”。因“梯己”不属“液体”,就要改“一滴”为“一点”实是不解吴语之故。谓予不信,请阅《吴歌甲集》,其文有云:“十指尖尖一双描花手,三寸金莲一滴滴”⑧。
其三,所谓“校订”(又称“校勘”“校讎”),目的是“考校订正”,“指谬纠讹”要求校订者审慎精心,当尽力避免自随己意武断乱判。例如早期抄本《红楼梦》中有“素昔”“素习”“各自”“各人”“自为”“自谓”等词汇同时出现在各回的现象,均有所据,均有所解,没有谁对谁错之分。又如,抄本中有“矌矌”“逛逛”“嬷嬷”“姆姆”等词语,是否要“统一”,我认为应视各种校本的读者对象而定,似不必强求一致。至于抄本中一些对话和人物情态描写本是鲜活生动,大可不必借“普及大众”为由,以今日语法进行修饰性的“改造”,否则极容易造成看似语法“通顺”,却使得文气不畅,死板少趣,毫无生气。要知道,生活中的对话与写作文有一定差异,某些添改的结果,失去了原文中特有的生活气息[19]。《红楼梦》抄本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之别,后期的抄本明显有“通俗”化、“去”南话的弊端。如果再一代又一代地“改造”《红楼梦》,那么《红楼梦》的“原貌”会离18世纪中叶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愈来愈远。我想如此“校订”《红楼梦》,并非是广大读者所真正需求的“普及”!
曹雪芹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巨匠。他熟悉社会生活中各个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密码”,经过精心地选择、锤炼、升华之后,作为自己思想感情的载体,书写他对人生的体悟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红楼梦》方言构成与演变的考察,虽然只是这部小说语言艺术中的“一角”,但我们从中所获得的信息和启示则是十分宝贵的。作为《红楼梦》的热爱者、研究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拾回那些已经流失或正在流失的文化,还给曹雪芹、还给《红楼梦》。
近年来不少学人不断呼吁“回归文本”,这是一个明智的声音。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几乎被“泛娱乐化”的噪音所掩盖。但是,我坚信“戏说红楼”“揭秘红楼”“大话红楼”只能喧闹一时,绝不会成为永久。如果每一个红学人都能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红学就不会迷失方向,红学的学术品格就不会蒙受玷污!
《红楼梦》正在走向世界,时代期待着我们!
2008年5月8—18日
写于北京惠新北里饮水堂
注释:
①周春在《红楼梦评例》中指出:“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又说:“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此为读《红》研《红》之要诀。转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67页。
②赵存义:《〈红楼梦〉生活语言与绛州口语》,自印本,第10页,第12页,第16页,第30页。
③爱新觉罗·瀛生认为,“八旗中的汉族人员随满人入关,以北京为中心,活动和居住,将辽东语(沈阳语)带到北京。当时的北京话是明代北京话,它是在大都话的基础上受明初各地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又说“八旗中的汉族成员是清代北京话的主要创造者之一,所以了解他们的语言状况,对于了解现代北京是必要的。”见《北京土话中的满语》第126页。
④读者亦可与石汝杰、(日)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等专书对照。
⑤张爱玲:在《红楼梦魇》(台北皇冠杂志社1977年8月初版)一书中,较早注意到早期抄本中方言修改问题。她在《初详红楼梦》——《四详红楼梦》各文中列举抄本改文多例之外,还指出小说中有些词语来自江南的“弹词”,如“尤氏女”、“贾公子”等。
⑥“浇头”,吴语,见《清嘉录》诸书。意为“放在面饭上的菜肴,面码儿”。北京人则称为“飘码儿”
⑦赵存义:《〈红楼梦〉生活语言与绛州口语》,自印本,第71-72页。
⑧“滴”:北京方言中又作“嘀”“提”,如“滴楼”“滴溜”“提掳”“提拎”等。“滴”即提、提着、提起之意。释义与吴语不同。
标签:方言论文; 红楼梦论文; 北京话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金瓶梅论文; 曹雪芹论文; 林黛玉论文; 官话论文; 吴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