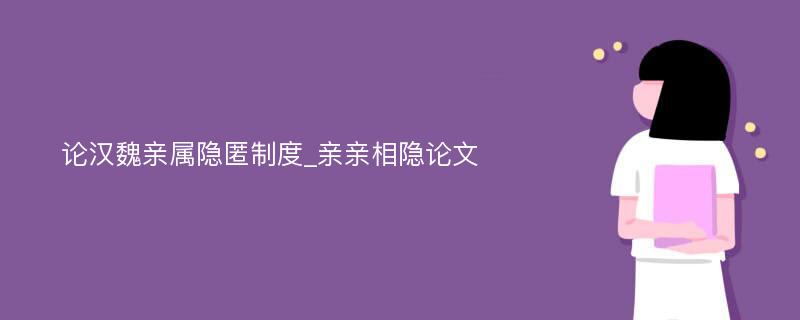
汉魏无“亲亲相隐”之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征之一,“亲亲相隐”制度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许多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这一制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存在。据笔者看来,不仅秦汉政权,甚至魏晋南朝政权,也从未制定过亲亲相隐的法律条文,“亲亲相隐”制在汉魏时期从未存在。以下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一 秦及西汉前期“亲亲相隐”资料辨析
瞿同祖先生较早对亲亲相隐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根据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说法以及孟子关于舜父瞽叟杀人,舜必定会弃天下如敝履,窃负而逃的假设,认为“历代的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孔子的说法、孟子的假设,在先秦时期,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落实到法律层面的例证。瞿同祖所举法律方面最早的例证是汉代,认为“汉律亲亲得首匿”,并举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书为证。①
也许受材料的限制,秦代是否存在容隐之法,瞿同祖并未明示。睡虎地秦简问世之后,学界根据其中“非公室告”和“家罪”等法律条文,认为秦代已经形成亲亲相隐的制度。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的是范忠信。他说:“最早将容隐原则应用于法律的似乎是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这或许可以看做中国容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②将“容隐法”概括为“非公室告”,本来没有太大问题,但将“容隐法”等同于“亲亲相隐法”,这就与史实又拉开了距离。但是,这一观点影响很大,直到近年,学界认为秦代存在“亲亲相隐”制度的,仍不乏其人。③
“亲亲相隐”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有其思想来源的。有研究者将这一源头一直追溯到《春秋公羊传》,④但直接标明亲亲相隐之义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⑤在这个案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孔子强调父子之间互相容隐,容隐的主体与客体完全相同,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就是双向容隐,这正是“亲亲相隐”的基本特点。倘若仅强调“子为父隐”,而不主张“父为子隐”,那是单向容隐,只能称为“容隐”,而不能称为“相隐”。第二,叶公假设的“其父攘羊”,是父亲对非家庭内部财产的侵害。可以看出,孔子与叶公对话的基础,是亲属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侵犯,所以,孔子主张的父子相隐,实际是亲属间对危害公共秩序行为的互相隐瞒。第三,孔子的回答是对“子证父攘羊”的否定。所以,他主张的亲亲相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不仅不应该揭发,甚至也不应该主动或被动作证。
但是,秦律中的“非公室告”完全背离了上述三项标准。关于“非公室告”,秦律的规定如下:
1.“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2.“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3.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⑥
根据律文1,子告父母,如果是“非公室告”,政府是不予受理的。同样是“非公室告”,对于父母告子,政府又当如何处理呢?有研究者认为,政府同样不予受理,⑦但这一看法未必正确。按律文3,与父同居的子犯有“家罪”,父亲去世后,如有人提出控诉,政府亦不予受理。依此反推,如果父亲在世,并提出控告,政府是予以受理的。⑧“家罪”即“非公室告”,⑨因此,父亲以“非公室告”的形式控告子女,政府并不会拒绝。“非公室告”不可以行之于卑幼,却可以行之于尊长,假如将类似的不能控告勉强视为“容隐”的话,那么这也仅仅是单向“容隐”,而不符合孔子主张的双向“相隐”。其实,即就单向容隐而言,也并不彻底。按严格意义上的“相隐”之制,无论尊卑,只要互相控告,均予以惩罚。但按律文1,子告父母,反复控告,才加以治罪,所以,秦律中的“容隐”是大打折扣的。
根据律文2,可以知道在政府拒绝受理的“非公室告”中,父亲的犯罪行为仅限于对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的侵害,并不涉及公共秩序问题,这与叶公、孔子讨论的情况恰好相反。有研究者认为:“秦律中所谓的‘子女、臣妾不得控告父母、家长’,其实质是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对亲属相犯、以主犯奴行为的不干涉,对亲属相讼、以奴诉主的不受理,而不是国家对亲属主婢之间的互相包庇、隐瞒犯罪之行为的不追究,所以秦律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亲亲相隐原则的正式体现,而只能作为亲亲相隐精神的一种不成熟形态。”⑩更有研究者谓:“认为亲属容隐制度起源于秦律,在史实上混淆了亲属相隐与亲属相犯、亲属相讼,在理论上没分清家庭内部的法律关系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11)这些看法或间接、或直接,但均根据“非公室告”针对的犯罪行为,对其与“亲亲相隐”的关系提出质疑或否定。
父母既然可以控告子女对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的侵害,当然也可以控告其在家庭以外的犯罪行为。那么作为卑幼的子女,是否可以控告父母的此类犯罪行为呢?关于这个问题,秦律未见明文规定,但商鞅是禁止隐瞒犯罪行为,鼓励告奸的,《商君书·禁使》:“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12)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以楚国令尹杀证父攘羊的直躬,导致“楚奸不上闻”为例,认为人君如果行令尹之事,“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13)商鞅、韩非禁止亲属相隐,提倡亲属相告的思想最终落实在法律层面,秦对以下盗窃案的处理可以证明这一点:“削(宵)盗,臧(赃)直(值)百一十,其妻、子智(知),与食肉,当同罪。”(14)妻、子明知夫、父盗窃,却不告发,罪属隐匿包庇,所以,与盗窃者同罪。但如主动告发,则可以减轻处罚:“夫有罪,妻先告,不收。”(15)妻告夫为卑告尊,政府对此行为既然加以鼓励,揆诸情理,也不会禁止子告父的行为。秦鼓励亲属相告的制度在汉初继续得到执行:
4.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遍)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5.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遍)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
6.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16)
根据律文4的规定,如拥城邑亭障反叛、投降诸侯、弃城逃亡或投降、谋反,父母、妻子、同产均处弃市刑,但如果被株连之人预先主动告发,则免予处罚。唐律“同居相为隐”条特别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行为不在相隐之列。汉律以上规定性质大致与此相同,似乎据此不能否定汉初“亲亲相隐”之制的存在。但是,律文5涉及的犯罪行为仅为普通抢劫罪,超出三谋范围,妻子、儿女如不告发,将被处以城旦舂这样的重刑;如主动告发,官府捕得罪犯,告发者免予治罪。律文6规定,对盗铸钱者同居不告,处以“赎耐”之刑。在秦及汉初法律规定中,同居指同籍者。父子兄弟未必一定同籍,但同籍者肯定大有人在。此条规定的主旨在于禁止亲属间互相隐瞒盗铸钱的犯罪行为。这两条律文说明,在汉初法律中,告发、揭露亲属犯罪行为既是权利,更是义务。而在严格意义上的“亲亲相隐”制度中,隐匿、包庇亲属犯罪行为才是权利和义务。因此,汉律的规定固然不符合孔子“父子相隐”、子不证父的看法,更完全背离了“亲亲相隐”之制的基本精神。
汉初亲属不得相隐的法律精神一直贯彻到汉昭帝时期,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作为体现亲亲相隐之制基本精神的隐匿亲属权利,始终被政府否定。昭帝时期,文学在盐铁会议上攻击当时的弊政之一即是重首匿之法:“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耳。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17)在文学看来,父子互相隐匿、包庇犯罪的行为天经地义,惩罚藏匿亲属的谋首伤情败理,自然应该加以废除。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同样反对惩罚藏匿亲属者。他在《春秋决狱》中假设了如下案例:乙为甲之养子,乙杀人获罪,甲藏匿乙。甲该当如何论处呢?董仲舒的意见是:“《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18)既然主张父可匿有罪之子,当然更不会反对子匿有罪之父。可见,在董仲舒看来,藏匿有罪之子、之父,是父亲、子女的权利,这一行为理应受到保护。尽管有这样的反对声音,首匿之法在昭帝时期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在此之前的汉武帝时代,首匿之法更被推行到极致。东汉梁统对此曾有所评论:“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19)
董仲舒以春秋决狱虽然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经常被用作判案的依据,但在武帝时代是否得到执行十分可疑。有研究者认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的部分或者是大部分,是董氏任职江夏相、胶西相时,所判疑狱之精华。(20)不过,这毕竟于史无证,仅属推测。而且根据下文所举诏书,可以知道,直到宣帝地节四年之前,首匿犯罪亲属仍会受到追究。即令董仲舒确曾将《春秋》之义应用于司法实践,可能仅限于他任职的江夏和胶西两地,未必成为普遍的司法依据。(21)甚至《春秋决狱》完成以后,在司法实践中,汉政府仍对隐匿犯罪亲属者予以严惩。《后汉书》载:“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22)可见,《春秋决狱》是董仲舒为解答廷尉张汤之疑而作。董仲舒致仕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张汤自廷尉迁御史大夫在元狩三年(前120年)。也就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两起案件。一起在元朔五年,西汉开国功臣灌婴之孙临汝侯灌贤藏匿犯伤人罪的儿子。此案详情难知,但最终结果是灌贤被免爵。(23)此案的处理说明,当时隐匿亲属并非如董仲舒主张的那样,免予惩罚。政府对首匿者并不区分所匿是否亲属,一律加以惩处,梁统谓武帝“重首匿之法”,是有其根据的。
与亲属相隐被否定相反,子告父罪作为一项权利,在当时的另一个案件中则得到肯定。元狩元年,衡山王刘赐与子刘孝意欲谋反,后者担心谋泄被诛,“闻律先自告除其罪”,遂主动坦白并告发父亲的犯罪行为,刘赐自杀,刘孝则因为“先自告反,除其罪”。此案所涉为谋反罪,但所谓“律先自告除其罪”,当不仅指谋反,而是包括了所有犯罪行为。身涉犯罪案件者告发自己和亲属可以除罪,未曾涉案者告发亲属当然更不会受到惩罚。由此推测,秦及汉初鼓励告发亲属,禁止亲属相隐的法律规定,在武帝时期仍然得到执行。有研究者根据《汉书》刘赐太子爽“言衡山王与子谋逆……坐告王父不孝……弃市”的记载,认为武帝时期“单方面强迫‘子为父隐’”。(24)但据学界研究,刘爽仅告发过刘孝,并未告发刘赐。相反,根据《史记》记载,刘爽是因刘赐病时,称病不侍,被刘赐以不孝罪名告发而处弃市刑的。退一步言,即使刘爽确实告发了刘赐的谋反意图,应该与刘孝一样,有罪免罪。无罪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被处死。(25)所以,刘爽一案并不能证明武帝时期已经存在了“子为父隐”之制。
当然,《汉书》关于“告父弃市”的记载,也并非子虚乌有,汉初法律确实明确规定控告父母,要处以弃市刑:“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26)但是,这一规定应该是对秦代“非公室告”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汉律所禁止的,只是子女对父母伤害家庭成员和侵害家庭财产提起的诉讼(27),至于父母其他方面的罪行,如上所论,子女不仅没有隐匿的权利,相反,有告发的义务。
既然昭帝以前,秦汉政府均鼓励亲属相告,那么,孔子、董仲舒等儒家学者主张的父子相隐就不会落实到法律层面上得到执行,尽管他们提倡的相隐主体范围较诸后世还相当狭窄。
二 宣帝地节四年诏书与“亲亲得相首匿”律
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具体内容如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8)这道诏书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自诏书颁布之日起,卑幼隐匿直系尊长及妻匿夫无罪,此前首匿之法中与之冲突的法律条文作废。这道诏书在法律制度史上的意义不容否认,唐代以后的“亲亲相隐”之制确实与此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宋代儒学家邢昺说:“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盖由汉宣此诏推广之。”(29)邢昺谓宋代亲属相隐之制由此道诏书推广而来,而不认为诏书的颁布代表亲属相隐制度的成立,肯定是注意到了诏书与此后相隐制度的差异性,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最早将这一诏书视为“亲亲相隐”之制的,大概是明代学者丘浚,所著《大学衍义补》谓:“按律文亲属得相为容隐始此。”(30)清代学者陈立祖述其说,释孔子“父子相隐”云:“汉律即有亲属得相容隐之令。”并引宣帝诏书及上文所举《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为证。(31)近代现代学者在丘、陈之说的基础上,将诏书内容进一步概括为“亲亲得相首匿”,并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即出现在此时,(32)这种看法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定论,这与学界对秦及汉代早期存在亲亲相隐之制产生经常产生质疑的情况颇不相同。
但是,将宣帝诏书内容概括为“亲亲得相首匿”,未必妥当。“亲亲得相首匿”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条对季友不诛杀弑君的兄弟庆父解释为“亲亲之道”,何休注:“论季子当从议亲之辟,犹律亲亲得相首匿,当与叔孙得臣有差。”(33)何休在这里只是提到汉代有“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规定,并未将其与宣帝诏书相联系。至于这一规定的具体内容如何,无从得知。季友的行为,属于隐匿旁系亲属,与宣帝诏书不合。从这个角度说,何休提及的“亲亲得相首匿”律可能并非宣帝诏书,而是另有所指。
其实,以“亲亲得相首匿”或亲亲相隐之制解释宣帝诏书是存在问题的。从隐匿主体看,诏书重在强调子为父隐,孙为祖隐,妻为夫隐。虽然后者隐匿前者的限制较此前放松,但只有殊死罪才上请廷尉,决定是否从轻发落,至于其他罪行,应该与此前判罚没有区别。所以这一规定从本质上说,仍更倾向于单向容隐;而无论是“亲亲得相首匿”律,还是“亲亲相隐”之制,从名称上看,应该是承认亲属之间有互相容隐的权利。从隐匿客体看,诏书仅承认隐匿直系亲属或妻匿夫,范围相当狭窄。而较为严格的“亲亲相隐”制度是可以隐匿大功以上亲属甚至外亲的。当然,两者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诏书中的隐匿仅仅是一项权利,而且作为直系尊亲属而言,这项权利还打了折扣。这项权利仅在不存在连坐之制的情况下才具有可操作性,一旦犯罪行为累及亲属,亲属自保的方式必然是告发而不是隐匿犯罪者。这样,容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亲亲相隐”制度中的隐匿,无论对何种亲属而言,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一旦揭发犯罪亲属,告发者将受到惩处。所以,隐匿成为义务,是“亲亲相隐”制度存在的前提。按此标准,宣帝诏书距离“亲亲相隐”制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至多只能视为意义有限的隐匿制。
既然隐匿直系尊长不是卑幼者的义务,告发也就成为卑幼者的权利,这在宣帝以后有史实可证。成帝时期,太中大夫张匡上书诋毁丞相王商,提及王商之子王俊欲告王商:“商子俊欲上书告商,俊妻左将军丹女,持其书以示丹,丹恶其父子乖迕,为女求去。”王俊意欲揭发之事当是王商“与父傅通,及女弟淫乱”的行为。(34)所谓告发之说,也许是张匡的捏造,但无论如何,捏造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上允许子告父,否则,捏造就失去意义。史丹因王俊告父,令女儿与其离婚,并不能否定法律允许子告父,只能说明在社会观念上,人们对这一行为是不以为然的。其实,就当时的社会观念而言,不仅否定直系亲属之间的相告,旁系亲属相告也被视为违反伦理道德。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韩延寿迁左冯翊太守,民间有兄弟因田争讼,韩延寿因自己未能尽到以德化民的职责,闭门思过,兄弟二人受到感化,登门谢罪,不复争田。韩延寿不仅对亲属相告持否定态度,对吏民相告同样也不赞成。韩延寿任颍川太守之前,其前任赵广汉“患其俗多朋党,故称会吏民,令相告讦……颍川由于以为俗,民多怨雠”。韩延寿代任,反其道而行之,召集吏民,“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一郡之内,风化大行。赵广汉鼓励吏民相告,或许于法有据,而韩延寿所行所为,却仅能代表道德观念。有研究者根据韩延寿处理兄弟争田事,认为当时“亲亲之间不允许争讼……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35)显然是片面的。不夸张地说,宣帝以后,父子、祖孙、夫妻之间是否相隐、是否告发,主动权完全在亲属手里,更遑论作为兄弟的旁系亲属。地节四年诏书的颁布,并不是对亲属相告的否定,而只是让亲属在告与不告之间多了一个选择。
何休所说“亲亲得相首匿”律,究竟是汉律原有律名,还是他自己对汉律某一类法律条文的概括总结,已经难以确知。如果概括并不准确,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如果概括准确,就等同于汉律存在这样的律名。无论是何休的概括,还是汉律原有律名,从名称上分析,“亲亲得相首匿”似乎意味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匿,而不再是单纯的卑幼隐匿直系尊长或妻匿夫,这较之宣帝诏书确实是一个发展。不过,“得”字表明,这种隐匿仍只表示可以隐匿、能够隐匿,而不是必须隐匿,这在本质上与“亲亲相隐”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们不知道“亲亲得相首匿”之类的律文是出自西汉还是东汉,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东汉末年,隐匿亲属仍然只是权利而不是义务。东汉学者班固讨论“亲属相容隐”云:“兄弟相为隐乎?曰:然。与父子同义……朋友相为隐者,人本接朋结友,为欲立身扬名也。夫妻相为隐乎?传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36)班固将容隐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兄弟、朋友。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发挥,与法律无关。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讨论容隐类型时,用语是有所区别的。论“兄弟相为隐”,他以发问方式开始;而论臣为君隐、父为子隐则直截了当:“所以为君隐恶何?”“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不同的表达方式说明在当时人看来,臣为君隐、父为子隐理所固然,至于兄弟互隐则存有很大的疑问,所以班固要特别加以解释。
与西汉相似,东汉确曾发生过兄弟相讼的案件。和帝时,桂阳境内有蒋均兄弟争财,“互相言讼”。太守许荆以自己未尽教化之责,上请廷尉治己之罪,最终“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37)即令被视为理所固然的父为子隐,在现实中也没有成为一项义务。顺帝时吴祐为胶东相,政崇仁简,民不忍欺。啬夫孙性私敛民钱,为父买衣。其父令其自首伏罪。吴祐怜孙性之孝,宽肴其罪,并向其父表达谢意。(38)卑幼控告直系尊长也时有发生。章帝建初元年(76年),胶东侯贾敏诬告其母杀人,“国除”。贾敏爵位被废,并非因为他告发其母,而是因为所告之事纯系诬告。 (39)贾敏告母十年以后,又发生了齐王刘晃及其弟利侯刘刚与其母太姬互相诬告案件,此案最终以“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收晃及太姬玺缓”而收场。(40)章帝对涉案主角处罚虽有轻重之分,但颇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显然,他们的获罪均是因为诬告而不是告发。(41)贾复告母以及刘晃等母子相告,意味着直系亲属相告是他们的权利,政府对此行为未必鼓励,但不加惩罚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行事了。
到东汉末年,政府对亲属相告不仅不加惩罚,似乎隐匿亲属在法律上反倒是被禁止的行为,这在当时的士亡法中有所体现。《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军士逃亡,官府拷问其妻子儿女,显然是因为妻子、儿女在法律上没有隐瞒丈夫、父亲的权利,相反,主动坦白交代,则是他们的义务,否则,就不会有“考竟妻子”的律条。即使如此,曹操仍担心惩罚亲属太轻,士兵逃亡不止,遂更改旧法,“更重其刑”。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形势下,亲属相隐是绝对被禁止的。这条法令并非徒具虚文,在现实中也得到了执行。当时有鼓吹宋金逃亡,负责办案者欲杀宋金之母、妻、二弟,只是由于高柔的建言,宋金家属才逃过一劫。史载此后“蒙活者甚众”,就此推测,曹操大概废除了诛杀逃亡士兵亲属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许“考竟妻子”的旧法也许仍然存在。即令此法废除,告发亲属也应该不在禁止之列。
我们知道,汉魏之际,士兵地位低下,众所周知。拷问逃亡者亲属的律条,也许仅行之于士兵,但是,很难想象,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禁止普通百姓亲属相告,另一方面又禁止士兵亲属相隐。所以,通过士亡法可以推测,当时法律对普通的亲属相隐固然未必禁止,但同样不会禁止亲属相告。从这个角度说,汉魏之际仍不存在“亲亲相隐”之制。
三 两晋南朝的亲属相告与作证问题
“亲亲相隐”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否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学界常引东晋初年大理卫展的上书,作为当时法律上存在“亲亲相隐”的证据。(42)不过,卫展上书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晋书·刑法志》:“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43)卫展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行为加以指责,但是,司法官吏逼迫子证父母,父母证子,却不能说是滥施酷刑,而是于法有据,这一根据就是皇帝颁布的诏书。卫展所攻击的“举家逃亡家长斩”,也是来自于《庚寅诏书》。元帝回答卫展上书,有“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之语,所以,在卫展看来违背“相隐之道”的诏书并非东晋所定,而是沿自西晋惠帝。根据惠帝诏书可以推测,西晋《泰始律》也许仍然继承了宣帝以来可以隐匿直系亲属的规定,但这仍然只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庚寅诏书》的颁布意味着即使《泰始律》给予直系亲属隐匿的权利,惠帝元康(291~299年)以后,这一权利也已经被禁止,相反,告发、证明直系亲属罪行成为义务。之后,诏书发展为“故事”,成为官吏司法的依据,官吏可以对隐匿亲属者严加拷问,因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法律规定。元帝说元康以来“法禁滋漫”,可见在他看来,卫展攻击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当时的法律。
相反,卫展的主张于法未必有据。他指责官吏逼迫直属亲属相证,是因为这样做“伤顺破教”,“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可见卫展只是从伦理角度驳斥亲属相证,而不及法律。就在卫展上书之前不久,主簿熊远因为当时“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也给晋元帝上一道奏疏,建议:“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44)熊远在奏疏中一再强调“驳议”“立议”的依据应当是法律,其次是经传。至于单纯以情立议,那是破坏成法,应该禁止。西晋的刘颂更把法律视为断案的唯一依据,不但否认“情”,也否认未人律令之礼:“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45)卫展的做法与熊远、刘颂的主张不同,无论否定亲属相证,还是主张亲属相隐,均不涉及法律条文,而仅以“教”“道”“义”这些抽象的理论为据。我们当然不是说卫展这些依据就一定是熊远所说的“情”,但所谓“教”“道”“义”,即使是“礼”,也肯定没有入律,否则他就会以更有说服力的类似法律条文来“驳议”或“立议”了。卫展主张直系亲属相隐,固然算不上“任情以破成法”,但若说“任礼以破成法”,大概没有问题。
对于卫展的建议,元帝的回答是:“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至于最终是否被采纳,不得而知;即使被采纳,也不意味着“亲亲相隐”制度的成立。卫展只是否定在父母不知道子孙逃亡的情况下,追究父母之责,但仍认为,“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这意味着知情不举,父母仍要承担连坐之责,与此相对,官吏仍有拷问知情亲属的权利。
东晋中后期,经学家范宁注《论语》云:“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46)这条法律规定与宣帝诏书有异有同。相异之处是,容隐的客体扩大到期亲以上,不再局限于父子、祖孙。从名称上看,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匿,不再局限于卑幼隐匿尊长。相同之处是,法律仍然只是强调亲属之间可以相隐,隐者无罪。但是,法律仍不禁止亲属之间的相告、相证,义熙五年(409年)发生的一个案例可以为证。《宋书·何尚之传》:“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合从原。”’(47)王睦告发王延祖之“于法有疑”,其“疑”在于:告子之父该如何判罚?即是仍按连坐之制的原刑科罚呢,还是应当减刑或免刑?由于当时的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官员产生疑惑,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禁止父告子。相反,从何尚之“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的回答来看,连坐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亲属相告”,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从根本上杜绝犯罪。如上文所论,如果亲属相隐只是权利,不是义务,那么,在特殊的环境下,必然导致亲属相告,王睦告发王延祖,就是在连坐制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这样说,连坐制之类规定的存在,极大地压缩了原本就意义有限的“亲属得相为隐”生存的空间,最终必然导致“期亲以上得相为隐”的法条名存实亡。
王睦原本应受连坐之刑,但由于主动告发,在何尚之的建议下被认定无罪。这一案例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可以想象,遇到类似情况,亲属相告将成为多数人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在这一案件发生没有多久,逼迫亲属相证又成为当时司法的风气。《宋书·蔡廓传》:“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48)蔡廓并没有涉及具体案例,大概与卫展上书时一样,当时断案逼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的情况十分严重,所以蔡廓才有上述建议,所针对的是普遍现象。仍然和卫展上书相似,蔡廓也是从“亏教伤情”的伦理角度而不是法律角度,指斥官吏逼迫子孙证父祖之罪的行为,这反映官吏的做法既普遍,亦不违法。刘裕封宋王在元熙元年(419),距王睦告发王延祖不过十年,但是,我们看到,那时官吏对王睦主动告发亲属如何处罚尚有疑惑,而现在则一变而为主动逼迫子孙证父祖之罪了。
隐匿亲属仍处连坐刑,主动告发则可以免罪,加之以官吏逼迫亲属作证,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的规定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是徒具虚文,甚至令人怀疑,它是否一直存在到东晋末期。按《宋书》所载,蔡廓的建议被采纳。但是,以何种形式采纳,是否成为法律条文,史籍未曾明言。我想,即使他的建议已经入律,大概也只是暂时的;即使一直存在,也只是禁止官吏逼迫亲属相证,并不禁止亲属自动作证。因为在梁代初年发生了一起与王睦告子十分相似的案件。
《隋书·刑法志》:“(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49)王延祖案是父告子罪,此案则属子证母罪。史书云“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从迹象上看,似乎是法官提问景慈回答。景慈证母之罪既不好说主动,也不好说被动。官吏取证于罪人之子,未必滥施酷刑,但仍然有违“亲亲相隐”之制。景慈除选择证明母亲犯罪外,还可以有如下两种选择:或者当庭拒证母亲之罪;或者此案判决后,要求重审。要求重审,如果证明是冤案,景慈自然无罪,但此案显然情节清楚,无法翻案,那么景慈只能接受“五岁之刑”。拒证后果如何,史无明文,但肯定也会被处罚,倘若当时存在与唐律“大功以上亲,有罪相为隐,勿论”相类的规定,景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拒证。无论乞鞫,还是拒证,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证明母亲有罪,大概与王睦告发王延祖犯罪一样,可以免除株连,所以,他选择了作证。这可以说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使然。至于作证免罪,究竟是梁朝的新制,还是此前就有相关法律规定,就不得而知了。就何尚之一案的处理结果看,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景慈证明母亲有罪,没有得到获免,反而被判流刑,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是法官虞僧虬罔顾法律,依经断案的结果。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第一,虞僧虬要求处罚景慈的理由,丝毫未涉及法律,只是强调其行为违背了传统的父子相隐主张,“伤和败俗”。假如像唐代一样,梁朝存在禁止父子相告的法条,虞僧虬不会大费周折,引经据典,而是直截了当,以法条证明景慈所行所为应该受到严厉处罚。以“直躬证父,仲尼为非”证明景慈有罪,不过是引经决狱的老调重弹,于法无据。第二,如果景慈的行为真正触犯了法律,虞僧虬完全可以据律处罚,不必上奏中央。将此案上奏,反而说明景慈并没有违犯法律,直接处罚于法无据。但在虞僧虬看来,此等“伤和败俗”的行为不处罚不足以敦教化、厉风俗,权衡之下,遂将此案上报,由中央裁决。裁决的结果,景慈流放广州。但是,这并不说明当时存在“亲亲相隐”之制,只不过是此前屡屡上演的以礼败法、以情败法的又一次重现而已。
四 余论
“亲亲相隐”之制的理论依据来自孔子“父子相隐”的学说,根据孔子的看法,“父子相隐”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为双向容隐,其二容隐主要表现为义务,当然也是权利。这两个特点在《唐律》中均得到落实。《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50)此条规定亲属容隐为双向容隐,“勿论”“减凡人三等”则表明,容隐是一项权利。《斗讼律》“告祖父母父母”“告期亲尊长”“告缌麻卑幼”等条则表明,亲属相隐又是一项义务。(51)当然,唐律与孔子所说的“父子相隐”相较更为系统、具体,这主要表现在容隐主体及客体的扩大方面,但就本质而言,两者并无根本差异。
学界讨论的秦汉魏晋南朝“亲亲相隐”之制与此就大不相同了。根据上文所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有关容隐制的材料,主要表现为卑幼隐匿尊长的单向容隐,这与唐律的“有罪相为隐”有本质区别。是单向容隐还是双向容隐,唐人区分得相当清楚。关于亲属隐匿,法条概括为“相隐”,关于部曲、奴婢与主人的隐匿,则曰:“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疏议曰:“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当然,更主要的差异表现在,无论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还是何休所说的“亲亲得相首匿”,以及范宁所说的“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为罪”,所强调的亲属容隐,仅仅是亲属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容隐与否,基本由其自行决定。相反,禁止亲属告发、作证,从未入律。如前文所论,缺乏这一规定,即使单向双隐也容易流于形式,更遑论双向容隐。也许有人认为,“亲亲相隐”之制在唐代已经完全成熟,以此否定汉魏存在这一制度,未免缺乏说服力。但是,即使与孔子“父子相隐”的原初主张相比,学界所谓的汉魏“亲亲相隐”之制也颇有距离,这既表现在容隐的主体性方面,更表现在容隐的义务性方面。孔子“父子相隐”主张是“亲亲相隐”之制的源头,当这一源头的两个基本特点——特别是“容隐”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这一特点——在汉魏两晋南朝的法律层面上尚未得到落实时,我们只能说,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亲亲相隐”之制。学界所谓的“亲亲相隐”制,最多只能视为“亲亲容隐”制。
当然,唐代“亲亲相隐”之制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孔子“父子相隐”说可以视为其理论依据,不容否认的是,汉魏两晋南朝有关容隐的规定,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对其影响最大的,大概是北朝。北朝法律史料本来就比较缺乏,与“亲亲相隐”有关的法律规定更是难得一见。不过,从迹象上看,北朝在这方面的规定,似乎较同时期的南朝更为完备。北魏早期并不重视亲亲相隐,相反,和南朝相似,告发亲属受到政府的鼓励。《魏书·安同传子颉附传》:“尝告其父阴事,太宗以为忠,特亲宠之。”(52)这是子告父。《魏书·王建传》:“建兄回,诸子多不顺法,建具以状闻,回父子伏诛。”(53)这是弟告兄、叔告侄。不过,据窦瑗所引,东魏《麟趾新制》已经严格禁止子孙告父祖,《魏书·窦瑗传》:“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是在讨论“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法条时,征引此律的。(54)既然法律不允许子告杀父之母,当然也不允许子女告发父母三谋以外的其他犯罪。所以,“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的立法精神已经不同于秦及汉初,而是扩及一般犯罪行为。子孙告发父祖既然被严格禁止,与此相伴随,隐匿必然成为子孙的义务;或者说,禁止告发的规定很有可能就是以子孙隐匿父祖律条为基础的。这与南朝的情况大相径庭,而与唐律“同居相为隐”“告祖父母父母”两法条的立意相当接近。
北朝政府是否禁止告发旁系亲属,不得而知,但至少隐匿旁系亲属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魏书·刑罚志》:“《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即对于一般犯罪,期亲以上亲属相隐无罪。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之律称为“期亲相隐”。从名称上看,似乎有禁止期亲相告之意,这与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以及东晋的“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仅仅表达亲属可以相隐有很大的区别。即使此律没有禁止亲属相告之意,至少亲属相匿真正得到了落实。北魏神龟年间(518~519年),驸马刘辉因与百姓张智寿妹、陈庆和妹相奸,与兰陵公主发生冲突,“殴主伤胎”。门下建议:“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刑。”三公郎中崔纂引“期亲相隐”律反对,并云:“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认为因此判罚智寿、庆和,违背“期亲相隐”之律。智寿、庆和最终还是判处流刑,崔纂亦被免职。但是,这个结果只是因为被殴伤流产的主角为兰陵公主,身份非同常人,所以诏书说:“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55)反之,假如被殴流产者并非权贵,判罚必然以常例即“期亲相隐”律为准,智寿、庆和不必为其妹之事负责,因为按法律,他们本有隐匿其妹的权利。北魏孝文帝以后的有关史籍中,未见因隐匿亲属被治罪的案例,亦未见官吏逼迫亲属作证之事。这或许不是史料缺乏所致,很有可能意味着隐匿亲属作为一项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真执行,这同样与南朝徒具虚文的情况有别。隐匿亲属不被追究,并不意味着“亲亲相隐”之制的建立,但却是这一制度成立的先决条件。这一条件出现在北朝,而不是南朝,似乎也隐约暗示着唐代“亲属相隐”之制与北朝相关规定存在着密切关系。
北朝从鼓励亲属相告,到期亲相隐成为一项真正的权利,再到禁止子孙告父祖,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北方为何发生这种转变以及为什么这一转变发生在北方而不是南方,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予置论。此处可以推测的是,唐朝“亲亲相隐”之制来自北朝而不是南朝,因为汉魏两晋南朝本不存在这一制度。
注释:
①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第56页。按,宣帝废除亲属首匿相坐诏书颁布于地节四年,瞿著引为本始四年(前70年),误。
②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88页。
③崔永东:《出土法律史料中的刑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90页;胡谦、张文华:《论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马启华:《论亲属容隐与亲属相犯》,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张松:《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反映的秦汉亲亲相隐制度》,《南都学坛》2005年第6期;康宇:《试论“亲亲相隐”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广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郭齐勇:《“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的启迪》,《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8期(上);谢娟:《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之评析》,《理论新探》2008年第12期(中)。
④新近研究可参陈壁生《〈春秋〉经“亲亲相隐”义》,《国学学刊》2009年第1辑。
⑤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922~924页。
⑥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118、117、118页。
⑦崔永东:《出土法律史料中的法律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42~143页。
⑧王辉讨论“非公室告”时,对此律文做出如下解释:“如果父子不是‘同居’关系,而是‘异居’关系,或是父亲依然在世,那么父亲如果提起‘子盗父母’的诉讼就会被受理。”(《试析汉代子女对父母的告发权与诉权》,《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65页)这一表述并不十分妥当。从律文原意看,所谓“家罪”,是以父子同居为条件的,如果异居,“子盗父母”自然不属于“家罪”,政府受理在情理之中。
⑨于振波:《秦律的立法精神浅析》,《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273页。
⑩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01页。
(11)宋大琦:《亲属容隐制度非出秦律说》《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83页。
(1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第135页。蒋礼鸿认为,“弃”当为“弆”之误。
(1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第449~450页。
(14)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8页。
(15)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4页。
(1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第7、18、35页。
(17)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下)卷一○《周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第599页。
(18)杜佑撰《通典》卷六九《礼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1911页。
(19)《后汉书》卷三四《粱统传》,中华书局,1965,第1166页。
(20)黄静嘉:《中国传统法制之儒家化之登场、体系化及途穷——以程树德编两汉春秋决狱案例为切入点》,载柳立言主编《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第173页。
(21)关于“春秋决狱”的局限性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限度,可参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家化”》,《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10,第488~489页。
(22)《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第1613页。
(23)《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第549页。
(24)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88页。
(25)相关研究可参岳庆平《子告发父母而被处死并非始于汉武帝时期》,《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40页;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06~107页;陈万良、刘惠琴《西汉衡山太子刘爽获罪原因考》,《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3~64页;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02~103页。
(2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7页。
(27)王辉:《试析汉代子女对父母的告发权与诉权》,《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66页。
(28)《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1页。
(29)王先谦:《汉书补注》(上),中华书局,1983,第112页。
(30)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188页。
(3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谏诤》,中华书局,1994,第241页。
(32)近代学者中,较早持此看法的代表性学者为杨鸿烈。他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辟“亲属相容隐问题”专节,举宣帝诏书为证,谓亲属相容隐在汉代成为国家律文(第188页)。上举瞿同祖观点亦与此相同。近来持此观点者可参范忠信《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程、规律和启示》,《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第115页;宋大琦《亲属容隐制度非出秦律说》《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83页;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02页。
(33)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3,第2243页。
(34)《汉书》卷八二《王商传》,第3372页。
(35)郭程:《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材料与秦汉“亲亲相隐”制度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18页。
(36)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谏诤》,第241~242页。
(37)《后汉书》卷七六《循吏·许荆传》,第2472页。
(38)《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第2101页。
(39)《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第667页。
(40)《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縯传》,第553~554页。
(41)关于这一案件的讨论,可参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47页。
(42)可参范忠信《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程、规律和启示》,《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第116页;郭齐勇《“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的启迪》,《社会科学论坛》,《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8期(上),第103页。
(43)《晋书》卷三○《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第939~940页。
(44)《晋书》卷三○《刑法志》,第938~939页。
(45)《晋书》卷三○《刑法志》,第938页。关于熊远、刘颂对断案依据的看法,可参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家化”》,《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第490页。
(46)皇侃:《论语义疏》,《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中华书局,1998,第254页。
(47)《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1733页。
(48)《宋书》卷五七《蔡廓传》,第1570页。
(49)《隋书》卷二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第700页。
(50)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上),中华书局,1996,第466~467页。
(51)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下),第1623~1636页。
(52)《魏书》卷三○《安同传子颉附传》,中华书局,1974,第715页。
(53)《魏书》卷三○《安同传子颉附传》,第709页。
(54)《魏书》卷八八《良吏·窦瑗传》,第1909页。
(55)《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第2886~28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