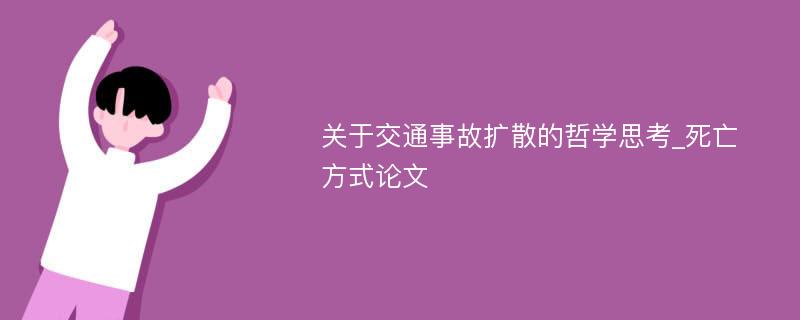
车祸泛滥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车祸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1)05-0001-07
生存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提升为一种社会属性,就是对安全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安全需求已经以契约形式制度化为人的生存权(body rights)。“如果有什么是神圣的话,人类的躯体就是神圣的。”——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不朽名句为人的生存权做出了最好诠释。
技术进步(无论这一概念在技术批判主义者的眼中是多么可疑)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能力,为满足人类的安全需求、保障人的生存权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然而,每一具体技术形式的使用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衍生出超越技术设计者预期之外的效能,甚至可能异化出一种危害人类自身的负向价值。车祸便是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异化的结果。
一、和平时代的战争
1899年8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利斯科的妇人与家人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游览路线上游玩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撞倒殒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车祸牺牲者,自此拉开了车祸悲剧的帷幕,而这出悲剧一经开演就再也没有收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二十世纪,医学科学完成了人类历史上95%以上的重要发现,大大降低了人的机体遭受疾病侵害的广度与频度;而在另一方面,同样是人类现代技术的汽车,却在频繁地产生着车祸,将痛苦、伤害、残疾甚至死亡强加给人类。当前,车祸已成为社会人口非自然死亡及伤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早轿车化了的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4万以上,伤残的人数则多达200多万。车祸还是大脑和脊椎损伤的最主要制造者;美国每年有8万人因车祸导致颅脑损伤而瘫痪,2000人成为植物人。[1]
即使在刚刚开始进入轿车社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车辆数目的增加,交通事故也在稳步上升。在中国,1986年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4万多,到1997年,死亡人数已猛增到73861人,受伤者达190128人[2],到了1999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83529人,受伤者286080人。[3]这就是说,每天大约有230人在车祸中丧生,780多人受伤。
今天,在这个有5.5亿辆汽车爬行的行星上,车祸造成灾难甚至超过某些自然灾害。例如,1900-1990年90年间,地震造成的死亡人口是130万人。在同一时期,车祸则夺去了2235万人的生命。而且每年的车祸死亡和受伤人数呈增长趋势:1900-1920年死亡100万,1921-1940年死亡200万人,1941-1960年死亡500万人,1961-1991年死亡1435万人。迄今为止,全球被汽车夺去的生命已达到两千五百多万,受伤者则难计其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现在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机动车辆的事故,1000-1500万人受伤。[4]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每45秒钟就有一人因车祸死亡,每两钞钟就有一人受伤。
车祸的危害其实已不亚于人类之间的战争了。在美国,九十多年来,死于车祸的美国人已超过270万,是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和越南等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4倍;而在车祸中致残的人数则多达9200万,是本世纪所有战争中受伤的美国人的30倍。从1963年到1969年,死于公路上的人数超过同一时期美国人死于越南战争人数的10倍。在1992年针对伊拉克发动的40天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战争中丧失了146条生命,而在同一时期的高速公路上,有4900美国人“死得同样惨烈。”[5]在中国,车祸造成的死亡,相当于每三年有一颗广岛原子弹爆炸。
车祸造成的伤亡同战争中造成的伤亡亦大致类同,都会出现殒身碎首、血肉分离的可怖景象。它不但使受害者遭到巨大痛苦,也给受害者的亲属造成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车祸其实就是一场战争,是汽车向发明、制造和使用它的人类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却又不无残酷与血腥的战争。
二、对车祸的冷漠与宽容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荒秽盈途的惨烈景象令人们对战争苦难悚然而思。经过深刻反省与批判,人们开始自觉地抑制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将和平与发展树为新时代的主题。不无遗憾的是,大规模战争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而由汽车向人类发动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却仍在持续和蔓延。一百多年来,车祸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同样给人类带来灾难与创痛的车祸事故,却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没有像我们发动的惨无人道的、不可宽恕的越南战争那样惹人耳目。”[6]
车祸甚至失去了新闻的关注。早年的杂志封面或报纸的头版尚能刊登街道上的车祸场面,随着车辆增多事故频仍,媒体对地球上无时无处不在发生的车祸已经习焉不察,习非成是了。新闻媒体对橄榄球明星辛普森(O.J.Simpson)涉嫌谋杀前妻的案件的长达两年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同一时期公路上几十万亡灵的关注。足球场上的骚乱、社会名流的绯闻、政客们翻云覆雨的表演,可能比每年几万人丧生车轮之下更能引起“新闻兴趣”。即使英国王妃戴安娜车祸罹难,新闻热点也集中于对戴妃个人私情的猜测,至于发生车祸的原因,只是原单归咎于记者们对戴安娜如影随形的追逐烦扰,而很少有人将这件看似偶然的事故与汽车事故的高发率联系起来,很少有人追问轿车交通技术系统本身存在缺陷。假如我们的媒体有彰善瘅恶的责任,难道车祸之中不也含普遍的社会伦理与社会公正性因素吗?对于根本没有能力使用汽车的老人、幼儿、残疾人和买不起轿车的穷人而言,对于这些难以享受到“轿车文明”的、依靠自行车或步行出行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无辜地承受随时可能发生的车祸危险,不也涉及到社会的公正性与进步性的深刻论题吗!
难道说车祸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危及大多数的普通公众吗?非也。只要将统计数据作一些转换处理就会发现,遭遇车祸的人群发生率非常可观。1970年,有280万人口的洛杉矶,429人因车祸死亡,52823人受伤。照当时这个数字,假如洛杉矶人的平均寿命为72岁(当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的话,那么每90人中就有一人会死在路上,每个人一生之中至少会因车祸受伤一次。[7]进入90年代,虽然轿车的安全性能得到了技术上的改进,美国死于汽车事故的人口略有减少,但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个人驾驶里程数延长,每个人一生遭遇车祸的几率反而比70年代提高了。以现在的死亡率,今天美国生下的婴儿,大约每70人里就有一个最终会死于车祸。车祸造成的“这种死亡数量如果是来自伤寒或霍乱的话,那是会引起一场革命的。”[8]
或许有人会认为,一切的技术运用都会有发生事故的危险性;车祸就像所有其它的技术失误一样,是人类现代“机械文明”之必付代价,在“危机四伏”的技术生境中,当代经济、社会乃至日常生活须臾不可脱离的汽车招致的灾祸,不必反应过敏。这种看法显然来自于对事物的表浅认识。
诚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交通,所有交通方式乃至所有技术操作都有危险性:火车会出轨,飞机会跌落,即使步行也可能摔倒。但是要将汽车与其它交通方式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各种交通方式的安全性能有着霄壤之别。根据奥地利交通安全办公室人员对一些国家近十年的造成死亡事故的研究,行驶相同距离造成的事故死亡人数,汽车是火车的3.6倍,是飞机的14.7倍,轮船的18.8倍。当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交通安全设施以及管理方法不同,因而各种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字及彼此间的比例也会有变化。但无论如何,汽车交通之危险性高居榜首的地位却是不会改变的。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出人意料的是,汽车虽然具有更高的事故率,却拥有某种其它交通形式不可企及的“豁免权”。重大的航空事故或轨道交通事故,往往会招来公众广泛的关注和批评,而公路交通事故却能超然于贬斥之处。1997年,美国每天死于公路上的人是118人,中国是200多人。设想一下,在这两个国家,倘若每天有一架中型客机坠毁会是什么情形?它不仅会危害航空业对潜在旅客的吸引,对航空经济的核心形成致命打击,甚至会导致社会对这种交通方式的根本否定。然而,危险性高于航空、水运和铁路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公路交通系统,却可以招至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毫不影响此系统的正常通行。
那么是什么使这个世界能如此不经意地接受每年七十万人暴死轮下的事实?为什么在制定了限制核武器等一系列条约的和平主题下却没有制定出减少车祸的更严厉的规则?为什么在进入数字化高技术时代的今天却没有产生更安全的交通方式?是什么使人们对威胁人们安全的车祸采取了隐忍默从的态度?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用一种因果模式就能解释的问题,它牵涉到技术、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个层面,需要做综合的考察与分析。
三、关于车祸的责任问题
车祸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车辆本身的技术缺陷或机械故障、道路环境不良如路面破损和阻障以及交通主体行为不当。根据传统的交通事故分析,主体行为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事故的90%以上。[9]酒后驾车、超速驾车和无执照驾驶等拙劣的驾驶方式和拙劣的驾驶者,一直是发生车祸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因而,目前的责任界定,考虑的焦点往往是驾驶者对车辆的操作正确与否,以及是否遵守了交通规则。长期以往就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车祸是技术使用者主体行为不当造成的,因而,汽车交通技术的使用者就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种过于简单的责任判定方法,无疑使我们忽略了直接原因之后那些间接的却又不无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如果放弃单线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的认定远非通常想象的那么一目了然,谁应对此事故负责?其实答案可以有许多种:
一、孩子,——因为不懂交通规则而走到了公路上。
二、妈妈,——没有看管好孩子。
三、司机,——车开得太快。
四、司机,——没有购买可在短距离煞住的车,而市场上可买到煞车距离为6米的轿车。
五、汽车设计者,——未能设计出更好的煞车装置。
六、制造商,——没有要求设计者设计出好的煞车装置。
七、政府,——没有要求生产厂家必须安装现有最好的煞车装置。
八、普通公众,——推选了这样一个没有尽职的政府。
当然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可能责任者。
显而易见,事故的责任关系远比人们的直观认识要复杂得多,有时甚至根本没法确定直接责任者。不妨把上面的假设再演绎下去。车祸后调查发现:一、孩子年龄太小,尚不具备理解交通规则的能力,也不具备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二、孩子的母亲正在上班,而看管孩子的保姆正在清理打碎的餐具以免玻璃碎片扎伤小孩;三、司机驾车的时速在最高限速以内,而社会并没有制定出必须使用效果更好但价格昂贵的刹车技术。从这个假定的案例可以看出,可能的直接责任者都在责任之外,很难明晰地指出车祸的直接负责人。诚然,这个假设是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极端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相反,理想化的假设更有利于洞悉复杂事件的本质。
简略的责任认定又必须导致了简略的后果处理。目前各国的处理的原则大体是:如果过错方是伤亡者,便是自取其咎,目前国内某些城市施行的“撞了白撞”的交通法规就是典型;如果肇事者死于车祸,则免于追究;若是肇事者幸免于难,则要赔偿无辜的受害一方的损失并承担各种处罚,以此来实现社会的公正性。(现在车祸中的各种关系和善后处理要复杂得多,这里不做技术细节上的详尽论述。)
不难看出,尽管车祸中的伤害存在施于和被施于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被断定为有过错的肇事,往往同时也是受害者,因为在车祸中,他或者是自戕其身,或者要为某种失常状态下意外造成的他人的伤亡承受良心上的谴责,甚至受到经济上或刑事上的惩罚。他们当中很多人会为自己感到无辜,因为在轿车主导交通的社会,放弃使用轿车就意味着生存的艰难,甚至失去行动的自由,在某些国家,人们出行时甚至到了别无选择程度,驾驶有车祸危险的汽车由社会存在方式所决定的。即使有严重过失的驾驶者也有理由为自己辩护,比如对于一个夜半在酒吧喝多了的人,在没有其它交通方式可供使用的情况下,他若不开车回家又能做何选择?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即使那些尚未牵涉到某一具体车祸中的一般民众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无处不在的汽车的牺牲者,面对每人一生受车祸伤害一次的几率,没有多少人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可以说,汽车社会中的所有公众都是受害者。
对于车祸责任者的界定和处罚,直接关系到人们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认定,也从心理的潜在层次上影响了人们对车祸的态度。由于都是受害者,区别的只是受害的程度和方式,实现公正的方式只是由受害严重的或更无辜的一方受害较轻的或有过失的一方寻求公道。这样,当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另一受害者时,人性中的善良与仁慈唤起的恻隐之心便使人们失去了批评的道义勇气和力量,最终形成了对车祸的集体“失语症”。
此外,简略的责任认定与后果处理,实现的只是一种表浅层次的公道或心理上的平衡,根本无助于减少车祸,反而使本应承担责任的汽车技术系统、社会管理者及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逃脱了批判,使得车祸得不到有效抑制而泛滥成灾。
四、轿车交通系统是否可靠?
由于通常形成的思维定势,人们很少怀疑技术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认为一切人类技术都必须含着理性与进步的因素,因而技术是不会犯错误的:车祸的发生只是理性不健全的人操作中的失误。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错误认识。且不说在现实驾驶中,有一定比例的车祸是由车辆本身的技术缺陷、由低劣的质量管理导致的机械故障引起的,就是机械部件没有问题,这种将人与技术割裂开来,把技术看作可以独立于人的外在手段的认识也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一切技术都是人的创造物,其工作及运用的原理和程序都是人所赋予的,同时技术又服务于人,由人来操作,并同操作者和整个社会形成一定的关系。就此而论,根本就不存在脱离人的纯粹的技术,也不存在与社会文化无关的“价值无涉”、“伦理中立”的技术。因此,一个技术系统如果不能将人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那么这个技术就是不完整的。同样,在考察某一技术时,如果不能将人和社会的因素当作技术系统的一个部分考虑进去,那么这种认知方式就是不可靠的。
传统的汽车交通技术系统事故的责任分析方法,恰恰忽略了驾驶者主体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忽略了人与机器的协调关系,忽略了车辆与驾驶者及其运行其间的人类社会构成的关系。
首先,汽车交通技术系统是由人、车、路及社会管理等要素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人的操作错误的确是车祸发生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因为,机器的缺陷以及管理的问题皆容易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予以改进和弥补,而驾驶者主体的缺陷则是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的遗留物,非短时间能人为地予以完善。就人而论,虽雄踞进化梯进之顶端,却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人不但存在着如视觉、反应速度等生理上的不完善,人的理智也十分脆弱;即使有了安全设施和减少事故的法律条文,驾驶者仍屡屡拒绝使用相应设施,拒绝遵守法律条文;人们对于高速行驶,就像对大麻、海洛因等迷幻药一样,存在着明知有害却又难以自制的渴望;语重心长的告诫和严谨刻板的规则所起的作用绝不可估计过高。在面对无可争辩的癌症统计资料和种种吸烟有害健康的谆谆劝诫时,人们不是还在消费比以往更多香烟吗?正因为如此,完善的技术系统才应当充分考虑构成系统整体的人的缺陷,通过技术弥补人在生理及理智上的不足,以避免技术事故的多发,因而,人的错误实际上也是技术系统的错误。
其实,早在60年代,被弗洛姆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美国的城市学之父芒福德(L.Mumford),在考察汽车安全问题时就指出了弥补人的缺陷的方法。他认为,汽车专家在设计轿车时不应只考虑样式,而应当考虑到驾驶者主体的因素,考虑使用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行车经历及能力等因素,考虑他们正常的健康状况、他们的视力、他们内在的紧张和压抑程度及每日的涨落变化,并且将此提到最高的认识程度,必要的话通过立法来保证。甚至认为制造商应减少其利润的1/3用于加强安全设施。[10]但遗憾的是,制造商根本不会“理睬”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学者的“迂阔”之论,迄今为止,尚没有开发出一种能够保证轿车使用者始终处于神志清醒的理智状态的可靠的技术方法。
其次,汽车的使用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的行为,汽车总是出现在人类政治文化与经济最活跃的场所,总会同其它乘用者之外的人群形成一种关系,因此,对单个车辆的结构和设备的改造虽然能提高乘用者的安全系数,但对于车外人群并无多少效用,而在车祸中的伤亡者有很大比例是车外行人或骑车者。而且从心理上来说,车体本身安全性的增强,更有可能促使驾驶者放松警觉而高速行车,反而增加车外人群的危险性。研究表明,各国公路车祸的伤亡者中,行人、骑自行车和骑摩托人的人占到30%以上,芬兰、丹麦、荷兰、瑞士、英国等国,车祸中的车外死亡者达50%以上,日本车外死亡人数则高达62.7%[11]中国车祸的伤亡构成中,车外死亡人数更是达到了66%。可见,良好的汽车设计对减少伤亡事故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而企图把行人与自行车隔开、把自行车与汽车隔开的措施,常常受到空地不足的限制。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国、日本则更是不可能。
另外,虽然技术改良使单位里程的死残率下降了,但轿车主导交通的现实又使得车辆的数量增加了,行驶里程增长了,从而又抵销了这一成就。以美国而论,自197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交通里程增加了90%,而注册的汽车增加了70%。在这个时期,轿车和卡车的使用增加了将近50%,因此,在美国单位里程车祸死亡大大下降的今天,车祸发生的次数以及引起的死亡人数并无明显下降,全国车祸死亡人数仍高达四万多人。
整体而言,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存在着使用操作上的个人性与交通运输的高度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目前从技术上尚难以找到有效解决方法。所以,只要轿车仍是无序运行着的私人的交通方式。只要汽车还在高速行驶,只要汽车仍然是由几吨重的金属制成的,那么其运行过程中巨大的动量就会构成对人的威胁,车祸发生率就难以降下来。
这就是说,发明、制造和改进这种技术的工程师是负有责任的,将这种技术用于工业实践的企业主是负有责任的,允许社会广泛使用这种不安全的技术,并促使这项技术社会化的政府、国会和其他公共决策者们也是负有责任的。尽管这种责任就程度而言可能有多种形式,在法律上可能是刑事责任,它通过惩罚违反者而保护公众利益;也可能是民事责任,它通过赔偿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也可能是伦理责任,它不是通过责罚形式出现,而是通过道德感、良心和灵魂考问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各方面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车祸这种技术应用中导致的不合理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止。
五、车祸是经济增长的必付代价吗?
既然汽车交通技术系统负载着更高的事故危险性,并已经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决策者却能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反而将其为交通发展的主导方式予以鼓励和扶持呢?为什么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已不需要做复杂的预测,而是明明白白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社会有关方面却不承担责任而任其恶化呢?
这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价值准则。
在当今我们这个被称为“经济中轴”的社会,经济增长被当作社会进步与繁荣的标志。尽管不少学者明确指出,财富不等于幸福,经济的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并非成正相关关系,物质的占有和消费也不等于生活的真正意义。但我们当前的主流价值中,仍视利润、商品量和经济增长为一切社会行为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的。汽车商以获取最大利润成为产业的第一要义,政府管理者以经济增长指数和就业人数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在这种以利润和经济增长为圭臬的价值准则下,当经济指数与死亡数字在同涨同落的时候,是降低利润、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以抑制意外死亡呢,还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高速经济增长呢?制造商和政府当局的政府倾向和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以赢利为最高目的的制造商自然不会有改进汽车安全性能的内在动力。对他们而言,一切安全性技术的采用都意味着增加成本,若因成本增加而提高售价又要承担失去市场的危险。因此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厂家是不会主动提高安全性的。相反,倒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将消费品做得更不耐用,更短命。实际上,本世纪20年代通过汽车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A.P.Sloan)“发明”的“人为废弃商品”(Planned obsolescence)策略,便是历史明证。这种策略就是故意制造不耐用商品,使之很快坏掉或过时,从而提高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以达到增加产品销售量的目的。当汽车市场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饱和时,这种策略的使用则达到了极至。制造商在设计汽车时,考虑更多的是美化式样或加大功率、提高速度(这些只会增加事故频率),以此招睐消费者,而不是增强机械性能的可靠性来保护消费者。那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市场上以零售方式进入消费者手中的轿车,有24%是有缺陷的。美国汽车安全中心主任L.道奇(L.Dodge)曾愤然指出:“在1955年7月1日,由三大汽车公司制造的有九年车龄的轿车,有80.7%仍然行驶在公路上,而在1967年7月1日,同样是由三大汽车公司制造的有九年年龄的轿车,仍然能够行驶的则只有55.23%了,这绝非偶然,它显然是人为故意设计的结果。”[12]
对于我们的社会决策者而言,选择这样一种危险的交通方式,也是因为经济价值主导的结果。汽车工业以及相关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驱动力。轿车交通可以带动机械制造、钢铁、橡胶、石油、玻璃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现实经济利益。
车祸自然也会带来经济损失。如近两年我国交通事故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已达180亿元。美国用于汽车死亡事故的费用则达1765亿美元。但这与汽车产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产生的利润相比实在微乎其微了,更何况这笔损失并不由制造商等盈利者直接承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车祸竟然也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服务行业,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医药、整形、警察、律师、保险、汽车修理和丧葬殡仪业等一整套的服务部门,时刻准备着处理事故伤亡的善后问题。交通事故产生了对这些服务的经济需求,使其得到高额利润。遭受残害的躯体和生命竟然能够以这种方式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实际上车祸中的伤残和死亡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成本,可以纳入国家的投入—产出的总预算和决算之中。在市场专制的社会里,人也可以被赋予市场价值,其价值量因国家地区而不同,大约相当于肇事者赔偿给牺牲者的金钱数额。因此,依照经济学的法则,只要车祸的损失低于汽车系统带来的巨大利润,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值得的。
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尊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市场价值,甚至远不如自己制造出的一辆名牌轿车。当机器的市场价值超过了人的价值的时候,当车与人的关系发生颠倒的时候,人们对车祸肆虐漠然视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要将宝贵生命从无情的车祸中解救出来,就必须首先改变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尊重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权利,建立人性化的交通方式,使我们的技术能力服务于人的发展和完善,使我们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改变能够激发并推进人的成长和活力。如同弗洛姆(E.Fromm)所言:“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所有计划的标准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13]
〔收稿日期〕2000年12月26日
标签:死亡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