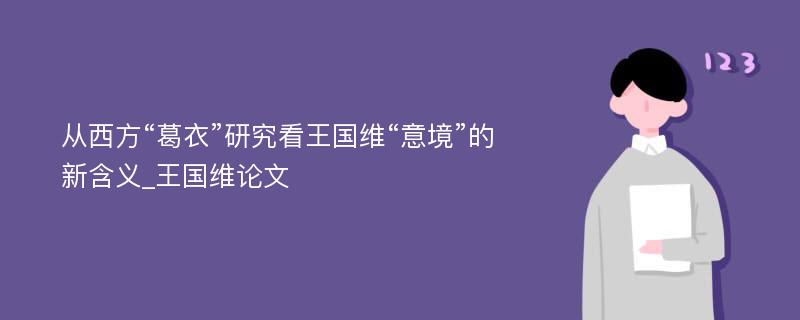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意境论文,王国维论文,新义源出论文,格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7-0107-09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王氏的“意境”说也就难得确解。以往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通过“意境”的传统习惯用法来研讨王氏采用它的取意,二是通过王氏的美学接受探寻其“意境”理论蕴涵的西学因子。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两种研究路径均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前者而言,相关的论著虽然十分丰富,但却无法证实“意境”的传统习惯用法与王氏的使用存在什么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一些学者甚至据此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如王文生就曾指出源出佛家的“境界”与王氏的“境界”没有必然的联系①;蒋寅则更进一步,认为清代以来诗论家对“意境”的使用与王氏不存在什么相通之处,王氏的“意境”根本“不是中国文论自身生长出的东西”。②对于后者来说,曾经几成定论的叔本华影响说,近些年来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陈鸿祥、罗钢都曾撰文指出叔本华美学解释不了王氏“意境”说的理论问题。③肖鹰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完全否定了叔本华影响说,他认为以叔本华哲学为“本”来诠释王国维“境界”说是一个根本误解,王氏“境界”说的“核心是以席勒提出的人本主义理想为核心的诗歌理想,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资源”④。席勒影响说虽然弥补了叔本华影响说的不足,但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是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之上的,这与王氏因主体观照客体方式之不同而产生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很难说存在完全对等或者说直接的承继关系。
平心而论,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对认识王氏“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均颇有助益,但它们的缺陷都在于无法解决王氏“意境”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它既然是中西诗学的合璧,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此一环节得不到合理解释,任何结论都只能说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自然也就难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王氏提出“意境”理论既不是孤芳自赏,他对“意境”的独特阐释与使用必有为时人可以理解之基础,至少应该语有所本,否则便是犯了学术著述的大忌。因此,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意境”在晚清的意义嬗变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事实上,在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中,笔者发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与西学的结合并非王氏的首创,而是源于晚清盛行一时的西学“格义”。这种“格义”才是“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氏只不过是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中国文学的批判实践中去罢了。本文即是通过这一“格义”过程的考察,揭示王氏“意境”新义产生之渊源,以期为解决王氏“意境”说的理论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汤用彤说:“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⑤“格义”一词语出梁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⑥据汤用彤的解说,“格”有“‘比配’的或‘度量’的意思,‘义’的含义是‘名称’、‘项目’或‘概念’;‘格义’则是比配观念(或项目)的一种方法或方案,或者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等”。具体而言,就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习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⑦。可见,“格义”作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种方法,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作用意义。
清末西学东渐与汉晋以来佛教的传入有相似之处,所以“格义”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学界的普遍现象。今人尹炎武在总结刘师培的学术时说他“生平手不释卷,而无书不览。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咸有造述。其为学报,好以古书证新义,如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流,内典与六艺九流相配拟也”⑧。“以古书证新义”非独刘师培而然,其时学界稍知西学者几无不如此。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早期的西学翻译中,被梁启超称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⑨的严复,其译作中以中土义理拟配外来观念者比比皆是,“意境”即其中之一。
据笔者所见资料,严复以“意境”拟配外来观念最早见于《天演论》(1898年)下卷第九篇《真幻》的案语中:
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借思求理,而诐谬之累,即起于思,即识寻真,而逃罔之端,乃由于识。事迹固显然也,而观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实。梦,妄也,方其未觉,即同真觉;真矣,安知非梦妄名觉。举毕生所涉之涂,一若有大魅焉,常以荧惑人为快者?然则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无可疑,而可据为实乎?原始要终,是实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惟意为实乎?盖意有是非而无真妄,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疑,故曰惟意无幻。无幻故常住,吾生终始,一意境耳,集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谓真我者也。特嘉尔之说如此。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其义曰:世间两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果,不得径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⑩
这段话是严复对法国哲学家特嘉尔(今译笛卡儿)《道术新论》一书中心观点的概括,其中即用了“意境”一词,虽不能确知它拟配的具体概念,但大体可知“意境”是指因“心物之接”而产生的各种意识活动与现象。严复以“意境”拟配西方类似的概念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其译事始终,如其1905年所译之《穆勒名学》,“意境”作为译词即频频出现,今摘引数例如下:
1.此而析之至微,将为觉性而非意境。
2.譬如始义为在、为存、为有,而其所以在、所以存、所以有,或自有形,或惟体物,或为意境,无所异也。
3.当知感为意境,而与感我之外物大异。
4.吾云往往者,有不尽然之辞也。盖两物可见,如二人焉,其极似虽至于相乱,不谓同也。独至言心之意境,则恒用之;如云今见某物,使我所感与昨者同,又如吾之所见与某所见正同,甚者或言与之为一。
5.万物固皆意境,惟其意境而后吾与物可以知接,而一切之智慧学术生焉。故方论及于万物,而明者谓其所论皆一心之觉知也。
6.今如吾心忆某物之居某地,则地与物必同时皆呈于意境之中。假使心拟其物已亡,则吾意中只为其地而亡其物。依显,使其物无色而吾意为之色,意境之变在益一物为前无者;而使其物为赤而吾意以为非赤,此非于吾意境中祛前有之一物必不可也。然则不中立例非他,即意境有所相灭者之所会通已耳。(11)
由于严复采取的是一种隐括式的译法,因此上引数例中“意境”并非都对应有具体的英文名词,如例2与例6即是如此。同时,“意境”虽对应有具体的英文名词,但并不是固定的对应关系,如例1对应的是“idea”,例3对应的是“Sensation”,例4对应的是“feeling”,例5对应的是“states of consciousness”,例6最后一“意境”对应的是“mental states”。不过总体而言,“意境”对应的概念范围应如例5所说是“一心之觉知”。
无论在笛卡儿还是穆勒那里,“意境”关涉的都是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如前引例5所说:“万物固皆意境,惟其意境而后吾与物可以知接,而一切之智慧学术生焉”,严复在此段话后的案语中说:“观于此言,而以与特嘉尔所谓积意成我,意恒住故我恒住诸语合而思之,则知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言,此为之的解。何则?我而外无物也;非无物也,虽有而无异于无也。然知其备于我矣,乃从此而黜即物穷理之说,又不可也。盖我虽意主,而物为意因,不即因而言果,则其意必不诚。此庄周所以云心止于符,而英儒贝根亦标以心亲物之义也”。(12)认识论中的“意境”如何能与文学艺术产生联系?其实在西方二者是同出一源,只不过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差异而已。严复发表于1906-1907年间的美学译著《美术通诠》即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该书为英国美学家倭斯弗所著,严复所译仅三篇(13),“意境”作为译词亦多次出现,如《文辞》篇谈“意境”之产生:
世唯两物,曰我、非我。自我而外,一切万物皆非我也。以我而交于非我有二涂焉,一曰由其客观,一曰由其主观。有生息息之倾,皆由此两观觉察身外之万物,以此观念萃成觉身。其一部分由于色界之形质,有有生者,有无生者,交于吾前,受以官窍。其一部分由于法界之意影,来往心象之间,有时与色界之物连类而并呈,有时纯为意影,无关形气之事。顾所观主客不同,而自我以观,非我则一。盖凡可观者,皆非我也。凡物皆有两观,从其在物则为客,从其在心则为主。以客主两观而交于非我,使学者自思之,将见主观之所交,其广远实大过于客观。盖主观之交于非象也,纯以意影,其起伏由于记忆,或由于推籀,或由于记忆推籀二者之杂施互用而得之……夫界说曰:托意写诚谓之美术,意主观也,诚客观也。是故,一切之美术,莫不假客观以达其意境。
与前引赫胥黎讲解笛卡儿的哲学观点加以比照,不难发现倭斯弗探讨的“意境”与笛卡儿所讲的“意境”在产生的根源上是一致的,而倭斯弗这里探讨的就是作为美之渊源的“意境”。倭斯弗指出“意境”产生于主体对“非我”(客观世界)的观照,“非我”虽一,但因观照方式的不同——“客观”与“主观”,会产生不同的“意境”。这种“意境”再经不同的材质呈现出来,便形成了世间所谓的各种艺术,如倭斯弗在《艺术》篇中这样界定“美术”(即今“艺术”):
一凡为美术,皆必有所托以为达者,自营建瓦石之最粗,至诗词韵律之微眇,使非有托,无以为功;二其感人之用,必借径于官骸,而大抵在目之为视与耳之为听;三其有所托以为达,与其有所由以为通,言其大用,期诸感人而已。其感惟何?盖操美术与观听之者两心之相接也。是故,艺林之事,自宫殿楼观之巍巍,至于短什小词之娓娓,以言其物,皆托寓也。托寓云何?官与其物接,其所见所闻者为一物,而所见所闻之外,别有物焉,与吾心为感通也,惟此为美术同具之公德。夫既知其物之公德,则美术界说可试言之,美术者何?曰:托意写诚是为美术。又曰:美术者,以意象写物之真相者也。
这个“美术同具之公德”就是后文所说的“意境”,因为倭斯弗接下来就说:“欲证界说所赅之义,则试取世间美术一一为之分论,约而举之,大抵所可论者有三:一其所托之物质也,二其为接于耳目之涂术也,三其意境之显晦也。”在这三者之中,“所托之物质”是美术借以呈现“意境”的材质,“接于耳目之涂术”指的是美术作用于主体感官的途径,因此均与美术的价值体现无涉,唯有“意境”才是作者与观听者心灵感通的价值载体。如倭斯弗在论述目治美术中的营建(建筑)时说:“试观闳丽之工,游者为之神动,当有以悟相感之所由然,何则?建者意有所寓而呈故也。”而且“意境”之有无多少也是倭斯弗衡量美术的唯一标尺,如其说:“若夫阴阳帅霅、藻绘陆离、天宇之清澄、山川原隰之雄秀而平远,虽皆营建者所得以借资,顾其事无关于巧术,非若他端目治美术,欲使观者移情,恒有所寓之巧智也。盖其故有二:非以象生物动作之事,一也;其成功之坚浑形色,假于所用之材而未尝变之,二也。虽然设为所成之物皆真相,而无有意境之事寓于其间,则大不可。”这就是说自然景物没有“意境之事寓于其间”,因此不得与于美术之列。“意境”虽然带有自足性美学体现的性质,但它却不能单独呈现,必须借助物质材料体现出来,并通过感官传达给观听者。不过,意境一旦通过这种途径展现,则必然受到物质材料的限制而为其所遮掩。这即是倭斯弗所说的“美术可贵,存乎形上,必其事有待于物材弥寡,而后其为术弥尊”。根据所需物材之多寡,他将美术划分为五等,依次为营建、刻塑、丹青、乐律、诗歌,前三者为目治美术,后两者为耳治美术。耳治美术高于目治美术,因为“既为耳治,其所托之物质自少,而非显然可见如前三术者,亦惟其托质之少,其意境之事愈多”。营建为品最下,因其“虽然意寓之矣,而以其有待物材之众,往往意为所掩,而所寓者,有时而不传”。可见,美术的品级实际是由托寓之意境的多少决定的,而且与托质成反比例的关系。
由于倭斯弗的《美术通诠》主要探讨的是语言艺术,所以除总论性的《艺术》篇外,其他两篇均讨论的是语言艺术方面的问题。在《文辞》篇中,倭斯弗指出,“我”之交于“非我”有两种途径:“客观”与“主观”。但他同时又指出:“我之交于非我也,必先有客观之事,而后主观从之。主观者,客观之意影也,然主观虽受成于客观,而浸假客观乃又蒙吾主观之影响,而被其范围陶铸之功。盖吾观物之神智,抚景之欢忻,与一切接时生心之赏会,将与吾读书穷理之所积者,相长而俱深。是故,我之交于非我也,惟善用其主观者,而后有喻客观之微,得客观之实……德意志鉴别家解尔第(Goethe)有言,客之游罗马,其有取而去于罗马者,无一物焉,非其所挟而入于罗马者也?嗟乎!彼游宝山而空手者,以其非怀宝而来客耳。解之为言,不亦深切著明也哉?”因此“两涂之为异”,便形成世间两种不同之文类,如倭斯弗在《古代鉴别》篇中说:“其一,所益我者,在其中所言之事实;其一,所益我者,在其写情叙事之文章。大抵吾读一书,二者之益常兼有之,特轻重多寡异耳。譬之一画,前者其中之景物,后者其中之绚染也;前者一书之质,后者一书之文也……是故,以文质之可分,而创意之文与实录之文区为二类,而所以介绍心灵于万物者,其用固不可偏废也。”倭斯弗原文虽针对的是所有文类,但对文学艺术而言亦复如此。同时,倭斯弗还明确指出文学艺术的“写实”与学术著作存在根本之不同,即“词人之文纯由创意,方其写物,所写者,非即物也,乃其心目中之万物,设观不同,为用亦异……夫立诚,诚不可废,然而诚矣,有官觉之诚,有意念之诚。官觉之诚征于实,为理解所可论;意念之诚集于虚,非理解所可论,此美术所独有之境界也。”
由于笔者遍查资料,亦未能确定倭斯弗的身份,所以无法与原著对照以确定“意境”对应的英文名词。不过根据时人对翻译的相关论述,《美术通诠》中的“意境”应该对应的是“idea”,如王国维1905年撰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
“Idea”为“观念”,“Intuition”之为“直观”,其一例也。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观念”亦然。观念者,谓直观之事物。其物既去,而其象留于心者,则但谓之观,亦有未妥,然在原语亦有此病,不独译语而已。“Intuition”之语,源出于拉丁之“In”及“tuitus”二语。“tuitus”者,观之意味也,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最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Idea”之语,源出于希腊语之“Idea”及“Idein”,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故谓之观;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或有谓之“想念”者,然考张湛《列子注序》所谓“想念以著物自丧”者,则“想念”二字,乃伦理学上之语,而非心理学上之语,其劣于观念也审矣。(14)
王氏讨论的“idea”虽然是“心理学上之语”,但是通过他的辨析可知它与倭斯弗所说的“意境”同出一源,而且在英语中“idea”本身也是一个哲学与美学的核心概念,如朱光潜在讨论“idea”的翻译时说:
idea源于希腊文,本义为“见”,引申为“所见”,泛指心眼所见的形相(form)。一件事物印入脑里,心知其有如何形相,对于那事物就有一个idea,所以这个字与“意缘”(image)意义极相近。它作普通用时,译为“观念”本不算错。不过在哲学上,已往哲学家用这字,意义往往各不相同。柏腊图只承认idea是真实的,眼见一切事物都是idea的影子,都是幻相。这匹马与那匹马是现象,是幻相,而一切马之所以为马则为马的idea。这是常存普在的,不因为有没有人“观念”它而影响其真实存在,它不仅是人心中一个观念,尤其是宇宙中一个有客观存在的真实体。近代哲学家康德与黑格尔用idea字,大体也取这个意义。所以它不应译为“观念”,应译为“理式”,意思就是说某事物所以为某事物的道理与形式。(15)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严复以“意境”对译西学诸概念是典型的“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法”。经过这种“格义”,作为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实际的情况是“意境”的古典内涵被相关的西学概念所取代。这种微妙的意义转换,若非对晚清盛行一时的西学“格义”有相当之了解,是很难觉察得到的。因此,“意境”与西学的融合,或者说它由传统诗学一个不含价值色彩的中性概念,至晚清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本体意味的美学核心概念,可以说“格义”正是其中关键性的一环。没有这一环,“意境”在晚清的意义嬗变便成一无法理解之事。同时,“意境”的这种意义嬗变也得益于严复在晚清西学翻译界的非凡影响,其译著的风行无疑为“意境”的新解新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可能。
陈跃红说:“‘格义’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种早期的互译性策略选择。到了20世纪初,林纾、严复等人对西方文学和思想著述的翻译,从一开始,也基本上是遵循类似的路子,近于原创性地去展开其译解性的‘格义’工作的,那时的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双语性的词典类书籍可以参照。当后世的读者通过他们典雅的古文翻译去接受所谓西学思想和观念的时候,其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学说,而是在经由跨文化对话和双方视域融合以后,在各方面都显出文化的交互性、混杂性和生长性的新东西了。”(16)如果说“格义”始初只是为了便于理解而采取的一种互译性的策略选择的话,那么当这种经过“格义”后的概念重新融入本土思想话语,它实际已脱胎换骨,既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而真正成了一个具有“生长性的新东西”了。王国维“意境”的奥妙与难解全在于此。
王氏在西方美学视域下使用“意境”最早见于《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这是一篇完全以西方理论与运思方式撰写的文章,文中说:“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17)这段话中的“意境”虽然难以确知其理论来源,但从“意境”前面所加的定语“惝恍不可捉摸”以及整句话的表述来看,它与传统的用法已有明显的不同。对比《叔本华与尼采》(1904年)中的话:“今有一物焉,超乎一切变化关系外,而为现象之内容,无以名之,名之曰‘实念’。问此实念之知识为何?曰:‘美术是已。’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由其所寓之物之区别,而或谓之雕刻,或谓之绘画,或谓之诗歌、音乐,然其惟一之渊源,则存于实念之知识,而又以传播此知识为其惟一之目的也。”(18)稍加分析则不难发现王氏所说的“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美术“所寓之物”,也即“静观中所得之实念(Idea,今译为理念)”——美的“惟一之渊源”。
王氏将“意境”的新义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中,首见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托名樊志厚撰的《〈人间词〉乙稿序》。这篇序文是王氏“意境”理论成熟的标志,在短短的一篇序文中“意境”竟然出现18次之多,而王氏撰于光绪丙午(1906年)三月的《〈人间词〉甲稿序》,正如王文生所指出的那样:“却始终没有提到‘意境’、‘境界’的概念。”(19)王氏《乙稿序》声称他是“夙持此论”,这说明其“意境”理论的形成时间是介于《甲稿序》与《乙稿序》撰成时间之间。王氏在《乙稿序》中这样表述他的理论: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20)
蒋寅针对这段话分析道:“这段话看似脱胎于前人的情景二元论,其实思想基础完全不同。情景二元论着眼于物我的对立与融合,处理的是吴乔所谓‘情为主,景为宾’(《围炉诗话》卷一)的关系;而王国维的‘观我’、‘观物’,却有了超乎物和我之上的观者,也就是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因为有主体,自然就有了意识对象化的意境。情景二元论虽也主张诗中情景的平衡和交融,却没有不可偏废的道理……而观我、观物则不同,既然不存在没有对象的纯意识,则无论观我或观物都是一种‘意’之境,自然不能偏废。这种基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文学观,不仅给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带来主体性的视角,还促使他从本体论的立场来把握意境,赋予它以文学生命的价值……这正是王国维对‘意境’概念最大的改造或者说曲解。”(21)蒋寅虽然准确地指出了王国维“意境”蕴涵的西学内涵,但他不知道“意境”概念的改造已由严复率先完成,王氏只不过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去罢了。
实际上,王氏不唯“意境”一词与西学“格义”存在直接的关系,其整个理论构成几无不如此。如其《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意”与“境”对应的应如《文学小言》中所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22)可见在王氏那里,“意”与“境”、“情”与“景”这些源自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都通过格义与西学产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不明此点,势必难以索解。(23)“观我”与“观物”也源出西学的格义,如其《孔子之美育主义》中说:
至叔本华而分析观美之状态为二原质:(一)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二)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何则?由叔氏之说,人之根本在生活之欲,而欲常起于空乏。既偿此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苟吾人之意识而充以嗜欲乎?……然吾人一旦因他故,而脱此嗜欲之网,则吾人之知识已不为嗜欲之奴隶,于是得所谓无欲之我。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苏子瞻所谓“寓意于物”(《宝绘堂记》);邵子曰:“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有我于其间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七)此之谓也。其咏之于诗者,则如陶渊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24)
王氏在这里以邵雍的“以物观物”来阐释叔本华所说的“观美”境界,亦是典型的格义之法。邵雍的“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连同陶渊明的诗例,后来又被移植到《人间词话》中,由此可知王氏对“观我”与“观物”的使用已均非本义,而是通过“格义”与西学产生了直接联系。因“观我”与“观物”之不同,遂有“有我之境”(亦即“造境”)与“无我之境”(亦即“写境”)之分,前者“意余于境”,后者“境余于意”。这两个概念学界历来聚讼纷纭,其实“观我”与“观物”对应的就是《美术通诠》中的“主观”(“从其在心则为主”)与“客观”(“从其在物则为客”)。依据倭斯弗的理论,“我之交于非我有二涂焉”,一为主观,一为客观,此“二涂”必然同时存在,且只有多寡之分,而无偏废之理。因主客观之事的多寡,形诸文字则有所谓“创意之文”与“实录之文”的分别——此单就文学艺术而言。这与王氏“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内涵可以说完全一致。王氏《人间词话》手稿针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述有“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25)一句,在定稿中被抹掉,这抹掉一句中的“主观”与“客观”无疑直接暴露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庐山真面目。(26)
需要说明的是,王氏使用的概念中还有与“意境”近似的“境界”,二者常交互使用,而未加以区分。据魏鹏举考证,王氏发表于1904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境界”作为译语出现,对应的英文是“state”,并认为“此虽译语,却与美学已有了密切关系,已初步具备了后来《人间词话》中一些含义”。(27)在严复的翻译中,“state”也往往被翻译为“境”或“境界”。但是在西方,“state”从未作为独立的美学概念出现过——如王氏标举的“境界”。而且据《人间词话》手稿“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28)语可知王氏所说的“境界”也是一种“意”之“境”,正如前文讨论严复的翻译那样,“state”只有与表“意”的“consciousness”或“mental”配合构成词组才成为一种“意”之“境”。所以,“state”不可能与王氏的美学概念“境界”产生直接的联系。另据与王氏有通家之好的罗振玉后人罗继祖说:“‘意境’、‘境界’一字之异,同出于静安先生笔端,而有前后之不同(序在前,《词话》在后),两者实在没有太大的差别,大概后来静安先生决定用‘境界’。”(29)
综上可见,王氏《乙稿序》不单关键性的术语“意境”与严复翻译的《美术通诠》完全一致,而且整个理论构成也如出一辙。严复翻译的《美术通诠》又恰在王氏《甲稿序》与《乙稿序》撰成期间发表,这很难说是出于某种巧合。即便退一步说,王氏“意境”新义之产生,与严复的“格义”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也必然受到其时盛行之格义现象之影响,当无疑义。同时,通过前文论述亦可看出,“意境”与西学概念的拟配并不是固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它并非专指某一家的美学观点,那种认为王氏的“意境”说完全来源于叔本华或席勒的美学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它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具有极其相似的关系。(30)就王氏“意境”说的实质而言,其基本理论应该取自于西方的唯心主义美学流派(31),其核心内涵当如该派美学概念中的“idea”。关于该派美学的基本特点,蔡元培在《美学的趋向》(1921年)一文中说:“在理想派哲学上,本来有一种假定,就是万物的后面,还有一种超官能的实在;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全从现象构成,还有一种理性的实体……所以美术的意义,并不是模拟一个实物;而实在把很深的实在,贡献在官能上;而美的意义,是把‘绝对’现成可以观照的形式,把‘无穷’现在‘有穷’上,把理想现在有界的影相上。普通经验上的物象,对于他所根据的理想,只能为不完全的表示;而美术是把实在完全呈露出来。这一派学说上所说的理想,实在不外乎一种客观的普通的概念,但是把这个概念返在观照上而后见得是美。他的概念,不是思想的抽象,而是理想所本有的。”(32)蔡氏所说的“理想派哲学”就是今天的“唯心主义”(idealism)哲学,所谓能体现美的“理想”(也称“实在”)就是“idea”的转译(33),与作为“格义”名词的“意境”具有共同的语源。所以在近代学人的文艺批评中这两个概念常被对等使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氏“意境”说理论内涵的真实来源。借用西方一般美学理论来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这也符合清末文艺批评界的常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与中国本土的理论相通,同时也更容易为时人所理解与接受,王氏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格义”的出现在两种不同文化交流的初期具有必然性,其初衷虽然是为了便于理解与接受外来概念,但是生长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概念在相互拟配时不可能完全做到“允惬”的地步,更多的情况恐怕如西晋名僧道安所说是“于理多违”。(34)既然“格义”难以做到“允惬”,其结果势必造成概念理解上的混乱。所以无论是汉晋以来的佛教输入,还是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格义”都是一种过渡性的方法,随着新方法的兴起而很快被取代。正如王国维所说:“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所不能逮。而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若夫粗陋佶屈之书,则固吾人之所唾弃,而不俟踌躇者也。”(35)严复以古语拟配西学的“格义”翻译方式显然不可能像“日本已定之语”那样精密,从掌握与理解西学的深义或核心来讲,严复的翻译方式必然会被取代,这也就标志着“格义”作为一种翻译方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或“变得不那么重要”。(36)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格义”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最终为历史的大潮所淹没。但是严复“格义”的译解精神并未因此而消逝,而是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古语新用”与“古书新解”,也即人们常说的“反向格义”。王国维对“意境”的使用即属后一种形式。
王氏以“意境”之新义阐释证解中国本土固有之文学材料,在当时因有严复的“顺向格义”在先,时人或不以为异。然而过了近二十年后,严复的“格义”已不为世人所知(37),“意境”的新义自然也就被归为王氏的创造,并随着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进程而呈日渐拔高之势。但是这种评价王氏本人似乎并不认同,据时人回忆,王氏晚年不仅因撰有《人间词话》而深以为悔,而且当有人问及论词主张时,甚至还予以矢口否认。(38)这种鲜明的对照是颇耐人寻味的。
王氏生前好友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其“第三目”云:“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陈氏这里虽未列举《人间词话》,不过既言“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则理应包含在内。“互相参证”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的方法,也即广义的格义,陈氏研治魏晋佛学深有造诣,又首揭“格义”之奥义,对王氏之治学方法自必深有体会,所论当非泛泛。王氏之学说正如陈氏所评“或有时而可商”,其价值“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而示来者以规则也”。(39)
从根本上讲,王氏的批评范式实际未脱晚清盛行一时的“以西例律我国文学”(40)的牢笼与范围,虽然他使用的“意境”源出中国,但其内涵实已西化。他将一个“格义”名词脱离对译西学的历史语境,重新纳入本土文论话语,虽使这一古语得以“重生”,却不可避免地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今日关于“意境”美学内涵阐释的分歧,及其被日渐拔高的批评趋向,均可或多或少找到它与王氏“意境”理论之间的联系。因此,澄清王氏“意境”新义的生成语境及理论来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本文详论“意境”一词之格义历史,其意仅在揭示王氏“意境”之渊源所自,以为重新论定其学说之基,无意对其理论作出全面的评价,相关问题只能俟诸他日另文详论。
注释:
①王文生:《论情境》,第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②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3)。
③两人观点分别参看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第18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罗钢《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断;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探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
④详参肖鹰:《被误解的王国维“境界”说——论〈人间词话〉的思想根源》,载《文艺研究》,2007(11)、《自然与理想:叔本华还是席勒?——王国维“境界”说思想探源》,载《学术月刊》,2008(4)。
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第174—17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⑥慧皎:《高僧传》,第1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⑦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石峻译,见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第283—2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⑧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刘师培全集》(影印本),第1册,第1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⑨严群:“序”,见[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⑩[英]赫胥黎:《天演论》,第69—70页。
(11)(12)[英]约翰·穆勒:《穆勒名学》,严复译,第22、47、49、67、69、246、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引文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13)这三篇依次名为《艺术》、《文辞》与《古代鉴别》,分载于《寰球中国学生报》第三期(丙午九月,1906.10)、四期(丁未二月,1907.3)、五六合期(丁未五月,1907.10)。下文所引该著只在文中标明篇名,不再一一注明。
(14)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2册,第3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5)《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6)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20)《王国维集》,第1册,第182、245—246页。
(18)《王国维集》,第2册,第175页。
(19)王文生:《论情境》,第13页。
(21)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3)。
(22)《王国维集》,第1册,第23页。
(23)蒋寅就曾针对这段话说:“这就属于很糊涂的说法。分析文学的基本要素,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思考方式,而以情景为二要素却是中国诗学的老生常谈,且只适用于古典诗歌,怎么能泛化到整个文学呢?”见《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
(24)《王国维集》,第4册,第3—4页。
(25)(28)王国维:《〈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影印本),第65、6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6)王国维在《莎士比亚传》(《王国维集》,第2册,第8页)中说:“当知莎氏与彼主观的诗人不同,其所著作,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称莎士比亚的客观描写为“无我之笔”,亦可为佐证。
(27)魏鹏举:《王国维境界说的知识谱系》,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5)。
(29)罗继祖:《王国维与樊炳清》,见《鲁诗堂谈往录》,第29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0)王柯平在近来发表的《境界“为探其本”的深层意味》(《学术月刊》2010年3月号)一文中指出王国维的“境界”在思想资源上“借鉴了席勒的‘审美状态说’,叔本华的‘直觉观念说’和康德的‘审美观念说’”。这一研究说明王氏的“境界”在思想资源上并不是专主某一家美学观点,其理论构成与诸家学说的相似性与其说王氏“境界”是吸收他们的学说,倒不如说王氏借用的西方美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特点,因为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王氏的“境界”既能与诸家学说相通,又不是完全对等的微妙关系。而且这也与“意境”在晚清“格义”西学概念的实际情况恰相符合。
(31)参看叶秀山:《也谈王国维的“境界”说》,见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32)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参见史群编:《新编日语外来语词典》(修订本),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4)慧皎:《高僧传》,第195页。
(35)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集》,第2册,第307页。
(36)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2)。
(37)《美术通诠》作为清末唯一一部通论性的美学译著,迄今为止竟未受到学界的重视,皮后锋曾不无感叹地说:“这是严复一种重要的未竟译著,大多数从事严复研究的学者至今尚未发现这一译著,更谈不上利用。”(皮后锋:《严复大传》,第30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美术通诠》被历史遮蔽如此,也难怪王国维“意境”的理论来源不为人知。笔者即因阅读皮后锋大著,深感此材料之重要,即与之联系,承蒙其慷慨惠赐影本,而得有此种发现。
(38)参王水照《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的相关论述。
(3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见《陈寅恪集》,第246—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0)1905年《新小说》第7号发表了署名定一的《小说丛话》,其中就明确提出了“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批评观念。事实上,在诗歌、散文及戏曲领域,这种批评观念与方法在晚清也同样十分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