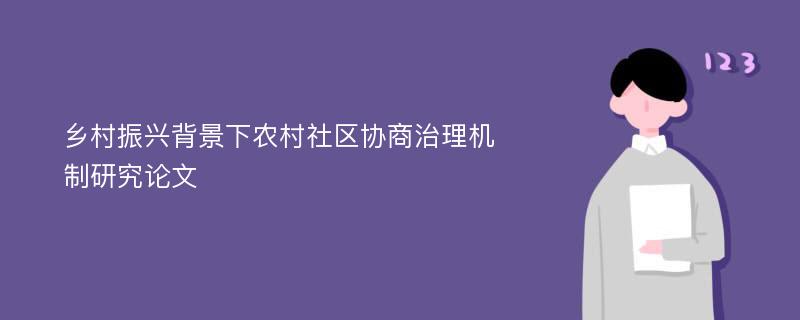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张 锋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200233;上海财经大学,上海200433)
摘 要: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 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认同性整合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社区治理不同程度存在基层党建薄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农民利益诉求不畅等问题。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多重利益整合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 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对推动乡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文献梳理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关键。 协商治理是协商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融合互动的成果,哈贝马斯指出协商沟通在民主治理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理性的协商能够实现偏好的转移和价值的认同,培育社会资本,建构公共性[1];亨德里克斯认为需要强化协商民主的整合性研究,注重协商民主机制之间的衔接和互动[2]。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3]。 协商民主与治理具有逻辑上的契合性、过程上的连接性、价值上的统一性和主体上的互动性,对开展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建构性,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章荣君认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能够推动精英主政向协商治理转型,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4];季丽新认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利于巩固党组织核心地位、防止村干部腐败、培育现代新型农民、维护农村稳定[5];何包钢认为通过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建构理性、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农村民主发展方向[6];谈火生认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理念偏差、农村公共领域发育不充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规则、程序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7];张国献认为流动性的农村社区遭遇协商主体 “虚置化”、协商渠道 “堵塞化”、协商会议 “形式化”、协商成本 “高企化”、协商监督 “短缺化” 等困境[8];胡永保提出应完善协商制度及程序规则,保障协商主体的平等,培育农村社区协商主体的民主素质和协商技能[9];马奔强调应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协商基础、完善协商制度、建构协商机制、健全协商法治化路径、发展农村网络协商[10]。
以上成果为深化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但还存在尚需深化拓展的空间:一是尚需加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性整合机制、功能性整合机制和认同性整合机制的功能研究;二是尚需加强农村社区协商、农村社会组织协商、乡镇政府协商、乡镇人大协商等制度的系统性研究,力求在我国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内,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和衔接联动机制等。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整合机制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它具有多重利益整合功能,从民主参与维度上能够促进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性整合,从多元共治维度上能够实现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性整合, 从价值重构维度上能够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认同性整合,并且三种整合机制之间具有良性互动和协同共进的逻辑关系。
1.民主参与: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性整合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不高,这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农村社区民主参与能够激活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农民利益诉求、民主参与的组织化、理性化和制度化。其一,促进农民利益诉求的组织化。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机制是党内公推直选和村民直选,农民主要通过村两委组织实现利益诉求,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利益诉求的组织化问题。 但是,这种以农村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为载体的乡村治理是一种存量民主,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约束较多,不利于农民持续性的利益诉求和民主参与。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增量民主的形式[11],嵌入到农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之中,以党内协商、村民自治协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监会)、农村社会组织协商等方式,提升农民利益诉求的组织化水平。尤其是以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农村社会组织开展的民主协商,拓展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主体,丰富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内容,创新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形式。其二,提升农民利益表达的理性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利益分化等现象加剧,农民的权利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民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还有待于提升,不少农民缺乏理性表达诉求和协商沟通的意识和能力。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通过建构丰富多样的协商性平台,充分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在一个开放、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利益诉求、利益表达,通过农民主体之间的协商沟通来提升农民利益表达的理性化水平。其三,推动农民利益参与的协同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基础是选举性民主和自治性民主,如何激发选举性民主和自治性民主的制度功能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通过协商性民主的制度性嵌入,弥补了农村选举性民主和自治性民主的局限,缓解农村 “公推直选” 和 “村民直选” 带来的 “民主陷阱” 和“治理危机”,破解了农村自治性民主中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 “形式桎梏”,推动农村选举性民主、自治性民主和协商性民主的协同联动,提升农民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利益参与的系统性、衔接性和整体性。
周祖谟先生指出,“禅母等韵图列为正齿音三等。禅母古音,黄侃音略归之于定母,高本汉之《汉语分析字典》则考订禅母之古音d,与定母相近。”[4]周先生运用经籍异文材料证明了禅母与定母的关系最为密切,郭店楚简中也是如此,共有5例。
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民主机制,应体现规范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功能。 但是,我国部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随意性较大,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平台和方式不健全,关于 “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和怎么协商”,缺乏制度化保障和清单化管理;协商还没有贯穿社区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协商结果的公开、监督、应用及反馈机制还不健全,制约了协商治理的质量和效率。
2.多元共治: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性整合机制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处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整体性转型和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性转型的过程之中,治理主体的结构和能力都有待于优化和加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封闭,大多仍是传统的农村两委组织,协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代表性、专业性不够,缺乏对乡村社区中乡贤、老党员、“两代表、一委员” 等本土资源的深度挖掘,以及乡村社区外部治理资源(如律师、专家、社会组织等)的制度化吸纳,导致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公共性、公益性和专业性不足。 同时,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主体能力不强现象严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确定协商议题、协商规则、协商程序、协商形式、协商过程、协商成果应用等环节的组织力、引导力、号召力、影响力不强,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农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技能和素养不够,制约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发挥和价值引领。
例如,对陈述性知识——细胞器,教师可从各细胞器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联系将其结构化,并以图解形式呈现。教师还需要适时地进行课堂小结,对教学内容总结归纳,反思与升华,促成教学内容结构的生成性与开放性,有助于学生的第二次笔记与第三次笔记。在此例中,教师可以设置问题: 图中的序号分别代表什么结构或过程?请解释唾液淀粉酶的分泌过程。胞吐到细胞外是否一定是大分子蛋白?细胞是如何控制分泌蛋白的合成与分泌的?
3.价值重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认同性整合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还具有重构农村价值、文化、信仰等功能。 要强化农村社区的软法之治,培育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构建农村社区的精神共同体,以协商治理促进农村社区的认同性整合。 其一,强化农村社区软法之治。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自治、德治、法治、共治的统一,重视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等 “软法” 的功能,要真正发挥农村 “软法” 的认同性整合功能,要在 “软法” 制定的过程中尊重农民的权利、利益、风俗、习性,“软法” 规则得到村民的参与、认同和接纳,符合村民的生活常识、惯例、习俗等。而这种建立于全体村民的充分协商、沟通、互动和讨论基础上的 “软法”,能够促进农村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理性、协商理性、价值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统一,真正发挥 “软法” 的引领、规范、激励、约束的功能。 其二,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社区善治的基石,建构在信任、互动、网络、情感、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来自村民的理性协商、合作共治和心理认同,来自农村社区组织公共性的成长,来自社区意识、社区记忆、社区认同的整体性建构。 村民通过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监会等协商性平台参与社区自治,开展协商沟通,可增加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村民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互动。 通过农村社区组织内部的协商,社区组织之间的协商以及社区组织与农村两委的协商,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为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提供原动力和保障力。 其三,建构农村社区精神共同体。 随着农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农村社区的利益矛盾冲突加剧,亟需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能力,化解农民之间、农民与村两委、农民与基层政府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种种矛盾。 开展农村社区协商,能够化解多元主体之间的矛盾,找到多元主体之间的 “最大公约数”。
新闻发布会由滕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峰主持。在新闻发布会上,滕州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农业局局长李广耀介绍了滕州马铃薯产业融合发展和节会有关情况。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实践中还面临一些困难瓶颈,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理念存在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失衡,协商治理法治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机制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衔接、互动、联动不够等。
贾承造:从天然气供应方面来看,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速也在加快。2017年,世界天然气产量3.68万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达到供需平衡。6大产气国中,美国在页岩气增长的推动下生产天然气7345亿立方米,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气国;俄罗斯天然气产量6356亿立方米;伊朗产量为2239亿立方米;中国天然气产量1480亿立方米,成为第六大产气国。
1.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理念存在偏差
涉众型经济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为社会资金供需间的矛盾,为了有效的解决社会融资问题,部分中小企业只能选择向社会进行非法筹资,而由于缺乏资本保证和监管,导致资本的风险加大,如果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出现资金链的断裂,投资人的投资难以保证会返还。所以在对这类犯罪的预防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对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机制的完善。虽然我国当前面临着外资银行的挑战,应该加大对民间金融的发展,但是由于民间金融发展中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同时配套制度不完善,如果盲目的开展民间金融,极容易导致出现集资诈骗行为。所以当前金融制度的改革中,关键还是要注重对市场经济环境中金融活动的监管。
2.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主体的结构不优、能力不强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多元主体的共治,激活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活力和动力,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多元主体的共建、共商、共治、共享。其一,推动农村社区共治主体多元化。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途径是建构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性平台,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尊重既有制度结构的前提下[12],通过建构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乡贤会、老年协会等协商性制度平台,吸纳农民、农村社会组织、乡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驻村机构的参与,突破了既有农村社区共治的主体局限,完善了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其二,探索农村社区共治载体多样化。传统农村社区共治的载体主要是党支部和村委会。 协商性共治平台的构建,创新了农村社区共治的组织载体,出现了自治性民主范畴内的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监会等,创新了农村社会组织协商载体,产生了农村老年协会、乡贤理事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社会组织等协商性主体。 其三,强化农村社区共治程序规范化。 协商民主既是一种民主形式,更是一种社区共治的机制,从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程序、协商形式、协商反馈、协商监督等都有一系列的制度性规范,能够保证农村社区共治的质量和水平。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量的人才、资金、资源、项目涌入农村,通过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协商共治机制,可以提升农民民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农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
3.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内容失衡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要特别重视党组织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其一,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内协商引领社区协商的方向。加强基层党组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范化水平,尊重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引导党员参选村民代表及议事代表,村党组织成员可以兼任议事会代表,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中的领导力功能。其二,强化农村党组织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题、主体、内容、形式、程序和成果应用等方面的引导性。在协商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广泛听取村民、农村社会组织、相关利益主体的意见建议,引导协商议题形成;在协商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协商的主体、内容、形式、程序要严格规范,确保参加协商的主体符合协商内容,推动多元利益主体充分表达诉求,严格遵守协商程序,按照协商议事规则形成书面的协商意见;在协商结束后,要及时公布协商成果,如果存在异议的,要进行必要的反馈说明,并监督相关责任主体落实协商成果,定期对协商意见进行评估考核。 其三,完善区域化党建机制。 针对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结构不优、能力不强的问题,以区域化党建为抓手,整合区域服务资源,鼓励驻村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其他机构参与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提升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能力,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格局和机制。 如江苏省张家港市探索以 “党建引领+议事平台” 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议事会实现对民意的制度性整合,既是体制内的一种深化和拓展,也是体制外的一种激活和吸纳,激活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实现了农村社区治理的 “四个有、六个化” 目标(有方向、有底线、有秩序、有活力;党引民治实效化、社区协商制度化、基层治理法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服务体系社会化、信息资源统筹化)。
4.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
第一,由各个行政单位来负责项目的申报。在项目前期研究阶段,行政单位要在项目实施前期做好一系列的文本研究,精心准备申报材料。第二,教育主管部门对上报的项目进行初次审查,结合年度预算编制的要求、基本财务安排、单位财务管理情况、发展规模等对单位申报的资金项目进行综合审批。第三,教育主管部门要部门预算报告给同级财政部门进行审核,在审核之后将最终复批结果传递给下一层部门。
5.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联动不够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能够有效激活我国政治制度的治理资源,实现协商民主体系的联动、嵌入、衔接和融合。 “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 ”[15]但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大多还没有嵌入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更多地是作为农村社区解决村民自治瓶颈的一种制度安排,缺乏与乡镇人大制度、乡村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社会组织协商等良性联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用村民议事会取代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等情况。
瓦拉德斯指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 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 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 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13]随着农村社区转型的加速, 为了更好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果, 不少地方都进行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从整体上看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对协商治理理念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偏差。 不少基层干部主要把协商治理作为一种工具、手段和方式,更关心农村工作的推动和落实,普遍存在过分重视协商治理的 “工具理性”,忽视协商治理的 “价值理性” 的现象,比较关注协商的结果、形式和方式,忽视协商的过程、规则、程序及协商结果的公开、评估、监督和反馈,甚至出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协商治理的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 转移治理风险、 进行权力寻租的案例。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的系统建构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关键要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而协商民主治理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机制,能够促进农民利益诉求的组织化、农民利益表达理性化、农民利益参与的协同化,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制度性整合;能够推动农村社区共治主体多元化、共治载体多样化、共治程序规范化,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功能性整合;能够强化农村 “软法” 之治,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建构农村社区精神共同体,实现农村社区的认同性整合。所以,应充分重视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 “工具性价值” 和 “目的性价值” 的统一,坚持理念上的民主性与协商性,规范上的程序性和操作性,形态上的有效性和多元性,环境上的兼容性与扩展性,资源上的延续性与创新性,战略上的内生性与移植性,推动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6]。
1.强化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纳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反映强烈的实际困难和矛盾纠纷,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在农村社区推进落实情况,各类协商主体提出的协商需求以及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纳入协商的议题等,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公共性、社区性和政策性的特点。 但是,实践中农村社区协商的内容面临结构性失衡,表现为议题大多是 “自上而下” 形成,主要是为了完成乡镇党委、政府的行政性任务,是一种 “自上而下” 的权力逻辑和实施路径,缺乏协商应有的互动性、回应性和过程性,而真正涉及村民核心利益,反映农村社会矛盾和治理风险的议题较少,由村民 “自下而上” 形成的协商议题不多[14];征询型、听证型和协调型的协商议题较多,而关涉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公正性的决策型、评议型的协商议题较少,农民参与协商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2.构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要以农村社区协商性治理平台为依托,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级基层协商格局,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动力和潜力,建构农村社区多元参与的共治机制[17]。 其一,充分挖掘农村社区治理本土资源。 建立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充分挖掘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本土资源。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各种地缘、血缘、姻缘都能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调动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等新乡贤的主动性,发挥他们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其二,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性主体,它是乡村社会分工、利益分化的产物,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公共性、专业性和公益性,有很强的凝聚力、整合力和引领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农村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农村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商、沟通、互动,推动农民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利益参与的组织化、理性化。 其三,结合协商主题,引入专家学者、律师、外来群体代表等外部性力量。 为应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应围绕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难点、痛点、堵点等瓶颈问题,引入专家学者、律师、外来群体代表等外部性力量,进一步丰富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内涵,优化协商治理的结构,健全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体系。 如江西都昌县探索将基层协商民主 “下沉” 到自然村,吸收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老复员退伍军人参与社区协商治理,克服了由于村委会管理幅度过大、行政色彩过浓而导致自然村层面群众自治的 “空转” 现象,推动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3.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内容的规范化保障机制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重点是强化协商治理内容的规范化, 真正把与村民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纳入协商治理机制。 其一,强化 “自下而上” 的议题产生机制。 为避免出现将农村社区协商单纯作为推动乡镇工作和村两委工作的形式,提升协商议题的广泛性、公共性、代表性,应完善以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老年协会、农村社会组织为主体的专题协商,听取农村社区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和建议,将协商议题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主要内容,形成 “自下而上” 的议题产生机制,促进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 “激活” 功能和 “吸纳” 功能的统一。 其二,重视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矛盾突出的决策型协商、评议性协商。 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性、表达权和监督权,拓展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形式和类型,加强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性协商、评议型协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农民对农村社区治理的监督机制,形成社区协商治理的参与机制、倒逼机制和问责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共治和善治。 其三,完善协商成果的公开、应用、监督、反馈机制。 农村社区协商是一种公共协商、民主协商、参与协商,是培养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要载体。 影响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效果的重要机制是信息公开机制、成果应用机制、监督反馈机制。 农村社区协商要在阳光下运作,尊重协商中少数人的意见,健全反馈解释机制。 针对当前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新问题,如农村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环境综合整治、农民心理健康问题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农村社区网络协商治理新机制。 如浙江省余杭区探索 “1+3”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模式,打造 “一个协商主体(农村社区邻里协商议事中心)”、“三个协商要素(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性整合,落实 “谁来议、议什么、怎么议、规范议、有效议”,逐步实现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4.完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法治化支撑机制
坚持法治为本,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探索清单化的协商治理制度,强化对村民民约、自治章程的深度协商,培育农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资本。 其一,以清单化的形式明确社区协商治理的内容。 为提升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在法律、法规不易修改的背景下,探索运用负面清单、正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形式,对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主体、内容、方式、载体、规则、程序进行规范,强化对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经验的总结、提炼,逐步将成熟的经验做法转化为立法和政策。 其二,强化对乡规民约、自治章程的协商。以乡规民约、自治章程为代表的软法,它根植于农民的生活习惯、习俗、习性,建立在农民之间深度信任的基础之上,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是农村社区协商的制度成果,也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心理基础,具有很强的规范力、约束力、监督力。其三,积极培育农村社区资本。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原动力来自对村民自治的信任、合作、理解、互动和协商,通过协商治理形成以社区记忆、社区意识、社区情感、社区认同、社区精神为内容的社区资本[18],强化对村民行为的价值引领、情感共鸣、行为规范,建构农村社区精神共同体,推进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中自治、德治、法治的良性互动。 如上海市金山区探索用法治思维完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 引入法律顾问参与农村“村规民约”“自治章程” 的协商、制定,实现对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清单化、法治化、乡土化,促进党建引领下的农村社区 “自治、法治、德治” 的统一。
5.构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理念、机制和制度只有嵌入到乡村治理的制度之中,融入到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结构,才能切实焕发出持续的生命力。 其一,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衔接联动。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制度成果,既符合农民的心理认同,又有法律上的制度保障,是一种有效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而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是为了促进农村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理解、互动,提升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有效性。 应坚持将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村民自治机制衔接联动,推动农民议事会、农民理事会、老年协会等协商治理组织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之间的衔接,激活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强化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韧性。 其二,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与乡镇人大协商的衔接联动。 针对农村社区协商治理过程中有可能超出村级组织解决的范围和回应能力的一些共性议题,需要将具有代表性、关键性、重要性的议题上升到乡镇政府层面。 乡镇是我国五级政府体系的一级,乡镇人大是权力机关,拥有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选举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副镇乡长的权力。要充分借助乡镇人大制度(人大代表联系制度、人大代表的选举权、质询权、罢免权等)的资源,实现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与乡镇人大制度权力实施的衔接联动。 其三,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与农村社会组织协商的衔接联动。 农村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主体,它往往代表某一领域的农民群体利益,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老年协会等。应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内部的协商、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社区其他主体的协商,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提升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公共性、专业性和公益性[19]。 如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充分立足农村社区协商性平台,发挥乡镇人大的权力机关功能,对于村级民主恳谈会上意见分歧、争议较大的事项,由乡镇政府提请人大主席团召开镇人大代表会,由乡镇人大代表审议表决做出决定,实现村级协商与乡镇人大制度的衔接互动。
五、结语与讨论
综上所述,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和回应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创新、优化:其一,拓展了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 改变传统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代表、村民这种纵向的治理,吸纳了农村社会组织、专家、律师等主体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实现了乡村治理对社会力量的 “激活” 和 “吸纳”。 其二,创新了农村社区治理的协商程序。基于协商民主的制度性嵌入,从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反馈、协商监督入手,健全系统化的协商程序,培育村民的理性精神和民主能力,建构农村社区资本和公共性。 其三,优化了农村社区治理的格局。通过农村社区协商与乡镇人大协商的互动、衔接,优化了政府治理、村民自治、社会协同的良性格局,促进了农村社区自治、德治、法治和共治的协同联动。
当然,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建设,需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厘清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边界问题,即哪些议题更适合协商治理解决,哪些议题不能纳入协商治理范围。 不能以协商治理为由突破法律、法规的要求,更不能以协商治理的方式损害农民、村集体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合法权益。 二是如何保障协商治理过程中 “少数” 村民的利益。 协商是一种理念和价值,更是一种能力和权利,乡村精英更易于操控社区协商治理的议题、程序、流程、结果等,要避免协商治理中的 “精英主义”,防止忽视或损害 “沉默的少数”。 三是如何提高协商治理的效率。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乡村治理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沟通、博弈、互动都需要巨大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20]。 所以,要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大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挖掘农村社区治理的本土资源,激发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活力,系统构建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和衔接联动机制。应将协商治理的理念嵌入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社区治理之中,科学界定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内容,规范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形式,完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机制;充分激活乡村社区治理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注重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开放性、规范性和均衡性,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共同体;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乡村政治制度的衔接和互动,提升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的整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Carolyn Hendriks. The Ambiguous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Refer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Jubilee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ctober ,2002.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章荣君.从精英主政到协商治理: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15,(5):75-76.
[5]季丽新.中国特色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创新的典型案例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53-54.
[6]何包钢.中国农村从村民选举到乡村协商:协商民主试验的一个案例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2017,(4):98-99.
[7]谈火生.混合式代表机制:中国基层协商的制度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18,(12):39-40.
[8]张国献.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现实逻辑、制度导向与实践旨趣[J].浙江社会科学,2018,(12):149-150.
[9]胡永保,杨弘.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1):124-125.
[10]马奔,程海漫,李珍珍.从分散到整合: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2):92-93.
[11][澳大利亚]约翰·S·德雷泽克. 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 丁开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2]王岩,魏崇辉.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6,(7).
[13]Jorge M. Valadez.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 -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M].USA Westview Press ,2001.
[14]马奔,程海漫,李珍珍.从分散到整合: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2):66-67.
[1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6]唐鸣,魏来.协商民主的生长逻辑——中国经验的整体性视角和理论研究的整合性表达[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5):76-77.
[17]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审议民主意味着什么[A].载谈火生主编.审议民主[C].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8]John, Parkinson, and Mansbridge Jane. Deliberative Systems: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9]武中哲,韩清怀.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8-19.
[20]张锋.环保约谈:一种新型环境法实施制度[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4):78-79.
Study on th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Rural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Fe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are some bottlenecks and shortcomings in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such as weak party build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low degree of farmers'organization,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weakening and alienation of villagers' autonomy, poor demands for farmers'interests, increasing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rural areas, and depresse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ural areas. It is urgent to draw on new governance theories, tap new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m.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s a democratic governance mechanism, has multi-dimensional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 of farmers'interests. In view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 faced by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such as "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poor main structure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eak capacity and consultation. The content of governance is structurally unbalanced, the leg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s not high,and the integration, cohesion and linkage between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nd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re not enough; the leading mechanism of Party building, multipl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standardized guarantee mechanism, support mechanism of legalization and linkage mechanism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are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Communities; Negotiation Governance; L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Functional Integration ;Identity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176(2019)06-082-(9)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风险规制视域下我国环保约谈法律制度研究”(19BFX182)、中宣部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研究”(2018XZD06)、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 “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ZK201802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4-30
作者简介: 张锋 男(1979- )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矫海霞)
标签:乡村振兴论文; 农村社区论文; 协商治理论文; 制度性整合论文; 功能性整合论文; 认同性整合论文; 上海行政学院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