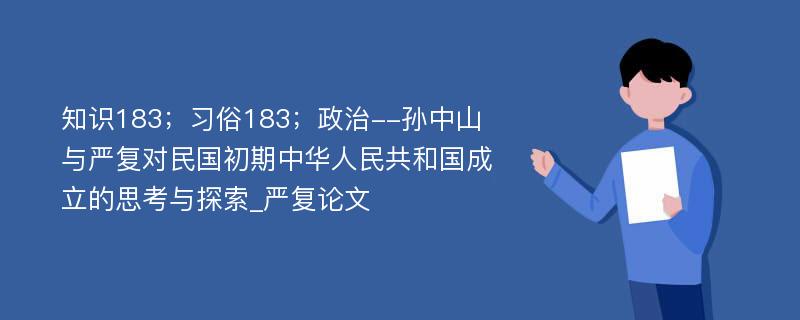
知识#183;习俗#183;政治——民国初年孙中山与严复对建国问题的反思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习俗论文,政治论文,知识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1-0024-09
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1866-1925)先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严复(1854-1921)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两者之间势同水火,不可能有太大联系。而考诸历史,则大不然。他们之间有着极深的历史渊缘。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国使馆囚禁,旋因英国政府出面干涉而获释。次年初,孙中山所撰《伦敦被难记》英文版在伦敦出版[1],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很大轰动,孙中山一时之间成为国际知名的革命家。(注:有关孙中山伦敦被难前后形象的变化,可参见J.Y.Wong: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Hong Kong,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86年。)1898年5月11日开始,日本宫崎寅藏所译《伦敦被难记》在《九州日报》开始连裁。1898年7月18日,英国下院就香港当局驱逐孙中山一事提出质询,认为“孙先生为现代中国维新人物,其在英属地方居留,未尝违反或触犯英国法律,遽被放逐出境”,要求有关当局撤消驱逐命令。此事成为当时报纸的重要话题之一,孙中山的去向也成为清朝政府与英国交涉的重要问题之一。从那时始,孙、严之间思想上的交锋便陆续见诸于文字。(注:详见1898年7月31日至8月1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十四日),严复等人主编的《国闻报》所发《论中国分党》一文,收入王栻:《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7-490页。)
1905年春,严复应张翼之邀,为开平矿务局事,赴英国打官司,孙中山适在欧洲活动,得知严复在英,随前往拜访。这是见诸文献记载的孙、严首次面对面的交往。严复的长子严璩(注:严璩(1871-1942),字伯玉,时任清朝驻法公使馆参赞。有关他的生平,可参见曾意丹、徐鹤苹:《福州世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0-161页。)在所编《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记载:
张学士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先生时适在英。闻府君之至,特来访。谈次,府君言:“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乎?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注:王栻:《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50页。此后,王蘧常编:《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栻、俞政:《严复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8页)、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页)、厨振甫著《严复思想述评》(《周振甫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以及其他有关严复传记与研究著作在提到此事时,均依据严璩所编年谱,而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中,早期较少引用此材料,新出者中,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35页)等开始引用此条材料。)
此后,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与严复之间不断有思想上的交锋。辛亥革命前,严复译《社会通诠》等书,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过批评。而革命党人方面,不仅胡汉民、章太炎等人均有专文批评严复的译著[2],而且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在文章中对严复所译《天演论》等提出过批评。(注:详见1908年9月15日孙中山发表的《平实尚不肯认错》一文,收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4-385页。)民国成立以后,双方在约法、参战等一系列问题上意见相左(注:新发现的《公言报》上严复化名“地雷”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有《保障共和亦虚语耳》、《铸像时机》等多篇是针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如在《保障共和亦虚语耳》中,严复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对德宣战誓众时说:“欧战乃共和、专制争存之机,美之加入,不但扶持人道,亦以保障共和,余无所利。”严复由此感慨:“夫二语尝喧于吾国矣。扶持人道,吾闻之于辛亥,保障共和,吾闻之于丙辰(1916年)。是二语者,真公等之旗帜也,今乃欲弃之,然则所扶持、保障者,果何物耶?”(《公言报》,1917年5月12日)显然是针对革命党人而发的批评。),似处于完全对立地位。但透过历史表面,我们则可以看到,在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上,孙、严之间却有着很多共同的理念,特别是对国家统一、政权建构、社会发展、引进外资、群己关系、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上,双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点,有的是偶然的;有的则显然是孙、严之间思想互动的结果。在不少重要问题上,孙中山显然受到了严复的影响。(注:参见Y.C.Wang:The Influence of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on the San Min Zhu I,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34,No.2(May 1965).第163-184。该文是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篇较为全面地探讨严复对孙中山思想影响的学术论文。)
二
1919年春夏间,《孙文学说》第一卷《行易知难》出版。该书是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以来第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也是最能代表孙中山思想理念的作品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孙中山对传统的“知”的观念及知行关系提出了挑战。
在《自序》中,孙中山说: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俞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所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摧覆专制,创造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孙中山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情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思想错误”。他说:
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故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在《孙文学说》正文,孙中山用饮食、钱币、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证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格言“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3]他特别声明,之所以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篇幅来证明“知易行难”之非,证明“行易知难”之理,原因在于:
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更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尤为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4]
孙中山进一步把人类进化划分成三大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5]又把人群相应划分为三种:“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者则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所以,秦汉以后之事功,无一能比于大禹之九河与秦皇之长城者,此也,岂不可慨哉!”[6]
关于这三种人,孙中山又进一步补充说:
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由此观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乃吾党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实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为改革国事之实行家,真谬误之甚也。……故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而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行者,此也。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7]
孙中山认为,既然知识与实践、掌握知识的人与实际执行的人可以分开,因此,知固可以行,“不知亦能行”,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于国家建设来说,知识与教育并非最为迫切之事,当务之急,是利用外资,发达中国之实业:
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今者宜乘欧洲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者,此也。[8]
曾几何时,孙中山在与严复的对谈中还以“实行家”自居,而十几年后,在历史的大变动之中,面对着随成功而来的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失败和全国政局的混乱,他却不能不承认光有实行家不行,而必须有他这样的“理想家”出来阐发理想和新知,以调动成千上万的“实行家”来完成建国大业。孙中山思想上的这一转变,实昭示着近代中国思想正在发生着某种巨大的变化,近代中国人对于政治改革与革命的视野正从制度转向更深层的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
三
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正式撰写于1917-1919年,正式发表是在1919年春夏间,而撰写这样一部理论性极强的著作的动机则产生于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注:见胡汉民:《〈孙文学说〉的写稿经过与其内容》,收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条下,台北: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6年。胡文中说:“民二的失败,实在是总理发明孙文学说的动因”。)在同一时段里,严复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民国以来的混乱局面进行反思,试图提出救正的方法。
严复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及有关发展实业的主张,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完成。民国成立以后,严复在继续坚持其有关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主张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转向对于习俗、民族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层次思考。主要途径是利用经典和传统资源,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加以适当改造。
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任后,严复就计划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鉴于过去所谓将新旧学问“合一炉而冶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终至于两亡”的教训,严复希望经文合一后的北京大学文科能够“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9]次年6月,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和西方文化中的“帝国”观念的对比开始,对现代国家的建立所需要的最基本要素进行了探讨,指出:“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晋以降,五胡之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此虽易代,顾其彝伦法制,大抵犹前,而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10]
“国性”在现代国家中既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国性从何而来?严复指出,使中国历久而不亡的特别国性,不是来自别的,而是来自孔子之教化,来自孔子所删定的群经。严复由此得出结论说:
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返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弃。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11]
严复主张尊孔读经,是因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因此,经书不可不读,“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但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遂困也”。[12]
同年9月,严复发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杂引旁行鞮寄之书”,重释《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指出:“自西学东渐以来,(此章)甚为浅学粗心之人所疑谤,每谓孔子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与其平日所屡称之‘诲人不倦’一说矛盾参差,不可合一”。他认为,这完全是对“圣人”的曲解,事实上,“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他指出,孔子此章中所谓的“民”,“乃统一切氓庶无所知者之称”,试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哪种文明,哪个国家,“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因此,当政者没有办法使这部分人完全明白政教之中所包含的理念,而只能“由”之去实行,此章中的“不可”二字“乃术穷之词,由于术穷而生禁止之意,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其次,章中两“之”字,都是代名词,所代者有三:道德、宗教、法律,“是三物者,皆生民结合社会后所不可一日无者,故亦遂为明民图治者所必有之事”,如果三者都要先让所有的民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则不可能有宗教信仰之事,“法律之行无日”,道德也无从谈起。可见,孔子之言“殆无以易”。“夫使民于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以事理、情势、利害言,皆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如此则圣人此章之言,后世又乌可议乎?”[13]这篇文章表面是重释《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则反映出严复欲从教化、法律、风俗入手,建设国家政治的基本构想。
同一时期,严复领衔在北京发起成立孔教公会,颁布《孔教公会章程》(注:《庸言》杂志第一卷第十四号附载《孔教公会章程》(1913年),只有中文部分,无英文部分。),规定公会以“阐扬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在北京设立总会,在各地设支会、分会,不分国界、种界,凡信仰孔教者,均可经会员介绍入会。孔教公会《序》文(注: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未收此《序》文。)认为,今之欧美国家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并不徒在其政治,更因为其物质和教化方面的原因,“政治、教化之与物质,如鼎之足峙而并立,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缺一不可者也。……嗟乎!天下岂有无教而可为国者哉!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顺,则从之;非其历史风俗人心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从这种标准看来,适宜于中国历史风俗人心的只有孔子之“遗教”。
1914年初(农历1913年底),严复被推选为“约法会议”议员,不久又被袁世凯聘为参政院参政。当选议员后,严复很快向国会发起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案。在此项议案中,严复痛切提出,“国于天地,其长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那些亡国灭种或沦为异族奴隶者,也大都是“以道德扫地、人心窳涣为之先,从未有好义首公、忠信相扶之民,而不转弱为强、由衰而盛者”。严复指出:
国之通患,存夫贫弱。顾有土有财,则贫者可徐转而为富;生聚教训,则弱者可振刷以为强。即今民智闭塞,学术空疏,无乘时竞进之能力,此其患若较前二者为甚矣。然得先知先觉之传,为振兴其教育,专门普通,分程并进,则拙者可巧,蠢者可灵,其转移尚非无术也。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感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14]
严复对4000年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国性进行了探究。他分析说:“稽我先民,坚苦卓绝,蹈义凛然之事,史不绝书……此实为吾民之特性。而后此所恃以为立国精神者,将亦在此。”[15]应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之“立国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将对新成立的民国“大有裨益”。他建议国会应该通过法案,确立以下各条:
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
一、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
一、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
一、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
一、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孝忠于元首,即无异孝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诵民间,以祛天下之惑。
一、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16]
差不多同一时间,严复翻译的英国人卫西琴(注:Dr.Alfred Westharp,英国学者,1913年来华。1919年在山西办试验学校——大通学校,后因故离去。1925年到北京,二年后赴上海讲学。)所著《中国教育议》陆续在《庸言》杂志上发表,并于1914年4月,由庸言报馆出版了单行本。卫氏在书中以长期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和刚刚师法德国教育、实现脱亚入欧的日本对民族文化教育独立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对民族教育独立的倡导等为例证,提出希望中国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同时,保持和发扬孔子的精神,“庶几中国原其本来而为独立之教育,而泰东西合为教化,于以拯人类于无穷,非曰相效,亦各本其所得于天之分,而各为其自成者,以尽人性、赞天地之化育而已矣。”[17]
同年12月21日,严复在约法会议发言指出:
吾国自改革以来,四五千年之政局为之改观。大凡改革之初,必有一番纷扰。况以现在吾国情形而论,外交、内政、军事种种,较前尤为困难。现在为吾国前途计,其第一要义,在先求国家安宁固定,万不可使乱众复生,否则数年一乱,国基杌陧,无论有何种良好宪法,皆无救于中国之亡。五大洲中民主政体之国甚多,从前罗马时代已行之,而现在最有效果之民主国,则莫如法、美,然因国民性质之不同,而效果亦以不等。若以法、美相较,美又视法为良。考其原因,美大总统权重,法则徒拥虚名而已。至于南美各国,又无足论,每届选举大总统时,必有一番纷争,立国逾百数十年,而仍未能发达,盖貌袭共和之制,而实蒙纷扰之害者,革命频仍,殊可危也。[18]
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血战,再加上中国自民国建立以来所出现的种种乱象,对严复所产生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严复的冲击,可参阅林启彦:《严复论中西文化》,《汉学研究》第14卷第2期,1996年12月;林启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复的国际政治观;以参战问题为中心》,收入清华大学、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严复思想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何君超:《侯官严先生眼中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十六号(收入《严复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等文。)严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19]严复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认为“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20]大战结束之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不可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吾辈观此,则知救国根本,当在何处着手矣。中国目前危险,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21],“根本救济,端在教育。”[22]
严复的上述意见有些虽被袁世凯等人所利用,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严复本人也因此备受史家诟病,但从所引材料中,不难看出,严复的用意在求国家之“固定安宁”,否则,“貌袭共和之制,而实蒙纷扰之害者,革命频仍,殊可危也”,其用心可谓良苦。
四
以上简要列举了孙、严两先生民国成立以后对于知识、习俗和立国精神问题上的认识与主张。其中,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虽正式发表于1919年,正式撰写过程却贯穿在1917-1919年间,而实际开始构思,则从1913年就已经开始。(注:参见胡汉民:《〈孙文学说〉的写稿经过与其内容》,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条。)而严复的有关论述则是陆续发表于1913-1919年期间,时间上基本与孙中山构思、撰写《孙文学说》相吻合。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哲学角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认为这是一部代表了孙中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注:较早提出《孙文学说》是哲学著作的可能是孙中山先生本人。1919年8月14日,孙中山支持下创办的《星期评论》第二号为《孙文学说》刊发下述广告:“孙文,孙中山,孙逸仙,中华民国的妈妈,中国人的先生,三民主义的宣传者,中国近代史的骨子,东方文明的曙光,黄色人种的福音,世界大同的征象,哲学的政治家,这许多个名词,如果诸君想把他联合在一块儿去研究批评,请看这部书。”(《星期评论》第二号)此后,研究者多采此说,把《孙文学说》看成是代表了孙中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参见尚明轩:《孙中山的历程》,下册,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第255页;孙文著、刘明、沈潜评注:《建国方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直到最近,很多学者仍坚持此说。),是在他已“觉得革命党没有任何一点实力”的情况下,“只好把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而写出来的一部著作。[23]而对于严复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研究者则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复古倒退的表现。(注:参见周振甫:《严复思想评述》,中华书局,1940年;王栻、俞政:《严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越光等:《摇篮与墓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徐立亭:《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等。)二者所受到的评价虽如此悬殊,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所得出的结论却略有所不同。
首先,孙中山、严复两先生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巨变进程中的关键人物,而非如后来研究者按照学科分类观念而划分出的哲学家、翻译家等普通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并非普通的学问或学术,在他们的头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的现代国家。无论是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还是严复的有关论著,都只有在这种眼光下,才能看出其真义。从这样的角度看,孙中山先生之撰著《孙文学说》并非政坛失利而不得不关门著书以度时日的消极之举,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性行为,而严复之倡导立国精神,也绝非老来落后,无事生非,而是有着深层的考虑。在这方面,两位历史人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近代中国建国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其次,由于两先生在民国成立以后,政治上的处境很不相同,孙中山在担任过民国第一届临时大总统之后,很快即宣布退位,准备十年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铁路等实业建设,以便为中国的富强打下根基。然而,政局的变化却使孙中山的计划一一落空,从1913年开始走上流亡的漫长道路。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他回到祖国,虽发动了护法等一系列运动,但总体上看,政治上仍处于流亡状态,国际上很少有人承认他所组建的政府,国内也缺乏足够的政治上的同情者和追随者。而严复在民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大总统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等职,比较接近中央政权。政治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他们在考虑问题时表现出很大的立场上的差异。
从以上两点出发,再来研读孙中山、严复两先生,特别是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我们便得出与以往不同的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孙中山把“知易行难”看作是中国近代积弱不振、奄奄待毙的唯一要因,而把“知难行易”视作“救中国必由之道”,这未必能够完全成立,至少也是过于简单化,把知识与观念看作了民国初年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略了当时更为重要的国际格局变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国内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重新组合及革命党内部分化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对革命党带来的不利因素,而对于经典本身的解释尤其不能说十分妥切。(注:“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语出《尚书》:“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罔闻于行。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颖达传:言知之易行之艰以勉高宗)。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孔氏传:王心诚,不以行之为艰,则信合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孔氏传:王能行善,而说不言,则有其咎罪)”(见《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5页下)。此典本指大臣建议,君主推行,建议易,推行难,关于傅说的事迹,可参见司马迁《史记·殷本记第三)。)但是,考察孙中山作《孙文学说》的历史语境,则知在撰著《孙文学说》之前,孙中山已经几次提出,民国成立以后他所提出的筹集外资建设20万里铁路的计划、二次革命等一系列主张之所以失败,“就是一般党人不肯服从他的命令,把他的主义政策视为理想难行”(注:参见胡汉民:《〈孙文学说〉的写稿经过与其内容》,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条。),他提出要做“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希望党员“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24]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拟以此为原则,组织一个由他绝对控制的中华革命党,由于部分领导人的反对而收效不大,但回国后,他仍坚信自己的上述主张是扭转被动局面的唯一办法,因此,在《孙文学说》中,遂借着批评古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向革命党内部不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注:《孙文学说》第六章后,孙中山特地附上了1915年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孙中山本人还对书中一些具体地方加了注释。书中“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有负中山先生者”五事(民元借款、定都南京及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振兴实业、讨袁、二次革命),尤以后二者之失败归咎于黄兴不服从孙中山先生之结果。信中还特别指出:“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人凤)、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此语一入于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见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5-222页))这种语境提醒我们,在谈“知行”关系问题时,孙中山先生头脑中所考虑的并不是学术上对经典的诠释是否得当,而是考虑如何借用经典的权威来打破社会心理的权威,从而在革命党内部建立起真正的权威,实现革命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团结,以便形成一个集中高效的领导集团,领导全国建设现代国家,简言之,欲借对于经典中观念的重新诠释,达到知行分工、以知统行、以行从知的目的,所欲解决的问题,仍是革命党内部的权威问题。具体说来,从在野的地位出发,孙中山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建设一个统一强健的政党来恢复失去的政权,以便实施自己的建国方略。这是一条通过建党来实现建国的道路,而知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为这一计划的倡导者提供某种合法性。这种知识不是认识论上所说的那种科学的、有系统的、可以通过实验验证、感观观察、可以通过演绎推理等逻辑方法加以证明的、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相对的、不能通过实验方法或逻辑方法加以验证的知识。这种动机孙中山先生本人后来也有所透露。他对于佑任说:“默察年来国内嬗变之迹,知武人官僚断不可与为治,欲谋根本救国,仍非集吾党纯洁坚贞之士,共任艰巨,彻底澄清不为功。又以吾党同志向多见道不真,故虽锐于进取,而无笃守主张之勇气继之,每至中途而彷徨,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25]
相比之下,接近政权中心的严复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利用经典的权威,对风俗加以改造,实际上走的是“造民”建国的道路(注:近期关于“造民建国”问题的研究专著,参见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香港教育出版公司,1999;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Zarrow(ed.):Imag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M.E.Sharpe,Armonk,New York,London,England,1997.),希望通过“新民德”,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倡导尊孔读经,背后有着一个极其深远的终极关怀,目的是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包括科学在内)与政治文明的同时,也像西方国家建立各自独特的教化那样,改用新式机器来发掘和淘炼中国固有的宝藏,建立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教化”,从风俗、民情、世道人心方面,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换言之,严复之所以倡导读经尊孔的真实用意,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既在政治和物质上适应现代世界潮流,又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独立性的新国家,而不是建立起一个虽在政治和物质上适应世界潮流但却丧失了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
再次,由于近代中国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孙中山、严复两先生在构建知识与习俗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双重文化”性或“文化混杂”性(注:“双重文化”(biculturality)或“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是近年来国际跨文化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术浯,指的是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与交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不同于原有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现象。据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的学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混杂的……作为一个分析性的观念,文化总是混杂的。”参见Pnina Werbner and Tariq Modood ed.: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Zed Books,London and NewJersey,1997,p.15。该书第1章及第14章对文化混杂问题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另可参见Fred L.Casmir: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 Third Culture Building Model,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Volume 23,Issue 1(1,February,1999),第91-116页;Philip Huang: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26,1(1999),第3-31页;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两先生青年时代均在海外接受过系统的近代西方科学教育,本身文化素养中已有东西两种文化的成份,而在各自写作的过程中,又多参考中外文书籍,精通翻译的严复自不待言,孙中山在创作过程中,曾专门“向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购置了大量英日文参考书籍。”[26]换言之,他们所说的“知识”、“习俗”、“文化”决非中国固有的“知识”、“习俗”与“文化”的翻版,而是在充分吸收中外一切相关知识、习俗与文化中的有益成份的基础上,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知识、习俗与文化体系。孙中山先生的“知识”体系既试图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加以改造,以便通过这种改造,与传统的权威挂起钩来,同时也包容了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有关知识、人生与行为关系的思潮,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倭铿的人生哲学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等联系起来,甚至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有所联系(注: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113页;吴相湘:《蒋梦麟振兴北大复兴农村》,《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页。),这就使其“知难行易”说与世界新文化、新知识发生关系,通过这种外来思想的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其“知识”的地位。而严复先生所倡导的“习俗”与“文化”,不仅继承了明末以来一直到晚清时期以顾炎武、龚自珍、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风俗左右国家政治的传统,而且更是充分吸收了近代西方以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和功利自由主义思想中关于国家政治好坏取决于构成国家的每个公民素质的好坏的观点,即所谓“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27]
总之,孙中山、严复两先生的反思及其成果虽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却都是试图在法律和政治制度之外,另寻维系社会、政权和政治制度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并不相同,但是,面对着民国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混乱的政治局面,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知识、习俗与文化,希望从知识、习俗与文化入手,为政治社会和政治制度寻找合法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奠定坚固不拔之基。从他们的探索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认识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中华民族正大步迈向世界舞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他们的思考对我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2001-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