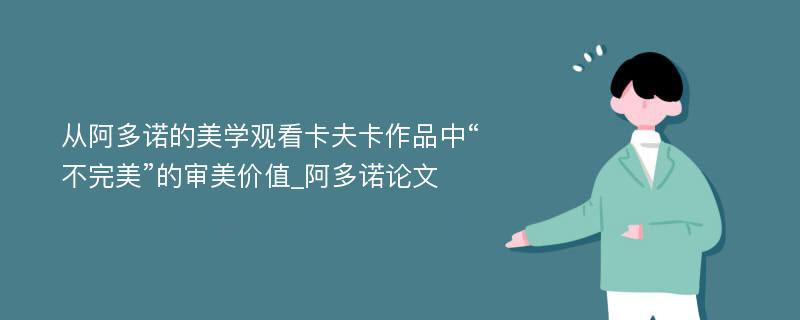
由阿多诺美学观谈卡夫卡作品“不完美”的美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不完美论文,卡夫卡论文,价值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14)06-0114-03 传统美学赋予“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美的事物不仅涵盖了“和谐”与“高贵”,更主导了其他与之相反的概念和形式,使之为美所用,为美存在。但凡不容于美的思维、价值、观察或事物,在传统美学中,无不受到操控、扭曲、贬抑、排除,并背负着令人不解、意义卑微、荒诞诡异等罪名。而作家卡夫卡在传统意义上来说就不是一个唯美是从的人。正因如此,也没有人用“美”来形容卡夫卡的笔下乾坤。但是,也没有人否认卡夫卡的作品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其实“美”不一定全部都有吸引力,有吸引力的也不一定全部都是美。这种与传统的美学价值观相违背的美学体验正是卡夫卡所提倡的写作态度,也是一种探测自我定位、活化存在感受、质疑生命意义的程序。对此,阿多诺在他的美学理论中也有解释。他认为,在纯净的传统的美当中,与此悖离的将全然归于寂静,此类的消解对于美学以外的事物是致命的。 一、对阿多诺“不完美”美学观的理论探讨 即使现在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得不到众多美学家认可,但没人否认其传统美学仍然需要“丑”这类负面元素来成就“美”,或者说是需要以那已然被既有形式法则所整合的“丑”作为对照与陪衬,并相对于题材而为其佐证。“美”也许执著于制造张力的效果,但这种张力乍看之下也仿佛与和谐、均衡格格不入。然而正因为这种干扰的穿插,使得最终获得的美的均衡与和谐越发的可贵,就更高层面而言,题材所彰显的“美”也就更为高贵。因此,“丑”这类负面元素正是“美”学目的的手段;也只有在此前提下,“丑”和它的同类才能组成艺术元素。 有鉴于传统美学的虚伪本质与一些不合时宜,阿多诺驳斥传统美学的正统性,揭发“美”的强制性与变态性。他表示,艺术所要追求的,正是它所压抑的。而艺术所压抑的除了那些背离了“美”而“全然归于寂静”的“丑陋”、“令人恶心之事物”、“肉体上令人反感之事物”、“粗鄙之事物”、“不和谐”、“残酷之事物”[1](P219)等等负面价值之外,还有它们所反映的符号系统与世界观。 这类负面价值不仅是美学议题,也与道德哲学不可分割。阿多诺正是结合负面美学思维与道德哲学观的先驱之一。他由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主张在人性的丑陋中探测美学与道德哲学,刻意强化丑陋人性的“告发”潜质与功能。在《道德哲学的问题》里,阿多诺指出:“当今道德哲学的位置较可能在对不人性事物的具体告发中寻得,而较不可能在冷漠而抽象的人类存在定位之上。”[2](P15)而他透过《美学理论》也明白揭示:艺术必须以被视为丑陋而遭受诋毁的事物为职责,不再是为了整合它,淡化它,或为了借助那比所有令人厌恶的事物更令人厌恶的幽默,使它抵消存在,而是为了在丑陋中告发那依照自己的图像制造并复制丑陋的世界。[3](P164) “告发”之所以富含深意并能发挥作用,在于丑陋或者不人性等相关负面价值如前所说的受到了压抑,以致正面价值及借之延伸出来的事实与真相成为欺骗与虚伪的伎俩。 换句话说,传统“美”所制造的表象与假相,不论是以乌托邦的形式,或者是以升华或超脱世俗的程序,或结合意识形态的操控,都掩盖了真正而超然的事实与真相。其实“真”的追求既然无法透过“美”的形式与内容达成,是以在求“真”的诉求下,“美”逐渐失去信赖,违“美”俨然已经成为了疏离手段及对“美”的抗议。随着“不美”的扶摇直上,“不悦”就成为了必然,而“美”以外的关照与价值更能逾越原来定位。为求“真”而在负面价值中翻搅,因而日渐普及。尽管在现代美与不美、正面与负面等价值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其间的灰色地带也越来越宽广,但我们所要警觉的是,负面价值为了避免重蹈传统美学的覆辙,应当汲取“美”的教训,跳出它的限制,包容与己相悖的范畴,从而追求真正的“真”与“美”。 因此,为颠覆“美”的倨傲与独断,阿多诺立意挑战既有的美学典律,为那些被压抑和被否认的负面价值正名。过去与“美”相违背的负面元素,抵触主导作品的形式法则,如今也咸鱼翻身,在现代艺术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与质地,继之而起的是其美学意义的赋予,不论是在美学层面上或者是在社会、道德面上也一并受到了质疑。 二、从阿多诺美学解析卡夫卡作品的“丑陋”美学元素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诠释了现代艺术的美学认知应该是为了“舍美求真”而倡导“不美”的负面美学观。因为后者可以避免被“美与高贵”的外表蒙蔽,使得事实与真相拨云见日。这也就不得不提到与阿多诺有着同样反抗传统美学精神的作家卡夫卡。他正是这类理论认知应用于具体实践的开路先锋。他的作品更是将这种认知发挥到极致的典范。 卡夫卡笔下人物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怪诞的、充满矛盾和变形的世界里,有着底层小人物的惶恐不安和那种渴望明天但又看不到出路,遭受质疑与压迫但又无力挣扎反抗的态度。比如《一个梦》里的死亡陷阱,主人公约瑟夫·K凝视对方对自己架构活埋过程。他虽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但却明白一切已经回天乏术,因此选择默默承受,甚至主动协助挖掘坟墓。不为自己申辩,不视自己无罪,不自觉含冤,认定自己的结局,坦然受死。这不难看出是卡夫卡蓄意用这种态度来挑战死亡,消磨生命。又如《一位饥饿艺术家》里的主人公,盲目执著于饥饿艺术导致最后临死前被人像烂掉的干草一样遗忘。而他最初选择饥饿的原因竟是他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他认为好吃的食物。而若以饥饿艺术家的行为来检视卡夫卡本人,其文学意图的背后,依他个人所见,仅仅是一种可笑的坚持。饥饿艺术家透过表演来冒险赌命,最终是否真的死得其所,也许无法盖棺定论,然而在卡夫卡心中,饥饿艺术家的孤寂末路与凄凉衰亡无疑已为他个人的艺术生命预下定论。 而读者在享受卡夫卡为我们营造的这种氛围中,能透过作品直白地看到他为读者架构出的残酷现实,同时可以感受到他的写作中的自我定位与质疑生命意义的做法,而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晦暗与消极,也照映出他身处俗世却极力追求真实与真相的意图。 就如同卡夫卡在出版的个人日记中提到“一切之于我,形同建构。”[4](P97)同样他也坦承:“我正在追逐建构。”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又失望地体会到:“此类建构即便是驻扎在想象中的,也只能到达到一种生动表达的表层,而且势必将被掩盖。”[5](P133)他也同样切身体会到,文字总是难以呈现真相,并且语言容易失真。或许是看到了文字符号的无力,并且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片面的“美”学形式与内容无法满足他的设想,同时也违背他所期望的写“真”实的内心。所以借助作品描绘,他结合了“建构”与“虚构”,大幅采用超乎传统美学所抗拒的负面元素,并且将他们运用到作品中去。而这一点连卡夫卡自己也坦承,他无法抵挡自己笔下所营造出来的逼人寒气。在1911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卡夫卡曾提到,检验前一年的作品,文中的冷酷如何对他穷追不舍,充盈在笔墨间的冷漠无不一丝丝地撩拨着他内心炙热的痛楚。在1912年9月23日的日记中,他更是毫不避讳的讲述是因为小说的撰写让自己沉沦在了痛苦的深渊,而只有在全然开放的肉体与日渐悲壮的心灵下才能顺利地走笔行文。 而相对于此,读者也难逃卡夫卡这股凛冽气势的侵扰,无不感受到来自于卡夫卡笔尖的锐利威胁。但庆幸的是,卡夫卡的“唯丑”美学违背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样使读者无法产生共鸣,因此不致于盲目认同。如此看来,卡夫卡作品中的“美学距离”竟是为读者制造了一种安全距离。而这种距离也正是阿多诺在《卡夫卡札记》中所表达的疏离手法:“卡夫卡的艺术疏离,也就是那种促使客观性异化的显而易见的手法,借由内容获得证实。他的作品虚构了一个场域,由此出发,世界就像他所理解的地狱一般被梳理,被残害。”而阿多诺所表达的那种对于丑陋人性的告发本质与功能在卡夫卡笔下也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般情况下,这种疏离都是作家为了避免读者认同或者为了跟读者保持心理距离所采用的策略,以便使读者客观地发现已经异化的事物及其因此所裸露的异常本质。也正因为卡夫卡直截了当地将寻常事物背后的这种异常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纸面上,以致与读者保持了一种独立的疏离空间,所以阿多诺洞察了卡夫卡对此的情有独钟和乐此不疲,并且以欣赏的方式称这样的写作是“卡夫卡所爱”[6](P251),是一种“对不悦的愉悦”[7](P252)。从而迎合了这种卡式独家的“美学距离”。 卡夫卡作品所展现的艺术观察与艺术美学的价值能够引起我们关注。为“舍美求真”,卡夫卡倡导负面美学观。他独有的美学与价值观似乎正是对传统美学与价值观的寻衅。也正因如此,若以传统美学要求与价值期待去过滤卡夫卡,也定会满腹狐疑,处处碰壁。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与行为动作恰可反映传统美学观察与美学价值的缺失。因此,不可否认卡夫卡所倡导的这种美学俨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美学桎梏,在有限的可能下更进一步贴近“真”的境地;而作家也得以借此来窥视自己的“真”性情、“真”面貌、“真”原委。换个角度来看,“建构”与“虚构”无疑也是他摆脱自我、想像自我、捏造自我、丰富自我的一种自由活动,游刃其间正是一种享受。 总体而言,卡夫卡的作品好比在泥中赤裸裸的打滚。他利用创作活动持续展开自我剖析、自我泄漏、自我欺骗、自我伤感、自我伤害、自我娱乐与自我解救的多元化的可能。然而,他的笔下乾坤可以用来剖析内外世界,却无法用来切除存在于其间的祸因与病兆。所以只有卸下所有理性、清洁、优雅的门面,才能尽情在松绑、丑陋、失序的欢乐状态下生存着。 三、负面美学观对于当代美学的研究意义 美学要求“美”、“丑”兼具,以呈现理念的整体。而“丑”作为现实世界与真实心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无法被全盘泯灭。传统艺术的基础思维仍以“美”为主轴,“丑”则居于陪衬地位,以彰显对方的主导地位。而卡夫卡与阿多诺则大反其道而行。阿多诺极为认同卡夫卡在文学世界里与丑陋、肮脏、恐怖为伍。虽然,如阿多诺所言,相对于“美”,负面元素具有背叛与告密的功能和本质,卡夫卡的艺术之所以让人敬畏、甚至不敢苟同,也许正同此有关。他的写作目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在于想要为一种长久以来就被人所贬抑的负面价值所正名,并且更在于追求生命真相。然而,如果“美”作为传统艺术的对象与手段,以脱离现实真相为前提,而难脱欺瞒与虚伪的本质,则卡夫卡有时一味执著且停留于负面艺术观,又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呢? 文学写作必须脱离生活,摆脱现实,即便其中包含生活体验,也是一种超写实化、譬喻化,甚至一种负面化和滑稽化。透过如此的书写经验摸索真相的真实面貌,赋予真相一种新颖意象,想必这正是卡夫卡寻“真”的必经途径,以及求“真”的独特手段。 总体而言,卡夫卡和他笔下的人物的确渴望社会认同,但他却不遵循传统的艺术路线,反而以拨“正”反“乱”的方式来挖掘正统艺术的伤疤,进而追寻更大的艺术自由。然而,这样的艺术途径却是坎坷而孤单的。毕竟传统的美学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改变现有的正统方向。选择除了亦步亦趋就是偶尔挣扎。所以无论对于阿多诺还是卡夫卡而言,就像德麦尔所评价的一样:“他们总是处于旅行的状态之中,既来自四方,也不知来自何方;既前往四方,也无处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