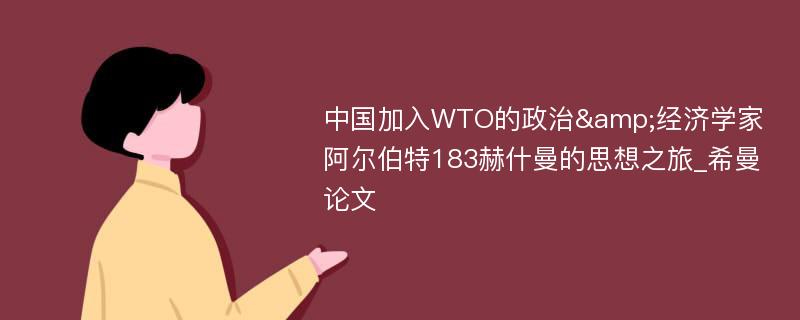
入世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183;赫希曼的思想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尔伯特论文,之旅论文,经济学家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在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扛鼎之作《激情与利益》①一书所做的序言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的开篇第一句就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Hirschman,1977/1997,p.ix)。森教授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大致总结了当代世界的一位思想大师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在当代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花十余年研究功夫、亲身访谈和查询档案资料所撰写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全面、细致而翔实地介绍了赫希曼这位当代全球化知识分子一生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和学术贡献。而贾拥民花数年精力而翻译的这本800余页的思想传记巨著,也向广大中文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和可信的中译本。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文明史上,20世纪可谓是一个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和波澜壮阔的世纪。在20世纪,世界上曾发生了上亿人伤亡的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希特勒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发生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也在十几个国家发生了70余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转制和中国与越南的市场化改革。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里,西方国家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和演进过程。伴随着20世纪人类社会的跌宕起伏的制度演进和变迁,也有无数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多学科的角度在探索、反思和理论化地揭示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原理与基本法则。这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詹姆斯·布坎南、阿玛蒂亚·森等等。本传记的主角赫希曼,无疑也是这些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不过与其他跨学科的伟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同,赫希曼一生的坎坷而又辉煌学术探讨和著述的经历有以下几个特点:(1)赫希曼更多地是从身临其境的现实观察而不是从宏大的理论推理和逻辑叙事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和演变的一些基本原理;(2)与其他一些思想家更多地在西方大学中教书和做研究相比,赫希曼一生坎坷,从事过多种职业,更多地是参与到现实社会实践而进行观察和思考,因而被这位传记的作者称为“worldly philosopher”(这个词组在中文语境中可被理解为“俗世的哲学家”、“入世的哲学家”和“现实世界的哲学家”);(3)赫希曼早年背井离乡、历经磨难、漂泊无根,居住过许多国家并中年和晚年在数所著名大学执教和做研究,使他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学术流派,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知识分子(见本书中译本②第18~19页,下同);(4)由于赫希曼真正开始其学术著述是在二战后移居到美国之后,与上述大多数当代思想界的巨擘相比,赫希曼的理论著述更晚近一些。因而,尽管他在世界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是西方国家“学术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第26页),但相对较少地为学术圈外的普通人尤其是中国读者所知。 一、赫希曼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思想探索 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全球知识分子”的赫希曼有着传奇、神秘也无疑是辉煌的人生。阿尔伯特·赫希曼于1915年4月7日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大致是在进行长达14年的大众民主实验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长大的。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阿尔伯特在柏林的语法中学里学习,且比较早熟。早在14岁的小小年纪里,赫希曼就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在16岁左右的青少年时间里啃读了黑格尔艰涩难懂的《精神现象学》,还从中引申出了“一种人类理性出现的‘道德秩序’”。在这一时期,他还喜欢上了经济学,并注意到了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的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的“长波理论”(Kondratiev long cycles)。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热血青年,赫希曼曾参加了当时德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并“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和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通讯等等,从而“一生都痴迷于探究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97页)。在希特勒纳粹政党取得德国的政权后,赫希曼因担心种族和政治迫害,在他的18岁生日之前流亡到了巴黎,开始了他的“无国籍人士”的流亡和学习生涯。 到了法国,年轻的赫希曼进了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并在1935年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年的研究奖学金,去这世界的经济学重镇学习。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赫希曼有机会听了当时声名卓著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和哈耶克的课,并选修了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学的一些课程,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多年之后,赫希曼本人还回忆道:“一直到英国之后,我才如梦方醒……只有在那里,我才真正认识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学”(第165页)。在一年的英国访学期间,赫希曼还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听了凯恩斯的讲演,但并不怎么欣赏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何形式的宏大理论了”(第166页)。在英国期间,赫希曼还结识了阿巴·勒纳(Abba Lerner,——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并与剑桥的另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有了较深入的交流,还深受其思想影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年的学习生活,对赫希曼来说意义非凡。到1936年6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的经济学家了(第170页)。 回到法国后,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赫希曼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并于1938年6月在意大利的特瑞亚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赫希曼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陆军,抵抗德国入侵。在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和法国政府投降后,赫希曼隐瞒身份,几经周折而流亡到马赛,参加了当时一个美国人瓦里安·弗莱(Variant Fry)所组织的紧急营救委员会,给一些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伪造证明、代办签证、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他们逃出德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多犹太人逃出了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以及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等等。 这个紧急营救委员会很快就成为纳粹德国和法国傀儡政府(法语:Régime de Vichy)的眼中钉。1940年12月,因担心纳粹的搜捕,赫希曼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14日逃至美国,在25岁的时候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无国籍人士”。到美国后,赫希曼很快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生活,并很快结识了一名来自立陶宛和巴黎的富裕犹太商人家庭的少女莎拉·夏皮罗(Sarah Chapiro),于1941年6月22日在伯克利市政厅举行了婚礼,两人结成了终老夫妻。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赫希曼就在美国两本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美国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在发表于《美国统计学会杂志》9月号上的关于《有限分布中离差的度量》的文章中,赫希曼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中所常用来测量产业集中度的“赫希曼指数”(这个指数在经济学中又被称为“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在1945年,赫希曼(Hirschman,1945)③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国家实力与外贸结构》。在这部著作的第7章,赫希曼运用统计方法计算了多国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情况,实际上首次使用了目前经济学和媒体中所常用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这个概念,即根据劳伦茨曲线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因而目前国际学界已经基本公认赫希曼才是收入分配中的“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者。④ 新婚燕尔,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写作与发表,并没阻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赫希曼再回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念头。1943年,赫希曼在旧金山应征入伍,随后到华盛顿加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并被派往欧洲,在进攻意大利的美军中做了一名随军翻译。在意大利期间,赫希曼买到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战争的间隙中细读了这部著作,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正如这部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评论的那样:“哈耶克对‘奴役之路’的悲叹对赫希曼的意义在于,他促使赫希曼将更加自觉地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更加彻底地怀疑完美知识,并加深了他德国纳粹政权的集体主义灾难性社会实验后果的认识”(第302~30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赫希曼从美国军队退伍回到了华盛顿,随即为了家庭生计而到处求职。非常幸运地是,受当时已经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邀请和举荐,赫希曼在美联储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他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欧洲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制定与实施。由于厌倦在美联储的官僚机构工作,在1952年,赫希曼应邀去南美的哥伦比亚,担任了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走遍了哥伦比亚各地,开始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为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献谋献策的生涯。之后,他自己又在哥伦比亚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变成了一个衣食无忧的企业家,从而应验了赫希曼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于最少的计划”(第371页)。 二、“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 1954年10月,赫希曼回到美国,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讨论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赫希曼结识了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斯·密立根(Max Millikan)、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Rostow)、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以及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等等。在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赫希曼受哈耶克的思想的影响,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自负”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无法免俗,同样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因此往往不“承认他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利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为不发达国家绘就详尽的发展蓝图”。当然,赫希曼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过分着迷于理论分析,同时对那种制定“包罗万象的综合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赫希曼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坚持到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而不是盲目依赖于总量统计数字,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第403页)。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幸运女神向还在哥伦比亚开私人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开始微笑了。1956年7月,赫希曼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收到了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耶鲁在1956-1957学年做一年的客座研究教授。赫希曼很快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后来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当地找到了房子,全家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搬到了美国的诺斯黑文(North Haven),真正开始走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道路,使他“从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外围一跃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心脏地带”(第407~408页)。 到了耶鲁大学后,赫希曼被聘请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客座教授。基于在哥伦比亚的多年的观察和咨询实践,赫希曼在这段时间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这本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赫希曼(Hirschman,1958)⑤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学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赫希曼在这部著作中对政府计划的发展提出了批评,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聚焦在“企业家”身上,而不是计划者。这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家们”的能力的强烈质疑。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的结尾,赫希曼告诉人们,传统社会(欠发达国家)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也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是企业家精神,“而那也正是争取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石”(第432页)。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当时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则纷纷发表评论。老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曾是赫希曼在美联储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在书评中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old)却高度赞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则表示赞同,而当时还年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虽然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也为这部著作给发展经济学这个“一度被陈词滥调主宰的经济学分支带来了缕缕新风而表示无比钦佩”。这本《经济发展战略》一问世,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也从而奠定了赫希曼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的学术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出版后,赫希曼在耶鲁的客座教职也接近结束了。这时,幸运之神又再次对赫希曼发出了微笑。在他于耶鲁认识的一个反传统的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推荐下,赫希曼先在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接着,哥伦比亚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为正式教授,教授国际经济学。赫希曼很快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而回到纽约,从而正式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学术殿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赫希曼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成了好友。这一期间,赫希曼继续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Hirschman,1963)⑥。与他的第二本书一样,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成了一本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虽然赫希曼并不希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改革落入了‘国家安全至上’的框架,那么即使避免了革命,也未必一定是‘不幸中之大幸’”。此外,赫希曼还在书中突出了社会科学家参与的重要作用(第473页)。《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本人获得了一个“改革贩子”(reformmonger)的绰号。赫希曼坚持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进步的观点,在美国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现代化和改革将使第三世界陷入剧烈的动荡;而历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曾认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发展就会陷入停滞,以往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随着沃勒斯坦对非洲经济前景的警告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赫希曼发现,自己与他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了”(第474页)。 《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马上给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老友——也是对他本人有知遇之恩的伯乐——格申克龙教授寄了一本。格申克龙本人其时也是在他个人影响的巅峰期。他立刻在背后运作,努力把赫希曼从哥伦比亚大学挖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来。这对赫希曼来说当然是个最好的选择。当赫希曼做出选择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校方都竭力挽留,但是为时已晚。他随即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而就职于哈佛,被任命为卢修斯·N.利陶尔(Lucius N.Littauer)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发展经济学的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巴西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曾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由此,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在这本拉美发展的三部曲之三中,赫希曼提出了“项目”可以形塑制度因而往往是“制度促进器”的观点。在第一章,赫希曼还创造了一个术语“隐蔽之手”(Hiding Hand)的隐喻,用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琢磨的力量。赫希曼提醒读者,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即那种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他所说的“隐蔽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无法事前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践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这一发展经济学的三部曲出版之后,虽然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乃至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巨大反响,以至于美洲开发银行策略规划部首席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科·梅西亚(Francisco Mejía)曾认为“赫希曼是近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但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却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多少接受和实施,他的发展理论也曾遭到一些老派发展经济学家的冷漠对待和批评。因此,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赫希曼感叹地说:“阻碍人们形成正确变革观念的那些东西变成了变革自身的重要阻碍”⑦。对任何一个处在制度变迁中的社会而言,赫希曼的这句话是多么正确和切中时弊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年末,刚从拉丁美洲旅行回来的赫希曼写了一篇《在拉丁美洲如何学会放手?为什么要放手?》的短文。这篇草稿尚墨迹未干,赫希曼就把它送给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⑧尽管当时有着左倾思想的鲍尔斯对赫希曼本人很尊敬,但还是判定这篇文章是“一篇力图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宣言”。鲍尔斯认为,主张在拉丁美洲“放手”,或者说听任拉丁美洲自行发展,“就意味着把这些国家留给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第515页)。 自1966年加入哈佛大学,到1972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赫希曼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实际执教了大约只有6年。其间,他不但与一些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做了同事和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名满全球的经济学家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等——这些经济学家很多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和一些正在迅速成长的年轻经济学家如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以及塞缪尔·鲍尔斯做了同事和朋友。这段时间,赫希曼也从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新意迭出,洞见满篇,字字珠玑。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博采众家之长,将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研究和思考综合起来,以及将社会观察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冶为一炉,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中一个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赫希曼发现,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赫希曼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这些观点看来似乎都是对现实观察而悟出来的大实话,之前好像还没有思想家做这样的理论化阐述。故这部著作一出版,有关评论就如潮水般涌出,“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完全不吝溢美之词的好评”。就连这本书出版时的审稿人、当时已经是名满学界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也对这本书评价很高,称赞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而且偶有惊人之论”,因而建议将之立即出版。于是,这本书很快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然,在国际上也不乏有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对这本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如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巨匠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就对这本书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呼吁与组织的衰退没有任何关系,一切只与垄断有关。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Jr)实际上对这本书评价也不高。就连当代一位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也对这本书颇有微辞,说这本书论述的虽然是“简单的”本质性问题,但却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一发行就影响力非常大,使这本书出版本身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 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出版不久,赫希曼在哈佛又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政治经济学与可能主义》。在这篇重要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可能具备完备的知识,我们必须欢迎不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历史不但是不可预知的,而且如果历史不是不可预知的,那么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第560页)。这显然与哈耶克(Hayek,1937)⑨在1937年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人》上的《经济学与知识》和1945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知识在社会中运用》(Hayek,1945)⑩两篇经典文献中的观点完全精神相通。然而,赫希曼却发现,在当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越来越痴迷于预测的准确性和完美性,因而他认为这种倾向太糟糕了:“我们总是试图去预测变化”;“天下熙熙,皆为确定性而来;天下攘攘,皆为预测确定性而往”。据此,赫希曼用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一句格言来警告当代社会科学家:切勿“急于做出宏大结论”(la rage de vouloir conclure),因为那只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由“伪洞见”、“唯一结果”和“唯一路径”所组成的世界。由此,赫希曼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出发点的主张:应彻底拒斥时下最流行的那种以“确定成功或失败的‘先决条件’为目标的‘研究方法’,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可能的路径、奇特的事物、异常的现象以及突发的和意外的后果上来”(第561页)。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理论基本假设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实践导向。赫希曼认为:“社会科学家总是在寻找最优政策和最佳状态,这通常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寻找构成这些状态的理想的但却相互对立的成分的最优组合。与之不同,我们要寻找的则是正确的组合,不仅仅包括接触型政策与非接触型政策的组合,还包括中央控制与分散行动的组合、精神与物质奖励的组合、技术进步与社会正义的组合,等等”。之后,赫希曼还补充道:“我之所以会与激进主义分道扬镳,是因为我认为,人类行为所非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哈耶克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著述中所常用的一个术语——笔者注)是非常强大的,也是‘统治阶级’绝对所无法控制的。‘统治阶级’即使能启动某些事件,这些事件也可能引导整个国家进入‘统治阶级’所从来不想涉足的某个领域”(第562~564页)。今天看来,单凭赫希曼的这些洞见本身,难道就不值得获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退出、呼吁与忠诚》的出版,标志着赫希曼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跨学科的经济社会思想研究。在与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同事赫伯特·金蒂斯、鲍尔斯等的交流中,赫希曼把人们对来自于他人奖赏的快乐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快乐的偏好“按字典顺序进行了排列”(Lexicographic ordering),创作了一篇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Hirschman,1973)(11)。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隐喻效应——“隧道效应”(the tunnel effect)。对于这个隧道效应的发现过程,本书是这样记述的: 赫希曼用它来刻画人们的情绪从满足变为愤慨的动态过程,并用它来揭示决定了这种情绪变化的预期变化的奥秘。有一天,赫希曼在波士顿洛根机场隧道入口处陷入了一场交通大堵塞,他耐心地观察了其他司机的情绪变化,也细心地品味了自己的情感变化。当拥堵开始缓解时,赫希曼注意到,那些被堵在纹丝不动的车道上的司机在看到相邻车道上的车子开始移动时,心情显然变得舒畅了一些,因为他们预期到,既然别的车道已经疏通了,那么他们自己所在这个车道应该也很快就会变得畅通。然而,这些司机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他们开始羡慕别的车道的司机了;很快地,他们的心情从轻松变成了嫉妒,而嫉妒又转变成了愤怒,因为这些司机开始觉得有人在欺骗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情也就变得比原来还要糟糕很多——他们曾经觉得受到了帮助,因此大感欣慰,现在又觉得被剥夺了,因此非常愤怒。(第577~578页)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代人类学大师,也是赫希曼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和好友克利福德·格尔茨就高度赞扬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比奇妙生动的比喻,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千个复杂的图表。这篇论文也印证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件事情:小汽车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移动实验室。在自己的小汽车里,人的本性会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远在英国剑桥的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数年之后读过这篇文章后,也深为激动,立即写信给赫希曼,称赞他这篇文章是“最微妙的讽刺写作方法的典范之作”(第580页)。 除了这一活泼生动比喻的“隧道效应”外,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再到拉丁美洲访问中,赫希曼在巴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迷人的悖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或者说,有人相信经济增长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到1974年的时候,隧道效应实际上已经耗尽,这可能是因为在政治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步。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却是,人们并不相信经济扩张的真实性”(第600页)。在巴西的这次访问中,赫希曼还发现,在拉美当时的发展阶段,政府养成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习惯,即,竟然相信了自己真的能够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高经济增长率造成了一种过强的白噪声,完全淹没了源于其他社会问题的其他‘噪音’,从而有效地隔离了决策者。”这个发现促使赫希曼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对隧道效应的修订”: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决策者有可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对“伟大成就”的宣传,以及对高增长率能否维持的忧虑,就会淹没那些来自“忘恩负义的群众”(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抱怨)的、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声音。同时,由于社会辩论(如果存在社会辩论的话)的焦点也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会误导政府,使政府以为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尽管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成为自己压制表达自由的政策的受害者。(第600页) 对任何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赫希曼的这些发现好像都总是有着亲临其境的现实意义。 三、从观念史的宏大背景思考现实世界问题的思想史家 《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这篇论文撰写出来后(于1973年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赫希曼与哈佛大学的缘分似乎到了终点。赫希曼离开哈佛的因素是多种的。其中之一是鲍尔斯离开哈佛大学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时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的鲍尔斯极具学术创造力,在基本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造诣也是属于出类拔萃的,且知识面之广是让人叹为观止的。除了经济学外,鲍尔斯在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也都有涉猎。但是,鲍尔斯因其左派背景,特别是他反越战的行为,以及与激进经济学家金蒂斯的合作关系,其学术晋升一度受阻。后来因为拒绝对哈佛大学“忠诚”宣誓,与校方打了官司。鲍尔斯虽然最后赢得了官司,却被哈佛大学解雇了。赫希曼虽然在左倾立场上与鲍尔斯和金蒂斯不一样,但私人关系甚笃。恐惧教书、鲍尔斯的解聘,乃至与格申克龙在如何对待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反越战和麦卡锡主义的运动问题上的分歧,触发了赫希曼离开哈佛大学的念头。1971年11月,赫希曼写信给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卡尔·凯森(Carl Kaysen),询问他能不能在第二年到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立即得到这位原来哈佛大学做过讲席教授的院长的肯定答复。于是,在1972-1973学年,赫希曼首先是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去了普林斯顿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而把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留给了阿玛蒂亚·森。 就在赫希曼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前,凯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为高等研究院招兵买马,已经聚集了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2),当代杰出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一年之后,格申克龙第三次做了赫希曼一生重大转折的“幸运之神”。在高等研究院提名罗伯特·贝拉(Robert Balla)为终身社会科学家之失败的“贝拉事件”之后,在高等研究院内部出现了分歧。在一次电话中,格申克龙告诉凯森,他们的共同朋友赫希曼并不十分愿意回到哈佛大学去,建议凯森提名赫希曼做高等研究院的终身社会科学家的职位,说他可能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格申克龙在电话中说:“赫希曼的论著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总是非常有思想,赫希曼的思想的独创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没有几个人能够比肩。”在格申克龙、凯森和格尔茨的举荐下,赫希曼以全票通过其作为终身社会科学家的申请,并于1974年全家移居到普林斯顿,以至在后来做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并在普林斯顿写作、退休到终老。 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赫希曼发现:“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完全绝缘——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事实上,赫希曼在这个方面的立场越来越坚定,他敦促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关注他们的经济分析的政治含义。他说,自己“深感不安的是,许多政治灾难似乎恰恰是我们[经济学家]造成的,或者,至少是我们促成的”。当时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当时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情况,令赫希曼失望,他于是转而“向内”,开始回溯历史,思考资本主义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因此,赫希曼决定暂时从关注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撤出,进入了思想史的世界,“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盘桓’一段时间”,开始研究人类社会的观念史。在普林斯顿高研院做访问教授期间,撰写出了他的最为著名的著作《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胜利前的政治争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第502~635页)。“《激情与利益》一书的出版,也使一些学者看到,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两个赫希曼:一个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另外一个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第646页)。 《激情与利益》是“赫希曼最出色的著作之一”(阿玛蒂亚·森为这部书所写的序言中的评价),是一部把人类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和政治分析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观念史的著作。在这本书的“20周年纪念版的自序”中,赫希曼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反驳任何人或任何特定的知识传统。它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任何现存的思想体系,它具有立场超然的特殊性质,有超然而独立的内容”(Hirschman,1977/1997,p.xxi)。这部著作实际上探讨了世界各国为什么走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原因。按赫希曼自己在这本书的“导论”中的解释,“本书的缘起是,当代社会科学没有能力阐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后果,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带来的十分频繁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无论这种增长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混合型的社会”(同上,p.3)。 今天看来,《激情与利益》不是一本容易读的著作,尤其不是那种越读越薄的一本书。通过对人类进入近代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运行基本原理的论述的回顾,赫希曼讨论了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的思想起源和社会演变过程。正如赫希曼本人在这本书的二十周年纪念版自序中所说,这本书实际上讨论了两个命题:一个是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的发现,即“追求利润的商业精神开启了通往‘以贸易为基础的民主政制’的政治智慧之路”(同上,p.xxii,p.120);另一个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Denham Steuart,1712-1780)爵士的断言,“近代经济(即各种利益)的复杂系统必然是已经发明出来的对付专制主义蠢行的最有效的辔绳”(同上,p.xxii)。这样,赫希曼试图把人类社会现代过程中经济与政治互动从思想史的角度和盘托出。 在《激情与利益》一书中,赫希曼首先讨论了古代社会价值,发现在西方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圣奥古斯丁曾认为对金钱和财产的贪欲是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之一,而其他两桩大罪则是“权欲”与“性欲”。在古代社会,与单纯追求私人财富不同,对荣誉的热爱被认为能够重振社会价值。近代以来,这一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曼德维尔、弗格森(Adam Ferguson)、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乃至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真实本性,而曼德维尔、斯密和孟德斯鸠从各种视角发现了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却为社会和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赫希曼认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观念史的论争就是从承认并从制度上保障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抑制驯化古代人为荣誉和名望而奋斗的激情。赫希曼一开始就引用了18世纪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新科学》中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驯化过程:“社会利用使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者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道的存在,通过他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同上,p.17)。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维科已经从人们追求私利能转化为公共秩序和社会福祉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的天道,但仍然有圣奥古斯丁所论述的古代社会的价值判断的影子。由此,赫希曼进一步讨论了近代思想家的财富观:人的行为受利益支配,增加个人财富是正当的。按照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希望借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这是最普通、最明显的手段……”(同上,p.17)这些近代的思想家还论述了由利益支配世界之优点,包括人的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持久性、市场交易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业繁荣和社会风俗的改善。书中,赫希曼还引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温和得体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同上,p.61);“商业精神天然地会带来简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秩序和守纪的精神。只要存在这种精神,他所获得财富就不会产生任何坏的效果”(同上,p.71)。在其后,孟德斯鸠还认为:“商业的自然作用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互相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基于相互需要”(同上,p.80)。赫希曼接着评述道,可能孟德斯鸠对商业的赞美过于夸张了,但他自己相信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幸运的人们处于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赫希曼是如此欣赏孟德斯鸠的这一发现,以至于他把这一句话作为这本《激情与利益》一书的引语。赫希曼还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欲望制衡欲望,用权力制衡权力,人类社会就产生了有权力分立原则的现代民主政制制度,用孟德斯鸠的原话说:“要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对一些事物的安排(disposition of things),以权力阻止权力”。对此赫希曼进一步解释道:“用权力限制权力无限膨胀的‘事物的安排’,主要是通过各种制度性和宪法性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系来实现的。”(同上,pp.73~78) 在这本《激情与利益》中,赫希曼还讨论了诸多近代思想家关于激情与利益的关系的各种论辩,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是提到了托克维尔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第三章,赫希曼引述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从推罗人、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举出哪怕一个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民族它同时又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的例子。可见在自由与工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同上,p.122)。但是,赫希曼也同时注意到,托克维尔本人并不是主张只遵从和顺从人们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商业的发展,就必然会走向一个自由国家,因为“利益远不是驯服和约束统治者欲望的力量;相反,如果公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而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接着,赫希曼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句先知式的名言:“一个民族,倘若只知道乞求自己的政府维持秩序,那么在其心灵深处就早已成为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在它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打算给它套上枷锁的野心家也很快就会粉墨登场了”(同上,p.122~123)。回顾二十世纪跌宕起伏和充满巨大历史灾难的世界历史,再看看当今世界,托克维尔的这一判断似乎仍然有现实意义。 赫希曼在《激情与利益》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起源的阐释,在世界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潮好评在世界范围内纷至沓来。其中许多来自赫希曼从来没有预想到过的地方。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全都异口同声地赞誉这本书。这本书也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激情与利益》出版后,巨大的成功也把赫希曼推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他本人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思想企业家”和学术网络的“经纪人”。安排访问学者计划、聘任研究员、组织申请研究项目、组织和主持研讨会、为高研院募集资金,以及在世界各地做学术报告,占去了赫希曼的大量时间。但是,晚年的赫希曼,还是出版了两本篇幅不大但却在学术界有较大反响的学术著作:一本是《转变与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Hirschman,1982)(13);另一本书是《反动的修辞:悖谬论、无效论与危险论》(Hirschman,1991)(14)。 在《转变与参与》这本小册子中,赫希曼讨论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人们有时候积极参与像选举、游行、示威、罢工等等这些公共活动,而有时却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私人事务之中,而不愿参加公共行动?今天,一问这类问题,人们马上会想到,这可以用曼瑟尔·奥尔森(Olson,1971)(15)所提出的在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搭便车行为”理论来进行解释。如果这样理解,可能就误解赫希曼了。实际上,赫希曼正是从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商榷和争论中萌生出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的。赫希曼认为,“奥尔森是错误的”:他只抓住了一个点、刻画了人们可以选择的许多反应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就创造了一种“理论”,把人们偶然做出过的一种选择说成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将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第663页)。为了驳倒奥尔森的理论,赫希曼首先提出人们在私人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中的“失望”概念,且通过公众在私人领域的失望和参与公共活动的失望,解释了从私人领域参与到公共领域参与又回到私人领域参与的循环过程。因而,在这本书中,与奥尔森的无情“经济行动的逻辑”所提出的必然性理论不同,赫希曼从失望的概念入手,给出了人们在私人领域和公共活动“转变参与”的钟摆式的变化过程。 从赫希曼与奥尔森的论战来看,好像最后是奥尔森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理论上赢得了胜利,因而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广为引用的著作,而赫希曼的“转变参与理论”却很少有人提到和引用,并且遭到了不少经济学界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界的批评,包括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这些国际著名学者的商榷,而罗尔斯(John Rawls)好像也不赞同这本书的结论(第663、697页)。但是,如果我们把《转变与参与》和之前赫希曼在《激情与利益》中所提到的“弗格森—托克维尔悖论”的担忧联系起来,就会理解赫希曼为什么这样执着地坚持研究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和动机了。在《激情与利益》第三章,赫希曼指出:“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含蓄地批评了一个古老的思想传统,即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可取代争夺荣誉和权力的激情。他们没有乞灵于‘合成的谬误’,但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观点:尽管不是人人都玩‘无害的’赚钱游戏,只要大多数公民完全沉迷于这种游戏,就会让少数追逐更大权力的人更加容易实现其野心。如此一来,用利益代替激情作为大多数人行为的指导原则的社会安排,就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即这会扼杀公民精神,从而打开通向专制之门”。接着,赫希曼还追加道:“弗格森指出,丧失财富或担心丧失财富,可能使人们倾向于赞成专制体制”(Hirschman,1977/1997,pp.124~125)。读到《激情与利益》中的这些发现,我们就会理解赫希曼一个深层的担心: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遵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铁律,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动力又会何在?又怎样成为可能?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赫希曼撰写《转变与参与》这本小书的意旨了。从中我们也可以体感到早年受希特勒专制体制的迫害而一生坚持反对专制统治的这位现世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最终理论关怀了。 理解了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的上述终极理论关怀,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差不多十年后赫希曼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悖谬论、无效论与危险论》了。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探讨,晚年的赫希曼发现自己好像兜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希曼承认,“我可能是在探讨一种与‘通往进步之旅’相对的‘通往反动之旅’(或‘通往灾难之旅’)”。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总之,赫希曼终于要与他的“辩证的对立面”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了!要想理解改革进程为什么会充满艰难险阻,他就必须“更好地理解改革活动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和抗拒,为什么改革措施的回报一般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例如,被独裁政权中断,等等)”(第778页)。正如这本赫希曼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发现得那样:写作《反动的修辞》这本书,“赫希曼已经把自己一生的‘战斗经验’(或者说,人生体悟)全都倾注到了这个‘新项目’中了”(第783页)。 要理解《反动的修辞》,还要理解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变迁史。法国大革命以来,尤其是在德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实行了一种试图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的国家制度,后来受经济发展所迫,这些国家进行了一些改革,开始利用市场,进而承认并发展了私有产权制度。在德国,则出现了纳粹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这种在世界范围的“大革命”后从整体上设计一种国家制度的社会工程试验,哈耶克(Hayek,1944)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已经做了深刻的讨论和批判。这对赫希曼早年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战后,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一个政府干预、民主制度的完善和“福利国家”的制度演变过程。在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反动(reaction)思潮。这种保守主义的反动思潮之一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变革,反对民主制和普选制,反对福利国家制度(包括亨廷顿和哈耶克)。照赫希曼看来,这些保守主义的反动思潮,认为民主会危及自由;福利国家制度会危及自由或民主或二者全部,因而反对任何改革,主张“无意图”的制度演化。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一书中对这种世界范围的保守主义“反改革”思潮进行了批判,从而提出了批判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悖谬命题”(the perversity thesis)、“危险命题”(Jeopardy Thesis)和“无效命题”(the futility thesis)。赫希曼认为,悖谬论产生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当中。根据这种论证,任何旨在带来某种改善的有意图的努力都会使希望救治的对象的状态更加恶化:“一切都将事与愿违。”赫希曼认为,在两个世纪内,悖谬命题又进一步生发出了两个命题:“危险命题”和“无效命题”。“危险命题”是说,改革的成本不仅极其高昂,而且是带有惩罚性的,因为改革会危害所有以前取得的、非常脆弱的进步。“无效命题”则强调,所有旨在带来某种改革的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而都是无的放矢,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对付保守主义的这三个命题,赫希曼提出了要从“反动的修辞”转向“进步的修辞”。像他在早期《发展项目之观察》中提到的“隐蔽之手”要注重改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一样,赫希曼主张要积极地推动改革。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所撰写的一篇《〈反动的修辞〉:两年之后的回顾》的文章(收入赫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的文集第二章)中,赫希曼还特别指出,在俄罗斯、东欧和世界上的一些转型国家中,“各种各样的改革与过渡措施正在被摆上议事日程。这些国家面临着无数项紧迫的任务,其中最常被人提及的包括:民主化、私有化、经济重组、稳定宏观经济、补偿原先的业主,等等”(Hirschman,1995)(16)。在如此众多和重大的改革日程面前,赫希曼主张要避免“综合锁入症”(the getting-stuck syndrome),更要警惕反动的修辞,要更加积极地推进改革。 《反动的修辞》一书显然是赫希曼步入老年后对世界进步的最后“大声呼吁”,而在以前,赫希曼曾经考虑过退出。“时间老人的威严迟早会显露出来。现在,赫希曼已经太老了,他无法再做太多的实地研究,甚至没有精力重新退入历史中去与古人对话。逐渐地,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接过他留下的旗帜”(第788页)。1996年6月,赫希曼在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做完了帕托卡纪念讲座(Patocka Memorial Lecture)后,去阿尔卑斯山休假旅游。在下山的路上,赫希曼一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之后,医生将他诊断为脑血肿。自那之后,赫希曼的语言能力遭到损害。在阿尔卑斯山上摔得那一跤,也十分不幸地结束了赫希曼这位现世哲人的漫长写作生涯。16年后,在2012年12月10日,97岁高龄的赫希曼先生在靠近普林斯顿的尤因镇(Ewing Township)逝世。 四、余论:哲人的思想遗产 赫希曼逝世后,全球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各界社会科学家都表示了沉痛悼念,也给了这位伟大的现世哲学家很高的评价。如日裔著名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在《美国视野》(The American Prospect)上发表悼念文章,认为赫希曼“遗留的不是资料的收集或微观的成果,而是持续形塑我们思考方式的伟大观念(big concepts)”。赫希曼留给全人类的思想遗产确实是巨大的,这不仅包括他的十几本学术专著和几十篇学术论文,不仅包括他发现的许多经济学概念和原理,包括不平衡发展理论、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隧道效应、极化涓滴效应(Polarization trickle-down effect)等等——也许这每一个发现都值得获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重要的是他留给了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探索精神。 在1992-1993年撰写的一篇《自我颠覆的倾向》一文之最后,赫希曼曾引用了当代大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只有改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并且去进而发展某种新的观点时,才感到自己真正有活力”。赫希曼接着感慨道:“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Hirschman,1995)(17)。对于赫希曼这样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知识分子来说,自我颠覆只是其思想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能够不断超越自己过去的成见、偏见或误识,去发现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去阐释和弘传之,才是一个像他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大思想家当为的。哲人留给世人的,是他的思想和正确的、有益的理论,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传奇人生和事迹。 ①赫希曼的这本《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在英文书名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目前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李新华和朱进东的译本;一个是201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冯克利教授的译本。两个中译本都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就读了这本书的中译本。通过反复琢磨这本书的论述,我比较倾向于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和本书译者贾拥民的见解,觉得把“Passion”翻译为“激情”为好。另外,由于这本书的书名包含着“political arguments”,而不是“political debates”,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最好还是被较为精确些地翻译为《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辩》,而不是《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 ②Jeremy Adelman,Worldly Philosopher:The Odyssey of Albert O.Hirschman(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中译本:杰里米,阿德尔曼:《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贾拥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即将)出版。 ③Albert O.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eley,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5),reprinted 1969. ④1964年,赫希曼在《美国经济评论》(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根据那篇文章,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⑤Albert 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⑥Albert O.Hirschman,Journeys toward Progress: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3). ⑦Albert O.Hirschman,"Underdevelopment,Obstacles to the Perception of Change,and Leadership," Daedalus 97:3(Summer,1968):925-937.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还指出,拉丁美洲人并不是(旧)范式和观念的唯一囚徒,支配着北美。(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决策者的思维也好不到哪里去(第514页)。这种评论自然会引起一些经济学同行们的不快乃至愤懑,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总是对赫希曼“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是尽管赫希曼一生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发现(包括创生了“基尼系数”这个概念)但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原因。 ⑧鲍尔斯早年是一个在美国偏左的经济学家,现为美国桑塔费学派(Santa Fe Institute)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制度的演化理论中有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鲍尔斯早年曾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职,曾于在职期间状告哈佛大学,虽然他赢得了官司,但后来被哈佛大学解聘。2008年,我们曾邀请鲍尔斯教授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学,是笔者所熟悉的一个学术朋友。 ⑨Friedrich A.Hayek,"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Ⅳ(new ser.1937):33-54. ⑩Friedrich A.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XXV,No.4(Sept.1945):519-530. (11)Albert O.Hirschman,"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ith a mathematical appendix by Michael Rothschild),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4(1973):544-566. (12)其子也叫罗伯特·默顿(Robert Carhart Merton),是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因为与费雪·布莱克(Fischer Black)和迈伦·斯克尔斯(Myron Scholes)共同发明了金融期权数学模型,故与Myron Scholes共同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3)Albert O.Hirschman,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14)Albert O.Hirschman,The Rhetoric of Reaction:Perversity,Futility,Jeopardy(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5)(Mancur Lloyd Jr.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2[nd] ed.(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6)Albert O.Hirschman,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55. (17)Albert O.Hirschman,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