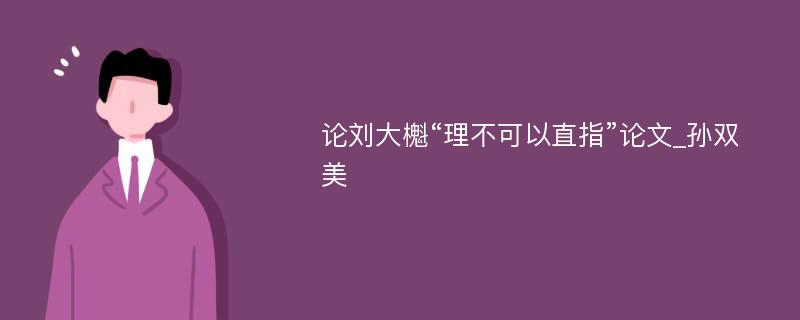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刘大櫆“理不可以直指”受“比兴”传统的影响,融“情”、“理”的表达于“不直”当中。字句的转折和托物言志、因事寓情是不直的基本内涵。梅曾亮、吴孟复等人的观点为这一说法做了有力补充。
关键词:《论文偶记》;“比兴”;直寻
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出:“理不可以直指”[1],认为:“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理”和“情”是作家思想表达的两个层面,从某种角度说可以上升到我国古代诗学的两大传统:诗言志和诗缘情。但从先秦、魏晋发展到明清,文学作品样式变得多种多样,受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乃至宋明理学、心学的影响,“情志”传统扩大到“说理论事”的层面。刘大櫆指出“理不可以直指”显然就是对这一方面的观照。
一、“比兴”传统与“不直”
单就“理不可以直指”而论,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比兴”。《毛诗序》中最早提出“《诗》有六义”,其中“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钟嵘《诗品序》:“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朱熹也对“比兴”做出过解释:“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5;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2]2”。通俗地讲,“比”就是比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吴孟复先生也说:“触景起兴为兴;托物寓意为比。”“比”与“兴”常常连用,作为文学家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
不论是“比”还是“兴”,其关键点就在于强调,表达内容或思想不能以过于直接的方式,而应借助一定的手法。也就是刘大櫆所说的:“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但刘大櫆并不是第一个将“比兴”说成“不可以直指”的人,唐代皎然、白居易等人就已提出类似的观点。
中唐皎然《诗式》中有“四深”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他还举例说明“比”应深曲“不直”,要耐人寻味:“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蛛丝’,以‘清’比‘玉壶’。”[3]
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有类似的论调。他指出“六义”中“风、雅、比、兴”的重要性:“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4]
到了宋朝,“理趣”成了宋诗的重要特点。唐诗“重情”,因此诗歌要表达的“情”、“理”多以抒情的方式展现,这种情感或思想的表现方式是磅礴的,汹涌的,讲求一览无遗、一泻千里式的充沛。宋诗不像唐诗一般浑厚浓重,往往以平淡语说真谛,但这种平淡并非思想的浅直,而是通过简单的物象,设置一个“曲径通幽”的探索途径。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全诗紧紧扣住游山来谈自己独特的感受,借助庐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哲理,故而亲切自然,耐人寻味。宋代有较多意象寻常而含义深刻的哲理诗,就是“不直”在宋代得以发展的佐证。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理不可以直指
这种“不直”进一步被刘大櫆界定为“理不可以直指”。刘大櫆所谓“不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不直”首先要体现在字句的层面。钱澄之《诗说》中即有“一句而有数折,一字足当数转”的言论。认为选择字词应当精当,字词句转折之中还应连贯顺畅。从刘大櫆《下殇子张十二郎圹铭》中一段就可以看出:“盼性缓,每垂髫自内庭徐徐行,至学舍,北向端拱立,长揖,乃就坐。又徐徐以手开书册,低声读;读一句视他人殆三、四句者。读毕,或归早餐,又徐徐行如来时状。”[5]简单三句话,三处“徐徐”,将人物性格、动作特点刻画地入木三分。
二是强调通过对物与事的描写来明理、喻情。如其《送姚姬传南归序》,通篇没有直接的安慰之词,但又无一字不让人体会到他对姚鼐的赞赏与鼓励。文中言自己的漂泊事迹,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姚鼐暂时的“不得志”的安慰,从而流露出作者的包容、惋惜、鼓励之情;又以“昔王文成公童子时”之事迹,借王守仁之口说出孟子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尧舜为不足为,谓之悖天,有能为尧舜之资而自谓不能,谓之漫天”的道理,并言“若夫拥旄仗钺,立功青海万里之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而余以为抑其次也”,以此表达对对姚鼐的期望。因此这篇文章很好地表现了刘大櫆“即物以明理、即事以寓情”的观点。
刘大櫆作为“桐城三祖”之一,对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同样,桐城派中其他一些作家的观点对刘大櫆的“理不可以直指”也做出了有力补充。
一是文章结构应注意有反有正、有开有合。在论及这两方面时,梅曾亮说:“文气贵直,而其体贵曲,不直则无以畅其机,不曲则无以达其情。”这其实就是“即物以明理”、“即事以寓情”的另一种说法。姚永朴也说:“文章忌平铺直叙,要有反正,有开合,有宾主。正面不宜繁衍;反与开与宾无非托出正面。”这里的“忌平铺直叙”就是要“不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处理好文章的正反、开合问题。文章有中心,就意味着行文中的诸多线索最后要有同一个归宿,线索的排列就不得不论清主干和旁支。旁支不能简单看成次要,它对一篇文章的气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共同为文章的“反正”、“开合”服务。吴孟复先生甚至认为:“由于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曲折的,所以要多方面地写,要曲折深入地写,但它又是一气呵成的。曲与直,这也是辩证的统一。”[6]将文学与哲学相联系,吴先生的观点将刘大櫆的“理不可以直指”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从不同的文体中解析出散文创作的独特方法,但又不排斥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汲取有利于文意充分表达的手法。但这种手法并不是固化了的创作模式,而是将古文创作的自由思想、雅洁风貌运用到“时文”的创作中,也因此方苞的“时文”较之当时一般“时文”有更强的可读性。可见,文体本身不存在高下之分,重要的是创作者能否充分利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或艺术思维来进行创作。在刘大櫆及桐城派其他作家意图找到文学创作的适应性语言时,就已经是在文章的曲折尽意处下了功夫。这是不同的文体之间相交融的结果,更是桐城派作家们对待创作须“不直”的态度的体现。
“理不可以直指”并非文学创作的唯一标准,文体的不同、创作动机的不同、表达方式的不同或是作家个人才力的高下以及欣赏者爱好倾向不同等各种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的审美结果。但我们必须看到刘大櫆此观点及其源来的合理性。“理不可以直指”不仅仅对当时作家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今时代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江小角,方宁胜.桐城历史文化丛书•桐城明清散文选[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110.
[2]朱熹.诗集传[M].王华宝,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
[3]沈松勤,胡可先,陶然.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57.
[4]霍松林.白居易诗选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330.
[5]刘大櫆.刘大櫆文选[M].吴孟复,选注.合肥:黄山书社,1985:105.
[6]吴孟复.桐城文派论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50
作者简介:孙双美(1995—),女,安徽宣城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论文作者:孙双美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9/4/4
标签:不可以论文; 桐城论文; 刘大论文; 明理论文; 安庆论文; 安徽论文; 文体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