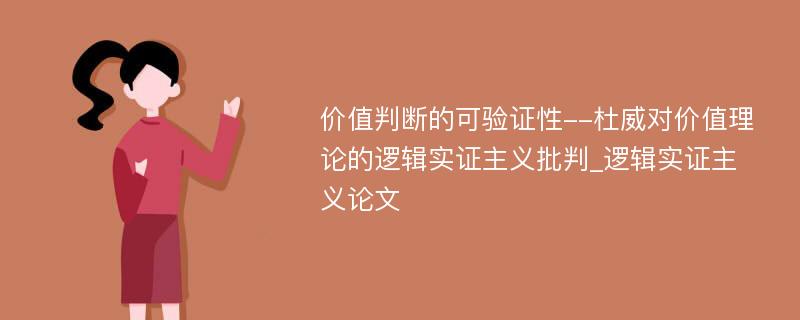
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杜威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价值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5—0112—008
20世纪价值哲学最强悍的对手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断言:价值判断只是情感的表达,它无真假可言,因而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并以此为由粗暴地将价值问题驱逐出哲学。的确,倘若价值判断真是无真假可言、真是不可能进行理性的讨论,倘若价值判断的有效性真是无法得到理性的辩护,那么哲学将价值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事情。倘若人类生活可以没有价值判断的引导,倘若价值判断的好坏对人类的生活的结果微不足道,那么价值判断是否有根据、有道理、有效用也就无关紧要。然而,所有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人类行动,似乎无一不受价值判断的制约[1—p2]。而且人类历史的每一步都证明着凡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都受到价值判断的引导,其间区别仅在于受未经理性反省的价值判断的引导,还是受经过理性反省的价值判断的引导;受他人价值判断的引导,还是受自己价值判断的引导;受有根据的价值判断的引导,还是受无根据的价值判断的引导。而且人类历史的每一步也都证明着因为价值判断的不同而行动的结果有天壤之别。通过有根据的价值判断而引导人类生活,这是哲学的存在方式。而当人类活动比以往更需要有根据的价值判断引导的时候,哲学却说:对于价值问题我无能为力,而且我原来所为也是一种僭越。这不啻是对人类理性和哲学本身最大的讽刺。难怪当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立场被艾耶尔以极端的语言表达出来后,会引起哲学家们强烈的愤慨和连绵不断的斥责。它同样也激起了杜威的愤慨: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价值判断堕入强权的股掌和习俗的玩弄。一定要捍卫哲学研究价值问题的合法性,一定要使价值判断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基础之上。这就是杜威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始情感。在杜威看来,对于人类生活而言,价值判断是否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是否可以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的问题,绝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杜威来说,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就是捍卫哲学研究价值问题的合法性,就是捍卫哲学和理性的尊严。因此,杜威价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艾耶尔所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
“可证实性原则”是艾耶尔放逐价值问题的根据。艾耶尔对这一原则的界定是:当且仅当一个陈述要么在分析的意义上是可证实的,要么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时,该陈述在字面上才是有意义的[2—p5]。根据这一原则艾耶尔做出了以下推论:当且仅当一个陈述具有分析意义上或经验意义上的可证实性时,这个陈述句属于命题;只有命题才有真假意义可言;只有具有真假意义的命题才可以进行理性研究;只有可以进行理性研究的才属于哲学研究范围;而伦理判断、审美判断等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既不具有分析意义上的可证实性,也不具有经验意义上的可证实性,所以价值判断不是命题,无真假可言,理性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价值问题不能是哲学研究的题材。对于艾耶尔的推论,我们至少可以有四个选择:一是接受艾耶尔的可证实性标准,也接受艾耶尔关于价值判断不是命题的断言。即使这样,在逻辑上我们也并非必须接受艾耶尔关于“价值判断仅是情感表达”这一结论。如果我们连艾耶尔的这个结论也全盘接受,那我们就是艾耶尔这一理论的彻底的支持者。二是接受艾耶尔的这个标准,但反对艾耶尔关于价值判断不是命题的断言。那么,我们就需要证明:价值判断是可证实的。三是不接受艾耶尔可证实性的这个标准,也不接受他关于价值判断不是命题的主张。如果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可证实性原则的局限性或批判其荒谬性。如果不仅是批判还要建构的话,我们就需要阐明价值判断的性质及我们判断价值判断性质的根据。四是跳出艾耶尔的推理逻辑,而揭示在这一逻辑背后、支撑这一逻辑的信念。普特南采取的是第四种选择。他将批判的火力集中于支撑这一逻辑的信念基础: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割,并将“事实”作为分析的焦点。而杜威采取的是第二种选择。杜威认可“可证实性原则”,但反对艾耶尔关于价值判断不是命题的结论。因此,杜威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就表现为对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证明。
杜威将艾耶尔的理由分解为三:其一,价值表达是纯粹的喊叫,它不包含任何命题,因而是不可证实的;其二,价值判断表达的是情感和欲望,而情感和欲望是主观的任意的,因而是不可证实的;其三,价值判断不包含任何可以得到经验证明的命题,因而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针对这三个理由,杜威的结论是:1、价值表达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因而对此可以、而且必须进行理性研究;2、情感和欲望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因而对此可以、而且必须进行理性研究;3、价值判断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因而对此可以、而且必须进行理性研究。
一、价值表达的可证实性
价值表达不能由命题构成,因为价值表达纯粹是喊叫。它们并没有表示什么或陈述什么,甚至没有谈论情感;只不过是表现出或显露出情感而已[1—p6~7]。艾耶尔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价值判断与判断者的利益、欲望是那么密不可分。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又存在着那么多像喊叫似的价值判断。而且用“那不过是喊叫”而打发掉自己所不赞同的价值判断是最省事而且最心安理得的饰词。但与艾耶尔不同的是,人们原以为只有“坏”的价值判断才这样,只有别人的价值判断才这样;人们原以为可以用绝对可靠的理由支持自己的或自己认同的价值判断。所以当艾耶尔说所有的价值判断都不过如此的时候,这个全称判断沉重地打击了人们的信念。当意识到左右我们行动的所有价值判断都不过是毫无理由的“喊叫”,而我们的选择只能受这样的判断支配时,人们感到了恐惧与绝望。在貌似强悍的对艾耶尔的谴责声中其实浸透着这种恐惧与绝望。而杜威通过将价值表达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看成主体间的“交互作用”而揭示了价值表达的本质,批驳了艾耶尔的断言。
杜威的批判从分析婴儿原始意义上的哭开始。虽然这种原始意义上的哭只是有机体活动的事实,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什么价值表达,但是它可以被当作某种有机体状态的信号,因此它会引起一定的回应。而这种回应会使婴儿逐渐意识到哭的作用,即意识到特定的哭与所能引起的行动,及其由这种行动而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联。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种原始意义上的哭,就被一种有目的的、为引起特定结果而进行的哭取代了。而有目的的哭是一种语言性的信号。它不仅说了什么,而且是有意识地说、有意识地告诉他人什么的[1—p10~11]。那么它究竟说了什么呢?杜威认为它说了三点:(1)存在一种将带来不良后果的状况;(2)我不能应付这一状况;(3)如果能得到他人的帮助,那么这种状况将得到改善,我所期望的就是这种状况的改善。这三点都可以得到具有经验证据的检验,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可观察的。这种哭所欲达到的结果是可观察的,并且也是可用命题表述的。杜威认为,发生在可观察的情境中的这种哭,表达了某种复合的东西。这种复合的东西不能用“情感”一词来囊括。艾耶尔曾说,价值表达与这种哭具有同样的性质。那么价值表达就是以唤起他人的反应为目的的有机体的活动,是一种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现象。因此,应该得到重点解释的就是:价值表达通过引起他人的反应而影响他人行为举止的作用,而不是价值表达者的心理状态。
杜威认为,在我们讨论诸如此类主体间交互作用的时候,引入“情感”一词是多余和毫无理由的。首先,它与使我们讨论得以开始的明显的事实相反;其次,它引进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如果不说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问题。因为我们所着手讨论的并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以哭、眼泪、微笑等所组成的一种有机体的状态。因此,“情感”一词要么是一种严格的行为术语,是包含了哭和姿势在内的整个有机体状态的一个名称,要么就是被毫无必要地引入的一个词。如果哭是原始意义上的,那么它是更大有机体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哭是故意而为之的,那么哭所表达的就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改变有机体状态的要求,而这种改变只有靠其他人采取某些行为才能实现。既然如此,我们需要解释的就是主体间的交互作用。而要解释这一点却引入根据其描述完全是私人的、是仅在个人内省时才可以触及的状态,引入了一个难以进行公开检查或证实的术语,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1—p10]。假如我们要讨论价值表达,我们就必须集中考虑具有经验意义的部分,即集中考虑那些能引起他人某些反应的、而且能控制其产生的有机体的活动。杜威明确地说:价值表达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心理现象。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主体的内在状态,而是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或交互作用。如果我们剔除了“表达”的模糊性和“情感”的不相干,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价值表达”只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相关,或者说,价值表达只存在于人与人交互作用的关系中。这种交互作用是可以接受公共观察和描述的[1—10]。杜威认为,一旦手势、姿势和言语被理解为信号时,尤其被用作信号时,它们就成了语言符号,它们就表达意义并具有了命题的性质。在可得到经验观察、可得到经验验证这一点上,这类命题与一切真正的物理学命题是相同的。因此杜威的结论就是:如果艾耶尔所说的表达是评价的话,那么:(1)评价现象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或主体间交互行为现象;(2)评价现象就和那些能为可被经验证实或驳斥的事实命题提供素材的现象是同样的。表达价值需求的命题直接涉及的是现存状况,间接涉及的是意欲达到的、所期望引起的未来状况。而价值表达就是人们用来引起从当前状况到合乎期望的未来状况的转变的一种媒介[1—p11]。
杜威指出价值表达实际包含了三个命题:赋予实际存在状况以否定性的价值命题;赋予所预期状况以相对肯定性的价值命题;作为中介的命题(这类命题可以包含、也可不包含评价表达)。作为中介的命题,是一个引导行动的命题,即是一个关于改变现有实际存在状况,形成一种新的实际存在状况的行动的命题[1—p13]。这三个命题有两个是关于实际存在状况的,一个是关于改变实际存在状况的行动的。无论是关于实际状况的命题还是关于行动的命题,都是在经验上可证实的命题。因此,根据艾耶尔的“可证实性”原则,理应得出的结论是:价值表达是包含命题的,这些命题是有真假意义的。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价值理论,杜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价值表达”是一种喊叫,即使它以喊叫的方式而影响他人的行为,关于价值表达的真正的命题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探究这些表达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并且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成功地获得了预期结果的事例,与不能成功地获得预期结果的事例的条件是不同的。在此,区别“情感”语言表达和“科学”语言表达是很有用的。即使“情感”语言表达没说什么,但是,它们仍然能像其它自然事件一样,作为对其条件和效果进行检验的一种结果,而成为“科学”命题的题材[1—p51]。
通过上述分析,杜威将对价值表达的研究转换成对社会行动的研究,转换成对行动情境、支配行动的态度和人们行动“所期待的结果”的研究,而这些都是可以得到经验支持和经验证实的研究。这样价值表达就不再是一个不可说、不可讨论、不可争论的问题,就不再是应该被排斥在理性之外、哲学之外的问题了。哲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价值表达作为自己的研究题材了。对价值表达的这一分析,尤其是对引导行动这一中介性命题的揭示,是以往价值理论研究严重忽略的诸多问题中致命的一个。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价值表达、价值判断才会被当成一种主体情感和偏好的表达,才会被当成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不可说、不可进行哲学研究的内容。换言之,艾耶尔的断言才会被当成伦理学、美学等诸如此类的价值研究的死刑判决书。因此揭示价值表达所包含的这三个命题,尤其是引导行动的“中介性命题”,对于批判艾耶尔的反价值理论来说可谓一剑封喉。人际间的交互作用、社会行动是杜威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关键。我们所有的价值表达都是与人际间的交互作用相关的,只有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在社会行动中,我们才能把握价值表达的真谛,才有可能对价值表达进行理性的反思,也才有必要对价值表达进行理性的反思。离开了行动,无论我们将价值表达看成什么都无关紧要。
二、情感、欲望的可证实性
“价值”不过是情感的别名,不过是欲望的表达,艾耶尔因此而放逐价值问题。情感、欲望与价值的确难解难分,从哲学关注价值问题开始,研究者们就无一不将价值与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情感、欲望看成价值判断的特质,看成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界石几乎成了价值论研究者的共识。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价值判断与情感、欲望如影随形、都曾感受到情感、欲望的飘忽不定,所以逻辑实证主义将价值判断看成是情感,欲望的表达似乎无懈可击,将表现这种飘忽不定和具有极强个体性和时间性、情境性的价值判断看成无真假可言似乎顺理成章。面对这样一种获得常识强有力的支持而逻辑上又似无瑕疵的论证,杜威能证明情感的可证实性吗?
如果抽象地谈论情感、欲望,我们很容易得出与艾耶尔相似的结论;如果我们将情感、欲望放置在提出问题的语境中,放置在评价活动中,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与杜威相似的结论。这种放置意义重大。因为如果离开了提出问题的原始语境,我们就会把一个本来可以讨论的具有具体形态的问题变成一个抽象的甚至不可讨论的问题。通过这种放置,杜威所要证明的就不是抽象的情感、欲望是否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而是具体的评价活动中的情感、欲望是否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因此,问题的重心就从情感转到了评价活动、转到了人的行动。还是那句话,离开了行动,无论我们将情感、欲望看成什么都无关紧要。杜威证明情感、欲望可证实性的关键是:行动和情境。
评价是在有问题的情境中发生的。正是由于对现有环境(影响人活动的各种条件的综合)的不满意和创造一种新的环境的渴望才使评价活动得以产生。如果没有这种需要、没有改变现有环境的欲望,就不会有评价,就如没有疑问就没有探究的理由。恰如激发我们进行探究的问题是与出现问题的经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欲望和对作为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评价,也是与具体的环境及其改变环境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考察构成匮乏和需要的条件,考察作为构建可实现的目的或可达到的结果的积极手段的条件,就是构建正当的(必需的和有效的)欲望和所期望的目的的方法。这一考察和构建活动就是评价,换言之,评价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1—p55]。而评价所考察的这些问题和所进行的构建都是可以获得经验证实的。
评价中的情感、欲望与发生评价的这一具体的情境血肉相联,它们是在这种情境中生成,受这种情境限制的。因而它们都不是任意的,都不是无根由的,都不是不可进行理性研究的。面对身处其中的环境,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二是拒绝。“接受”就意味着努力保持现有的环境,并想方设法抵御会使这种环境发生改变的各种不利条件。而“拒绝”就意味着努力摆脱现有的环境和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环境。接受和拒绝不单是情感、不单是欲望,它还是行动。这种行动以“所期望的结果”即一种新的环境为目的。人们把什么看作是有价值的,而把什么看作是没有价值的都是受这个目的制约的。如果我们脱离这个具体的情境,而将情感、欲望当成是原初之物,我们就会认为情感是不可分析的、不可研究的,我们就无法对它们进行经验检查或检验,也无法对它们进行批评了。而这在杜威看来,脱离具体的情境而把情感、欲望(包括兴趣)看成是原初之物,是当时流行的价值理论产生混乱和出现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情感、欲望、兴趣真的具有这种原初性,如果它们真的独立于具体的经验情境的构建和需要,并且真的因此而对情境的改变毫无作用,那么,坚持每种情感中、每个欲望中必然有观念的或理智的因素,并且进而坚持实现有效的经验条件的必要性,也就是多余的和不切题的。但是,在经验事实中,离开了产生情感和欲望的行动领域,离开了情感和欲望、兴趣得以产生和作为拙劣的或有益的手段而发挥作用的活动领域,就没有任何情感、欲望和兴趣可言。所以杜威认为坚持每种情感中、每个欲望和兴趣中必然有观念的或理智的因素,并且进而坚持实现有效的经验条件的必要性这一点,纯粹是、而且完全是为了对现实情况进行恰当的经验考察,为了避免大而空地玩弄情感、欲望和兴趣概念。因为,将情感、欲望和兴趣与其存在情境隔离开来,必然导致大而空地玩弄情感、欲望和兴趣概念[1—p55]。
杜威认为:如果我们发现情感、欲望只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即只有当某种匮乏妨碍了行动意向直接实行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感和欲望的产生;发现情感和欲望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以弥补现存缺憾的方式起作用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可以要求以可证实性命题的形式表述情感、欲望和评价的关系。(1)我们看到,情感、欲望的内容和对象依赖于使它产生的特定情境,而这一情境又依赖于人的活动和先前存在的周围环境。(2)我们看到,包含在情感、欲望中的最基本的张力是努力,而不是随情感、欲望而至的东西。因为情感、欲望并非仅是个人的,它还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行动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真正的欲望与纯粹的想要和幻想区别开来。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情感、欲望相联系的评价,是与情感、欲望存在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存在环境中,情感、欲望是不同的,评价是不同的。既然评价的存在依赖于环境,那么它的恰当性就在于它对环境所产生的需要与要求的适应。既然环境是可观察的,并且评价适应环境与否应根据对努力之结果的观察得以判定,那么,一种特定欲望的适当性就可以通过命题来表达。而且这些命题能够经受经验的检验。因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方式,而探知一种特定的欲望与它发挥作用的条件之间的联系[1—p16]。
杜威处理评价中情感、欲望和兴趣的基本立场就是:从可观察可辨认的行为方式的角度来考虑它们。杜威认为,就行动而言,“情感驱动”这个形容词,还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将“情感”解释为私人的“感情”。因为这样的解释会抵消这一词组中“驱动”一词所表达的那种能起作用的和可以进行观察的要素。“驱动”发生于公共的可观察世界。而且与发生于这个世界的其他事情一样,“驱动”具有可观察的状态和结果。如果把“喜欢”这个词用作指称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用作指称一种私人的、难以捉摸的感情,那么它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类活动:为了使那些能让我们从中而获得满足的条件延绵不断而“费尽苦心”、“想方设法”。这是一种行动意义上的享受,它以花费精力赢得作为满足之源泉的那些条件为特点[1—p14]。如果我们从行为方式的角度去理解情感、欲望,那么我们就可以免于那种脱离所指的对象而界定词意的徒劳。这样我们就会去注意那些能够做出详细说明的实际存在着的情形,去观察在现实情形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去观察我们的精力是否被用于创造某些条件和维持某些条件。用日常术语来说,就是去注意是否已经尽力了,是否已经尽力去创造那些条件而不是其他的条件了[1—p14~15]。这样情感和欲望就是可以进行观察的,关于情感和欲望的判断就是有经验根据和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至于情感、欲望是否飘忽不定,是否因人而异,这根本不能成为情感不可证实性的理由。在关于评价中的情感和欲望的问题上,我们所需要弄清的就是:情感和欲望是不是无经验根基的;情感和欲望是不是不能进行经验考察的;对情感和欲望的考察是不是不能借助经验的方式。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情感和欲望就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这就是杜威讨论评价中情感和欲望问题的逻辑。
三、评价判断的可证实性
人类生活中有两种典型的价值体验情形:一种是在我们并没有对某种东西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我们就堕入了对这种东西的珍爱,就享受了这种东西的美好。另一种,我们必须通过评估、鉴定或评价才能确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才能进入对有价值的东西的珍爱,才能感受这种东西的美好。后一种情境的显著特征是怀疑、不确定和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或是应该要什么。在这种情形中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目的、我们所期望的善和达到这种善的方式进行仔细的考虑和权衡。在前一种情形中没有评价也没有价值判断,只有价值体验。只有在后一种情形中,才有评价,才形成评价判断,才有值得价值论研究的题材。在后一种情形中,只有当按照这一评价判断进行了行动,并且这种行动产生了某种结果之后,才会有前一种情形意义上的价值体验。杜威不否认前一种价值体验的存在,杜威将引起这种体验的价值称之为“直接价值”,但杜威否定将这种价值作为价值论研究的题材。对于前一种情形,杜威说过一句很著名的但也引起了很多误解的话:“价值就是价值,它们是直接具有一定内在性质的东西。仅就它们本身作为价值来说,那是没有什么话可讲的,它们就是它们自己。”[3—p251] 因此如果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是这种价值的话,那么首先他们根本不应该用“价值判断”(相当于评价判断)这个术语。其次,他们的反价值论结论就无关痛痒了。因为哲学并不是以这样的价值为对象的。哲学是一种以真的方式诉说价值好的学问,因而哲学不是描述现实,而是筹划未来的学问,哲学的旨趣是指向未来行动的应当,所以只有第二种情形中出现的问题才是哲学研究的题材。伦理学如此,美学如此,哲学也是如此。
杜威认为,人类生活中一切令人困惑的境况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我们真的难以形成关于具体情境中的价值的判断[4—p268]。因此,如果说价值论能对人类生活有所作为的话,那它就必须直面这一难题,为解诀这一难题提供智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在未经任何努力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价值,价值论描述这一现象不能说毫无用处,但绝无大用。因为这不是人类生活中的难题。哲学要研究的是人类生活中的难题,换言之,只有生活中的难题才应该成为哲学的题材。所以,杜威明确地将自己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聚焦于评价判断这一难题,而将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第三个理由的反驳限定为:对评价判断可证实性的证明。
“评价判断”是杜威独创的术语。杜威之所以要用这一术语指称“价值判断”,是因为价值判断这一术语已被滥用。杜威说,人们在使用价值判断这个术语时,常常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混为一谈。其中一种判断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一种是“评价判断”。所谓“关于价值的判断”就是对已经存在的某个东西的价值的报道和陈述。这种判断是一种事后判断。作为判断它与其他关于已经存在的事实的判断没有任何不同。而评价判断则不然。因为评价判断就是关于经验对象的条件与结果的判断;就是对于我们的向往、情感和享受的形成应该起着调节作用的判断[4—p268]。① 评价判断是一种事前预测性判断。只有当我们面临困境不得不谨慎地进行选择的时候,才会有评价判断。在进行评价之前,作为评价之目标的价值尚未存在,它只是一种可能性[5—p10~11]。所以评价判断是关于经验对象的条件和可能结果的判断。这种判断是预期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是实验性的,而不是报道性的;是假设性的,而不是陈述性的;是复合性的,而不是单一性的。
评价判断由一系列次一级的目标和次一级的判断所构成。行动是评价判断的直接目标。换言之,评价判断首先表现为关于一种行动的价值的判断。而关于这种行动的价值的判断是建立在一系列非价值的事实分析基础上的。评价判断中比行动更进一步的目标是:建立在更充分的数据和理性基础上的关于喜欢、兴趣的价值判断。即对什么是我们应该喜欢的、应该欲求的判断。我们喜欢的和我们欲求的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喜欢、应该欲求的。这种“应该”是建立在对事实、关系和各种可能性、各种因果关系的分析基础上的。在这种分析中我们肯定或者修正我们的喜欢和欲求,或者否定我们的喜欢和欲求,或者建立一种喜欢和欲求。杜威将经过判断的喜欢和欲求称之为深思熟虑的喜欢和欲求。它们就是评价判断继行动之后的又一个次一级的目标和判断。评价判断中具有决定性的目标和判断,是关于所要创造价值载体的价值的判断[5—p15]。这三个次一级的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评价判断完整的整体。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评价判断,在这样的意义上考虑评价判断的可证实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评价判断的性质,杜威分析了评价过程。杜威说,在形成这些次一级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将我们要进行判断的东西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观察。观察,是行动的座右铭,更是判断的座右铭。我们必须收集各种相关的非价值事实,并且对这些非价值的事实做出陈述。我们还要做出一些关于给定关系的一般性的判断或陈述,同时我们还要对不在这一判断之中的价值,或者这一判断所认可的价值做出陈述。许许多多直接的“好”和颇有价值的东西,许许多多内在的“好”和贡献的“好”,我们可以将它们合并在判断形式中。如果评价判断是理智的,或是评价判断要成为一个判断的话,我们就必须这样对它们做出陈述[5—p16~18]。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大量判断都是可以在经验中得到证实的。因为这些判断是对一系列后果、因果关系的判断,它表达的是在经验上可证实的事实。如果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不可证实的,那么科学也是不可证实的;如果连科学都是不可证实的,那么“不可证实性”就不独是驱逐价值判断的理由。如果“不可证实性”能让我们驱逐所有的判断,那保存它只能是人类思想的自虐和自杀。但杜威的批判并没有在此驻足。
杜威明确地意识到,忽略这些次一级的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判断,恰是逻辑实证主义将一个现实生活中实际的行动选择问题变成概念游戏的症结所在。尽管这些次一级的判断不等于最后的价值判断,但它们支撑着最后的价值判断。离开了这些次一级的判断,最后的价值判断就是任意的。同时杜威也明确地意识到,评价中的这些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对已知价值的陈述以及这些判断和陈述之间的联系,并不足以确定具有决定意义的评价判断。我们仅仅将这些判断和陈述结合起来是不够的,仅仅将各种已知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够的,因为那些判断和陈述存在于不同的维度中。在构成新的评价中不同给定价值的相对权重问题,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就这种争论而言,任何给定的事实和价值都不具有决定的意义[5—p18~19]。即使评价判断中所有关于非价值事实的判断都能得到经验的证实,也无法证明最后形成的评价判断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因此我们必须直接面对最后形成的这个评价判断是否具有经验可证实性的问题。
杜威的观点是:最后形成的这个评价判断是一种预测性判断,它所预测的是一种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可以得到经验检查的,因此这个预测性判断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像所有其它判断一样,评价探究所达到的判断或多或少在特定境况中是有充分根据的,尽管它没有超时空的绝对根据;它是部分地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尽管它无法得到经验的完全证实;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得比这更多一点。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可以被完全证实,就像没有什么事实判断可以被完全证实一样。任何实验在解决一个疑问的过程中都隐藏着一种新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判断和实验性检验就对我们毫无益处,或是我们应该靠投掷硬币这样的方法来决定取舍[4—p123]。评价判断是“实践”判断,也就是说,它是与某些情形相关的。在这些情形中事物的价值,或行为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而且它们是与某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会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创造一种条件,以使某种具有确定价值的东西能够产生[6—p23]。
生活本身是充满风险的。评价判断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的评价深思熟虑,但我们的选择依然要舍弃某种东西,而被舍弃的东西,也是我们无法再对它们进行实践检验的东西。这是评价判断经验可证实性的盲区。正因为这一事实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为评价和实验确定一个相当重要的座右铭:“留意你的可选项,以判断为条件的行动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在一定条件下的检验的可能性,以及最大限度的有充分准备的重新评估。”这一座右铭与偏执——对可选项的忽略和拒绝——正相反,也与乌托邦——含糊其辞或泛泛而议——正相反,否则我们将在选择和计划的结果的意义问题上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杜威认为,没有什么“理想”是无准备地或批发式地全部实现的。我们只有通过行动使之具体化,其意义才能更加清晰,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理智地行动[5—p25~26]。一个特定的对象是值得尊敬、值得钦佩、值得赞赏、值得向往的,这样的判断是假设判断或逻辑论证判断。而逻辑论证不能直达存在。行动是通往存在的唯一道路。“值得”是理性赏赐给“价值”的礼物。当理性悬浮在假设中时,在理性转变为行动之前,它还只是有名无实的、无效果的[5—p26~27]。我们只能通过行动的结果来反思和改善我们的评价,并通过评价而引导新的行动。我们只能这样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一步一步前行。
价值判断是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因此我们可以也必须对价值判断进行理性的研究,我们必须在进行价值判断时采取审慎的科学的态度;价值判断得到的经验证实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行动和对行动结果的理性的反思而不断修正我们的价值判断,再通过行动验证我们的判断。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每一次选择的风险与可能的遗憾。杜威就这样通过对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证明,捍卫了哲学研究价值问题的合法性,捍卫了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尊严,捍卫了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实验经验主义的价值研究之路。
[收稿日期]2006—05—21
注释:
① 重点号为杜威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