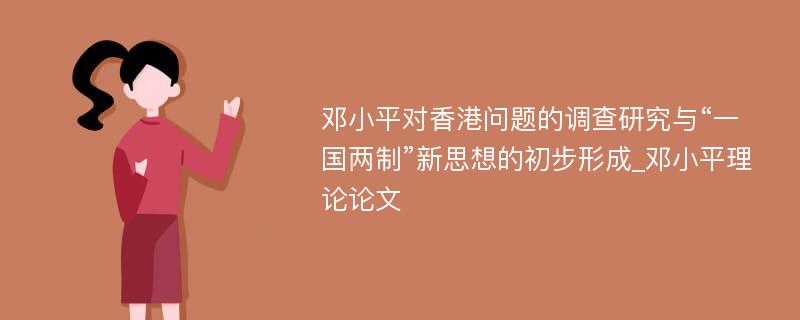
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香港论文,调查研究论文,一国论文,初步形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是以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正式拉开序幕的,而其“前奏曲”是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自1979年至1982年,中国政府对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进行了整整三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维,制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为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主要是由于时间性、政策性和资料性的限制,在“九七”前后的学术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的“人与事”在香港回归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省略了,视野模糊。本文拟根据近年来海内外公开发表和正式出版有关香港回归的历史资料,对1979至1982年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香港模式”新思维的初步形成问题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彻底地解决香港问题、彻底地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的决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新中国缔造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香港问题“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将“香港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作为自己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之责,有决心和信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国家统一之梦!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讲:“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注:邓小平:《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是由英国方面首先“解冻”的,其“敲门声”就是1979年3月的麦里浩访华。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其“重中之重”——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在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发表了多次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7页。)。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内部谈话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1979年1月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即:“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注:《人民日报》1977年1月1日。)。它标志着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已经开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国一制”的传统模式,向“和平统一”和以“制度不变”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嬗变。
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为紧迫性的问题而列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具体政策上的“纠‘左’”,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使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经济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978年4月,受邓小平的委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一个月,重点是清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对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指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事务办公室(1978年10月开始改隶国务院)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于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务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指出:“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注:《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0页。)
但是,中国方面“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的“香港的现状”的策略性安排,很快被英国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上的突然发难所打破。为迎接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英国方面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将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这是“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根据197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囿于此一“大限”,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第68页。)。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能够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将治权与主权剥离,“以主权换治权”。当时,有两件事激起了英国人的幻想:一是邓小平的开明形象和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引进离不开香港这个传统的国际通道,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扼杀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鹅”的“愚蠢的想法”(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58页。)。二是中葡两国建交时对澳门问题的“搁置”。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中葡两国政府在建交谈判中就澳门问题秘密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管理,适当时候将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注: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英国首相欧文“非常兴奋地”发现,在1979年2月8日发表的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只字未提澳门问题,“他觉得中葡好像承认了澳门作为葡萄牙托管的领土的地位”,这样,英国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门模式”对主权作出让步,而要求以“续约”的方式继续维持管治权(注:David Owen,Time to Declare,London,1991,p407.(欧文:《宣告之际》)。)。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忽略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对于台湾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英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解决台湾问题与解决香港问题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以至于在以后的中英两国外交交涉中,邓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动的英国人,要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新思维。
英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里浩访华时和4月英国首相欧文访华时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非正式地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
二
英国选择“土地契约”问题发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70年代末期,由于距离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愈来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开始表示关注。特别是愈来愈多人感觉到新界各项批地契约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英国政府与当时香港总督磋商,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后,作出结论,认为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减少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因此,当香港总督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于1979年3月前往北京访问时,英国政府便主动试行设法解决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注:White Paper:A Draf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September,1984.(白皮书:《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草案》)。)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敏感性,英国政府决定“侧面进攻”。他们在麦里浩离开香港前发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务问题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约的问题,而不应以政治问题的形式提出来。他特别应该强调英国并不准备在现阶段寻求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而是仅仅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着想,以方便长期投资。麦里浩还要询问中国,香港政府对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中所注明的1997年6月27日这一期限能否修改为本契约‘在英国统治这地方的时间内有效’。……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开对话的局面。”(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2页。)
1979年3月28日,麦里浩一行抵达北京。29日,邓小平会见麦里浩。由于中国方面对麦里浩北京之行的目的心中有数,所以邓小平在与麦里浩的谈话中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并没有回避,“未待麦里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议,邓小平已抢先表态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讲:“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29日。)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归回祖国的方式。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29日。)
关于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英国人是有心理准备的。“麦里浩认为当天会议气氛甚为融洽,所以随即向邓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十五年为期售卖官地的刍议。”(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第20页。)麦里浩字斟句酌地“点题”:“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29日。)但是,“英国期望的‘点头接受’并没有出现”。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对于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偷步”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小动作”十分敏感,他明确地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8页。)邓小平告诫麦里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9页。)。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邓小平讲:“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因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会见结束前,麦里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第21页。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三
在邓小平面对面地迎接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突然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思维——“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在酝酿过程中,其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而且其设计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如“一个中国”的原则,“两手准备”的原则,“尊重现实”的原则,“特殊地位”的原则,等等。邓小平讲:“‘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但是,由于英国人在“九七大限”的压力下提出香港问题,解决香港问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邓小平在继续倾主要精力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将解决香港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开始考虑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根据其基本精神,对“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及在1972年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以“1997年”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成熟时机”的决策和特殊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邓小平会见麦里浩时阐释的“制度不变”的新观点,就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具体化。当然,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在适用于香港问题时有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均涉及国家统一的问题,但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性质毕竟不同——一个是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一国两岸的政治谈判来解决;一个是国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来解决。而且解决香港问题还关系到一个“结束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不能不考虑“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问题。
对于香港,邓小平并不陌生。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五次过香港的经历,时间累计近三个月,对这座兼有殖民主义之“短”与资本主义之“长”双重特性的“自由港”印象深刻。这一感性认识,成为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提出“剔除其殖民主义因素、保留其资本主义因素”之“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原始思想素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是在1974年。5月25日,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与访华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会见。“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同志)的事情了。”(注: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年5月25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邓小平说:“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注: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宴会上的讲话(1974年5月25日);《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1975年、1977年,邓小平会见第二次、第三次访华的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也都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邓小平晚年以麦里浩访华“解冻”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香港问题为历史契机而发轫的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逐步成型、成熟的。当时邓小平进行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设计欲“解惑”的主要难题是:一方面,由于“结束英国殖民主义”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没有让英国人“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且,1997年是“香港回归”一个绝不允许“过期”的时间底线;另一方面,具体在什么时间、具体以什么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必须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减小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的和平途径圆满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阻力和冲击力,必须考虑如何维护“香港回归”前后“旧香港”、“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资本主义“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地位、经济资源、经济价值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是在研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过程中,对自“1949年的香港”至“1979年的香港”的“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由于英国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掠夺性的殖民”,而是为了开发经营其为英国商品、英国资本进入亚洲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滩头阵地”,开发经营其为英国、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亚洲、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因此,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初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并一直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整整100年以转口贸易为单一经济结构的慢速、匀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加速发展时期。短短的30年,香港经济经历了由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向新型的工业中心和多元的、复合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嬗变,经历了由近代化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嬗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普普通通的转口贸易港,其经济实力尚逊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上海、广州,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几十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不过几千港元,至1979年中国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和“东方明珠”、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其经济实力足堪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相提并论,一年的进出口贸易额高达几百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达几万港元。香港经济的腾飞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工作重心自阶级斗争转移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与解决台湾问题一样,“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都不能不将“制度不变”以维护其“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战略出发点和支撑点。
为了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从1979年上半年至1982年上半年,邓小平对香港问题进行了逾三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
1979年3月麦里浩访华一结束,邓小平即指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他当时的另一个身分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解决香港问题要未雨绸缪。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时期的国家统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必须抢时间酝酿成型、成熟并付诸实践,争取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新思维之“香港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要提前进行,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香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将来中央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廖承志协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外交部、外贸部等单位的力量组织了若干个专题小组,就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廖承志在香港和北京两地举行了十几场小型座谈会,倾听各方面的声音。(注: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1~553页。)
经过逾一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内部的反复讨论,各个专题小组在1981年初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初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完全排除“九七”因素的干扰,按照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继续“维持香港的现状”,遵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己关于“国家统一”的“时间表”,俟“成熟时机”解决香港问题。其理由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英国“割”、“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九十九年”的期限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绕开1997年处理香港问题。第二种意见就是不回避1997年,“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在1997年收回香港。当然,也有顾虑:收回香港易,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维护“稳定和繁荣”难。
一开始,第一种意见是占上风的,因为当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我们不希望“四面出击”。但是,按照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继续“维持香港的现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像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一样,英国政府必须承认“香港是英国管理的中国领土”,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这样的条件,英国是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法理根据是三个条约,如果没有三个条约,就没有了法理依据,因此希望通过中英之间的正式谈判,允许英国继续管治香港三十至五十年”。“认为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要尽快发展经济,需要充分利用香港,因此有条件逼使中国作出决定。”(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1997年编印,第11页。)从1979年3月麦里浩访华提出香港问题开始,在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上半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朝野两党的三位领袖和前首相希思、麦克米伦、卡拉汉一拨一拨地赴北京与邓小平会见,继续麦里浩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的发难,不断非正式地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也就是说,对于1997年,中国方面已经没有了第一种方案理想化的“维持香港的现状”的退路,而第二种方案则一步一步地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1981年3月,在廖承志主持的、由进行香港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统一思想的“神仙会”上,“1997年收回香港”的第二种方案就替代了“维持香港的现状”的第一种方案,成为主流意见。其中,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不收回香港主权,上无以对列宗列祖,下无以对子孙后代;内无以对十亿人民,外无以对第三世界!”“神仙会”一结束,廖承志即向邓小平汇报了“1997年收回香港”的倾向性意见,重点是章文晋的发言。邓小平表示赞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不收回香港而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了,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中国领导人不可以做第二个李鸿章。”(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1、12页。)
1981年4月,对于中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的“缄默”,“沉不住气”的英国人又派出英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访华,正式地要求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表态。卡林顿对邓小平讲:“英国毫不怀疑邓就香港问题所作的保证。但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人不安。由于1997年日益临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然要考虑期限问题,这方面将碰到不少困难。”(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4页。)但是,邓小平不为所动,仍然是借台湾问题淡化香港问题,仍然是言香港问题的解决将循台湾问题的解决模式,而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则避而不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里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对台湾我们提的条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取消的只是国号和国旗。这个问题的处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所以,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它的话,现在不能讲得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十亿人民。”(注:邓小平副主席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的谈话(1981上4月1日)。)对此,廖承志解释说:“英国人想要我们摊牌,他们在步步进逼,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不会表态,中国不会被逼去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注:〔英〕罗拨·郭瞳:《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90页。)
由于卡林顿访华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英国政府希望尽快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磋商和谈判的意愿,中国方面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冷处理”的时间不宜拖得太长。所以,与麦里浩的会见一结束,邓小平即发出党内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6页。)。根据邓小平1979年3月29日会见麦里浩和1981年4月1日会见卡灵顿的谈话精神,由廖承志主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香港问题调查研究情况和各方面意见的报告,正式向中央建议“1997年收回香港”,并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三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既要收回香港主权,也要保持香港安定繁荣;第二个原则是,收回香港主权后,要尽可能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和经济制度都要保留;第三个原则是收回香港时,香港政府原有官员也不改变。”(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3页。)至于具体政策,“初步设想是:香港收回后将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特区。除涉及国家主权必须改变外,其它基本不变。”(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8页。)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81年4月和12月两次召开书记处会议,以廖承志的报告为基础,讨论、研究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对廖承志报告“1997年收回香港”的建议,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但未作最后决定。再经过几次酝酿后,到1981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拍板”(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3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1981年4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两次书记处会议酝酿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工程的突破口选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作重心转移,以“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历三经年时间的“发酵”,在1981年下半年成型、成熟。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正式出台,即著名的“叶九条”。邓小平讲:“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04页。)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大业的总体设计,是预期以台湾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打开国家统一大业的新局面,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和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没有为台湾当局所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均被台湾当局视为“统战阴谋”而加以拒绝,两岸关系的僵局久淤不化。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0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考虑“国家统一”工程突破口的重新选择问题,不能不将解决条件和时机相对成熟的香港问题提前,不能不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化”“一步到位”,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为台湾问题的解决“率先垂范”。
所以,在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讨论、研究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1997年收回香港”的意见非常统一。不仅对“1997年收回香港”“下了决心”,而且决定加快“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成型和出台进程。在会议上,廖承志对“1997年收回香港”的可行性和“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会议肯定了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后原来的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针。”第二次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参加,但是有指示:廖承志并有关部门必须在会议结束以后的“三个月内拿出解决香港问题最后方案”(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70页。)。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1月,廖承志组织了一个进行“一国两制”“香港方案”设计的“五人小组”,继续在北京和香港两地进行专题性的调查研究,整理出近20份关于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本情况的分析报告。由于在1981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廖承志已经以解决台湾问题的特殊政策“叶九条”为蓝本初步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廖承志是“叶九条”的起草人,解决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直接“移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特殊政策),因此,“五人小组”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十二条”进行“具体化”的“深加工”,进行补充和修改,并邀请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加以可行性论证。
对于廖承志和“五人小组”的工作,邓小平抓得非常紧,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听取他们的汇报。邓小平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乱”。他要求廖承志和“五人小组”在设计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况”,如中国的外汇收入可能减少1/2甚至2/3(当时中国约75%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邓小平讲:“收回香港主权,小乱不可避免,中乱很有可能,要尽可能防止出现大乱。”(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6页。)1983年3月底,廖承志和“五人小组”在邓小平规定的三个月内拿出了以“十二条”特殊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初步设计,交中央中央书记处审议。邓小平批示:“拟原则同意。方案待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71页。)
四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酝酿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过程中,邓小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的香港人尤其是维护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大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对1997年收回香港有抵触情绪——怕,怕香港“变天”,怕香港“赤化”、“社会主义化”,怕中央的“政治干预”和内地的“政治运动”,怕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将“没有自由”。为了打消香港同胞对“1997年收回香港”的顾虑,为了争取香港同胞对于“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理解和支持,在198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已经正式拍板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亲自向香港的各界人士做“思想工作”。自3月至6月,邓小平在廖承志的陪同下会见了十二批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当然,邓小平对于“为什么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非常明确——“不讨论”。“邓小平一开始就讲清楚,‘九七’收回香港主权是不容改变的,一切文章都要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这一前提下做。”他重点是阐释“1997年收回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重点是就“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征求意见。对于邓小平的“思想工作”,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均表示“有道理”,“可以接受”。香港知名人士黄丽松讲:“他到北京之前,不知道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态度是这样坚决,现在知道以后,认为中国的政策不失为最好的政策。”(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8页。)
在1981年上半年邓小平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向香港的各界人士“吹风”的过程中,英国方面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进行“摸底”。1982年4月,英国方面派出与中国方面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前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由于当时解决香港问题“十二条”特殊政策已经酝酿成形并且已经开始对香港的各界人士“吹风”,所以,邓小平决定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思一个“面子”,通过希思向英国人“喊话”——“现在是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希思问邓小平:“我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人不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它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17页。)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邓小平对希思明确表态:“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1974年我们见面时,我对你说过香港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解决。现在这个时机到了。一个是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一个是我们有逐渐好转的国际关系。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希思先生,现在是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了。”(注:萧亮、蓝潮:《董建华家族》,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自1979年3月会见麦里浩、1981年4月会见卡林顿至1982年4月会见希思,邓小平对英国人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的“迭迭的纠缠”印象深刻,他预感到,接下来的中英外交谈判将会是一场“激烈而艰苦的政治较量”,对于英国人的“合作”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像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一样,有“文”、“武”“两只手”。邓小平在1982年6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我对收回香港主权有一个问题始终来能解决,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取得英国人的合作,假如英国人不合作,那怎么办?我们的方案中有一条是说要充分照顾英国人的利益,换取英国人和平有秩序地交出政权,我们这个政策是有诚意的,但如果英国人不合作怎么办?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英国人说:假如你们不合作,我们就提前出兵收回香港,收回以后对香港仍实行特殊政策。”(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20页。)此一解决香港问题“文”、“武”“两只手”的重要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指导接下来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
1982年8月,邓小平召集所有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一方面研究香港可能出现的“金融风波”的问题,一方面讨论撒切尔夫人访华的准备工作问题。中央领导人指出;“要准备十五年当中香港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港澳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它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作。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要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作出新的考虑。”邓小平最后表态:“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83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揭幕”中英两国外交谈判前举行的研究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最后一次“高层决策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