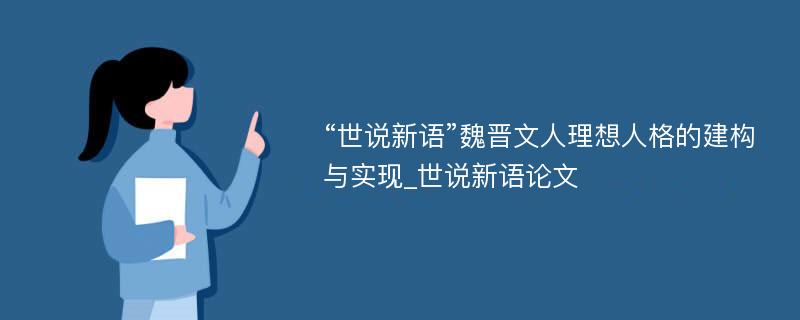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魏晋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2-0128-05
《世说新语》上承东汉桓灵之世,下讫南朝刘宋之初,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再现了魏晋士人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士人群体形象。他们张扬个性,恃才使气,以体认玄虚,遗落世情为高,相对于注重社会价值的前辈们,他们更关注于个体精神的逍遥抱一,风流得意。本文选取“理想人格”的角度,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联系当时思想背景来解析他们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希望由此更深入地探究其精神生活与心理特征。
人格指“人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旨在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包括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实际行为中所凸现出来的精神素质。”①而理想人格则是人们最为推崇的人格范型,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价值标准。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思想界也呈现玄、佛、道多元发展的兴盛状态,作为载体与传播者,魏晋士人的思想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那么,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推崇与实践的理想人格如何呢?
才性之辨——重才智,轻性行
汉魏之时,才性之辨是名理学家探讨的重要命题。才指个体才学智慧;而性谓本性或天性。何晏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时说:“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认为性秉之于天道自然,合于天理。嵇康也认为人的真性在于其本之自然之性,郭象在《庄子注》中提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②,“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③的观点,认为性理相通。魏晋之世,“才性”问题由社会伦理发展到宇宙本体问题的讨论,涉及才性、性情,性理等问题。这种讨论实际影响到时人关于理想人格内涵的探讨与实现。
汉代以来推举人才的察举与征辟之制强调才性统一。魏时品鉴人物专著《人物志》便依据秉性不同而把人分成“圣人”、“兼材”、“偏材”三等,因性别才,又分为十二种人才。“性言其质,才名其用”④的观点被时人所接受。就理论而言,“性”因天而成,无好恶之分,但实际品评中常赋予先天之性以仁孝道德等内容,如《方正》篇“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条刘注引《魏志》“父植,……选举,先性行而后言才”⑤,性行表示德行置于才能之上。魏九品官人制的中正品状,品美其性,状显其才,常有性美而才庸或才俊而性鄙者,性才不符是普遍的情形,《世说新语·轻诋》篇“褚太傅南下”条便说时人鄙薄孙绰“才而性鄙”。才与性是当时品评推荐人物常用标准之一。而才性四本⑥也是魏晋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因为资料缺失,才性四本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确知,但由以上材料可知,这个命题在当时既有现实品评标准的实践意义,也有探讨宇宙本体的理论意义。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才”成为品评人物的标准,也成为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世说新语》中处处体现对个人才智的推崇与赞颂。如《品藻》: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啖尽。
推崇有才智胸襟的古人如廉颇、蔺相如虽死如生,虎虎有生气;曹蜍、李志虽为当世高官,权重一时,却因庸庸碌碌、缺少才智而被贬为“厌厌如九泉下人”。不禁令人想起《三国志》中孔融劝刘备任徐州牧时称拥有重兵,而且四世三公的袁术为冢中枯骨,而曹操也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⑦。相对于个人的谋略与才智而言,家族出身、权势重兵,甚至生死都不再重要。于是在彼时,才华横溢、机敏过人成为品评人物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准。《言语》、《政事》、《文学》、《方正》、《贤媛》、《排调》等篇章记录了一个个精彩生动的小故事,体现了时人推崇的各种才能机智:通达机警、文思敏捷、贤德良吏、玄理颖悟,甚至诙谐幽默。
《世说新语》处处可见对文学上超拔俊逸之才的称颂赞誉。《文学》篇中多记知识分子间的清谈应对和探讨文艺的片断。曹植七步成诗,才思迅捷,时人称善;阮籍宿醉扶起,草成《劝进文》,“时人以为神笔。”袁宏机对辩速、文章绝美,曾受到谢尚、桓温和谢安等名士权臣的称赏赞颂。而在玄学清谈时对义理别有所见,卓然新发者更受到敬重与嘉许。支遁援佛入道,解庄能够标新立异,时论以此高之。于法开、竺法深、康僧渊、竺法汰等僧人也以个人才辩思理立足于权贵士林。
在当时风气中,“才智”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不仅男性品评以此为标准,女子亦复如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为了表现个人才情智力,甚至出现了挑战禁忌有违纲常伦理的言行。六朝之时,最重避讳,触犯家讳便被理解成一种公然的挑衅行为,如《方正》篇“卢志于众坐”条。然而《排调》篇中却有两则为了考校才智而故意触犯家讳的嘲戏之语:“晋文帝与二陈共车”与“庾园客诣孙监”,这些都是朋友之间的玩笑之语。在严格避讳的风习之下如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对文人来讲,这类应对酬答更像是智力游戏,在游戏中通过挑战日常生活须时时遵守的纲常伦理禁忌展现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心理满足。
从以上所述可见,“才智”是当时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而前代评价人物的核心标准“品德”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德行》和《方正》,所嘉许推崇的道德观念涉及仁、忠、孝、义、礼、信等传统道德观,然而,在《世说新语》中这些品德已不再是评判人格的决定因素。当才德之间有冲突时,则取才舍德:
然日磾之贤,尽于仁孝忠诚、德言纯至,非为明达足论。高座心造峰极,交俊以神,风领朗越,过之远矣。⑧
王珉拿金日磾与帛尸梨密多罗对比,一言其德,一言其才,才已凌驾德之上。详而言之,才德虽然都是个人品性,德行伦理体现妁是群体的价值判断,关注个体对群体与社会各种规范的服从程度;而才却是完全属于“自我”的品质。重才轻德之风实肇始于东汉末年。余嘉锡先生在《任诞》篇首按语中说到:“自曹操求不仁不孝之人,而节义衰。”⑨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观念对时代风气的影响显而易见。继之的司马氏虽以孝立国,但统治策略却直接导致了社会道德观念的混淆。元康时期文人无行,重利轻德便是这种情形的直接后果⑩。
要而言之,魏晋士人对才性问题多有辨析,一方面探讨其蕴含关于宇宙本体的理论内涵,同时也将其作为人物品评的重要标准。才智成为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之一,文人名士多以才自矜,恃才使气,重才智、轻性行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情之所衷,正在我辈——“情”的表现与表达
魏晋时期,玄佛道多元并兴的思想状况使士人们可以脱略束缚,重新审视自我。个体的感性世界苏醒了,活泼生动的情感也纷纷呈现出来,喜怒哀乐怨,亲情、爱情、友情和对山水人物等一切美好事物的赏爱之情,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情”被认为是士人先天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观念(《伤逝》“王戎丧儿万子”条)已被时人接受。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是鲜活生动的,他们的情感是敏锐深挚的。
日常生活中的亲情最为自然朴素,也易为人忽略,魏晋士人对亲情的捕捉与感受却极为细腻生动: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言语篇》)
魏晋时最重门第阀阅,家族的权势和地位决定了个体发展之路,东晋后陈郡谢氏家族逐渐成为声势显赫的甲等士族,谢安因其才识地位,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培养教导后辈子侄的责任,他在不伤害子侄自尊的情形之下委婉地烧掉谢玄的紫罗香袋,又纠正谢朗无意中触父亲之讳事,还常常聚子侄一起探讨文义,清谈玄理,培养子侄的才学见识与家族责任感和荣誉感,而后辈也颇能理解他“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篇》“谢太傅问诸子侄”)的良苦用心。谢安与他们的感情可想而知,临别而生伤感之情也理所当然。谢安喜好伎乐常受时人非难,但深谙情理的王羲之解读时甚至把长辈惜别又不愿影响儿孙辈心情这样幽渺微妙的情绪传达出来。王羲之的理解建立在他和谢安有相似的情感体验:“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11),天伦之乐带给他心理愉悦,流连山水使他发出“卒当乐死”的感慨。与谢安为遣离情而“丝竹陶写”之举不同,王羲之通过寄情山水、散发林阿来遣难解之情,方式不同但有情为一,遣情为同。
亲情之外,朋友之情、两性之爱,甚至感时伤逝的种种微妙思绪都进入到他们的情感领域。《伤逝》篇中多有生死离别之情的感受与描述,真挚而深厚的情感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支道林丧法虔之后”记支遁在知己竺法虔去世后感到精神空虚寂寞,不禁感叹“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郁郁而亡。而现实中伤时悲逝、感念人生之情更是比比皆是。桓伊“一往有深情”(《任诞》),王廞自叹“终当为情死”(《任诞》);桓温北征,见先前手植之柳时“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凡此种种,可见魏晋士人已开始审视自我的情感世界,没有把这种“感物而动”的情感一笔抹杀。
魏晋士人在生活中从不讳言对美丽事物的赏爱之情,人物山水都进入到了他们的审美感受领域。《文学》篇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顾长康从会稽还”等以简洁传神的语言传达了个体面对山水美景时内心的情绪。以后者为例:“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山水景物已不是纯粹客观描写,“竞”、“争”直以自我之情感贯注于无生命之山树瀑流之上,使其充满了灵动的魅力。魏晋之时,文人雅士徜徉流连山水之中,不仅在于山水美景的娱情之效,更重要的是通过山水以遣情悟理(详见第三部分)。当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主体感受领域时,山水文学随之产生了。
这种深沉真挚的情感在表达时很难遵循“礼”的规范。“礼”本是效法自然,顺应人情而定:“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12)然而,礼制却限制了情感的自由发挥。在尊重个性,重视自我的时代氛围下,常可见任情越礼现象。《任诞篇》“阮籍遭母丧”最有代表性。丧礼仪式繁复严谨,《礼记》数篇都涉及丧礼的规制,阮籍所为违背丧制,而他的行为却渊源有自。《世说新语·德行篇》“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余嘉锡先生笺疏提到《后汉书·逸民传》中的戴良丧母事,究其根源,戴良之辩或出于《论语·八佾》中孔子之言:“丧与其易也,宁戚。”言严格遵循礼仪规章不如有哀痛惨怛之实。阮籍在何曾的攻击之下依旧淡然处之,想来其心中所思当与戴良同,只是不屑反驳而已。戴良虽有辩论,当时的舆论清议却对他的行为颇不以为然;阮籍虽没有反驳,但时风所趋,居丧无礼竟成为大家效法的对象。《世说新语·德行篇》“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和峤丧不备礼,却因哀毁骨立而为世人所贵。而《言语》篇又记:“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至则哭,何常之有!’”孝武的回答恰肯定个体之情对于外在之“礼”的超越与突破。
西晋以孝治国,而居丧无礼者居然受到嘉许,看似矛盾,实非矛盾。阮籍虽曾傲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大人先生传》也对儒家正人君子极尽讽刺之能事,嵇康在《与山世源绝交书》中大谈七不堪与二甚不可,菲薄汤武,攻击礼教。然细品文意,发现他们所菲薄与反对的并不是礼教本身,而是礼教的外在形式,就其内心而言却是真正笃于礼意者。这一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一文中早已指出。不过,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带来社会风气的败坏与混乱,倒是阮籍等始料不及的。
丧礼之外,《世说新语》中多处记载魏晋士人日常生活中种种任情越礼之举。《简傲》篇王徽之赏好竹交友,王献之非礼赏名园,《伤逝》篇曹丕和孙子荆学驴鸣悼友,王戎丧子几乎灭性,《任诞》篇阮籍送嫂与别,王徽之与桓伊郊野吹笛,凡此种种,都在尽情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对个体情感的放纵恰恰体现了对个性的欣赏与尊重。得意忘言本是当时探讨最多的玄学命题之一,他们这种任情越礼的行为恰是这一理论命题在现实中的实践。礼意已得,属于津梁这一层面的外在规范是否遵循便不再重要了。
抑情顺理——情的节制与转移
对魏晋士人而言,情是必要而且值得肯定的。他们以“有情”自许,把“情”看作是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之一,在情感表达上也常常有任情越礼之举。然而,相对于恣情任性、毫无节制的情感表达而言,魏晋士人更欣赏节制与转移情感。表现于外则是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雅量篇》多有此类记载,这里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情绪:悲伤、愤怒、羞愧、惊恐、喜悦等,对这些情绪的理性处理体现了个体性格中包容、镇定与从容,这都是当时备受推崇的人格因素。《德行篇》“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条,刘注引《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可见这种评价标准已被士人普遍接受。
《雅量》篇“豫章太守顾邵”条谈到魏晋士人排斥过度放纵情感的原因:顾雍知子之丧,心中固然悲痛万分,但他极力控制哀情,做到“神气不变”。由其自叹之语:“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可知支持他这么做的理论依据在于合礼保明。延陵葬子,处处合于礼仪,子夏哭子丧明,被曾子讥讽劝喻,过度的悲伤或快乐都容易灭性丧明。在相似的境况中,像延陵、曾子和子夏那样才符合理想人格的标准。这便是控制悲痛之情使其表现于外时合乎理,再以理化情,最终遣去悲意,神明朗然。“明”为何意呢?《老子》十六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五十二章“见小曰明”,可知“明”是指能够洞幽察微、体悟至理的内在智慧。保持神明是体悟玄道至理的基础,而“悟理”则可以遣去世俗之情。何谓“理”?“物无妄然,必由其理”(13),“理”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即本体道,天理。以理遣情与当时圣人人格的讨论有关。
魏晋时期“老不及圣”是大家的共识,何晏、王弼、向秀和郭象持此观点。而圣人有情与否是魏晋玄学的核心命题。何晏主张“圣人无情”,而王弼则主张“圣人有情”,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14)向秀和郭象在《庄子注》发展了王弼的理论,提出“无情之情”之论。时至东晋,有情之论已被时人普遍所接受。圣人智慧自备,人格完善,能时刻保持“神明”的境界。圣人与凡人一样,天赋五情为自然之性,应对万物时也有喜怒哀乐怨之情,但圣人有感于物却循理而动,于是情役于理,无累于物。“人之性禀诸天理,不妄则全性,故情之发也如循于正,由其理,则率性而动,虽动而不伤静者也。……动而正,则约情使合于理而性能制情。动而邪,则久之必至纵情以物累其生而情乃制性。情制性则人为情的奴隶(为情所累)而放其心,日流于邪僻。性制情,则感物而动,动不违理,故行为一归于正。”(15)圣人因为能做到性其情,所以感物而动,动不违理。而普通人能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呢?
先秦儒学中,荀子提出只要勤于后天修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自汉代以迄魏晋,逐渐盛行圣人生知,不可学而至的观点。玄学家也认为圣人体天道至理,而天道盈虚非人力所能达到,主张圣人不可学不可至。但儒家又有见贤思齐的教诲,勉励人们去学习圣道,由《世说新语·言语》“孙齐田、齐庄二人小时条”可知魏晋时人虽然认为圣人不可学不可至,但都不废劝教勉学,鼓励人们以圣者的标准来规范自我之立身行事。谢安所言“贤圣去人,其闲亦迩。”(《言语》)认为凡圣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简文感叹“陶练之功,尚不可诬。”(《文学》)则强调个体为达到理想人格需要不断努力。
在魏晋士人看来,圣人人格或许难以达到,但在自我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实践中却以圣人人格为标准,通过不断的努力接近圣人理想人格。圣人能够应物而无累于物的根本在于循理而动,神明则是循理的基础。所以体玄悟理时要心境澄澈,志气专一,只有如此方能保持“神明”。具体而言,要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言:“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因此,魏晋士人虽然肯定五情是人格修养的必要内涵,但又强调要抑情顺理,以理遣情,保持神明朗彻,认为如此方能如圣人一样不以情累生。
在完善自我人格修养、以理遣情的实践中,自然山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玄学家看来,自然万物中蕴含大道至理,随着汉末希企隐逸之风的进一步盛行,乐山好水成为一代风尚。于是在魏晋士人的观念中,蕴含自然中的道就集中到山水中,山水成为道(理)的化身与载体。这样,当主体“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16)之时,便可由山水悟道(理),由此遣去胸中世俗之情。王羲之《兰亭诗》言:“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仰望春日湛然清新的天空,俯察曲水流芳碧草青青的河岸,悠然忘我而与物冥合,胸中玄思与山水所蕴之理遥相呼应,主体由此而获得精神愉悦,这种愉悦与初对山水之时所感的喜怒哀乐怨等世俗五情已大不相同。东晋玄言诗人对此多有论述:“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王羲之《兰亭诗》),“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兰亭诗》),等,都强调主体在自然山水中悟理遣情,当悟及“理”在万物中生生不灭的永恒时,便可超脱个体生死困惑的痛苦,得以豁然达观,从而达到遣情散怀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在魏晋士人看来,禀于自然的先天之性为人品底色,有仁契理,圣人之性为“中和之质”,所以能够总达众材;常人只能是五常之性中偏据一材:“或明于见物,或勇于决断,人情贪廉,各有所止。”(17)圣人天赋五情,循理而动,应物而无累于物;凡人任情,喜怒违理,虽然凡不及圣,但常人可以通过陶冶修炼不断完善自我人格修养以期接近圣人境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才、有情是时人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必要内涵,才是先天之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反映,而情为个体心性之源。而情在表达中注意节制,抑情顺理以保持神明朗彻成为接近理想人格的必要方式。
注释:
①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逍遥游》,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页。
③〔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卷七《达生》,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31页。
④魏袁准:《才性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69页。
⑤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方正》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下文引文皆出自本书,不复一一注明。
⑥《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刘注引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⑦〔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二《蜀志·先主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5页。
⑧〔梁〕释慧皎撰,汤用彤点校:《高僧传》卷一《译经》,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
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5页。
⑩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8-80页。
(1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2页。
(12)《丧服四制第四十九》陈澧《礼记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9页。
(13)王弼著《周易略例》,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2页。
(14)〔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附王弼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95页。
(15)《王弼圣人有情论释》,汤用彤:《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
(1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容止》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页。
(17)〔三国〕嵇康:《明胆论》,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三国文》卷五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36页。
标签:世说新语论文; 魏晋风流论文; 魏晋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方正论文; 三国志论文; 伤逝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