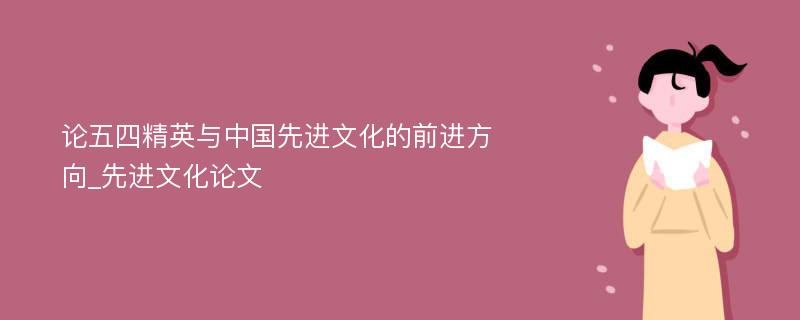
论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进方向论文,精英论文,中国先进文化论文,论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3-0069-06
回溯五四时代,人们总会自然地想到两个名词:“知识分子”和“文化”。作为一个时代,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和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就主流来看,文化的变动是最具本质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五四知识精英事实上成为那个时代最为活跃和备受注目的社会群体。也正因为此,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热门的话题。从擎扛“民主”和“科学”大旗的陈独秀、“肩担道义”的李大钊、呐喊社会的鲁迅,到风华正茂的青年一辈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尽管学识功力和阅历地位的差异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各不相同,但五四文化变动的主流铸就了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的共同特质,即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变革者。
一、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与五四精英的文化价值意识
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群体崛起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这场以“唤醒国民”和“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被冠以新文化运动之名,正好说明了近代中国社会前进过程中人们对先进文化的需求。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而呈现着两种趋势:一种是苟延残喘于不断丧失主权的现实,力不从心地维持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随时有可能倒塌的大厦;另一种是忐忑不安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努力于改变世界残酷竞争下中国的弱势地位。两种趋势演绎出近代中国守旧与革新、落后与进步两股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斗。后一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代表近代中国前进方向的社会变革是一个由弱到强、由潜到显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有一个大致的线索。其最初萌发于对中国落伍于世界的觉悟。一些有民族觉悟的中国人从与英国交战中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折射着近代文明的光亮。于是,他们“开风气之先”,大胆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这个主张尽管在鸦片战争时期遭到冷落,但终于在20年后付诸实践。中国人也学着西方人造出了兵舰、枪炮和子弹之类的“利器”,并由此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然后的觉悟是到了19世纪末。甲午海战将中国人打懵了头,拥有“先进船坚炮利战器”的北洋水师惨败在一向被中国鄙视的日本弹丸小国之下,这一耻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从打赢中国的对手那里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的新型政治制度同样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荟萃。于是,他们冲破“中体西用”的思想牢笼,提倡起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以及天赋人权、民主平等之类的主张,并由此发生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从而结出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硕果。再后来的省醒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取代皇帝专制统治的共和制度不仅没有给中国注入生机,社会反而更加恶浊黑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备感愤怒,他们认识到,中国光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不够的,西方近代文明的精华不只表现在生产力和政治制度方面,其背后还有孕育这些东西的文化韵力。于是,社会变革的视线又深入到文化的层面。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的缘由,也是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群体崛起的时代背景。
以主政北大蜚声论坛的名流蔡元培深感改造中国的根本在于更新人们的思想。他指出:“吾国以病夫闻于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持一手一足之烈。”(注:《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手足之烈不可持”无疑是对以往武力革命的觉悟。所以,蔡元培对于新文化运动寄予厚望。他甚至把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等同看待:“考欧洲文艺中兴之起点,群归功于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文学。今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亦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诸氏所提倡之白话文学,已震动一时。吾敢断言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注:《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五四时期的蔡元培不仅因革新教育界而引来诸多麻烦,而且也因提倡新文化而成为旧势力群起围攻的靶子。
李大钊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就忧心重重,焦虑不安。目睹政治恶浊、民生凋敝的现实,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之处。他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来表示对中国社会的忧虑和悲哀,并苦苦思索一条能够改变现实的新路。他得出结论:“时止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注:《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这里所说的“昌学”就是宏扬文化的意思。李大钊成为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的事实表明,他也对革新文化寄予厚望。
陈独秀的认识更是鲜明。在创办《青年》杂志时,他就十分坚决地指出:今日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民主和科学两样东西。于是,民主和科学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陈独秀坚信文化的力量,他说得很绝:“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6页。)其言下之意,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不仅能够武装工人,感化资本家、改造政治,甚至还要制止战争,其威力实在令人震慑。
五四精英的上述认识是当时“文化救国”潮流的思想缩影。虽然五四精英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认识到单纯靠文化的变革并不能救国的道理,但他们在当时将文化视为改造中国舍此无他的利器,则显示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先进文化的需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戊戌、辛亥、五四已经成为固定的名词分别与政治改良、制度革命和启蒙运动相联系。这三个固定的名词代表着三个前进的阶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三次进步,他们之间既有着传承相接的关系,也有着全然不同的阶段特点。这样的切换表明,近代中国前进的方向呈现着从经济的物质文明到政治的制度文明,再到观念文化的精神文明这样一条递进的轴线。五四精英的文化价值意识正是对中国前进方向的应答。
二、五四精英与五四时期的文化斗争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头一炮。当时还在海外的胡适首先点燃了炮火。尽管这位洋博士倡导文言改革的最初意图还拘泥在语言文字的形式上,但语言文字的改革却成为文学革命的导火线。胡适后来承认自己倡导文言改革时有“态度太平和”、“太持重”的缺点,并十分敬佩陈独秀的勇气,赞扬陈独秀为进行文学革命“最重要的急先锋”(注:《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胡适一边。当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一哄而起的时候,他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8页。)陈独秀这种武断的态度,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语言文字的形式改革与文学内容改革的内在关系。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在陈独秀看来,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重要意义。有位读者写信给陈独秀说:“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对这种说法,陈独秀十分赞同,并称之为名言。他答复说:如果一味地“模仿古人”,“以如是陈陈相因之文化,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革命、革新思想耶?”(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9页。)这就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改革上升到思想文化革命的境界,这样的认识无疑比胡适深刻得多。就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新文化运动从提倡白话文开始,很快就发展为对旧文学的总体性批判,并引发一场激烈的新旧思潮论战。陈独秀、胡适等因提倡白话文而受到恶毒的攻击。因此,语言文字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革命,是五四精英开辟文化斗争的第一仗。
五四时期文化战线上发生的另一场重要斗争是对孔教和儒家思想的批判。反对孔教的斗争,起初是为了反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将孔子思想定为“国教”写入宪法。五四精英中首先表示愤慨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他们之所以对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加以批判,第一动因是基于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对统治阶级将孔子和儒学抹上宗教色彩强烈不满。李大钊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等文章,指出:把孔子的思想定为“国教”,“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注:《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陈独秀也发表了《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号召国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8页。)。围绕“国教”问题展开的斗争是五四精英掀起反孔浪潮的第一波。更为猛烈的反孔浪潮是从文化审视的角度对儒学发动的批判。李大钊认为: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支配中国人心二千多年,就是“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5页。)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骁将之外,易白沙、吴虞、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打倒孔家店”的讨伐檄文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一方面竭力反对孔子及其思想宗教化,另一方面更将儒学视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孔子思想的根源和实质,并由此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易白沙、吴虞则数落儒学的种种罪恶,发出儒学革命的号召:“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注:《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7页。)这样来评判孔子思想显然具有文化审视的意义。五四时期反对孔子和批判儒学的斗争同样激起思想界的巨大波澜,从而构成当时文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精英批孔和反儒学的态度正是他们决心从文化上改造中国的体现。
五四时期的文化斗争最为热闹的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这场论战以陈独秀、李大钊与《东方杂志》的杜亚泉之间的辩论拉开序幕,到1920年以后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展开的讨论,争辩延续十余年。论战中,各式各样的主张歧见纷呈。激愤者基于中国社会的腐朽僵滞而主张大胆抛弃本土的传统文化,用近代西方文化取而代之;守旧派则恋情于中国传统,死守东方文化的壁垒以排斥西方近代文化;暧昧者既不满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又因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对西方近代文化敬而远之。不仅中国内部的声音不一,当时来华的外国著名学者也各唱各的调。杜威、罗素在中国各地到处演讲,充满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泰戈尔访华则竭力赞颂东方文化的优美。五四精英们自始至终关注和参与了论战,并以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形成文化倾向上占主导地位的一派势力。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同仁,基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痛感两种文明之间先进和落后的明显区别,认定东方文化“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9页。)。他们强调:“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主张“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07页。)。他们断言中国社会要与世界相融合,必须采用西方的近代文化。五四精英的这种文化倾向,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偏激之处,在抨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缺乏冷静和科学的理智态度,暴露出形式主义的方法缺憾,但他们表现出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则使他们的文化取向具有合理性,并在引导先进文化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五四时期文化变革涉及方方面面。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文化斗争外,文化领域中的各个层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文学体裁上,陈独秀揭示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戏剧方面,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了“戏剧革命论”,曾产生较大的影响。《新青年》曾两次出版戏剧专号讨论戏剧改革。虽然意见并不统一,但改造中国传统旧剧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诗歌方面,由于倡导白话文的影响,五四时期新诗运动蓬勃兴起。这些白话诗在体裁方式上的自由性和题材内容上的朴实性,鲜明地与旧诗形成对照,体现了时代精神。在绘画方面,五四精英强调创新。陈独秀主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3页。)总之,五四精英竭尽全力要把新思想的阳光照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文化革命意识。
三、五四精英把握先进文化的历史特征
五四精英在把握文化问题时,心中有一个落后与先进的衡量尺度。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也不必比较的讨论相杀残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妇(如印度)、殉节阉宦(如中国)的东方文化孰为健全;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社会上将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落后。”陈独秀明确地指出,无论提倡哪一种文化,都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55~456页。)。从社会进步的需要来确定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就是五四精英能够把握先进文化的原因所在。
五四精英发动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掀起东西方文化的讨论,宗旨十分明确,即为中国确定一种能够指导社会前进的文化。就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而言,值得重视的不是五四精英对西方文化的钟爱,而是他们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历史特征。
第一,立足时代的进化来审视文化的价值意义,树立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念。自从19世纪末,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出版以后,进化观念从此支配中国的先进思想界。此后,许多五四精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念便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飞跃。李大钊、陈独秀在文章中突出地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思想文化的变动是物质变动的必然结果。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就是代表作。他阐述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因此,“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7页。)。陈独秀也指出:唯物史观“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他还形象地比喻文化等这些“心的现象”只是“经济的儿子”(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7、379页。)。五四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取舍正是基于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念。
第二,力求从世界的整体性来思考中国先进文化的重新建构,倡导汲取人类的先进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封闭状态下演化的。封闭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时期对自己文化的孤芳自赏,排斥或拒绝接受任何外来先进的文化。随着新文化运动迎来的思想解放,五四精英领受了世界先进文化潮流的洗礼,认识到把文化封闭起来的做法是难以发展进步的,如井底之蛙。因此,文化的选择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李大钊指出:“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瞿秋白认为:“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他还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相通的,“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东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注:《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由此可见,五四精英把握先进文化明显具有世界主义的取向。
第三,努力剔除封建迷信的糟粕,将文化建立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基础之上。两千余年封建历史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抹杀自我。压制个性自由、埋没人格独立的极权专制,生产的是精神依赖、迷信神威、听命盲从的文化因子。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威力震动思想界,就是因为民主和科学震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实,在近代中国,提倡民主和科学,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也不是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第一人。为什么以往的宣传没有达到陈独秀提倡民主和科学那样的效果呢?个中的原因是,陈独秀宣传的科学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技艺范围,而是将它伸展为指导思维的科学精神;他宣传的民主也不局限于制度构造的内容,而是将它与人权相联系,提升到个人思想启蒙的境界。陈独秀说得很明白:“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页。)可见,这里的民主和科学都抹上浓厚的文化色彩。瞿秋白也指出:“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注:《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因此,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才能理解它们所产生的威力。新文化运动的主攻方向就是扫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遗毒,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融入文化之中。
第四,以能否满足民众的普遍需要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强调文化的大众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化形成一个悖谬的过程,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仅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且也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品。五四精英倡导文学革命,出发点就是要打破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于是文学的“平民主义”成为新兴的潮流。在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我书我口”,目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能够读书看报。因此,陈独秀曾把白话文视为“文学的德谟克拉西”。在内容上,批判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提倡写实主义,主张更多地去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可见,五四时期的文学已开始朝“国民文学”、“通俗文学”的方向迈步。当然,五四精英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很有限的,但在衡量文化的价值标准上,他们已经引入了大众意识。
第五,坚持把创新与文化的建构相联系,引导文化朝新的方向拓展。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决定了它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时代呼唤创新的意识。五四精英非常自觉地将创新意识融入到对文化的认识与实践上。李大钊指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他崇尚创新,强调创新,希望人们“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191页。)。陈独秀认为:“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因此,他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方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516页。)尽管五四精英之间对待儒学或西学的态度有着差异,但对重新建构中国文化存在着共识。他们中的某些人,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痛下针砭,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他们深恶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但对西方文化出现的问题同样尽情地揭露。评价五四精英的文化态度,重要的并不在于判定他们是不是所谓“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者”(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是海外学者林毓生在分析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时下的结论,国内许多学者不赞同这样的评价,并撰文加以反驳。),更不是讨论他们的“西化”倾向,而在于认识他们重新建构中国新文化的使命感。从五四精英的创新意识来看,他们的文化态度侧重在再造中国文化的探寻上。
四、中国社会前进方向与先进文化的关联
五四时期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两件实质性的事情。一是领导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的世界观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其成果是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是近代中国的先进组织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所取代,其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两件大事都与五四精英和五四先进文化有关。前者表现的是先进文化促使五四精英中一批思想更为敏锐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新的世界观,后者表现的是世界观转变后的知识分子将先进文化开始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
从概念上理解,思想与文化严格地说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但就它们的属性和相关性而言,这两个概念又很难截然分开。思想融于文化,文化表现思想;思想是文化的指针,文化是思想的展示。思想和文化都受制于社会经济,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从这个意思上说,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具有文化意义。可以说,它既是政治现象,又是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所体现的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大进步。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过程,是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来认同的过程。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就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个课题,几代先进的中国人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不管是他们所羡慕的西方物质文明,还是他们所倾心的西方精神文明,输入或引进中国后必然是以一种文化形态出现的。电讯、铁路、轮船、利器是看得到的实在物件,民主、自由、平等是摸不着的精神理念,但它们输入或引进中国时受到的巨大阻力是相同的。其原因就是它们共同遭遇的是浸润了两千余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所以,不少眼光敏锐之士在反思中国腐朽衰退的症结时,率直地将文化冲突视为最关键的问题。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攮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5页。)因此,当陈独秀用“伦理的觉悟才是最根本的觉悟”这样的认识来启蒙大众时,当五四精英将改造中国的视线转向文化的途径时,在他们的眼里,西学已不再是船坚炮利之类的物件,不再是议会、宪法和政党之类的制度,也不再是民主、自由和平等之类的观念,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
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性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五四精英强烈主张效法西方文化,头脑中的蓝图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救世方案。然而,经过三个年头的宣传,虽然在知识界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救国道路。不仅如此,由于人们能够从整体性的角度认识西方文化,易于发现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弊病,从而产生怀疑并不断加深。正在这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犹如一片使天下惊秋的桐叶,“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瞿秋白语)。五四精英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赤旗的世界”。他们猛然感觉到文明进化的世纪性转换。“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于是,受十月革命启发的五四精英,开始是一小部分人,随后是一个群体,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视为过时的文明而抛弃,转向接纳代表新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思想转变相对应的是文化观念的转变。李大钊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瞿秋白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断言将有第三种文化诞生,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概念。他认为,东方式的封建文化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都是“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而马克思主义则“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注:《瞿秋白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65~166页。)。于此可见,当五四精英在中国树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的时候,不仅是将它作为救国的指针来看待,也是将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来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既是中国革命发生部分质变的标志,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进步的一个阶梯。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在近代中国具有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站在社会前列指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在推翻封建帝制以后,就暴露了底气不足和后劲乏力的先天性缺憾。民国初年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政党明显失掉了组织人民建设新社会的凝聚力,而试图东山再起的孙中山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也无补于事。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对抗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社会力量必须更新,组织这种社会力量的政党必须更新。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是由两个本质性的东西决定的:一是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体现。前者是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两者必须紧密结合,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运动是不成熟的工人运动,没有工人运动作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失去对象的空洞学说。只有当两者会合在一起,才产生了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主体作用。这恰恰说明,共产党的建立与知识分子和文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介。马克思主义因为知识分子的大力传播而融化为工人运动的政治意识,中国工人运动因为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主义而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相会合,迸发出的力量无疑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
五四精英的文化意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包含着这样一个道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必然的使命。党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虽然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革命战争上,但始终没有忽略文化建设。继五四时期之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开展的文化斗争,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足迹。尤其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还领导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1940年1月,毛泽东在该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也就是后来《解放》杂志登载时改题为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2月,延安创刊《中国文化》杂志,对文化建设起着指导作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使命说得很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当然,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在不断地进步,先进文化也总是不断地前进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有一定历史内容的阶段性,又是一项没有停滞的永恒使命。
标签:先进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陈独秀论文; 李大钊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新青年论文; 国学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