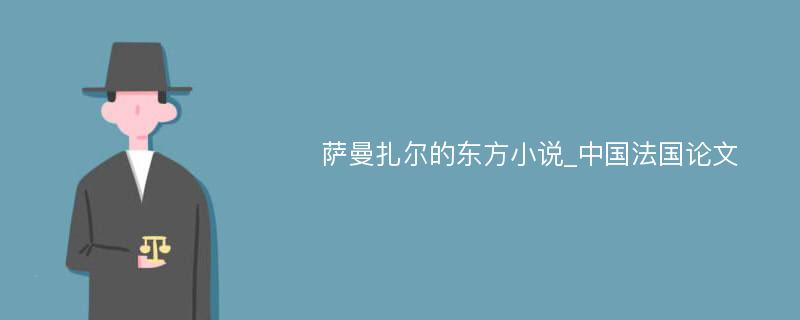
萨曼纳扎的东方虚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曼纳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4-0054-13
游记类作品与文学伪作历来关系密切,也是最容易勾起作家想象的领域,人类对未涉足过的环境总会产生期待和幻想。14世纪《曼德维尔游记》一书风靡整个欧洲,现存的抄本超过263部,远远高于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82部,更是被翻译成十多种欧洲文字。[1]作者在序言中自称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是位骑士,从公元1322年出海冒险,穿越了土耳其、波斯,最后来到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了60%以上的篇幅。书中详细记述了大汗不仅国土广大,统治严明,而且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一样,大汗有一百多位妻子,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异域传奇让马可·波罗对东方的真实描述相形见拙,而曼德维尔本人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欧洲”。[2]
18世纪末另一游记类伪作是《本尼奥瓦斯基伯爵回忆录》。本尼奥瓦斯基是匈牙利冒险家,于1786年替法国殖民者卖命,战死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1790年伦敦皇家学会一位叫尼柯尔森的人炮制了上述回忆录,编造了一番在1770-1772年间类似奥德赛式的浪漫传奇,杜撰出本尼奥瓦斯基不仅参加了欧洲1756、1757、1758年三场著名的殖民战争,并且登上日本和台湾的土地,而且一位倾慕他的漂亮女仆始终陪伴左右。为求真实,尼柯尔森不惜将本尼奥瓦斯基的出生年从1746篡改成1741,以避免让人发觉他10岁就参加战争的荒谬。[3]
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东方的追逐与美好想象不断贯穿于游记类伪作,传奇作家与地理学家都喜欢在伊斯兰和东方的土地上留连忘返。16世纪海上新航路开辟后不久,欧洲的东方思想逐渐从阿拉伯地区向远东延伸。冒险家们经印度果阿或马六甲等地辗转澳门、宁波、东京湾各地,欧洲与东亚的交往进入发轫期。早在1517年葡萄牙人费尔南·阿德拉德就带领使臣皮莱资将船只靠泊于珠江口,等待与中国通商。随之是一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先后来到东亚各国传教,如西班牙人沙勿略(St.Francis of Xavier,1506-1552)。自1549年起的两年时间,沙勿略以日本鹿儿岛为中心发展了大批教徒;1552年他又登上广东沿海的上川岛,试图踏上中国大陆的辽阔土地。31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终于完成了沙氏之夙愿,抵达广东肇庆,此后为欧洲带去了大量关于中华帝国的信息。
这个时期,通过贸易以攫取巨额利润是东西方交流频繁的主要因素,以印尼班达群岛出产的肉豆蔻和豆蔻干皮为例,在16世纪,“10磅的售价分别是半便士和不到5便士,运到欧洲后每磅的价格飞涨到1镑12便士和16英镑,利润大约是320倍”;[4]301664年,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仅12磅2盎司,至1783年仅东印度公司就销售了5 857 882磅。曾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此总结道: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稻米;最好的饮料——茶叶;最好的衣料——棉、丝和皮毛。伴随着贸易,欧洲对东方文化的热情也达到了顶峰。1500-1800年间,欧洲出版了大约1500本有关亚洲的书籍,包括各类游记、经济专著以及自然史。即便是到了1750年,这一数量仍让关于美洲殖民地的书籍相形见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18世纪之前,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是欧洲人向往的东方圣地。
远东唤起的无穷遐想不仅萦绕于商人脑海,也渗透到那个时代的作品中间,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11章描写了天使长迈克尔把行将被逐的亚当、夏娃领到伊甸园中的最高峰,让他们极目眺望人间帝业的荣耀与雄伟:“从契丹可汗的首都大都,那里有坚固的城墙;/从帖木尔王座所在,阿姆河旁的撒马尔罕,/一直到中国列王的北京,再从那远眺,/从蒙古族莫卧尔人统治下的阿格拉和拉合尔,/到马六甲的黄金半岛。”[5]弥尔顿从未去过中国,不知契丹(Cathay)与中国(Sina)实指同一国度,大都(Cambalu)与北京(Paquin)也没有区别。利马窦的日记对此早有说明: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在欧洲人中有多个名称,最古老的名称叫Sina,大约为托勒密时代起用;此后马可波罗称为Cathay。[6]5利马窦的这本中国日记于1615年出版,在弥尔顿40岁之前至少有4个拉丁语版本,3个法语版。我们不能责备弥尔顿的粗心,却可体会他对东方文明的渴望和赞叹。虽然如此,与法国文学相比,英国文学对东方的热切程度要晚很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模仿,甚至直接译介于法国文学作品。
法国文学中东方思想的兴盛有法国耶稣会士的一份功劳,他们将大量关于亚洲的文化、语言等信息或真或假地传播到欧洲,使得东方文明在17世纪的法国受到尊崇。与法国文学不同,伴随着怀疑论思想,英国社会并没有出现东方崇拜的高潮时期,在大多数人眼中,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与地区仍是神秘莫测之域。
当西方人大批涌入远东的同时,欧洲却难觅东亚人的面孔,最早踏上欧洲土地的估计是4位13岁上下的日本少年。他们在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Valignano,1539-1606)的安排下,于1584年8月登陆里斯本。在罗马,日本少年受到了教皇的隆重欢迎,圣安哲罗城堡礼炮齐鸣。[7][8]相隔68年之后,首位华人来到欧洲,可惜没有留下太多记载。①此后,沈福宗(1658?-1691)的经历却显得风光无限。沈是生活在南京的基督徒,在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的陪伴下于1683年②抵达荷兰。沈自踏上欧洲大陆那一刻起便引起极大轰动。在巴黎,路易十四曾邀请他进餐,惊讶其能用两根短小的银筷进餐,特为沈开启了凡尔赛宫所有喷泉;1687年,英王詹姆士二世邀请沈参观皇宫,期间命画师在皇宫卧室为沈绘制了一幅身着中国服装的肖像画。5年后莆田人黄嘉略(Arcadio Huang,1679-1716)与传教士梁弘仁(Artusde Lionne,1655-1713)一道从厦门出发于1702年底到达巴黎,遂转道罗马拜见教皇,这位能够使用拉丁语交流的华人教徒令教皇十分喜悦,当他重返巴黎时引起了文化界与皇室的极大兴趣,并且成为国王图书馆的翻译。
一、虚构身份
在当时那种追逐异域想象,并且缺乏人种、肤色等概念的氛围中,逐渐有人虚构身份,冒充亚洲人特别是华人以引起社会关注。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中国定居多年,他在1697年的书中曾有记载,说在巴黎曾遇到一位奇怪的“中国”妇女,称自小生活在皇宫内院,是地位显赫的皇家公主。一次母亲与她登船出海,欲将其嫁到日本,途中不幸被荷兰与法国海盗两次洗劫,匪徒将这位公主辗转带到巴黎。李明认为根本无须盘查就知此妇女假冒身份。其面部特征、处世特点、脚的大小以及一切行为特征都暴露出她根本不是中国人。为了更具说服力,李明首先写下几个汉字让该妇女朗读,可惜对方将纸张都拿倒了,随后他又以朝廷通用的官话与其交流,而对方回以听不懂的胡话乱语,最终使得该妇女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冒充。[9]
1703年的伦敦忽现一东方人,自称来自葡萄牙人所谓的福摩萨岛(台湾),③这位年轻人不仅熟练使用拉丁语而且操着一口听不懂的台湾土语。当时虽然中华文化在整个欧洲特别是法国上流社会深入人心,这座中国东部的海岛却并不为人熟知。曾经踏上这片岛屿的也仅仅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的少数探险家和传教士。第二年,此福摩萨“番民”为证明自己,遂将其所谓的经历写了本《台湾历史地理见闻》(以下简称《见闻》)以飨读者。作者自称乔治·萨曼纳扎(George Psalmanaazaar,1679?-1763),原为台湾土著,父亲是当地的富有人士。[10]12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在1705年第二版《见闻》再版序言中,他含混地说父亲属于“钦命总督、邦主、福岛总督、将官以及其他富豪人士”,④自己19岁时在耶稣会土狄罗德⑤的鼓动下逃到欧洲。
我们今日仍然无法确认这个冒牌货的真实姓名。“乔治”是其后来接受洗礼时别人送的名字,而“萨曼纳扎”也非典型的台湾方言。作者在第一版《见闻》中使用了Psalmanaazaar的拼写,在第二版以及此后又改为Psalmanazar。如此杜撰的理据似乎从拉丁通俗本《旧约·列王记下》能够得到一丝线索,该书曾经提到亚述王Salmanassar。⑥在希伯来语中shalom是表示“和平”的词根,该意义与《见闻》的陈述似乎有巧合。萨曼纳扎说台湾人开始不信神,只敬重日月,后来神震怒,暴雨冲毁大地的果实,一些地方发生地震,导致野兽横行。经人们的长期殷切恳求,神为那里的人们派了一位先知,代表了神与人类新的和平与和好,因此台湾人将先知称为Psalmanaazaar,也就是“和平缔造者”的意思。[10]154从他名字的来源我们可以推断,萨曼纳扎此前已经掌握了一些希伯来语,或者有可能具有犹太血统,而他后半生始终保持着对犹太历史和语言的兴趣。当时持这一看法的不止一人,在1705年《见闻》再版序言中,萨曼纳扎也承认,他在被征召入伍之后,“军中小队长登记名册时询问本人姓名,以为本人为犹太教徒,本人予以否认”。[11]40
世人对萨曼纳扎成名前的了解仅仅局限于其去世后于1764年出版的一本《自传》,而该书的真实性同样令学者生疑;最大的障碍是萨曼纳扎连自己的真实姓名、出生地都不敢透露,只是说,他“并非出生于欧洲以外,也没有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受过教育,或者游历过,从小在南部地区生活一直到大约16岁”。[12]在《自传》的“致读者”序言中,与萨曼纳扎有过20年交往的维莱特牧师说他毫无疑问是法国人,带了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涅口音,应该是法国南部地区朗格多克人。
目前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个自称萨曼纳扎的人出身于法国南部天主教家庭,在圣方济各会、耶稣会以及多明我会的学校中就读,使他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毕业后,由于出色的语言天赋和记忆力,他曾做过短期家庭教师,后回到母亲身边。母亲无力支持其生活,于是他徒步500英里去德国找寻自己的生父。见到父亲时,这位近六十岁的老人生活同样窘迫,这个孩子像乞丐一般不得不再次出走。途中,他萌发了冒充东方人的想法,起初将自己假扮成日本异教徒,在耶稣会士的诱导下皈依天主教,成为教徒。期间他创造了一套新的语言,叫福摩萨语,以及相关的语法、宗教思想体系,并且将一年分成20个月。此后,他在德国科隆加入了荷兰雇佣军,驻防于法国丝路易斯地区。他的奇特行为引起了军队将领乔治·劳德的注意。1703年2月,劳德邀请教区长助理达玛维以及随军牧师亚历山大·伊尼斯(Alexander Innes)一起对这个“日本人”进行盘问,讨论了关于日本宗教及其对天主教的看法。牧师伊尼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几次盘问期间他私下让萨氏做了些翻译,先将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拉丁语文章拿出一段,让对方翻译成他所谓的土著语,翻译完毕之后将译文收回;然后用同样的一段让其做第二次翻译,由于萨氏一时无法完全回忆起自己生造的语言,结果两篇译文出现巨大差异。伊尼斯很快察觉出其中的奥秘,但出于个人升迁的考虑并没有揭露这冒牌身份,他希望自己能以劝异教徒皈依的功劳向上表功,于是让这个日本人“好好考虑一下未来”。估计就在这个时期,萨曼纳扎改进了身份,把自己编造成所谓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1703年底萨曼纳扎公开接受了洗礼,劳德以教父身份把自己的名字“乔治”赠于他,然后这个乔治随伊尼斯一同来到伦敦,并于1705年在牛津大学教授自己独创的台湾语。
二、作者与真实
作者与真实这对关系中包含有两个要素。首先,既然权威(authority)、真实(authentic)以及作者(author)为同一词源,因此内涵一致,那么“权威”的“作者”是否历来与客观真实相符?其次,声称的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实?
有学者总结说:所有来自中国的欧洲作品都是凭空杜撰,这些古今作品或存在谬误或是虚构。[13]18世纪前,人们是否真正踏上最遥远的东亚土地并不重要,众多具有说服力、被认为是最可信的权威作家或许根本从未游历过该地区,所谓的真实仅仅是基于整理前人资料之上的想象,更不乏建立于虚构之上的虚构。17世纪前,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帝国史》是关于中国最畅销的著作,该书于1585年在罗马首次出版,截止16世纪末,已经有30个版本,以欧洲7种语言重印了46次。[14][15]1-2:744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阅读面很窄的年代,毫不夸张地说,17世纪初大部分受到良好教育的欧洲人都读过门多萨的书,它的影响面如此广泛,甚至连培根这些人的中国思想都来源于此……而门多萨本人最远只到过墨西哥”。[16]门多萨直接或间接地大量盗用他人资料是公认的事实,历史学家经过仔细考证和比对斥责其夸大其辞,伪造数据以及明目张胆地抄袭、改编。然而在他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因抄袭改编而受到处罚,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没有一部情节是其原创,却并不影响莎翁的魅力。葡萄牙人平托(15097?-1583)在自传性作品《平托航海及冒险记》(1614)中叙述自己曾经在亚洲冒险21年,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不仅多次逃脱海难事故,而且被收监并贩卖过16-17次,先后成为海盗、奴隶、大使、士兵以及传教士等。该书有众多前后矛盾和匪夷所思之处,学者卡茨认为平托随意借鉴了克鲁兹的《中国论》(Treatise on China,1569),因此17世纪末“平托的名字与谎言家是同义词”。学术界目前可以证实的是他可能仅仅数次登上过广州沿海的几个岛屿,不太可能去过中国的其他地区,因为1555年前后葡萄牙人不可能在中国内地随意游历,这些内容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然而就是这本充满谎言的作品仅在“17世纪就已经有19个版本,翻译成6种语言”。[17]
即使长期在东方生活的作者也不见得客观真实地讲述事实。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1597-1647)是最早进入台湾的传教士(1627年5月),并且长期生活在土著居民中间,对台湾土著的生活做过详细描写,并且成为18世纪前欧洲了解台湾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对当地女性婚孕习俗有如下描述:“依据那里的法律和习俗,女人一直到35-36岁甚至37岁才允许生育。之前一旦怀孕,子宫内的胎儿就要被打掉。方法如下:他们会叫来女祭司,怀孕女子躺在地上或卧榻上,然后祭司挤啊,掐啊,粗暴地让孩子流掉。……那些台湾女子向我承认说,她们都怀过15-16次而且每次都这样流产,有一个女人告诉我,一直到17次怀孕的时候,她才让这个孩子生下来。”[18]20
干治士的这段描写既耸人听闻又毫无科学根据,而萨曼纳扎非常善于利用读者的常识观念来反证自己的正确,他在第二版“序言”中就对于治士此番言论进行了驳斥:“干治士自己说许多女性因为这一陋习死于非命,即便人口众多之国,不出几年,人口势必绝减。天气炎热如福岛者,女子生育年龄更早,而上了年纪后很少能够怀孕。果真行此恶风,我国人口必已所剩无己。我敢说福岛女性过38岁者很少能够怀孕,更不要说经历女祭司15、16次致命的踩踏。”[11]47萨曼纳扎充分利用了这些常识性错误,毫不留情地反击耶稣会传教士在这一方面的作伪,以求反证自己作品的真实性。这些内容是否真实有效,对于读者来说首先要考察作者是否真的土著,然后确定其权威性话语结构。
从早期东亚人来到欧洲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看出,以异国身份叙述本土风土人情不仅受到追捧,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体现出“权威者”的话语。这种借力的方式早在文艺复兴早期就已经出现,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1516)中就曾借助异国人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eus)的身份评论当时英国社会与政治。18世纪英国文学中游记类作品达到了空前繁荣,而大量旅行者利用这个机会对于异国风情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一叶蔽目,或者遮遮掩掩;他们在廉价的版本中充斥了游记谎言,在取悦公众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偏见与虚荣心;他们虚构事实,生造在南太平洋以及美洲的野蛮人种,而对东亚的国情歪曲也不例外。
作家身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从口头文学到早期书面文学,作品在传承中经历过不同人的反复修改,无法确定具体个人在文本定型中究竟做出了何种贡献;在早期书面文学,特别是抄本文化中,作品的读者往往局限于友人等小群体内部,作者的身份与作品的归属较为清晰,署名既无必要,也无法带来经济利益。学者洛夫认为:经过对英国文本的调查,作家权的根源在于宗教改革后神职人员对英国教会古典传统的考证,以及17世纪法律工作者对英国习惯法以及代议政体的探究。[19]17世纪之后,人们对于“作者”概念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1709年英国第一部版权法案通过后。群体作者的思想逐渐被个体作者所取代,作者的真实性身份伴随着文学批评发展显得特别急迫。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场争论比得上围绕萨曼纳扎身份以及其伪作《台湾历史地理见闻》的争议。
何谓身份?林奇在引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后说:“个人身份只存在于意识当中,跨越时间的个人身份显然是通过记忆过程存在于跨越时间的知觉意识当中。……应该说,身份至少在理论上是客观的,可以被第三方论证的,是唯物的;而洛克时代的身份在定义上是主观的。”[20]146观念来源于心理知觉和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判断来自概念间的比较。欧洲对台湾的了解相当有限,这也是萨氏假冒身份的成功之处。在缺乏人种概念以及其它外部条件的前提下,人们无从比较后下判断,而对作者身份真实性的探究只能依靠其言行举止,正如李明所遇到的冒牌中国公主那样,一个成功的身份很大部分依靠是否表里如一。18世纪初,除了黑人外,人们对人种、肤色、毛发等尚缺乏严格的科学概念,因此无法辨别国与国之间以及种族的外部差异。萨氏说白人耶稣会士为了避免受到日本政府迫害,首先是学了日本语言,然后穿着日本衣服,就不会引起怀疑,“当他们来到日本,他们装扮成国内其他岛屿的居民,当地百姓丝毫不怀疑,当成是真的。因为他们穿着本国的服装,讲着一样的语言”。[10]4同样道理,即便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在欧洲谎称是亚洲土著也仅仅受到怀疑而已,远没有像语言与生活习俗那样成为直接判断的依据。为了证实萨氏的土著身份,伦敦皇家学会特意邀请了曾经在宁波、北京以及南京传教18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参与调查,而他的记载也仅仅说萨氏金发、皮肤白里透红,估计是荷兰人。[21]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说18世纪初人们对萨氏的身份有怀疑,并不是说他不像台湾人,而是因为他皮肤比较白。当时人们对皮肤白皙的理解并非基于人种概念,而是认为人受到日照时间的长短。对此,萨曼纳扎自有自己的解释,“尽管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炎热……有产业的人特别是女人却非常白皙,因为在炎热季节都住在阴凉地方的地下,花园、果林树木茂密,阳光无法穿透……他们用蒸馏水不仅能够清洗自己,而且能够去除皮肤表面的斑点,故皮肤白皙”。[10]197
英国与欧洲大陆交往中逐渐显露其强烈的岛国意识。在新航路的开拓中,英国社会以更开放的眼光对比与其它岛屿的文化差异。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其综合国力与民族自豪感迅速增强,欧洲中心论思想很快被英国中心论所替代。18世纪起,英国社会一方面越来越关注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优势,另一方面以鄙夷的目光看待其它异域文明,也时有对自我的关注。当某一社会意识到自我的强势地位后,任何其它文明便被贴上“野蛮”的标签,古希腊如此,18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古希腊人将不使用希腊语的人通称为“野蛮人(barbaros)”,当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的海地之后,食人族(cannibal)很快成为荒岛文学的重要内容,任何一座未知的岛屿都能触动英国社会的神经。为了强化荒岛土著身份以及“权威话语”,以迎合读者想象,萨曼纳扎不惜脱离欧洲文明,以食人生番的身份刺激社会,甚至啖食带血生肉。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曾经发表在1765年的《君子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上,记载了萨曼纳扎1704年与客人一同进餐时的言语。他吹嘘说,福岛男人对自己的多位妻子具有绝对权威,如果发现女人偷情则完全有权杀掉她们,然后生食其肉。听了这话,席间受到惊吓的一位女士尖叫道:野蛮(Barbarous)!他解释说吃人肉并非罪恶,不仅如此他祖父坚持每天早晨饮用蛇血,活到了117岁。[22]183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三部分拉格纳岛的几位寿星。为了证实福岛土著身份的真实性,萨氏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食用生肉,他在第一版“序言”中记述说,洪若翰“看见我吃生肉非常惊讶,因为他说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都是经过加工后才进食”。[10]xxxix
三、空间虚构与科学辩正
1704是英国文学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阿拉伯的《天方夜谭》英文版首次面世,同时萨曼纳扎这位冒牌土著出版了《台湾历史地理见闻》,引起社会极大兴趣;第二年就有再版,且很快有多个法文、荷兰文和德文版本。《见闻》颠覆了过去西方传教士对东方国度歌功颂德式的传统写作,启发未曾游历过东方的读者用质疑的目光看待东方文化,逐渐形成了对东方文明“尊崇”与“诋毁”两种想象风格。冒牌台湾人萨曼纳扎开宗明义地反对传教士对东方传奇式的描写,他在序言中不屑地说,“我时常听到关于遥远东方国度的诸多传奇故事,尤其是我的故乡,这些故事令诸位读者以为是真理,并坚信不疑。……但是真理应当驱散那些无稽之谈,我自己深感责任在肩,不愿读者陷于无知与误导当中,而应当给诸位一个更加忠实(more faithful)的福摩萨岛历史”。[10]xxxi
18世纪英国是个充满“真实”或“忠实”等情结的时期,为迎合读者口味,众多标榜为真实的叙述大多为虚构性文学想象,所谓“真实”仅仅指作者创作目的的明确性;美国学者林奇先生利用“简短标题目录”检索了整个18世纪英国版图书的书名,发现题目冠以“真实”(包括authentic,genuine以及real)的做法在这10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包含这三个英文单词的书名从头10年的1、10、27本分别飞涨到1790-1799间的324、302、214本。[20]1这一数据表明18世纪英国叙事文学正在摆脱明显幻想(fantastic)的罗曼司影响,进入到具有想象力的(imgsinative)写实主义文学。虽幻想与想象均属虚构,但在浪漫主义大师科尔律治看来,幻想是仅仅摆脱了时间与空间次序后的回忆方式,从联想规律产生的现成材料中取得素材,[23]也就是说幻想是在不改变素材前提下进行重新排列组织;而想象是在相互对立或斗争中寻求质的平衡与协调,将一些不可能的素材创造成新的整体。《见闻》就属于想象类型,它是建立在部分真实基础上的虚构,将一些杂乱的材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张冠李戴,誓言真实。
台湾是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部分。依据中国古书,台湾曾有“岛夷之地”、“瀛洲”等多种称呼;到了明代,台湾被称为“大员”,或“台员”,估计是闽音之谓,实指现在的台南。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南的安平,沿用了“台员”之音,有“Tayoan”,“Tayouan”,“Tyowan”等拉丁拼写,后来泛指整个台湾岛。与现代地理地貌不同的是“台员”过去曾是个小岛,尚未与台湾主岛连接。范伦厅(Francois Valentyn,1666-1727)的《新旧东印度志》(Oud en Nieuw Oost lndien)出版于1724-1726年间,该书记载说1622年荷兰人首次登陆台湾,“他们在福摩萨岛的南端确定了一个港口,靠近台员这个小岛屿,发现已经有中国人定居在那里经商。然后他们用小船将物资运过来,这里离佩斯卡多尔列岛有12-13英里,当然也并不顺利,毕竟水深只有11英尺,而且航道弯曲,大船无法驶入。还要说明的是这个台员仅仅是个小岛屿,或者叫干的沙洲;长度不到1英里,离福摩萨只有半英里”。[18]27
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就已经了解了台湾的大致情况,1515年葡萄牙人皮勒斯在《东方志》中曾经提到包括台湾在内的琉球群岛附近海域。在1550-1570年间,鲁特斯(Rutters)将台湾称为“福摩萨”(Ilha Formosa),意义为“美丽之岛”,[15]1-2:722此后与中国人称呼的“琉球”交替使用。
为图与中国互市,荷兰人长期盘踞于澳门、台湾等中国近海,并于1624年从澎湖退到现在安平的台员,以期进一步发展贸易。萨曼纳扎等西方人对这些信息恐有所耳闻,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台湾也与此事有关,一封1623年2月24日写于巴达维的信提到,“中国特使现已到此,提出可以与荷兰互市,条件是荷兰人离开佩斯卡多尔列岛(Pescadores,即澎湖),居住在台员(Taywan)”。[24]而英国第一次进入台湾更是50年之后的事情,因此当时社会缺乏了解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早在1662年郑成功就已经将整个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1593年日本丰臣秀吉曾有袭台之议,并且日本德川家康分别在1609和1616年两次入侵,但均未成功。萨曼纳扎正是利用英人对此的无知,虚构台湾属于日本,并且编造故事,说一位叫马里安大奴的中国人曾从小到日本,后深得日本皇帝和皇后的信任,但他设计害死二人并篡夺皇位。登基后第二年,他托病需要到台湾向神祭祀还愿为由,取得了台湾国王的许可,再以类似木马计的方式控制了国王以及整个国家,使台湾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18世纪英国社会批评之风盛行,科学与文学之间充满了火药味。萨曼纳扎的“台湾人”身份自然引起了伦敦皇家学会的怀疑。该组织特别邀请洪若翰参与盘问,前后至少进行了3次。第一次估计在1703年2月2日,学会会员首先问洪若翰福摩萨岛的归属。洪回答说:属于中国皇帝,理由是曾有一艘英国船只遭遇风暴后搁浅在福岛海滩,幸存的耶稣会士去信与他请求帮助。洪上奏中国皇帝,皇帝下诏要求福岛居民归还人员与船只,对方照做。萨曼纳扎认为属于日本,同时辩解说福岛并未与中国交战,漂流到沿海的船只人员理应交还,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然后萨曼纳扎问洪:我希望他告诉我,中国人是如何称呼福摩萨的,他回答道,不知有它名,只知叫福摩萨,或者台窝湾(Tyowan);萨氏答,“这很明显无论从我所知(当然我最清楚了),还是从一位刚去过台窝湾的先生那里所述,台窝湾(Tyowan)实际是离我们有点远,而完全不同的岛屿;现在属于荷兰的殖民地。对此神甫承认一无所知。我又进一步告诉他,中国人称我们这个岛叫帕堪多(Pak-Ando),这与我们自己所说‘加答维’一致,都是指福摩萨”。[10]xxxvii
洪并未亲身游历台湾,他以满清朝廷的知识了解台湾,比较粗浅。台湾的称呼大约是万历年间开始于民间,直到1684年康熙将台湾收入版图,台湾才正式指称整个台湾岛。[25]24萨氏需要对自己的伪作叙述创造一个可信空间,他对“福岛”做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帕堪多”的说法估计是来自在台湾传教近10年的干治士,他曾经说,“这个大岛屿土著人称为帕堪(Pak-an),或者帕堪德(Pak-ande);中国人叫大琉球;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叫福摩萨”。[18]1干治士的Pakan估计是指明朝中期后,汉族人讲的“北港”,也就是指台湾。1617年的《东西洋考》中有如此说法:鸡笼、淡水洋,在澎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25]23因此,萨认为帕堪多就是福摩萨是有依据的,而其认为“台窝湾实际是离我们有点远”纯粹杜撰,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可信的虚拟空间,有意与人们的既有知识保持距离。
第二次盘问特别邀请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哈雷彗星的精确计算者——天文学家哈雷(Edmund Halley,1656-1742),期间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对此却有粗略记载。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一本《见闻》二版扉页上有以下一段铅笔记录的评注,估计是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手笔:“许多细节都暴露出该书对公众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欺骗。哈雷博士生前曾巧妙地问他几个问题,一切便被揭露出来,作者自取其辱。哈雷博士问在福摩萨每年的曙暮光持续时间多长,太阳直射烟囱有多久。他的见解暴露出他从来未曾去过那个岛屿。”[26]41,43
哈雷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他自然明白问题的答案。考虑到台湾横跨北回归线,只有在方位角时,太阳才能直射进烟囱;针对曙暮光,由于英国与台湾的纬度不同,持续的时间当然有差异。作为土著居民,萨曼纳扎理应知道这个常识。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萨曼纳扎如何即席回答这些问题,才导致“他的见解暴露出他从来未曾去过那个岛屿”,然而他在第二版序言中的辩解却显得非常聪明:阳光亦不可能自烟囱直射而下。因在福岛烟囱并非直立,屋内排烟经过墙内的弯曲烟管而出,烟管末端直立向上,以便送烟至空中。最后一次质询是1705年6月13日,在会议上有人宣读了几封来自格里菲斯(Griffith)先生的信,他长期在台湾岛上生活,信中内容与萨曼纳扎的描述存在许多差异。
萨氏的所有言论并非全无依据,在描述福岛祭司时,他使用了番僧(bonzo)一词更增加了真实感,[10]167该词原本是日语“坊主”。沙勿略在书信中提到这些日本番僧穿着灰色衣服,每第三或四天都要剃一次头发。[27]《见闻》中描写的“踏绘(yefumi)”更是日本幕府迫害天主教徒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另一些内容仅仅是张冠李戴,如“福岛男性描述”一章中有:你们要知道,中国和日本人故意将牙齿弄黑,而福岛之人却是白的。[10]198我们相信这些令欧洲人惊异的习俗的确长期在东亚存在。在明朝之前,越南有长达1000年的时间属于中国附属国,直到17和18世纪与中国的交往仍非常密切。英国海盗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2-1715)一度活跃于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他出版的《新环游世界》(1697)、《游记与见闻》(1698)曾记载说在越南部分地区,“无论男孩女童都会在进入青春期后将牙齿染黑”,[15]Ⅲ-3:1290并且有将生肉用树叶包裹进食的习俗。染黑牙齿原本在越南非常普遍,人们通过咀嚼槟榔叶子在几天内就可以使牙齿变黑。[28]因此萨氏的一些描述也并非完全出于想象和编造。
四、《见闻》的目的性
虽为伪作,《见闻》仍与其它作品一样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该书1704版由两个并列部分组成,首先是讲述个人皈依新教的自传,第二部分是伪造的台湾历史地理描述;1705年二版则在两部分次序上做了颠倒,并增加了更多虚构内容。萨曼纳扎的轰动效应不仅反映了18世纪英国社会对东方的想象,“满足了英国人对奇异事物的热情,同时卑劣地迎合了英国当时盛行的反耶稣会情绪”。[29]从政治上说,《见闻》反映的思想体现了英国社会的反耶稣会传统,它的成功也在于得到了一批反耶稣会人士的默许。
1534年在巴黎成立的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该组织无论在宗教思想还是在政治理念上都非常保守,是整个欧洲反对新教运动的重要力量。耶稣会极力主张“教皇绝对权力”,既然教皇是基督在尘世的代表;认为上帝在尘世创造了两个管理体制,一曰世俗体制,另一为高于世俗的教会体制;而作为我们心灵守护者的教皇有权约束所有基督教君王。如有必要,教皇完全可以解除任何新教或其他天主教君王的政治权利。世俗的管理权原本属于百姓,君王与百姓具有契约关系;而教皇的权力则直接来自上帝。英王詹姆士为代表的新教政府以及支持者反对这一论断。早在1605年11月,一些天主教人士趁英国国会开幕式时,企图引爆事先埋藏在地窖中的炸药,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以及其他新教贵族。英国耶稣会首领亨利·加尼特事先已经知晓此阴谋,非但未通知政府,反而撰文强调其有权保持沉默。此后,英国不断涌现讽刺耶稣会的政治手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伊那修斯与他的密会》,该文由玄学诗人约翰·多恩于1611年发表,讽刺那些耶稣会士的科学实践。作品展现了一幅地狱的幻境,耶稣会创始人伊那修斯·罗耀拉与魔鬼撒旦并肩坐在椅子上,听取哥白尼、哥伦布以及化学家帕拉切尔苏斯等的陈述,他们均认为自己的邪恶创新为地狱贡献不小,但在罗耀拉看来,这些小发明在耶稣会士面前却小巫见大巫,例如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克莱维斯,他编订的格里高历书足以让天堂和人间永不安宁,所以除了撒旦之外耶稣会的成就无人能及。撒旦惊恐罗耀拉等人的潜能,担心地狱终有一日被耶稣会统治,于是打发这些会众去月球开发新的地狱。[30]
耶稣会众一直认为福岛的祭司因羡生妒,加上荷兰人排除异己故造成日本对天主教关闭大门。而萨曼纳扎移植了17世纪.日本德川幕府迫害基督徒的时代背景,反驳耶稣会的欺世之举,认为“其中另有隐情”,“草丛中有蛇,只有自己发现了”。[10]xxxv虽然在序言中萨氏并未点出其中“隐情”,却以虚构的亲身经历故事为例,说明耶稣会成员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不惜乔装改扮,混到当地居民中,以邪恶的方式诱导并欺骗当地民众。如耶稣会士狄罗德谎称为日本富人后代,在13个兄弟中排行最小,分到的产业也最小,只好无奈地在各地游荡,以教授拉丁语谋生。这番谎话让萨氏的父亲以年薪17磅黄金聘其为儿子的家教。4年中,他丝毫未透露天主教徒身份,只是从不进福岛的庙宇,说自己另信他教。期满临别前,他反复盛赞天主教国家,说教徒对异国人士非常热情,若日后返回,必以巨额财富赠送。此番言辞让19岁的萨曼纳扎心有所动;而狄罗德非常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却马上拒绝说,将其从父亲身边带走是天理不容,这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大大提高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因此在某天夜里,狄罗德怂恿萨氏从父亲那里偷盗了25磅黄金作为路途的盘缠。[10]12经过长途跋涉,两人最终来到狄罗德的故乡——法国阿维尼翁,这时他才坦陈自己为基督徒,然后答应说如果萨愿意回家,他可以提供生活必需。萨氏在书中写道,“这个建议口是心非,他无意履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因为他知道,我倘若回到祖国,他会一无所获,而他希望我能留下来,皈依他们的宗教”。萨曼纳扎的讽刺是深刻的,狄罗德是早期耶稣会士的缩影,影射了范礼安、柏应理、干治士等耶稣会士以不正当的方式将东方青年带到欧洲,目的是“为他自己取得更大的荣耀,甚至放风出去说我是国王之子——真是天晓得”。[10]16
萨曼纳扎不仅反对耶稣会的政治与宗教主张,而且反对他们所代表以及推广的科学理念。耶稣会众远非单纯意义上的传教士,而是以自然哲学武装起来的学者,其成员大多是数学、天文和地理等科学家。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更加说明他们在自然科学、艺术史以及教育学等领域的突出地位。[31][32]与前人不同,耶稣会成员在传教中特别注重发挥自己的自然科学专长,在满清的中国,“17世纪中叶以来,受过良好教育的耶稣会科学家担任了钦天监的职务,逐渐参与朝政。为了强化基督教地位,他们教授数学,参与监造炮台,协助与沙俄的外交谈判,绘制中国地图”,[33]在利马窦等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一些明清时期的科学家纷纷接受洗礼,如崇祯时期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以及担任工部外郎的李之藻等。耶稣会士去世界各地传教前均需接受系统的科学培训,学习“天体星球数量以及运动状况、星象多角度观测、星球因相合相斥造成的相互影响……一年级学生需要在4个月内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4册;一个半月学完实用算术;两个半月学完行星运行,2个月完成地理,假如尚有剩余时间则学完欧几里德的5、6册。二年级学生要在2个月内学习测量天体运动的星盘,4个月学习天体理论,3个月完成光学,剩余时间学习钟表制作和教会计算法。成绩优异者进入3年级自主学习,包括天体高级理论,学习制作万年历、星象表,使用象限仪等”。[34]像洪若翰、李明等6位耶稣会成员全部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御用数学家”的身份到达中国,他们带着科学仪器、年俸和国王下达的“改进科学和艺术”的敕令扬帆东来。在美洲的印第安村落,“德阿科斯塔神父还用典型的西属美洲的叙事风格撰写了一部具有神奇色彩的游记,于1590年发表过比较人种学著作《印第安人的自然与风俗史》”。[35]
我们不妨将这部萨曼纳扎的伪作理解成以虚构与幻想为特色的文学对求真务实的科学的反击。萨曼纳扎虽然没有如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亲自登上福摩萨,而他在读者中一时取得的真实度远远超过这些科学家兼传教士的科学报告。《见闻》基本按照耶稣会士惯常内容结构为蓝本,编撰台湾风情。倘若对照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1655年英文版)就可以看出两者内容的相似性。《大中国志》包括了中国总述、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国人的科学特别是他们的艺术、中国人的礼节仪式、中国人的宴会、他们的婚姻、中国人的丧葬、中国的教派等章节;同样,萨曼纳扎在《见闻》中罗列了地理概况(1章)、各阶层男女服饰(19章)、语言文字(30章)、学术艺术(36章)、社会礼仪风俗(17章)、饮食起居方式(28章)、婚姻礼俗(12章)、殡葬礼俗(13章)、宗教信仰(4章)等内容。[36]传统耶稣会书简或者报告集往往是作者数年甚至几十年在异域经历的积淀,需耗费很长时间进行修改和出版,但《见闻》不同,萨氏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便完成了创作,其中涉及大量异域信息竟在如此短时间内合成,并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正说明科学进步的同时,想象力文学在与之争夺社会支持。伦敦皇家协会组织耶稣会成员以及部分科学家先后进行了三次质询,然而结果显然没有推翻萨曼纳扎的虚构。在一定时期内,《见闻》超越了科学辩正,取得了科学暂时无法涉足的广泛认可。两个英文版之后,相继有2个法语和2个德语版本面市,甚至到了1739年仍有法语译本出版,而1808年更有权威的学者将萨曼纳扎的《见闻》定性为关于台湾的权威作品,而且肯定他是出生于此。[37]
《见闻》这部伪作不仅给萨曼纳扎带来了读者的轰动效应,而且有同时代名人的支持和尊重。约翰逊博士的传记作者曾经说过,萨曼纳扎在邻里中“非常出名,而且备受尊重,霍克斯沃思博士有一次对我说,任何人,甚至孩童在路上遇见他时都会敬重地向他致意”,约翰逊博士“非常尊重乔治·萨曼纳扎”,并且“过去时常与他一起去城里的酒吧坐坐”。[38]思瑞尔夫人(Hester Thrale,1741-1821)是约翰逊博士的密友,她在日记中证实说,“博士认为萨曼纳扎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好的”。[39]萨曼纳扎在去世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些作家热议的对象,著名作家贺拉斯·沃波尔在1777年2月17日写给友人梅森的信中说,“独萨曼纳扎一人在才气上就已经超越了查特顿”。[40]一年之后的5月23日,他又给友人比利写道,“总之,我相信再也没有像萨曼纳扎这样的才气卓绝之人,他能在22岁前创造出一种语言,使得整个欧洲的饱学之士虽有怀疑但无法察觉”。[26]248
五、伪作对名作的影响
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东方虚构对现代小说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正如康南特所说,“在17世纪中叶,一些虚构的东方英雄传奇,如斯居代里小姐(Madeleine de Scudery,1607-1701)和其他一些人的创作,被翻译出来并获得巨大反响,这些英雄传奇在18世纪被重印,形成了这两个时期中小说的重要联接”。[41]以我国台湾为背景虚构的《见闻》为同时代英国小说提供了不少可借鉴之处,这不仅由于《见闻》是建立在部分历史真实之上的虚构,这与该时期小说所标榜的真实具有相同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细节真实铺垫成就虚构的现实主义色彩。
《见闻》虽未对中国文化进行正面抨击,却在怀疑论背景下对异域文化提出了质疑,这些缺乏事实根据的质疑往往建立在欧洲中心论上,或者基督教至上论基础之上,认为基督教之外的文明均是野蛮社会,而无论是东方还是美洲的,只要是野蛮社会基本都存在生食人肉的现象。而这种原本基于歪曲想象的所谓见闻却鼓励了《鲁宾逊漂流记续集》(1719)在诋毁中国文化中浅浅地试了一脚。笛福没有了解亚洲文化的直接证据,却是基督教至上主义者和欧洲中心论者。他认为只有基督教美德才能让野蛮人开化,而尊崇祖先的中国人都在搞偶像崇拜,他们的宗教都集中在孔子理论中。这种神学实际是政治、道德和迷信的大杂烩,根本比不上基督教渗入后的台湾,那里“基督教总能让人们文明进化,进而调节人们的行为”。[42]笛福与萨曼纳扎属于同一类别,他们都具有明确的虚构目的和民族偏见,因此能够从外在材料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对自己有用的素材,同时他们比较肤浅,因为并没有身临其境,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所以很容易露出马脚,例如笛福将南京当成是中国最北端的“海港”。[43]
相比之下,讽刺大师斯威夫特从萨曼纳扎处得到了更多的虚构素材。1722年斯威夫特着手创作《格列佛游记》之后不久,就在书信中谈到自己正“另外研读许多关于历史和游记的书”,[44]我们相信这本《台湾历史地理见闻》的第二版应该就在其中。《格列佛游记》的四个部分中,第三章“飞岛”是最后完成的内容,大约跨越了1724年4月和1725年。[45]从这个时间推断,斯威夫特在1729年发表《一个小小建议》(以下称《建议》)前肯定读过《见闻》这部伪作。《建议》中曾经提到一位在伦敦并且深谙内情的美国人建议,喂养壮实的一岁小儿无论炖、烤、烘、煮都是非常可口、营养卫生的食品,并且这位谋士称自己“受了那个出了名的台湾岛人萨曼纳扎的启发。约在二十年前,那个人从他本土来到伦敦,在交谈中对我那朋友说,在他本国,如有青年人被处死刑,刽子手就把犯人尸体当作一种珍馐美味卖给王公贵人;还说,当时有一个十五岁少女因为图谋毒死皇帝而被处磔刑。她那肥胖的身体挂在刑架上,肉给一片一片割下来,卖给万岁爷的宰相和其他宫廷大员,一共卖了四百克郎”。[46]于是这位谋士一本正经地提出建议,把贫困的爱尔兰孩子卖给有钱人当作佳肴品尝。吃人肉的习俗并未在《见闻》头版中出现,而是第二版中萨曼纳扎特地增加的素材,虽然我们一时无法断定斯氏是否看过第一版,但是仔细研读过第二版是肯定的,这本书为其提供了《建议》的主要构思。萨氏在第二版中如此写道:“福岛人也吃人肉(如今我已知这是野蛮行径了),除了吃被俘虏被杀的敌人之肉,也吃被处死刑的罪犯,而罪犯的肉一般视为佳肴,价格比其他稀有美味肉品贵上三倍。买死刑罪犯的肉要找刽子手,因为依法,行刑者的尸体乃是刽子手的薪酬。受刑者死后,他便将尸体分割,放掉尸血。他的家于是变成肉铺,买得起的人便可上门光顾。我记得约十年前,一名十九岁的奉腴、漂亮、美肤的高个子小姐被处死。她本是邦主夫人的梳妆女侍,因为计谋毒死邦主而被判了判国罪,依法要受最残酷的死刑。因此她被钉上十字架,每当她痛得晕过去,执刑者就给她灌烈酒,尽量拖长她受苦的时间。钉至第六天,她死了。长久的疼痛,加上她年轻肉嫩,使她的尸肉又柔韧又美味,价钱卖得极贵,达到八它伊娄(Taillo)的好价钱。买者争先恐后,连富贵人家都未必抢购得到。”[11]164-165
《见闻》启发远远不止一处,如果说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度在欧洲并不陌生,我们无法判断斯氏在《建议》中所说“留下两万(婴儿)做配种……一雄配四雌”是否受到《见闻》的启发,然而萨氏的确在“婚姻习俗”中有:“神许可男子——世俗男子——娶多位妻子(福摩萨人的妻子与英语所说的妻子意义不尽相同,贵国指的是共同治家的同等地位者,福岛却视之为奴隶)。因此福岛男子有娶三、四、五、六名妻子不等者。”[11]97
在《建议》中,斯威夫特一直摇摆在两个极端之间,一是对爱尔兰人的极端同情,二是对爱尔兰人的极端愤怒,这两个极端让斯威夫特几乎走上了疯癫的绝境,文中内容真真假假。斯威夫特在《建议》结尾中说,“我的子女最小的一个已经九岁,所以不能拿出去赚钱”。假如我们再将此年岁同样理解为疯癫之语,或不仅疑惑为何斯威夫特不将此岁数定为10岁,或干脆说成5岁?而唯独选择了9岁?那么我们就低估了斯威夫特的深刻了。他实际在影射《见闻》中以9岁童男童女祭祀异教神灵的可怕习俗。萨氏在“福岛宗教”一章中说,“有两位哲人来到都城附近的山上,告诉人们神的旨意,即要求福岛之人建座神坛,在那里要焚烧2万名9岁以下儿童的心脏。当神坛建好后,这个神化成牛,然后告诫人们将一年分为10个月,以后新年第一天都要献上9岁以下男童的心脏18000个”。[10]153-158这里可以推测,斯威夫特对数字的处心积虑是希望借助当时《见闻》影响力的余波,引导读者将当时的岛国爱尔兰与异教的岛国福摩萨进行类比,将残暴的英国剥削者比作可怕的邪神,令9岁以下的孩子献给他们当作佳肴享用。
《格列佛游记》(1726)的第三部分“飞岛”也不时围绕着萨氏的“福岛”:1707年4月格列佛抵达印度马德拉斯,然后转道越南东京,在那购买了单桅帆船再次出海,遭遇风暴后,船只连续5天朝东北方向漂移,然后再朝东航行。最后被海盗劫持,日本海盗船长给了他一艘独木舟任其漂流;格列佛朝东南偏南方向航行了5天后在一座较大的岛屿登陆。[47]141-142虽然斯威夫特并没有说明所处的精确地理方位,然而他却读过丹皮尔的《新环游世界》1698年版本,[48]而且读者很容易与“福摩萨”的附近岛屿联系起来。随后格列佛登上了飞岛,这座直径4英里半的飞岛仿佛是所罗门的魔毯,毫不在乎相隔千山万水,然而哪怕飞到拉嘎多(Lagado)再越过美洲,最后仍落到一座东方岛屿之上。斯威夫特说有这么一座长生不老之岛,叫拉格纳格(Luggnagg),“位于日本东南部相距100里格,日本皇帝与拉格纳国王具有同盟合作,因此两岛之间常有航路”。[47]180这座岛屿的部分居民可以长生不老,整个王国大约有1100名这样的老寿星(Struldbrugs),首都占了50名。[47]193斯氏不明说拉格纳格就是伪作中的“福摩萨”,也不敢妄称在日本统治之下,而萨氏在《见闻》中的确说过“百岁以上的老人而无任何病痛者,在福岛很常见”。[11]157
不仅如此,格列佛觐见拉格纳国王也带有典型的中国宫廷传统,即中国特有的三跪九叩。[49]斯氏用惯用的讽刺口吻说,“去舔国王脚凳前的土,这就是宫廷的习俗”,然后是“双膝跪着,然后用我的前额叩地七次”。[47]190-191我们不能嫌弃斯威夫特的笨拙,毕竟“kowtow(磕头)”先有概念描述,直到1802年才选定这个中文发音成为英文中的外来词,萨氏在那本伪作中早有说明,恐是斯威夫特在此基础上的戏讽延伸。《见闻》说福岛人“有特殊的习俗,令一些人喜欢,而让其他人不快:首先是他们将帝王敬如神灵……百姓见他之前都要双膝跪地,匍匐于地面去膜拜他,然后才能起身仰望他”。[10]91向皇帝磕头的习惯无论对萨氏还是斯威夫特都可能印象深刻,自中西交流以来,磕头是争议最大的中西方礼仪。利马窦说,“在一些严肃的场合,作揖之后还要双膝跪地,以前额触地”。[6]60西方人对中国这一特殊礼仪偶有零星记载,由于不熟悉东方的繁琐礼仪,甚至导致外交纠纷以及使节外交失败,在萨氏时代最著名的案例是俄国特使拜可夫(Feodor Iskowitz Backhoff),他于1656年到达北京,却拒绝向康熙皇帝磕头,并且辩称:我们没有跪拜的习俗,甚至对我们的沙皇也仅仅是脱帽鞠躬。⑦
《格列佛游记》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站是日本,这里没有三跪九叩的礼节,但是在日本却需要更特殊的仪式以分辨并驱逐天主教徒。日本从德川幕府时代起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在荷兰人的帮助下,日本自1631年起首先在长崎港施行踏绘,以后蔓延到日本各地,以隔离与辨认这些教徒,即将事先刻有圣母玛利亚,或者是耶稣像的木板或铜板放在地上,让每个人去踩,教徒自然誓死也不会如此践踏这些圣物。斯氏对日本类似描写的来源也有争议,有些学者完全忽略了《见闻》这本伪作的影响力,转而求其它一些不可靠的来源,认为荷兰东印度医生、德国人堪普佛(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提供了斯威夫特这些信息来源。事实上,堪普佛的《日本史》英文译本出版于1727年,比《格列佛游记》晚了一年,甚至有学者牵强地宣称斯氏看过英文翻译的手稿,[4]255然而这一断言耸人听闻,毕竟不令人信服。从上面所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斯氏看过《见闻》第二版,而这本伪作早已如实描写了日本这一历史事件,“后来荷兰人就说,为了要证实他们不是十字架人,不信葡萄牙人的教,他们请求面谒日皇,以便教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即陛下令各海港市镇制作十字架,凡有外人入境,必须向十字架掷物、吐痰,并予以践踏……如此必可测出其真实身份”,[11]213《见闻》第一版开头部分就使用了“trample upon the Crucifx”这样的字眼,这正与《格列佛游记》202页“trampling upon the Crucifix”的字眼完全一致,这绝非是一般性巧合。
让我们以斯威夫特自己的语言替萨曼纳扎做最后一次有利的辩护,它让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伪作与名作之间并非有明显的人为界线:“正如最粗劣的写手都有自己的读者,最伟大的谎言家也有他的信仰者;时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则谎言只要被相信一小时就可以达到目的,……虚假飞逝之后,真理才蹒跚而来;当人们意识到骗局后,却一切为时太晚,成功已获,影响已扩。”[22]207
收稿日期:2008-03-09
注释:
①陈安德是第一位到达欧洲的华人。这位明朝宰相的特使与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一起取道果阿,于1652年12月抵达意大利圣马列克,详情参见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卜弥格——中国的史臣》一书的115页,张振辉翻译,2001年大象出版社出版。
②关于沈福宗到达欧洲的具体时间学者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1685年到达欧洲,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是1684年。孟德卫(David E.Mungello)在《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中认为是1683年10月抵达荷兰,见该书112页。
③本文中两个称呼交替使用不作区别。
④台湾版《福尔摩啥》依据《见闻》1705年第二版翻译而成,参见该书35页。本文涉及第二版的翻译均采用《福尔摩哈》。
⑤历史上曾经有一位Alexandre de Rhodes(1591-1660)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大约1624年在中国南部与越南之间传教,1652和1653年法国巴黎先后出版过他两部关于越南和中国的作品。
⑥参见Biblia Sacra Vulgata,quartam emendatam edition(New York:American Bible Society,1990)529页。《圣经》钦定版中拼写为Shalmaneser。
⑦西方没有三跪九叩之礼,故历来对东方的这一习俗无法适应,曾经酿成多次外交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