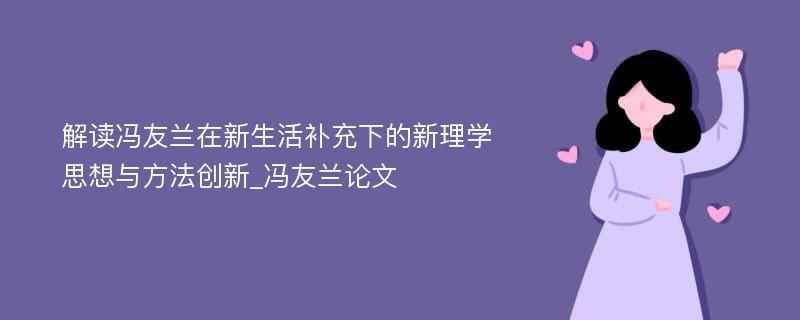
“阐旧邦以辅新命”——解读冯友兰新理学之思想方法创新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思想论文,方法论文,阐旧邦论文,辅新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6-0082-04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麟等哲学家们用现代化的思维和知识担负起中国哲学重建的重任,其中对哲学方法的高度重视和精深研究是他们的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冯友兰先生无论是作为哲学史家还是作为哲学家,无论是致力于阐旧邦还是辅新命,其对哲学方法论的讨论都贯穿于始终,并用其支撑和构建了他的“三史论古今,六书纪贞元”的中国哲学史以及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理学开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对方法的创新,实现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结合,古今中西的相会通,理学与心学、儒家与道家的相圆融,从方法上明晰了儒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如何得其真精神、真意思。
一
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说,冯友兰先生确实可以说“是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人”。新理学之所以是新理学,在冯友兰看来是因为他的理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冯先生认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哲学也需要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缺少逻辑学的洗礼,显得不够彻底,那么运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1]。这也就是说,新理学讨论的虽是中国传统哲学(理学)中的一些范畴,但采用的却是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是“求道”而非“求学”的,其根本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所以他说,求道所讲的是哲学,求道之哲学只能提高人的境界,不能使人有对实际事物的积极的知识,因而不可能使人有驾驭实际事物的才能,但是,这些哲学的观念却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以及道德的境界,而达到天地境界,从而“经虚涉旷”而“廓然大公”,也就是达到所谓“圣人”的境界。因而他认为“无用而大用”的哲学,就是一种使人成为圣人的学问。新理学是最玄虚的哲学,它所讲的,虽仍是内圣外王之道,但却要在人伦日用中觉解到宇宙规律的具体体现,看到万物与我一体,天地与我同生,从而竭尽自己之力,促进人生美满社会幸福与进步。从最不落实际、抛开了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式的、逻辑的观念开始,最终却结束在这非常具体、实际的结论中,这就是新理学的最重要特征。冯先生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曾一再表示,他的哲学研究,不仅在于叙述中国哲学的过去,更是为中国的现代哲学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曾一再地引诗言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从事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新的时代下,通过“接着讲”,来创造性地复兴民族传统哲学,实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这可以说是冯友兰先生哲学创造的精神追求所在。
二
新理学之新,新在方法,所谓“新瓶装旧酒”的“新瓶”指的就是新的方法。因为新理学采用了新的方法,所以新理学较之旧理学前进了一大步,新理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冯友兰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并使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的学者。冯友兰试图对中国传统哲学“接着讲”,他之所以严格地说明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其根本点就在于逻辑分析法的运用。冯友兰的新理学继承了程朱理学,把宇宙一分为二,一个是形而上的理世界,也叫做“真际”,一个是形而下的器世界,也叫做“实际”。生存在宇宙之间的人类,必然会以他们所固有的独特的灵性,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觉解”去探讨宇宙、人生的奥秘,这就形成了哲学,因此冯友兰认为“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2],形上学则是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哲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人对于人生底最后底觉解”。这种觉解,是人拥有最高的境界时所必需的。而如何达到对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觉解呢?也就是说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呢?这是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认为“人学形上学,未必即有天地境界;但人不学形上学,必不能有天地境界”[3]。
冯友兰对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接受了西方逻辑分析主义的方法论,对其推崇备至,在这个时期冯友兰认为中国传统哲学重直觉而轻逻辑,造成概念范畴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因此要想使中国哲学重新焕发生机,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向西方哲学虚心求教,学习西方哲学中发达的科学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法。但冯友兰在构建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他的观点又发生了转变,开始将直觉思维纳入其方法论中,认为哲学方法应包括两种,一是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法;一是负的方法,即直觉法。
在冯友兰的“接着讲”方法中,逻辑分析方法是其中主要的方法。反思他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了解他的“接着讲”方法,无疑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冯友兰非常重视逻辑分析方法,且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在他看来,逻辑分析方法进入中国以后,“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4]。冯友兰还将逻辑分析方法形象地比喻为近现代中国人向西方求得的思维“点金术”。似乎一旦掌握了逻辑分析方法,中国人就寻找到了国家独立富强和追求真理的捷径。“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4](380),将逻辑分析方法看做西方哲学对中国学术的“永久性贡献”,并明确将它提高到时代精神层面来认识,在近现代中国学人中,冯友兰是很突出的。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建构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就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
三
冯友兰所谓的正的方法,就是以理性思维对于形上学命题、范畴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是从正面阐释形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冯友兰又称之谓“逻辑分析的方法”或“形式主义的方法”。正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由肯定达于肯定的方法,是用名词、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而得出结论的方法,是可以思议、可以言说的一种方法。冯友兰吸收了蒙塔古式的逻辑分析和哲学看法,并有中国文化的发挥。用从蒙塔古那里继承过来的柏拉图式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稍加概括、发挥,并用来分析改造宋明理学及中国哲学,这就是冯友兰“接着讲”方法中逻辑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
在《新理学》的绪论中,冯友兰从方法论的角度给出了哲学的第一个定义:“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其中,“对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就是指这种方法,冯友兰的正的方法,是从新实在论那里引进的。冯友兰受他们的影响,提出“从形式逻辑里可以推演出哲学”。冯友兰正是通过这种形式逻辑,从概念出发,利用概念的含蕴关系,推演出“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即有物必有则”等一系列命题,然后又把逻辑的先在性这一认识论问题,赋予本体论意义,得出理先于事,真际先于实际的结论。冯先生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它是中国哲学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自墨学绝断后,中国哲学一直缺少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和重视,这是传统哲学的一大弱点,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哲学概念、命题的不明确,哲学思想的模糊性。冯友兰利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澄清了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名词,为后人弄清哲学命题的理论意义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冯先生借用逻辑分析来构建新理学体系,他对思想确定性的追求是中国哲学得以系统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冯友兰先生高度肯定了逻辑分析方法对于真正哲学的重要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得到了厘清,使之更加完备,更加明晰,从而使传统理学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当冯友兰进一步解释气、道体、大全这三个观念时,却发现用逻辑分析法是无从下手的。冯友兰认为这三个观念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是拟意即乖的,这就说明,思辨在哲学中的效用是有限的,单靠纯粹的思辨是不能完成建立形上学的任务的。在《新理学》中通过正的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得到了四组空灵的哲学命题和四个超验的形式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建构了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后来冯友兰发现,用正的方法所得到的四个观念中有三个,即气、道体和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气乃绝对的料,是没有规定性的绝对的无,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这三个观念的所指都超出了理智的范围、语言的范围,所以既不可思,又不可说。此外,新理学中的几个主要观念,能使人游心于物之初、有之全,从而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而同天境界作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同于大全的境界,大全不可思议,这样新理学便从思之说之,止于不思不说,于是不同于正的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的一种新方法——负的方法便应运而生。何谓负的方法?冯友兰先生说,形上学的正底方法,从讲形上学讲起,形上学的负底方法,从形上学不能讲讲起。所谓从不能讲讲起,就是讲形上学的对象之不可感觉,其实就是直觉主义的方法。
四
冯友兰把直觉主义的方法称之为负的方法,负的方法也是新理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负的方法就是由否定而达于肯定的方法。冯友兰说:“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这就是负的方法的精髓。”[5] 用“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讲形上学不能讲,并非不讲形上学,因为直觉主义讲底形上学,并不是讲者的直觉。形上学是一种学,学是讲出底义理,而直觉则不是讲出底义理,用直觉主义讲形上学者,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能讲,但讲其所不能讲亦是讲,此讲是形上学,不说它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中国哲学思维最大特点是虚实相生、有无相生,西方的话语系统用明确的概念、定义来认识、表达世界是什么,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则认为真实的世界是语言所不能穷尽的,语言所能表达的小于世界的意义,言有尽而意无穷,故讲望月而忘指,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解读中国哲学不仅要看到其呈现于世之实存的一面,更要关注到其背后虚而相一贯的特性,如果仅看到一面就认为中国哲学是不成体系、零散的智慧,而领悟不到其虚实相生的特性则无法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的中国画,在画月亮的时候,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大片云彩,在云彩中间留一块空白,人们一看就能看出是一个月亮,这种画法叫“烘云托月”。这种画法,可以说是画其所不画,画其所不画亦是画,哲学的负的方法类似这样的意义。冯友兰认为,讲形上学不能讲,即对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示,这也是一种讲。人类的言语,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一个字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死的概念,所以如果仅从言语中去了解他所说的对象,就很可能把对象也了解为静止不变的东西,仅只是许多性质堆积起来的东西。这就和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大不相同。……所以,从言语这个框子里去了解客观世界,那就像戴一副有色的眼镜去观察事物,很难得到事物的真象。他认为中国道家、禅宗都是以这种方法讲形上学的:道家为追求最高境界主张去知,去知而无知,但这种无知并不是原始的无知,而是经过知而后的无知;禅宗的超佛越祖之谈,即所谓的“第一义不可说”,如果说出来,就不是第一义了,但总要有办法表现出来,于是禅师们利用各种办法,行不言之教,以便使人们在顿悟中觉醒,可谓无声胜有声。冯友兰认为这都是负的方法,同时,冯友兰认为从方法的角度来看,禅宗认定对“第一义”“拟意即乖”,并非肯定第一义不可理解,第一义虽不可说,是超佛越祖之谈,但总须想办法表现之,不然则即等于没有第一义,或没有超佛越祖之谈。“因为所谓义或谈,总是一种义理”,义理总是可以使大家知道或了解的,“不言之教,亦是教”,既是教,总有使人可知道或了解其教的方法。对“第一义”这种佛法真理,不能凭借正常的逻辑语言描述,但可以采用默契或形象暗语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
负的方法以体悟的方式直接契合形上学的对象,它虽然超越理性或理智,但不反理性或理智。天地境界也是不可思的,中华文明与中国哲学是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的“中”就源于对天人合一精神的演绎。在中国哲学话语系统中的很多语境下,天人合一是默认而无须重申的前提,很多理论看似难于理解,正是因为淡忘了这一前提以致得不到觉解,正如袁枚《续诗品》中言:“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体悟的方式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肯定天人合一,天道在人之为德。天道人德是相贯通的,体悟就是体天道、明人德,而后达到天地境界,实现“游心太玄”、“与物冥通”、“与道同机”。
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方法,它们有着不同的范围、对象和目的,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正的方法是新理学开端的方法,负的方法是新理学完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虽相互区别,但同时也互相衔接、互相配合,诚如冯友兰所说: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冯友兰先生融通理学和心学的境界,认为如果认识到真正的哲学都是理智和直觉的结合,心学和理学的争论亦可以息矣。于此可见,冯友兰的理学立场是对于心学和理学的分歧的总结与超越,是以改善的方式重新肯定了新理学的思想。
标签:冯友兰论文; 哲学论文; 理学论文; 新理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新邦物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