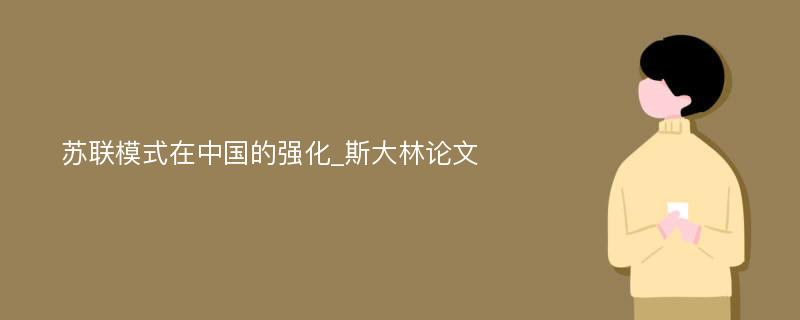
苏联模式在中国是如何被强化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在中论文,国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2)04-0078-(08)
在《俄罗斯研究》的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一边倒”,在浅层次上所表明的是一种外交政策,而在深层次上则意味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锁在苏联模式上,为此还专门阐述了苏联经济模式中国确立的过程(注: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载《俄罗斯研究》,创刊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又进一步论及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确立的基本前提条件(注:孔寒冰:《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前提和表现》,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9月号。)。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实表明,不论是在外交方面,还是社会发展模式方面,中苏两党、两国不仅都没有能够真正站在“一边”,相反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多,最终导致相互关系的完全破裂。本文先将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与矛盾抛开,重点放在苏联模式是如何在中国被强化的,进而揭示出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以及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暗淡的光环——苏联模式的弊端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外交体制。我认为:这种模式就是马克思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注:关于斯大林模式问题,可参见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正因如此,在完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主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在政治上排除了一切异己之后,1936年底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就标志着这种模式的最终形成。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苏联是世界共产党人的“圣地”,斯大林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五彩环绕,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仿效的楷模。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和亚洲的中国等,在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之后,都纷纷仿效苏联实行五年计划(个别国家是六年计划),按着苏联的样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初期都选择了政治、经济呈多元化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东欧各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注:参见[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78~110页;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406页。);而中国从一开始就主动地学习,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注:《新华月报》,1955年第3期。)。这样到了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在苏联本土已经存在了30年,在东欧也确立了起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少有些例外),在中国则正在确立之中(1953年才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可以在短期内高效地调动、指挥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实行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甚至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不过,短暂的辉煌外表并不能消除苏联模式在产生和推广过程中先天的内在不足,即这些国家都不具备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产生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很落后(注:这里还涉及到了长期争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我认为:落后国家由于特殊的各种原因先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任务,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差距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超越的,只能一点一点地弥补,赶上资本主义之后,才能谈得上超越。)。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其中政治上的最突出。
第一,在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大搞肃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苏联30年代后半期连续进行了三次大清洗,50年代初又先后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件”,蒙冤者无计其数。东欧国家在反对南斯拉夫的情报局事件发生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蒙难者和受牵连者都是党员干部。上述这些几乎百分之百是错案!(注:参见[苏]尼.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建国以后,中国于1951~1952年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已存在打击面过大的问题(注:参见《罗瑞卿同志的发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第283页;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7页。);1955年进行的肃反运动所造成的错案率则超过94%(注:参见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64。);而株连无数,沉冤长达24年之久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更是地地道道的错案(注:参见梅志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万同林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个人迷信盛行。苏联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开始于1929年,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导所受到的尊崇和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大同小异。比如,在匈牙利,拉科西被歌颂为“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到处都是以拉科西命名的工厂、街道和幼儿园。
第三,经济上也并非没有问题,苏东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些弊端:党政不分、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过急、过快地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结果,农民缺乏劳动生产积极性,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城市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注:参见周尚文等著:《新编苏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6、285-290、498-499页:[英]乔.肖夫林:《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实践》,载《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第195-223页。)。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尽管比起苏东国家来,步伐还算稳健,但今天看来也仍显过急过快(注: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230页;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至于高强度的计划管理,与苏东相比较也不分仲伯。
二、“末端”上的调整——毛泽东的探索
针对着苏联模式上述种种弊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在同程度上做出的反应。在苏联,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开始打破权力高度垄断并且实行党政分开,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别担任政府和党的一把手。不仅如此,马林科夫1953~1955年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实行了主要是调整斯大林时期经济政策的“新方针”(注:参见[俄]安.马林科夫著:《我的父亲马林科夫》,新华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06-119页。
),而赫鲁晓夫在纠正了斯大林时期破坏民主、践踏法治的错误的基础之上于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所有这些都被国内外学者视为苏联改革的发端(注:参见[苏]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126~134页;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200页。)。
东欧国家在斯大林去世后爆发了一系列事件,如1953年的民主德国的东柏林事件、匈牙利的切尔佩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事件,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反对苏共干涉内部事务的十月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等。尽管这些事件的具体起因、过程和后果并不相同,但都反应出东欧各国人民对苏联模式的反抗、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反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事件也被视为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始(注:参见徐午:《试评匈牙利1953~1955年的改革尝试》,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83页。)。
在中国,一方面,正处于“斯大林模式化”过程中的中国,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逐步显露出来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注:参见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5、123、151~154、165页。);另一方面,深受引起轩然大波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的触动,中国最高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在二十大以后对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也进行了思考(注:参见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56页: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以后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第3期:陈云:《社会主义改选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9月)》,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然而,对中国怎样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言行。
如何防止斯大林悲剧和东欧风波在中国重演,归根到底也就是中国应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1956年4月初,在谈到应从苏共二十大得到什么教益时,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注: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于是,1956年3~4月和11~12月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写作和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两篇文章,1956年4月到1957年5月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多篇讲话,都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文件。
从思考的结果上看,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和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东欧国家出现动荡除了有阶级斗争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由于共产党在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政策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7、324~325页。)。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开出的治病药方是“整风”,即“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却是维护苏联模式,因为在他心目中,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标本。何以见得?第一,毛泽东坚决反对铁托、陶里亚蒂等人将斯大林所犯错误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反对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迷信归因于官僚机构这种苏联模式的看法。他认为,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注: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关于铁托的观点,见铁托:《在普拉市向伊斯特拉地区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的讲话》,载《铁托选集(1952-1960)》,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119页;关于陶里亚蒂的观点,见《陶里亚蒂答“新主题”记者问》,载[意]贝尔纳多.瓦里主编:《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140~149页。);第二,毛泽东坚决维护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对于前者,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他要保护斯大林,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全面评价斯大林(注: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3页;《忆毛主席》,第26~29页。);对于后者,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和“共同规律”,认为“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注:引自《忆毛主席》,第19页。);第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其外延十分宽泛而内涵十分原则,实际上是以赞成不赞成苏联模式作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3页。)。第四,这期间有两个重要变化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一论》充分肯定了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且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再论》则不再强调反对个人迷信,相反认为这是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来“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注:见《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晏晓明:《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其实,毛泽东认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弊端根本原因的“三风”(也被称作“三害”),只是苏联模式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由于历史的和自身的局限,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苏联模式本身的问题所在。与这种面上的思考相适应,毛泽东提出的整风也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即便对于“标”也仅仅是量上的、暂时的调整,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政治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他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下来了的”(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这种旨在维护苏联模式的“末端”上的调整不仅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更严重的是还具有极大“变数”,非但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很快走向它的反面。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探索是为了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决心打破苏联的框框,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注:许全兴著:《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事实表明,毛泽东是想避免中国走苏联、东欧国家的弯路,但并没有想打破苏联模式,否则的话,在以后的20多年中就不会率领中国党开展反对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了。
三、“根本”上的触动——知识分子的探索
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本很值得读但又没有真正写出来的书。或许正是因为具有超出其职业范围的自由批评精神、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和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些基本特点(注:余英时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他们大都经历过本不该经历的悲剧人生。
1956~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和探索的热情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激发出来的。决定进行主要是批评党员领导干部缺点错误的整风之后,毛泽东特别向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注: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批示》。)。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知识分子建国后因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受到整治、冲击而产生的消极、怨恨情绪,“缓和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注:《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进行一次火力侦察,因为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这不能不引起本来对知识分子不十分信任的毛泽东的戒备心理。
面对着礼贤下士的毛泽东和诚恳相邀的中共,素有“士为知己者死”品质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冬眠”,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整风运动(注:参见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傅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160页;鲁丹著:《70个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及各高校党委主持召开的各种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敞开心扉,真诚地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出现了热火朝天的“鸣放”或“大鸣大放”的局面。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除了对“三害”的种种表现进行批评之外(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因长期受压、受排挤或受忽视而产生的忿忿不平情绪),更主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
综合起来看,知识分子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
政治上,许多人提出个人迷信和“三害”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这突出表现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具体说,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订的“设计院”(注:参见张锡锟:《三害根源》、群学:《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林希翎:《我的思考》、张景中:《在1957年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以上文章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张百生、黄振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章伯钧:《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黄绍闳:《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376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构成1957年鸣放的主要内容,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注:参见《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华主编:《荆刺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或暴露出来、或显露出来的苏联模式的弊端。
经济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人也很多,这里提几个非常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著名思想家顾准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命题(注: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这篇文章对于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不是一个挑战,顾准因此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他的思想对孙冶方等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影响(注: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载《顾准文集》,第62页。)。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低效率,当时民建中央副主委章乃器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应当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的私营企业,其原因就在于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注:章乃器:《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载《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98页。)。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经过细致后研究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不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则被忽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必定是速而不达。在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而且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经验,要善于全方位地学习(注:《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第178~179页。)。
知识分子探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直接反对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用这样一段引文表明了相同的观点:“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注: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44页:谭天荣,《第二株毒草》,载《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33页。);民盟上海副主委彭文应认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人民大学的学生更是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决不可着苏联的脸色行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注:引自《反右派始末》第431页;《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第182页。);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民盟中央常委曾昭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等人对高等教育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注:参见傅鹰:《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57-463页;曾昭伦:《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第182页;另参见江沛、王洪学:《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除以之外,还有许多人,对中苏两国交往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谴责。沈以光指出,“中苏关系不平等,中国实际上处在殖民地地位。苏联专家渗透到我国防大学各个部门,对我国的机密了如指掌(幸亏中苏友好,否则不堪设想)。总之,苏联把我国抓得太紧了。反对学习苏联一面倒。一切都学习苏联,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中国好象殖民地。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在中国建立‘东方的南斯拉夫’。集中中西之大成,搞个综合式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注:沈以光:《让青年去独立思考》,载《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98页;另参见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384页;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上述这些绝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观点,而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真心报国的品质的反映。也许有的批评言辞过于激烈,也许有的观点过于尖锐,也许有的思考还不深入,也许有的论证还不充分,也许探索者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苏联模式本身的根本缺陷,他们的主张是要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强化——两种探索的冲突及其结局
对此如何评价暂且放在一边,但是,将毛泽东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的探索并列地放到一起,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冲突,继而也就不难看出1957年反右派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探索碰撞的结果,即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改变的苏联模式恰恰是毛泽东竭力维护的。更有甚者,有的批评还指向毛泽东本人,除了储安平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外,1957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还转载了《陕西日报》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类似的文章和语言还有不少。斯大林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党及其最高领袖只能恭维、歌颂,而绝不能批评、不敬。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不仅领袖本人接受不了,就是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党员群众也接受不了。当然,对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来说,最不能容忍的还是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挑战。于是,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并亲自部署了“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的“阳谋”;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4日、16日和20日接连下发了3个文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社论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
这场冲突的表面结局是有55万多人被划为与“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相并列的“右派”(注: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正式或变相“改正”了,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错案,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都有过不堪回首的“右派”经历。);可实际结局远远比这可怕,即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都中断了。一位公安局长在对劳动改造的右派训话时所讲的话可做一个反证:“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全国高高飘扬。”(注:刘衡:《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载《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74-175页。)
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中断直接后果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反向地总结,将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最大化。政治上,由于认为反对个人迷信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到1957年开始转变为对个人迷信的推崇。同时,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两方面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
经济上,由于认为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初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党又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相反搞得比它更加集中和僵化(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新华月报》,1984年第10期。)。
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中断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纷纷缴械投降和随之而来的“既可杀又可辱”境遇。那一篇篇检讨书、认错书和形形色色的思想汇报映射出的是真理在谬误面前的无奈和屈服。虽然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像顾准这样“点燃自己照破黑暗”并“在地狱里思考”的人,虽然也不乏有像林昭、张志新这样“舍身求法”的人(注:参见刘发清:《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乐黛云:《透过飞逝了烟尘——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载(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60-468、197-201页。),可随着成为“臭老九”后地位的沉沦,知识分子的“悟性”也逐渐消退,而被鲁迅尖刻批判过的“奴性”日益上升。“为民请命”者少,而对领导人的言语进行恭维、歌颂和“煎、炒、烹、炸”者多,一本小书经“学者”们妙手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大全”或“百科”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呢?
顾准的女儿说,1957年以后,顾准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注:顾淑林:《迟到的理解》,载《顾准日记》,第422页。)。其实,整个知识分子,整个中国人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各方面的逆转综合起来,中国在1957年以后的20年间实际是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当许多国家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大好时机快速地发展自己,实行“无产者有产化”、“劳动者知识化”,中国却在自残、自误,实行“全民贫困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如果按汉语词典那样将社会骚动不安解释为动乱,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不过是前十年“动乱”合乎逻辑地延续。
苏联模式就这样在中国被强化了。正因为这种强化,中国才经历了20多年的极其曲折的发展阶段。这段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它,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过去,还有助于认识它们的今天和预测它们的明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同样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再思考和再探索的过程,但是,它不再是“末端”上的调整,而是一场改变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深刻革命。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化,中苏两党发生的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并且成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的原因之一。在研究中苏关系时,注意各自的民族心理和国家利益固然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情结,否则中苏关系中的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的。
标签:斯大林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右派分子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毛泽东论文; 顾准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