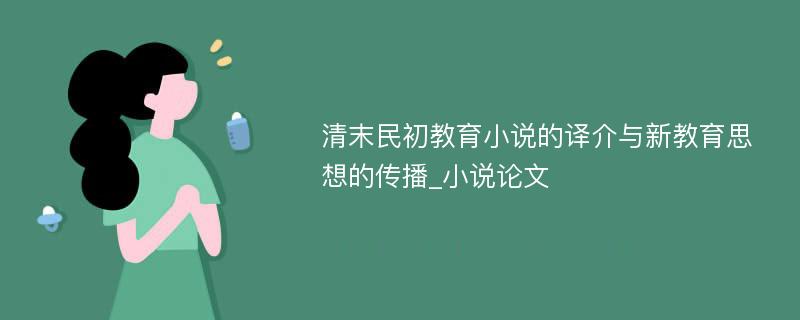
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与新教育思想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思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3-0208-08
教育小说源于德语“bildungsroman”一词。在西方,教育小说一般以年轻主人公的道德、心理和智慧发展为主题,叙述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具有某种教益和惩戒性质。教育小说随着地域、时期的不同,对于叙述主题“少年成长”或“学校教育”各有偏重,因此又常与“educational novel”、“apprenticeship novel”或“initiation novel”等名词交互通用。中国自古有“诗化教育”和“故事化教育”的传统,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小说”主要是受西方的启示。教育小说这一语词在清末传入中国后,一直没有被严格界定。人们往往把阅读对象主要针对儿童、学生,题材方面主要反映儿童成长和学校教育的小说都冠之以教育小说。清末民初,大量外国教育小说经译介进入国人视野,这些小说的译介,同时承载了倡导新小说和传播新教育思想两种使命。它们在为国人提供外国读物的同时,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把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导入了中国,并在中国传播。
一、教育小说的译介
1.背景
外国教育小说在清末民初进入中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概括地说其译介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动力:
首先,教育小说的译介肇始于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人极力推崇和引介西学,并将小说置放在配合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位置加以倡导和呼吁。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而译介西方小说可以补旧小说之弊,并起到“开启民智”、“保国保种”、“救国图强”的作用。在他们的积极倡言下,这些主张引起文坛与思想界的极大共鸣。一批具有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学者,将目光投向西方,开始译介西方小说。林纾(1852~1924)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其所译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1899年一经刊行即引起轰动,一时之间文人学士争说“茶花女”。受此刺激,林纾又译介了一系列域外小说。林译小说以其脍炙人口的古文笔法,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独具魅力与品格的翻译小说范例,并以事实印证了时贤对西方小说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20世纪初,西方小说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译介外国小说之风盛极一时。教育小说即是此时乘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化舶来品。晚清翻译文学中,教育小说是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同时萌发和勃兴的小说门类,都是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新小说类型,为时人开启了迥异的阅读视界。
其次,外国教育小说的译介还受新教育发展的召唤。20世纪初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两部学堂章程的颁布,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全国出现了兴学热潮,新式学堂大量涌现。汲取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革中国教育,成为大势所趋。外国教育小说的译介,正好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新式学堂需要与儿童生活相近的新式读物。当时就有人指出:“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②这里虽然没有出现教育小说一词,但显然是指向教育小说并倡导教育小说的“著译”的。教师、学生是教育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随着新学堂的兴办,这个群体日益庞大。对“教育小说”的需求,成为推动一批文人学者投身译介工作的主要动力。
再者,近代报刊、书局的出现和繁荣与小说界革命、新教育的兴起之间存在着互生互动的关系。尤其是近代报刊,与近代小说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是近代小说的主要载体。近代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首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由书局出版单行本的。以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作品为例,他的16部中长篇和全部短篇小说,除《恨海》一部是先出版单行本外,其他均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的。在当时,各报刊为吸引读者、增大销量,争相刊载小说,其中译介小说占了很大比例,教育小说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门类。如《小说林》、《绣像小说》都明确地把教育小说作为征稿的主要内容之一。对翻译教育小说特别青睐的是那些主要针对教育界的专业期刊,如《教育世界》在办刊的几年中,一直积极译介外国教育小说。《教育杂志》从办刊之初就以较高稿酬向包天笑约稿,请他“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译者受此委托后,“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于西方文化界了”③,便选译了《馨儿就学记》,以译充著,满足了商务的条件。随后《教育杂志》登载了一系列外国教育小说。
随着报刊书局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晚清稿费制度开始建立,小说稿酬不菲。包天笑初期翻译的《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两部小说共计四、五万字,得了一百元版权费,按他自己的话说“可以代几个月的家用”④。1907年《小说林》刊登的一则“募集小说”的启事中称:“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⑤小说作品成了一种文化商品,教育小说是其中一个门类,必然会成为驱使一些译者的动力。正是在各方面积极倡导及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教育小说”的译介在晚清出现并在清末民初文坛上盛极一时。
2.译介概况
包天笑(1876~1973)是清末民初外国小说翻译的健将,除了林纾,译作数量无有能出其右者。而教育小说的译介则代表着包天笑翻译外国小说的最大成就。包天笑通过各书局及《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外国教育小说。1903年,他从日文译介了两本适于儿童阅读的小说,即《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铁世界》是一部浅显的科学小说,《三千里寻亲记》实为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e.Amicis)的著作《爱的教育》(Cuore)中之一小节。1909年包天笑首次据日译本把《爱的教育》较完整地译出,改题为《馨儿就学记》。译本先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上连载,除第2期缺一回外,从第1卷第1期连载至第13期(1909~1910),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小说写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一年间的见闻,其中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尤其是师生间和同学间感情的叙述非常动人。1920年夏丏尊得到原作的日文译本,1924年在参照英文译本的基础上,才把这部小说完整译出,并首次使用《爱的教育》这一译名。小说先在《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号至第23号上连载,1926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
继《馨儿就学记》后,1910年至1918年包天笑又在《教育杂志》上陆续译载了《孤雏感遇记》、《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二青年》等教育小说。《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的原作者是法国作家艾克多·马洛(Hector Malot),包天笑是据日译本转译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叙述了主人公可民到处流浪,历经坎坷,最后终于找到幸福的故事。由于该书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及其影响,在包译本初版十几年以后,不断有人将此书重译,如徐蔚南译的《孤零少年》(1932,世界书局)、林雪清、章衣萍合译的《苦儿努力记》(1933,儿童书局)、何君莲的《苦儿流浪记》(1936,启明书局)及《无家儿》(1938,商务印书馆)等等。这些译本都译自法文原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章合译本,受到许多教育界学者如蔡元培、陈鹤琴、陶行知的推崇。《埋石弃石记》则是一部译自日本人写的教育小说,据包天笑回忆,作者“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⑥其中有很多教育理论,是日本人对于教育的看法。1913年1月至12月,包天笑还在《中华教育界》译刊了长篇小说《儿童历》,1914年又与张毅汉合译了《蔷薇花》、《留声机》等作品。《中华教育界》上刊载的还有严畹滋翻译的教育小说《劳》(1914)、《英儿汤姆》(1915)等等。
包天笑的教育小说译作主要刊载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上,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则是另一个比较注重引进外国教育小说的刊物。在其所设“小说”栏目中,登载的大多为译自外国的教育小说。1903年,该刊发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骚(J.J.Rousseau,卢梭)写的《爱美耳钞》(Mile:ou De Education,《爱弥儿:论教育》)。小说描写一个贵族儿童经过良好的教育终于成长为一个理想新人,一个反对封建特权和压迫的坚强战士的故事。全书渗透着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1923年魏肇基根据英文节译本译成《爱弥儿》,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瑞士著名教育家贝斯达禄奇(J.H.Pestalozzi,裴斯泰洛齐)的《醉人妻》(Lienhard and Gertrud,《林哈德和葛笃德》)在该刊乙巳年第5期至第24期(1905~1906)陆续载完。小说通过讲述廖讷德和额特德(林哈德与葛笃德)夫妇及其子女的生活故事,体现了裴斯泰洛奇的教育应遵循自然及企图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1935年,傅任敢重译为《贤伉俪》在《教育杂志》上连载,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教育世界》在1904年至1906年间,还译载了《姊妹花》、《村学究》、《制造书籍术》、《迷津筏》等外国教育小说,及阿褒利武斯所著的心理伦理小说《爱与心》,奥国萨尔曼的两部教育寓言小说《吾家千里驹》和《造恶秘诀》。
除了《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和《中华教育杂志》,其他一些教育专业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教育小说译作,如《学生杂志》上有《五伟人》(1914~1915)、《少年旅行谭》(1915)、《拉哥比在校记》(1916);《湖南教育杂志》上有《佛兰可》(1914)、《青年镜》(1915)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在一些非“教育”类的刊物上,也常常刊有译介的外国教育小说。例如《月月小说》的《含冤花》(1907~1908),《小说林》的《好男儿》(1908),《环球》的《弃儿记》(1916),《小说月报》的《青年镜》(1917),《竟业旬报》的《青年美谭》(1909)、《学问贼》(1908),《小说大观》的《塾师》(1916)、《柳原学校》(1916),《小说时报》的《孝子碧血记》(1911)等等。另外如法国作家都德所著的《最后一课》被不同译者翻译,先后刊载在《湖南教育杂志》(1913)、《留美学生季报》(1915)、《礼拜六》(1915)、《中华小说界》(1915)、《工读杂志》(1917)、《南开思潮》(1917)等刊物上,篇名除了《最后一课》,还使用过《割地》、《小子志之》、《末次之课程》、《最后之授课》等等。
书局出版的外国教育小说还有《苦学生》(作新社,1903)、《冶工轶事》(文明书局,1903年)、《青年镜》(广智书局,1905)、《儿童教育鉴》(文明书局,1906)、《女学生旅行》(上海时报馆,1907)等等。除了书局杂志,晚清报纸大量涌现,许多综合性报纸也设有“文艺副刊”专栏,其中也刊载有部分翻译的教育小说,如上海《大共和日报》在1912年11月5日刊登了由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都德著),译名为《割地》。
据笔者粗略统计,五四之前,通过各书局杂志以“教育小说”名义刊布的译介小说约五十余部。它们以上海为地域中心,以教育类期刊为主要载体,广泛分布于各地大小报刊及书局。随着这些报刊、书籍的刊行和出版,教育小说在社会各类群体间流转、传播。
3.译介特点
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首先,从译介途径来看,虽然所译介的教育小说以欧美小说为主,但多数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有的作品甚至直接由日本人翻译,如《教育世界》上刊载的《爱美耳钞》,是由日人中岛端根据日译本翻译成中文的。更有甚者,许多教育小说译作上没有署原著者名,只有日文译者名。以日本为媒介译介西方教育小说,这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日本为中转站,学习、介绍西方文化的现象是一致的。之所以会产生“途经日本”这一特点,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对于教育小说的翻译来说,主要是因为日译本相对“易得”且“易译”。当时的翻译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式文人,他们外文水平有限,甚至完全不懂外语。他们要么与外语好但缺乏中文根基的人一起合作,要么从汉字较多的日文书籍中转译。当时在教育小说译介上有突出贡献的包天笑就是一位典型。他自学日文,但程度并不高,只有短期访日的经历。他的第一部翻译小说《迦因小传》即是与学英文的朋友杨紫驎合译的。因当时译出的外国小说少,该书还颇有人读。受此刺激,包天笑开始寻找外国小说翻译。他说:“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而此时,一方面留日学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于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⑦这一切使得国人寻找日译本小说变得容易。既然日译本易得又易译,取道日本、翻译西方教育小说成为当时不少译者的首选。包天笑先是托人在日本的旧书店寻找能翻译的小说,后来自己到上海的日本书店找。他翻译的《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就是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店淘来送给他的。包天笑要求朋友们为他搜寻小说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⑧其次,从翻译风格上来说,小说翻译在当时通行的做法是进行“意译”。译者在翻译时经常如钱钟书所说的“明知故犯”地“删节原作”、“增补原作”,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⑨教育小说的翻译同时还受日本译风的影响。包天笑说:“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指《馨儿就学记》)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小说中“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⑩经过这么大的变动,又译又创,似乎说成译作或创作都有失真实。包天笑自己也经常混淆,他既说这书是从日本转译而来,又说自己如何“写”出此书。此书发行时,封面并无原作者或日译者署名,赫然印着“天笑生著”,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署名曼陀译著的《女学生旅行》,在书前《例言》里交代:“是书以日本五峰仙史所著之《女学生旅行》为蓝本,更杂译东京各新闻杂志及《女学生气质滑稽》、《学生生活》等书,复杂以平日之闻见杂糅而成”,故题之曰“译著”。这类译作中作者的发挥很多,以至于研读当时许多作品很难分辨是译作还是创作,也有很多译作很难找到原作的作者与书名,但总的说来,翻译的内容占大多数。再者,教育小说译介过程中,因译者的兼译兼作,经常把传统观念与新思想相结合,使译本表现出中西、新旧价值观念折中、糅合的现象。如《造恶秘诀》的“编者识”说明了该小说的译介过程:由于“彼我风俗各殊”,如将书中所写“按之于吾国家庭,多有不合”,于是,便由编者据原著“采取其意义,易其面貌”,不但“凡与我风俗相戾者,悉更易之”;而且还“益以编者所闻见,务欲其尽态极妍”,以便使读者阅后掩卷反思,“此真吾国之家庭也”。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不仅改换相异之风俗,在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也经常流露出挥之不去的传统思想影响。《馨儿就学记》与原著表现之“爱”不同,包天笑译作中的“爱”蕴涵着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通篇充溢着孝亲敬老、忧国忧民、知恩图报等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儿童修身之感情》中则把三千里寻母评价为是孩子对母亲的“至孝格天”,使人们在“中外无别”的意识中感受这种母爱。这些译者在译作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和某些教育观念赞赏、认同的同时,受社会背景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通过“删改”、“添加”等方式,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依附、杂糅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中,显现出过渡时期特有的文化品格。
此外,当时选择教育小说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于改革社会风气与教育能有所裨益,因此译者对这些作品在艺术方面的价值和技巧并未给予特别关照,翻译过程中,在选材、语言表达、翻译手法上,也主要是按照成年人的意志与价值尺度、按照国情来增删、改写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要阅读群体之一的儿童的个性需求及语言特征。因此,这种以“载道”为目的的翻译无疑削弱了异国作品的民族情调、独特风格及原文独具的语言特色和思想理念。
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受制于时代特点,显然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经常因此遭受后人的非议,但钱钟书、陈平原等肯定了此类翻译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作的贡献。当时这类小说翻译家,大多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汉语水平高、语言纯熟、译笔轻秀。他们以浅近文言译出,符合时人的语言风尚、欣赏习惯和语言基础。对于教育小说的翻译来说,译者把新教育思想夹杂在旧道德中进行传播的译著方式也基本符合转型时期的时代气氛和读者的接受心理,因此这些教育小说译作颇为时人所接受。
当然还有一类译作是较为忠实于原著的,如《最后一课》、《苦儿流浪记》、《爱美耳钞》、《醉人妻》等。到五四前后,随着译者外文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翻译风格逐渐转变,一般都直接根据原著进行忠实翻译。这与当时文学界整个翻译风格的转向是一致的。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取得了成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教育思想的导入与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教育小说译作中的新教育思想及其传播
1.教育小说译作中蕴含的新教育思想
教育小说是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繁荣表达了启蒙时期对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培养“完整的人”的追求及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特殊关注。清末民初,外国教育小说也是因“教育启蒙”、“小说启蒙”的召唤来到中国的。教育小说的译介除了对“小说界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教育小说”成为一个新的小说门类在中国兴起并发展外,其主要功绩在于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传播了新的教育思想。
教育救国是清末民初盛行的一大社会思潮,许多编译者企图借助翻译外国教育小说的形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启蒙,宣传其“教育救国”思想。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刊登的《醉人妻》是裴斯泰洛齐的作品。裴氏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认定社会及政治的改革,无不赖于教育。《醉人妻序》中强调:“全篇宗旨,首在改良社会。借一村落为世界之缩影。而谓改良之道必由家庭以推及学校”,即通过“施教于家”,让社会之细胞的家庭“开明”起来,最终达成改良社会的目的。编者借这篇译作表达了教育是改良社会之根本的思想。该刊登载的另一部教育小说《造恶秘诀》,在“编者识”中指出,此书原名《恶德养成法》,又名《蟹之横行》,作者是取西方寓言中“老蟹不能直行,小蟹遂至横行一世”之意来命名其书的,意在说明“家庭教育之不良,过由父母”。编者借小说希望使“纯洁高尚”的道德教育理想,通过“家庭教育”而推及整个社会。此外,在教育小说的译介过程中,译者还经常通过穿插对社会时局的议论抒发忧国忧民之情怀,呼吁青年认真求学以拯救强敌环视、危机四伏、千疮百孔的中国。如《馨儿就学记》中就借杨先生口说:“我愿诸君敦品励行,咸潜心于学业,他日学成,为世所用,足以起我衰敝之祖国,藉与列强竞争,勿使他姓男子,来躏吾土,是岂诸君与鄙人之幸,抑亦吾国前途,均蒙其福也。”(11)都德的《最后一课》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歌颂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小说中的背景、人物处境与当时中国社会相似,更是激发时人爱国、救国情感的佳作。
外国教育小说中,有一部分是讲述儿童历经苦难成长的故事。它们往往鼓励儿童个人奋斗,为达目的、不危艰难,进行的是一种少年励志教育。这些小说情节曲折感人,很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儿童修身之感情》里的意大利瑞那儿童,年方十三,却冒着艰危,去三千里外的北美洲寻找母亲。《苦儿流浪记》中的弃儿可民,小小年纪一直流离失所,历经被卖、跟着卖艺老人流浪、与花匠一起生活、再度流浪等艰辛的生活遭遇,最后找到了亲生母亲,找到了幸福。这些故事,通过主人公历尽坎坷艰辛,逐渐变得坚强、勇敢、乐观,最后终于苦尽甘来的经历,塑造了一个个努力奋斗、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少年形象。它们不仅成为鼓舞、振奋青少年成长的理想楷模,也与时人激励青少年发愤图强、变革“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理想相吻合。
在大量教育小说译作中,现代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馨儿就学记》是对“爱”的教育的礼赞。小说以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表现了师生、邻里、父母家人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等等。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爱”使全文洋溢着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温馨的人性之美。感人的师生之情,是小说描绘的重点之一。小说以原作中的教师为原型,向读者重新“塑造”了一系列献身于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牺牲精神的教师形象。如终日以发达儿童心性、增益儿童学问为己任的杨震亚;在病榻上弥留之际还“念学生不置”,叮咛学生“勤勉读书,勿以为念”的曾静宜。《埋石弃石记》塑造了同样具有“爱心”的教师模范沈宝栓,因与学生相处亲切、负责,学生对他都甚“感服”。小说还进一步从教育之责任和使命的角度来强调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小说把教师比作“建筑屋宇时埋入土中之基石”、“筑堤时投入水中之弃石”,(12)希望教师“能以弃石埋石为心”,强大国家之基础。
《爱弥儿》的译介,为中国教育界送来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史上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向把儿童成人化、非人化的封建专制教育挑战,为保护儿童的天性和权利大声疾呼。小说篇首就指出:“凡万物之初出于造物主之手也,无一不善良者。而一入人手,则败坏无余矣。”(13)卢梭主张将爱弥儿带到乡村去,远离腐朽社会的恶劣环境,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和侵蚀,到大自然的怀抱中,用自然赋予的感官获得知识,求得教育。裴斯泰洛齐的《醉人妻》受卢梭影响,强调必须要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教育,以发展人的本性。并指出新教育的根本原则在于发展人的内在力量,使人与大自然相结合,使人具有向善的心性和较好的才能,成为一个于社会有价值的善良公民。
可以说,这些教育小说译作中,既包含了译者对时代思潮的投射,也反映了时人对新教育观念的理解及对理想教育的向往。教育小说的译介为国人开启了“新教育”和“少年成长”的想象空间,在清末民初,对于传播新教育思想、发展学校教育、转变时人教育观念及启发儿童之智慧、德性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传播与影响
教育小说的译著在20世纪初很受欢迎,且不说它们随报刊的发行而四处传播,其流布之广、影响之大从单行本销量上即可窥见一斑。以《馨儿就学记》为例,自1910年出版后销路一直很好,至1931年已印行10次,1935年出“国难后一版”,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仍在重印,标明“国难后第四版”。另外除商务版外还有各地盗版翻印的,总销量高达数十万册。(14)译自《爱的教育》中的《三千里寻亲记》于1903年出版后,1905年即易名为《儿童修身之感情》再次出版,1917年重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1926年3月出版后10个月即重印,两年半之内重印了5次,至1935年11月已印行达20次。1930年夏丏尊又译出意大利作家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由开明书店出版,重版速度不亚于前者,一年不到就印了3次。夏译本出版后,逐渐代替了包译本传播“爱的教育”之使命,但出于各种需要,包译本一直在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在重印包译本。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爱的教育》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包天笑译本不仅在当时很受欢迎、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其影响持续不衰。其他教育小说销量也不错,重印时间间隔极短。如《孤雏感遇记》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后,次年重印。《苦儿流浪记》编入“说部丛书”,19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同年10月就重印。到20世纪30年代其他译者再译之前,包天笑译本一直是这部小说在中国的经典译作。《苦儿流浪记》与《馨儿就学记》还被当代学者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5)
教育小说的译作在各界广泛传播,在教育界的反应最为热烈。外国教育小说的译介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视。如包天笑译介的《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和《馨儿就学记》,在民初受到教育部嘉奖。徐传霖、陆基译的《儿童教育鉴》,1906年被清学部列于《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之中,成为各地阅报处、宣讲所等通俗教育机构学习、演讲的重要内容。1916年,一份“(北京)外左三区地方公立第一通俗教育讲演所”的视察报告中仍显示,《儿童教育鉴》是其讲演资料之一。鉴于此书在民众教育中的特殊贡献,民国教育部通俗教育会对其进行了褒奖。同样受此殊荣的还有包天笑翻译的《儿童修身之感情》。教育小说译作在教育基层广为传播,有的小说内容被选进教材,如《馨儿就学记》中的“扫墓”一节,被当时商务版高小国文教材以《扫墓》为题长期选用,以致许多当年读过这篇课文的人都能背诵。有的小说则直接成为教科书,如1907年苏州商会档案收存的一份“文明书局教科书清单”里就有《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冶工轶事》等。(16)也有教育小说被作为奖品以示对学生的奖励,据包天笑回忆:“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指《馨儿就学记》)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17)《苦儿流浪记》出版后曾经盛极一时,不少学校把它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1925年还被明星电影公司改拍成电影《小朋友》上映,在当时青少年儿童中影响很大。教育小说译著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梁启超等人欲以“小说”来启蒙大众,“教育”童蒙的理想。
这些小说负载的教育思想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可从时人某些言论中得到印证。如《爱美耳钞》是卢梭宣传其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它对于打破传统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漠视和禁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魏肇基在1923年重译《爱弥儿》时说:书中“‘返归自然’底一大狮子吼,不但使十八世纪欧洲面目为之一变;而在二十世纪底我国,尤有深长的意味。对于虚伪、怠惰、束缚、蔑视儿童底我国教育界,无异投下一颗爆弹”。(18)五四前后,受时代思潮激荡,中国作家积极讴歌童心的真、善、美,以此抨击世俗;中国的教育界关注中国的儿童问题,推崇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些新教育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爱弥儿》的译介与传播是一个重要途径。夏丏尊在译《爱的教育》时曾说这本书比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醉人妻》给他的感动更深,他流着泪三天三夜读完此书。(19)足见这些小说在他心灵激起的震撼与感动。巴金在晚年谈到其外孙女的教育问题时,联想到年轻时读的《爱的教育》,最初读的是包天笑翻译的《馨儿就学记》,后来是夏丏尊译本。他说“书中叙述师生间的感情和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动人”,并认为“办儿童教育,首先就应当在学校中培养尊师爱生、同学互助的感情”,“不尊重老师,就办不好学校”。(20)都德的《最后一课》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两个月后,即有人赋诗发表读后感:“柏林书到意苍茫,汉麦先生辍讲章……稚子亦知亡国恨,春风和泪看胡桃。”(21)全诗写得沉痛、激愤,说明作品在当时引起读者深切的共鸣。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这些小说对时人思想、情感产生的激荡,对读者心灵影响的持久深远。
20世纪初教育小说的译介以“集大成”的形式体现了“教育”与“小说”、传统思想与新教育理念等问题的碰撞、交汇与融合。清末民初,既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步期,也是传统教育的退场期。译者采用译著参半等方式,选取适合国人接受的题材与观念,通过教育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把西方教育思想以更易为读者接受的方式植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机体,这对处于新旧交替“过渡”时期的中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教育小说以青少年奋斗成长及学校教育生活为主题的叙事特色,反映了当时憧憬“少年中国”、兴办新教育,强调教育启蒙和小说启蒙的社会需求。它们不仅为青少年的学习成长,提供了具体的学习榜样,还为新教育的兴办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理想模式,在教育儿童、开启民智、传播新教育思想等方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价值不容小觑。因此,这一课题值得我们研究、关注。
注释:
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卷第1期。
②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第10期。
③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85页。
④包天笑:《译小说的开始》,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174页。
⑤《募集小说》,《小说林》1907第1期。
⑥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⑦包天笑:《译小说的开始》,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173页。
⑧包天笑:《译小说的开始》,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173页。
⑨钱钟书等:《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32页。
⑩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86页。
(11)包天笑:《馨儿就学记》,《教育杂志》1909年第1期。
(12)包天笑:《埋石弃石记》,《教育杂志》1911年第1期。
(13)约翰若克·卢骚著:《爱美耳钞》,载《教育丛书(3)》,山口小太郎、岛崎恒五郎译,中岛端重译,上海:教育世界社,1904年,第1页。
(14)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88页。
(15)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16)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31-734页。
(17)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87-388页。
(18)魏肇基:《序》,载《爱弥儿》,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19)夏丏尊:《译者序言》,《爱的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20)巴金:《三说端端》,载《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
(21)健铁:《〈最后一课〉题辞》,《湖南教育杂志》1913年第2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