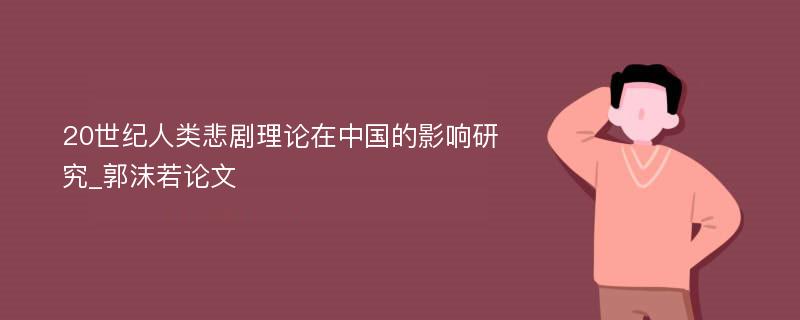
马恩悲剧理论在20世纪中国接受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悲剧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8)06-0632-05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马恩悲剧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并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熟,成为20世纪中国接受的各种悲剧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主流,对20世纪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现有资料显示,马恩悲剧理论正式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930年代中期①,但它真正发生见诸文本的影响则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熟期——1940年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是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和蔡仪的论著《新美学》。这可以说是它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第二次大发展则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标志性的事件便是那场关于悲剧的大讨论。如果说经过第一次大发展,中国对马恩悲剧理论的接受在误读中建构完成,那么第二次的大讨论则是一种理性论辩、重读中的解构与扬弃,其结果不仅是马恩悲剧理论在中国的解放,更在文艺观念多元化的语境中带来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蓬勃发展,并最终将马恩悲剧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推向第三次高潮,以一种开放的眼光进行着新的建构。
1.首先来看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以一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方式在中国普及了马恩的悲剧理论,尽管这未必是郭沫若当时的创作追求。
进入1940年代,诗人出身的郭沫若转向了历史悲剧创作。一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时代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是一幕伟大的悲剧;二是因为他认为悲剧能“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1]257从这两点认识已多少可以见出郭沫若对悲剧的现实化理解,他也正是在这种现实化的诉求中接受并化用了马恩的悲剧理论。
郭沫若的几大历史悲剧,无论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的《棠棣之花》;还是要“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不屈不挠,为真理斗到尽头”的《屈原》;或是以“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为主旨的《虎符》,都在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之中,谱写着一曲曲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要求的进步的仁义思想与违背历史规律的专制的暴虐统治斗争的战歌,而且所构筑的悲剧冲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揭示的悲剧主题等,无不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国共合作、抗日等时势问题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或神似。这是郭沫若以革命为纽带将历史与现实同构的创作意图所在。
早在20年代,郭沫若就曾宣称革命是悲剧的诞生地,[2]38-39经过40年代创作的锤炼和思想的发展,郭沫若对悲剧作了明确的理论总结,“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的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的诞生。”[1]257这一归纳本质上与恩格斯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的命题内涵并无二致,方生的力量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发展之初它还比较弱小,而将死的力量尚还强大,所以使得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暂时不得实现,形成悲剧。如果说有不同,主要是郭沫若在创作中作了一种更为简明化的处理,在历史的语境中对新旧力量(即冲突双方)的斗争作了鲜明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情感判断,借此来肯定和推许方生力量,以张扬民族正气、国家正气,为现实的抗战鼓呼。
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郭沫若洋溢着理想和激情的乐观的历史英雄悲剧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这使它不仅大受欢迎,发挥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果说充沛的情感力量和独特的艺术成就是其产生影响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当时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则是其广入人心的深层根源所在。其时,郭沫若被推许为新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这种文化权威地位无形之中强化了其创作的影响力,使他的作品和观点在当时的文艺界具有了某种不言而喻的方向性意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沫若的社会—历史悲剧只是悲剧中的一种类型,而且带有太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内涵。但在特殊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出于现实需要,中国文艺界却在有意无意之中将这一种类型尊奉为唯一的一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悲剧发展史上的一个悲剧。
与郭沫若作品的影响力相比,蔡仪的阐释则具有一种理论的总结作用。蔡仪是这一时期新崛起的美学家,他关于悲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新美学》中。
蔡仪是从社会反映论的角度阐释文艺的本质的,他的悲剧论述也由此阐发。在他看来,“文学是主要表现社会美的,而社会美则是规定于社会史的”,所以,“在社会史是矛盾冲突的阶段”,就是“悲剧的时代”。[3]273依据这样的认识,他指出,虽然历来的人们都对悲剧作了三种的划分:以古希腊悲剧为代表的“命运的悲剧”、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性格的悲剧”和近世以来的“社会的悲剧”,但说到底,“悲剧的真正的根源是在于社会”,是社会矛盾冲突的结果,只不过人们到近代才对社会的悲剧作了特别的指出。所以,社会悲剧的出现和它对悲剧的社会根源的强调,“是悲剧的进展的一个标志”,因为一切真正的悲剧本质上都是社会悲剧。[3]275-279从哲学反映论出发,蔡仪已然将悲剧看成是反映社会、认识社会的一种艺术工具,并以此来衡定其价值和意义。
明确了悲剧的根源和本质,蔡仪进一步指出,悲剧就是表现“必然的冲突”,“是表现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的美”。所谓“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是就冲突的社会事物而言,即它们的冲突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不可能避免。而且,他认为,它们既是冲突的,就是两种相反的社会力量:一方是正的力,另一方是负的力。冲突的消解,要么是这两种相反的社会的力一齐灭亡,要么只是正的社会的力的灭亡。在他看来,负的社会的力的胜利,是有它的存在的必然性的;而正的社会力的灭亡,则是由于在当前它的必然性尚小于负的社会的力的必然性,所以不免于灭亡。但,他又特别指出:正的社会的力的前途是必然的,而且正是由于“人们对它的必然的前途的期望,随它的灭亡而受挫折,所以是可悲的。”[3]275-276蔡仪这里所提出的“必然的冲突”显然是对马恩悲剧理论,尤其是恩格斯悲剧冲突论断的一种朴素浅近的转述和解释。就其阐释本身而言,并无错误,但是,当蔡仪将所有的悲剧都归结为社会悲剧、强调一切真正的悲剧本质上都是社会悲剧时,这种认识的简化和独断已然将马恩所论述的社会革命悲剧和冲突理论从悲剧的一种类型变成了唯一的一种。这不仅不符合悲剧艺术的历史传统和实践,而且人为放大了马恩悲剧理论的论域,对正在摸索中发展的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形成了一种理论的误导。当然这样说并非将责任推向《新美学》,实际上它只是当时理论界普遍看法的一种体现。
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和颇有代表性的观点,郭沫若的创作与蔡仪的理论实际上已构成并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悲剧观此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如果说郭沫若的悲剧创作在以史写实的意图中强化了马恩悲剧理论的历史必然性,那么以蔡仪为代表的悲剧论述则在社会反映论的指导下放大了马恩悲剧理论的适用范围和社会根源,两方面交互影响,最终建构起了中国的社会悲剧理论和社会悲剧模式,并且因为这悲剧冲突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政治内涵,将它理所当然地与社会制度的创立和维护相联姻。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这类悲剧艺术自身的悲剧,还使20世纪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展在艺术和理论的缺漏中陷入单一化的困境。
2.新中国诞生伊始,沉浸在解放和新生狂欢中的人们循着此前的构想放逐了悲剧。1948年5月,郭沫若为《白毛女》的演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即“悲剧的解放”,这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认识。逻辑在于,所谓悲剧,就是社会悲剧,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意味着悲剧在中国的彻底解放,因为产生悲剧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不可能再产生悲剧。所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悲剧也应该而且可以束之高阁了。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和推理,显然是极其简单片面和理想化的,但在当时却少有质疑。悲剧,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无奈而必然地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1960年代初,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引发了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悲剧的讨论,但这次讨论参与者非常有限,理论意义也相当寥寥,最终的结果只是使“社会主义悲剧”(当时的提法并不是很统一,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社会主义悲剧”、“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特定的悲剧性事件”、“革命悲剧”、“乐观主义的悲剧”等等)这一政治化的悲剧概念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而且随着社会的风云突变,它也不了了之,一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的悲剧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悲剧不再犹疑,以伤痕文学为发端的一大批悲剧性作品的出现更引发了人们对悲剧问题的思考,由此,文艺理论界也再度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悲剧问题的讨论。讨论从1978年起,一直断断续续延续到1985年才告沉寂。
在这次讨论中,马恩悲剧理论尤其是恩格斯的悲剧命题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论争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对其原意的理解问题、它的普遍性问题、它在西方悲剧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问题、它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等。焦点则集中在两个紧相关联的方面,即它的原意和它的适用性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结合《济金根》剧本和它所取材的16世纪德国历史,认识虽有细微的差别,但基本结论已与今天无异。比较棘手的,也最让论者费神斟酌的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让论者格外伤神,是因为这场讨论从其发起之初就不是纯学术的,夹杂了太多历史记忆和政治内涵。如果说在这次大讨论中,最为敏感且无法回避的是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根源问题,那么与之紧密相连的就是对恩格斯悲剧论断的重解和对其适用性的重新衡定。因为这其实是在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悲剧的问题寻找理论的依据。在当时,马恩的悲剧理论是人们普遍认可并一直信奉、应用的理论,也是在中国长久清除封锁西方文化期间一直独尊的悲剧理论。不可否认,这里存在着其他悲剧理论暂时匮乏的无奈,但从理论的接受和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的角度看,却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只有亲手打开自己曾经系上的结才有可能真正拨云见月、轻装上阵。
从表层看,论争有两派意见,一否定一肯定。否定论者明确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决绝地认为它不适用,但原因并不是马恩悲剧理论有局限,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一定能够实现,根本就无所谓悲剧。肯定论者则现实地承认依然适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悲剧”,“文革”中一系列惨痛的不幸记忆正历历在目。不过,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前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最优越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他们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事物,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4]简言之,这是在确保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承认发展的曲折。显然,这同样是从维护社会制度的角度立论,只不过不是决绝地不顾事实单作理论的推导,而是在强调、确证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最终一定会实现的前提下,承认实现的过程中会有波折,会付出一些代价、牺牲。这是当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悲剧的分析文章的基本思路。
从上面的论析可以见出,否定派意见已然是很主观,肯定派的论述也不全然客观,它之所以作这样那样的强调便是明证。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彼时的人们尚未完全摆脱对悲剧的单一的社会化认识,悲剧依然与社会制度和政治绑缚在一起。不过可喜的是,二者的二而一的关系正在慢慢松动,马恩悲剧理论返归自身论域的发展趋向已隐隐可感。这可以从董学文的一些文章见出一二。在1979年《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一文中,董学文对恩格斯的悲剧论断给出了自己的阐释:“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即事物受必然性决定的现实性;所谓‘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则是和现实性相对的可能性之一种。”[5]据此他还对悲剧性冲突作了三种的细分。概观其分析,虽然确如一些批评所言,存在着引申过于宽泛的问题,但它也让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有意的超越,对胶着于革命或政治问题的、教条的注经式论述的超越,相比而言,显然启示意义更大。另外在1981年专门谈悲剧冲突的《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一文中,通过对历史上各种悲剧冲突观点的评述,他也对自己此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恩格斯的论断“有特定的含义,它是对历史上济金根暴动事件悲剧性因素的科学表述,随意把它定义化、抽象化、任意套在各种有矛盾特殊性的悲剧现象和悲剧艺术上,显然是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作法。”[6]66其实,这同样是对一直以来学界所存在的错误做法的总结和批评,而且与前文相比,认识更趋于客观、开放。
历史地看,这次讨论存在着思想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片面,即使是对恩格斯悲剧论断的理解整体也较机械。但作为一个总结认识、清理成见的过程,其意义又是非常突出的,主要在于它纠正、澄清了此前的一些错误、偏见,促进了研究者们学术思想的解放和调整。具体说有两点,其一悲剧在中国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其二不同的悲剧理论和观点开始走上前台。就马恩悲剧理论而言,则在于一种真正的解放和回归,它终于可以慢慢卸下历史重负,在多元化的悲剧理论中自由地展示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3.概观马恩悲剧理论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接受历程,可以说正是一个革命的建构和审美的解构的过程。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最终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被确立下来,革命现实主义也随之成为中国文学和文论的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恩悲剧理论的革命化阐释和现实铺衍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一种选择。循此,新中国的成立也自然意味着悲剧的结束,但历史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此后,反思与讨论成为中国文学、文论在长时间禁锢后再发展的基础。反省意味着重新思考,讨论意味着观点的交锋,而思想解放的大潮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作为契机和历史文化语境,则为这次文学、文论的反思、解构打开了思想之门,中国的文学、文论开始从统一规范的革命话语和现实主义书写中慢慢走向多元化的审美言说和自我表现。悲剧观念作为这次解构的一个焦点,不仅结束了自己被驱逐的命运,重新浮出地表,并且随着各种悲剧艺术、悲剧论述的大量出现,其研究也走出了单一的社会批判、政治分析时代,开始众声喧哗。马恩悲剧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开始回归文学,在审美的视域中,慢慢褪去了中国历史所赋予它的浓重的革命色彩和沉重的政治内涵,从独尊的一元、单一的权威发展成为多元中的一极,进入客观的理论研究时期。当然,这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发展也密不可分,实际上它为马恩悲剧理论在中国获得进一步发展并确立主导性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如学界所研究,中国80年代文艺思想的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识而发生的,其中尤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为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让人们发现了另一个马克思,一个肯定实践主体,批判异化的马克思,随着对《手稿》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人学思想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是中国接受马恩悲剧理论发生质的飞跃的重要理论基础,并最终孕育了90年代的收获,代表性人物当推蒋孔阳。在影响甚巨的《美学新论》(1993年初版,2006年再版)中,蒋孔阳专门对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悲剧进行了研究,尤对马恩的悲剧观点作了特别的强调。
首先他对西方的悲剧艺术和理论进行了历史梳理,并总结指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美学家的共同缺点是都从抽象的概念来理解悲剧性,没有从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中,从客观的社会历史力量对人所造成的威胁和摧残中,来探讨悲剧的产生和发展。在他看来,这是西方悲剧发展中的不足,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论述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从而为悲剧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然后,他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他们的悲剧冲突理论进行了归类:“大致说来,主要有两种:一是新生的社会力量,为了争取美好的未来所进行的斗争。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尚未成熟,‘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因此导致失败和毁灭;二是‘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7]432第一种冲突阐释的是恩格斯的悲剧论断;第二种冲突借用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根据其归纳,在社会的历史变革中,新生力量的失败和旧制度的灭亡都是悲剧性的。这一判断和分类与向来的认识有所不同,而旧制度的灭亡之所以被纳入,主要缘于他对马恩悲剧理论所作的人学阐释。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们认为在社会历史关系中所形成起来的人的本质力量,总是希望自由地得到实现和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本质力量不仅得不到实现和发展,而且受到阻碍和摧残, 以至遭到毁灭,造成悲剧。”[7]432这阐述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另一方面又把悲剧艺术与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实现相联系。这样一来,马恩的悲剧理论在葆有自己的社会性内涵的同时,更从人性的角度得到了拓展,表现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从而不再单纯地拘泥于制度的新旧。而且,当它将目光投向人的自由存在、人类的生存、人生的意义等命题时,悲剧本有的丰厚人性主旨和哲理内涵也在马恩的悲剧论述中得到了相应的表达。此外,文章还特别强调,造成悲剧的因素虽然很多,但首先是美的或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其次则是这种毁灭在具有历史社会的必然性的同时,还必须具有“性格的坚强性”。也即真正的悲剧人物是“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并把自己的命运承担到底”、具有宁死不屈的精神的人。[7]432-433这是他对马恩悲剧论述的哲理意蕴和人性内涵的具体分析与强调。
马恩悲剧理论在中国,虽然经过80年代的审美解构,回归文学,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包括其适用范围的划定,基本上仍偏重于社会政治层面,所以使用有限。从这个角度看,蒋孔阳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人学思想基础上的阐发,的确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在充实、丰富其内涵的同时,也打破了它的局限性,使之更具有普适性。不仅如此,对马恩悲剧理论自身来说,这一阐发同样也是一种发展,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它实际上是从其内部深化并拓展了其悲剧理论的内涵和视界,毕竟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的生存境遇,关乎的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所带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所在,也是悲剧,尤其是现代悲剧的中心主题所在。
收稿日期:2008-07-01
注释:
①据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整理:1935年11月,《文艺群众》第2期发表了易卓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1939年11月,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内收二信;1940年6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了曹葆华、天蓝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亦收二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