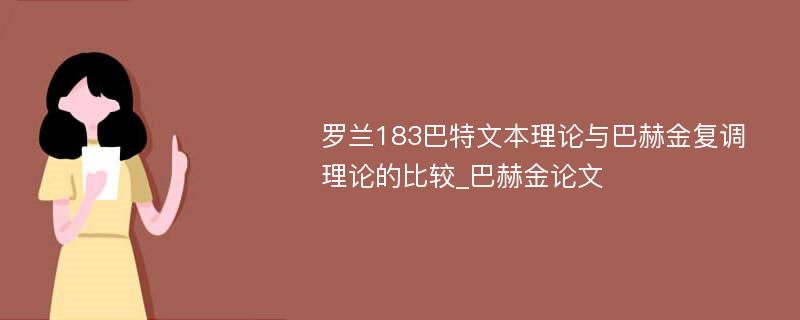
罗兰#183;巴特文本理论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理论论文,巴特论文,文本论文,罗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兰·巴特与巴赫金都是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他们富有原创性的符号学、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等思想成果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世纪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源。无疑,两人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想阵营、不同的学术领域,其理论创造也属于不同时期。巴特是法国五、六十年代思想学术的先锋派,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弄潮儿,文风华丽、飘逸、奇诡,在碎片式的文本写作试验中创造并体验冲破单一、僵化、形而上学语言牢笼的快乐。“巴特更多是一个文本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家”。巴赫金却是在二、三十年代高压政治的阴云下,秉承俄罗斯思想家坚定、虔诚的思想传统,在19世纪俄罗斯小说、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土壤上默默耕耘,获得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硕果。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巴特的文本理论创造受到了巴赫金的影响,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巴特思想形成了冲击,在某种意义上,巴特1967年—1968年的思想及文本实验就直接受到巴赫金思想的启迪。① 在巴特主持的研讨班上,克里斯特瓦以《巴赫金与小说词语》为题介绍了巴赫金的思想,巴特接触到了这一与他以往所坚持的人文科学模式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思想,在提交给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6年—1967年研讨班教学总结”中,巴特提到了这一思想带来的启示,“一种真正的语言空间”不应该是“为真实的逻辑服务的简单的线性话语,而是多样题材的并存(polygraphisme),其目的在于让各种写作与逻辑彼此对话。”② 巴特的文本理论与巴赫金“复调”理论是其代表性成果,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认真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以下就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的相关方面做一简单的比较。
一、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的相同性或曰相通性
(一)、巴特和巴赫金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批评中提出理论主张,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们的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而非纯粹思辨性、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哲学美学。巴特的文本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如《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的快乐》、《文本理论》便是建立在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等文本试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S/Z》、《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便是其思想实验的成果。巴特在1970年出版的《S/Z》中开始使用文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互文性”一词。③
同样,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是建立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精心解读基础之上的,他的“复调”理论就发轫于1929年问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文学理论、美学方法论的特征,就是从典范性的个案入手,进入历史的长河,进而把握特定历史文化现象的本质。有学者指出,巴赫金的美学研究,也许是和他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双重角色有关,他总是对西方文化史上的典型文化现象甚至具体个案紧抓不放,就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从剩余价值入手一样,巴赫金美学研究有两个典型个案一以贯之,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④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系统的精细研究,如果没有对拉伯雷创作系统的精细研究,就不可能有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理论”。⑤
巴特和巴赫金的理论不是脱离文学实践、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理论信条,而是既有比较扎实的个案研究,又有鲜明的理论主张的理论创造,这在20世纪的文论史中是极具特色的。
(二)、巴特的文本理论(theory of text)、巴赫金的“复调”理论(theory of polyphony)深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影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也存在一个类似于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潮流。西方学术界认为,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流行,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他关于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和选择以及共时和历时的关系的一系列观念,往往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⑥ 在这方面成就卓著的思想家中,巴特及其理论建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关于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思想,构成巴特符号学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思想起点,也是他的文本理论重要的影响元素。我们知道,巴特的文本理论主张,文本是开放的,是“可写的”;文本的意义是生产性的,是多元的;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没有汇拢点,没有收口,所指被一再后移;文本的指向是一种自由、快乐的想像和操作游戏;等等这些都可追溯到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语言的本质的思想。巴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热衷于语言的游戏、放纵想像的快乐,他继承并发挥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任意和约定关系的思想,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符号运用真相的揭示,来达到“总体上摧毁代码是自然的这类观念”,进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地批判。有学者指出,巴特的学术思想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化,其对语言本质的揭示及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的倾向,是一以贯之的。这可以看作是理解巴特符号学理论的一把钥匙。⑦
巴赫金的美学理论与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也有一致之处,在“语言学转向”的总的背景下,巴赫金的美学理论,特别是他的“对话理论”代表了特别有生命力的、至今影响越来越大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对话性”(dialogic)或者说“对话理论”,就是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学批判性反思的成果,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的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M.巴赫金(Mikhal Bakhtin)。他以同事V.N.瓦洛施诺夫(V.N.Voloshinov)的名字于1929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题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巴赫金既强烈地反对索绪尔的‘客观主义的’(objectivist)语言学,也批评那些想代替它的‘主观主义的’(subjectivist)语言学。他把注意从抽象的Langue(语言)系统转向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个人的具体言谈(utterances)。语言应该被视为本身就带有‘对话性’(dialogic):语言只有从它必然要面向他者这一角度才能被把握。符号(sign)主要不应被视为一个(像信号[signal]那样的)固定单位,而应被视为言语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而符号在种种特定社会条件下浓缩于自身之内的种种社会语调、价值判断和内涵则会限制和改变它们的意义。”⑧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一个稳定不变的系统,关注的是符号本身的内部逻辑,认为语言先于个人意识而独立存在,既与意识形态无关,也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索绪尔把鲜活的语言系统化、概念化、抽象化了。强调言语的对话性,强调对话当中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强调意义在对话中产生,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核心观念,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巴赫金反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客观主义倾向,反对语言研究中切断历史文化因素的作法,表明他在美学、文学理论研究中注重历史主义的原则。就此而论,巴特文本理论稀薄的历史感较之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不能不说是较明显的缺陷。
(三)、巴特的文本“多元化”理论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都有拒斥“同一性”、“去中心化”、消解人为性“权威”的理论指向。巴特提出“可读的”与“可写的”文本,强调唯有写作滋生意义的多元化,才能转向无限丰富多变的状态,才能消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条件下语言及其意义被中心化、总体化的倾向,才有可能获得解放与自由。他在《作者之死》中写道:“实际上,在复合写作中,一切都在于分清,而不在于破译什么;结构可以在其每一次重复和其每一个阶段上被后续、被编织(就像有人说的长丝袜的网眼编织的情况),然而,却没有底,写作的空间需要走遍,而不可穿透;写作不停地提出意思,但却一直是为了使其突然消失;写作所进行的,是有步骤地排除意思。就在这里,文学(今后最好说写作)在拒绝给予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一种‘秘密’的同时,也解放可被称为是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一种活动,因为拒绝中断意思,最终便是拒绝上帝和它的替代用语,即理智、科学和规则。”⑨
写作在消除意义的同时又产生意义,而意义的垄断和人为的限制,在写作的过程中被粉碎了,写作的本质乃是“编织”意义多元化的巨大的网络,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活动,一种对专断意义的“革命”和“解放”。巴特惊人地宣判了“作者之死”。作者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写作的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意义垄断的主体。宣判“作者之死”,就是意味着读者的诞生,意味着结束意义专制和垄断的时代的到来。由此,巴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概念和思想,如两种“写作”,“及物的”写作和“不及物”的写作。也由此,巴特提出“可读的”(lisible)文本与“可写的”(scriptable)的文本。前者中的能指与所指有着清晰的对应关系,其意义是确定的,具有以反映现实这样一种假定为先决条件;而后者要求关注文本语言本身的性质,它让能指自由发挥作用。对于这样的文本,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生产者。他们通过能指的自由活动透视文本中来自其他文本的影响(互文性),聆听不同信码的声音从而参与写作,领略这种自由写作的快乐。“可写的文本”是等待读者再发现、生产意义的,是建构性的、未完成性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尤其是他的“作者之死”的提出就是反对唯一的意义本源,抗议古典文本那种专断的意义中心化和一元化。
巴赫金的“复调性”,潜在的目的就是针对“独白性”的专制的、垄断的话语霸权,就是追求不同层面的声音独立而平等话语权,就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对话性”的社会实践开辟道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样也有谋求“自由”、“解放”的理论诉求。不同的是,巴特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享有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占有较丰富的学术资源,他是力图揭示西方社会年深日久的符号运用的真相,采取语言游戏的策略解构、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语言符号的中心化、总体化,意义被垄断的现实秩序。而巴赫金却是在原苏联黑暗、高压、专制的意识形态淫威之下,萌发出“人格独立、平等自由”的渴望,默默地在思想的荒原上为未来可能实现的“平等对话”开辟道路。在与西方思想界几乎隔绝的年代里,应当说巴赫金的思考与研究更其艰难。巴赫金的著作大多不能以他的名字发表,而是署名弗洛希洛夫和梅德维德夫。他曾被流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遭受过打击。但这并没有使他丧失追求真理的热情和力量。他在遭受不幸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思路,决不盲从政治形势及其要求而改变追求真理的立场。“他的著作谈的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是对话、复调、狂欢,但在这些问题背后我们总能感受到巴赫金虽然不好直说,但他是有话要说,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反对无视人的个性和价值,要求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价值,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独立存在,而这种思想正是他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基础……他反对等级和专制,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也是对话,主张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关系,热切向往人的自由和快乐,而他的狂欢化理论也正是体现出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一种更替和更新的精神,一种民众的快乐的哲学”。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讲到一个与“复调性”相对立的概念“独白性”,他将陀氏之前的欧洲与俄国的长篇小说归结为“独白型”,如托尔斯泰的《三个生命之死》之类的小说。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作者如全知全能的上帝主宰着一切,在冥冥之中俯瞰着人物,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甚至内心的秘密都无法掩饰都在其掌控之下。人物完全受制于作者,体现的是作者的意图,作者过于优势而强大的声音淹没了人物的声音。作品中即便有人物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也完全被小说作者本人终结性的声音所取代,参与对话的人物不过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而已。这类小说只有作者的声音是独立的、具有充分价值的,而其他人物的声音只能屈从于作者。“独白性”体现的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者的声音与意志被高度权威化、绝对化,体现的是人物主体性的失落,人物的生命之轻。“复调性”要突破的就是作者与人物之间关系上的不平等格局,要颠覆的就是这种由作者独断专行的“独白主义”倾向。“复调型”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同等价值、有平等地位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许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舞台。巴赫金的“复调性”的核心语义就是“对话性”。“对话性”与之针锋相对的就是“独白性”。巴赫金甚至把“对话性”确立在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一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基础上,对此他写道:“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语性的对立”,(11) “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2)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又是什么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关系联结、沟通起来的呢?这只能是用话语呈现的对话关系。人类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交流思想感情,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才能显示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
(四)、“文本”游戏策略与“狂欢化”诗学,是巴特与巴赫金文化哲学思想相同之处。在不同的文本之间穿梭、嬉戏、游弋,连缀思想与文明的碎片,彻底消解作品的整一性,作品意义的确定性,进而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是巴特的文本实验的重要策略。瓦解、清除日常生活状态中的钦定的尊卑、等级观念,让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在同一时刻、同一个广场狂欢,在一个特定的仪式性的时刻让人们获得自由与解放,是巴赫金文化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都有一个相同或相通的特点,即无论是文本还是“复调”型的对话,都是未完成性的、动态性的、而非静止的、封闭的结构。巴特在文本理论中区分出两种文本,“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可读的”文本是一种描绘性的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一种生产性的文本。关于“可写”的文本,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生产性使得“可写”的文本具有一种开放性,它们可以不断地被“生产”(重写),这与“可读的”文本的描绘性明显不同。其二,“可写的”文本处于一种永恒的现在时,就是说,他和读者同时存在,不同于“可读的”文本注定回到“过去时”,“可写的”文本的现在时,就是这种文本永恒的生命力和开放性的另一种表述。文本作为“可写”的“文本”,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作品,而是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其意义是在不同的文本之间参照、渗透、互证的,也就是互文性。在巴特看来,所谓互文性,就是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引证参照时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文本本身是一个意义生产的无穷尽的循环之链。
“复调”理论强调对话永远是一个开放性的、未完成的系统,真理的意蕴在不断的对话中呈现出来,沉默和封闭不是真理存在的条件,只有不断地对话,才能达到真理的真谛。前述我们讲过,人类生存的本质是对话性的,没有对话,人类将一事无成,更谈不上对真理的认识。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不能也不会是绝对的。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伴随着人类生活发展的历程而指向永恒,却不会停留在所谓永恒的结果上。巴赫金对此有极其清醒的认识。没有谁能最终垄断、占有真理。他在陀氏小说中发现了这一点,“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说出他最终的见解。”(13) 在陀氏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的反对出自别人和对他们个人所做的某种定论。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深信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巴赫金指出:“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14) 对话的这种未完成性、未定论性、自由的开放性,是对独白型的封闭、单一话语的反动。巴赫金指出,对话无论是作为一种文体还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都源自古希腊,对话成了古希腊时代人们在各个领域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日常生活等领域探索真理、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等人都对对话这一文体及其精神流传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古希腊这种学术民主、自由的精神,不仅促进了古希腊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而且也成为推动西方文化尤其是人文科学发展的驱动性力量。
巴赫金不仅仅是思考陀氏小说的问题,所谓“对话”也不仅仅是指小说,而是联系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并由此扩展到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甚至想到人类的全部生活,全部的文化,全部的历史,他的思考是那样的广阔,那样的深邃。他写道“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渗透了一切含有意义的事物。”(15) 源自陀氏小说的“对话”这一术语,经由巴赫金的提炼变成一个极富动力感的思想文化的螺旋,跨越了文学、哲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穿越了自古希腊以来浩渺的历史时空,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了以强凌弱、多元民族文化并峙、意识形态对立、国家利益纷争的世界上,对于人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人类社会,是一种深刻的启迪,至今仍闪烁着动人的思想光辉。
二、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之差异
(一)、巴特的文本理论一个潜在的目的是消解主体性,在文本理论中“作者”是不在场的,文本理论力图切断作者是文本意义之父的血脉,激昂地喊出“作者”之死的口号,明确反对任何追求文本意义的企图,反对古典意义上的作品理论,反对作者至上、作品至上的理论。1968年,巴特写了一篇不长的论文《作者之死》。他写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16)
“复调”理论并不排斥“作者”的声音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作一个独立、平等的与文本其他声音对话的伙伴。相对于巴特偏激的言辞,“复调”理论带有“主体间性”的意味,“虽然这里巴赫金并没有提到‘主体间性’的概念,但从他的思想实质来说,对话各方的独立性不但是差异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一种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他道出了一种平等的相互沟通的对话关系的本质乃是主体间的可理解性。”(17) 复调理论所强调的是把作者与人物都放置在一个平台上,作者与人物一样都是平等独立的主体,作者本人只是众多独立平等声音之一,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优越性,也不具备任何垄断和统治别的声音的特权,作者与人物是彼此共生共存互相交流的,是对话性的关系。
(二)、“文本理论”格外看重读者的作用,将其看作意义生产的、创造性力量。“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头,也不是文本的终极。他只能“造访”文本。文本向读者开放,由作为合作者和消费者的读者驱动或创造。“可写的文本”的提出与审美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复调”理论缺乏读者声音的思考。
(三)、比较而言,巴特的文本理论关注的是现在时,“可写的”文本是具有当下意义的现在时,是切断了历史联系的当下时,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多元化,这是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强调现在时,主张不确定性、非中心化和多元化。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对话性”,不仅仅关注当下意义的存在,更是从丰厚的历史文化中延伸出来,指向未来的理论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巴特的文本理论较之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缺乏一种深刻的历史感。
三、相关问题的思考
1.巴特反对作者是文本意义之父,力图将作者形象从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中心位置清除掉,将文本推至中心位置,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一个重大转变,即由“作品”到“文本”。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作品”的终结。(尽管我们还很难说巴特有明确反对欧美新批评派的作品至上,作品研究中心论的思想,但他的“文本”理论的提出却消解了作品作为文论研究的中心地位。)文本理论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文本”理论为后现代背景下文本多元化的理论思考开辟了道路。比较而言,巴赫会的思想肖像更其复杂,他研究陀氏小说时并没有面临巴特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理性膨胀,语言“中心化”、意义“总体化”的诸多问题,他仍然是在作品意义的层面上讨论“对话性”问题,这就是说他还是相信作品的意义是给定的,作者是文本意义确定性的一个环节。但是他的“复调”理论所揭示的多种声音并存的现象,又是注重多元、注重差异的,这又有后现代思想文化的因子。2.“文本”理论的出现,意味着对作品或文本本原意义追求的消解,意味着作品意义的确定性受到质疑,作者是意义垄断者地位的丧失,权威不复存在。能指一再被延续,没有终结,这是一种无序状态。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强调在多种声音并存、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彼此的对话性却给今天的人们极大的启迪,对话是人们能够而且应该选择的方式。对话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秩序,一种意义的建构。3.“文本”的存在在于其“互文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文本之间彼此互证、参照、渗透,意义之网取代了以往稳定的结构。每一个意义的节点,都是意义蔓延的开始,是一个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开始,这一蔓延没有终结。这又是今天网络时代的一个写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强调对话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强调它的未完结性,它的永恒性。
注释:
① 参见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② 转引自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③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和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④⑥⑦(17) 周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第358页,第361页,第344页。
⑤⑩ 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第224页。
⑧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⑨(16) [法]罗兰·巴特《作者之死》,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第307页。
(11)(12)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9页,第344页。
(13)(14)(15) [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第221页,第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