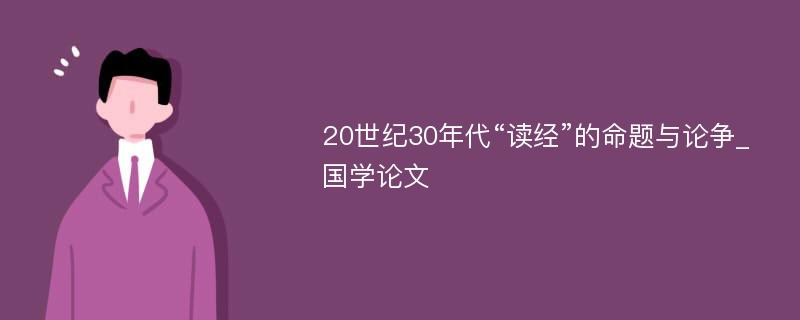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7-0070-06
1930年代围绕“读经”问题发生的争论,既是民国初年和民国十四年“读经”争论的继续,但更是前两次争论的深化和发展,其中包含的意义更丰富。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与“孔教会”研究较多,研究者的批判态度也为人们认可;但对1930年代的“读经”问题则研究相对薄弱,①且难免囿于惯性思维,把后者与前两次“尊孔读经”活动同视。其实,对历史上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现象,一概视为“花样翻新”、“沉渣泛起”,有可能失之简单。
一 读经主张和争论背景的历史考察
在1935年5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刊载的“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中,无论是坚决反对读经的朱秉国、倪守因,还是持折中立场的任鸿隽,以及主张读经的钱基博,都曾追问或表白“主张读经的,其真正的目的”[1](p38)和“所持之理由”[1](p26、72)。这一追问不仅适用于主张者,也应适用于折中者和反对者。而且所谓目的和理由,不能仅据各方的自白,必须全面了解当时的种种历史和时代背景,进而分析各人对这些背景的认识和反应。
对于193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时代背景,人们所熟知的是此时国民党正尽全力建立自己在中国的“合法”统治,但直到1933年以前,国民党内各派系冲突不断;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艰难发展,所以国民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线上持续进行反革命“围剿”,而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军事侵略采取妥协和退让。不过除此之外,通过阅读参与“读经”讨论者的发言和文章,就可以发现还有一些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对1930年代的读经问题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于1931年9月底到12月中旬在中国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无锡、苏州、广州等地考察,其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于1932年年底翻译出版。报告书指出,“外国文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是必要的,但机械的模仿却是危险的”,“中国为一文化久长的国家。如一个国家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着重大的祸害”[2](p24、26)。《中国教育之改进》曾引起国人广泛注意,在考察团足迹未至的河南洛阳,亦因此于1933年春创办了河洛国学专修馆,许鼎臣、周维新、阎永仁、叶连三等人主讲经史、诸子、《近思录》等,不仅吸引了一些读书人,甚至一些政界、军界要员亦来听讲。河洛国学专修馆办了四年多,“七七事变”后因洛阳遭日机轰炸才解散。[3](p36~37)
唐文治从1920年代就开始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国联教育考察团曾经参观的学校之一。考察团称该校是“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国有文化之责”[4](p92~93),使该校师生大受鼓舞。此外,1921年就产生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三年后清华大学(时名清华学校)设研究院,也是“先开办国学一门”。1920年代后期,其他几所综合性质的国立大学,如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也设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到1930年代,教会大学也出现了国学研究热,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辅仁大学都有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其中辅仁大学几乎把国学作为整个学校的重点和特色。
1930年代是一个“运动”和“讨论”层出不穷的时代。除了上述国学研究运动之外,还有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民族复兴运动,学者或民间形成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建设讨论等。这些“运动”和“讨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学”和“读经”的内容,而且很多人在不同的“运动”和“讨论”中都是活跃分子。如主张读经的唐文治就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不仅提倡而且实践了乡村的读经;在中国文化建设讨论中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反对读经;而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十教授中,王新命、陶希圣等,反对读经的态度却很激烈。还有,在一份1935年6月15日刊出的《新生周刊》上,由文学社等17个团体,艾思奇、老舍、李公朴、胡绳、郁达夫、周予同、叶青(任卓宣)、万家宝(曹禺)、叶圣陶、周建人等148人署名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5](附录p42~45)通篇内容都是批判读经。这些足以显示,读经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运动”相关联。从“国学研究”和“文化运动”的背景加以思考,就能发现外部因素并不限于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劝告或激励,更多的还是挑战。主张读经的郑师许在了解了日本的“支那学”研究情况之后说,还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就对学生说:“在学诸君要努力专攻支那经学。十年之后,支那无人认得经学了,我们预备到支那去讲授经学。”郑师许接着说:“虽然服部的造就甚少,而狩野直喜、内藤虎诸人的确已值得我们佩服了。其他新进之士如增本桥吉、宇野哲人……都已超过彼邦服部宇之吉、后藤朝太郎之上了。看了别人家的进步,我们那得不惭愧不惊讶?”[1](p35)
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武力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利用“尊孔读经”。1932年春夏,刚刚由日本“代产”的伪“满洲国”当局,就下令“所有学校一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并作“祭孔预备:表彰孝子、节妇,于祭孔时行之;印《孝经》读本三万册,颁于各省;编修身教科书,加入建国意义,治国宗旨”[6](p2716、2739)。1935年4月,毁于1923年大地震的东京汤岛孔庙经重建落成,日本政府邀请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四圣后裔”代表、中华儒学会代表和中华儒学研究会代表多人前往东京参加典礼。据1935年5月25日《申报》报道,中华儒学会和中华儒学研究会的代表汪吟龙、王永乐等人返国后,就商量“筹组曲阜研究院。该院以研究东方文化、儒家学说,推行世界,促进大同为宗旨,而辅以其他有关之学科,分设各研究所。如:甲、经学研究所……现此事已得河南刘(峙)主席、山东韩(复渠)主席等赞助”[7](p952)。
日本的这些行动无疑是对中国要否读经讨论的刺激。
1930年代规模颇大的读经讨论,由统治广东的陈济棠和统治湖南的何健分别在1933年和1934年下令两省中小学校开设读经课程而引起;其后南京政府教育部虽还维持着“禁止中小学读经”的明令,但1934年5月南京政府“通令全国恢复纪念孔子诞辰并颁布种种礼节。八月二十七日全国都奉命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中央政府且特派大员亲临曲阜祀孔,接着如重修孔庙,优待圣裔等,都有命令”[1](p71);还有1934~1936年统治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宋哲元也提倡读经,他不仅设立了河北莲池讲学院,在多个“通令”中“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德,垂为信条,通令尊行”,还在机关和部队中开展读经活动,“特聘请前清翰林、汉学家梁式堂为省府顾问,使其为众人讲经。每逢星期三、六晚7时至9时,省府大礼堂红烛高烧,气氛肃穆,讲师高坐首席,省府各厅处局长,驻军团长以上官长,皆环坐听讲,宋哲元本人也安坐师右,持书静听。读经遂蔚然成风”[8](p114、121~122)。但我们在回顾1930年代的读经问题的争论时,仍然不能只注意到国民党的地方武人和国民党中央这些政治对象,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因素;而应该扩大视野,实事求是地作全面深入的历史背景考察,这样才有利于对各方的“目的”和“理由”作出分析评判。
二 读经主张之评析
1930年代曾参与“读经”争论的有数百人之多,但大体上可以简便地分为主张读经、反对读经、折中对待三派。主张读经派中虽然有前述陈济棠、何健、宋哲元等几个国民党的地方武人,湖南的地方绅士等,但代表人物仍是几位“大师”级的“鸿儒”,如唐文治、姚永朴、钱基博、章太炎、郑师许、梁漱溟等,还有不少大学教授如古直、陈朝爵、杨寿昌、曾运乾、王节、顾实、李权时、崔载阳、陈尊柱等。另外还有江亢虎,他在民国初年以组织中国社会党、宣传无政府主义、遭袁世凯通缉而著名,此时却高度肯定“群经”。
武人如陈济棠、何健、宋哲元还是有相当旧学根底的,如何健称“余今尚可诵经文三之一,皆记自幼时”。他们认为“国家削弱危乱,已成不讳之事实”,多年取法欧美,但“形殊势格”,“桔变为枳”,使国家人民“弱而进入削,贫而入于乱”。而经书“适合于我国性民性”,要治理国家,培养和扩充“民族精神”,“读经纵非唯一之资料,然不能不谓为第一有力之资料”。[1](p11)宋哲元在《孔子祝文》中表示,他赞成尊孔读经,是为了“挽救世道人心”、“发扬中国文化”、“强固民族精神”和“保存国家正气”。[8](p121)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后面,虽然也有担忧国势危亡、日本入侵(宋哲元的部队在华北曾对日军有所抵抗)的成分,但更有为国民党和自己的统治地位寻求合法性的意图,因而欲用儒家经典“纳民于轨物”。
不过主张读经的人中,绝大多数还是保持着学术文化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立场。综观讨论者的意见,江亢虎的总结较为全面。他提出读经的理由有“群经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结晶”;“群经为中国先民自我之创造,精神之遗产”;“群经为二十四史前唯一百科全书”;“群经为诸子百家分立以前最普遍概括之记载”;“群经为孔子删订之书,孔子为中国最伟大一人格”;“群经为中国德育教育之宝典,可以替代狭义之宗教”;“群经为中国文学最高标准”等七条,并判定这些文化成就“实世界最高尚优美文化之一种,其本身价值及过去、现在、未来之影响于人类者皆甚大,故为明了及推进世界文化,不可不读经”。[1](p37)他是从世界和全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群经的。其他人虽是从中国和中国人自身的范围立论,赞赏的角度也大同小异,如王节、朱君毅、杨寿昌等人。他们强调经书所体现的文化的优美,精神的高尚,以及人类生活原理原则的普世性。
主张读经者也重视“救亡”的时代要求。如章太炎面对日本的大举入侵,强调发扬“民族之精神”,“保持国性”,故“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义,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隶而已矣”。[7](p951)唐文治则以为,读经可以“养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1](p4)。当然他们也承认,读经并非唯一的救国之道。郑师许说,“救国应从各方面一齐做起”,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学术”等等,“经学也是一种学术,这和社会科学当中的政治、经济等等,自然科学当中的地质、无线电、机械工程等等,处在学术上一般的重要地位,所以极需要有一部分的学者负起这个重责”。以往读者和研究者往往觉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的口号,不是别有用心抵制革命,至少也是过甚其词,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那些人视自己的主张为唯一的救国途径,这或许是一种误解和强加。所以郑师许特意作了上述说明。他还说,“大凡教育和学术之事,一方面要提高,一方面要普及”,[1](p36、33)所以对于经学,既要有专家学者作高深研究,也要有青少年打下经学知识的基础。
为了批驳来自反对读经者诸如“复古”、“抱残守缺”一类的指责,主张读经者不仅如前述着重介绍了日本人如何重视儒学经典的情形,还列举了欧洲人如何学习和研究古文字和经典的事例。如王节说,欧洲“希腊、拉丁文字,真古人之陈迹也,而彼国研求高深学问者,列为必修之科。新旧约全书,大都神话,语涉迷信,与科学相违戾,而彼国大学列神学一科,专门研求者不乏其人。吾国经学,讵尚不足当希腊、拉丁文;讵尚不及新旧约全书?而固有之国粹,竟不足当其一盼耶”[1](p10)?
十教授之一的何炳松有些看不起“国学专家”的成绩,曾说:“我们既自命为国学专家,为什么要让瑞典的安特生来代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石器?为什么要让美国的卡德来代我们研究中国印刷物的西传?为什么要让法国的伯希和来考订敦煌石室的古籍?为什么要让法国的考狄厄来代我们编中国通史……我们既然自己有国学,为什么要从荷兰出版的《通报》这类出版物中去翻译中国的史料?”但这番话恰恰被主张读经、宣传国学的郑师许用来说明西方和日本不仅在研究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文化,而且还在研究中国的经典和传统文化,甚至比中国人还做得好。“所以我说我们读经的人如果读得不好……后之研究吾国经学者,将不必需要到我们中国来了,这一个问题实在是何等严重。”[1](p35)中国人不研究甚至对自己的经典加以轻蔑,而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已有瑰宝而不知爱惜,已有财富而不知利用,甚而至于毁弃之,灭裂之。吐掷己之精华,而乞取人之糟粕;断损己之骨干,而拾袭人之皮毛。国民而具此心理,何异自杀”[1](p9)?所以当前述批评读经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出来之后,赞同读经的徐北辰在《主张西化的又一群》一文中,就反过来批评对方“一笔抹杀了先民创造的才能和创造的功绩,那也未免是奴性的表现”,而“全盘承受了人家的东西,即使有用,也只是文化上的奴隶而已”[5](p47)。
三 反对与折中观点之评析
反对读经的人数众多。如上述《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就有148人署名,不过这只是一种“表示态度”的宣言。《意见》简单地判定“救国不必读经,读经和救国没有关系”;称“以为从群经里可以取得许多道德的教训,作为立身处世界的标准,那也只是妄想”;还有以为教“古文”可以“提高一般学生的国文程度”,实际上“是阻止了他们的进步”。《宣言》称主张读经者“虽然未必是‘王道’政治论者的同群,而其结果却是一致的”;认为“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5](p43~44)著名的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根据民国四五年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民国十四五年段祺瑞、孙传芳提倡读经,都是为了“镇压……革命群众的热情”这种历史观察结论,推断此时的读经也是要“将大多数的国民变成‘阿斗’,预先替帝国主义者制造顺民”。因此在他看来,日本人和伪“满洲国”读经的事例,恰恰反证了中国人不应读经,“我们还不是‘伪满洲国’的臣民,我不知何以有读经的必要”?[1](p117)鲁迅先生也仍然坚持他1920年代反对读经的主场,和周予同一样,认为经书是造就顺民的利器。他说,“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意即提倡读经,就是在为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最终也是为外国侵略者制造奴隶。他还批评孔子,“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是一点也没有”。[9](p296,329)这些从政治立场来否定读经的理由,其中隐含着一个前提,即经书和孔子学说中有麻醉人民思想的成分,故能被统治者和帮闲们所利用。
傅斯年也认为,民国以来的几次读经,的确是政治上“右转”的表现,“事鬼神”、“弄玄虚”,使得他“替国家的前途担心”。他概述了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他以王莽的新朝、偏安的南朝、宋仁宗之后的宋朝、明末的情形为例,证明“古时经学制造的人物已经是好的敌不过不好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一旦国家充分提倡”,经学成了官学,做官的读书的人都把经学“用作门面装点”,或者“念经念到迂腐不堪”,总之不切实用。他因此得出结论,“读经从来不曾真正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曾真正靠他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他笼络学究……又有些外来的君主用他破除种族见解”,而且“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于立义不适用于民国”。特别“在这个千孔百疮的今日中国,应该做的是实际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虚是不能救国的”。[10]傅斯年当时在新旧学界都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这篇文章被多次转载和广泛引用。有的文章就进一步发挥傅的观点,如吴研因就援史书证明,汉朝独尊儒术,公孙弘以儒相,其后共有十人“‘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讥。’足见汉以来极有名的儒臣,就多数有缺德了;他如王莽、刘歆、王朗、长乐老人(五代的冯道——作者)、钱谦益、郑孝胥、罗振玉——古今多少奸臣、贰臣、汉奸、卖国贼,差不多多数是饱读群经或者多少读过十年以上的经书的”。所以他说,“读经不但无补于个人的道德,无益于统治者的统治,有时还会被利用,并且足以促统治者灭亡”。[1](p82,83)杜佐周认为,人的道德“完全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徒知若干德目,绝对不能担保他即有道德的行为”,“例如从前的官僚、军阀和政客,大都是受过《四书》、《五经》的陶冶的,何以做官必要贪污,从军只好私斗,为政不顾廉耻呢……我们若果真正关怀世俗,希望民众都要知道礼义廉耻,实践有道德的行为,第一还须自己切切实实作出榜样来”。[1](p75)此类意见包含较多针对现实的意味。
反对读经的主要理由,还有一条就是经书不符合“科学”,不适合社会需要。王新命认为,“不论是五经还是十三经,我都觉得这里面所含的古董成分太多,就中五经尤其是完全的古董”。“十三经都是最难读最漫无系统的”,“反科学而又毫无用处”。他强调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生活条件的不足”,因此教育也要以“用最短时间来求最多知识”为原则,“不应准备把整个古代的遗物来充实现代人的生活”。[1](p48,49)不少人强调,中国当时最需要“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复兴中华民族”,所以“应该极力设法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研究,推广科学应用。这一类的问题,实在是当前的急务”。[1](p47)这是反对“读经救国”而相信“科学救国”的思想反映。
主张折中的人对待读经问题的意见也得到较多支持。这些人多信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如郑鹤声认为,“孔子之删述六经,不过就古籍加以整理,实即古史之流”,所以多数人“对于经书皆未尝主张废弃”,“经非不可读”。[1](p43)因为经书是中国“先民生活方式与经验之记载”,中国文化“无不渊源于此”,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上古至春秋时期的种种情形的必经之途和资料宝库,而且“在现代亦不失其重要之价值”。西方人和部分中国人“研究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著作,不以为怪”,何以中国人自己一读经就“为开倒车”?[1](p39,40)林砺儒注意到了读经与救国的关系,他在《对于读经的意见》中,说“处国难严重当中,要振作民族精神,而恢复普通学校读经,这一点挽救民族颓丧的热忱,我十分承认”,但他强调“道德教育关键在社会环境及学校生活训练”和“成年人少做坏事”,而“至于多读点古训,纵有效果也甚微甚微”。[11](p693)这毕竟不同于认为读经只会造就利禄之徒、伪善者和顺民的观点。
折中派没有在该不该读经及其理由上多费神,而是在该怎样读经,即读经的态度和方法上作了一些讨论。黄翼表示“用宗教的态度去读经”,或者“以读经为道德教育的方法”,他都是“排斥”和“反对”的,只能以求知的目的去“读些经史古籍”。[1](p58)陶希圣反对把经书当作“信仰”的对象,“只许你拜,不许你……评头论脚”的态度和方法,主张“用学术的观察”来“自由研究”,这样才叫“通经”,才“会把你的思想弄活泼了”。[1](p113)
折中派还鉴于有些人提倡读经其实是装模作样,甚至别有用心,或者是迂阔,或者是盲从,故还提出了什么人该读,什么人不该读的问题。陈高佣说,“拿历史家的态度可以读经,用宗教家的眼光不可读经”;“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可以读经,未脱玄学气味的人不可读经”;“把握住现实问题……的人可以读经,不认识现实环境,盲目崇拜古人的人不可读经”;“学者为学术的研究可以自由读经,普通人为求得生活上的实用知识不必读经”;“大学生可以自由读经,中学生小学生绝不应勉强读经”;“了解现代思想,懂得科学方法的学者可以指导人读经,权利熏心、头脑腐旧的官僚武人以及文化骗子无资格提倡读经”。[1](p74)
刘英士也表示,他赞成“中学生们读些比较易读的经”,赞成“大学生们自动读经”,赞成“想做经学家的人们专门读经,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但是他“反对那些带兵从政的长官们提倡读经,因为凡是他们所提倡的,大部分是他们所不配提倡的”;“反对那些自己并不读经的人提倡读经,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在欺世盗名”;“反对那些伪道学家提倡读经,因为他们言不顾行”。[1](p55)其意思和陈高佣相近但有所补充。而沈从文因为只赞成对经书作学术研究,不相信“儒术”和“道德”可以治国,尤其是当权者自己都不能“正心诚意”,所以他说,如果读经和讲道德“真算得是一种‘救国政策’,那么当前应该读经的,实为下面几种人:一、国民政府大小官吏。二、国民党各级党员。三、国内各种军人。因为这些人正是当前社会国家的直接负责者,政治不良这些人必须负责”[12]。陈高佣、刘英士、沈从文的意见殊途同归,都是就读经一事批评国民党当局。因此可以说,提倡读经的大小当权者并没有从中得到政治红利,反而受了一番嘲讽。
民国初年和民国十四年的读经运动,是不同背景下不同运动的混合物。1930年代的读经运动,虽仍是一种混合物,但由于时代发展和背景变化,故无论是提倡读经的主动力量,还是参与读经讨论的群体,范围都大于前两次,实质内容也更丰富、更复杂。除了其中隐含的政治意味之外,还包括抵抗日本侵略、民族复兴、“国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等问题。所以这次讨论的意义,从宏观上看,展现了讨论者对古今、中西文明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从微观上看,讨论者表达了各自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教育改革、与文化创造、与知识传授、与道德及人生观等等关系的多样看法。讨论者“开诚相见,互相辩论,使双方的理由得以和天下人共见”,结果或如讨论组织者所说,能使读者“得到一种很好的参考,来决定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1](p2)或如主张读经者所说,“非有甲之主张,无由显乙之真理也。不知甲之主张,无以防读经之弊;不知乙之主张,无以成读经之功”[1](p19)。因而这场由读经引起的讨论,值得全面探讨总结。
收稿日期 2007-11-15
注释:
①研究1930年代“读经”问题的专著暂时阙如。论文则有罗玉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尊孔读经之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尤小立:《“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赵美玉:《20世纪30年代反击尊孔读经复古逆流》,《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