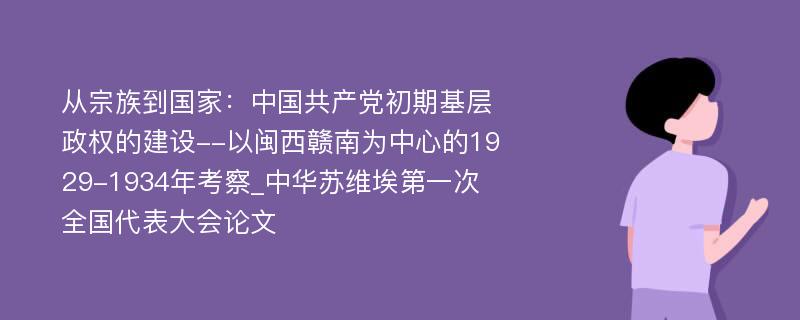
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以1929-1934年的闽西赣南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宗族论文,赣南论文,闽西论文,基层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5-0089-06
1929-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赣南地区(即中央苏区)进行的革命活动,对整个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该时期的基层政治组织建设为分析对象,揭示社会基层控制力量从以宗族为主体到以地方政治组织为主体的过程,以及其间所体现的宗法观念与国家主义,进而总结现代化过程中有关社会基层控制的相关问题。
一
自宋元以后,中国的宗族组织有较大的变化,有学者简单概括为两点:“一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使一个族姓所联系的族众范围较前扩大。二是宗族关系的政治性加强。此前宋元时期,宗族制着重于尊祖敬宗和睦族收族,此后则更着重于对族众的控制和制裁,变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注: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宗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从上述概括的内容看,宗族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功能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满足同姓族人的群体要求,维护宗族内部的稳定,达到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获得控制基层社会的效果。
当时的国家也认可宗族行使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能的作用,如催办钱粮、维持治安、处理户婚田土、殴骂窃赌等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都由宗族处理,甚至行政设置中的里甲制度,也为宗族所兼理,“地方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注:《大清律例·刑律·贼盗》。)。
这种状况在闽西赣南地区也同样明显。宋元之后,闽西赣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社会特征就是宗族组织的发达,外来移民进入闽赣山区后,为了进行社会活动,扩大力量,就利用血缘关系建立了宗族组织,宗族在其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
在明清之际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宗族性的血缘网络还成为了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部分。当时闽赣地区社会动荡、人口流动频繁,地方控制出现了松弛,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地方基层控制体系,运用一种社会组织来维持地方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民众行为,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利用何种组织重整地方社会呢?由于官方政治体系无法提供可资利用的体制资源,因此只能利用乡民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宗族。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些地方精英主要是利用在商品活动中积累的财富,普及宗族组织,修建祠堂,整编族谱,购买族田,在内部结构上强化宗族力量,支持宗族实体的存在;在外部职能上则使之从原来局限于尊祖敬宗发展到维护地方秩序,控制地方行为(注:详见拙稿:《客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的变迁——以闽西为考察对象》,第四届客家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年11月。),如一些宗族就被官方委以区域防卫的重任,如武平封候何氏,在边境关隘——黄石、崆头衰败之际,首先被民间选为关长,而后,“委为团练守府,又赐剑一把,除暴安良”(注:武平封候《何氏大同宗谱》。)。再如宗族对基层的经济活动也进行控制和调节,严格管理墟市,上杭的蛟洋集和新坊集,掌握在宗族手中(注:乾隆《上杭县志》,卷9。),长汀县邹氏更有建墟《合同》:“立合同人胜公子孙同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洪生、熊云、中彦、雄彦、一彦、圣乾、微耀等,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俱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共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注:长汀《范县邹氏族谱》。)通过宗族,本乡与他乡在商业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也得以解决,如永定古竹的墟市,“倘苏姓与外乡人争斗,则苏之老成必呵责族人而好言以安外人,其有外人实系无礼,亦必以理劝释之”(注:道光《永定县志》,卷16。)。社会慈善活动也基本上由宗族承担,“每姓必建祠堂,以安先祖,每祠必公置产业,以供祭祀,名曰公堂。其公堂,合族公举一二人司其出入,四时祭祀外,有赢余则惠及族之鳏寡孤独,量给养赡,子姓有登科甲入乡校者给予花红赴城,助以资斧,略做范文正公义田之意”(注:《瑞金县志·风俗》,转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对于这些行为,官方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如乾隆年间,江西巡抚陈宏谋根据江西的情况,奏准给予族长官牌,以约束族人(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181。),使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道光十年(1830年)更是重申:“该省通省皆聚族而居,每姓有族长绅士,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切听族长士绅判断。”(注:《户部则例》,卷3,保甲。)
因此,宗族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是全面的,成为基层控制力量的主流。正如郑振满教授所说的:“家族组织已直接与里甲制度相结合,演变成基层政权组织。……‘私’的统治体制不断得到了强化,乡族组织与乡绅集团空前活跃,对基层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控制”(注: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242-257页。)。也就是说家族组织与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逐渐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治安、司法、产籍管理、赋税征派等主要行政职能,同时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社会救济等再生产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延师设教,培养科举人才。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组织各种民俗文艺活动,推行道德教化和维护传统价值观念。也如王沪宁所指出的,“各村落家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些自治的共同体”(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自明中叶以后,宗族组织一直是闽西赣南社会基层运行机制中的有效部分,一位日本学者这样评述:“保护客家人(注:闽西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的唯一障壁,是其宗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注:[日]稻叶君山:《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注: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二
宗族组织之所以能够在该地区成为强有力的基层控制力量,与手工业、农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小农经济有一定的联系,在小农经济基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宗族组织就能保持内部结构的稳定,成为社区的基层控制力量。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有了较大的变化,宗族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随着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传入,要求建立新型国家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强化国家控制力量的思潮下,从观念上开始动摇宗族组织作为基层控制力量的合理性。国家主义和国民的自主性提升为社会建设的首要目标。
梁启超强调了国家主义对于国民的重要性:“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但“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这是民族之不强、国家之不昌的重要原因之一(注: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第1号。)。国家主义为什么薄弱?孙中山是如此解释的:“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显而易见,实现近代国家建设的难度不仅仅是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模式改造上层的国家政体,而且要将国家落实到社会的基层层面,即国家如何将国家的力量延伸到每个人身上,国家将如何使“民”成之为“国民”,而不是宗族之“民”。
将民众从宗族组织中剥离出来,直接的、有效的办法是削弱宗族组织作为基层控制组织的能力,改造社会基层的运作机制。随着20世纪初年“家天下”的王朝制度的彻底崩溃,思想界对宗法观念的彻底否定,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的种种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为了确立近代国家的模式,开始极力改造宗族组织或消除宗族组织的影响。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思想中,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也延续了这种思维,并且得到了极为突出的表达。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将“家族系统”与封建的“国家系统”、“鬼怪系统”等同,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绳索(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这些都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组织的不满,因此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要通过强大的政治实践瓦解宗族组织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如在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就对宗族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缔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那么中国共产党独立进行的、最早的、最为有层次的国家建设是什么区域呢?是在闽西赣南地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家建设的实践不是简单地挂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牌子,而是要切实地进行各层政权组织的建设,尤其是要面对着原来十分强大的社会基层政治单位—宗族组织,只有把基层改造好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才能落实,才算达到整个国家建设的目的。因为宗族观念、宗族组织的存在,使社会革命出现了很大的阻碍,“人们聚族而居,死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占有很大部分土地,族绅、头人可以利用这部分土地为所欲为,在‘有事不离祖’的宗法幌子下笼络群众,树立门户,党同伐异,寻找借口,挑起氏族或地方械斗。这种械斗有的连年累月,甚至结成世代冤仇”(注: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星火燎原》(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12月,第8-9页。);“村的支部会议简直是家族会议”(注: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在该时期,基层政治组织的改造经过了一个由破到立的过程,首先从内在结构和外在的功能上消除“家族系统”的力量,其次则是构造与整个国家政治活动能一而贯之的“基层组织”——乡村苏维埃。
瓦解宗族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宗族内部结构的三个关键部分展开:宗族财产、宗族精英、宗族意识。
第一,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乡族势力在几百年时间积累的经济基础。因此在土地政策的制订上,无论大的土地法规,如《苏维埃土地法》、《土地法》等等,还是地方性的土地条例,均将祠堂(或叫公共地主)的土地作为必须没收的对象。如1930年的《全国苏维埃土地暂行法》规定,“凡属于祠堂……占有土地,一律无偿没收”;1931年《江西苏维埃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1932年7月的《福建省检查土地条例》规定,“祠堂、庙宇等公田,过去未完全没收者应查出没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629、710页。)。“学田”、“义田”、“蒸尝田”等宗族公共财产的消失,不仅消灭了宗族进行地方秩序调节、缓解社会矛盾的经济能力,而且连基本的敬宗收祖的血缘联络活动也无法进行。
第二,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清除原来在宗族组织有巨大权威的、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宗族事务中,主持人士不是拥有财力,就是拥有功名,而这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阶级定位为地主阶级或土豪劣绅,是作为革命的对象而存在的,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清楚地阐述了政治上打击他们的方法,认为这样可以很好地达到重建地方秩序的目的,“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6页、第31页。)。闽西赣南经过阶级斗争,很多地方精英跑到了城里,“闽西各县的豪绅地主,闻朱、毛到长汀,便四散搬家躲避,逃到漳、厦者甚多”(注:《中共福建省委报告——闽西最近情况及省委对闽西斗争的估量与指示》,1929年4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63页。),开始脱离对宗族组织的控制(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23页。);而留在社区中的乡绅地主,境况也极为糟糕,“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17页。),如兴国的地主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威信(注:《毛泽东调查文集》,第211-212页。)。显然,在原来社会基层控制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主、乡绅由于自身经济优势、文化优势的被剥夺,他们所能发挥的政治优势也不复存在。
第三,宗族组织之所以有强大的基层社会控制能力,很大的原因在于宗族意识从血缘层面向地缘层面的延伸,社会组织的“泛宗族”化倾向是国家建设较大障碍,因此消除宗族观念在基层政权上的延伸,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它采取的办法就是灌输阶级意识,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宗法性定位转化为阶级性定位,明确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注:阶级划分的作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大力提倡,其后在客家地区所进行的《寻邬调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都采取了类似的标准,而且划分的标准越来越明确。),按照阶级建立的社会关系,其直接的作用就是将民众从宗族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不再以血缘认同自我的身份,而是以阶级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过去有两姓斗争的地方,须在两姓群众的代表会议上订立‘团结公约’,互相承认过去错误,相约以阶级斗争代替过去的两姓斗争”(注:《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1933年6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489页。)。
四
宗族的经济基础、领导阶层、认同意识被清理后,宗族权力在基层政权上的作用已经被改变,不再是直接的基层社会控制力量。那么基层社会由什么力量进行控制呢?当时闽西赣南平均每县人口为14万左右,每乡也有1500-1600人(注:详见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0页。),以每乡2-3个村计算,大约每村也有500人以上,如果不重建基层社会控制体系,国家力量只到达县一级,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填补权力的真空,在闽西赣南重建乡村的基层控制体系是势在必行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分两步:一是将原来只下达到县的国家权力机关普及到区、乡两级;二是区、乡政权的工作中心在于村,在于具体基层工作。
1929年的《闽西苏维埃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乡苏是最基层的政权,一区有三个乡苏维埃政权时,要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它们的组织与县一级政府是相同的,除了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层级结构外,还设有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建设兼文化委员会,委员会都由国家安排固定编制和人员(注:《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政治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4页。)。
加强区与乡的政权,目的在于巩固与发展村级组织,“乡的工作重心在村,所以村的组织与领导,乡苏主席团应该极力注意”(注: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区苏主席团应经常派巡视员或“工作小组”到各村进行考察,“深刻的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注:张闻天:《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页。),因为村级政权的巩固与否,直接关系到由此而上的各级政权的稳定。那么如何构建村级政权呢?
第一,设立村主任、副主任,他们由乡代表会议在该村的代表中选出,乡代表会议10天一次,而乡主席团会议5天一次,“即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的中间主席团要开两次会。村主任可以要他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乡政府的意见就可以直达到村一级。
第二,健全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10天一次,忙的时候5天一次,而会议时间,则由乡政府规定,因为乡主席要出席会议,实际上就使村政的讨论置于乡政权的控制之下。
第三,建立代表联络制度,比如某村代表15人,居民500人,就可以按照家屋的远近,代表能力的强弱,多的管50、60人,少的30、49人,“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的制度”,“很快吸收群众的意见提到村代表会议及乡代表会议上来,很快去解决群众中间的困难”。
第四,建立乡主席对村的负责制,注意各个村里怎样开展工作的,哪一村的工作比较落后,要加紧哪个村里的突击和帮助。与副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会议,收集各村工作上好的与坏的现象,以供主席团会议或代表会议讨论,进而带动“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276-342页。)。
第五,乡一级设立的各种委员会,一些重要的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生产教育、春耕、山林、水利、教育、卫生”等委员会,相应的村中也要有委员会,“村里有了组织,工作才更容易一些”,虽然村一级的委员会由村主任提名在村代表会议通过,但乡委员会主任直接管理村级委员会,而乡的委员会作为官方工作人员,与区、县、省的各级委员会是一脉相承的。
第六,乡村中设立了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如互济会、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乡村俱乐部、列宁小学等等。“各乡都有群众集股开设的消费合作社,减轻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还组织了各种生产合作社,共同经营,共享权力”,“区乡政府聘请了医生,设立公共看病处,苏维埃下的群众有病去诊断,不取分文钱”(注:定龙:《闽西的春天》,《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如长冈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注: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09页。)。取代了原来乡村中的宗族性的慈善组织。
村一级组织的建立,在实践中被检验是有效的,“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25页。),同时,也“使苏维埃密切接近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注: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因此,国家的意志和政策通过同样构造的各级组织层层落实、层层传递,很容易并且很快地传达和灌输到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普通民众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如军事动员、公债购买、修建河堤水利、组织互助社、发展犁牛社、进行春耕运动、扩大红军等等在当时都相当有成效地被推广(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276-342页。),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毛泽东自认为“苏维埃制度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25页。)。
五
中央苏区时期基层社会组织从血缘性宗族转化为有极大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性单位,应该说是国家制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主要是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起步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不是先有社会分化,然后通过整合来补偿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秩序的脱节和混乱,逐步形成良性的循环,使社会获得现代化的能力;而是先经过整合,然后才运用整合后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动分化。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建设所达成高度的结构分化、社会流动以及规模更大的、统一的、集中化的制度,才能获得现代化的资源(注: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转见{美}西美尔·E·布莱克编,杨豫等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2页。),国家只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达到倡导者、计划者、推动者和实行者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设想就是通过各种制度的构建,不断改造与分化社会肌体中独立于国家的部分,或者说不利于近代国家实现资源动员的制度,使国家的力量能深入社会基层,使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按照国家设想而进行,而统一,而不是像明清以来,地方基层虽有保甲、乡约等组织,但国家中央权力大体只能延伸到县一级,县级以下广大地区的权力结构组织则为宗族所控制,在从县级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每个家庭——的权力运作中宗族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上可以不接受命令,对下则可以发号施令。
从上述的基层组织历史演变看,1929-1934年中国共产党从基层社会开始建设国家政权的目的达到,建立了一个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国家模型,使“民”属于“国”,能够与整个国家活动同步,使农民真正进入了国家建设的行列,只有农民卷入了国家的行为轨迹中,农村才能彻底发展,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想完全从传统的基层控制模式转变为近代的模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血缘性家族(或宗族)和地缘性的自然村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尤其是外在的国家模式对之进行改造的时候,“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注: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因此宗族主义还隐性地起着一些作用。比如在中央苏区早期的活动中,“因为在两省边陲之地,隔重要地城市太远,文化及经济政治等都要较他处落后,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从前边界采取拉夫式的征收党员时,党的组织,每每一个乡村,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来简直就是等于家族会议”(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4-15页。)。再如在分田运动中农民还是愿意以村为单位分田,因为在一村一姓的情况下,“摸熟了的田地,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注:毛泽东:《寻邬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结果则容易造成“一切大姓分好田,小姓分坏田的错误”,“被非阶级分子利用姓氏来包办分田”(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第574页。),一不小心,很快会重蹈“土客之争”的覆辙。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国家建设对整个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这次社会现代化的尝试,对于以后他们所推行的现代化计划有借鉴的意义,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变迁或制度的重建,都要与原有的制度发生冲突,其间的关系极其复杂,需要对之进行周密、详尽的分析,才能理解其中所具有的社会变迁的意义。
标签: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苏维埃共和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历史论文; 才溪乡调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