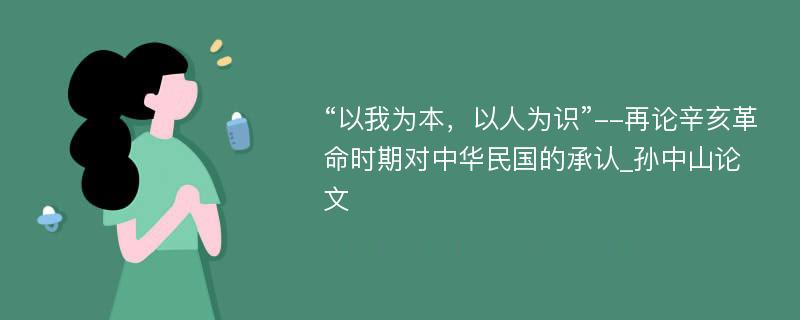
“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在我论文,中华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大多循革命党的正统活动为叙述主线,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成立,再到袁世凯当选总统,中间穿插清政府及袁世凯的历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于完整认识中华民国的缔造过程无疑是科学的。但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后,清帝逊位以前,清政府仍然是法理上的全国性政权,如果将此一过渡时期的历史主线完全以革命活动来讲述,对于外交史的认识可能会有局限,毕竟此时的中国驻外公使仍是清政府的派驻代表。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对承认问题的研究更加偏重国际法及传统国际关系视角。
承认问题是民国成立后的重大外交问题之一,学界现有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对承认问题已经有所交待。①美国与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态度引起学界较多关注。美国是较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其对辛亥革命具有较多的同情,尤其是在威尔逊(W.Wilson)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及活动已经比较清楚。依据目前的材料,一般认为,日本在拖延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俄国在很多问题上具有与日本类似的立场。②但亦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强调日本曾与美国同样坚持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的方针,后来由于英、法等国的牵制才不得不放弃了立即承认的主张,并提出了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双重外交关系”。③除美、日之外,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在承认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④既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列强方面,力图梳理各国决定承认中华民国的历史过程,贯穿研究的主旨则是揭露各国如何通过“承认”问题尽力榨取在华利益,扩大已有的各种特权。比较而言,中国方面的决策过程鲜有梳理,至于中国必欲求得承认的目的、动机及其背后的外交理念则更少有追问。不可否认,列强确有借承认问题继承、扩大在华特权的动机,但各国之间分歧甚大,不可以等同视之。
一、承认的缘起:湖北军政府交战团体身份的外交确认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对内发表了系列通告,昭示新政府的成立。在发表对内政策的同时,军政府非常关注对外交涉。10月12日,军政府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表示承认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缔结之条约、赔款与外债,各国在华权利及外人在华财产一体保护,但同时表示,如有帮助清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⑤该照会明确表示了革命党人对晚清外交遗产的继承态度,以及所准备采取的外交原则。姑不论其反帝精神如何,正如学界所认识的那样,这样的声明其实是同盟会既定政策的运用,并无特别创新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正确的选择。⑥军政府的对外方针是中华民国外交政策的源头,奠定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外交基调。在如何对待列强问题上,中华民国没有跳出同盟会和湖北军政府所发表的对外声明的框架。⑦
湖北军政府照会是理解承认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除对外宣示自身的外交方针外,照会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要求列强的承认。在照会中,军政府强调主权国家所必备的三要素自身都已具备,“在昔各友邦未遽认我为与国者,以惟有人民主权而无土地故耳。今取得四川属之土地,国家之三要于是乎备矣”,行文至此,照会并未明确提出要求承认,转而提出国民军对外行动的7点方针。⑧细研照会,其行文中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如各国遵守照会所宣称的7点对外宣言,采中立态度,即表示默认军政府已经具备主权国家的三要素,亦即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有研究明确指出,军政府的照会具有明显的策略意义,“其目的在于打消列强对革命党人的担心,争取列强的同情”,“消极目标为避免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积极目标则为促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承认”。⑨
历史的进程亦证明了此点。军政府在发表对外照会后,紧接下来的举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明确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交战团体是一个近代国际法上的概念,并不为晚清普通中国人所熟知,但进入20世纪后,国人在翻译和编辑国际法著作方面出现了大量成果,那时的知识精英对国际法已经不再陌生,关键在于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运用国际法。⑩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际法学著作这样定义交战团体:“一国中之叛乱者,谋颠覆其政府而有强大之势力,或一国之殖民地有独立企图之政治的团体也,亦曰反乱团体。”(11)既然是一国内部事务,别国本无由干涉,“胡为而有交战团体承认之事耶”?根本原因在于叛乱团体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如损及第三国利益,母国已不可能处罚,出于这种利害关系,第三国只有承认其交战团体的身份,以国际法条款约束交战团体,以求达到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叛乱团体均可被承认为交战团体,在1900年的万国国际法学会上,就此问题通过了决议,规定下列情形下不得承认为交战团体:一、虽占领国家领土之一部,而与国家有别,不能保一定领土之存在时;二、其占领土上非有主权之外观及未备正当政府之元素时;三、非有军事的组织,非有规律之军队,且不从战时法及战时惯习法或宣战不用己名时。(12)以当时的国际法通行标准衡量,军政府具备了交战团体的要素。
军政府要求各国承认自身的交战团体身份,在更深远的层面上代表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程度,这种依国际法而进行的外交交涉,暂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种进步。17日,驻汉口各国领事回复军政府,承认“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表示“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13)美国在此之前已经宣布中立。英国等国的中立照会在中外双方有不同的解释。军政府认为,英国等宣布中立,不干涉革命,是对革命军交战团体身份的承认,此举无疑为革命军外交上的一大胜利:“我军政府与清政府交战,承蒙贵领事一秉至公,承认为交战团,并宣布中立,殊深感佩。”(14)驻汉口各国领事不认同革命军的解释,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在致格雷(Edward Grey)的电报中指出:“至其自谓各国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体,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15)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Herbert Goffe)的言语亦可印证朱尔典所言不虚,“且据各领事所闻,革军都督因吾等无论如何,迭次不予承认,颇为厌恶”。(16)
英国等国驻汉口领事是否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似乎成为一桩悬案,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英国等国宣布中立的性质。考诸军政府与列强驻汉口领事之间往来照会的事实,可以确认,军政府显然有意通过照会获得列强对其交战团体身份的确认,列强虽然对照会予以回复,并先后表示中立,但并未明确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军政府发表7点宣言,并将战时管禁物品清单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后,各国领事无法置之不理。如果不予回复,各国在革命军控制区域内的利益将面临危险,但如果回复,意味着与军政府发生正式的公文来往,有默示承认军政府的倾向。10月21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致电朱尔典,指出各国领事迫于情势,“遂决定由领袖领事代各领事答复,声明该两文业已收到”。(17)这里的迫于情势,据戈飞的解释就是“革军首领之地位,建设日益巩固,益难置之不理”。在10月28日的驻华各国公使会议上,对于驻汉领事为维护租界治安而与革命军的正式交往,公使会议也予以了承认。11月8日,朱尔典在致外交部格雷的电文中说明了当时驻汉领事的矛盾心态,“明知不便承认革军政府,然实不能不与之公文往来”。(18)
英国等默认驻汉领事与军政府的交往,并未对军政府的照会提出有针对性的否定声明,这些举措虽然不能等同于正式承认军政府,但隐约已经有了暗示承认的意思。(19)笔者认为,英国等国的态度主要是基于三点原因:一、革命进展迅速,在各国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时,军政府已经有了自立的基础,不但控制了相当的地域,而且拥有了稳固的军事力量,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一个交战团体的基本要素;二、革命军处处照顾了各国在华的利益,可谓“举动文明”,地方秩序良好,并无排外性质,这些举动无疑赢得了列强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20);三、清政府仍然是名义上的全国性合法政府,在形势并未完全明朗以前如果贸然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必然会引起清政府的抗议,并最终损及他们的在华利益。
军政府曾对外宣称所建立的政权为中华共和国,并致电各国请求承认,“中华以革命之艰辛,重产为新国,因得推展其睦谊及福利于寰球,敬敢布告吾文明诸友邦,承认吾中华为共和国”。伍廷芳在电文中特意强调新政府的共和性质,“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政体”(21)。
现有研究认为,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观察。武昌革命爆发前,革命党人主要与英、日、法三国接触,三国态度无友善不友善可言,大体上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武昌革命爆发后,列强或主干涉,或主中立。革命政府起初要求列强中立,继求世界各国的承认。(22)本文赞同上述观点。鉴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笔者建议进一步把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对承认问题的态度相区分。当然,二者之间的关联亦相当微妙,各国之间有区别,一国亦因时间不同而有变化。
学界曾经认为,列强的中立都是假中立,如果透过列强偏袒袁世凯的个别事件,上述看法也不无道理。新近的研究观点认为,“尽管列强都曾宣布或表示过中立,但动机各不相同,表现也不一致,有的在某阶段确实中立,而在另一阶段则偏离中立;有的在某地区实行中立,而在另一地区则不愿中立”,如果以一种纯粹的标准要求列强的中立,那么列强的中立的确值得怀疑。(23)但抛开一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列强的中立宣言对军政府的支持是客观存在的。在当时国际关系的理论中,这种中立是对军政府可能成为全国性政权的一种乐观估计,具有国际法上的积极意义。
二、过渡时期的承认问题
就中华民国承认问题而言,武昌起义后列强的中立及对革命军交战团体的默认是一个序曲,实质性的进展尚未开始。此时清政府仍属中国的合法政府,再加之军政府的根基未牢,各国尚可依国际通行惯例在承认问题上采取拖延和观望态度。但随着革命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随后的清帝逊位,使得承认问题走上前台,临时政府逐渐具备获得承认的各种要素。各国逐渐意识到,承认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检验列强各自外交政策的时机来临了,因各种利益而驱使的承认交涉大体反映了各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向。从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到最终获得各国承认,依国际法而言,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清帝逊位。自民国肇造至清帝逊位则属于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月5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在内容上继承了同盟会7点宣言及湖北军政府对外宣言的主要内容,除承认前清政府所缔结条约及借款外,增加了对满人的保护条款,并允诺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宣言最后,孙中山呼吁“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这是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首次正式要求列强的承认。(24)对外宣言发表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在积极试探各国对承认中华民国的态度,因此在争取列强承认问题上,在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前可分为两条线索:革命力量和袁系政治力量,这两种力量均曾试探获取列强的承认。袁主政民国后,承认问题就成为袁系政治力量的外交目标。在袁主政前,其各自的对外活动及交涉并无协调。
1月19日,王宠惠代表南京临时政府致电英国外务大臣格雷,希望英国在清帝退位后即承认中华民国,但英国并未回复南京临时政府的照会。格雷在致英国驻日大使电文中表明了英国的态度:“本大臣接获南京共和政府外交部长来电,言及成立共和政府、推举孙逸仙为大总统及承认共和国等问题。对此,本大臣拟不给予任何回答。”(25)袁系政治力量同样关注承认问题。1月11日,梁士诒秘访朱尔典,探寻英国对将要设立的临时政府的态度,朱尔典称“如此重大问题,本使并不处于发表意见之地位”,婉言拒绝承认袁世凯将要掌控的临时政府。英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均未获得实质性进展。同日,孙中山致电法国,委派张亦舟为南京临时政府驻法代表。外交总长王宠惠亦致电法国外长,要求承认民国政府。法国未予答复。(26)
1912年1月16日,英国驻日大使往访日本外务省石井,就清帝逊位后的国体及承认问题展开接触,英国驻日大使告诉石井,英国政府对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要求的推举孙逸仙为大总统及承认共和国问题,没有表态。英国驻日大使认为,在承认问题上,日本将与英国保持一致,“一旦共和政府宣告成立,而各国政府又迫于承认之际,日本国政府当不致有与我国政府分离而单独采取特殊态度之意向”。(27)
日本在拖延承认问题上扮演了主要角色,此结论现在看来仍是恰当的。(28)日本阻止列强早日承认中华民国,并力图扮演领导角色,现有的档案已经可以充分说明此点。但细研史料可以发现,在清帝逊位前,日本并未就承认问题提出预案,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该问题,反而是英、俄等相继以此问题探询日本的态度。在英国探寻日本态度的同时,俄国亦进行了类似的举动。早在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前,日俄两国已经就如何划分两国在华利益问题展开密谈。1月24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会晤俄国外务大臣,商讨南北满洲分界线及划分内蒙古势力范围问题。俄国建议“日、俄两国在划分内蒙古势力范围时,如能在两国势力范围中间设定一中立地带,较为适宜”,日本则建议“设立中立地带,不免稍有怀疑。但贵国政府若作为对案提出,本使可立即报请本国政府充分考虑。”此时,俄国提出承认中华民国问题,让日本考虑。俄国外务大臣已经意识到共和政府将于近期内成立,“共和政府一旦成立,必然要求各国政府予以承认”,“届时日、俄两国可否作为承认新政府之交换条件而进一步要求巩固两国在满洲之权利?”本野建议日本政府断然采取措施。(29)日本政府得悉俄国的建议后,回复本野,“关于俄国外务大臣所谈承认清国共和政府问题,因事关重大,帝国政府正在考虑中”。此时日本已经初步表达了所谓的各国协调一致原则,“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均以维持国际协调为原则,故对新政府宣告承认时,势必亦将采取协同步调”,正是基于此种立场,日本建议日俄两国与他国保持同一步调。(30)
就国际法而言,清帝逊位以前中华民国政府不能获得列强的承认,并非仅仅是列强对中华民国的要挟,在当时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亦有例可循。一般认为,不适时地和过急地承认交战团体为一个新国家,不仅是对母国尊严的冒犯,而且是一种国际不法行为。1903年,当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时,美国立即承认其为独立国家,一般认为,美国的行为构成了干涉。(31)就清帝逊位前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而言,革命党人虽然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仍是清政府。清政府仍然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袁世凯掌控的北洋新军名义上仍然是清政府的军队,所以在理论上中华民国尚未真正、确实和永久地建立起来,而是正朝着这个目标进行努力。袁世凯要求列强给予其治下的共和政府的承认许诺,以及孙中山要求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就国际法层面而言,皆因清政府的形式上存在而未能实现。此时列强不予承认,尚有借口,但当清帝宣布逊位后,列强对承认的种种迟延,从性质上而言已经发生了改变。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32)至此,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退出了历史舞台。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5日,袁世凯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退位诏书颁布后的第二日,外务部致电各驻外使臣,“所有出使大臣改称临时外交代表,接续办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时代。3月11日,民国统一临时政府成立,外交部致电各外交代表:“本日外交部以中华民国统一临时政府已告成立,袁大总统于三月十号举行受任礼,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国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33)
对于承认问题而言,清帝逊位意味着中国完成了政府更替,中华民国成为在国际法上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日本开始成为承认问题的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并试图主导承认的决定权。1912年2月21日,日本提出了一个关于承认问题的备忘录,就承认的条件问题征询各国意见。该备忘录建议各国要求中华民国保证外国人“仍继续保持其在中国所享有之一切权利、特权及豁免权”,其中包括没有条约依据的特权,并建议各国保持共同行动。鉴于日俄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首先试探俄国的态度。内田外务大臣致电驻俄大使本野,认为“鉴于目前形势演变,迫使吾人承认新政府之时期迟早终必到来”,建议“日、俄两国与其他各国同时表示承认”,要求本野征求俄国政府意见。(34)内田康哉于21日致电日本驻英代理大使山座,电称“鉴于目前中国之形势演变,迫使吾人承认新政府之时机何时逼来,实难逆料”,在此种情形下,“帝国政府拟首先披陈所见,藉以向各国政府征询意见”,日本计划首先征询俄、美、英三国意见,然后再扩展至其他国家。(35)英国22日收到日本方面的备忘录(36),24日对日本表示原则上同意该备忘录,惟细节需要再商讨。(37)美国于23日得到备忘录,27日做出表态:只要日本不故意拖延承认进程,美国原则上同意共同行动原则,并乐意进一步回答任何关于保证条款的其他问题。美国同时提请日本政府注意,中国的条约义务与政府的更替并无直接关联,临时政府自然需承担原政府的义务,美国需要与该政府保持联系,直到该政府最终获得国际承认。(38)
日本的备忘录与法国的政策可谓不谋而合,“法国于收到日本照会后,外长保安卡累极表赞同,但谓训令驻北京公使照办之前必须征得俄、英两国同意”。(39)德国亦赞成日本的提议。(40)日本基本上获得了俄、英、法、德、美5国的支持。奥地利没有答复日本,意大利则表示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综合各国的初步反应,原则上,并无国家对共同承认问题提出异议。美国出于国际法角度的提议可谓最为客观而合乎国际惯例。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草拟了《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条件细目》,并于3月23日致日本驻英、美、俄、法、德、意各国大使,进一步细化了承认条件的具体规定。(41)该细目提出后,各国就承认中华民国问题暂时达成了一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任临时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决议政府迁往北京,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统一。承认问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成立在我,承认在人”:民国政府对承认问题的研究与应对
从武昌起义至中华民国终获承认,在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中,关于承认问题存在着三个阶段三种势力的斗争。自武昌起义至民国肇造是为第一阶段;中华民国成立至清帝逊位为第二阶段;清帝逊位至获得承认为第三阶段,此阶段内包括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等重大政治变动。第一阶段之所以定位于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1月1日,是因为军政府在此前一直要求列强承认其为交战团体,并希望列强中立,而此后则是希望列强承认民国政府的合法性,要求列强承认民国政府即中国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清帝逊位不仅是中国帝制结束的标志,也是清政府国际法主体身份资格丧失的标志;在对外关系上,清政府不再代表中国,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各国承认的政治形势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因此将其定为第二个阶段的标志。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过渡,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系政治力量之间处于对立状态,中国尚未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府,一时还无法确定究竟谁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清帝逊位、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标志着全国性统一政府的出现,民国已经具备获得承认的各种要件。未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作为划分标志,最主要的依据是,在此前后关于承认问题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内政治形势亦未出现影响承认问题的因素。三种势力分别是湖北军政府及其后继者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系政治力量、清廷。在第一阶段,湖北军政府希望被承认为交战团体,而袁系政治力量基本上与清廷站在同一立场。到第二阶段时,临时政府希望获得承认,袁系则试探各国对于由其掌控的共和政府的态度,二者内部虽存在分歧,但政治目的具有一致性,促使清政府下台。在第三阶段,主要是孙中山等革命派与袁系之间的政治纷争,列强开始具体考虑承认问题,在此阶段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成为承认问题的实际负责人。
中华民国成立,清朝覆亡,就国际法层面而言,其本质是政府继承问题,中国所有的国家权利和义务,由清政府转移至中华民国政府。政府继承不同于国家继承,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更经常的是政府继承问题。“在政府变动的情形下,不论是按正常的宪法方式还是一次政变或革命成功的结果,一般公认,在所有影响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事务方面,都是新政权代替前政权”。(42)对于通过革命途径建立新的政权,外国必须决定“新国家是否已经真正确实地和永久地建立起来,还是仅仅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而尚未成功”。(43)对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的承认问题,业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已经完成表面上的统一,“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列强在承认问题上并无文章可做。因为这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两个独立的政府,而民国政府与清王朝的更替又纯属中国内政,对于独此一家的中国政府并不存在需要列强承认的问题”。(44)
中华民国成立后,发布对外宣言,要求各国承认。对这个宣言及其所列举的种种条件,当时伍廷芳就提出不同见解:“至于通告外国,要求承认,既不必待各国之回章,自不必列于条件”,其列举的理由可谓一语中的,“盖成立在我,承认在人”,“今宜先求其在我者”。伍廷芳强调承认问题的关键在于清帝退位后“以筹设统一政府为第一”,“统一政府尚未成立,外人无从承认也”。(45)
历史的进程验证了伍廷芳在承认问题上的远见,但其纯粹基于法理角度的分析,过于强调自身的努力,而忽视了列强在承认问题上的各自考虑。在清帝退位问题上,他建议:“宜由袁世凯君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同意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如此,则统一政府成立之后,于内必能统一全国之秩序,于外必能得各国之承认。”(46)伍的观点并非孤立,陈其美、温宗尧、汪精卫等都持同样意见。应该承认,伍廷芳所提出的“成立在我,承认在人”的观点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民国政府本不应过分强调各国的承认与否,否则更易为有关各国所要挟。但该认识低估了各国在承认问题上的实际利益诉求,列强固然以中国未能成立统一政府为理由不予承认,但其背后自有其各自的国家利益。事实证明,统一政府成立后并未如伍廷芳事前所预设的那样获得列强承认,而是一再迁延。1913年,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专就承认问题提出报告,分析了承认问题的种种情形。报告从承认的要素、承认的迟速、承认与否的利害、承认之手续及临时政府能否获得承认等问题展开探讨。清朝覆亡,民国成立,在事实与法理上属于政府更迭,中国的国际法人格并未消失。报告在法理上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今之言承认,非指国家而言,乃指政体而言”。(47)
自民国成立以来,国内政治形势一直未能实现稳定局面,临时政府自南京而北京,临时总统由孙中山而袁世凯,中国的确没有建立一个巩固而确实之政府,但情况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以后已经开始好转。当时的国际法对于承认问题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须旧国停止争端”,二是“须新建国果尔巩固”。民国政府属于政府更迭,第二个因素就属于主要考虑的内容。报告认为,当时的民国临时政府“虽曰临时,而国基已固,况国会指日召集,政府对于前清所订之约章,屡次声明接次遵守,是对于承认之要素已觉充足”,然民国政府一直未获承认,对于其背后的原因,报告举国际法学者奥本海的学说为例,认为“纯系各国政策问题”。(48)报告另以葡萄牙政府更迭一事举例,认为虽然葡萄牙王室逃出国外,不赞成国内共和政府,并一直与共和政府对抗,但各国仍然承认葡萄牙共和政府。将该案例与中华民国情形相比较,显然民国政府自应在获得承认之列。对于中华民国迟迟未得承认,报告认为该情况并非中国特有,“凡政体变更,布新除旧,应由他国承认,而承认之迟速,则无一定条例”,而其背后的根本,或者说承认缓急的关键“终不出于利益二字之范围”,并非国际法上的问题。(49)条约研究会的该项分析无疑呼应了伍廷芳所提出的“承认在人”的观点,亦属客观之论。
中华民国是否获得各国承认,并不影响中国国家权利。不论是否获得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均可以行使国家权利,同样亦需承担相应义务。报告感叹“法理每与事实不符”,中华民国可以不要求各国的承认,但国内现实形势却不容许,“承认之后,外款既易筹借,内债亦易举行,否则信用不敷,事多掣肘,此承认与不承认利害之彰明昭著者也”。(50)
报告认为,承认手续并无固定形式,“然就事实上研究之,似不外乎两种,即正式之承认与隐默之承认是也”。此外,承认还有“分认”、“合认”的区别,“各国自行承认是谓分认”,“各国开会共同承认或以外交文牍会同声明承认之事,是谓合认”。报告指出,合认一般都有具体要求或附带条件,而这正是中华民国所面临的一种情形,“现在各国对待中国,往往由外交团进行办理,此次承认之事,难保不盟故智”,建议政府早作准备。(51)日本竭力主张共同承认实即报告所讨论的“合认”问题,而关于承认问题则先后提出两次备忘录,对民国政府提出种种条件限制。
报告认为,不论中华民国政府是正式政府,还是临时政府,都属于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承认并无关系,承认早晚“初不待乎要求”。民国迄今未获承认,各国“一则藉口于政府之未巩固,一则取协同进行主义,以为牵制”,关于承认问题“日、俄提议满蒙特权,英国提议西藏特权诸事,吾以引为寒心,宁可再行自出要求,致铸错于九鼎”,不建议中国政府自行一再主动要求各国承认。报告综合研究的结果,就临时政府能否暨应否要求各国之承认提出了建议:虽然临时政府可以要求各国承认,但由于日、俄、英等国提出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临时政府此时不宜主动要求各国承认。目前要做的是安定国内秩序,令驻外代表与所在国先行联络,促进感情,为承认问题做好铺垫。(52)
报告基于国际法及国际惯例所作的分析,可谓到位。其对于承认问题的透彻分析无疑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自民国成立以来,曾有屡次要求各国承认的外交言行,报告显然并不赞同。
四、迁延过久问题与美国的承认
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中华民国完成了表面上的统一。统一后的北京政府并未停止寻求承认的努力。1912年4月3日,北京政府令驻法外交代表向法国政府要求承认,法国认为中国政府未能达到日本所提出的承认条件,拒绝了中国的要求。(53)美国在承认问题上一直给予国人以希望,这也是北京政府寄予厚望的西方国家。5月6日,美国政府电询驻华美使关于承认新政府的意见,时任驻中国公使的嘉乐恒(W.J.Calhoun)主张迅速承认中国政府,以有益于中国内政的安定。(54)现有资料表明,当时美国国内舆论一般支持承认民国政府。是年6月16日,美国各大城镇商会邀请中国驻旧金山领事发表演说,向美国人呼吁承认中华民国,各会“均表决呈请大总统塔厘速行承认”。(55)据欧阳庚副领事汇报,除在旧金山发表演讲外,仍有美国人邀请领事前往美国其他城市演说,请北京政府外交部批准。
1912年6月29日,陆征祥继唐绍仪任内阁总理,值阁揆履新之际,新内阁向英国表达要求获得承认的意愿:“希望共和国政府能在最近期内得到英国政府之承认”。英国的回答给出了承认的明确条件:“在召开具有代表性之国民会议明确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条文顺利选出大总统前,关于承认中国政府问题,英国政府碍难加以考虑。”(56)这是英国政府就承认问题提出的明确条件,这个条件不同于日本政府第一次备忘录及其细目,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标志。
经美国国内热心团体的不断努力,美国舆论界要求承认民国政府的呼声已经实质性地影响到了美国国内政治。有感于舆论压力,美国驻日大使告诉内田,“政府如不采取某些措施,国会有可能在闭会之前亲自向政府施加压力,届时政府将陷于十分困难之境地”,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对承认问题加以考虑。(57)在向日本提出的秘密备忘录中,美国询问日本政府:“是否认为中国现政府实质上已具有国际法上迄今为止已被公认之基础,从而准备考虑是否应予正式承认问题?”但日本并不认可美国的提议。(58)
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在与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谈及美国政府的备忘录时,询问其意见,嘉乐恒认为以往所坚持承认须建立在中国成立巩固政府之后的观点须加以改变,现政府虽不十分巩固,但也不会再有大的变乱发生,“如再迁延,将无止期”,主张予以承认。(59)嘉乐恒向伊集院透露,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认为中国情况最近已经取得了很大改观,已无必要再事迁延。
7月23日,日本驻美大使珍田会晤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后者表达对中国共和政府的尊重,批评各国迟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原因是“为庇护欧美资本家之私利,不得不谓为横暴之举”,该主席认为,“此次中国建成共和政体,乃近世最堪叹赏之一大进步,各国本应尽早予以承认,并尽可能给予援助与支持”。(60)
美国还将该备忘录照会英、法等国。英国在回复美国备忘录时指出,“英国政府所获之北京报告,则与此见地不相一致;且袁世凯本人已曾自行承认,中国某些地方实际上不能履行条约义务”,不支持美国的观点。(61)法国则以中国不接受六国银行团所提借款条件为由,认为中国财政窘迫,各地情况亦不稳定,不主张予以承认。(62)
美国备忘录并未得到日、俄、英、法等国的支持,在此次外交过程中,日本政府在联络各国反对美国的备忘录方面出力甚多,美国最终不得不表示,“除非遭到舆论压迫而处于万不得已情况外,关于承认问题必始终坚持与各国政府保持协同步调”。(63)
前文曾述及,学界在论述日本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有不同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在阻挠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扮演了主要角色。虽然其论证系围绕日本如何阻挠承认中华民国问题而展开,但并未明确提出日本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了始终阻挠的态度,不过读者从论证中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64)另一种观点则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阶段性划分,认为日本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转变。该观点认为,在1912年7、8月间,日本围绕是否立即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有一个转变,先是坚持立即承认,然后被迫放弃。(65)
二者的不同在于,日本的态度是否有变化,后者的观点似乎是前一种观点的发展。笔者认为,1912年7、8月间日本在承认问题态度上是否有一个转变,尚需谨慎考察。在收集更为直接的证据和进行更为全面的论证之前,还须存疑。虽然日本在致各国有关承认中华民国的备忘录中提出“一旦中国建成一个巩固而且具有实力之新政府,并足以证明此新政府抱有履行中国所负担之一切国际义务之意志时,即可立即予以承认”,但日本政府为此所设的种种条件,按照一般逻辑理解,很难让人置信是为了立即承认中华民国政府。(66)后来的历史进程亦可证明美国政府在回复此备忘录时所添加的“不拖延承认”的语句,应有所指。不可否认,当美国政府退出六国银行团,并表示要在1913年4月8日国会召开之际承认中华民国时,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件中亦曾出现“尽早承认中国新政府”的字样,仔细研读该类文件,可发现该语句出现的上下文环境均非要说明日本曾坚持立即承认中华民国,如果以此孤立的一句话作为论证的依据显然并不合适。其实,如仔细梳理此时日本的外交方针,显然这样的言辞无非是套话,紧随其后的是对中国政局不稳等情况的说明。(67)亦有材料证明,在日本议会中亦曾出现一种要求政府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的声音,但这些要求承认的声音并未为日本政府所采纳,当然不能作为证据来说明日本政府曾要求立即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美国国内早已酝酿着承认中华民国的舆论,威尔逊总统的当选为陷入停滞状态的承认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1913年3月18日,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同日,美国驻北京外交代办提议尽早承认中华民国政府。(68)3月23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致函美国国务卿白莱安(Bryan),希望美国承认民国政府。美国的行动无疑刺激了正以承认问题要挟中国的日本,日本认为六国对华借款与承认问题密切相关,而美国完全清楚谈判借款的前后经过,此时抛弃各国协同原则实出意外。日本此时已经意识到美国可能于近期内单独承认中华民国。在日本看来,美国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在通商贸易等方面获得某种特殊利益。(69)日本显然错估了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有研究指出,威尔逊之所以改变塔夫脱政府“与大国一致”的政策,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并非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是出于扩大美国对中国的道义影响,所追求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利益。(70)
日本一直力图掌握各国对华的承认主动权,并适时在各国之间联络信息,但日本尚未强大到取得压倒性优势的程度,从而完全掌控承认问题的进展。日本关于承认问题的备忘录更多关注的是寻求继承特权及各国之间的协调一致,并未依据当时通行国际惯例认真提出能为各国所公认的承认条件。在提出究竟必须满足何种条件才可获得各国承认问题上,英国比日本对该问题的考虑更为周详。继向袁世凯政府明确提出获得各国承认的条件后,英国在回答美国所提出的备忘录时再一次强调承认民国的条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选出大总统,临时政府成为永久政府。(71)后来事实证明,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所依据的正是英国政府所提出的条件。
4月2日,美国正式通知各有关国家,将于4月8日中国国会开幕日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美国致各有关条约国的备忘录内容如下:“总统委嘱本人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贵国政府通告:总统拟于四月八日中国国会开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贵国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采取同样行动。”(72)收到美国的备忘录后,英国首相格雷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建议对承认问题英国政府需坚持原有的观点,即列强之间的协同原则及各国在华既得特权及利益的正式确认。(73)日本亦明确表示“碍难满足美国政府之希望而采取同一行动”,并致电英国寻求支持。(74)虽然美国此时仍未放弃各国协同原则,但威尔逊总统并不因他国的反对而更改美国的决定。4月7日,英国驻美大使白莱士(Bryce)会见美国国务卿,白莱士被告知,尽管中国最近发生的宋教仁被暗杀事件以及召开国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美国先前所作决定的有效性,而且美国也意识到英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持有和美国政府不同的立场,但“美国政府必须坚持既定政策,于明日承认中华民国政府”。(75)
日、英、法等先后向美国表示应暂缓承认中华民国,德国则表态积极。(76)经与英国商议后,日本发表了有关承认问题的第二次倡议书,专门做出3点声明,其第一点系专门针对美国的单独承认而做出的:“如列强中之某国与他国意见不同,认为中国前途尚难预料,或者固执其本国之特殊见地,而始终不愿承认时,其它各国不应因此而妨碍其协同行动”,仍然希望美国之外的国家继续保持协调行动。(77)尽管美国直到5月2日才递交了承认国书,并不是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但影响广泛。在美国正式承认之前,巴西已于4月8日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袁世凯在致巴西的复电中称:“贵国此举,既属优待,又系首倡,敝国所以感之尤深也。”(78)
当美国已经确认要承认中华民国后,日、英两国为了尽可能从承认问题上得到更多利益,协谋筹划了袁世凯政府的对外宣言书。1913年5月间,巴西、美国、墨西哥等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尚未承认的各国在承认中国临时政府问题上也已经达成大致意见,惟有德、英两国在承认的条件上存在不同解释。德国政府在回复日本政府的建议时提出,“中国政府履行其以往所承担之国际义务乃属理所当然,完全不必作为条件提出”。而英国的见解则与德国不同,英国认为“应置重点于取得中国新政府关于履行上述国际义务之保证”。日本为了协调德、英之间的不同意见,建议英国“不坚持中国在承认之前主动向各国公使提出适当之书面声明,以使各国得到满足”。日本向英国表示,如果英国同意日本的提议,则日英两国政府“即可分头电示其本国驻北京公使就声明内容进行磋商,然后向中国政府征询意见”。(79)袁世凯政府很快同意了日本政府的提议。5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将中国政府的决定电告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已决定在向各国驻北京公使通告大总统选举结果之同时发一声明,言明中国政府将严格尊重其所承担之一切条约义务以及外国人根据既成惯例所享有之一切在华特权与豁免权等”,英国政府对袁世凯的声明果然表示大体满意。(80)
在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前,日本政府曾做出了种种努力,试图阻挠美国做出该项决定。此次美国政府似乎决心已定,不为所动,日本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发出了第二次关于承认问题的备忘录,其目的在于协调尚未承认的各国,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主导权。
1913年10月6日,英、俄、法、日等13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10月10日,袁世凯发表了宣言书:“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遵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友谊而保和平。”(81)至此,延宕日久的承认问题终获解决。辛亥革命期间的继承问题也落下尾声。正如后来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袁世凯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方面走得比南京临时政府还要远。相比于孙中山的对外宣言,袁世凯的声明已经完全超出了条约继承的范畴,更大程度上迎合了日本所提出的关于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条件的细目。事实上,这个宣言就是日、英等国的反复商讨后才得以确定的,文本的最初提出者是日本而非袁世凯政府当局。
仔细研读日本外交文件,可以发现,日本在承认问题态度上并非一以贯之,在某个阶段确曾有过一定的动摇,但在时间上绝非1912年7、8月间,其转变也并非放弃了坚持立即承认的主张,事实上日本从未提出该种主张。目前暂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动摇的时间大约在1913年3、4月间,动因是由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并宣布将承认中华民国,而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企图掌握对华外交的主导权。牧野外务大臣在致珍田驻美大使的电文中毫不掩饰日本控制外交主导权的欲望,“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与帝国政府关系綦重,为考虑将来各方面之对华政策,帝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保持主导地位,实属至关紧要”。(82)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外交演变与其力图获得的对华外交主导权密切相关。
自1912年2月发出有关承认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备忘录后,日本在承认问题上俨然成为列强之间的核心,除担当联系各国的角色外,还确立了以其所提议的承认条件为基础的外交共识。美国起初就对日本的备忘录有所保留,担心其故意延迟承认中华民国,迨至1912年7月,美国掀起一股承认的浪潮,这可谓对日本主导权的第一次挑战,但日本成功平息了此次承认浪潮。1913年3月18日,美国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紧接着通告有约各国将于4月8日承认中华民国,这些行动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美国的行动直接挑战了日本所努力经营的对华外交一致的原则,否认了日本在该问题上的主导权。
五、余论:承认问题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
学界认为,列强是支持袁世凯的,不论是在南北议和还是在当选总统问题上,袁都获得了列强或多或少的支持。虽然列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但总体而言,对袁支持的力量超过了反对的力量。当然,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其前后态度也有变化,不过,这并不影响对该国态度的总体判断。学界还认为,在承认问题上列强是处处为难民国政府的,不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北京政府,为了取得列强的承认似乎下了气力。综合现有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列强支持袁世凯,但又拒绝承认其治下的政权。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类似的现象:列强积极给予袁世凯贷款,但对承认问题却甚为冷淡。(83)翻开历史的细节,这其实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究其根本,无非在于有约各国试图在变动中的中国继续获得各种利益,只是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需要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并给予支持。在由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上,袁世凯显然先后击败了清廷和孙中山为首的政治力量,获得了列强的垂青。但选择由谁代表中国与是否立刻承认中国新政府并不矛盾,袁世凯虽然获得了列强的支持,但各国显然并不相信袁会使其在华利益获得最大化,借承认问题而获得袁政府的保证声明是他们共同的外交目标之一。
纵观承认问题的发展过程,列强固然有借承认问题保持自身在华各种特权的动机,但如果单纯站在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似乎说服力不够。有研究已经注意到此点,并举出美国的例子加以探究,认为至少美国在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并非基于经济利益考虑,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理想政治战胜现实政治的一个典型个案。(84)
在承认问题上,学界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湖北军政府——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这样一条线索上的历史节点,而忽略了清帝逊位以前晚清政府的政治存在及其依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有人认为这是以传统的革命视角进行的辛亥革命研究。笔者认为,循此视角而进行的承认问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贬抑湖北军政府及孙中山、袁世凯等为获得列强承认而进行的努力,并夸大列强在承认问题上对中华民国的刁难。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通行国际惯例,至少在清帝逊位以前存在这样的可能。就国际惯例而言,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时,清政府仍然是合法政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清帝逊位,属于过渡时期。如果我们以清政府为研究的立足点,那么列强的中立及湖北军政府交战团体身份的获得都属于革命力量获得的积极成果。列强的中立及对革命军交战团体身份的默认,是中华民国寻求列强承认的前奏。在寻求列强中立的同时,军政府在既有同盟会对外方略的基础上的对外宣言,奠定了此后中华民国外交的基调,尤其是在对待各国在华特权及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态度。
辛亥革命已逾百年,对于其进行的研究可谓是近代史学科中最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之一,即使在这样一个领域,学者们亦已意识到尚有许多问题未能理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需进一步扩展。张海鹏研究员提出,研究辛亥革命的发展历程应该和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深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认为应“跳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着重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章开沅教授形象化地提出了辛亥研究的“三个一百年”,认为目前的研究稍显具体,应将目光向纵深和宽度上发展。(85)这些提议无疑提出了辛亥研究的整体性问题,有研究者更是以此为题撰文呼吁。(86)就列强承认中华民国这一问题而言,如果我们跳出传统的以革命者为中心的视角,而是依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将目光扩大,关注到当时仍然处于统治地位的清政府,很多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此种研究不仅关注到了革命者,同样也关注到了被革命者,这样做不是为了所谓的研究平衡,而是为了还原辛亥研究本应具有的整体性,从而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注释:
①通史类综合性著作如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外交史专著如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论文有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6月),张水木《一九一三年列强对中华民国政府之外交承认》(《中国近现代史论集》2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王立新《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等。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48页。与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7—28页。
③参见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第242页。
④法国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参见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6月,第237—256页。
⑤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5),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
⑥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下,第275页。
⑦同盟会对外宣言共有7条: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给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见黄彦编《孙文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⑧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5),第152页。
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⑩关于国际法传入晚清中国的情形,可参见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11)程树德编:《平时国际公法》,上海普及书局1906年版,第65页。
(12)程树德编:《平时国际公法》,第65—66页。
(13)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下,第275页。
(14)《译革军都督致英署理总领事戈飞文》,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15)《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格雷文》,《辛亥革命》(8),第342页。
(16)《署理汉口英总领事戈飞呈英使朱尔典文》,《辛亥革命》(8),第343页。
(17)《署理汉口英总领事戈飞呈英使朱尔典文》,《辛亥革命》(8),第343页。
(18)《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葛磊文》,《辛亥革命》(8),第342页。
(19)奥本海认为,在承认交战团体场合,宣告中立或做类似不容置疑的行为,可以构成默示承认。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20)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2页。
(21)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7—368页。
(22)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4页。
(23)廖大伟:《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及其表现》,《史林》1992年第2期,第36页。
(24)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1页。
(25)《英国驻日大使与外务省石井次官关于清帝逊位后建立共和政府及其承认问题的谈话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
(26)参见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第253页。
(27)《英国驻日大使与外务省石井次官关于清帝逊位后建立共和政府及其承认问题的谈话纪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88页。
(28)列强在承认问题上的拖延及对中国的勒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137—148页。
(29)《本野驻俄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89页。
(30)《内田外务大臣复本野驻俄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90—391页。
(31)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208页,注释第51。
(32)《清史稿》,本纪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04—1005页。
(33)《外交部关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致各外交代表并万国保和会通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34)《内田外务大臣致本野驻俄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96页。
(35)《内田外务大臣致山座驻英临时代理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98页。
(36)Memomdum communicated by Mr.Yamaza,February 22,1912,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313/F8413.
(37)Sir Edward Grey to Sir J.Jordan,Foreign Office,February 24,1912,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313/F8413;《内田外务大臣致珍田驻美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00页。
(38)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Japanese Embassy,February 27,191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p.69.
(39)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40)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51页。
(41)关于此细目的分析请参见《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138—139页。
(42)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150页。
(43)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103页。
(44)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20页。
(45)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6页。
(46)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第451页。
(47)《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页。
(48)《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8页。
(49)《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8页。
(50)《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9页。
(51)《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30页。
(52)《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30页。
(53)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54)转引自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第254—255页。
(55)《驻旧金山副领事欧阳庚关于在美国各地演说力请承认中华民国事致外交部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31页。
(56)《英国驻日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1页。
(57)《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华公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2页。
(58)《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美国大使交来之秘密备忘录摘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3页。
(59)《伊集院驻华公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3页。
(60)《珍田驻美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5页。
(61)《加藤驻英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9页。
(62)《石井驻法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7页。
(63)《珍田驻美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8页。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137、139页。
(65)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第242页。
(66)《内田外务大臣致本野驻俄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97页。
(67)《牧野外务大臣复珍田驻美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28页;《牧野外务大臣致小池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39页。
(68)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3年3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
(69)《珍田驻美大使致牧野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8页。
(70)参见王立诚《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第144—145页。
(71)《加藤驻英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18页。
(72)Mr.Bryce to Sir Edward Grey,Washington,April 2,1913,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622/F15250;《珍田驻美大使致牧野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27页。
(73)Sir Edward Grey to Sir J.Jordan,Foreign Office,April 4,1913,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622/F15250.
(74)《牧野外务大臣复珍田驻美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28页;Sir C.Green to Sir Grey,Tokyo,April 4,1913,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622/F15589.
(75)Mr.Bryce to Sir Edward Grey,Washington,April 7,1913,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622/F16062.
(76)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3年4月4、7、8日。
(77)Sir Edward Grey to Sir J.Jordan,Foreign Office,April 22,1913,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FO371/1622/F18121;《牧野外务大臣致小池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39页。
(78)《大总统袁世凯关于巴西的承认复巴西大总统电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37页。
(79)《牧野外务大臣致小池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45页。
(80)《小池驻英临时代理大使致牧野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46页。
(81)《政府公报》第516号,1913年10月11日。
(82)《牧野外务大臣复珍田驻美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23页。
(8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84)参见王立新《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85)《做好辛亥革命研究的“三个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第1版。
(86)桑兵:《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问题》,《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标签:孙中山论文; 国际法论文; 军政府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民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华民国大总统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清代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袁世凯论文; 中华民国政府论文; 伍廷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