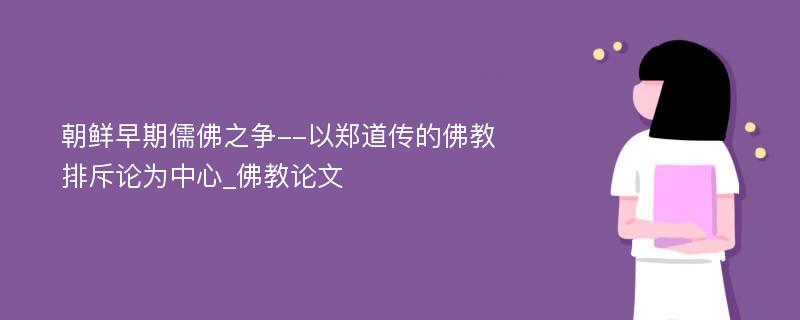
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中心论文,高丽论文,初儒佛论文,排佛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6—0143—04
在韩国史上,高丽末朝鲜初期,随着王朝的交替,政治上社会上的动荡加剧,思想界的主流,也从佛教转换到性理学。这对于高丽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而言,具有改革的性质,同时具有为朝鲜建国的思想奠基的历史意义。进而言之,在性理学被确定为朝鲜的国家理念以后,带来了全社会各阶层的总体意识的变化、革新及发展。
佛教没有提出能够克服高丽末期的矛盾的社会指南。宗教势力在膨胀,佛教界从教理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却不够充分,过于强调他力的功德信仰的副作用持续存在。而且,当时佛教界,戒律松弛,伦理败坏,无法免除批判。
高丽末期性理学者们的佛教批判,是从郑道传的排佛论开始并以体系化的论难而展开的。朝鲜王朝建国以后持续推进的抑佛政策,导致了佛教在经济上被剥夺的状态。特别是成宗代以后,士林兴起的同时,儒教文化对于佛教的压抑更为强化,佛教教团缩小为山间丛林,仅能维持命脉。
朝鲜标榜儒教立国,此理念的普及,以及儒教的生活样式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可反映出儒教理念是具有发展性的理念。但是,朝鲜初期的儒学者们也有把性理学理解为最高的思想和理念的闭锁性、局限性。例如,过于强调儒教的现世性和合理性这一优点,以及教条主义风气等,是其体现。对佛教、道教等性理学以外的思想和宗教,他们以神秘主义或异端乃至邪学而定性,加以强烈的批判和弹压。
学术界对高丽末朝鲜初思想史的研究,也对性理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它积极的历史作用;① 由于排佛论和为纠正它的偏颇而作出的努力以附属形式兴起,对于以郑道传为中心的排佛论者们的佛教观形成集中性的检讨。② 同时,这个时期的佛教史的研究,也主张朝鲜王朝的建国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佛教只以皮相形式存在。
本论文旨在检讨高丽末朝鲜初儒教和佛教间进行的思想论争,首先要以当时政治社会的变动为基础,对儒佛争论的背景做一下概述。为了更具深度,要分析一下在朝鲜建国中作出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郑道传的排佛论。他的排佛论是以居敬和穷理为基础的具有体系性和客观性的理论,比起一般的佛教批判来,具有为现实改革和朝鲜建国服务的功利性。甚至,在早期以朱子性理学的实践伦理为基准而作出的佛教批判缺乏客观性。因此,郑道传的以实践伦理和宇宙本体论为基础的佛教批判,在高丽末朝鲜初的思想史上既有它的意义,也有思想局限性。
一、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的背景
高丽末对于佛教的批判,恭让王三年(1391)演福寺塔重创问题是直接的起因。[1] 当时佛教界与权门势族紧密结合,独占了政治上社会上的权利。作为反面力量兴起的新进士类力图以性理学为基础来刷新高丽末期的社会,正在摸索社会改革方案。1388年李成桂威化岛回军之后,新进士类掌握政权,并且断然实行新政。以郑道传为中心的许应、郑摠、金子粹、朴础等成均馆儒生和儒学者们,在反对营造寺塔的上疏文中,全面批判了佛教界的弊端。[2] 出家僧侣的还俗、佛教界的五教两宗革罢和僧侣的充军、寺刹及其所属奴婢财用所在官司提出分属的要求,在朝鲜建国以后也是儒学者们在排佛疏中显示出来的一般性的争论点。
14世纪之际的高丽,王朝体制几乎全部崩坏,社会矛盾激化,陷入总体的危机。贵族、官僚、寺院的土地兼并引起了农民经济的破产,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高丽政府的中央集权弱化,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的极度虚弱。恭愍王曾经试图改革政治,但因贵族势力的抵抗以及红巾贼和倭寇的入侵而失败。因为李成桂的失权,改革派儒臣们以田制改革运动为中心,断然施行了正式的改革措施。儒臣们政治上、社会上的改革目标达到某种程度以后,对寺院经济和寺院旧势力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追究。佛教寺院拥有巨大的经济力和劳动力,成为侵害国家经济和国役制度的主要原因。因此,寺院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改革派的指导理念之儒教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佛教的排斥也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兴起的与寺院经济的弊端或是佛教徒的堕落相关联的批判在高丽朝并不是第一次。恭愍王初李穡等已经批判了寺刹滥立和僧侣过多的现象,随着儒教的振兴,对于佛教的批判逐渐高涨。
排佛运动的阶段性进展是从急进的改革派开始掌握实权的昌王代开始的。赵仁沃、赵浚、尹绍宗等不仅仅攻击佛教的末弊,对佛教教理本身也加以指责。更甚者,成均馆的儒生们加强了排佛运动。但是比起恭让王,儒臣们的排佛运动还算温和,并没有取得显明的成果。但是朝鲜建国以后,排佛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而进行的。在实践伦理和国家社会层面上的批判,根据是华夷论,那是对祸福论的否定。在朱子派性理学的经史子集的注解中,排佛论的根源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
对高丽末儒学者的排佛论和朝鲜初议政府、六曹、司宪府、司谏院、集贤殿以及书云观所呈献的排佛疏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个时期排佛论的背景不仅是政治、社会、经济,而且是从思想的立场上以总体的形势形成的。在这之间,实践伦理和国家、社会层面上的佛教批判,是最为激烈的,“佛切断父子的亲情,作为匹夫抗命天子,灭除君臣之义”[3] 败坏了三纲五伦。往常所合称的三纲五伦是所有性理学者们所强调的人伦的核心,形成著者的小学根源。小学是指有关大学以前,修身大法的著述,是人伦教化所必须的教本。[4] 高丽末朝鲜初儒学者们对小学的重视意味着,对性理学的形成造成影响的中国元代儒学者许衡对小学的尊重以及儒教本身所具有的日常实践的性格开始发挥影响。同时,以佛教的弊端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伦理的堕落为背景,朱子学的实践伦理首先受到瞩目。在朝鲜初期,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小学教育受到了奖励。③ 但是,对于这个时期性理学的理解,比起修己来,着力点放在了治人上。为了物质上、政治经济层面上、特别是富国强兵的需要,对于政治经济的改革很关心。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和民本理念,还有建设立脚于周礼的儒教理想国家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因此,他们自封性理学为实学和正学,佛教作为异端被彻底排斥。[8] 因此以郑道传为中心的建国主体势力的排佛理论有很多局限。无视佛教的宗教性,在朝鲜建国以后国王和王室的崇佛事例中也显现了其后遗症。郑道传的排佛论,在当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思想上虽然形成了体系,但它是立足于儒教至上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思想,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实践伦理和佛教批判
郑道传的佛教批判在他所著述的《心问天答》(1375)、《心气理篇》(1394)和《佛氏杂辨》(1398)中变得理论化、体系化。《心气理篇》是对道教和佛教进行哲学性的攻击,主张性理哲学的优位性的册子,《佛氏杂辨》是在性理学的立场上批判佛教哲学的排佛书。这些排佛书,认识到了佛教的反伦理性与儒教的宇宙论或认识论相冲。例如,佛教认为自然现象不真,是假象、幻影,进行否认;同样,至亲以及君臣、夫妇关系这样的人间关系也是假合,对人伦进行否认。因此,佛教毁除伦理,使风俗堕落,就好像使人类沦落到禽兽的世界,它被断定为人伦的蟊贼。[6] 儒教伦理是将人间社会和人间关系的问题,在社会道德上变得更有价值。其中重要的一点,它是使人间关系与天理——即善,附合而成的。更甚者,将政治、社会、哲学等思想体系的基本核心放在伦理原则上的郑道传,对佛教的实践伦理无法容纳。[7]
另外,郑道传对佛教的反国家社会性作出的批判,是与高丽末朝鲜初社会经济的欠缺相关联的,这与佛教实践伦理上的不足同样严重。例如,郑道传对僧侣们说:“你们在华丽的殿堂和宽大的住宅中,穿著阔气的衣服,吃着好的食物,舒服地坐着享乐,这和王者的待遇一样……将大约相当于平民十家的财产,在一个早晨全部消费掉……”[8]
当时佛教界因为寺院经济的扩大、寺院奴婢的增加,与社会构造的矛盾相应,意味着佛教丧失了自净能力。高丽末,寺社建立的禁止④ 寺院施纳的料物库所属宫庄土的没收[9]、朝鲜初太宗代的寺社革除寺社田民的消减⑤ 等的排佛政策,是必然的结果。
另外,与这样的社会经济问题所关联的儒者们的批判,是与高丽末朝鲜初的悬疑问题联在一起的,《职分论》和《经世论》认定了一定的相关关系。例如,郑道传曾说过:“对一个人来说虽然吃是件大事,可是苟且而食有损义理。”天子和公卿大夫治理百姓,农工商人卖力干活,儒者以在家行孝道、在外恭敬行事、卫护先王之道、传道授业的形式而存在。[8] 那些不能进入拥有天职,接受天养而生存的天子、公卿大夫、士农工商的行列的奸民即“游手之民”即是数十万的京城居住民、僧侣、闲散子弟、公役庶民、巫觋、才人等。[10] 僧侣掌控了农业,即重要的生产手段、国家经济的源泉,在当时是非生产性和浪费性的代表部类。对此的不满成为佛教批判的重要原因。它与当时的社会问题中所显现的人民流亡也有所关联。即由于自然灾害、赋税制度不合理以及寺院经济的扩大等自然的社会的原因,使得农业生产不安定,人民面对没落及流亡的境地。
当时儒学者们对于人民的流亡的言论,以《孟子》中所说的恒产和恒心为基础,考虑到人民具体的恩惠。在这之中,以郑道传为中心的急进儒学者们认为:“虽然人性上不管是谁都是善良的,但没有恒产的人,受到寒冷和饥饿逼迫,因此不再注意礼仪和廉耻。”[11] 只有人民拥有充足的物业,才能发展伦理道德。像这样的谋求能够保障人民恒产的儒学者,认为僧侣的无为徒食以及同土地制度结合的寺院经济制度的扩大等,只会给成产手段带来更大的反作用(减半)。
高丽末朝鲜初儒学者们,对于与此类似的佛教界社会伦理的弊端的指责和对策,在当时社会混乱的处理和国家安定的层面上,在作为改革的思潮而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这一点上,可以认定其价值。
三、道统论和祸福说
另外,认识到佛教不注重世俗实践伦理、国家社会性、强调宗教功能的普遍性,儒学者对于由此定型化而形成的祸福说,逐渐转向批判。当时的祸福论批判,是随着寺院的滥设和寺院田产的扩大,国家财政有可能陷入枯竭的境地而展开的。在这里,性理学的正统意识,即道统论和宇宙本体论作为此理论的基础,非常强硬。
从孟子摒斥杨墨推崇孔子开始,到汉朝的董仲舒和唐朝韩愈以及宋朝的程子、朱子,全部都抓住此道,摒斥异端,成为天下万世君子⑥。
道统论的渊源,是孟子针对墨子的邪说天下横行的形势,担心孔子的道无法显现而作的阐述。唐朝的韩愈,使道统论得到了发展,并批判了佛教。朱子继承韩愈的道统论,阐述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和孟子的道的传授过程。宋代朱子学的道统论成为朝鲜的性理学的精神支柱,加上空间上世界中心观念为前提的华夷观,儒教的正统论确立起来,为攻击佛教、道教以及与异端连接的政治势力,形成了理论的借口。
郑道传从道统论出发指责道:“佛氏的情况,他的言语高尚且美妙,因为他出入于性命和道德之间,所以迷惑人的程度比杨、墨还要严重。”[12] 这里,儒教=正统,佛教=异端意识,以“夷狄之教”而规定佛教,置于绝对对立的地位。更甚者,郑道传不仅以排斥异端为己任,而且到了以的朱子传人的身份在道统谱系上为自己编派位置的程度,以此来彻底进行正统的确立和佛教批判。⑦ 他说:“从后汉的明帝开始,推移到梁武帝、唐太宗,中国历代帝王因为崇尚佛教,而使政事和社会风俗变得紊乱”,以此可证明佛教信仰的全无效用。“夷狄之教”传入中国后,王朝短命,“佛法入中国年代尤促”的批判,最终导致当时的儒学者们以强烈的儒教优越、中心的认识为根据,忽视排佛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⑧
像这样的道统论,以祸福说的批判为前提,形成了实际上对佛教宗教性的全面否定和弹压。特别是,同因果报应论结合的祸福论,与宇宙本体论相对峙,大大地压缩了儒教的宗教机能。性理学的宇宙本体论认为,在同阴阳五行的气运结合分离之中,处于生成及消灭之中的人或事物的个体,拒绝接受通过轮回而持续存在的精神不灭说。[13] 例如,因为太极的动静生成阴阳;在阴阳中,出现老阳、少阳、老阴、少阴的四象,阴阳变合;因为五行的变化、生生不息,所以一瞬间也不曾停止的创造和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发展。[14] 受此影响的人类或万物,以魄和魂构成。人类的死亡意味着,魄和魂气的分离、分散。魂魄一旦分散,就不可能重新结合生成人物。[15] 最终,人间的形体和精神,全部因为气而形成,气凝聚生成形体,随之而产生精神;气离散则形体变没,精神也会随之消失。宇宙万物的差等,以及人间内部的不平等是气的差异的结果——如此理解的儒学者们对“人间的吉凶祸福也和阴阳五行的气没有关联是错误的;肉身消失,精神也可以永生不灭,可以以其它形态再生”的精神不灭说进行了批判。
根据他们所说,频繁地举办佛事,可以镇压住有本事的妖异;不放下、不断掉香的话,可以无限增大供养功德;但并没看到天灾和地怪的消灭。还有,虽然祈福的人们,为了可以活得更长不惜万金祈求长寿,但并没有看到活到百岁的证验。⑨
儒家宇宙本体论的“生生而无穷说”,从理论上否定了佛教的精神不灭说。在引用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祸福说和因之而增多的佛事进行了指责。即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国家财政枯竭的原因是在虚妄的祸福说上,试图进行源泉上的批判。
最终,以郑道传为中心的高丽末朝鲜初儒学者们否认了因气的差异而左右人间的吉凶祸福立场的绝对性、佛教的精神不灭说即因果报应和与之互为表里关系的祸福说。
四、高丽末朝鲜初排佛论的历史意义和局限
郑道传是经历了高丽末朝鲜初的历史转换,认识到了高丽社会累积的弊病,并进行改革的人物。他的改革立场在朝鲜王朝有开创性。朝鲜王朝不仅以易姓革命的形态出现,而且王朝开创后政治制度及社会改革等广范围的形态变得更为具体化。郑道传对于高丽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方案,依据的是元朝重新兴盛的性理学。这一点在他的排佛书《心问·天答》、《心气理篇》、《佛氏杂辨》等中,很好的体现出来。他在这些书中提出,性理学比起佛教,不管是在理念的层面上,还是历史上,都更具合理性。
《心气理篇》提倡的心功和养气功效,虽是佛教、道教的主张,但他强调了心和气如果没有理(人伦)的话是不可能存在的;是同禽兽没有区别的,最终显示了佛教和道教的非现实性和反伦理性。二教的反社会性是可以依据性理学来克服的。郑道传批判异端的强硬立场,在《佛氏杂辨》中得到了更具伦理性的、历史性的展开。他对佛教的轮回说、因果说、慈悲说、真假说、地狱说、祸福说及心性说,及诸般学说的虚构性进行了攻驳。同时,对自身的排佛论进行的历史性论证就是佛法外来、事佛得祸、舍天道而谈佛果、事佛甚谨年代尤促等的项目。但是,郑道传的排佛论也具有只考虑到性理学观点的局限性。
特别是,郑道传的佛教批判论虽然受到东亚细亚世界的推崇,在思想的层面上具有很重要的意味[7],但在性理学的确定期,没有超出教条主义的范畴。即此时期儒学者们对性理学的理解是和时代状况关联,不是穷理的追求,而是集中在以居敬为中心的实践伦理。因此,没有发展到理论层面上的完全理解,或是自己创新的阶段。例如,佛教批判的大部分沿袭了唐代韩愈的《原道》、《佛骨表》及宋代性理学者的排佛论,和《夷狄之法》、《无父无君之教》、《祸福说》等中国排佛论,没有主体上的省察。更甚者,以朱子性理学为中心的佛教教理的全盘性批判论,彻底否定了佛教是和儒教一样包含着普遍性的伦理观和宗教观这一事实。郑道传的排佛论,其热度和深度是卓越的,虽然也可成为他对于佛教的理解达到某种深度的证明,但系自身述怀,批判理论在儒教的立场上形成,主观上的臆测和独断较多,在当时佛教界,他的疑问明显得暗示。例如,他在排佛论展开的过程中说自身的论理是牵强附会的,称颂华严的法相一体和理事无碍论。还有称颂僧侣湖长老的端庄容貌,安详行止,有度的言语,对于教的“作用是性”,也曾经请求指教。
另外,虽然初期寺院的数目缩小,佛教宗派也并合了禅宗和教宗二大宗教,但是佛教所具有的宗教性本身并没按郑道传的意图而消失。太祖将王师作为无学,在宫中供养了200名僧侣的饭食以“法华经”3部金字写经,为高丽王室宗族的冥福祈祷。同时,曾施行抑佛策的世宗以及元年(1419)老上王定宗辞世时,在兴德寺、兴天寺、津宽寺等处举行了七斋。此外,朝鲜初期,王室和士大夫家并没顾忌排佛政策,进行了救病和以四十九斋为首的多样的佛教仪式。最终,高丽末朝鲜初期,佛教和佛教界在排佛论和政策下也施行了其宗教的机能。
注释:
①李泰镇.朝鲜性理学的历史性格[J].创作和批评(第9卷第3号)1974.韩永愚.朝鲜前期研究的诸问题——以身分·土地·思想史研究为中心-[A].朝鲜前期社会经济研究[C].乙酉文化社,1974.
②琴章泰.郑道传的辟佛思想和其理论的性格[A].东乔闵泰植博士古稀纪念论丛[C].1972.宋昌汉.对于郑道传的斥佛论——以佛氏杂辨为中心[J].大邱史学1978(16):15,金海荣.郑道传的排佛思想[J].清溪史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4.李延柱.关于权近的佛教观再检讨[J]历史学报.1991:131,
③文喆永.朝鲜前期儒学思想的历史特性[A]韩国思想史大系(4)[C].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99~134.文喆永.高丽末新兴士大夫的性理学受容及其特征[J].韩国文化1982(03)。
④高丽史(卷38)恭让王1年2月条[M].
⑤朝鲜王朝实录(卷10)[M].太祖5年11月癸丑条[A].
⑥高丽史(卷120).金子粹列传云:自孟子辟扬墨尊孔氏以來,汉之董子,唐之韩子,宋朝之程子,皆扶斯道,辟异端,为天下万世之君子也。
⑦高丽史(卷119).郑道传传云:结庐三角山下,讲书学者多从之,常以训后生,辟异端为己任……
⑧郑道传.佛法入中国[A].事佛得祸[A].事天道而谈佛果[A].事佛甚谨年代尤促[A]三峰集(卷5)[C].
⑨高丽史列传(卷第30)云:其曰:张皇梵采 能压妖异,而降香绛绎,供亿浩广,未见天灾地怪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 能使人寿,而不惜万钱,俾之祝寿,未见百龄之验也。
标签:佛教论文; 高丽国王论文; 郑道传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高丽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学论文; 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