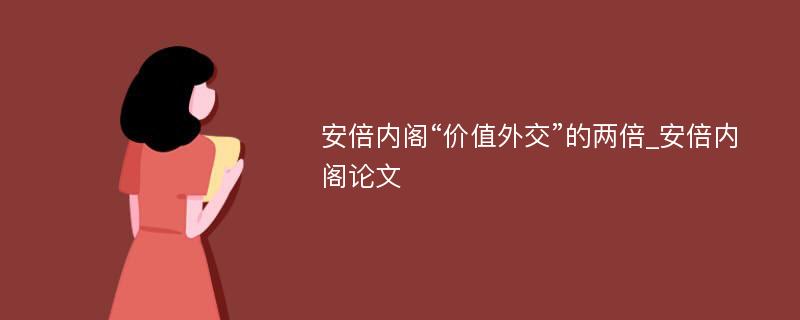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内阁论文,价值观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是冷战后即有所体现、在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阁(2006年9月~2007年9月)时期明确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针:这一外交方针有牵制中国的着眼点,其背后不乏冷战思维甚至反共思维,对此学界已多有关注和批评。①但是,更重要的是,被用作“价值观外交”招牌的“价值观”本身也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近年来,日本在“价值观外交”中宣传的“价值”形式大于内容,即使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相比,也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第二次安倍内阁(2012年12月~)再次将“基本价值观”当作外交方针之一高调提出,但安倍用以区分国际阵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在日本的内政外交实践中并未真正体现,“价值观外交”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名义下的战略、利益导向而非价值导向。事实上,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价值观外交”与战后日本的一系列外交方针具有连贯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安倍在2013年以来多次强调“历史认识和外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②但是,对于战后日本而言,不论是外交方针或国内政策的变化,还是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关系,都无法抛开历史认识问题去简单看待。毋宁说,上述变化、关系背后的结点之一就是历史认识问题。本文将梳理两次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的方针与实践,通过国际与历史比较概述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特征与本质,并对其与日本政治及“历史认识”的关联进行初步探讨。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方针 2012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并取代民主党上台执政,组成了第二次安倍内阁。该内阁延续了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的“价值观外交”方针,对“价值观”内容的表述基本一致,但对“价值观外交”的定位随着外交整体方针的侧重而稍有不同。 2006年首次当选时,安倍着力强调“美丽的日本”,在外交方面则提出了“有主张的外交”。在2006年9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称:“在进一步增进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同时,作为亚洲的民主国家,为将自由社会的范围扩展到亚洲与世界,要与澳大利亚、印度等与日本共有基本价值的国家开展首脑级的战略对话。”不过,该演说在涉及外交的其余部分都没有提到“价值观”,“价值观外交”也并非唯一被提及的外交方式。③在2007年1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再次提及“在与东盟各国和共有基本价值观的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要扩大首脑间的交流”。这种“价值观外交”被表述为“有主张的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加强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各国之间的合作,构筑开放和富有创造力的亚洲,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以此作为三大支柱,进一步推进为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真正贡献的有主张的外交。”④但在2007年9月的施政演说中,通篇未出现有关“价值观”的内容,在外交部分强调的是“有主张的外交”,并主要是结合“日本的国际贡献”来阐述的。⑤总体来看,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价值观外交”已被用来处理与印、澳的关系。同时,除了被当做“有主张的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外交”,为建成“美丽的日本”,“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也仍是日本着力推动的方式。 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价值观外交”的定位有所变化。在2013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称:“外交不仅仅局限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上,而是在地球仪上俯瞰整个世界,以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开展战略性的外交为基本。”虽然安倍此前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发表了“对东盟外交五原则”,其中第一条即称“要与东盟各国一起,为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的确立与扩展而共同努力”,⑥但在该施政演说涉及东盟的部分并未提及“价值观”,而只称“面向2015年的共同体构筑,强化与作为增长中心而持续发展的东盟各国的关系,对于地区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也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从本次访问开始,今后也要开展将世界局势纳入广阔视野的战略性外交”。⑦ 在2013年2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称:“我的外交是有原则的。此前在访问东盟各国之际发表了对东盟外交的五原则,而我的外交是以战略性的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守卫国家利益的有主张的外交为基本的。”但该演说亦未在涉及东盟的部分重述“价值观”,而是称“以紧密的日美关系为基轴,深化与澳洲、印度、东盟各国等亚洲海洋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在安倍的历次同类演说中,“价值观”首次出现在关于美国、韩国的表述中。⑧该演说称,“在开放的海洋上,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有必要不断强化这种关系”,而“韩国是与日本共有自由、民主主义等基本价值与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⑨ 事实上,以上“价值观外交”的表述并非全然属于第二次安倍内阁的“创新”。2007年安倍辞职后,福田康夫首相并未继续强调“价值观外交”,而是侧重于在美日同盟基础上加强与邻国的协调。不过,福田内阁外相高村正彦虽不赞成以“价值观”摆出“举刀过头”的姿态,但在主张对华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也称“韩国是我国的重要邻国,与我国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并面临朝鲜问题等共同问题”。⑩2008年麻生太郎组阁后再次回归对“自由繁荣之弧”的强调。而2009年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后,对“价值观”的态度表现出转变的过程:鸠山由纪夫首相当选前即公开表示讨厌“价值观外交”,(11)任内主要强调重视亚洲、增进信赖;菅直人首相也表示要重视亚洲,但在2010年8月对韩国单独发表的“道歉谈话”中表示,“在当今的21世纪,日韩两国是共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等价值的最重要的关系紧密的邻国”;(12)野田佳彦内阁则重新开始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其实践“价值观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安倍、麻生时代提及的印、澳、东盟国家(如菲律宾、印尼等),还涉及法国、加拿大、秘鲁、韩国等。(13)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提出“价值观外交”后,虽然主张从现实出发重视亚洲的几任内阁对此未加强调,但“价值观”仍被用来表述与韩国的关系,民主党政权后期甚至进一步扩大了“价值观外交”的涉及对象。第二次安倍内阁可谓“不计党派、不计派系”地吸纳了上述言行。 2013年10月的施政方针演说形式相当独特:该演说除“日美同盟”、“驻日美军整编”、“绑架问题”的字样外,通篇都未提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强调“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强化首相官邸的外交、安保政策司令部功能”、“在以长远眼光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确保国家安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这些内容虽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即已提出,但在施政演说中如此集中露骨地强调尚属首次。值得注意的是,该演说在主张“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基调上,继续提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加强与共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价值观的各个国家的合作”。(14) 2014年1月的施政方针演说在政治上最为突出的内容是“积极的和平主义”:“……积极的和平主义,是我国最初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贯彻的基本思想。其司令部就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对于集体自卫权、集体安全等,将基于‘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的报告,讨论应对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该演说首次明确将“积极的和平主义”与“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除再次强调“韩国是共有基本价值与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外,“价值观”已被当作“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说辞:“若无自由的海空,就无从期待人员往来、贸易活跃。民主的空气绽放人们的‘可能性’,生发出创造力。我相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原则正是给世界带来繁荣的基础。为了今后日本与世界的发展,要与共有这些基本价值的国家深化合作。不用说,其基轴就是日美同盟……在基于国际合作主义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之下,日本将与美国携手,为世界的和平安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5) 综上,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价值观外交”所涉对象由印、澳等国扩大到包括美、韩在内的更多国家,并与“战略性外交”、“守卫国家利益的有主张的外交”等并列表述。相比第一次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在定位上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在形式上的针对性有所模糊,但其指向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尤其需要重视的是,所谓“价值观外交”始终是处在“有主张的外交”、“战略性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框架之下的。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实践 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2007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范围界定为“从北欧诸国开始,经波罗的海诸国、中东欧、中亚高加索、中东、印度次大陆、再经东南亚联结东北亚的地区”。具体而论,“要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与同日本共有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盟国美国的合作自不待言,加强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G8、欧洲各国及欧盟(EU)、北约(NATO)的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基于普遍价值形成繁荣稳定社会这一‘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基本想法并不局限于上述地区,也应当让中国、中南美及非洲共有”。“将与尚无协商框架或机制尚薄弱的国家加强对话。具体包括CLV诸国(柬埔寨、老挝、越南)、V4诸国(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GUAM诸国(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16)。也就是说,此处强调的“价值观外交”对象以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印度为主,兼及东南亚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与此同时,“自由与繁荣之弧”是作为“外交的新支柱”与“强化日美同盟,重视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合作,强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关系这些既有的日本外交支柱”并列的,(17)俄罗斯、中国、韩国、中南美、非洲并非“自由与繁荣之弧”包含的对象。 如前所述,第一次安倍内阁的主要着眼点是“有主张的外交”,安倍在诸施政演说中并未像麻生演说或《外交蓝皮书》那样着力强调“价值观外交”。不过,在外交实践上,安倍提及“共同价值观”的对象又并不仅限于澳、印两国。依据外务省记录,第一次安倍内阁在首脑会谈中的“价值观外交”有以下几个特点。(18) (1)“价值观外交”的对象除澳、印两国外,集中涉及的是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捷克、罗马尼亚),《外交蓝皮书》中未提及的韩国也被包括在内。有趣的是,虽然意大利、瑞士亦实行自由民主制,但首脑会谈记录未显示安倍提及“共同价值观”;而在与美国的多次会谈中,除日美韩早餐会的三边场合外,也未使用“共同价值观”的表述。 (2)对东盟各国(多为民主制)虽有谈及民主法治等内容,但除对新加坡外,会谈中未使用“共有基本价值”的说法。对中东、非洲、拉美国家(多非民主制)则基本未谈及价值观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是否“共有基本价值”并未成为经济、政治、安全合作的障碍。 (3)与“价值观外交”相比,“伙伴关系”是更加值得关注的外交实践。被日方界定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战略性全球伙伴”)、越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沙特(“战略性多层次的伙伴关系”)、埃及。而韩国、蒙古、相关东盟国家(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及欧洲国家(丹麦、比利时、捷克、罗马尼亚)被界定为“伙伴关系”(“最重要的伙伴之一”、“综合伙伴关系”、“可信赖的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广泛的伙伴关系”、“共有责任与目的的伙伴”、“共有基本价值的伙伴”等)。此外,俄罗斯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伙伴关系”,利比里亚为“国际场合的重要伙伴”。可以看到,“伙伴关系”并不拘泥于是否“共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战略伙伴关系”当中,“战略”的考量明显要大于“价值观”的考量。 (4)“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外交、安全合作等方式并行,且通常并非首脑会谈中最主要的内容。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首脑会谈中普遍谈及的是经济援助与合作、朝鲜问题、联合国改革及日本“入常”、环境问题、文化交流等。 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价值观外交”除在施政演说中的定位有所变化外,在外交实践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据日本外务省主页,自2012年12月至2014年4月上旬,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实践有如下一些特点。(19) (1)提及“共有基本价值”的对象主要是欧洲国家(仍是对美国基本未提、对意大利未提;此次除英、法、德外,对爱尔兰、西班牙亦提及),对“V4”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及其他中东欧、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土耳其)尤有积极强调。此外,对加拿大、新西兰、密克罗尼西亚、巴西(对阿根廷则未提及)、牙买加亦提及,对马尔代夫写入了两国声明。由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日韩首脑会谈尚未实现,但将韩国当作“价值观外交”对象的思路并未改变。(20) (2)对澳、印等国更强调“战略伙伴关系”,而非“共同价值观”。例如,在与印度的多次首脑会谈中均强调了两国的“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但均未提及“共同价值观”,相关内容仅写入两国声明。(21)对于东盟各国基本未谈到民主法治问题,对新加坡亦未谈及“共有基本价值”,但对这些国家都谈及了“战略伙伴关系”或“伙伴关系”。 与第一次安倍内阁相比,被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除澳大利亚、印度、越南、法国之外,还包括蒙古、印尼、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墨西哥、欧盟、柬埔寨。此外,新西兰为“战略合作伙伴”,南非为“战略合作关系”,爱沙尼亚为“共有战略利益”。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为“全面伙伴关系”,吉布提(为自卫队应对海盗提供合作)为“战略上极其重要的伙伴”,而加拿大、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拉脱维亚、波兰、西班牙、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巴西、爱尔兰、老挝、莫桑比克、阿曼等国为“伙伴关系”(“亚太地区的伙伴”、“可信赖的伙伴”等)。可以看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仍并非以“共同价值观”为标准,英、德等此次未被列入其中。 (3)对中东、非洲、拉美国家仍基本未谈及价值观,对非洲国家更强调“稳定发展”。2013年6月非洲开发会议期间,安倍与38个非洲国家进行了首脑会谈,期间虽对若干国家的民主进程表示了肯定,但除对毛里求斯称“两国共有人权、法治、民主”之外,皆未以“共同价值观”名之,有非洲国家称日本为民主先进国时亦未积极回应。与此相对,非洲国家的“稳定发展”则是被反复强调的。 (4)“价值观外交”仍主要体现为安全合作、经济外交的补充。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首脑会谈的主题除经援合作、朝鲜问题、环境问题、文化交流外,还侧重于能源资源合作(尤其是日本的核电输出)、南海问题、反恐合作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自民党参院选举获胜后,“集体自卫权”等修宪诉求立刻成为重要主题:2013年7月22日参院选举结果公布后,安倍立刻开始在25~27日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的首脑会谈中为“集体自卫权”或修宪“谋求理解”。其后,安倍在大多数首脑会谈中(包括泰国、越南、印尼、匈牙利、欧盟、爱尔兰、土耳其、阿曼、俄罗斯、瑞士、阿联酋、沙特、爱沙尼亚、马尔代夫,以及“达沃斯论坛”等)都强调说明了“积极的和平主义”。 综上,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实践既有基本一致的延续性,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其延续性主要表现在:除用于与澳、印两国加强联系外,“价值观”也被用来与以欧洲为主的其他国家拉近关系;同时,“价值观外交”始终是与“经济外交”、“政治安全合作”、“文化外交”乃至“资源外交”(获取资源)、“核电外交”(推销核电)等“非价值观外交”并行的,“价值观”并未成为上述合作或“伙伴关系”的先决条件或障碍。而变化主要表现在:与第一次安倍内阁相比,第二次安倍内阁对欧洲国家继续积极提及“基本价值观”,但对澳、印、东盟则开始更直接地强调“战略伙伴关系”而非“价值观”;与非洲国家的互动亦可进一步印证“战略性”重于“价值观”的倾向。耐人寻味的是,安倍在与相关领导人会谈时,不仅称与欧盟“共有基本价值观”、是“战略伙伴关系”,(22)还特别强调“日本与北约是共有基本价值的伙伴”。(23)这一强调可谓充分体现了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性质。 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特征与实质 日本虽不断强调与西方国家“共有基本价值观”,但即使其“价值观外交”本身,也与美、德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有显著区别。在西方学者看来,“所谓‘价值观外交’是一个与‘现实利益外交’相对的概念,也称为‘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意指一国采取对外行动的直接出发点不是(或不全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本国的价值观体系,以及扩展本国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24)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实践基本遵循了上述定义:虽然各国都默认不会将价值观与经济利益对立,但会为拓展价值观而弱化乃至暂时放弃部分利益诉求。相比之下,日本的做法有相当明显的不同:在面对欧洲国家时,日本会积极提及“价值观”;在对待印、澳等国时,日本的宣示重点从“价值观”转向了更直接的“战略关系”;而在对待“价值观”相异的对象时,日本会以是否有利来衡量,基本不倾向于让“价值观”影响利益诉求。 以近年来西方国家与日本对津巴布韦的外交为例。2005年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受到广泛关注。在2007年12月的第二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上,默克尔指责津巴布韦政府侵犯人权,引起了非洲国家的不满。(25)2009年6月,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向津巴布韦提供援助,但有关援助将取决于津巴布韦的民主进程。(26)实际上,这种不惜以非洲国家的不满为代价的“价值观外交”并非默克尔时期才开始。即使是在被默克尔批评为“忽视人权和民主”的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也曾在2002年以津巴布韦压制反对派为由几乎停止了对它的发展援助。(27)此外,英、美等国多年来均在以民主、人权等理由指责和制裁津巴布韦。作为其结果,2013年7月,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威胁将制裁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在津企业,以抗议其长达十年的不公正制裁。(28) 与此相对,日本对津巴布韦的态度要“宽容”得多。2013年6月非洲开发会议期间,安倍在与穆加贝总统会谈时表示,“欢迎穆加贝总统第三次访问日本”,“对津巴布韦面向大选进程的着实进展表示好评,期待穆加贝总统连任”,“着眼于与津巴布韦双边经济合作的实质性恢复,决定开展有关灌溉设施的调查,并计划派遣援助协调顾问,希望这些支援能够为津巴布韦的政治、经济状况稳定作出贡献”。(29)这里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民主”,与英美等国明显有较大距离。 也就是说,西方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看似都是以价值乃至意识形态划界,但西方的“区别对待”更重在以某种价值标准去批评与之相异的国家,而日本的“区别对待”是对有某种价值标准的国家积极提及价值、对与之相异的国家并不强调价值。虽然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同样有拓展本国利益的出发点,但日本的“价值观外交”除战略、利益导向之外,在方式上首先就更为显著地存在双重标准、两面下注的问题。这只能说明日本自身并不信奉其所宣扬的“价值观”。 纵观战后以来的日本外交,可以看到相当丰富的“××外交”概念。从外交依托方式来看,有20世纪50年代以战后赔偿开始、60~70年代发展确立的“经济外交”,70年代开始重视、80~90年代日益强调的“文化外交”,21世纪作为“文化外交”拓展的“动漫外交”(“酷日本战略”),以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价值观外交”。这些外交方式看似各不相同,但其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同时,虽然外交方针在内阁更替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但外交的保守路线体现出较强的延续性。事实上,除“酷日本战略”强调动漫等较为新颖的载体之外,包括“价值观”在内的其他外交方式自战后以来都是综合运用的,党派或派系更替基本未影响这些手段的延续,(30)外交方式侧重的变动也并未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本框架、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以确立加强日本“自主”国际地位为长期目标的国家利益追求。 关于日本外交背后的利益诉求,国内外学者已多有论述。但是,有以下两点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一方面,战后日本各种外交方式延续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赔偿外交是为了打开经济局面,经济外交是为了继续解决重返国际社会的限制,文化外交是为了改善“经济动物”的形象,酷日本战略是为了进一步增强青年一代对日本的好感,价值观外交是为了拉近与重要伙伴的关系,无论哪一步都是以实用地达到目标或解决问题而被推进的。另一方面,这些外交方式的实用主义背后隐含着一个统一的问题,就是回避对自身的正面反思。为什么战后日本多有经济贡献、文化魅力,却一直需要“重返国际社会”、“改善国际形象”?这显然无法只用“日本的危机意识”来解释,也不能完全以“日本的战略考量”来涵盖,更不应归咎于其他国家对日本“不够宽容”。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外交蓝皮书》都未正面将历史问题列为外交课题出现的动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至今缺乏对历史(及现状)的反思是造成日本国际形象反复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出于回避反思的心态,才有了面对问题时外交方式的步步演进;由于不论是经济援助、文化渗透、动漫影响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实用主义逻辑下才有了重新以不乏冷战思维的“价值观”为包装来发展伙伴关系的选择。但是,这种回避问题的方式归根结底是一种“死循环”,只能将日本带回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想要“超越”并认为已经可以“超越”的“战后”乃至“战前”。 在分析近年来日本的外交变动时,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等“中国崛起”的进程是常被提及的因素。自野田内阁开始的对“价值观外交”的回归,也常被日本方面解释为钓鱼岛等事态促发的结果。但是,即使“中日实力对比影响了日本对中日关系认知”的解释在此可以成立,也仍然存在如下问题:面对这种变化和认知,日本的选择为什么是“价值观外交”?可以看到,“价值观外交”最初以澳、印作为重点,主要体现了针对中国的安全战略考量。目前,这种战略考量仍在继续,但主要手段已由“价值观”转向了“海洋国家”、“战略伙伴”。如果说最初效仿欧美国家选择“价值观外交”是权宜之计,为什么在未获澳、印积极回应、又有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价值观外交”仍未就此消失?这表明,对日本“价值观外交”的观察不能只局限于澳、印等主要国家,不能只着眼于中日关系,也不能只是抽象地借助理论。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有所调整、有其回应,其诉求还体现在如下方面。 (1)与相关国家加强关系。这一诉求除牵制中国的一面外,也包括发展双边关系、扩展海外市场、寻求其他政治合作的一面。在前者已逐渐诉诸其他手段的情况下,侧重于后者的“价值观外交”仍在发挥独特作用,有助于拉近与相关国家的距离。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澳、印目前仍对针对中国反应消极,也未在首脑会谈中回应“共有基本价值”的提法,但印度对日关系特使库马尔曾在与安倍会谈时主动提及“价值观”,称“辛格总理非常重视同共有价值观的日本之间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31)韩国也曾在卢武铉时期肯定两国“共有基本价值”。(32) (2)增进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认可度,一方面同认为有价值的国家拉近关系,一方面转移其对慰安妇等问题的关注,平衡自身的负面形象。在此层面上,“价值观外交”与安倍在联合国关于重视女性的发言并无本质差别,其言论与实践的相悖可以充分证明其回避问题的实质。但应当注意到,部分西方国家对“共有基本价值”是有回应的。据日本外务省记录,两次安倍内阁期间曾对日本“共有基本价值”的提法予以肯定的国家有:丹麦、比利时、法国、德国、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爱尔兰、土耳其、加拿大、巴西、西班牙、匈牙利等。此外,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对此提法亦有回应。(33)美国在首脑会谈中未称日美“共有基本价值”,但驻日大使肯尼迪曾称“美日国民拥有共同的价值观”。(34)各国的出发点须具体分析,但未能认识到日本“价值观”的虚伪性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3)为“集体自卫权”解禁及修改宪法这一最大的目标服务。如前所述,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始终处于“有主张外交”、“战略性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框架之下,而“有主张”、“战略性”、“积极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修改《日本国宪法》。近年来,日本政府高调以“中国威胁”、“领土安全”为由扩充自卫队力量、扩大活动范围,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诸问题实际上都是为推进修宪而着意利用的借口。(35)如前所述,“价值观外交”在设计时更侧重于牵制中国,但不论是从安倍内阁的整体战略意图来看,还是从其实际效果来看,也都是为修宪服务的。近期,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表示欢迎,称“日本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36)英国外相黑格肯定日本迄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作用,称“从这一角度出发欢迎安倍政权推进的安全保障政策”。(37)这虽是基于现实考虑,但作为曾受日本侵略、战后初期主张对日进行更彻底改造的国家,如果认为日本与“基本价值”完全相悖,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欢迎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也有一些国家(如部分东盟国家、爱尔兰、爱沙尼亚、马尔代夫等)对“积极的和平主义”表示了支持。(38)“价值观外交”在此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值得关注。 事实上,这一本质也恰恰是“价值观外交”最为自相矛盾之处:安倍内阁希望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形象博得其他国家对日本“集体自卫权”、“正常国家”的认同,但政府违背民意和宪法基本精神、以既成事实为由推进有特定意图的修宪行为,本身就是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践踏。 “价值观外交”与日本国内政治:作为结点的历史认识 日本在多部《外交蓝皮书》中均反复强调外交与内政的紧密联系。事实上,这种联系不仅见于外交要为内政服务的出发点,还见于外交与内政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是“价值观外交”的背景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内政与外交背后有统一的逻辑,是日本政治整体的一体两面。 据《广辞苑》的解释,“价值观”意为“个人或集团对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进行的价值判断的整体”。两次安倍内阁宣称与诸国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但是,战后日本虽然建立了议会内阁制,并在宪法法律中规定了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保护、市场经济等内容,其在实践中体现的“价值观”却与这些制度形式有相当大的脱节。战后至今,日本在重要政治实践中多有对其标榜的“价值观”的背离。例如,在“民主”、“法治”方面,包括《日美安保条约》及诸多重要法案(如2006年《教育基本法》、2007年《国民投票法》、2013年《特定秘密保护法》),都是在未经国民、国会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以强行表决的方式通过的。政界保守势力无视民意、推进有特定倾向性的修宪进程,本身就是对作为《日本国宪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的国民主权原则的践踏。而无论是自卫队这一违宪的存在,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试图以既成事实导向修宪的政治行为,无疑都与“法治”相去甚远。在“自由”、“基本人权”方面,《日本国宪法》规定了基本人权与生存权,但饱受美军基地之苦的冲绳民众的基本人权至今仍受到极端的无视;宪法规定“思想与良心的自由不受侵犯”,但国家与地方政府仍在强制教师、学生在典礼上起立合唱“君之代”;(39)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但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始终在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宪法规定言论学术自由,但非保守色彩的言行往往受到政府与法律或直接或间接的限制。(40)唯一较为名实相符的只有“市场经济”,然而近年来对中小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保护与传统相比正在日益减少。也就是说,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日本政府并未真正信奉与实践其所宣称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价值观外交”具有双重的虚伪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本政界保守势力经常强调“历史认识和外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历史认识恰恰正是“价值观外交”(以及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整体脉络)与日本国内政治的结点:否认侵略历史与战争罪行不仅是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人权与自由,也是否定日本国民的国民主权和法治基础,因为军国主义战争正是建立在否认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教科书不但在删去或美化侵略他国的历史,也在否认逼迫冲绳民众“自杀殉国”等历史。靖国神社不但在供奉战犯并受到政要的参拜,也在以国家的名义拒绝日本民众希望将死去的亲人迁出的要求。为修宪造势的“主权恢复日”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也是对日本普通民众(尤其是冲绳民众)尊严的否认。曾为军国主义象征的“国旗国歌”不仅在排外游行等场合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国民感情,也在被强制升挂或合唱等场合侵害了日本国民的良心自由。 以上事实都表明,不论是在外交还是内政方面,若要解决战后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认真对待历史都是无法回避的一环。历史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实,如果先入为主地持有忽视变化的决定论,很可能会影响对现实的认识。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认识、看待、思考过去的方式与过去并无不同,现实甚至未来就很有可能会继续历史的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认识”是重要的。“新的”变化到底是正视和超越了过去,还是以另外的形式留存了过去的内容?如果不能对历史有真正的认识和反思,甚至根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历史不能等同于现实和未来,但历史认识是可以代表现实、预示未来的。战后日本看似以新的民主体制与战前划清了界限,目前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战后一代”的身份也已经开始有了疏离感。然而,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并未真正普及、甚至连正视历史的可能性也在被有意回避的情况下,政界、学界一部分人热衷于谈论的“告别战后”、“超越战后”恰恰只能反映出“战后”乃至“战前”的延续。这种延续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军国主义本身,却毫无疑问是国民主权精神的敌人,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自在地存于世界的障碍。因此,对于宣称历史认识与外交(及内政)是不同问题、无视国内民众意愿与别国人民权利却标榜“价值观”的日本政客,首先最应予以充分警惕的是广大日本国民。 两次安倍内阁的政策与实践显示,虽然近年来学界集中关注日本对澳、印等国的“价值观外交”,但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实际呈现为两个层次:一是联络感情层面的,可借以与相关国家拉近距离,显示“先进”的国家形象;一是以战略伙伴关系为依托的,实际上是“有主张的外交”、“战略性外交”的包装。在形式上,前者主要面向欧洲国家,后者主要面向澳、印等国。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对澳、印等国的侧重已由“共有基本价值”转向了更为直接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海洋国家”),而对欧洲国家乃至韩国提及“基本价值观”的做法仍在继续,涉及范围甚至有所扩大。应当注意到,除牵制中国外,其诉求和效果还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如扩展海外市场、寻求其他政治安全合作、改善日本国际形象、谋求实现修宪等等。 除去不乏冷战思维的指向性,即使同欧美国家的“价值观外交”相比,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也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脉络来看,“价值观外交”仍是实用主义、回避反思的既有思维模式的延续,在此意义上与“赔偿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酷日本战略”并无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国内重要政治实践与其所标榜的“价值观”多有背离的情况下,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可谓具有双重的虚伪性。在此,“历史认识”与“外交”恰恰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日本现任内阁在内政与外交方面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而历史认识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归根到底,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有维护国家利益或体现国家诉求的本质,“价值观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方式,利益导向看似并非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外交是在以标榜价值的方式去利用价值,甚至掩饰自身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背离,这就不仅仅是“外交都是维护国家利益”可以辩护的。若一个政府对内在未经国民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进有特定意图的修宪行为、对外辩解掩饰历史上的残酷罪行,却高调声称自己的“价值观”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并将“价值观”当做实现一己目标的手段,这就已经超出了外交方式的问题,是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恶意欺骗。对此,不仅其本国人民需要提高警惕,真正珍视人类基本价值的国家也有理由进一步认清现实。因为这种缺乏历史反思、缺乏价值底线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正是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在近期内也很有可能以“海洋国家”等新的形式被延续。 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并未因印、澳的消极回应而告一段落,在未来也会继续被安倍内阁作为“有主张的外交”、“战略性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包装和手段推行,并很可能会在提升日本国家形象、扩展海外市场与安全合作乃至为修宪铺平道路方面收到效果。在此意义上,“价值观外交”并未“过时”、不可小视,对其予以关注和回应不仅是紧迫的现实需要,也可能成为避免对日关系走向不必要的被动的突破口。对此,一方面,除关注“价值观外交”(及“海洋国家”等)对中国的指向性之外,还应在更宏观的视角上重点关注其背后的“有主张的外交”、“战略性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另一方面,对日本利用“价值观”混淆视听的行为本身应予以正面回应,有必要通过适当途径与相关国家及日本各界就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开展交流,指出安倍政府“价值观外交”的虚伪性。 目前已有国内外学者指出,日本即使推行价值观外交,也应以自身实践的价值观(如和平主义、重视环境等)为出发点。这也印证了当下日本“价值观外交”的问题。(41)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日本国宪法》虽明文规定“和平主义”原则,但日本政府论及“和平主义”时并不一定与宪法相一致,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理念。“战后68年间的和平状态”虽被安倍内阁用作“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辩护词,但“和平状态”实际很难被看做“和平主义”价值观的成果,相反,这种状态长期以来是与对“和平主义”价值观的挑战并存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所强调的要点并非“和平主义”,而是“积极的”,其实质仍是政界部分保守势力一贯主张的“武装和平”,是和平主义价值观的反面。鉴于日本政府已将迄今所标榜的“价值观”与“积极的和平主义”相联系,不排除未来将“积极的和平主义”也以“价值观”面貌加以推销的可能性,对此亦应予以必要的警觉。 注释: ①参见黄大慧:《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刘江永:《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07年第6期;金熙德:《印日安全宣言与“价值观外交”》,《当代世界》,2008年第12期;孙承:《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廉德瑰:《地缘政治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等。 ②《安倍谴责中国就尖阁利用历史问题》,共同网(日本共同社),2013年7月10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7/55733.html。2013年以来,安倍的类似言论还有:“不希望有关历史认识的问题被视为外交、政治问题”(《安倍称不希望历史认识被“外交问题化”》,共同网,2013年4月26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4/51163.html);“参拜问题的相关言行‘本身会发展成为外交问题’”(《详讯:安倍称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无可奉告》,共同网,2013年7月22日,http://china.kyodonews.ip/news/2013/07/56394.html);“关于何时参拜或不参拜,考虑到这一问题本身可能会发展为政治及外交问题,我不打算说什么”(《详讯2:日本两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安倍献“玉串料”》,共同网,2013年8月18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8/57947.html)。 ③「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ぃ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65回(臨時会)第3号(平成18年9月29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④「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施政方針に関すゐ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66回(常会)第2号(平成19年1月26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⑤「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ぃ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68回(臨時会)第1号(平成19年9月10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⑥「日·ィンドネシア首脳会談(概要)」、2013年1月18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vti_1301/indonesia.html。 ⑦「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ぃ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83回(常会)第1号(平成25年1月28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⑧第一次安倍内阁虽未在施政演说中形成明确方针.但在与韩国的外交实践中曾提及“价值观”。详见后文。 ⑨本段对安倍演说的引用出自「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施政方針に関すゐ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83回(常会)第8号(平成25年2月28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⑩「高村外務大臣の外交に関すゐ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69回(常会)第1号(平成20年1月18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11)「民主党代表候補討論会」、2009年5月15日、日本記者クラブHP、http://www.jnpc.or.jp/activities/news/report/2009/05/r00021945/。 (12)「内閣総理大臣談話」(平成二十二年八月十日)、首相官邸HP、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8/10danwa.html。 (13)参见日本外务省主页的野田首相会谈访问记录(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及《野田政府欲在亚太地区推行“价值观外交”》,共同网(日本共同社),2011年10月8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1/10/17717.html。 (14)本段对安倍演说的引用出自「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ぃ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85回(臨時会)第1号(平成25年10月15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15)本段对安倍演说的引用出自「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施政方針に関すゐ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86回第1号(平成26年1月24日)、衆議院HP、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8620140124001.htm。 (16)「平成19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07)」、2007年3月、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7/html/framefiles/honbun.html。 (17)同上。 (18)参见日本外务省主页的历次首相访问会谈记录,2006年9月—2007年9月,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index.html。“首相访问会谈”包括安倍出访外国、外国首脑或外长访日以及安倍在多边场合所进行的首脑会谈。“‘价值观外交’的对象”指记录显示安倍在会谈中向对方谈及“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19)参见日本外务省主页的历次首相访问会谈情况,2012年12月~2014年4月上旬,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index.html。 (20)例如,2013年6月,安倍称:“韩国是重要邻国,拥有自由和民主主义等共同的普遍价值观。愿(与韩国总统)直接会面交流。”7月,外相岸田文雄称:“两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是重要的邻国和伙伴。非常希望发展两国关系。”但韩国对此并无积极回应。参见《安倍称愿与朴槿惠举行首脑会谈》,共同网,2013年6月27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6/54899.html;《朴槿惠请求中方在华协助建立安重根纪念碑》,共同网,2013年6月28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6/55045.html;《详讯:日韩外长会谈就发展两国关系取得一致》,共同网,2013年7月1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7/55185.html等。 (21)笔者倾向于认为,在会谈中特别提及“共同价值观”比仅在声明中写入更能表明日本在与该国外交中对“价值观”的“重视”。 (22)「日EU首脳電話会談(結果概要)」(平成25年3月25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page4_000006.html。 (23)「ラスムセンNATO事務総長によゐ安倍総理大臣表敬」(平成25年4月15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6_000037.html。 (24)Andreas Wilhelm,Auoenpolitik,Grundlagen,Strukturen und Prozesse,München Wien:Oldenbourg Verlag,2006,p.257.转引自李文红:《人权外交的新版本——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国际论坛》,2009年第3期。 (25)《默克尔指责津巴布韦政府侵犯人权非洲国家不满》,中国网,2007年12月10日,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renquan/2007-12/10/content_21148016.htm。 (26)《德国承诺向津巴布韦提供2500万欧元援助》,新华网,2009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6/content_11550552.htm。 (27)同上。 (28)《津巴布韦总统威胁将制裁西方企业》,新华网,2013年8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25/c_125242516.htm。 (29)「日·ジンバブェ首脳会談」(平成25年6月1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5_000172.html。 (30)例如,在1988年的外交蓝皮书中即有“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一员的外交”的提法。可以参见日本历年的《外交蓝皮书》、外務省HP、http://www.mofa.so.jp/mofaj/gaiko/bluebook。 (31)「クマ一ル·ィンド首相対日関係特使によゐ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表敬」(平成25年9月18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4_000192.html。 (32)「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韓国訪問(概要)」(平成18年10月9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cn_kr_06/korea_gaiyo.html。但卢武铉同时提及了历史问题。 (33)参见日本外务省主页两次安倍内阁与相关国家的访问会谈情况。 (34)《新任美驻日大使肯尼迪表示愿在日本多交朋友》,共同网(日本共同社),2013年11月13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11/63505.html。此外,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内德斯曾称“美日两国是世界第一、第三经济大国,并共有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メネンデス米上院議員(上院外交委員会委員長)によゐ安倍総理表敬(概要)」(平成25年8月15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18_000024.html。 (35)近期如在2014年1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明确以中国“单方面设定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周边“反复侵入领海”为说辞,强调“为在以西南地区为首的我国周边广阔海空确保安全,将在新防卫大纲下强化防卫态势”。结尾部分则称“相信包括削减议席在内的选举制度改革、国会改革以及宪法修改,必将能够向前推进”。 (36)《澳大利亚外长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表示欢迎》,共同网(日本共同社),2013年10月15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10/61712.html。 (37)「ウィリアム·ヘ一グ英国外相によゐ安倍総理表敬(概要)」(平成25年9月18日)、外務省HP、http://www.mofa.so.jp/mofaj/kaidan/page4_000192.html。 (38)参见日本外务省主页的首相访问会谈记录,2013年7月—2014年4月上旬。 (39)许多日本教师因认为“君之代”与太阳旗是军国主义象征而拒绝起立合唱,并曾对政府的强制性处分提起诉讼,但目前相关强制性规定仍然存在。 (40)例如,政府机构对地方自治体不选择保守色彩的教科书予以干涉。 (41)关于此点,非常感谢时殷弘教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