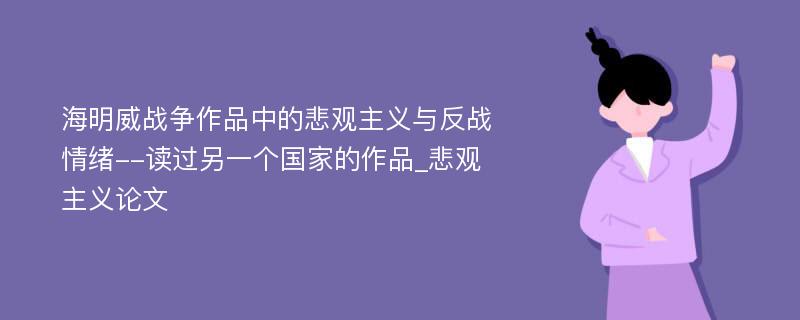
海明威战争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和反战情绪——In Another Country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悲观主义论文,读后论文,情绪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以In Another Country(《在异国》)为例,论述战争在身体和心理上对人的摧残,讨论海明威战争小说中的悲观主义和反战情绪,以及该小说对作者后期长短篇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 海明威 战争小说 悲观主义 反战情绪
一代文学大师,海明威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战争为题材的。《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永别了,武器》(1929年)和《战地钟声》(1949年)等长篇小说,都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灿烂佳作。通读他以战争为题材的各种作品,从他简洁朴素的表达中,读者无不感到一种使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和令人拍案而起的反战情绪。在他众多的著作中,最能表现上述特点的要算他的短篇小说《在异国》了。
《在异国》是1926年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的《没有女人的男人》集子中的一篇。它与《太阳照样升起》同年问世,但比他的其它战争小说都早若干年。不难想像,这篇小说是他其它战争小说的先奏,也是它们的准备。在这篇短小精悍的小说里,作者以冷静的头脑,描写了战争对人们肉体和灵魂的伤害,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是他战争小说的源头,确定了他战争小说的基本格调。
一、冰冷的环境,冷酷的现实
作者以第一人称,即一位美国军人的身份,描写自己在意大利米兰的经历。他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单刀直入地描写战争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个侧面:
时值秋天,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我们不再去打仗了。米兰的秋天是寒冷的,天很早就黑了……店铺外边吊着许多猎物,雪花落在那些狐狸的毛上,它们的尾巴在风里摆来摆去。一只鹿僵硬地吊在那里,沉沉的,肚子很干瘪。还有几只小鸟在风里荡来荡去,风翻卷着它们的羽毛。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冷风是从山上刮下来的。
从感觉上讲,“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冷风是从山上刮下来的。”还有“天很早就黑了”从视觉上看,“店铺外边吊着许多猎物,雪花落在那些狐狸的毛上,它们的尾巴在风里摆来摆去。一只鹿僵硬地吊在那里,沉沉的,肚子很干瘪,还有几只小鸟在风里荡来荡去,风翻卷着它们的羽毛。”真是环境冷,人的心里更冷。
一个远离故土,跑到异国他乡的军人,负伤后,每天得去医院进行治疗。秋风吹来,他感到冷飕飕的,自然会着眼于那些几乎与自己同命运,被别人猎来,挂在屋檐下,任凭寒风与落雪肆意蹂躏的猎物。读者不难看出,作者不是单纯地写这些猎物,而是在着意刻画自己内心深处的颤栗。
这种白描充分体现了海明威写景的语言风格。在如此寒冷的环境里,“我”怀着一颗冷透了的心向医院走去,而医院却是一个“在院子里经常举行葬礼”的地方。作者用一支冷冷的笔,把读者引到了一个萦绕着死亡幽灵的战地医院。
二、肉体上的伤害
“我”去医院是要“坐在那些机器上”进行治疗,因为“我的膝盖不能弯曲了,那条腿从膝盖到脚踝直直地吊在那里。腿脖子也没有了。”可见他伤得不轻。这时,读者会想到,他刚才是怎样艰难地从那条冰冷而黑暗的街道上走过来的。这种叙述一方面给文章一开始使人感到压抑的环境增加了一种凄惨的悲剧色彩,同时也预示着在这个医院里的幸存者们是一些什么样的活着的幽灵。
“我”曾经是个足球运动员,现在他的腿已经残了;另一位与他同机进行治疗的意大利少校“曾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击剑手,战前,是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击剑手。”现在却“长着一只像婴儿的手一样小的手。”另外还有一个“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的“男孩”。他“叫我们五个给他的脸上绑了一条黑色的丝手帕,因为他的鼻子已经掉了,医生要修补他的脸。他直接从军校来到前线,第一次上前线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负伤了。他们修补了他的脸,但……他们再也不能使他的鼻子恢复原样了。”
以上就是读者在这个战地医院看到的众生相。
三、精神上的创伤
肉体上的伤害可能还是可以治疗的,因为医院里有“那些机器”,而且它们“很有效”,更何况医生还有“一张照片”做为例证,但伤员们精神上的创伤也是可以治疗的吗?
对于军人们来说,奖章和证书应该是一种荣耀,但在海明威的笔下,它们却是一些无所谓的东西。“我们都有同样的勋章”。如果读者骤然没有看出这句话的深层含义,那么“那个脸色苍白,本来要做个律师的大个子男孩曾经是亚迪蒂的一位中尉。他有三枚勋章,而我们只有其中的一枚。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很久,现在对一切都有些无所谓了。”这句话就把这些年轻军人对奖章的冷漠态度交代得再清楚不过了,更何况作者还加了一句:“我们都有些无所谓了!”
读到这里,读者自然会问,这些军人为什么会对自己用生命换来的奖章这样“无所谓”呢?如果如此,他们的注意力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大伙都很了解可发餐馆。那里既豪华又温暖,而且灯泡不太明亮,有时人声嘈杂,烟雾缭绕,饭桌上总有姑娘伺侯你,同时,在墙上的架子上经常排着有插图的报纸。
对没有经受过战争创伤的人们来说,这段平淡无奇的描写可能没有多大意思,但对那些背井离乡,被战争将他们与普通人的生活隔离了的军人们来说,它就有其独特的含义了。在这种战火纷飞的环境里,他们只能在这家小小的餐馆里享受一下人生的温暖和安慰了。他们不需要战争,正如作者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的“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我们不再去打仗了。”同时,在谈到那三个意大利军人时,作者说:“他们中间的一位本来要做个律师,一位要做个画家,一位曾经想当兵。”从更深的层次上讲,他们也不需要战争授与他们的那些奖章和证书。他们需要的是应该属于自己的那点东西。他们需要温暖,需要宁静,尤其需要女人。任何有人间烟火的地方,都会引起他们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任何女人,也会给他们带来种种遐想和安慰。难怪作者那么喜欢马路边那个女人卖的“烧栗子”,不无深情地说:“随后,那些栗子在你的衣兜里热呼呼的;”难怪作者津津乐道地说:“我们大伙都很了解……饭桌上总有姑娘伺候你,同时,在墙上的架子上经常排着有插图的报纸!”
前面谈到,战争把“我”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谈到“我”的奖章和证书时,作者把这种隔绝的感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把证书拿给他们看……对他们解释,我得了那些勋章只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这与前面谈过的那种“无所谓”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但“从那以后,虽然我是他们反对外来入侵者的一位朋友,但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有点儿变了。”很明显,他的奖章和证书把他和他的意大利战友们在感情上隔开了,而这种隔离是任何外国军人都无法忍受的。因此,“我”不得不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他们的朋友,但从他们看了那些证书以后,我永远再也不能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他表示理解他们,知道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很久”,同时承认“为了得到那些勋章,我绝对不会干他们干过的那些事情……我很怕死,晚上常常独自躺在床上,担心我会死去,不知道我重返前线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即使是同病的战友,谁又能理解他呢?
作者对意大利少校的描写,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前面提到,他“长着一只像婴儿的手一样小的手”,后来,读者才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这台战争机器擦破他的一点儿皮,而它对他真正的伤害却是它毁灭了他的家庭,从而给他的心理上造成了永远无法医治的创伤。
他是一个“不相信勇气”的人,同时“当们坐在那些机器上,花了许多时间纠正我们语法”而且“祝贺我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可见这位少校并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战争凶神。但这样一位学究味很浓的人却为一件小事和“我”争执起来。
“如果这场战争结束了,那么你在战后将干什么?”他问我。
“我回美国去。”
“你结婚了?”
“没有,但我想结婚。”
“你这就更蠢了”,他看起来有些生气地说。“一个男人不应当结婚。”
“为什么,马吉奥尔先生?”
“别叫我‘马吉奥尔先生’。”
“一个男人为什么不应当结婚呢?”
“他不能结婚,他不能结婚,”他生气地说。“如果他肯定要失去一切,他就不能让自己再失去那个。他不能这样做。他应该找到一些他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很生气,很痛苦,一边说着,一边直直地看着前方。
“但他怎么会失去它呢?”
“他会失去的。”少校说,他看着墙壁。接着,他低头看了看那台机器,猛地把他的那只小手从捆着它的带子中间抽出来,狠劲地在大腿上拍着。“他会失去的,”他几乎是在咆哮。“别和我争了!”接着,他冲着管机器的护士喊道,“过来,把这该死的东西给我关掉。”
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为什么?原来是他的“妻子已经患结核病死了,而他只是在战场上彻底残废后才和她结的婚”。这时,读者才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直瞪瞪地看着墙壁……他直瞪瞪地看着我,看着窗外……看着门外”,看清了战争这个魔鬼把这个温文尔雅的人折磨到什么程度,理解了“那些照片对少校没起多大作用,因为他在看着窗外”的深层含义。
这就是海明威笔下的军人们的心态,而且越是战功卓著的人,他们的心理越是灰色,甚至到了痛不欲生的程度。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们在1957年编写的《美国文学》中,把《在异国》当做海明威的唯一代表作印行,是不无道理的。从文学角度看,这篇只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在各方面反映了海明威战争小说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和反战情绪,几乎笼罩了他后来的所有作品。与作者其它战争小说不同的是,海明威在这篇小说里没有把死亡,这个作者认为最珍贵的礼物,赐予他的主人公,而是让他“开始哭起来。‘我实在无法解脱自己’!”任何读者都会想到,让这样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苟活在世上,还不如让他的肉体和他的心一块儿死了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