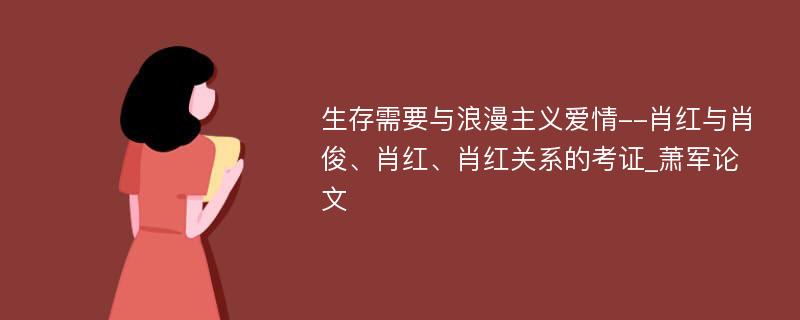
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对萧红与萧军及端木蕻良关系的几点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端木论文,浪漫爱情论文,需求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红是一位经历坎坷而又颇具艺术个性的短命女作家;但在研究中,她又是一位被时尚和潮流遮蔽得较深的作家。对观念的演绎和对潮流的趋从往往使研究者忽略掉萧红的真实遭遇和处境,从而漠视了她身上朴实自然的人格因素和生生不息的人性力量。我们曾冠于她抗战作家、乡土作家、思想启蒙者、女权主义者等等名号,可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与遮盖了她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现实境遇和情感生活的幽深面。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纠葛历来被当作文坛趣闻广为传诵,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颇富想象力的传记作家更是不遗余力地为这个涂抹上传奇色彩,历史的反复皴染早已使一段本来十分朴实平凡的人生遇合漫漶不清,面目全非。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萧红爱情经历的神圣性和浪漫性给予“祛魅”的处理:探究萧红与萧军结合的真实背景和各自动机;进一步考察萧红与萧军分手以及与端木蕻良结合的现实原因。
一
1936年9月,萧军在青岛写了散文《为了爱底缘故》[1],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二萧”结合的过程,成为“二萧”浪漫故事的最初“版本”。随着萧红与萧军分别以《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蜚声文坛,这对“作家夫妇”之间令人艳羡的传奇经历便广为流传。事隔四十二年后的1978年,萧军以颇富沧桑感的笔调再次叙写了这段偶然姻缘的前前后后[2],成为20世纪80 年代后的各种萧红传记的最具权威性的材料来源,学界的萧红研究凡在涉及“二萧”结合时大都依据萧军的这两份文献。在这两份文献中,萧军的叙述强调他与萧红结合的原因是“为了爱底缘故”,他侠义仁厚,古道热肠,救萧红于水火之中,引领她走上文学道路。
本文认为,“二萧”的结合并非“为了爱底缘故”,至少爱的因素比较稀薄;“二萧”走到一起更多是出于现实考虑、偶然际遇、青春冲动和生活需要。
首先,得到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的消息后,萧军反应十分冷淡,先到旅馆看望萧红的是舒群,而不是萧军。据赵凤翔说:“萧红落难的情况在《国际协报》副刊传出后,第一个去旅馆探望萧红的人,就是舒群。”[3] 真实的情况是,萧军当时十分困顿,他跟另一位同是当兵出身的方未艾一起在哈尔滨流浪,过着朝不保夕、饥寒交加的生活。萧军给《国际协报》副刊写稿,靠不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常常挨饿。当时,萧军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女儿,因无经济来源陷入困境,便将她们遣送回家乡[4]。在萧军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难以供养的状况下,哪有余裕去理会一个落难的女子?况且,萧军在下层流浪,对青年女子的不幸遭遇见得很多,为什么单单理会贫病交迫的萧红?因此,萧军在《烛心》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我明知我是没有半些力量能帮助你,我又何必那样沽名的假慈悲啊!所以在馨君他们要我一同到你那里去时,我全推却了。”[5],据孟希后来的回忆, 当时萧军第一次见到萧红是与《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笔名老裴)、琳郎和孟希三人一起去东兴顺旅馆。“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编辑部收到署名‘哨吟’的小诗,笔触细腻,感情真挚,大家都认为一定出于一位女作者的手笔。不久,因欠东兴顺旅馆的旅店费,有被卖入妓院的危险,悄吟(即萧红)又给裴馨园寄来了呼救信。”[6] “由此可知,并不是像萧军所讲述的由他一个人去见萧红,正如1933年《烛心》中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当时萧军对萧红是不感兴趣的,萧军单独见萧红是后来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后来萧军又接受了萧红呢?果真如萧军所说是因为萧红会写《郑文公》的“双钩”字吗?果真因为萧红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我认识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才下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7] 吗?有一则材料给我们提供了萧红与萧军的结合的另一个“版本”。因这个材料来自于台湾,在大陆较为稀见,引录时不妨详细一点:
这时在沈阳当兵的刘均和他拜把弟兄林郎大哥,一同化装逃出沈阳,来到哈尔滨,住在一家小旅馆里。
林郎会唱京戏,绰号青衣大郎。刘均一喝酒就上脸,绰号酡颜三郎。……
在明月饭店的时候,他认识了悄吟。
悄吟本来钟情于大郎,因大郎比三郎斯文得多,但是三郎当着大郎的面,逼着悄吟表示态度,他们俩兄弟,她究竟爱哪一人?悄吟在反对“旧礼教”这一点上,是很坚定勇敢的,但是在真正爱情面前,她是懦弱的,她没有勇气说明她真正爱哪一个人。她只会用哭泣和眼泪隐藏她的感情。
三郎看她不说话,便当着大郎的面抱住她亲一个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8]。
这几段文字说明,“二萧”结合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里面可能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和人事纠葛。材料所述的萧红、萧军、大郎[9],三角恋的关系虽无有力的材料来源和明确的引证出处。但它至少说明萧军和萧红的结合并非那么纯洁;又因这个材料来自海峡对岸,很少受到大陆内部人事纷扰的影响,且材料的提供者孙陵也是当时的东北作家,曾与萧红、萧军有过较多的交往,熟悉内部情况,立论也较客观和公允,材料有较高的可信度[10],因此,我们认为萧军与萧红结合很少出于爱的动机,很少出于对萧红的真心喜欢,而更多的是由于男人的自尊,争强好胜和青春冲动的缘故。
对于萧红来说,当时拖着怀孕的身体,到处流浪,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犹如一个即将淹死的人,只要有根救命稻草她都要牢牢抓住,她没有道理在择友上挑三拣四,也没有闲情逸致考虑什么爱情不爱情,爱情对她来说是一件奢侈品。她根本无暇思考这个问题,而当时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尽快走出困境。她需一个有力的男人帮她一把,救她跳出樊笼。这时,萧军出现了,尽管他看起来粗鲁不羁,好冲动,缺乏柔情和体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情人,但萧军孔武有力,热情洋溢,讲义气,有侠气,对当时的萧红来说,当然比斯文的大郎方未艾能给予萧红带来更多的帮助,所以萧红选择萧军并不是从“爱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更现实、更理性地把怀抱投向了萧军。事实证明,萧红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终于摆脱困境。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萧军可以靠拳头和耍赖渡过难关[11];在落魄的时候,没有人敢像以前那样轻易地欺侮萧红。更重要的是萧红在萧军的影响下居然从事了写作,而且进步很快,这是萧军给予萧红最重要、最实在、最可贵的礼物,它甚至能抵消掉他给予萧红的各种打击和轻慢。
为了能抓住萧军,赢得萧军的欢心,萧红在当时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只能凭借自己的惟一资产——女性的身体,尽管这个身体里还孕育着一颗苦涩的果实:她怀着别人的孩子。萧红必须打起精神,强作欢颜;她必须把痛苦压抑在情绪的底层,努力应对与萧军的肉体的欢会。这时的萧红仿佛一个赌徒,她要把自己的身体押进去,把一个女人的尊严押进去,把生命的庄严押进去,以求拯救自己。在“二萧”所有文字记载中,萧军的《烛心》记录了他和萧红的这段“狂恋”,而在萧红的散文和小说中你很难发现关于美好爱情的描写,更多的是像动物一样赤裸裸男女交合的场景,毫无美感可言[12]。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视到萧红的情感世界中,“性”从来就不具备身体美感和生命的庄严感,只不过是一种与说话、走路一样的交往方式或者讨好男人、换取利益的工具而已。我们可以从萧红从未发表的一组“情诗”里寻找到这个秘密的答案。诗《春曲》共6首,是萧红与萧军在1932年初夏“狂恋”的见证[12]。但若“细读”该诗,却会发现诗作极具反讽和张力,隐藏着深长的意味。《春曲》的后四首是这样的:
春曲(三)
你美好的处子诗人,/来坐在我的身边。/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你的唇任意我怎样吻,/你不敢来我的身边吗?/情人啊!/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
春曲(四)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三郎,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其间,/有说不出的风月。
春曲(五)
谁说不怕初恋的软力!/就是男人怎粗暴,/这一刻心,/也会娇羞羞地,/为什么我要爱人!/只怕为这一点娇羞吧!/但久恋他就不娇羞了。
春曲(六)
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爱惯就好了。/啊,可珍贵的初恋之心。
这几首诗是萧红写给萧军的“情诗”,因不是供发表之用,而是为表达心曲,诗中对情欲的表达相当露骨和直白,颇富暧昧和色情意味,但这在情人之间却是恰到好处,颇具煽情和逗引的力量。《春曲(三)》写到了腰、唇、吻等肉感的意象,仍进一步放肆地挑逗:“你不敢来我的身边吗!诗人啊,/你迟早是逃避不了女人!”《春曲(四)》在极具动作性和跳跃感的诗句中,把男女情事动感化、具体化,把“说不出的风月”鲜明地呈现出来;《春曲(五)》努力在男人的“粗暴”与女人的“娇羞”和“软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一个任你想象的空间,在这个诗的空间中填塞的只有一个主题:情欲;《春曲(六)》写爱的刹那和爱的感觉:“在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只有情人之间才能意会到的刹那的感觉,被萧红几笔便捕捉住,着实令人惊讶萧红的诗才。萧红的《春曲》竭力传递给萧军这样两个讯息:一是情欲和快感,二是感觉和诗才。前者表达了萧红对萧军身体需要的满足,后者让萧军知道萧红的文学才具不让须眉。这两点恰恰让萧军感到了莫大的欣喜,这就让萧军下了要“拯救这美丽的灵魂”的决心。萧红成功了。但这首诗的深层含蕴中却有着巨大的反讽意味。这可从诗的两个“裂隙”中解读出来。其一,是《春曲(三)》的第一行,“你美好的处子诗人”。萧红为了讨好自己的情人称萧军为“处子诗人”,这个赞誉是暗示自己的“不纯洁”——怀了别人的孩子的女人当然不再是处女,而自己的情人既是处子,又是诗人,与自己既不是处女,又不是诗人的地位形成比照。但反讽的是,当时的萧军正是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其诗才更是平平常常。“处子诗人”表面上是萧红讨好情人的称谓,但它无意中揶揄和颠倒了诗人的本来意图。其二是诗的最后一行:“啊,可贵的初恋之心。”无论是萧红还是萧军,此时此刻在情爱方面都已是“历经沧桑”,而诗人称他们之间的恋情是“初恋”,颇具解嘲和讽刺色彩;即便诗人真诚地认为自己的这次恋爱是“初恋”,与挺着大肚子的现实状况相较,更富闹剧和反讽意味:哪个女人身怀六甲还有能力进行自己的“初恋”?解读《春曲》可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萧红当时的现实处境和真实的心理状态。
二
正如前文所分析,“二萧”的结合并非为了“爱的缘故”,而是因缘际会,偶然性和现实性的因素较多。二人缺乏较深厚的情感基础,萧军总是扮演“保护人”和“救世主”的角色,而萧红总是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对她来说这在患难之初是需要的,可以容忍的,但随着萧红在文坛的崛起,她的文学成就使她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时,二人之间的裂痕便进一步扩大。实事求是地说,从1931年两人相识到1936年分手这6年的时光是萧红31岁短暂生命中最重要、 最辉煌的时期:她由一个不名一文的贫弱女子一跃而成为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从社会的底层进入社会的主流,艺术上由幼稚趋于成熟,形成独具魅力的写作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6年中萧红的生活道路、精神历程和生命质量得到完满的飞升和充分的发展;或许相反,萧红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痛苦与日俱增。公平地讲,这不能完全归咎于萧军情感的粗糙,行为的粗鲁,生活的粗疏,也不能只是责备萧红情感的脆弱和对男性过分的依赖。许多研究者在探究“二萧”关系最终破裂的原因时,把目光往往放在二者之间性格的差异上。其实,夫妇间性格差异未必一定会引起龃龉和抵牾,在多数情况下反而因性格的互补使婚姻更为融洽。萧红与萧军的分手有更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原因,比如身体方面,比如对配偶的不忠、轻慢和歧视等,都不容忽视;可能这些因素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考察这些具体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观察到他们的裂痕如何一步步扩大。
关于疾病。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14] 萧红短促的一生中被各种疾病纠缠着,常常因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她经常写出这样的句子:“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细得比丝线还细了吧!”[15] 自从萧红怀上第一个孩子,各种各样的疾病便与她结缘:头痛、脱发、贫血、胃疼、肺病、妇科病等等。据说,她曾吸过鸦片,后来被迫戒掉了[16];但她吸烟很凶,还常常以酒浇愁,不断地作践自己的身体。丁玲曾回忆道:“觉得有种很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预言。”[17] 张琳对萧红的嗜烟记忆犹新:“她的脸色很黄,样子也很憔悴,我私信她有鸦片的恶好。后来才知他并不吸鸦片,但对烟卷却有大癖。不错的,那天晚上,我便看见她烟不离手。”[18] 萧红的病主要还不是她的烟酒之好,而是贫血、饥饿、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的未婚先孕,在怀孕期间遭逢惊吓、冻饿和水灾等困扰,致使留下无法治愈的各种隐疾。许广平曾以一个女性的细腻和体贴记录过萧红曾因月经不调每月都要遭受肚子痛,而且“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19] 的情景。萧红的疾病使她敏感、脆弱,特别需要、甚至渴求别人的关怀和同情,而作为丈夫的萧军总是“粗线条”的,根本不把萧红的病痛当回事。当萧红在日本向萧军诉说腿肚上被蚊虫咬3个大包时,萧军认为“腿肚上被蚊虫咬3个大包,她也会说一说的,好像如此一说,这大包就不痛不痒了,其实我对这大包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我们俩体性不相同的地方”[20]。萧军的确很难体会萧红疾病的痛楚,他自夸自己是健康的,强壮的人,对于体弱的人,有病的人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何深刻的。所谓“关心”,对萧军来说,也仅仅是理性上的,以致“礼貌”上的关心,很快就会忘掉的。萧军对萧红疾病的漠视和冷淡使他们之间在身体上不能达成契合;当一对夫妇在身体和感觉方面出现了错位,便开始了心灵和情感方面的某种裂隙,因为所谓恩爱,首先指灵与肉的和谐与默契;很难想象对对方的“身体语言”反应迟钝、麻木不仁的配偶之间会产生“心有灵犀”的高度契合。
萧军不仅漠视萧红的身体,而且还对这个多病之躯施以暴力。关于萧红挨打的记载有很多,但萧军后来多次为自己辨白,说萧军在梦中与什么人争斗,竟打出了一拳。想不到这一拳竟打在了她的脸上,第二天她就成了个“乌眼青”[21]。但许多当事人如靳以和梅志都对萧红挨打的这件事有清晰的记载:
从前那个叫S(指萧——引者注)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蕴满盈盈的泪水了。”[22]
对于挨打的事情,萧红本人也有多次陈述,如1938年她就向聂绀弩抱怨说:“做他(指萧军——引者注)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23] 看来萧红对挨打始终愤愤不平,她几乎不能忍受萧军的拳脚,她的怨恨和委屈跃然纸上。在小说创作中,萧红也没有忘记借“闲笔”对男人打女人的事给予嘲讽和揶揄。《呼兰河传》中有这么一段: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
“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的。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24]。
可见,萧红身体方面遭受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疾病的折磨,一方面来自萧军的拳脚,而且当萧红成为知名作家以后仍遭此屈辱,她逃离萧军、摆脱萧军的情势在所难免。
关于“外力”干扰。所谓外力干扰是指萧军的外遇。如果说疾病和挨打使萧红的身体遭受创伤,那么,萧军的外遇和对萧红写作的蔑视则直接构成了对她心灵的伤害。对于夫妇双方来说,外遇并不仅仅意味着两人契约关系的违反和游离,在深层意义上更意味着对另一方人格和感情的轻贱、伤害甚至践踏。尤其对萧红与萧军这样的所谓“患难夫妻”来说,任何一方在感情方面的不忠诚都是对他们共同渡过的苦难岁月的嘲讽,所谓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庄严都予以无情的戏弄和颠覆,只剩下虚无和滑稽。事实上,萧军实实在在地做了践踏这种庄严感和尊严感的事情,而且不只一次。许多传记对萧军的“外力”干扰的事大都轻描淡写,甚至存而不论;许多研究者或出于不屑或出于怕遇麻烦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探究个人私生活是“无聊”的事情,致使作家的研究流于平面化和浮泛化。其实,情爱心理最能体现一个人人格的诸面相,透视一个人(尤其是作家)的情欲生活才能对他的行为(创作)和人生态度的动因、方向、兴奋点给予合理而有力的解释。就目前所搜求的文献资料来看,萧军至少有两次“出轨”行为。第一次是在1933年的哈尔滨,第二次是在1936年的上海。在哈尔滨时,因出版了《跋涉》且在报刊上经常有文章出现,萧红、萧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夫妇”了。这时,一个来自南方的16岁的少女陈涓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陈涓长得很漂亮,且是一个爱幻想、喜欢文学的女孩,对青年作家萧军崇拜自不待言。虽然不能说萧军是一个爱好寻花问柳之人,但他个性好冲动,任情感支配而不顾一切,尤其是对待异性,他更是如此。虽然文字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如何冲动地对待陈涓,但从她对萧红和后来的妻子王德芬拼命追求、死缠烂打的决绝态度上可知一二[25]。另外,两篇较早的文献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这件事。事隔11年后的1944年,陈涓给萧军写了一封公开信,来解释她当时与萧军的这段小小的情感波折,在信中说:“我总想详详细细地写一封信给你,把我们之间的误会的冤结解开。虽然我也曾奢望地期待你的归来,向你剖白我的心——对于你们两位作家的心,是如何忠诚,如何单纯,但是岁月无情……”[26] 据丁言昭叙述,当时的萧军对姑娘的追逐十分猛烈,又是送玫瑰花,写情书,又是上前拥抱、亲吻,弄得少女心慌意乱,不知所措[27]。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吓坏了,一个16岁少女怎能承受得了“萧军式”的猛烈的爱情火力,她只能悄悄离开了哈尔滨。这时,紧张而痛苦的萧红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28]。萧军在上海的“外力”干扰是与一位叫H夫人的女性发生的恋情。萧军后来承认了这件事:“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29] 这次“无结果的恋爱”的直接后果是使萧红出走日本,回国后又一次离开萧军去北京,以逃避这种感情上的伤害[30]。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萧红因萧军的外遇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只要读一读萧红的诗《苦杯》(11首)便十分明了。下面抄录5首可窥见一斑。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他又去公园了,/我说:“我也去吧!”/“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却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31]。
以上分析可知,萧红与萧军之间从身体到感情,从气质个性到思想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裂痕一步步扩大,最终分手在所难免。1938年4月在西安二人终于分开,从此,萧红再也没有见到萧军,便成永诀。
三
不管是当时的文艺圈,还是现在的研究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对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都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她与端木蕻良在1940年离开大后方,飞往香港的举动表示费解和不满,对她死于太平洋战争这个结局感到惋惜甚至愤怒。事实上,人们对萧红的责备并非没有道理,萧红委身于端木的确加剧了她的灾难,导致了她的速死;但萧红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投向端木的怀抱,自有她自己的道理,或者说正是她性格的逻辑发展。
“女人为爱情而生”,这几近滥调的流行语用在萧红身上倒不显得突兀。萧红从不讳言自己对“爱”的追求的决绝态度;她的短促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爱”和“温暖”[32] 的一生,不幸的却是“尽遭白眼冷遇”[33]。从哈尔滨到上海再到香港,从“李姓青年”到萧军再到端木蕻良,萧红对爱情都是怀了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但她的爱情神话却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后来可能有所醒悟,她在一首诗中这样吟道:“爱情的帐目,/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算也总是不够本。”最后,她终于明白:“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34] 客观地说,萧红在爱情方面是缺乏智慧和能力的。爱情作为两性间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总是被渲染得过分神秘、朦胧,总是夸大它的非理性和迷狂性的一面。其实,爱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需要双方共同遵守其间的“游戏规则”,更需要用心去经营和维护,需要更多的心智不断地去培育。遗憾的是,这方面恰恰不是萧红的独擅之域,甚至是她的弱点所在。与萧红有相当私交的一位日本女性绿川英子对她的这一弱点看得格外清楚,她十分中肯地分析了萧红与萧军和端木结合后如何越来越依赖于男性,以及由此所遭受的伤害: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结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方面的。……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们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是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一天一天加强了[35]。
可见,萧红对男性的过分依赖已经到了让她的朋友气愤的地步。骆宾基曾问萧红:“你离开萧军,朋友们是不反对的。可是你不能独立地生活吗?”可萧红却反问:“我为什么要独立生活呢?因为我是女人么?”[36] 应该说,萧红的独立意识是非常淡薄的,她以为一个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但是,事情走向了它的背面,对男人的过分顺从和依赖不仅没有赢得男人,反而遭到男人的轻贱和蔑视,这对萧红来说是始料不及并难以理解的。对于天真率直、不解世故的萧红来说,自如地驾驭婚姻之舟,实在是既没有经验,又缺乏技巧,难怪她在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时总是手忙脚乱、捉襟见肘。
正如前文所分析,萧红的疾病和挨打使“二萧”本来就很脆弱的感情基础雪上加霜,而萧军的“婚外情”使萧红彻底对他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萧红毅然离开萧军。因为萧红的软弱和对男性的过分依赖,不会促使她下定决心寻求独立的生活,只要萧军不表示抛弃她,她仍愿意维系哪怕已经死亡了的婚姻关系。从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分析,萧军的冷淡和羞辱倒不能构成萧红的致命伤害,因为上海时期的萧红已经不同于哈尔滨的萧红,她有一大堆值得称道的文学作品,她有一大批热爱她、崇拜她的读者,她有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的认可和垂青。萧红对自己的文学才能颇有信心。在临汾或是西安的时候,萧红曾发表过独具个性的意见:“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多式多样的小说。”[37] 但是萧军对萧红的创作颇不以为然。萧军曾多次在朋友面前故意贬低萧红的作品,说她的小说“结构不结实”,说她的叙述太过啰嗦,人物性格不明确等等[38],可以说,萧红可以容忍任何轻慢,但对她的文学才华的贬抑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这是她得以安身立命的坚实的地盘,她不允许任何人轻易地否定和排拒。事实上,夫妇间的真正契合是对对方的事业及其所取得成就的认同,双方之间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倾慕是维系双方情感更具“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因素,只有这样,夫妻关系才能滤掉“性”的吸引和青春的冲动,在更高层面上达到真正的两情相悦和高度契合。萧红与萧军之间恰恰缺乏这种因素,而端木蕻良的出现弥补了萧红心理的这一缺憾,在某种程度上讲,端木对萧红的欣赏和崇拜,满足了萧红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求,他们走到一起势在必然。
萧红是一个缺乏人际交往智慧的人,她的耿直和率真曾让丁玲感到吃惊:“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39] 在萧红眼里,端木蕻良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40],但心里却对端木的拍马屁感到十分欣喜。诚如前面所分析,萧红从小失去关爱,别人只要有一点点对她爱的表示,她都要付出比对方十倍的爱来回报。正如在她的一篇著名的散文中说的那样:“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41] 于是, 当端木蕻良向萧红表示了爱意,萧红便欣然接受。在1938年4月初的西安,三人在一所中学碰面后, 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离罢!”“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声“好”字,很快地走了出去。萧军后来回忆:“我们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42] 于是,萧红与端木蕻良双双返回武汉,过起了同居生活。萧红对“温暖”和“爱”的憧憬和追求到了近乎盲目的地步。所以她根本不顾这种“爱”是否可靠,是否真诚。就因为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正是萧红所要求的,这要求不是在对她作品的阿谀上,而是对萧军的轻蔑所含的她的社会独特性上,她周围从来没有一个朋友对她表示的独特友谊,像T所表现得这样‘坦白’而‘直率’。”[43]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萧红真的为端木的欣赏和赞美所陶醉,何况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正处于“胶着”状态,她对萧军失望已久,端木的介入是一个契机,她要从这个婚姻的泥坑里振拔出来,难怪她如此决绝地选择了端木蕻良。但她的苦难远没有结束,等待她的是无边的寂寞和苦涩的哀愁。直到三年后,正当进入创作的最佳年华,便消逝在烟波浩渺的南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