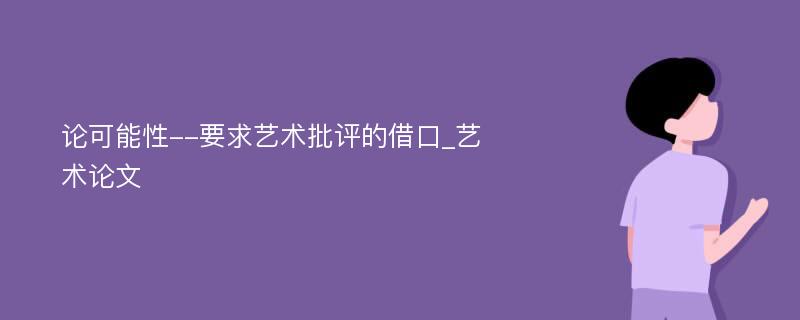
论可能性——被苛求的艺术批评之辩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能性论文,批评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们对于艺术批评的若干要求,其实是不恰当的。《镜与灯》作者艾布拉姆斯曾说过:“我们苛求批评去做其力所不能及的事,而对批评的许多真正的功能却视而不见。”这种苛求由来已久,大约自从有了批评,就有了对批评的种种指责。人们可以赞美创作、演出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称道艺术批评的积极作用,常见的是苛求。
通常人们会要求艺术批评“准确”;作家、艺术家们则指望批评与他们对批评的指望吻合。但这可能性是很小的。“准确”的前提是什么?批评家的艺术旨趣,他所依据的批评理论,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艺术领域不像某些精密科学,可求得某种无误的一致。人们也许会要求批评充当创作者与欣赏者的中介,传递创作信息,反馈作品被接受、欣赏状况,促成交流渠道的畅达;不久前甚至有学者倡导电影评论起宣传、促销作用。但这些要求过于专业化,不是每个批评家都具有这方面的本领。在贸易活动中有中介人,受卖方、买方委托,联络活动于彼此之间,务使交易成功。艺术批评家有没有受到创作、演出方或欣赏方的委托呢?倘有此委托,则其身份将成为中介人或称代理人、经纪人,而不再是批评家了。他们也会发表文章,其性质近乎某种类型之广告,应当从委托方根据协议、约定分得利润,如果仍和批评家一样支取微薄的稿酬,就有欠公允了。
人们还常常要求批评家宽厚,文学艺术处境艰难,严厉的批评或许会置人死地。人们提到久违了的别林斯基,称许他是如何的举双手欢呼新生事物。但宽厚似乎并不是别林斯基的主要特点。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别林斯基似乎是一位“毫不留情对待那些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的批评家。文坛确需抚慰,不过由领导、企业家担当此任,较易到位。批评家作领导状之“慰勉有加”,总觉装得不像。社会上一般认为评论不敢大胆批评,也许正是对艺术批评界某些搔首弄姿之领导腔难以忍受吧!人们常常将艺术团体、艺术家设想得过于脆弱,以为稍重的艺术批评,就会构成打击、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果真如此脆弱之艺术团体、艺术家,能有所建树吗?更何况中国有这样的一言可以兴团、一言可以毁团、一言九鼎之艺术批评家吗?批评家如果自以为其艺术批评有实力造成毁灭性打击,自我感觉是不是太好了?
艺术批评、文学批评能做到什么?“在孤单的灯火下”,龙应台与肯纳对话,肯纳的论述颇为切实。肯纳说:“以一般的文学批评来谈,文学批评是一种延伸,它是一种欲望去谈你感到有趣的东西。阅读是一种孤独的活动。孤单的灯火下,一个人抱着书,没人打扰你。这种情形下,你会想要和别人沟通或辩论。在完全孤独的读书过程中,运用并咀嚼你的生活经历并不有趣,你想跟人谈,说说你很感兴趣的部分。谈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下来。有些人对你写的东西一定会有兴趣。我想这就是一种自我延伸,而且很自然的很多人可以了解你对作品所说的一切。”肯纳又说:“一个文学批评者的功能在于描述读过一件作品之后,产生的感受或反应。由你的描述里,其他的读者因而有比较他们的感觉的依据。假如我读了劳伦斯的一部作品,并且有东西谈它,而你也读了这部作品,并知道我所发表出来的,这中间便形成了一种对这部作品的讨论或对谈。”龙应台问:“如果只是‘感受’,那么你跟一个缺乏文学素养的读者有什么不同?”肯纳答道:“我想有两点是不一样的。第一,我很强调文学经验,从经验里你可以提出许多例子来比较一部劳伦斯的作品。第二点,我善于写作上的表达……”
肯纳所说的自我延伸,显然包含有如实的意思。如实为艺术批评家应有的真诚。批评家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真诚有助于协调与群体的关系并确立批评家的地位。别林斯基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戏剧批评,虽有高下之别、精粗之别,均具有真诚的特点。最初别林斯基对法国文学、戏剧是偏颇的,在他看来高乃依、拉辛是诗中畸形的东西。当他转到新的观点后,对待这些作家就不同了。他说:固然,高乃依的悲剧就其古典形式来说是非常畸形的,理论家有充分权利加以抨击;但是,如果批评家只看到高乃依悲剧的畸形的假古典形式而忽略了这些悲剧的激情的极大的内在力量,那就大错特错了。别林斯基对格里包耶多夫喜剧《聪明误》的评论也有一个变化过程。1840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极大的遗憾,因为他曾认为这部喜剧不好,“从艺术观点斥责它”。写信时他认识到这是一部极其高尚的、合乎人道的作品,是对丑恶的俄国现实,对贪脏枉法的官僚和荒淫无耻的贵族,对愚昧无知和奴颜婢膝等等非常坚决的抗议。别林斯基的真诚获得广泛的赞誉。
表示歉意后,别林斯基在《1841年的俄国文学》中重评格里包耶多夫《聪明误》:
这部喜剧的内容是从俄国生活采取来的;它的激情是对于那鲜明表现着古旧风习的现实的愤慨。它的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往往被讽刺的因素所压倒。作者意识中还未完全成熟的思考的模糊不清,妨碍了它的艺术性达到完善的地步;他正确地反对毫无意思地盲目摹仿一切外国东西,可是又号召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式的对外国人的无知”。他不理解他所描写的社会的空虚和卑劣,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信念和任何合理的内容而产生的。他把全部罪过都归结到滑稽的剃得光光的下颚,归结到后面带尾巴和前面开口的燕尾服,他兴高采烈地谈论庄严的古代长袍。但是这只表明格里包耶多夫的才能是不成熟和年轻的。
显然,洞察力与真诚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戏剧批评的显著特点。
二
对于艺术批评的作用,人们的看法有极大的不同。或云缺少真诚、洞彻的批评导致创作能力的萎缩,或云尖锐的批评令人手足无措。其实不同类型的艺术批评对于不同类型的对象起何作用,应当通过设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获得必要的数据,并由此作出推论。可以设定抚慰型、洞鉴型等若干种批评类型,批评对象亦从不同角度作不同之分类,这样对批评作用的考察就可较为具体、切实了。艺术批评之作用还有一个时间长度问题,或仅有现场影响,或现场影响之后尚有短期影响,或长期影响。一通批评,如果数年后仍有影响,就可以勉勉强强地说是有较长期的影响了。
文学艺术界、艺术批评界似乎尚未进行此类调查、测验、统计。其他学术领域的一些工作可资参改。巴克教授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提供了这样的研究结果:
一个新手,在成千上万的可能性面前,他还没有学会选择一个正确的反应,在这种情景中,观众会唤醒他,使他在绝大部分时间中,作出不正确的反应。比如说,一个人学希腊语,或学弹吉他,或完成在困难程度上与之相类似的其它任务,他最初的反应可能是不正确的。然而,当一个人学会了一种技能以后,比如,当他能熟练地演奏吉他以后,正确的演奏吉他便成了一种习惯,正确的反应便成了优势反应。他人在场会刺激这些强烈反应的产生。
观众在场会加强优势反应的产生。如果优势反应是正确的反应,像在已完全熟练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反应一样,那么,观众的在场对于个体来说是有利的……
这个研究结果提供的消息是,一个尚处于学习状况的不老练、不成熟者,与一个老练、成熟者,对于“观众在场”、“他人在场”、“他人评论”的反应是不同的。该项研究以普通文化程度、智力程度者为对象,文化、智力高于这个程度者又将如何呢?人们要求艺术批评家是将评论对象定位在不老练、不成熟的实习生还是定位在已达一定水准直至成熟阶段的作家、艺术家呢?
杰出者常感孤独,不是因赞誉的欠缺,社会对这类人之赞誉是从来不吝惜的,而往往是因不为人所洞见,对长处与不足的洞悉,由是而生落寞之感。成熟的作家、艺术家有时需要一种被人看透的乐趣。话说遥远的古代,有一位九头魔王,他有一个极大的秘密,怀着期待的心情,悬赏征答。第一个人说,大王的心是黄金做成的,宝石做成的。魔王哈哈大笑,把他吃了。第二个人说,大王在七十二变之外,还有一变,无人能及。魔王又笑着把他吃了。第三个人说,大王有一件天下第一的宝贝,魔王不等他说完就把他给吃了。后来,来了一位读书人,他说,大王虽有九颗壮观的脑袋,魁梧的身躯,却长着一支猪尾巴,而且是小猪的尾巴。秘密猜对,魔王无比兴奋,他请读书人吃了一席山珍海味,然后,当然也将读书人吃了。魔王秘密被猜中时的兴奋,比之一些人因触及要害而恼羞成怒,境界要高多了。今天的作家、艺术家心态境界是不是更高一些呢?
批评家不应当是驯服的读者、驯服的欣赏者。让·斯塔罗宾斯基曾描述批评工作的心理过程:
在最初的聆听的情感同化中,我与作品的规则紧密地相一致,我从对它的客观研究中所获得的意识又使我能够从外部观照这规则,将其与其他作品和其他规则相比较,并且就这部作品形成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又不再是对产生于作品的话语的简单解释。这难道就是远离了作品吗?当然是,因为我不再是一个驯服的读者了。因为我的轨迹不再受作品的轨迹支配了:我脱离了作品,我离作品去追随我自己的路线。不过,这条路线与我刚刚还与之重合的作品总是有联系的;我所争得这种远离在我看来是必须的条件,以便我不仅仅是对作品点头称是,而是与之相遇。完全的批评著作总是包含着对于最初的驯服的回忆,它远非为了它自身而接受被分析的文学作品的引导,而是有它自己的路线,以便能在一个决定性的点上与之相遇。一束明亮的光就产生于两条轨迹相交的地方。
艺术批评家与欣赏者不同。欣赏者在欣赏前或欣赏时不宜有成见的框架,应当保持艺术的敏感,任凭想象力遨游,与欣赏对象建立无拘无束的关系。而艺术批评家的主见则是很重要的。成为艺术批评家应具备一般性准备与选择性准备。韦勒克和沃伦主张:文学史家必须是一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反过来,文学史对于文学批评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作品是继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二者分离的一般做法,对两者都是不利的。
赫伯特·曼纽什则认为:“批评高于创作”。“创作首先也是一种‘批评’,即对现实生活的批评。批评家与他所批评的作品的关系略等同于作家艺术家与实际生活的关系。批评家之批评是对现实之批评之再批评。批评是艺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创造活动。”创作是一种批评,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一种对艺术品的判断如果自身不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什么权利留在艺术领域里呢?
三
认识的可能性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困难起因于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关系问题。胡塞尔追问: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自在事物同我们的思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批评是对批评对象的认知,批评又构成对批评对象的切割和伸缩,批评永远不是作品的对等物,这固然是事实,但有时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艺术批评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为时间所鉴定是不妥的。如明代若干评论家对关汉卿的评价,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对曹禺《原野》的批评。俄罗斯果戈理时代,果戈理的《外套》和《死魂灵》,明显地被一些批评家读错了,所谓这两部作品是宣传品的论点是何等的谬误!今天,人们对《红楼梦》、《金瓶梅》的评说,能为后世认可吗?文学艺术作品与科学成果不同,有不知凡几的闪烁不定的因素,最老练的批评家亦常常眼花缭乱。让·鲁塞的看法是:任何艺术家都有一个秘密,创作的目的就是揭示该秘密。倘若没有秘密要公之于众,他为什么创作呢?直到创作终点,秘密才被揭示。可是事实上,有时艺术家自以为秘密已经揭开了,秘密却仍神秘地存在。批评家有可能指点迷津么?
阿尔培·贝甘强调:“随着巴什拉尔,接着是从中受益匪浅的让·皮埃尔·里夏尔的出现,人们才开始发现,把普通词语变成诗歌词语的这种特殊颤动总是产生于和物质世界接触中的那种个人的特性。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只有一个为大家所共有的客观感觉,那么,我们不难设想,文学也就不存在了。”作家、艺术家们有那么多的个人特性。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津治两人相互关联地从不同方面努力“使语言奇异化”,一个使熟悉的语言奇异化,另一个则把奇异的语言通俗化。画家德洛克罗瓦甚至说,画家要是画好了阴影,就等于画好了一切。荣格认为:“有创造力的人是一个谜,我们想方设法要解开它,可总是无济于事。”“伟大的艺术作品,犹如一场梦;虽然其外表一目了然,无须作自我解释,然而,它始终是含糊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作家、艺术家而言,是发现的最佳工具,那么他发现的或想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呢?
艺术批评家也许可寻求“原意”。余英时说:“我们屡次提到作者‘原意’或‘本意’的问题……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
艺术批评家也许可以“本文之外,一无所有”,视本文为封闭的系统与自足的实体而作发掘与穷究。这种方法,风行一时,而今是不是也已渐渐露出窘态来了呢?
郎加纳斯主张“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请读卢梭《忏悔录》第四章:“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各人有各人的幻想,我的幻想一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的想法不同。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一些,我也是偏爱她的。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这种坦诚是“导致崇高”呢?还是为卑微心态安排一合理的生存空隙呢?
数的概念是人人都该有的。《马太福音》:“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这究竟是浅短的牧人见识呢,还是深奥的人生哲理呢?
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写道:“叫他惊奇的是,刊载出来的作品里竟有那么许多死气沉沉的东西。文章里找不到五光十色的生活……生活是那么奇异,那么神妙,充满了许多的问题、梦想和英勇事迹,可是这些故事中写来写去只写些生活里的平凡事。他体会得到生活里的压力和紧张、生活里的狂热、血汗和激烈的动盈——当然啦,这才是写作的题材!他要表扬那些领导着没有成功的希望的运动的人们,以及在恐怖和苦难中、在重重压迫下作着斗争、用尽他们的力量来震撼世界的巨人们。可是,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似乎只想一味表扬勃特勒先生那一路卑鄙的孳孳为利的人们,只想渲染平庸无聊的男男女女的平庸无聊的恋爱。”但是近一、二十年,风靡世界的是《克莱默夫妇》、《廊桥遗梦》。是艺术鉴赏世风日下呢,是杰克·伦敦过于偏激呢,还是何时何事都该有个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呢?
艺术批评能做些什么?批评家当不了文坛、艺坛的裁判员,他们所能做的,只剩下对可能性的洞察。作家、艺术家将某种可能性转化为艺术作品,牢牢保护它,全力为之辩解,然而此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不好的,通常未必是最好的。艺术批评家的立场和素养使他有可能对极多的可能性有较广泛、深入的洞察,在已转化为艺术现实的可能性与尚未转化为艺术现实的可能性间,在人生、奥理与艺术间,纵横思考,反复探求,构建其独特的艺术创作领域——艺术批评。
作家、艺术家们,对于看不顺眼的艺术批评不必忿恨不已,艺术批评家们只不过是揭示另一种或数种可能性而已。
四
艺术批评确实不易。
十七世纪的叶星期有“才、胆、识、力”之说。他认为“无识不能取舍”,“无胆则笔墨畏缩”,“无才则心思不出”,“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才、识、胆、力四者皆俱的文学批评家、艺术批评家、戏剧批评家,有没有?有的。我们曾与之相遇,在典籍中,在现实中。他们点燃了星星点点的薪火,文学批评、艺术批评赖以维系其存在。
才、识、胆、力,四者之中,以识为先。叶星期说:“使无识,则三者皆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
叶星期又就胆发表议论。他认为胆与识关联,“因无识,故无胆,使笔墨不能自由”。胆与才关联,“惟胆以张其才”;“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胆能生才,但知才受于天,而抑知必待扩充于胆耶!”,“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近年艺术批评,常见媚、涩两种风格。无胆,故无脊骨,故媚,作小鸟依人状,寻求皆大愉悦。以拗、涩文其肤浅,正是内怯、对自己的见解缺少信心的表现。也许近年的艺术批评,常感不足的就是胆了。
于是我们想起《老残游记》中的翠环女士,她对野店诗人曾有透彻的批评。她说:“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客人见的很多,也常有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大约不过两个意思:体面些的人总无非说自己才气怎么大,天下人都不认识他;次一等的人呢,就无非说那个姐儿长的怎么好,同他怎么样的恩爱。那老爷们的才气大不大呢,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只是过来过去的人怎样都是些大才,为啥想一个没有才的都看不着呢?我说一句傻话:既是没才的这么少,俗语说的好,物以稀为贵,岂不是没才的倒成了宝贝了吗?这且不去管他。那些说姐儿们长得好,无非即是我们眼面前的几个人,有的连鼻子眼睛还没有长的周全呢!他们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嫱,不是说他沉鱼落雁,就是说他闭月羞花。王嫱俺不知他老是谁,有人说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难道都是这种乏样子吗?一定靠不住了。至于说姐儿怎样跟他好,恩情怎样重,我有一回发了傻性子,去问了问,那个姐儿说:他住了一夜就麻烦了一夜,天明问他要讨个两数银子的体己,他就抹下脸来,直着脖儿梗,乱嚷说……你想有恩情没有?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
翠环这通批评,批的是野店诗人,却也带上了我们的剧作家。才子剧作家袁于令写《西楼记》,所赞为天人的穆素徽,实即作家生活中的相好。但是袁子才说:“穆素徽亦中人之姿,而微麻,貌不美……”纪文达说:“《西楼记》称穆素微艳若神仙,吴林塘言其祖幼时及见之,短小而丰肌,一寻常女子耳!”文人的劣根性被翠环小姐兜底给揭出来了。因教育与地位的限制,翠环才、力自然不济;有识,但未经琢磨;最可贵者乃其胆,毫无顾忌地面对文人批评文人,推论虽不留余地却无懈可击。遗憾的是青灯黄卷,终其一生;万恶的旧社会毁了一位有胆的文学批评人才。
人们不必忧心忡忡,忧虑较有锐气的艺术批评令天下大乱。黄人瑞听了翠环批评后,虽然表示:“从今以后,我也不做诗了”,但据我所知,他后来还是做的。我曾略作调查,今日文学艺术界某些难题、戏剧团体某些困境,肯定不是寥寥可数的几篇稍许尖锐些的艺术批评造成的。有时或可起促销作用,如某地某剧团在演出海报中即注明该剧曾被某报批评为如何如何,观者倍增。据我推测,即使所有的艺术批评家都改行担任广告员、推销员,文学艺术现有的难题恐仍是难题。只有一样没有试过:如果有较充分的真诚的、切实的、有见识的艺术批评,艺术的状况是否会有较多的起色呢?试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