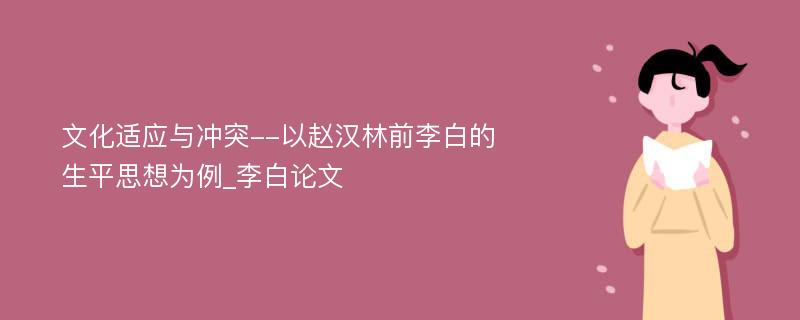
文化的顺应与冲突——以李白待诏翰林前的生活和思想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林论文,为例论文,李白论文,冲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2-0134-04
本文试图对李白待诏翰林前的生活和思想作出文化意义上的阐释。李白第二次入京成功在于他顺应了开元、天宝之际皇家文化大崇道教的形势,他的待诏身份应是道教徒;李白待诏翰林前生活在一个急于摆脱的文化环境中,鲁文化的排斥和对鲁儒的嘲讽使李白与儒学文化构成了一种冲突关系;同样,李白在东鲁的不幸婚姻也使他内心难以保持平衡。后二者的文化冲突恰恰有助于认识李白待诏翰林的意义,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体察李白待诏翰林前后的心态变化。
一、道教的崇盛与李白道教徒的待诏身份
李白入京的文化背景关系到李白待诏翰林身份的确定。李白入翰林正逢玄宗大崇道教之时,唐玄宗并非以文学之士征召李白。唐代帝王崇重道教,而天宝元年前后玄宗特重道教,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提高其地位。先是置崇玄学,令生员习四子,《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五月画老子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周至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很明显,这是玄宗为抬高道教地位而托言玄元皇帝云云。九月玄宗又亲试明四子人,《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御兴庆门,试明四子人姚子产(彦)、元载等。”天宝元年二月改四子书为真经,《旧唐书·玄宗纪》下载,亲享玄元皇帝庙,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李白入长安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而且是和道士元丹丘一起,在玉真公主即持盈法师的引荐下,才得到玄宗召见的,魏颢《李翰林集序》载:“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新旧《唐书》说出于道士吴筠的推荐,虽与事实有出入,但云道士推荐,却是事出有因。当时待诏翰林者成分不一,《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云:“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云:“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习惯上说李白是以文学身份供奉翰林的,但当时最直接的材料没有一则显示李白待诏翰林是以文学的身份,至少《旧唐书》中列举玄宗朝以文词待诏翰林者无李白之名。那么,李白是否以道教徒的身份,抑或以道教徒兼文学的身份被召入,还可以讨论。在玄宗重道教的背景之下,又由玉真公主来推荐,无疑李白入京与道教密切相关。李阳冰《草堂集序》明明说:“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值得注意的是,李白送人下第的诗仅有一首,即在翰林供奉时所写的《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1] 四子举,即试《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李白本人无意于科举,但对四子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从诗意看,李白与于十八并非旧交,李白写此诗的缘由可能是于十八拜访请托过李白,因李白以道学名;也有可能李白关心四子举,于十八落第,李白有心安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佐证了李白入京待诏翰林与道教有关。另外,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谪仙人”当然与道教有关,贺、李二人会见的地点又在紫极宫,紫极宫即玄元皇帝庙。此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2] 系于天宝元年。以上凡此种种,必非偶然,李白以文学之士入诏翰林的传统说法有待重新讨论。
李白以道教徒的身份入京待诏翰林,正是顺应了当时皇家主流文化大崇道教的结果。李白入诏翰林身份的确定,并不影响人们认识、评价李白在供奉翰林时的文学活动,而李白供奉翰林时的文学活动和其身份也不矛盾,因为人员很杂的翰林待诏都可以从事文学活动。了解李白入翰林的原因,可以进一步研究李白在翰林供奉时的思想状态。玄宗召李白入京只是崇道政治行为的不重要的细节,而李白误以为要被予以重用,大展宏猷,这必然会使他产生理想与现实不能一致的矛盾。
二、从地域文化看李白与鲁儒的冲突
东鲁是李白与儒家文化冲突表现最为极端的地点。李白在天宝以前主要生活在三个文化圈中,第一是少年时期的蜀文化,这是诗人最熟悉的文化环境。蜀地的人文和自然给李白留下难以拂去的印象,从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同乡司马相如的赋,他的《蜀道难》不管寓意如何,都表现出作者对蜀文化的熟悉。第二是楚文化,据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他来楚地是受乡人司马相如赋的影响:“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他第一次成家也是在楚地安陆。其《庐山谣卢侍御虚舟》诗开头两句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楚文化的认同。李白之于楚文化应当没有冲突,但需要指出的是,李白个性孤高自傲,不易协调周围的人际关系,所谓遭人谗毁,在楚地也是这样。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故其《鞠歌行》云:“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在《赠从弟冽》中则嘲讽楚人:“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第三是鲁文化,这是李白入长安供奉翰林前生活的文化圈,对李白入京供奉翰林影响至大。
李白和鲁文化没有作较好的调和,因此受到歧视是自然的。他来东鲁不久写过一首《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谓“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汶上老翁嘲笑李白的具体内容不太清楚,但李白的举止想法不符合鲁人的习惯当是其一。东鲁是传统的儒学之邦,汉初叔孙通议定朝仪就是征召鲁地儒生三十人共同讨论的。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描述鲁地风俗云:“土俗古远,风流清高”,“代变豪侈,家传文章”,“千载百年,再复鲁道。”其《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亦云:“白以邹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可见东鲁之地崇尚儒学,有周孔遗风、洙泗遗俗。唐代开元、天宝以前,兖州未出大儒,但与之在地缘上较近的齐鲁文化圈里还是出了一些儒学大师。李白在东鲁生活了一段时间,应该说对东鲁风俗人情已相当了解。他在《送薛九被谗去鲁》诗中说:“我笑薛夫子,胡为两地游?黄金消众口,白璧竟难投。梧桐生蒺藜,绿竹乏佳实。凤凰宿谁家?遂与群鸡匹。”“借问笑何人,笑人不好士。尔去且勿喧,桃李竟何言。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其中道出了文化认同的问题。鲁地儒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推崇是执著的,李白与鲁地儒生肯定会彼此诘难,《嘲鲁儒》一诗可视为李白与鲁文化冲突的直接表白,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行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集中体现了李白对以周孔遗风洙泗遗俗为代表的鲁文化的批评。李白讽刺儒生是有特殊的地缘因素的。
地域文化和李白思想的冲突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唐代其他作家与活动区文化上的磨合普遍存在,也有待深入探讨。其实,古代社会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能畅远,相对而言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要比今天明显得多。我们讨论古人的生存环境,因居住地的变换而产生的文化不适,实在应该重视起来。特别是李白,其生存环境的变化多数与婚姻有关,这和举家迁移不同。李白一定要和新娶之妻妾的当地人发生联系,以妻妾为中介的联系形式使李白无法超脱现实环境,他的行为不得不受到女方家族、同宗、村民以及以任何形式聚居的集体的关注,他们会以自己的文化去评价一个外来人的行为,李白当然经受不住这样的考察。李白在东鲁时曾和孔巢父等人隐居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六逸的活动情况不能详知,但孔巢父其人,史书说他性“轻躁”,大概包括李白在内的其他人也差不多是这样,因而,李白混迹竹溪的行为也便不免受到指责。冲突是难免的,李白婚姻不幸与此也有关系。当然,李白的个性同样也加剧了这种因地缘关系引起的文化冲突。李白一生漂泊不定,他自己说过一些原因,比如“一生好入名山游”,“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等等。我以为李白一生四处奔波,还有原因在,这就是李白常变换居住地以摆脱原有的令他不快的生活环境,也就是通过变换环境以求文化的适应。前面已经说过,他离开楚地是被动的,他曾得罪过安州李长史。在东鲁也是如此,甚至到了生活艰难而无人顾怜的地步,《赠新平少年》诗云:“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生活上如此,人际关系也大为不佳,《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诗云:“与君各未遇,长策委蒿莱。宝刀隐玉匣,绣涩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一朝攀龙去,蛙黾安在哉?”这都反映了他离鲁的原因与心态。
三、李白的婚姻危机及其逃逸
婚姻的危机也可以理解为文化冲突,只是其以细小而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古代作家生活态度的研究中,不少文章关注作家婚外的两性关系,这样可以了解某一时期社会的文人风尚以及与创作的关系,在音乐与文学、妓女与文学的研究中就有体现。婚姻自身的矛盾导致的文人内心的痛苦,由于资料的缺失而无法窥视或作进一步的探讨,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陷入这一矛盾痛苦中的解决方法很多,常见的方式就是逃逸和出走。李白入京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是愉快的,同样,在处理个人婚姻上也是愉快的逃逸。在东鲁,他在这两方面都在作不断的努力。
李白在开元、天宝之际婚姻是不幸的。魏颢《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据《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宋”当作“宗”。李白凡四娶,依次为许氏、刘氏、鲁一妇人、宗氏。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特作《李白的家室索隐》一文,对李白婚姻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考索。[3] (P36)许氏早逝,娶宗氏则在“赐金还山”之后,因此,李白入长安之前其妻或妾只能是刘氏或鲁妇人了。无论是谁,李白这一时期婚姻很不幸福,理由如下。其一,《南陵别儿童入京》云:“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写妇女的诗很多,大多是颂扬和友善的,而这首诗用了“愚妇”二字,用“愚”来形容女子,在李白诗中绝少见,可以看出对家室的讨厌程度。李白不能治产业,还嗜酒浪游,其妻妾或屡有劝阻,与朱买臣妻相似。不然李白诗中何出此语?这也成了李白急于求取功名的原因之一。这首诗和以后的《别内赴征三首》一比较,更能说明问题。赴征,一般认为是赴永王诏征,《别内赴征三首》有“出门妻子强牵衣”语,远离则别妻和子,和入京待诏翰林只别“儿童”大异其趣。李白《赠友人》“弊裘耻妻嫂,长剑托交亲。他日青云去,黄金报主人”,也是表白了对妻的不满情绪。其二,李白在一段时间内有思子女诗,独无念妻之诗。《寄东鲁二稚子》:“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赠武十七谔》:“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送杨燕之东鲁》:“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李白的朋友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云:“谪仙在梁园,爱子在邹鲁。”为何李白的妻妾在他们笔下没有反映?与杜甫比较,相去太远。一提到杜甫,人们立即会想起许多他对妻子描写的佳篇佳句,如《月夜》独看明月思念丈夫的妻子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江村》之“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等,无不表现了夫妻之间的深笃之情。其三,李白后来和宗氏感情甚笃,写了不少相关的诗歌,这正说明李白是重夫妻之情的,而入长安前后无诗言及其妻妾,正好是那时婚姻不幸的佐证。李白后来续取宗氏,郭沫若认为李白娶宗氏估计当在天宝三年,从上述李白思念儿女的诗看,李、宗结合时间还要晚些。李白《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与魏颢的记载“终娶于宗”相合。李白晚年写了许多爱情诗,正反证了开天之际的婚姻不幸。《万愤词投魏郎中》:“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朋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老妻当指后续娶之宗氏,宗氏在豫章。《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云:“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郭沫若认为李白和宗氏有共同的信仰,都信仰道教,而且宗氏和前妻的子女能和睦相处。李白的寄内、别内的诗大多为宗氏而作。可以这样说,李白入京以前在婚姻上的不幸也是文化上的不适,婚姻的不幸使其受到压抑,一旦得到被征召的消息,长久的内心郁闷便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李白入长安也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这一点研究者关注较多。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一直没有消退,入长安前,有人劝其隐居,他说:“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其《赠从弟冽》诗云:“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圭。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有人到长安,他在送别时也表明对长安的向往之情,《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李白对再入长安是渴望的。凡此种种,都说明李白受召入京其心情是无比兴奋的,“仰天大笑出门去”,一快长期积聚在心头的愤懑;但也预示李白在政治中心的遭遇,他会以失败而退出京城,事实正是如此。[4]
李白入京待诏翰林,在文化意义上可以作出许多有意味的诠释。他能入京是顺应当时皇家文化的结果,他的崇道行为在开元、天宝之际取得了朝野的认同和赞誉;而他在东鲁与儒学文化构成的是冲突的关系,他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应注意的,他对儒学的批评与其理解为是对一种思想的批评,还不如理解为是对具体对象即鲁儒的批判,对意识形态中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对具体对象的批判,在本质上有相当大的区别。另外,李白一生多娶,其婚姻在盛唐文人中颇有特殊性,由于材料的不充分,已经无法作出更为准确的分析。尽管婚姻的矛盾具有私人化倾向,但我们将李白在东鲁的婚姻危机作出文化冲突的解释还是合情合理的,通常讲的生活习惯的不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