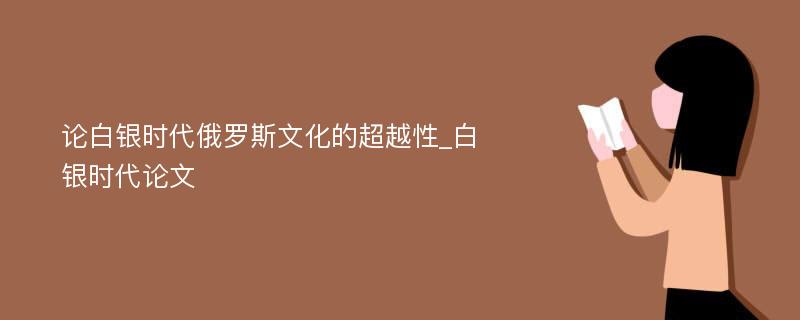
论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的超时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时代性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2)02-0022-07
近年来,在国内外俄罗斯文学界,“白银时代”已经成为热点和焦点之一:有关这个 时代作家、诗人、思想家、宗教哲学家及神学家等的中、外文论著及上述作家各类文体 著作作品等纷纷出版。无庸讳言,对这个时代的文化成就及其价值判断,具有整体意识 的归纳概括不是完全没有,但还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分歧。本文结合国内外专家的论述 ,陈述些初步观点,以求正于方家。
一、政治与文学:“白银时代”的上下限问题
政治与文学具有紧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须臾不可或 离的空气。欲要脱离政治而把文学从其赖以存身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犹如揪着自己的头 发想要脱离地球一样难。我们看到,在国内俄罗斯文学界,目前之所以在“白银时代” 的上下限问题上有分歧,根本原因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在国内外俄罗斯文学界,一般把“白银时代”的上下限,定为1895- 1917或1925年,没有把它视为一种跨时代(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的文化现象。而笔者则认 为:其上下限应当定为1890-1930年。
把“白银时代”的上下限定为1890-1917或1925年的观点,实际上是以“十月革命”为 文学或文化的分期标准,其隐含的前提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两种文化。这是传统文学史上通常的划分法。实际上,早在“白银时代”这种提法产生 之前,在苏联出版的浩如烟海的各类文学文化史(如各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 史”等)中,就是这么划分的。问题在于:文化与政治的变革在许多时候是不同步的。 并不是在一场影响世界政治的大革命发生之后,立即就产生了与革命的要求相适应的新 文化,从而与此前的文化截然有别。在更多场合下,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是不完全 同步、完全不同步甚至是相互抵触或对立的。文化或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如按 照同步的观点,则我们势必将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许多文学及文化现象,如“未来派”、 “俄国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宗教哲学派文艺批评等,腰斩为革命前和革 命后两段。而实际上,“十月革命”的发生并未造成这几种运动的断裂,支配这些运动 代表人物的“历史内驱力”,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都是同样的,那就是 想要变革社会、建设新文化的愿望。俄国“未来派”和“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在政治 和文学上,都是激进左派的代表,他们拥护革命的立场在革命前后是一贯的,不曾有任 何的间断。而且,这两个运动,都是在革命后才达到其发展的巅峰状态,即未来派的余 脉“列夫派”和奥波亚兹的“狂飚突进”(1918-1926)。
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俄国文化都处于文化的转型期阶段,是各种流派相互争奇斗艳 、各种主张针锋相对、众声喧哗这么一个“文化狂欢节”时代,嗣后才形成的大一统格 局和单一创作方法居主导地位的景观此时还是遥不可及。这和物质生活的困窘形成了一 种鲜明的对比。许多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作家、诗人、甚至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们 ,忍饥受寒,为着建设新文化而努力工作。1920-1922年间的全国性大饥荒,丝毫也没 有影响知识分子建设新文化的热情。当时,不但“未来派”、“奥波亚兹”这样的左派 知识分子,就连历来以自由派自居的知识分子,如巴尔蒙特这样的唯美主义者、索洛古 勃这样的“反动”作家、维亚·伊万诺夫这样的“古典知识分子”,以及像尼·别尔嘉 耶夫这样的知识界名流、“路标派”等,在革命后初年,也都是这一历史大变革的拥护 者。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分野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在此期间,一方面,俄国现代派中 的先锋派(“未来派-列夫派”、“构成主义中心”、“先锋派戏剧”等)正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传统的现实主义流派也有了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演变趋向,出现了从以高尔 基、布宁等人为代表的“星期三”派向后来被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的过渡,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倡导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为特征的经典之作,如《毁灭》、《 夏伯阳》、《铁流》、《静静的顿河》等。苏联文学的标志性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是在1934年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才被确定为官方的文学创作原则的。 在此之前的整个20年代,文化上的多元和转型——这一“白银时代”的文化特征——始 终都是这一时期中俄罗斯文化的突出特征。直到1929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同情现代派 的人民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被免职及次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一个轰轰烈烈、众声喧 哗、以对话和狂欢为标志的时代,才宣告结束。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和重组也才宣告最 后完成。
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文学并不单单只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因此,在分析文学及文 化问题时,首先要尊重文学或文化的发展规律,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才有望真正认识一 个文学或文化时代及其重要价值。
二、我们时代的重大发现
在当今俄国,“白银时代”是俄国处于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形势呼唤出来的一个产儿,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发现。具体说,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是当今俄国在苏联解 体后所出现的非意识形态化、历史的反思、文化的解禁、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折射,是召 唤出来的一个过往时代的幽灵,也是今天这个时代与往昔的一次特殊的对话。
无可否认,“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是一大笔值得深入研究和继承的丰厚的思想文化 遗产。这一遗产,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并未完全被其后的苏联文化所承继,而是出现了 不应有的断裂。对此,曾经不止一个文化人为之痛心疾首。在今日之俄国,就有许多文 化人在为这一文化断裂而痛惜,如有一部轰动一时的历史文献片,即起名为:“我们失 去的俄罗斯”。在这位知名记者及与其相仿的俄国文化人眼中,“十月革命”后,断裂 了的不仅只是俄罗斯精英文化,而且,甚至就连伏特加酿造法和俄式大餐这样的饮食文 化,也随之失传了。(注:指戈沃鲁欣主笔的电视纪实片《我们失去的俄罗斯》。1992- 1993年间,在俄国曾一度播出,颇为轰动。笔者曾看到过此剧的电视剧本。)这种观点 主要为当今俄国的民主派所宣扬,但它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正如白银时 代是俄国文化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是19世纪一直遭到贬抑的斯拉夫派学说和以莱蒙托夫 (1814-1841)、丘特切夫(1803-1873)、费特(1820-1892)等人为代表的文学传统的继承 一样,白银时代文化自身也是整个20世纪俄语文化和文学的先驱。在国外,侨民文学和 文化是她的显性体现;在国内,她是一系列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隐性先驱。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这样的非“十月革命”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之 所以能在今日俄国走红,正是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俄国文化召唤出来的一个幽灵。
实际上,在如何对待旧文化问题上,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有过明确指示:无产阶级文化 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而是此前所有文化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无产阶级文化是在继 承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的所有成果基础上才有可能。“无产阶级文化应当 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 展”。但在“十月革命”后初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外武装干涉 者的绞杀中生存,在遍布全国的饥荒中维持人民生存的问题,暂时还顾及不到或未全面 顾及到文化建设问题。尔后,随着列宁逝世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矛盾的激化,革命的近 期目标与文化建设的长远任务发生抵触,致使党在文化政策问题上发生了极左偏差,使 得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前景产生怀疑,知识分子队伍发生改组和分化。列宁的正确主张 因此而未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于是,产生了第一次侨民浪潮。第一次侨民浪潮由两部 分人构成,一部分是20年代被流放的国内知识界名流(即“教授船”),包括近200名知 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自愿流放的知识界、文化界、创作界人士(如列夫·舍斯托夫、 布宁、索洛古勃、巴尔蒙特等人)。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发生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必然。革命与文化都以瞄准 未来为指向,但在实现其任务方面,两者作用的层面有所不同:前者以现实地改造世界 尤其是政治经济关系为旨归;后者则更多地着眼于精神、观念、理念和理想层面的改造 ,是一个需要假以时间期之长远的任务。“十月革命”后的整个20年代中,大批知识分 子之所以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拥护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寄希望于继物质革 命之后必然而来的精神的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论”的影响是不 容低估的。今天,“白银时代”文化之所以能受到青睐,其根本原因也恰恰在于这一时 代文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对人的关怀、俄罗斯式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传统,俄罗斯民 族特有的传统理念(如弥赛亚意识、索菲亚观念等)。但我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 块儿倒掉,而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这一段文化的历史经验,为发展我国社会 主义文化提供他山之助。
我们肯定“白银时代”的文化价值,并不等于否定“十月革命”的全人类意义。“十 月革命”代表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苏联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20年代中人们相对忽略了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合理 继承问题,因而造成俄国文化的某种断裂。今天,我们有必要把断裂了的文化传统重新 接续上,从以往的文化遗产中,吸取对于今天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必要的因素,但不能因 此否认“十月革命”的全人类意义,而是要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从而为今天的文化建 设服务。
三、俄国的“文艺复兴”
“白银时代”这一术语自产生以来,其内涵有逐渐扩大之势。最初,该术语仅指20世 纪初的俄国诗坛。后来接过这一术语,并用它来表示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 文化的,是西方斯拉夫学界。近年来,俄国本国也基本上认同了西方对这一术语的界定 。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新的发现层出不穷,“白银时代”也被相应提高到了俄国“文 艺复兴”的高度。(注:认为“白银时代”是俄国文艺复兴的,有尼·别尔嘉耶夫为首 的几代文人。尼·别尔嘉耶夫的相关论述,参见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 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56页。)我们认为:“白 银时代”或“白金时代”的确可以说是俄国的文艺复兴。
首先,“白银时代”是俄国人文主义精神的一次显著的复兴。
和雅典“黄金时代”及欧洲以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样 ,俄国的“白银时代”也是一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解放运动。1861年俄国农奴制 改革只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而“白银时代”才是一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神解放运 动,是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俄国文化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也就不会有1890年以后的白银时代。而白银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理念, 主要是通过她的参加者,即俄国知识分子为主体体现的。参加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主 要是俄国两大京城里的文化界名流和知识界精英,其总数也和欧洲文艺复兴一样,不过 数百人而已。俄国由来已久的两类知识分子——向往西欧的贵族知识分子和来自平民的 知识分子(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等)——都被裹挟到这一历史 潮流中来。这些知识分子相互之间无论有多大差异和分歧,但在一点上是高度统一的, 即腐朽的专制政体已经走到尽头,时代呼唤更民主自由的社会政体和更新的民族文化。
促使俄国两类知识分子积极参加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动因,与俄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特 点密不可分。俄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一种弥赛亚意识,即认为俄罗斯民族注定要在世界 各民族中起主导作用。而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精英,必然肩负领导民众的使命。在强烈 的使命意识推动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创造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俨然以救世主自命 ,要为万世立则,为生民请命,开始了五花八门、形色各异的思想探索,企图给处于没 落中的俄国文化,寻找到摆脱普遍混乱的途径和出路。一场延续了30多年的思想解放运 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内驱力推动下形成的。这些思想探索是在专制政权已然腐朽并且 必然灭亡的末世论意识下进行的,而且,其所提出的命题,也都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特点。此时发生的力求寻找到社会的精神基础的“新宗教意识”运动,代表人物是梅 烈日柯夫斯基(1866-1941)、罗赞诺夫(1856-1919)、吉皮乌斯(1869-1945)等,就是一 场以探讨宗教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神学与政治结合形式为主旨的思想运动。“路标派 ”更是以探讨人的精神结构及人的观念建构问题为主旨的运动,它们的不适时性是相对 的。以上两种运动都是在末世论哲学的映照下进行的,它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俄国文 化深层次的矛盾。俄国文化历来受到双重性的困扰(多神教与东正教、专制主义与无政 府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等),而呈现出在两端之间摇摆的发展轨迹。是个人主义、自我 中心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公众性,其实也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命题 。
与这类时代命题相应,在大批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努力下,“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提出 了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主张。传统的真善美统一理念及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的唯 物主义美学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诗人可以不代表“公民”而只张扬个人。取代“美 能拯救世界”命题的是美的虚幻、善的软弱和真的相对。衡量善恶的那杆秤被置于新的 对比关系中重估。适应时代需求的精神界领袖,也不再是传统上的康德、谢林、黑格尔 等,而是尼采、叔本华、戈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诗学也借着美学更新的推 动而走上繁盛之路。国内战争时期枪炮的轰鸣也无法掩没缪斯的伦音。各种诗学研究和 诗歌创作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饥饿和严寒也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文化呈现出 多元共生的局面。
判断一个时代是否伟大,够不够得上“文艺复兴”的美称,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是否为 世界贡献了一流的文化瑰宝和一大批光彩夺目的天才。天才是民族性最深厚的载体。一 个没有天才也未产生天才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缺乏民族独特性和独创性的民族。而“白银 时代”恰好是一个如文艺复兴那样应该产生并且也大量产生天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涌 现出来的一大批天才人物,业已成为或必将成为整个20世纪的经典、大师。正如埃·莱 斯所说的那样,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所提供的成就,其后许多年中的人们仍将在黑暗中 摸索。这是一个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全面开花、到处结果的辉煌时代,末世论映照下的俄 国知识界,反而迸发出令世界各国都瞠目结舌的创造热情和蓬勃旺盛的创造力。
四、一笔有待研究的丰厚文化遗产
俄国文学和文化在“白银时代”焕发出了夺目而又璀璨的光辉,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 ,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芭蕾、舞蹈、音乐、美术、戏剧等领域里,涌现出一大批旷 世英才,创造了为世界各国所嘱目的辉煌成就。这些英才,有许多已经被写进了未来的 20世纪文化及文学史册,成为如今人们研究这个时代时不能轻易绕过的丰碑。
俄国人以不善于抽象思辨而著称。俄国哲学与文学历来有水乳不分之特点。19世纪俄 国哲学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影响,但却并未跟着西欧哲学大师们走上纯思辨和 抽象思辨之路,而是永远不脱离个人体验和现世经验。真正具有有机整体性和抽象思辨 性的俄国哲学,开始于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1853-1900)。其后德·梅烈日柯夫 斯基(1865-1941)、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安· 别雷(1880-1934)、维亚·伊万诺夫(1866-1949)等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美学体系 。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存在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神学、象征主义等,如若忽略俄 国人的贡献便将是残缺不全的。
在文艺学领域里,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及宗教哲学派文艺批评、俄国形 式主义(奥波亚兹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都是在很多领域里影响了 整个20世纪的文艺学流派。其中,俄国形式主义与后来的布拉格学派、塔尔图-莫斯科 学派(尤·洛特曼)、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和符号学(罗兰·巴特、托 多洛夫)、美国符号学(罗曼·雅各布逊)的联系,也有着清晰、可寻的发展轨迹和脉络 。巴赫金学派则是与该派平行发展起来的一种泛形式主义诗学体系。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相辉映、两相媲美、平行发展的 宏大景观。一方面,传统的19世纪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列夫·托尔斯泰、契 诃夫、布宁、库普林、高尔基、安德烈耶夫等人笔下,在与现代主义的交相对立过程中 ,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发展,对之,我们还研究得不够。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则提供了 不同于西欧的蓬勃发展的艺术经验。从象征主义而阿克梅主义再到未来主义先锋派,一 脉相承或批判继承的发展线索清晰可见,其美学诗学探索的经验有待更深层次的理论概 括和把握。在这方面,不宜把统一的未来派和列夫派分而论之,以为其在十月革命前后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活跃于这一时期的一大批散文大师、小说巨擘,其创作经验亦有待 于在新的意识观照下予以阐释和研究。如杂糅魔幻与现实的布尔加科夫与魔幻现实主义 的比较;安·别雷以音乐为主体艺术构架的意识流小说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比较;等 等。俄国现代派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19世纪乃至更早期的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 加进了适应新时代特点的变化,呈现出与西欧现代主义不同的本质,揭示其特点对于丰 富艺术创作经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俄国第一代侨民文学也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景观。其中获诺贝尔文 学奖的伊·布宁,名列美国当代文学前五名重要作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纳博 科夫等人,也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选题。其他如霍达谢维奇、亚当莫维奇、别尔别洛娃 、苔菲等人的有关资料,正在陆续出土,相信会成为俄苏文学界未来非常重要的选题。 此类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的成果势必会把重写苏俄文学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新的苏俄 文学史应当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学史和非主流文学史的有机统一体,而不是两者的简 单相加或凑合。写作这样一部文学史首先需要以写作者自身文学观念的更新为前提。
“白银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获得丰硕的成果。和文学一样,在戏剧舞台上,既有以斯 丹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涅米洛维奇·丹钦科(1858-1943)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表演 、导演体系,也有以打破“第四堵墙”为宗旨的梅耶荷德(1874-1940)的先锋派实验话 剧。音乐中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拉赫玛尼洛夫(1873-1943);斯克里亚宾(1871 、1872-1915)等,都是引起世界瞩目的成就。芭蕾舞则有嘉吉辽夫(1872-1929)为首的 巡回演出团,为俄国芭蕾赢得了世界顶尖级的荣誉,安娜·帕芙洛芙娜则是此期涌现出 来的世界级明星。绘画领域则有一大批名人——列维坦(1860-1900)、谢洛夫(1865-191 1)、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伯努瓦(1870-1960)、巴克斯特·多布任斯基(1875-1957) 、拉里奥诺夫(1881-1964)、冈察洛娃(1881-1962)、马列维奇(1878-1935)等,作为现 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传记和回忆录。这是此期文化成 果最丰饶的领域之一,也是传统文艺学方法可以大显身手之处。研究文学终究不能脱离 文学的语境。文学与人的命运的关联,不仅体现在文学特有的题材领域里,更多地体现 在从文者的命运——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域里。在这 方面,在看似个人的命运轨迹里,却折射着时代的身影和历史的悲剧性。如果时至今日 仍把安娜·阿赫玛托娃的遭遇当作是她个人的际遇,而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另一部苏联文 学史的话,那就会是一种浅薄。在这方面,“白银时代”文化名人及其相关资料的陆续 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库。有些好的传记或回忆录,本身就是对作家文本的 一种阐释,研究者只要读懂作家文本和传记这两部书,就有望真正窥见文学的底蕴。如 果说对于俄国研究者来说,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作品文本本身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 于我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仅仅研究文本或只限于文本本身,就不够了。正因为我们所 处的“外位性”,我们也才可以并且必须采取比俄国本国研究者更加宏大的视角,因为 我们担负的任务,要比俄国本国的研究者更大,即除了要讲清你对文本读解的心得外, 你还必须告诉你的中国读者,你论述的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及其他有关作家本人的种种缘 由。但我们也反对根本无视作家的创作、而仅仅根据一些已有文学史的结论论定作品的 做法。在文本阐释方面,应当鼓励有个人的独立见解,甚至出现一些“误读”也是可以 理解的,如若不然,搞舆论一律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未免太乏味了。“白银时代” 各类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作家、诗人,都有有关的精彩的传记或回忆录。华夏出 版社近期出版的“双头鹰文库”所推出的8本传记回忆录就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种。
总之,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应当向包括俄国在内的国际斯拉夫学界,展现我们中 国学者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跟在人家身后人云亦云。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所谓 俄国文学的中国学派才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可能。
收稿日期:2001-11-25
标签:白银时代论文; 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十月革命论文; 文化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艺复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