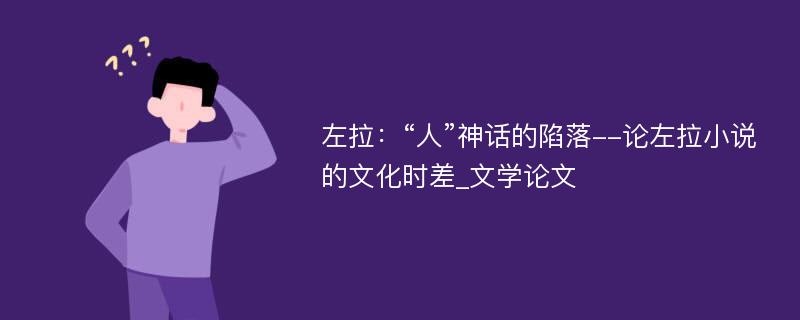
左拉:“人”的神话的陨落——论左拉小说的文化时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拉论文,时差论文,神话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作为自然主义所倡导者的左拉,他的名字往往和这一流派捆在一起,而由于自然主义在我国曾长期受贬抑,所以左拉也总是得不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那样的礼遇。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纷纷为他打抱不平,写了些“翻案”文章,以图扭转这种局面,给左拉和自然主义以应有的地位,但实际效果并不见佳。综观以往的研究,贬抑者认为,自然主义偏离了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它的出现标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的衰落;左拉作为自然主义的倡导者,他的成就不在于自然主义本身,而在于他的创作实践突破了理论的束缚后走向了现实主义,不过,自然主义的倾向在左拉的创作中仍然是存在的,是他的创作的“局限性”,因而他与正宗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相比还略逊一筹。翻案者认为,左拉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者,他的创作将巴尔扎克等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并不比正宗的现实主义作家逊色,甚至可以与巴尔扎克相媲美,因而,左拉实际上就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显然,无论是贬抑者还是翻案者,他们研究的结论虽然不尽相同,但评价的尺度和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他们都用现实主义这一人们“熟知”的价值尺度去衡量自然主义以及左拉在何种程度上投合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趣味和文化模式。这种价值尺度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熟知”的东西并不一定适于解释未知的东西。
自然主义作为19世纪后期出现于欧洲的新文学思潮,不管是继承还是背叛了现实主义传统,它都有自己产生与存在的历史与文化的根由。文学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或思潮都是文学史和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各自都有其不可重复、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价值,都代表着一种文化观和审美观的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但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同古往今来的其他文学思潮与流派一样,并不能成为可以取代一切的永恒的文学价值标准。事实亦已说明,20世纪的现代主义并不因为其反19世纪现实主义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它存在和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它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同样,步19世纪现实主义之后尘的自然主义虽然在创作上与现实主义不无继承关系,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影响的文学思潮,它也不应只有依附于现实主义的“霸权统治”才有生存权力,左拉也未必一定要由巴尔扎克来赐封文学殿堂里的座位。自然主义自有对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独特贡献,左拉也必然有其发展着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给予他的应有的地位。新一代的作家和文学思潮的出现,如果只能用旧时代的文化与美学标准去评判的话,那么这种评判永远只能削足适履,文学史也就永远裹足不前。当19世纪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已成为昔日黄花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只能站在现实主义的文化基点上,用现实主义的价值尺度去看自然主义——不管是企图贬抑还是翻案,那都缺乏历史发展的眼光。我们必须跳出“唯现实主义独尊”的思维怪圈,抹掉现实主义的“常识”蒙在我们眼睛里的透视障碍,以更公允、历史的态度,不带偏见地站到自然主义本身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点上,站在自然主义之后众多文学流派与思潮纷呈更迭的文化背景上去考察自然主义和左拉的创作,这样,我们也许会观赏到左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2
卡西尔认为,人是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文化则是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与对象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1〕因此, 特定时期的文化,必然投射了特定时期关于人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和总体认识。文学是人学,它作为构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而且以人的价值观念的演变为自身演变的重要动力源。特定时期的文学中必然潜隐着该时期的文化的投影,因此,新旧文学思潮的更迭,必然也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嬗变,新旧文学之间必然存在着文化时差。从这个意义上看,左拉走上自然主义的创作道路,是有其文化动因的,他的创作与他的前辈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文化时差。
在近代文明史上,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拓宽了人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视野,也改变着人对自身本质属性的看法。十九世纪是自然科学以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大踏步地推动文明、 文化进程的时代。 其中, 1859年问世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欧洲科学史、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在近代以来欧洲传统文化的“板块”上轰开了一道深长的裂缝。“在达尔文之前,人由于存在着所谓的灵魂而被排除在动物王国之外。但进化论却使人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成了动物世界的一个成员。这个激进的观点的被接受,就意味着对人的研究可以沿着自然主义路线去进行了。人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除了他的更复杂性之外,跟其它生命形式没有什么区别。”〔2〕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改变着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精神文化气候,左拉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形成其有悖于传统观念的新文化价值意识,从而走上自然主义的创作道路的。
左拉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崇拜巴尔扎克和雨果,但又为自己生于巴尔扎克和雨果之后而感到生不逢时。他的那种力求创新的个人意志时时警告着他:要超越巴尔扎克,而“不能象巴尔扎克那样”。〔3〕为此,左拉努力寻找一种能足以“向巴尔扎克挑战”〔4〕并击败巴尔扎克的方法。这种方法首先来自于达尔文等人的遗传学、生理学理论。1864年,法文版的达尔文著作在法国出版后,“左拉如饥似渴地阅读过”。〔5〕达尔文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人和动物在生物性这一层面上存在着共同性,生物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种自然属性。这种理论深深触动了左拉,他曾经为“被看作是命运化身的遗传学所激动”,〔6〕“生物的人”的观念也由此开始形成。 他曾经构想出撰写一个关于“科学或哲学的诗作的三部曲”的计划。〔7〕达尔文是促使左拉的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变化的自然科学家。 此后,左拉“又读勒图尔诺医生的《情感生理学》。1865年,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出版……左拉如获至宝地读过这部书,……不仅遗传学为他的小说里的人物提供了必要的联系,而且科学也为他提供了新的表现方法。”〔8〕在1868年到1869年两年间, 他又仔细研读过吕卡斯医生的《自然遗传记》,并作过详尽的摘录。吕卡斯认为,“人是大自然的缩影,研究人就是研究自然。在社会方面,遗传牵涉到所有制,政治方面牵涉到主权,世俗方面牵涉到财产。遗传是法制、力量、事实。”〔9〕左拉一度将吕卡斯的遗传理论看作科学真理, 并用来研究人和社会。除自然科学外,当时流行的实证哲学也深深影响着左拉“生物的人”的观念的形成。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是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孔德把社会现象解释为生理现实。他认为,“社会的流通有如动物的血液循环。整个社会象人的机体一样,存在着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器官的互相关联的关系。正因如此,如果某一器官腐烂了,其他许多器官将受到感染,于是,非常复杂的并发症将随之出现。”〔10〕孔德的这种思想当时遭到严厉的谴责,“然而,左拉却选中了他的这种思想”〔11〕,而且,以后他还根据这种思想绘制了一个关于人和社会的世界分支图,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就是以这个世界分支图为结构基础的。〔12〕泰纳的艺术哲学也为左拉自然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泰纳的理论是以生物学作为结构框架的,左拉无疑通过泰纳的理论加强了他在人的问题的认识上与生理学的联系。总之,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冲击下,左拉形成了对人与世界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总体认识,传统的那个理性的、社会的、抽象的人,在左拉头脑中成了“生物的人”。他认为,“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人的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样。”〔13〕“具有思想意识的人已经死去,我们的整个领域将被生物的人所占有。”〔14〕左拉的这种说法不免有些言过其实和极端化。其实,社会的、理性的人在左拉的观念中还是客观存在的,他所说的“具有思想意识的人已经死去”,只不过是当他拨开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迷雾,惊异地发现那个崭新的“生物的人”时产生的一种情感化的、辞不达意的表述而已。当然这也说明他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对“生物的人”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个“新人”形象凸现在他的脑海中,而传统文化所描述的那个关于“人”的神话,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支离破碎、模糊不清了。这标志着左拉的精神世界中新的文化观念的形成。
3
显然,在文化观念上,左拉超越了前辈作家巴尔扎克和雨果等人。对左拉来说,文学创作就是对人做实验,作家就是医生,而且,他认为,“作为生物学的人已经进入了文学,并且是那么强而有力。”〔15〕在创作中,左拉虽然并不对人作纯生理的研究,事实上也无法这样做,而往往把生理研究与社会研究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小说在描写人时,生理和遗传因素常常和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展示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社会的真实风貌。但是,生理学和遗传学始终是他研究人和社会的切入点和基本方法,“生物的人”也始终是他描写的中心。他是从“生物的人”这一透视点放射开去看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对人的作用的。因此,他的创作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不无反传统倾向。
左拉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要写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里,“自然史”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起点和贯穿始终的主线。1869年,左拉在给出版商拉克多瓦提交的关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计划中表明了他写这部巨著的基本设想:第一,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的问题,逐步探索同父所生的几个孩子由于杂交和特殊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不同的情欲与性格。总之,以生理学上的新发现为线索,到人的高尚品行和巨大罪恶得以形成的生活的深层,去开掘人类惊心动魄的戏剧。第二,研究整个第二帝国时代,从政变起到今天,通过典型的人物展示这个社会,描写英雄和罪人,通过描写各种事实和情感,并通过描绘千万种风俗和事件发生的细枝末节,来展现这个社会。从左拉的这个基本设想中可以看出,他描写人的前提是:人是生物。他在小说中要展示的就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怎样互相联系、互相争斗并形成一个具有生物性联系的社会,这个社会又怎样制约这些人。不管左拉的这种设想与观念是否正确合理,但事实上左拉是以此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的;不管左拉能否不折不扣地按这一指导思想进行创作,但我们确实可以从他的小说中看到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他笔下的中心人物基本上没有偏离他预先设计的家族血统图中的既定位置,这些人物大多都具有明显的生理学特征:他描写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结构是以自然性、生物性为内在基础的,这个“内在基础”就是他要寻找的“现实的内部隐藏的基础”。〔16〕
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阿戴拉意德·福格两次结婚所生的。由于福格患有精神病,她与健康的卢贡结婚所生的后代中多数是健康的,但有的因遗传因素而患有精神病。福格在卢贡死后与神经不正常、酗酒成性的私货贩子马卡尔同居所生的后代,都因父母双方的不健康而患有各种先天性疾病。显然,两大家族的成员都是按遗传规律繁衍开来的。而且,卢贡家族的后代中有的是金融家、医生、政治家等,成了上流社会的成员,而马卡尔家族的后代则多数是工人、农民、店员、妓女等,成了下层社会的成员。两大家族的后代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处境和结局虽然有其社会的原因,但作者充分强调了遗传因素的作用。这样的描写符合左拉的指导思想与创作原则,也体现出了“生物的人”的观念。
两大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虽然不能不具有社会的、理性的特征,但“生物的人”的特征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文化与审美的意义。《娜娜》中的娜娜可以说是情欲的象征符号,在她身上,左拉集中剖析了作为“生物的人”所具有的原始本能——性本能。性本能作为人的一种生物属性,是人类得以生存与繁衍的永恒能量,就其自然形态而论,无所谓善恶美丑,但在特定的社会群体、社会环境中,就获得了伦理道德的含义。左拉正是从自然的、生物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娜娜及其周围的人揭示性本能在社会群体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在这种表现形态中又显示出人的精神品格与道德风貌。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小说第一章中,左拉紧扣着性意识、性心理去描写娜娜那非同寻常的首次登场:
娜娜是裸体的。她凭着十分的大胆,赤裸裸地出现在舞台上。
她对于自己能够主宰一切的肉之魔力,有十分的把握。她披着一块
细纱,然而,她的圆肩,她那耸着玫瑰色的乳尖的健壮的双乳,她
那诱惑地摆来摆去的宽大的双臂,和她整个的肉体,事实上,在她
所披着的薄薄一层织品之下,那白得象水沫似的整个皮肤任何一部
份都可以揣想得出,都可以看得见。……她举起两只胳臂,她腋下
金黄色的腋毛,在脚灯的照耀下,台下也都看得见……从她身上,
飞出一道色欲的光波,就和冲动的兽类身上所发出来的一样,这个
光波在散布,并且越来越强烈,充满了整个剧场。〔17〕
当娜娜这个原始本能的象征符号出现在舞台上,观众的反应如何呢?作者有这样有一段描述:
台下没有掌声。没有一个人在笑。男人们往前紧倾着身子看,
一个个露出郑重其事的面孔,和受了猛烈刺激的五官,嘴里都有一
点发痒,有一点干燥。似乎有一阵风吹过去似的,一阵轻柔又轻柔
的风,风里带着一种神秘的威胁。忽然间,发现站在台上的这个女
人,象一个跳跃不定的孩子,她没有一处不暗示人兴起饥渴的念头,
她给人带到性的妄想,她把欲的不可知之世界的大门,给人们打开
了。〔18〕
台上台下的两种情景给人们揭示的几乎是纯生理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吸引,这两幅图景中的人的存在状态几乎完全是一种生物性的自然状态。观众们以娜娜为圆心,在她发出的“性磁力”作用下,形成一个向心圆。整部小说所展示的人物关系,也就是这样一个向心圆型结构形态。使这个向心圆得以稳态存在并发展的主要是“生物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性吸引力。莫法伯爵、舒阿尔候爵、银行家史坦那、公子哥儿乔治和他的哥哥菲力浦、戏子丰当及其朋友普鲁里叶尔,等等,这些所谓的“社会名流”、“上等人”轮番追逐娜娜,个个都想将娜娜占为己有。正如左拉所归纳的:“一群公狗跟在一只母狗后面,而母狗毫无热情,并且嘲弄着跟在她后面的公狗们。男性的欲念使得世界不得安宁的巨大力量。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供他们玩弄的女人和他们一心追求的荣誉与地位。”〔19〕这里的“男人们”显然只能是特指那些腐化堕落的“上等人”,在他们对娜娜的生物性追逐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他们卑下的道德风貌,也披露了畸形社会中人的变态的精神、心理与情感世界,小说也因此达到了强烈批判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现实的效果。但这都是在剖析人的性本能及其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形态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娜娜》的整个描写中都弥漫着性意识,主要人物形象的突出特征是生物本能的强烈奔突,小说为我们描绘的也是一个生物形态的人类社会——虽然其中不乏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德莱丝·拉甘》、《人面兽心》和《土地》中,左拉通过德莱丝·拉甘、雅克·朗蒂埃、塞瓦丽娜、弗安等人物的描写,集中解剖了情欲驱使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残杀。在这些人物身上,左拉形象地给“生物性的人的好斗和性欲以适当的位置。”〔20〕《萌芽》是一部描写工人斗争的优秀小说,它的社会意义之深刻,是左拉小说中少有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即使这样的小说,作者也没有改变从“生物的人”的角度描写人这一创作原则。在这种生物过滤镜的透视下,工人的行为方式是受生理因素的支配的,他们的反抗,是生存竞争的生物规律发展的必然。小说告诉人们,在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物的性本能成为男女关系的内在纽带。主人公艾蒂安身上,留有马卡尔家族中酗酒的遗传基因,这种生物基因使他的行为常常具有破坏性。这类描写当然有损于工人的形象,更谈不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但我们不能由此忽视其中的新的文化意识。《崩溃》是一部以描写战争本来面目为宗旨的小说,但左拉是用生物学观念去观察与分析战争的,因此,他揭示的“战争本来面目”也具有特殊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他描写的战争场面中看到这一点:
您可以想象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糟透了的洞窟
,一个真正的漏斗,四周都是树木,那些普鲁士猪猡可以四脚爬近
,使我们注意不到他们的偷袭……那时,刚七点钟,炮弹落到我们
的饭锅里。真是混帐透顶!不容迟疑,我们马上跳向枪架。直到十
一点钟,真的!我们以为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了……可是,您应该
知道,我们并不是一支五千人的队伍,而那些猪猡倒不少。并且继
续不断地袭来。我,我在一个小丘的荆棘丛后边卧着,我看见正面、
左边和右边,哦!爬出真正的蚁群,一行一行的黑蚂蚁,当您以为
没有了,可是他们还有,还继续爬来。这不是要说长官的坏话,可
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的长官都是没有头脑的金丝雀,他们要我们拥
塞在这样的峰窝里,远离友军,使我们被敌人压倒而无人来援助我
们,……城市大概被占领了,我们转移到一座山上,我想,这就是
他们所说的美斯贝尔吧。到了那里,我们隐藏在一个宫堡里,把那
些猪猡杀了那么多!他们从上往下跳,看着他们大头朝下倒下去,
的确很有趣的……〔21〕
在左拉的笔下,战争中的人是生物性的,战争也带有生物界那种盲目地互相残杀的意味。由此他对人类战争的作用也得出独特的看法:“战争是可诅咒的,然而它就是生命。在大千世界中任何事的诞生、成长和发展无不经过斗争。为使大千世界永远存在下去,必须吃掉别人,或者被别人吃掉。”〔22〕《崩溃》中表达的正是这种物种竞争思想指导下的战争观。正如法国小说家都德所指出的,“《崩溃》不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种关于战争的哲学著作。它研究人类最强烈的本能的大暴露。”〔23〕
我们如此强调左拉小说中的人的生物性和“生物的人”,并不是无视他的创作的社会性和在社会批判上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也不意味着对他的这种生物性的人的描写大加赞美,而是想强调指出:左拉小说中的“人”的形象确实是生物性的,这是否认不了的客观历史现象,左拉确实“不同于巴尔扎克,因为他要在他的作品里阐明生理因素的作用。”〔24〕文学是人学,左拉小说所展示的“人”既是社会性的,也是生物性的,而且首先是生物性的。人类不管进入到何种文明的社会,人的生物性永远是人性的一部分。正如左拉在小说《人面兽心》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有了火车跑得更快了,也更聪明了……但是,野兽终归是野兽,无论人们发明什么样的机器都无济于事,人类之中仍然还有人面兽心的东西。”〔25〕左拉小说中生物性的“人”的形象的描写,正是他对“人”的文化观念的艺术形式的表述。
4
左拉小说对生物的人的描写,当时曾引起了许多读者和批评家的谴责与攻击,他们把左拉的小说视为“腐败文学”,骂左拉是“一个热衷于色情描写的疯人”,一个“淫秽作家”〔26〕。而左拉却不以为然。在文学作品中到底怎样写人的生物属性?人的生物属性是否可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左拉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的生物性的格外关注,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淫秽”、“伪科学”,也不能只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出发,简单地把这种描写看成是对文学的社会性的削弱,将其列为左拉创作的“局限性”或“消极因素”就万事大吉了,而应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充分看到这种貌似“消极因素”的文学现象里蕴含的新文化因素,而且,这种客观存在的新文化因素不会因为人为地贴上“消极”的标签后就走向消亡,而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影响后世的文学,成为连接文学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个中间环节。
左拉小说中“生物的人”的出现,标志着自古希腊到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中关于“人”的神话的陨落,标志着20世纪流行于西方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文化观念的萌芽。在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殿上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的文学中就记录了童年时期的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们,实际上就是原始初民自我形象的幻化投射。神和英雄具有放纵原欲、追求自由的个性,因为他们把原欲和自由都看成是人自身的属性,而不是动物的属性,并且,原欲和自由都是借助人的理性和智慧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希腊神话与史诗中所揭示的“人”是一个高于动物的崇高的理性化形象。神话与史诗所具有的那种乐观与浪漫,正是离开了自然的母腹,摆脱了动物的习性的原始初民的自豪感的体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人”的形象实际上被上帝所取代了,而上帝在本质上是人的理性的异化形态。基督教把人的原欲看作是“原罪”,人性就等于理性,而理性便是上帝。中世纪宗教文学中“人”的形象是理性的抽象符号,由于他远离了动物,因而显得崇高而又空洞,神圣而又不现实。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既呼唤高贵的理性,又寻找失落了的自然属性——原欲,但原欲来到眼前时,却又不敢正视,“原罪”的宗教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与其说他们是“巨人”,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儿童,离开了上帝妈妈后步履蹒跚地走向“魔鬼”横行、充满险恶、前途渺茫的道路上,充满了焦虑、恐惧与迷惘。哈姆莱特便是最突出的典型。18世纪的浮士德深感自身存在着恶欲的冲动,但又坚信善与理性的力量,在他一生不断追求生命价值的过程中,理性与善终究战胜了原欲与恶,“人”永远不会丧失高贵的理性而变得“比禽兽还要禽兽”。浪漫主义者雨果虽然让恶站在善的旁边,让丑靠着美,让理性与原欲处于同一平面,但他最终仍然让美与理性的象征的爱斯梅拉尔达,让冉·阿让取代了一切融善与恶于一体的人。雨果似乎也不愿意承认人与动物有必然联系。巴尔扎克虽然已感染了自然科学的精神,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依然囿于传统的价值规范中。他虽在朦胧中感悟到人的原欲的难以扼制,这种原欲在环境的刺激下会使人从恶如流,对此,他感到恐惧与迷惘,但对人又抱有人本主义式的浪漫的幻想。当他借高老头之口喊出“人类将要灭亡”的惊呼时,其实又深信人并非动物,人的高贵理性在一时迷失后终将复归。总之,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长河中,人们对自身的自然属性虽不时地有所觉察,“人”的形象几经变幻,但始终在理性光环映照下,具有向上帝般圣洁的神话世界飞升的趋向。这种关于“人”的神话,在以非理性主义为文化内核的西方现代文学中已宣告破灭。左拉的创作则是“人”的神话破灭的先声。他有幸处在进化论等自然科学和哲学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下半期,这种精神文化气候使他在巴尔扎克等前辈作家的关于人的探索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他的创作把“人”的形象从理性主义的圣堂中拉回到生物的世界中。左拉当时备受攻击,不为许多读者和批评家所接受,其原因正在于他的创作中出现了一反常例的‘生物的人’,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时差的客观存在。我们当然应当看到左拉对“生物的人”的描写中存在的非科学、非道德化倾向,也要看到他的创作所达到的现实主义高度及其为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我们更应看到他创作中存在的那种文化时差。因为正是这种文化时差表明了他的创作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拨和对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的催化。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左拉创作中的新文化观念对20世纪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指现代派文学对性本能、性心理、“恋母情结”、白痴、虐待狂、偏执狂、荒诞主题、病态精神、酒精中毒、色情狂的人物等的描写都和左拉的创作有渊源关系,更重要的是,左拉小说中表现的“‘生物的人’这种思想,在他之后进入了世界各国的小说创作”;〔27〕这种“生物的人”的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文学对人的描写的既有领域,而扩展到了人的生理性区域。这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心理学是相关联的,他们是被同一条文化纽带所串联的。“生物的人”虽不同于现代主义文学热衷描写的“非理性的人”,但却已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文化范畴而步入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显然,左拉是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与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链条上的中间环节,他的创作在文化观念上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重性,正是他开创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与文化的价值之所在。
注释: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288页。
〔2〕〔美〕卡尔温·斯·华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 新美国文库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第5—6页。
〔3〕〔4〕〔5〕〔6〕〔8〕〔10〕〔11〕〔12〕〔14〕〔15〕〔20〕〔22〕〔23〕〔25〕〔26〕〔27〕〔法〕阿尔芒·拉努《左拉》,黄河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5、142、145、142、143、143、144、 178、178、345、355、359、345、133、345页。
〔7〕〔美〕M·乔斯弗逊《左拉和他的时代》,纽约,1958年英文版,第71—72页。
〔9〕转引自郑克鲁《左拉文艺思想的嬗变及其受到的影响》, 《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13〕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16〕《外国文学参考资料》(19—20世纪初部分)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789页。
〔17〕〔18〕〔19〕左拉《娜娜》,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21〕左拉《崩溃》,转引自阿尔芒·拉努《左拉》,黄河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页。
〔24〕〔法〕让·弗莱维勒《左拉》,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第40页。
标签:文学论文; 巴尔扎克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左拉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崩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