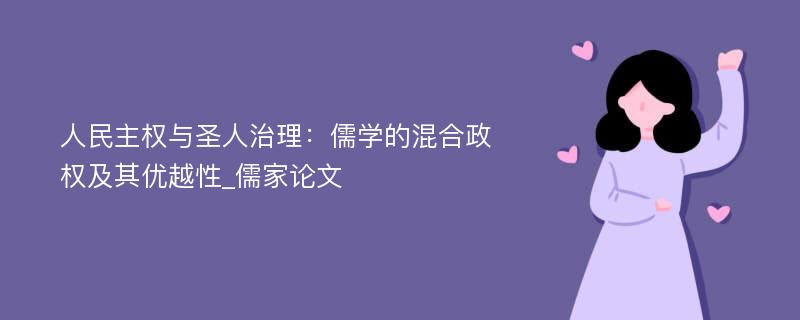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治权论文,政体论文,优越性论文,主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关注的主题,是儒家的理想政体是什么,这个理想政体比当今所公认的理想政体、“历史所终结”到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更优越。新儒家如牟宗三者,专注于从老内圣(儒家道德形上学)中开出新外王(民主)。放开这种开出是否扭曲了儒家、是否牵强造作不谈,这一努力的价值,即使成功,也很值得怀疑。因为它所达到的极致,也只不过是儒家可以是自由民主的真诚的拉拉队成员,对自由民主的批评与建设性贡献极其有限。我们也因此完全可以只读康德,不读儒家,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似乎也不会丢掉什么。
体会到这一点,蒋庆近年致力于政治儒学,要给出儒家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套制度①。但是,他所理解的儒学,乃是基于他对汉代公羊学的一种(很有争议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他对他所提出的儒教三院制的优越性的论证之主要方式,可以说是“因为它是儒教的,所以它是好的”。这种论证,除了能说服儒教——或者更准确地说,蒋氏儒教——信徒外,难以服人。并且,与此相关,他对其三院制之优越性与必要性的另一论证是,自由民主基于西方文化,即基督教,而中国乃儒教国家,因此无法采用自由民主,而必须采用基于儒教的政体。这一论证,问题之一是中国是否(蒋氏)儒教国家?虽然说“独尊儒术”,但是儒家(更不用说蒋氏之儒教)是否是传统中国唯一主流意识形态,很难讲。经过百余年对传统的肆意践踏,很难说当今中国人还保存有多少传统价值。问题之二是,尽管自由民主产生于西方,但是否它只能在西方生长?马铃薯生于美洲,但是现在却是全球人桌上的食物。第三,这一论证看似原教旨,但是违背了早期儒家视儒学为普适价值、适合所有“华夏”之人(这里“华夏”并非族群,乃是文明②)、甚至包括蛮夷的信条③。
因此,与新儒家不同,本文致力发掘儒家理想政体与自由民主之不同,并进一步给出这种政体优越性的论证。与蒋庆不同,本文的优越性论证,乃普适性论证。这里的儒家理想政体,无论对于儒家、中国人,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更好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着重于对当下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但是并非对其全盘否定。下面批评的核心,乃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但是自由民主的其他成分,比如法治(宪政)、权利(自由)等,问题较少,可以基本接受。当然,儒家如何不改变自身特点来接受法治与权利,也是个大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也认为新儒家为此太过削儒家之足,适西方之履,并认为可以有更保持儒家根本精神的认可宪政与自由的方式。对此笔者已有论述,不再重复④
儒家是个大传统。因此,谈论“儒家”,很容易落入大而无当的境地。本文所论儒家,将基于《孟子》。之所以选择《孟子》,是因为:第一,它是公认的儒家经典之一,至少代表了儒家内部的一个主流传统,而不是为了作者“欲加之罪”,而从两千年儒家传统的犄角旮旯的尘土下翻检出来的;第二,它比《论语》在论证上更详尽些,这使得我们的解读不至于被认为过于随意。因此,贯穿本文,凡提到“儒家”,我们所指的是基于对《孟子》解读的思想,而不是泛指。
一、孟子理想政体的基本要素
对孟子之政府合法性来源及其责任,笔者已有基于对《孟子》文本分析之上的论述,这里只是提纲挈领地总结一下⑤。孟子认为民为邦本,即人民之满足乃政权合法性之来源。当统治者不能让其人民安居乐业,他可以被废黜、甚至被革命(《孟子·梁惠王下》)。甚至当作为先祖、神的代表(后来进一步变成了国家象征)之社稷未完成其对人民的义务的时候,也可以变置(《孟子·尽心下》)。
那么,政府要满足人民的什么需求呢?这当然包括了人民物质需要的满足,但也要包括人民精神(人伦)需要的满足。就孟子而言,没有圣人领导的政府,人民不但无法使自己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而且,即使满足了物质需要,人民还可能因为没有五伦而近于禽兽。而只有圣人领导的政府,才能教民以人伦,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就孟子而言,理想政府不但不是当今西方主流思想中的必要的恶、甚至是不必要的恶,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源泉,即必要的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否认人可以脱离人群、社会、政府而存在,或者说,可以脱离这些而存在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最多是像人的禽兽而已。但是,孟子也意识到,人民的道德养成,是以物质满足为基础的,即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又见《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孟子认为,政府的责任在于满足人们的(短期与长期的)物质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他们的道德,即政府还要有教化人民的责任。
那么,人民是否满足,判据何来?答案自然是人民,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至此,孟子的理想政体中有了民有与民享。很多心仪儒家,但是又觉得民主不得不接受的学人,也就因此论证儒家与民主是吻合的。但是,他们忘记了,现行自由民主体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治。但是,虽然人民的满足与否自然要人民说了才算,但是,知道人民的满足或不满后,应该如何做,孟子认为,这是人民力所不及的事情。因此孟子坚持大人、小人之分,把治理国家的重担放到了大人肩上(《孟子·滕文公上》)。大人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恻隐之心。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他们还要从日常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治人者食于人”(同上)。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孟子又同时认为人皆有四端(《孟子·公孙丑上》、“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有责任创造一切条件(物质、教育等),让人民发挥潜能。但是,对大人的强调意味着,孟子又认为,现实中真的能够达到士人、君子的,终究是少数(为何如此,孟子没有明确说明)。其多数,即所谓人民者,因为智慧与同情心有限(从孟子由四端定义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人是小人,是描述性的,描述了他们人性幼小的状态),无法对政治有良好的判断,因此政治治理,要落在士人与君子的手上。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大人与小人的区别,并非天生,更不是基于既得利益或者固有权贵阶层,而是在起跑线上平等基础下“选举”(选贤举能)的结果。儒家的等级,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同时也是流动的。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对人的社会性和道德性的认知基础上,孟子的理想政体中对政府合法性来源和责任有所规定。这一政府要反映民意,但同时要有孟子意义上的精英和士人的作用。根据这些基本想法,我们可以想象孟子理想政府的构成。但是,不管它的具体实现方式如何(它可能有不同的具体实现方式),因为上述根本特征,尤其是它虽然认同民有与民享,但是不认同民治,它必然要与当今建立在民有、民享、民治的自由民主政体不同。在我们给出孟子理想政体的一种实现方式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当今自由民主政体内部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从这种政体内部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局限。对这些问题的认清,不但可以让我们看到上述孟子的根本观念的优越,也会给我们构建一个孟子式的理想政体提供指南。
二、民主的四大根本问题
世界上多数人可能仍然相信自由民主是可能条件下最好的制度,是“历史的终结”,有如福山的一本有广泛影响的书的书名所指出的一样⑥。当有人指出民主的诸多问题时,民主信仰者中相对温和与开明的人士常常诉诸传说是丘吉尔的巧妙回应:“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府形式,除了所有其他那些曾经被尝试过的[政府]形式外。”⑦虽然很机智,但是这一说法可能显示了我们思维的懒惰,因为它缺乏理论与经验的支持。经验上讲,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在控制腐败、制定好的长期经济政策、减低族群冲突、选择有能力的和代表人民的真实意愿的领袖上,民主国家并不总是或者并不明显地比非民主国家做得更好⑧。
从理论上讲,就笔者看来,民主,尤其是一人一票的制度,存在着四大问题。第一,在一人一票制度背后的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尤其在美国)是对人民能力的信任,并由此常常引申出对精英甚至政府权力的怀疑⑨。这种信任常常与一种极端的、歌颂自我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相共鸣。对人民的相信和对精英与政府的怀疑,在美国,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第一,一个候选人是否能当选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他是不是“可爱”(likable),是不是“我们”(大众)的人,是不是能够来我们家坐坐的人。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布什班子的“杰作”之一是成功地将克里(John Kerry)描述成东海岸的精英。支持布什的人相信了这个宣传,而反对布什的人认定布什是个与大众打成一片的乡巴佬。但是,事实是,布什家族也来自东海岸,并实际上比克里家族要显赫得多。小布什和克里同样上的是耶鲁大学,参加了同一个耶鲁大学内部的精英组织。并且,美国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小布什的大学平均成绩比克里还要稍高些⑩。布什阵营对布什背景的掩盖和对克里的攻击是一人一票背后之反智、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怪胎。第二,美国政客为了被选进中央政府经常要吹嘘自己是局外人,而他要在政府里做的事是(最大限度上)消灭政府。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支充斥着“凡人”,充斥着蔑视政府,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那些选他们的人也不会太尊敬他们。这大概是为什么:
在对美国人于政治机构的尊敬程度的大多数调查中,原则上所有政治机构里最代表民意的美国国会得分最低,而全是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军队、联邦储备银行得分最高。(11)
引述了这一事实后,贝淡宁用它支持他的基于贤能统治、因此要求对政府尊敬的儒家模式(12)。
第二,一人一票制缺乏有效的机制,将非选民(包括过去与将来的本国人和所有外国人)的利益考虑进来。因此,民主在应付下述问题上就有根本困难:财政赤字(即把将来国民的钱花在这一代选民身上)、环境问题(即把将来国民的资源花在这一代选民身上)、对在本国居住的外国人(合法与非法的移民)之处理(13),以及对外援助和其他涉及外国人利益的政策。比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那些与美国工人利益有关的利益团体(工会以及被这些工会所支持的民主党)经常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会伤害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外国工人的利益(14)。
第三,与第二个问题相关,哪怕是在那些现有选民中,其强势的和声音大的往往压制那些沉默的和被沉默的选民。这是导致民主国家种族问题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在那些新近民主化的国家里(这些国家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尚未健全),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种族清洗。
第四,即使对于那些可以表达自己利益的选民,他们是否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也十分可疑。如很多政治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公众对政治的可怕的无知是一个“六十年来现代公共意见研究”所很好地建立起来的事实(15)。
由以上因素共同导致的问题之一是外交政策。外交需要专门知识、耐心甚至是痛苦的对话和长远规划。但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在一个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中,比如美国,外交政策经常被一时的公众情绪影响。这一情绪常取决于电视里报道了什么,而不是什么在国际、外交事务里最重要。另外一个影响外交政策的是国内政治交易,即支持某项外交政策的议员或行政官员经常会通过答允支持另外一个议员或官员的一个国内项目以换取后者对该外交政策的支持。这些因素明显与好的外交政策的真正需要背道而驰(16)。
三、对上述问题之非贤能政治的解决及其根本局限
很多自由民主思想家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给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一个明显的回应是号召尊重理智(及有理智的人)和(尽责的)政府。对理智和有智慧的人的尊重并不必然意味着违背平等。人们还可以在诸多方面是平等的,因为平等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一种尊重政府的方式是通过公民的信念,它告诉公民政府是必要的善,而非必要的恶,更不是不必要的恶。普选应该被理解为首先是选拔最有能力、最配得上政府职位的,而不是对坏政客的惩罚(17)。这些修正可以在不违背他们的根本信条的基础上,为一些自由民主思想家所接受。
上节所述前三个问题的一个共同原因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不道德的、极端的版本,它被一些人当作民主的神圣意识形态基石。根据这种个人主义,我们是并且应当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除了自我利益外(这里的“自我”指的是原子或单子式的个人),我们不应该关心任何其他东西。通过部分让渡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我们成为一个政府下的公民,归属其管治。我们这么做或是因为在这一政府之下,通过某种机制(往往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我们摆脱了自然状态下我们的利益不断受到其他自私之个人所威胁的状态——这样政府就是必要的恶,或是因为我们被哄骗得这么想——这样政府就是不必要的恶。只要我们不违反作为交换条件的政府对我们的规管,我们就应当可以任意地坚持我们自己的利益。如上所述,这里“自我”是在其原子个人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自我利益是在狭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比如祖先与后人的利益,或是外国人的利益,并不必然成为这种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当然,这也不是说自我利益在这里只能包括自我的短期物质利益。它可以是这个狭隘自我所认可的任何利益,比如宗教信仰。在美国有所谓“议题选民”(issue-voters)。他们根据自己的某些信条投票(比如对堕胎、持枪权,等等),而对其信条之正确性不向与他人的公正与公平的讨论敞开。这样,民主就退化成了一种气力之争,哪一派强(以票数多少计),哪一派的意旨就得以实行,而另一派在不心服口服的情况下伺机反扑。民主的稳定只不过是一种权宜(modus vivendi)。
也许是看到了这种自私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及其后果,罗尔斯反对一人一票等同于数脑袋的观点,并论证,为了投票能够有正当性,投票者必须考虑公益或者其他投票实体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狭义的个人私利(18)。对选民的这种道德要求,我们可以从晚期罗尔斯对自由民主理解的一个核心概念,“讲理的”(reasonable),及其相关的公共理智(public reason)和礼尚往来(reciprocity)的概念里引申出来。关于“讲理的”这个概念,罗尔斯指出:
在公民互相看作是在一代代的社会合作系统中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他们准备好互相提供公平的合作条款……并且在其他公民接受这些条款的前提下,即使在己方在特定情形下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同意依照这些条款行事,这时,公民就是讲理的。(19)
与此相对,如果一个人只依照自己的“无所不包的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来投票,如果他只因为己方的主张没有达到多数支持,才不得已接受失败,并随时准备不择手段来改变己方失败的命运,那么这样达到的稳定罗尔斯称作“权宜”(modus vivendi),是一种没有基于正确原因的稳定(20)。所以,根据罗尔斯的想法,作为自由人民(liberal people)的一员意味着不仅仅是基于自己的私利(包括物质的和教义上的)来投票,而是要基于某种公益的概念。当然,他理解的“公益”可能要比儒家的概念弱些。但是,他对选民的要求依然是(薄的)道德性的。
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点?如何能让人民的道德达到罗尔斯对公民的要求和我们要面对民主的前三个问题的需要?为了能达到这种“公民友谊”(civil friendship)(21),罗尔斯诉诸教育和习惯养成——他称之为道德学习(moral learning)。这一学习的进行,要通过自由民主制度所安排的社会与政治机构(22)、通过家庭(23)、通过国际和国内的政治与文化环境(24)。他同时也寄希望于政治家(statesmen)的作用(25)。
但是,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和充分呢?如果选民的大多数能够是在罗尔斯讲的意义上讲理的,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关注非选民和弱势选民的利益。但是,如果讲理的选民不占多数,那么上面提到的民主的前三个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的坏影响、对非选民和弱势选民的忽视)还会存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明显出路是让那些不讲理的选民向那些讲理的选民(主动或更可能是被动地)让渡权力。但是罗尔斯寄希望于让所有或至少是大多数选民都讲理,而鲜有提及培养对讲理的选民和政府的尊重。但是,看起来我们不太可能现实地期待讲理的选民构成选民的多数。实际上,罗尔斯自己给出了为什么在一人一票制下这种期待不可能的一个论辩——他把这个论辩归于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回应这个论辩。他写道:
在每个公民都有一票的自由社会里,公民的利益趋向于缩减乃至集中在他们的损害社群纽带的经济私利上,但在一个咨询式的等级制下,当他们(所属)的群体是如此地被代表(即每个群体才有一票),不同群体的投票成员就会考虑政治生活里更广泛的利益。(26)
当然,是否讲理的选民可以构成多数,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民主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上面提到的民主的第四个问题,关于选民对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利益都不能正确理解的问题。包括罗尔斯在内的自由民主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以及这些解决的根本缺陷,笔者以前有过论述,现在还是坚持这些论述(27)。因此,本节所余论述,只是已有论述的摘要。
首先,罗尔斯接受了黑格尔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指出没有经济基础的自由是空的。政府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和教育需要。同时,要排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做到这两点,因此政治成了商业利益的工具,国会也成了这些利益的交易所。在政府没有做到上述两点工作之前,这种状态无法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除了罗尔斯提出的这些安排,言论与资讯自由以及其他对人民政治知情相关的自由的维护明显地也很重要。并且,公众还要有闲暇去消化这些信息。比如,公众是否应该被给予政治讨论的“假日”,在投票前对相关政治问题有所学习和了解(28)。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在当今民主社会已经会被看作很极端的方式仍然不能充分解决选民知情的问题。历史上看,第一个民主国家雅典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两条保障:奴隶制和小国。奴隶制把雅典公民从日常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成为孟子所说的劳心者和参与政治的大人。与此相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绝大多数是全民劳动的社会,公民没有闲暇。他们表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只是给了他们某种专门技能,而不是对政治的了解。雅典是小国的事实,也使得政治事务相对简单,人民对政治人物了解充分,国家利益与团体/个人利益更可能一致。这些使得共和制政体的良好运作成为可能。对后一点,西方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等人都有论述(29)。与此相对,尽管当代自由民主对公民参与的要求比共和制政体所要求的低得多,但是孟德斯鸠提到的根本问题还在,甚至可以说是加重了。当代政论家Robert Kaplan和政治学家Russell Hardin对此问题有类似的论述(30)。特别是,Hardin还指出,一个公民如果是理性的,就不应该去投票,更谈不上去为投票而对政治事务知情。另外,有些公民也不希望参与政治,这应该被自由社会所允许。但同时,他们对政治干预的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
总之,上面提到的这些当代社会现实造就了公民对政治知情这一一人一票的先决条件的根本障碍。我将其称为当代社会的第六事实(31)。这一事实包括:人类有滑向私利的倾向,而一人一票鼓励了这个倾向;总是有公民愿意选择对很多政治事务采取冷漠态度;绝大多数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民主社会,都太大了。其结果是不论政府和个人花多大努力,其公民的多数很难充分地对相关政治事务与政治人物知情。这一问题有多种根源:第一,由于现代民主国家太大了,并且我们高尚地拒绝了奴隶制,对政治(包括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基本的知情这一负担为大多数公民的智力、教育、意愿所无法承受。第二,现代国家的人口使得一张选票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第三,大公司和财团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近乎疯狂的财富在对公民道德、对精英献身公益事业的意向、对信息的控制上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都相对很大且要全民劳动的现代社会里,当代民主社会的第六事实就意味着罗尔斯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慎议民主制(deliberative democracy,它们都对人民的道德与知识有一定要求)是现实上不可能的。
四、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
在我们对民主的问题及其内部解决之局限的理解的基础上,现在让我们来依据第二节所讨论的孟子的想法建构一个儒家理想政体,看它是否能够更好地解决民主的问题。为简便起见,我将这个理想政体称为“孔氏中国”。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体现了孔孟的一些根本观点,并且它是一个理想形态。这个政体不预设狭义的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狭义的儒家文化指的是在中国或是东亚社会号称曾经或仍然占主导地位的、限定于特定人群的那种文化。正相反,这个政体设计是普适性的,适用于满足上节所讲的第六事实的所有社会。这个政体也不是要支持经济发展的所谓中国模式(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模式的话)。过去和现在中国的政体中也许有“孔氏中国”的一些特征,但后者从未完全在现实世界中充分实现过。下面,我会给出这一政体的架构。
第一,法治与自由/人权为“孔氏中国”所认可并被牢固建立起来。这如何可能、这种认可如何不违背儒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32)。
第二,从本文第二节对孟子思想的讨论,我们可以引申出,在“孔氏中国”,政府被认为需要对人民的物质与精神负责。它有责任帮助人民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需要、社会关系需要、道德与政治的需要、受教育的需要。在物质需要问题上,经济的不平等依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得到容忍并加以控制(33)。在教育问题上,除了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外,政府还有责任给每个公民以道德和公民(civic)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让他们懂得:每个公民应当对他人有同情心并与他人保持恰当的人伦关系;政府的功能是维护人民的物质与道德生活的幸福状态(道德幸福包括每个公民的五伦关系、公民之间的相互同情,等等);政治领袖应该是道德与智慧上超众的人(道德上的超众指的是这些领袖乐于将同情心外推和以“民胞物与”为目标);如果政治领袖确实在智慧与道德上出众,他们应该为人民所尊敬;公民对某个政治事务的政治参与权是与该公民是否愿意考虑公益和是否有能力对这项事务作出好的决定不可分。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包括对他们参政需要的满足。因此,在给他们以上述教育之后,如果一个公民有兴趣并有潜能参与政治,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参政提供各种方便:比如言论自由以保证公民能知情,必要的场地和时间(假期)以便他们进行政治讨论和投票,等等。
一些自由民主理论家可能可以接受尊重政府与政治家的必要性,但是,这一尊重是内在于儒家思想的。这使得“孔氏中国”能更强有力地处理当代民主的第一个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果)。一个被很多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在美国,政客经常装扮得比自己的真实状态更无知(比如像上面提到的,2004年竞选时,布什团队把布什打扮成平民中的一员,而将克里描绘成东海岸精英分子),而在东亚,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政客经常要装扮得比自己实际知道的要多。不懂装懂当然不好,但至少通过这种装扮,东亚的政客还知道有知识是好的,是执政所必需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揭穿伪造和文饰学历者,鼓励将来的领导人真正获取知识。哪怕是那些装扮者,在长期装扮后,也许会与他所装扮的信仰产生真诚的认同。如孟子在批评五霸假仁之后的修正所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但是,如果在一种文化里面(比如当代美国),有知识和经验成了对政客有害的东西,那么任何改进的希望都没有了!
上面提到过的其他民主制内部对民主问题的解决也会为“孔氏中国”所认可和推动。实际上,儒家教育可能比民主教育更能充分面对这些问题,因为,像上面提到的,民主理论家的期望在于某种公民友谊,但这在现代社会国家庞大的现实下变得不再可能,而儒家的教育强调的是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所针对的,恰恰是广土众民下的陌生人。
但是,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这些安排,哪怕有了“孔氏中国”的进一步修正,也是不充分的。这就导向了“孔氏中国”的第三种安排。这一安排明显地偏离了今天的民主思想家所能轻易认可的内在的、非贤能政治的解决方案。从我们对孟子思想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认定政权合法性来自于为人民提供的服务,并看到了上述安排对提高人民的道德与政治知情的根本局限,儒家会支持一种混合政体。除了一人一票制之外,这一政体引入和强化了那些有能力、有道德的贤能者(meritocrats)的作用。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些贤能者不像被民众投票选举出来的立法者那样为选票所左右,所以他们有可能在短期和长期、选民和非选民、多数和少数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时候,站在长期利益、非选民利益或是弱势群体一边,并且他们也有可能维护稳定和长久的政策。
儒家认为投票权(参政权)应基于(智力、道德、政治)能力,而现代民主社会的第六事实意味着很多公民在很多政治问题上都是没有能力作好的判断的。通过公民教育,我们期望他们在无法迅速提升自己的前提下,应该自愿不参与决策程序。但是,我们同时应有更多制度保障消除无能选民可能对决策带来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考虑,“孔氏中国”作出了以下的制度安排。
第一,我们应该看到,民众难以知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国家太大了。但是,对“严格意义上的”社群和地方(比如乡镇、街道)事务,几乎任何当地居民都比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的官僚有更好的认识。因为这里处理的是与居民最相关的日常事务,所以当地居民更可能有意愿去关心,而不会采取冷漠态度。当地居民的私欲也可能被地方政府制衡。所以,现代民主社会的第六事实的前提在小范围的群体里不成立。这就意味着所有当地居民都应该被允许参与其地方的事务,其参与方式或是一人一票选举地方主管,或是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公投。
当然,这里一个困难的问题是哪些事情应被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务。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当代世界里,没有地方事务是绝对地方的(只关乎一方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务”仅仅是那些对外界影响相对可以忽略的事务。就那些对外界有不可忽略的影响的地方事务来说,这一社区的选票只能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我们也要作出适当安排,以防本地选民做那些罔顾他人利益和短视的事情。同时,如果有些全国性的决策与地方紧密相关,而大众有可能对它们作出良好判断,这些政策应让公众参与,可以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一个更一般的问题是,一个有多少人的社群的政治事务的复杂程度是一般民众可以掌握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地方”的大小。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证的和经验的考察,而不是哲学家闭门造车能正确地造出来的。哲学家可以讲的是这里的一般原则:民主参与的程度取决于相应的民众作出良好决定的可能性(34)。
第二,在处理超出小群体一级的事务时,现代民主社会的第六事实的前提得到满足,这就意味着公民更有可能对很多事物采取冷漠态度,并且缺乏能力对很多事物作出好的判断。对此,我们就应该设法限制(无知和不讲理的)民意对政策的影响。这种限制可以由多种办法实现。比如,在更高一级的政治事务的投票里,在每个选民投票前,他们被要求去参加一些相关课程与讨论,或参加基于相关问题的事实的考试,而只有在参加课程或考试通过后他们才被允许投票。或者,选民投票权重可以因其课程、考试表现来调节,也可以通过教育程度、社会与政治角色等相关因子进行调整。
另外一个也许是现实里更好操作的办法是,在更高一级的立法机构里,除了直接民选的一支外(这一支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是民意表达、“天听自我民听”的机构,同时也可以制衡另一分支),我们可以添加另外的分支来制衡民意。让我们把前者叫做下院或人民院,后者叫做上院或贤能院。上院议员由智力与道德出色的人所组成(35)。
笔者可以想出三种挑选上议院议员的方式——这三种方式并不互相排除,而是可以互补的。第一种可以被称作一个层级模式。最低一级,也就是上面解释过的严格意义上地方一级的立法机构只有一个分支,其成员有相应社区的人民直选产生。他们应该尽可能地从他们本来的专业工作里解放出来,并广泛参与更高一级的决策工作。因此,他们更可能有能力参与一般民众难以把握的更高层次的政治决策。他们就可以有资格推选和被推选成为上一级立法机构中的上议院成员。这个过程可以被一级级重复,直到国家最高一级的立法机构。另一种办法是,低一级的上、下议院议员都可以成为更高一级立法机构的上议院之候选人或选举人。除了最低一级外,更高级的议员都应该是全职。
实际上,在美国政治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层级模式的痕迹。比如,在美国早期,联邦参议员和总统均非人民直选产生,而是由州议员或各州的选举人(electors)选举产生。之所以这样,恰恰是美国开国者、特别是联邦党人为了制衡无知且缺德的众意(popular will——也许应该更合适地被叫做“popular whim”)而设。他们的意图与笔者这里的意图完全吻合(36)。
第二种选拔各级上院议员的办法是以考试为基础的。比如,贝淡宁提出过以下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由一个民选的下议院和一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的‘儒家式的’上议院(他后来称它为贤士院)构成的两院制”(37)。当两院之间有冲突时,
“儒家”的解答可能是由宪法给予上议院“超级多数”(supermajority)的权力,凭借它上院[的多数]可以否决下议院的多数意见。政府的首脑和重要的部长均从贤士院里选拔。大多数重要的法令均由贤士院颁布,而下议院只起制衡上议院权力的作用。(38)
有人也许会对他的这个模式提出如下质疑。在传统中国,科举考试用来选拔官员,但是那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应试者来竞争有限的位置,这个制度经受着长期的且不断增长的压力。这还是在国家支持的普及教育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的(39)。现在,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了更彻底的国家支持的大众普及教育,这也就意味着有着更多的合格的和满怀期望的学生愿意参加考试,而可能的官员或立法者的岗位还是极其有限。我们只要看看现在中国的公务员考试有多疯狂,就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个生动的认识。这样一种考生和可能位置的比例会导致选拔的随意性以及连带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回应说,传统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没有充足的渠道来分流这些人才(40)。人才分流可以减轻上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如Elman指出的,传统中国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可以成为社会所需其他行业的有学识的实践者,这是一个不坏的无心插柳式的后果(41)。也就是说,这些考试可以无意地甚至可以说是有意地提高公民的整体政治智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考试人数远远超过可能的位置,谁被选拔变得太过随意。一个替代的方式是将通过考试当作上院议员候选人资格的条件之一。在通过考试之后,候选人可以通过相应选区的全民投票或者下一级议院的议员投票,进入上议院。另一种可能性是将那些通过考试的人送到某种学院里。在那里,他们会被给予进一步的教育,并切近观察政治运作,给出政治建议。他们也可以被送到地方政府部门,以便他们获得实践经验,以防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在这之后,通过一个进一步的选拔过程(考试或是投票),他们被选入上议院。考虑到当今世界专业化的事实,考试也可以分不同的轨道,比如经济轨、政治科学轨、自然科学轨,等等。被选人还是要被要求获得通识教育,但是同时会专攻某一特定方向。
很明显,在以考试为基础的这种选拔方式里,考试的管理是个重要议题。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道德优劣很难通过考试鉴别。这个困难确实存在。但是,考试可以引导参考人研习道德哲学著作,因此即使这无法提供他们的道德,但至少可以提高他们对道德的复杂认识。考试也可以引导人们学习过去的道德典范,而这对一个人的道德养成会有正面作用。对考试材料的掌握也不仅对人的智力提出要求,还能够考验一个人的某些德性(比如恒心),虽然这里能被有效考验的德性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全面。此外,上面提到的学院和实际工作经验等安排也可以被用来观察和考察一个人的道德与政治品格。
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法治和其他相关制度也明显具有必要性。可能有人还是会怀疑公平考试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只要想想,传统中国的科举考试、今天中国的高考、美国的SAT考试,以及有名的难考的美国外交官考试(foreign service exams)虽然有问题(大概人类社会里没有哪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决定考试内容和结果的相对公平和无争议的方式(42)。
一般来讲,对那些怀疑以考试为基础的选拔方式的可行性的人,科举以及一些更早的以考试为基础的选拔人才方式在传统中国之相对长久的成功应该可以回答他们的怀疑(43)。实际上,传统中国选贤举能的实践及其得失为我们今天设计以考试为基础的选举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44)。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科举制与以考试为基础的选拔模式有呼应。在这种模式里,笔者还提出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方式:考试通过的人被派往某种特殊学院或地方职位。明眼人可以很容易看出,前者与传统中国的太学、翰林院有呼应。至于以地方职位作为进一步考察和培训的场所,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中,我们可以找到其踪迹。在这一制度中,出色的学生先被选入太学,在太学里表现出色的学生进而被授予地方官职,在地方表现好的人再被选派回中央。还有,以考试为基础的模式也有层级,这与传统中国科举制中的书生可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以取得生员(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的资格,并且各层级都有相应的官学以及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实践渠道,也多有呼应。总之,尽管我们这里做的是哲学上、理论上的思考,但是传统中国选贤举能的诸多实践及其成败显示我们的设计并非象牙塔内随意的和过分理想化的创造。
选择各级上院议员的第三种方式是一个配额系统。上院的席位或者候选资格可以分配给那些在政治事务中表现出色并且愿意献身于公共事务的人,比如县、市、省/州的领袖、工业界领袖、科学家、各类(比如环保、少数族群、工会)非政府组织(NGO)的组织者,等等。他们的能力、经验、道德已经在他们的政治服务中得到检验,我们也可以因之而选拔他们(比如通过内部考核、票选,等等)。中国各级政协和香港的功能组别纸面上与我们这里讲的配额系统类似。但是,特别是中国的各级政协明显的没有满足“孔氏中国”的设计。比如,政协成员多是临时聚集到一起,并非专职,而我们设计上院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忙于日常工作的人民没有闲暇来思考政治问题,因此无法作出好的政治判断。“孔氏中国”的上院是立法机构,职能包括立法、选举官员,等等,而中国的政协成员没有这种权力。实际上,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都不常真的为他们所享用。法治和其他相关的政治安排(比如新闻自由)也没有充分建立起来。
这里,笔者想再次强调,这三种选拔上院议员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结合起来。特别是,我认为最后一种配额系统可能只可以是其他两种方式的补充。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上院的功能。他们可以被给予撰写全民公决草案的权力(45)。上院和下院也会被给予立法机构常有的职责:立法、宣战、选拔和确认最高法院法官、总统/总理、各级政府最高官员、大使等等。立法两院之间投票的权重应该有明确规定,在有关非选民和需要长远考虑的事情上,上院的投票应该被给予更大的权重(46),因为像笔者已经讨论过的,这些事情是选民不太可能有能力充分处理的,这也是我们要引入上院的重要原因。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所有这些选拔方式,尤其是层级模式,应该与代议制民主区分开。在笔者的设计中,那些进入上议院的成员并非是在上一级立法机构中其“选区”利益的代表,而是有能力参与更高一级的立法和决策的人士。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即使我们对他们的职责有不同于代议制的理解,即使他们可以通过成为全职议员,从他们特殊的职业中解放出来,但是只要他们要被地方上民众经常性地选举所制约,他们也不能从特殊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选民的当前的利益里解放出来。这是美国国会里常发生的情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议员通过利益交换,把联邦政府的钱花在其选区的往往是以公(联邦)济私(选区)的各种工程上(英文里称作“earmarks”或“pork barrel projects”)。这些工程往往使联邦有限的资金不能花在更有需要的地区,而是花在善于讨价还价、威逼利诱的政客的选区里。但对一个持孟子思想的儒家来讲,民众的参与并不是要发现他们当前利益的共识,政客也不应只是民众当前利益的传声筒,而是民众的真正、长远利益的谋划者。让他们摆脱特殊利益的限制是选择上院的各种方式的一个根本意图。
关于上院的细节我们可以继续整理,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安排是为了对众意形成制衡,而在政治上给予那些比较有知识、经验、道德的人士以更大的声音。如此组织的政体可以说是民有的和民享的,但不纯然是民治的。承担治理角色的,有人民,同时也有精英贤能。它是孟子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思想的一个具体制度实现,也是儒家面对自由民主的回应(拥抱自由法治,修正大众参与)的一个具体制度实现。
对“孔氏中国”模式的可欲性,会有很多批评。一类是外部的,比如,“孔氏中国”违反了自由民主的一些根本原则(平等、主权在民的合法性必须由全民投票来体现,等等)。一类是内部的,比如,“孔氏中国”会导致根据它自己的原则所认为的坏结果;我们不需要采取“孔氏中国”的模式,也能达到它所期望的结果,等等。笔者在《旧邦新命》一书的第三章对这些挑战有回答(47),在笔者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有修正后的更全面系统的回答(48)。因为本文篇幅有限,所以笔者只能希望仍然存疑的读者去参考这些文献。
本文除第一节外,主要是基于拙著《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三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77页)。但是,近年笔者对那里的观点多有改进。因此,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本文将着重于改进和变化之处。对那些没有变化的地方,笔者将只是总结以前的观点。详细论述,请读者参照上述章节。
注释:
①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蒋庆:《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如参见《孟子·滕文公上》中对陈良虽是“楚产”,但属华夏的论述。
③如孔子指出,于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另,对新儒家与蒋庆之政治儒学的具体批评,参见白彤东:《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新邦旧命还是旧邦新命?——关于儒学复兴的几点思考”》,《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
④参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第21-94页。
⑤参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第41-77页。
⑥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Avon Books,1992.
⑦出自丘吉尔1947年在英国下院的演讲(据http://en.wikiquote.org/wiki/Winston_Churchill,2011年11月29日)。
⑧Kaplan 1997和Zakaria 2003给出了一些例子。参见Robert Kaplan, "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80,Issue 6,December 1997,pp.55-80;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Freedom: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民主与腐败、民主与种族暴力冲突的关系,学术研究已经有很多(笔者感谢英年早逝的政治学者史天健让笔者注意到了这些研究)。比如,政治学者Jonathan Krieckhaus展示了在拉丁美洲,民主对经济增长在1960年代有负面的影响并应该有负面的影响(虽然在非洲,民主在1980年代有正面影响并应该有正面影响)。参见Jonathan Krieckhaus,"The Regime Debate Revisited: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Democracy's Effec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4:4(October),2004,pp.635-655.Krieckhaus,Jonathan,"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How Regional Context Influences Regime Effec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6:2(April),2006,pp.317-340.Daniel Treisman展示了影响感受到的腐败的因素有很多,而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就民主的影响而言,一个国家必须实行民主几十年,民主才会对感受到的腐败产生有意义的、但是相对较小的影响。参见Daniel Treisman,"The Causes of Corruption:A Cross-National Stud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76:3,2000,pp.399-457.Steven I.Wilkinson展示了在印度民主与种族暴力冲突之间关系的复杂图景,而Daniel Bell指出,常常地,民主化导致了种族暴力冲突的加剧。参见Steven I.Wilkinson,Votes and Violence: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Ethnic Riots in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Daniel Bell,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⑨有意思的是,在其建国初始,美国的民主实际上包含了比当今多很多的“精英”或贤能政治的成分。
⑩关于这一点的报道有一些。比如Richard Benedetto(2005),"Who is Smarter,Kerry or Bush?",USA Today.From http://www.usatoday.com/news/opinion/columnist/benedetto/2005-06-10-benedetto_x.htm,accessed on 09/28/2012.
(11)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Freedom: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New York,NY:W.W.Norton & Company,2003,248.
(12)Daniel Bell,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289,note 34.
(13)贝淡宁曾提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个有趣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合法劳工在官僚精英的管理下比在民主制度下过得更好。Daniel Bell,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281-322.
(14)我们看看比比皆是的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保护性、惩罚性关税和禁令,就可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竞选总统连任时,其政府向世贸组织就中国产品的一个申诉。对此,美国媒体明确地指出,这是为了争取那些工业州的选民。Mark Landler,“In Car Country,Obama Trumpets China Trade Cas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8,2012.
(15)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Righting the Ship of Democracy",Legal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4,34.Ackerma and Fishkin,Deliberation Da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给出了这个事实的详细描述。晚近一个对此题的学术讨论见于Bryan Caplan,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New E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在更通俗的渠道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关于美国人政治无知的报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Nicholas Kristof的一篇报道是最近的一个例子。Nicholas D.Kristof,"'With a Few More Brains'",New York Times,March 30,2008.
(16)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NY:Simon & Schuster,2001,p.27.
(17)详细讨论见Joseph Chan,“Early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the Ruler-ruled Relationship:From Political Ideal to Nonideal Institutions”,未刊稿。
(18)又见Jason Brennan,Ethics of Voting(paperback),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19)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xliv。这本书的第49页中有一个很近似的段落,而John Rawls 的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的第136页有几乎相同的段落。又见后面这本书的pp.86-88,177-178.
(20)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xxxix-xliii,pp.146-150;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9-150,pp.168-169.
(21)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7.
(22)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5,pp.44-45.
(23)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7.
(24)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7,pp.102-103,pp.112-113.
(25)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7-103,p.112.
(26)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3.
(27)详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第41-77页。
(28)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Righting the Ship of Democracy",Legal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4,34-9.
(29)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Anne M.Cohler,Basia Carolyn Miller and Harold Samuel Stone(eds.and t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24.
(30)Robert Kaplan,"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80,Issue 6,December 1997,pp.55-80.Russell Hardin,"Street-Level Epistemolog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Philosophy,Vol.10,Number 2,2002,pp.212-229.
(31)称其为“第六事实”,是影射罗尔斯曾提到的自由社会的五个事实。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xxvii,pp.36-38.John Rawls,"The Domain of the Political and Overlapping Consensus",in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ited by Samuel Freema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474-478.
(32)详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第21-40、78-94页。
(33)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60-62,pp.78-83.
(34)“孔氏中国”对地方选举的处理与当前中国的村一级的选举不同在于:第一,村(地方)的选举应该不受高一层的领导的干涉;第二,在最低的地方一级,民选政府应该是唯一的执政机构;第三,各种自由与权利应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第四,更高级的政府和立法机构也有选举成分,也就是说,选举不应只局限于村或乡镇一级;第五,某些国家事务应该由公投解决。在这几点上,当今中国所做的都不令人满意。对中国地方选举的另一个挑战是,在中国有些地方,村级选举导致了地方强势家族或强人对权力的垄断和滥用(感谢张庆熊教授向笔者指出这一点)。笔者认为,法治、对权利和自由的维护、每级政府的民主因素的加强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否是这样,我们还需要以政治学家的经验研究作为补充。
(35)很明显,在当今民主国家里,尤其是美国,这些名称会让后者注定失败,因为“人民”已经成为神圣,而“贤能”、“精英”已经天经地义地成为被调侃,刺的对象。但笔者仍然用“贤能院”是因为它表达了这个立法分支的意图,而哪个名字更能被兜售给当今的人民,这个问题笔者留给有政治智慧和手腕的人。
(36)参见Stephen Macedo,"Meritocracy and Liberal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Beyond",forthcoming.
(37)Daniel Bell,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267.
(38)Daniel Bell,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271.
(39)参见Benjamin Elman(2013),"A Society in Motion: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00-1900",forthcoming.
(40)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56-157页。
(41)Benjamin Elman(2013),"A Society in Motion: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00-1900",forthcoming.
(42)Philip J.Ivanhoe曾经向笔者提出外交官考试可以是选择上议院议员的一种可能方式。笔者这里感谢他的建议。
(43)笔者这里不是说传统中国的政体混合了贤能与民主成分,也不是说传统中国的政体是纯然贤能制或精英制的。如Elman指出的,晚期中华帝国的精英、贤能从来没有摆脱那个以皇帝为最高和最终权威的系统。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一个现代的政治系统反而可能与贤能制更相合。参见Benjamin Elman(2013), "A Society in Motion: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00-1900",forthcoming。这点笔者完全同意。实际上,如果我们用众意(popular will)替代皇帝,传统中国皇权与士权的丰富的博弈史(合作、制衡、对立)可以很容易地为我们今天探索混合制提供很好的教训。
(44)钱穆对传统中国政治提供了很多细致、微妙、充满洞见的分析。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45)参见Nicolas Berggruen和Nathan Gardels关于美国加州类似机构的功能讨论。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Intelligent Governance”,forthcoming.
(46)笔者感谢贝淡宁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47)参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第41-77页。
(48)白彤东,"A Confucian Version of Hybrid Regime:How Does It Work and Why Is It Superior?",forthcoming.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孟子·滕文公上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