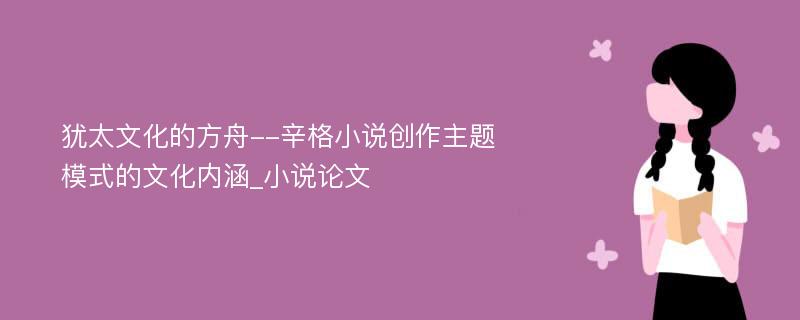
犹太文化的方舟——辛格小说创作主题模式的文化间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舟论文,犹太论文,文化论文,模式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当代作家艾·巴·辛格的创作是世界文学里一个独特的景观,它不仅固守着最贴近犹太民族的语言形式意第绪语,而且在创作中有其明确的内在一致性。对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辛格的小说“充分注意到了一个民族在放弃传统,向另一种文化靠拢时那种激烈的冲突和漫长的过程,以及相伴随的沉沦之感”。[①]国外一些研究注意到,“辛格的诸多长处之一是,他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犹太人进入现代历史的进程。从他的第一部小说《撒旦在戈雷》起,辛格就开始刻画17世纪以来欧洲犹太社会的逐渐分化。”[②]其作品的“中心主题是一个被剥夺了国家地位的民族的生存;中心的道德伦理是对人的仁慈教育,这些人被剥夺了世俗权力,却被选民的记忆和拯救的承诺所支撑着”。[③]劳伦斯·S·弗里德曼甚至更为具体地指出,“辛格小说中遍是忏悔者形象。他们受到世俗欲望和抱负的暂时诱惑,最后又回归到父辈们的信仰中去。”[④]而这种“对犹太价值的顽强坚守”在他的小说中“模式化了”。[⑤]本文认为,主题模式化正是辛格小说创作的一个总体特征,而这一主题模式,包融了丰富的犹太民族文化酵素。现有的对辛格小说的研究,虽已发现小说主题的某些一致性,但尚未加以系统观照;并且对于这个主题模式的文化意蕴,尚未给以应有的重视或充分的探讨。本文拟就此做进一步的梳理。
需指出的是,“主题模式”只是笔者行文过程中的一个工具性概念,意指主题内容及表达这一主题的基本形式上的模式化特征。两方面是融合一致的。
一
辛格虽自1935年起即移居美国,但他始终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坛的。意第绪语的创作形式使其小说如不经英译本的介绍就自动地远离主流读者群;而其小说力图复现的,也是已然消逝的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波兰犹太世界。犹太社团的分化以及分化背景下犹太主人公的“回归”,形成了辛格小说较为显见的主题模式。
按照辛格的小说描绘,进入19世纪以来,随着波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犹太传统生活滞留落伍的一面似乎越发鲜明。受到欧美大陆物质文明的吸引,犹太人激发了久受压抑的个人欲望,开始对异文化产生向往情绪;而近现代以来的数次排犹狂潮,更促使犹太人反思弥赛亚的救世神话,不愿坐等上帝的来临。此时涌入“格托”的各种运动、思潮,如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个人主义价值原则,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神秘主义,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等等,都为犹太人提供着新的价值参照。传统面临着危机,辛格以全景式笔法勾勒了犹太人的躁动心态。在他的笔下,既有被冠之以“同化者”之名的背教者,又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痛苦踱步的思考者;既有对“世界主义”的自欺欺人的信奉,又有以放纵来报复上帝的黑色幽默和无奈;既有对以暴力手段自救的迷狂,更有享乐主义和精神胜利法消除不去的阴郁悲哀。
另一方面,辛格小说又在情节设置上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追求世俗爱情自由的,反遭到遗弃背叛;从犹太教束缚中逃逸到尘世的,陷入深深的空虚落寞;听从魔鬼蛊惑的,跌进地狱深渊;处心积虑以求同化的,被非犹太世界视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总之,谁抛弃了犹太教义的基本信条,背弃了犹太道德良心,谁就归于幻灭、堕落和死亡;谁珍惜犹太历史,认同犹太身份,复归犹太精神传统,谁才会找到最终的生存价值。小说暗示了对传统价值的回归与肯定。而这里所说的“回归”虽是主人公心理流程的终点指向,但在辛格笔下,“回归”并不意味着对犹太教规教条的简单抱守或重建古老的“格托”生活圈,而是一种“适度同化”与坚持“犹太性”精神内核两相契合的浪漫理想。
但是,辛格小说中的“回归”几乎都包含着欲作分裂的内部张力。“回归”过程中的,甚至“回归”之后的悖谬感,成为主人公们常见的心态。这种悖谬感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内心的瞬时现象,而是贯穿文本始终,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回归”与“悖谬”直接参与建构了小说的主题模式,而这二者的浑然璧合,又使辛格小说在主题模式上具有了某种恒定性。不过,这一主题模式在各部作品中表现的情形是有所差异的。
公认为辛格最佳长篇的《卢布林的魔术师》,通过主人公从“背教”到“忏悔”的形式反思了回归传统的真正途径和内涵。小说描写了背教者雅夏经历自由放荡的享乐生活后,最终认识到无律法约束的生存形同死亡,而把自己关进小屋,一变成为“忏悔者雅夏”的故事。在这里,雅夏的“回归”充满悖反因素。虽然主人公最终回归到他曾极力嘲弄的最正统的“上帝——犹太子民”关系中,成为足不出户的忏悔者,但内心却感到“永远不得安宁”。这一行为本身充满强烈的自嘲和无奈,忏悔与其说是彻悟,莫如说是逃遁。雅夏正是感到了悖反张力的压迫,而采取了戏剧化的极端形式。
代表作《庄园》与《产业》(系未完成的三部曲《庄园》的前两部),通过主人公爱兹列尔的思想历程对“回归”问题进行探索,描绘了犹太人在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寻找“适度”生存点的努力和这种精神归向所面临的现实考验。处身于波兰工业革新浪潮之中,爱兹列尔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原则在犹太社区中造成的巨大冲击波,以及疯狂的排犹势力给犹太人带来的惊惧和困惑。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启蒙的爱兹列尔,同样感受到出路的迷惘。他认识到教规的无济于事,但又看到,离开犹太教义的博爱与自律法则,暴力解放会牺牲无辜,自由主义必导致放纵无度,片面追逐物利会败坏人的心灵。小说最后,爱兹列尔决定回到象征民族之根和真理之源的巴勒斯坦;同时,他并不为此而主张民族本位价值观念的无限膨胀,相反,他谴责为了“民族利益”而“牺牲人类”。小说中,追溯古老犹太精神的理想情绪昭然若揭。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第绪语作家伊萨克·雷卜·佩雷茨曾指出,“‘犹太性’应当是包含在犹太人灵魂中的博爱精神。”[⑥]而早在罗马统治时期,犹太领袖希勒尔也曾把犹太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⑦]。小说事实上认同了犹太教义中推己及人的博爱思想以及道德自律精神,然而小说主人公仍为犹太教中的愚昧保守因素所困扰。小说刻画了现代犹太人拥有“回归”的精神理想和在实践中很难将之具象化的分裂处境。
辛格最后一部有份量的佳作《萧莎》也暗寓了“回归”与“悖谬”的主题模式。小说描写已经部分世俗化的犹太青年作家艾伦,在希特勒即将进攻波兰、生活潦倒、写作处在低潮的情形下,拒绝了能给他带来成功与富裕的美国女人贝蒂和其他几个情人,娶了身心发育迟缓的犹太姑娘萧莎为妻。小说表达了犹太人对他们的根——他们的文化、历史、思想方式和表达自己的方式的眷爱和归附。在小说中,萧莎是个发育不健全的女孩子,20年来,她不但保持了孩子式的容貌身姿,而且一如孩子般纯洁天真。然而就是这种迟缓,锁定了岁月之流,使她成为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犹太人“过去”的化身。对艾伦而言,萧莎代表了他个人失落的天真品质,更代表了在战争残害和工业文明威胁下日渐萎缩的犹太生存方式。与萧莎相对照出现的是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拉、寻求刺激与死亡的西莉娅以及美国文明的体现者贝蒂。艾伦对她们的排斥、放弃,实则印证了“犹太人热爱的是《旧约全书》及其释文、神秘哲学、《生命之树》和《智慧起源》”[⑧],而不是某个激进的“主义”的领导。他们需要的不是闭目塞听地自欺,也不是逃到新大陆文化的“庇佑”下消融民族特征,他们需要的是犹太经义倡导的智慧,博爱和自律精神。小说结尾,海穆尔和妻子的一段对白颇耐人寻味:
“照你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和吉泰尔人[⑨]也没什么区别了,”吉妮
娅说。
“只要我不打人、不杀人,我这个犹太人就当之无愧。”
……
“吉妮娅,《十诫》也是人写的,而不是上帝,”海穆尔说,“一个人
只要不伤害别人,他自己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⑩]
小说对“回归传统”的意义作了宽泛化的界定。“回归”并非恪守教习,但无疑,它肯定犹太历史,犹太身份,以及自律、博爱的道德信条。微妙的是,辛格笔下的艾伦从来就不是忠贞不移的恋人,也不是自我牺牲的英雄。他从未有过理性分析的决断,也未曾对决定感到欣喜,相反,他以“宿命论”自嘲,甚至婚礼当天还感到绝望。小说仍然用“回归”与“悖谬”的模式表现了惯常的主题。
辛格就是这样,在其一系列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在欧洲犹太社会日趋分化的状况下,犹太人皈依民族精神传统的复杂心态。当然,任何一个基本主题模式都会有其变型,即在基本模式上的扩展、压缩或嫁接。例如长篇小说《莫斯卡特家族》,以20世纪初华沙一个犹太家族由盛而衰、最终解体的情节为主干,揭示了抛弃犹太教规,追逐同化和“现代化”所造成的悲剧后果。和辛格以往小说略有不同,这部小说未以一个“回归”式的主人公贯穿文本,但作者的苦心孤诣仍可体察。小说中,莫氏家族的败落显然并未归因于战时经济的衰退,而是归因于对世俗物利的追逐和对犹太传统规范的背弃。可以说,小说运用了基本主题模式的变型,以反证归向传统价值的意义。
还有一点已为论者注意并指出:辛格的短篇小说在题材与主题上与长篇不甚相同,“着意刻画小人物的各种深沉的激情。”而且相应地,在表达主题时,由于篇幅等因素所限,也不存在完整曲折的“回归”模式。这种差异显然不应当否认,不过,二者也有一定的关联和一致。
首先,在主题上,辛格用那些充满激情的小故事,善意地嘲弄了教条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揭露了唯理性论的苍白贫弱。名篇《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的菲谢尔森博士潜心钻研斯宾诺莎30年,对其哲学作教条主义曲解,到老年,体弱多病,了无生趣。最后是复苏的人性和迟来的爱情使他理解到人生的意义。菲谢尔森博士的生活喜剧,嘲笑了理性的不堪一击,同时这也和辛格长篇中的一贯主题相一致,倡导的是对犹太传统作精神上的把握。
其次,辛格短篇小说在正视人性的必然要求的同时,更重视对犹太教义传统,特别是道德自律品质的提醒。在《布朗斯维尔的婚礼》中,对死难犹太人的回忆和传统犹太人在美国格格不入的感叹掺杂在一起,吐露了失落传统的美国犹太人的茫然,以及对犹太传统的眷恋。《镜子》中,齐莱尔敌不过情欲和虚荣心的诱惑,终于和小魔鬼一起跌进地狱;《傻瓜吉姆佩尔》中,主人公虽虔敬上帝,却也难免听从报复的恶念唆使,往他即将做成面包售出的面粉团里撒尿。魔鬼的诱惑无所不在,正昭示出道德自律的拯救意义和势所必需。
此外,辛格小说中也不乏对传统信仰的怀疑、矛盾,甚至连犹太民族坚信已久的美好未来也不再有意义。《渎神者》的主人公查兹凯尔一生都在用“渎神”的方式跟那种以上帝的名义讲话的人斗。实际上他对信仰的痛恨和对强权的困惑与“卢布林的魔术师”雅夏如出一辙;《短暂的礼拜五》里,心灵圣洁的苏雪和丈夫的极度虔诚迎来的却是突如其来的死亡,他们的一生就是犹太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化石;《重逢》(又译《归亡》)则更流露了悲哀的色调:倘若说1957年作者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在受尽愚弄之后还深信来世必是“没有纠纷,没有嘲弄,没有欺骗”的话,那么1979年作者笔下历尽沧桑后重返人间的亡灵,在目睹世间的虚伪欺诈之后,对自己灵魂的永生也要发出哀叹:“最大的幻灭莫过于永生。”(11)现代犹太人对传统信条的困惑很鲜明地呈现在辛格的短篇小说中。
综观辛格的短篇小说,作者关注的焦点仍然在如何面对犹太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上。小说同样表达了坚定信仰、保持传统与怀疑困惑的双重心态,既认同了犹太传统信仰的救赎意义和犹太传统精神惊人的凝聚力,肯定对这个传统的“精神把握”,又呈现了传统受到质疑、挑战的趋向。较之长篇,短篇小说多以鬼怪出场等形式冲淡文化冲突的现实背景,然而核心仍然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抛弃之抉择上。它们或者偏向于心灵分析的角度,突出人身的世俗性与宗教性、向善的愿望与邪恶俗念的激战,或者以异乡异客的心态道出在美国文化大熔炉里犹太人所感受到的民族特性日渐销铄的无形压力,以及对未来无望的沉郁。可以说,短篇小说各自截取了长篇小说中“回归”的部分经历体验,而作微观上的放大处理。不妨说,辛格的短篇小说是其长篇的散点存在(当然这不等于取消短篇小说的独立价值),它所处理的主题是长篇小说反映的主题的变异或局部。虽然在表现主题上,短篇不是以模式化形式出现的,但在总体上折射了长篇小说中基本主题模式所存在的复杂特征。
二
如上文所述,辛格小说的主题模式充满了张力与悖反,那么这一主题模式究竟寄寓了怎样的深意?笔者认为,它的形成与内涵本身,寓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从它,不仅可以反观犹太文化本身的悖论性特征,而且可以透视犹太民族面临的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持的现实课题。这一基本主题模式的确定,既反映了现实景况下犹太人对传统的“现代性”的主动反思,又揭示了犹太文化的“内旋”特性,印证了犹太精神传统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当然,这也包含作家个人的创作倾向的因素。
辛格小说的主题模式展现了犹太人对民族身份与流亡历史以及传统信仰、文化传统等的复杂态度。这首先反映了犹太文化自身的某些悖论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选民观”、“末世论”、“救赎论”等具有核心意义的犹太文化要素上。
20世纪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曾指出,“犹太人的灵魂有两个主要的中心,一个是体会到上帝完全在人之上……我们无法与他比美,无法衡量,但他又直接地面对我们。二是认识到上帝救赎的力量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作用,但这救赎状态却从未存在。”(12)因而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具有两方面特征,简言之,一是超验的理想主义追求,二是对“神”安排的现实的认同、妥协。由于特殊的民族遭遇,这两方面被强化发展成以“选民观”为代表的诸种信念。(13)它们注重解决人与神的关系问题,力图达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然而,步入现代历史以后,犹太子民与上帝关系中的矛盾开始突破民族形成之初的和谐状态,久积成患,导致了现代犹太人日益严重的分裂意识。正像阿萨·海谢尔(《莫斯卡特家庭》)所说,“世界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应当去看精神病医生。……每一个现代犹太人。”(14)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思想观念又绝不仅仅属于神学范畴,因为与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同,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类别,而且成为种族文化的界定标志。“犹太民族的宗教和他们民族的历史是纠结在一起的”。(15)因而在历史演进沿革中,“犹太教泛化为一种广义的民族文化规范。”(16)犹太教的许多核心观念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中的共同意识和影响、支配犹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
第二,辛格小说的基本主题模式包含了对当代文化接触课题的思考,体现了犹太民族日益面临的文化保持与文化变迁的两难。
文化接触本是人类文化进程中极为自然的现象,但由于犹太民族没有固定的地域边界,它必强调以精神上的某些共同性来补偿空间完整性的缺失。对此,顾晓鸣在其《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中作过充分论述。几百年来,犹太人曾凭仗“格托”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形式维系、保护其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借以规避文化适应的尴尬,然而到近现代,特别是随着犹太人大批涌入美洲大陆,文化适应则成为必然。
我们还应看到,两难不仅是异质文化间的消长、磨合引发的痛苦态势,而且包含实际“操作”上无从把握的困顿。应当承认,从犹太文化的历史来看,其自身也在或主动或被动地不断接受着异文化的渗透,就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我们千万不可把希伯来主义说成是《圣经》成书时代的巴勒斯坦犹太教”,追求平易简朴人生的早斯犹太教倾向“距中世纪与近代犹太教的经济道德观同样遥远”(17)。同样,追溯纯而又纯的犹太文化的原生态是无意义的。困难的是,随着文化成长的不断进行,文化状况不断复杂,原来拒不能接受的或许已成今日主流。因此,何种程度的同化才能“既保持文化特征,又与异文化主体达到理想的共识”?合适之度往往游离不定,须不断矫正。
辛格小说关注的基本问题正是现代犹太人对适度点的求解。把一个变量确定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辛格小说只能用如此的主题模式作一个模糊的限定。
第三,辛格小说“回归”与“悖谬”相结合的主题模式,从侧面肯定了犹太传统本身难以言传的价值魅力,而这种文化的价值正是辛格小说主人公最终“回归”的内在动因。
犹太传统是个内涵广泛而模糊的范畴。各个作家基于本身的经历、体验和特殊的文化教育背景,对此有着不同理解,反映在各自创作中,也各有侧重。在辛格小说中,犹太传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面对世俗世界这一实践性问题上,而这首先与一种世界观相关。小说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诱惑无所不在,世界充满罪恶。就连日夜祷告的圣徒也自感“深陷在肉欲,愤怒,忧郁和其他邪恶之中”。“对辛格来说‘不洁净’的概念已远远超出了专指吉泰尔人欲望和暴力的世界范围……而且延伸至目力所及的整个世界。”(18)而这种世界观又在历史循环的打击中得到验证。如劳伦斯·S·弗里德曼所说,“辛格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大屠杀’之后创作的,这给他不断重申的对世界的否定提供了最有力的历史性的基本理由。”(19)
在这样的世界观统摄下,辛格所理解的犹太传统主要负载在一种精神传统上。小说并不热衷于宣扬贫穷愚昧,以及对犹太经文的锱铢必较,相反,这两种人生态度在现实困境前丝毫无补于事。辛格所钟爱的乃是犹太人依靠道德自律、博爱精神、热爱和平与知识而获得精神存在的意义。对“精神性”的强调一方面是犹太人将“用其思想统治天下”的犹太末世论在作家心中的回响,同时,这种对犹太传统的变革性的理解又与辛格的个人经验相符。辛格的哥哥伊斯雷尔早年曾离开犹太家庭投身艺术家的生活圈子,这一点及斯宾诺莎的著作,深深影响到辛格对传统信仰的认识。1917年,辛格在比尔格雷(一个犹太村庄)生活期间,意外发现了犹太文化丰富深邃的“精神宝藏”。特别是1932年,伊斯雷尔终于因转向意第绪语和犹太题材创作而获得成功,复出文坛,这使辛格再次体会到犹太传统谜一般的魅力。发掘这个谜,就成了他毕生创作的倾向所在。对于谜底,辛格未曾有过什么直白的表达,然而在他的故事里,犹太人正是因其根深蒂固的道德感、自律精神和几乎愚顽的固执才保存了作为“犹太人”的延续存在。令人感到困惑而又充满魅力的犹太精神的价值也正在此吧。
辛格小说中对传统价值的评判并不是以直接的是非判断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判断仅仅体现在对形形色色的非犹太意识观念与思潮的批判性认识上。也正是这些非犹意识形态成了左右主人公悖谬式回归的根源之一。小说写了一切虚假的救世学说在实践中的破产:它们不是把犹太社会引向混乱分裂,就是不加反抗地一味沉默,或导向任意为恶,或是追逐狭隘的民族利益而牺牲无辜,或为了当下利益彻底扼杀文化个性。如此,也就否定了对犹太性、犹太精神和犹太历史的背叛,从而反衬出传统的价值。
在对各学说与思潮的批判中,小说着重反思了启蒙主义的负面效应,并对“解放”、“自由”等观念重新作了界定,借以认同归化传统之路。辛格大写人的内心之复杂性,嘲弄理性、智性的贫弱,实际上也是对启蒙主义的一种反思。辛格敏锐地发现,“启蒙”思潮使犹太人了解了自然法则、科学新知,摒弃了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激活了被抑制的生命力,然而它并未对它所导致的客观现实后果作正确引导,相反,它只颂扬人的理性,无视完整人性的要求和其多重性、矛盾性特征。一些犹太知识分子走出无知迷信的蒙蔽,却又投入唯理性主义的束缚,于是产生了一幕幕禁欲主义的悲剧、笑剧。由于对“启蒙主义”思潮未加批驳地吸收,受到启蒙开化的犹太人走入两个误区,他们要么像菲谢尔森博士一样,以片面的智性、理性取代健全的人性要求,要么过于信任膨胀的物欲之合理性而无所信仰,游戏人生。因此,在辛格小说中,“‘启蒙的’一词渐渐成了一个讽刺性的专有名词,它用以确定这样一些犹太人的身份: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迷了路。”(20)他们失去旧有的信仰,又在新世界里受到异化和流放。富有意义的是,“现在,人们久已习惯把‘犹太人’作为流放与异化处境的恰当象征,……但是辛格……看到异化和流放的真正体验并不在贫民区的犹太人中,而是在挣脱了束缚和接受了启蒙的犹太人中。……恰恰是在‘解放’和‘启蒙’——那结伴而来,旨在将犹太人从中世纪生活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两个进程——来临之后,……犹太人被抛置到现代社会,晃来荡去,不能定位。在那个意义上,辛格认为,‘解放’和‘启蒙’的自由,有许多方面,既不是解放也不是启蒙。”(21)
与“启蒙”相联,辛格在小说中对“自由”的含义作了探讨。自由不是摆脱犹太教束缚的自由,而是复归宗教信仰所给予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奴役”,而是选择“自律”;不是虚假的否定激情,而是驾驭激情。小说给出了许多伪自由的实例。魔术师雅夏从不诵经祷告,不守教习,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不受教义约束的极度的“自由”却包含着纵欲和死亡的隐患,即使肉体尚存,灵魂也已喑哑。米列爱姆·列巴(《庄园》)弃家私奔,正是为了汇入现代繁华都市的“自由”之风,然而等待她的却是爱情的骗局,精神的萎顿。也正是出于对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理解,辛格才不厌其烦地以回归表象上的“不自由”为故事结局。雅夏虽不能从自我禁锢中得到安宁,但他已认识到犹太性、犹太精神的救赎意义,他相信“不伤害任何人。不诽谤任何人。甚至不生邪念。……咱们每个人必须尽力去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22)也为了重获精神“自由”,卡尔门(《庄园》)放弃了对世俗庄园的经营,而回到祈祷室。
第四,通过对异文化的反思和犹太人归附传统历程的描述,辛格小说借相近的主题模式表达了犹太人对本位文化价值的意义的再认识和认同。辛格小说对这一趋向的发现,实际又正与犹太文化的“内旋”特征相吻合。所谓“文化内旋”,愿意为“卷进去,复杂化,复归”等,“这个文化学的分析概念意指某种民族文化为了适应新的条件,解决新的问题,但又要维持传统结构,而采取现存结构自我调整和复杂化的过程。因此,从根本上说,内旋作为一种原则,是趋于不发展的状态的。……内旋的过程以维持传统为主旨。”(23)当然,“内旋”与吸收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犹太文化在异常境遇下久长而蓬勃的生命力证明,在内旋化方面,它的确是超凡的。
当然,小说主题模式的生成又与作家本人的创作观念息息相关。辛格强调,“真正的艺术家应当使读者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得到欢乐和解脱。”(24)在他看来,“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屠场,唯一的补偿是生活中小小的欢乐,小小的悬念。”(25)因此,尽管“回归”附带着抹不掉的“悖谬”,传统的温馨依托毕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将它补偿给漂泊无依的犹太人,其情可解,大约也正像鲁迅先生给瑜儿坟头平添的花环吧。辛格个人的亲身经历恐怕也加深了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情调。辛格到美国十年内,无一字问世,最后还是以意第绪语创作确立了在非犹太世界的独特位置。
辛格小说主题模式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他对人心灵的研究兴趣以及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推究起来,这又有内在的哲学背景。辛格在哲学观上深受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影响。斯宾诺莎认为,“凭借机械的物质观,不可能解释整个自然界,特别是人。”(26)又说,“情欲是消极的激情,……可以占据人的整个意识,不断地迫害它,……使被控制的人纵然看到好的,也势必去模仿坏的。”因此,“人要在行动上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就不仅要认识外在的物,而且要认识自身的全部激情。”(27)这些都明显地影响到辛格本人的宗教观、世界观、创作观。辛格也认识到人性的复杂绝非理性可以禁锢、简化,因此他的小说的主题模式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呈现了犹太人心灵探究的轨迹。
三
辛格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犹太文化的风貌,并在小说中通过“回归”与“悖谬”相结合的主题模式,启动了对犹太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他充分注意到了犹太民族文化不能湮灭的价值魅力和不可忽视的现实困惑,可以说他的小说创作就是一只不惜独行的文化方舟。
除此意义之外,辛格小说特殊的主题模式又具有更为广泛的思考价值。虽然艺术堪为生活提供一副标尺,但实践上的差距却不能或免。辛格小说主题模式中的困惑、悖谬,并未因这一模式的提出而终结。在文化交融已势所难免的现代信息社会,如何保存本位文化才是发展中的保持?显然,这已超出当代犹太文化课题的范畴,而带上了全球色彩。辛格的思考代表了对犹太人理想生存方式的设想,虽然它仅仅以言语的方式出现,且难以弥合与实践的距离,但言语的意义却是无可估量的,它复活了亡故的往昔,又洞照着未来的岁月。
注释:
① 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② Malcolm Bradbury and Sigmund Ro,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Edward Arnold Ltd,1987,p.79.
③ Alexander Edward,Isaac Bashevis Singer: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1936,p.109.
④ ⑤ (14) (18) (19) (20) Lawrence S.Friedman,Understanding Isaac Bashevis Singer,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p.10,p.12,p.89,p.13,p.14,p.18.
⑥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695页。
⑦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0页。
⑧ ⑩ 辛格《童爱》,孙强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329页。本文作者据英文版译作《萧莎》。
⑨ 即gentile,犹太人对一切非犹太人的称呼。
(11) 辛格《重逢》,霄柳译,载《外国文学》,1981年第4期,第58页。
(12) 马丁·布伯《希伯莱的人本主义》,载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16页。
(13) 关于犹太文化的“选民观”、“末世论”、“救赎论”等,学者刘洪一等多有探讨,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15) 汉弗雷·卡本特《耶稣》,张小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16) (23)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导论第8页,正文第65页。
(1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129页。
(21) Sharon R.Gunton and Laurie Lanzen Harris,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15,Gale Research Company,1980,p.505.
(22) (25) 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鹿金、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54—255页,译序第9页。
(24) 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46页。
(26) (27) 索罗考夫《斯宾诺莎的世界观》,彭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6、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