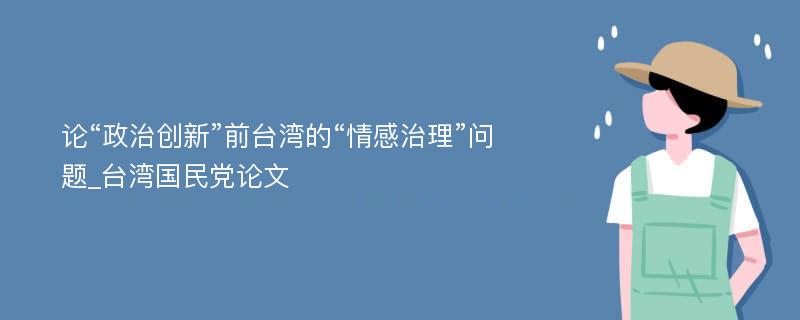
“政治革新”之前的台湾“情治”问题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政治论文,情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论苑
内容提要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岛一隅后,为安身立命计,更加强化了“情治”工作。一是通过整饬,建立了便于运作的“情治”机构,打破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二是完善侍卫制度,使“太上”“情治”职能再度强化。三是窥测风云,不断调整和变换活动手法:实施戒严法,派遣武装“情治”人员袭扰大陆,发展“敌后武力”,培养“情报细胞”……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台湾“情治”工作仍将发挥应有的耳目作用。在严密控制岛内局势的同时,将可能在客观上为两岸统一做些善事。
前两年,笔者曾就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期间的“情治”问题写过两篇拙文,(见人民大学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史》1991年第3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特务政治》、1993年第9期《试论抗战时期蒋介石特务政治的客观影响》),总觉意犹未尽。尤其是国民党偏居台岛一隅后的这方面情况,更觉有补白的必要。本文拟就国民党自大陆撤退至台湾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政治革新”之前的“情治”状况作一管窥,以飨读者。
(一)
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退至台湾。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解体。由“军统”演变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和由“中统”演变成的“内政部调查局”等“情治”系统也随之覆灭,余部一起逃亡台湾。“这些特工一向舒展筋骨惯了,来到台湾也不甘安于闲散,随时都有一展身手的欲望”①。更为严峻的是,“情治”系统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一时难辨忠逆,无法信任,因此,必须来一番整肃。1950年初,蒋介石在退台后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上称:要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进行改造。为确保“改造”顺利进行,决定整顿“情治”机构,清理门户,建成一支“强有力”的“情治”队伍,以旋转乾坤。
首先,建立了便于运作的组织机制。退台前,即1949年7月,蒋介石曾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为安身立命,决定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由唐纵任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②。不久,这个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蒋经国任主任。别小看这只是一个“组”,举凡一切党政军“情治”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其下设的保安处,实际等于当年保密局的权限,可见当时蒋经国的权力之大,连当年的戴笠亦难望其项背。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当天就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缉为主任委员,负责协调指挥党政军宪特各“情治”机构。“台情会”由各情治单位派出高级人员组成,全部人马须重新造册登记换证,方可开展情治活动。不久,“台情会”便被“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接管。蒋经国掌握了统制各派情治机构的权力后,即大刀阔斧重新调整和排列各情治单位的秩序。大体是:“内政部调查局”以岛内社会调查、防治经济犯罪、贪污、漏税为主;“国防部保密局”以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与防治为主。此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社会、海外、文化、青年等各项工作委员会,也都委以“特勤任务”,扮演协调情治系统的角色。
1954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党第二届“总统”之后,授意设立“国家安全会议”,并亲任主席。为掩人耳目,让顾祝同任挂名秘书长,由蒋经国任副秘书长,负实际责任。该组织下辖“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动员局”,这样,国家安全会议实际变成了制度化了的“太上‘情治’指挥机构”,蒋经国也实际成了特工共戴的魁首。其权力迅速膨胀,大有喝一声水即刻成冰之势。由于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班底就是过去的保密局残余,因此,安全局组建后,国防部保密局遂于1955年3月1日改为“国防部情报局”,仍由毛人凤任局长。
1985年7月1日,“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70年代初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组建)合并而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第一任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后因“江南案”而受囚,现任局长为黄世忠。为便于驾驭,以确保机密度极高的情报组织之绝对安全,因而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特别明显。据称,军事情报局内的“父子档”、“夫妻档”、“兄弟档”、“亲朋档”为一切机构之冠。
其次,打破了由大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大陆时代“情治”系统内部背景纷繁、派系倾轧、权力争斗的恶习仍沿袭至台,来自CC系、政学系、孔宋系、上海财团等各山头的大大小小特工人员之间的权力冲突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明显加剧,相互争斗的闹剧层出不穷。整顿中,冲击最大的是解除了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实权。CC系主持国民党党务系统长达20多年。它权力膨胀,树敌甚多,退台后,仍欲掌握党权,岂有不遭烹之理。二陈被迫退出政界。CC派的颓败,的确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应。在“忠于党国”、“忠于领袖”的喧嚣声中,各派系土崩瓦解。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例,第六届全部中央执、监委员589人中,除6人死亡和296人迁台后“归队”外,其余均被开除党籍。更有甚者,如堂堂代总统李宗仁亦只能亡命海外。其情同手足的白崇禧被视为“人质”滞留岛上,只要李宗仁在海外稍有微词,“小诸葛”便会在台岛遭“敲打”,连家也曾被翻抄。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回归大陆,白崇禧不仅未获“解脱”,反而于次年12月2日无疾而终,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至于长期握有重兵的何应钦,此时也只能当什么“道德重整会”的专家。素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大陆最后一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景况更遭,被逐至台北郊外一山上写“反共”理论文章去了。一些私蓄较丰的党国要人,则“自己放逐自己”,纷纷远走他乡。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则滞留香港等等。为防止任何人或任何部门权力过度膨胀,对党政系统实行了“人事制衡”,相互牵制;在军队系统建立“任期制”,使将领不能拥兵自重;对“情治”系统,格外赋予监控党政军系统的特权。这样,就奠定了蒋经国的权力基础,为最终建立起蒋氏父子为核心的权力结构铺平了道路。
(二)
在国民党“情治”系统中,侍从制度是其重要方面。因此,在整饬“情治”系统过程中,无例外地要进一步强化这个制度。追溯起来,侍从制度创建于军阀混战的1933年。当时,拥有一方天地的蒋介石既为自身的绝对安全,更为能在政敌间纵横捭阖,急需一股素养颇高的耳目力量。于是下令从各特务训练班、陆海空三军系统选调数十名身体健康、反共坚决的所谓文武“精英”,组成“侍从室”,又称“侍卫队”,下编勤务组、警卫组、总务组。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侍从人员,通过“忠君”精神麻醉,大都成为特务组织的要角。他们一身二任,除具备一般特工的技能外,还必须深谙“太禁”“保镖”一类特殊警卫性职能。此外,还刻意规定侍从室主任必须兼任军统局局长。由于侍从人员身份十分特殊,其言行被赋予了当权者的“影子”,这便构成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神密感”。正是借助于这种“权威”、“神密感”,他们的鹰犬作用、耳目威力才远非其他特工人员可比。由此可见,侍从制度是国民党特务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侍从室是实际上的“太上”“情治”机构;侍从人员是“情治”系统中的“情治贵族”、“太上”“情治”人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面对1949年的政治风暴,侍从制度也厄运难逃。失败、垮台的阴影,在侍从人员心目中如影随形,不少人不堪重负,或皈依佛门,或亡命海外。即使是仍左右在总统身边的“共患难”者中,也大都内心深处惶惶不可终日。为偏安求存,在“情治”活动中,蒋介石决心使侍从制度死灰复燃。“复职”后,他立即授意台湾国民党立法机构专门为总统府官邸制定了一套“总统府组织法”,以完善、充实侍卫制度,使侍从机构膨胀法律化。“总统府组织法”第18条规定:总统府法定侍卫人员115人,其中“置侍卫长中将1人、副侍卫长少将3人、上中少校侍从武官4人、上中少校侍卫官16人;书记官2人、事务官2至4人,雇员2人,”③余为其他军阶的普通侍从人员。当然,这仅仅是纸上的数目字,实际侍从人数则远远超过。仅以蒋介石生前长住的台北阳明山士林官邸为例,戍守该官邸(即行宫)的卫队就有一个营,警戒部队约一个加强连,总兵力达800人左右。类似行宫共建有47座,遍及台岛各地,其中不少蒋介石生前从未住过,但无论是否有人居住,每座行宫长年都必须有侍卫人员把守。而每座行宫的警卫网至少由三道防卫屏障——“外卫”、“中卫”、“内卫”组成。通常情况下,少将副侍卫长率宪兵队执行外卫和中卫任务,内卫使命则由中将侍卫长率官邸侍卫队完成。外卫和中卫一般设置相对固定的哨位,实行昼夜24小时不间断警卫。内卫一般不固定位置,以流动的方式警卫,警卫的人数则根据情况不断增减,这样算起来,光是固定守护行宫的侍卫人员就在千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外出巡视时临时增加的警卫人数。其侍从规模之大,人数之众,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台湾侍从制度鼎盛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优化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台北,1978年蒋经国继位,就任国民党第6届“总统”,同时也继承了其父的侍从制度。他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十分注重优化这个制度。实践中,蒋经国主要从两方面下功夫。
一是及时更换装备,提高侍卫能力。与蒋介石相比,蒋经国的侍从人员虽然减少许多,但侍卫手段及其装备却更为先进。如蒋经国长住的台北“七海山庄”官邸,警卫人员比蒋介石少300人左右,但官邸内安装了进口的电子报警装置,以取代“内卫”警戒任务。官邸附近还配置了数台防空雷达,所有飞机未经许可不得飞越官邸上空。另外,所有侍卫人员的装备全部更新换代,从防弹背心、微型冲锋枪、轻便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到德国警犬,一应俱全。
二是坚持严格训练,培养合格鹰犬。侍从人员虽不是左右政局的决策者,但却是决策者名副其实的鹰犬。为了使这些鹰犬既对决策者俯首贴耳,又对威胁决策者安全的人和集团有效施以淫威,必须让他们接受长期近乎残酷的训练。即一方面接受技能训练,使之深谙徒手格斗的技能,熟练使用手中武器,小至无声手枪,大至冲锋枪,射击精度要求百步穿杨,弹无虚发。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接受“忠君”思想麻醉。经过长期的法西斯熏陶和各种突如其来的模拟训练,他们必须始终表现出对决策者忠心耿耿,为职业肝脑涂地的意志,生要服从这个意志,死也要服从这个意志,要像机器人一般,没有个性,没有情感,剩下的全是“绝对忠贞”、“誓死捍卫”、“不成功、便成仁”。
(三)
综观国民党台岛“情治”工作情况,基本上依政治风云变化而不断变换其活动手法,且活动内容也随之各有侧重,大体如下:
退台初期,强化“戒严法”,为安身立命而疯狂制造白色恐怖。退台伊始,国民党风雨飘摇,各种危机交织。为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党政军残部,迅速确立蒋氏权力核心的统治,国民党决定强化1949年5月颁行的“戒严法”。设在党政军各系统的“情治”机构受命频繁活动,他们在“防范共产党活动及叛乱组织”,“缉拿共谍的经济或以经济为掩护的机构”④的借口下,或荷枪实弹游弋巡逻,或跟踪绑架,或警犬汪汪狂吠乱咬,或囚车呜呜横冲直撞,侦讯所谓危及当局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愿、罢工、罢市、罢课、张贴标语、散布“非法”言论、携带藏匿武器弹药等“迹象”。在“宁可错杀三千,决不同情一个”的口号下,动辄抓人、起诉、定罪。如此腥风血雨、滥杀无辜,使全岛阴弥漫,军民人等无不挣扎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不仅普通军民深受其害,就连“荣辱与共”、“忠贞不二”、拼死“护驾”至台的重臣宿将也难幸免。1950年6月,以“通共罪”枪决了前副参谋总长吴石、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接着,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处决了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原第六兵团司令陈延年、第十三军军长李天霞,也因“平潭战役不力”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就连台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祯、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也以“匪谍罪”为由,前者被黜,后者遭终身软禁。
如果说50年代初,台湾“情治”工作重点相对放在岛内的话,那么,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重点就相对转向以大陆为中心的岛外阶段了。他们大量派遣武装“情治”人员侵扰大陆东南沿海,渗透港澳地区,寻觅一切机会,重演跟踪、暗杀、刺探各类情报等故伎,捣乱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1955年4月,万隆会议时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即由美蒋特工所为。毛人凤因此曾得到蒋介石和美中央情报局的奖赏。此外,蒋特还在我周边国家和地区设置情报网,全天候搜集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在香港、澳门、南朝鲜、南越西贡、泰国均设有“情治”机构,并直接领导泰缅边境所谓“金三角”的李弥残部。在印度,设立“大青岭组”和“噶伦堡组”,还和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相勾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台湾当局企图利用这次战争以“光复”大陆的美梦已成黄梁。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鼓吹所谓“反攻大陆总体战”,“反攻复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希望大家加速完成各种准备,迎接胜利”。⑤在随后的“五中”、“九中”全会上,先后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反共复国总体战》方略,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国防部情报局还专门拟定“陆海空三面反攻大陆的计划”,即“龙翔计划”。扬言要从陆上、海上、空中派遣武装“情治”人员渗透大陆,组织退台时留下的“地下军”,集情报,发展组织,绘制军用地图,摧毁军用设施,为“反攻复国”作准备。仅1962年至1965年1月,就约有35股420多名所谓武装“精英”窜扰偷渡,均为大陆军民截获消灭。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为配合冷战而图谋发展“敌后武力”。由于武装派遣的一次又一次惨败,加之至1965年已损失军舰8艘,人员伤亡数万,美国政府更加怀疑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能力。面对更加紧张的冷战局势,为自身利益计,美国白宫的决策者们决定执行暂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潭的原则。年轻的新任总统肯尼迪于1962年8月警告说:“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⑥并指出:台湾单独发动对大陆的战事,是违反《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的基本原则的。失去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更加感到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遂决定改变策略。这样,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3个月后便悄然收场。
1963年底,国民党在九全大会上不得不变换口气,声称“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并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而应以“政治为前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湾战争相结合”。⑦即所谓“三分敌前,七分敌后”。为此,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针对当时美国为应付冷战,急切需要以台岛作为军事情报搜集的重心这一心情,加紧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局”等特务机构相勾结,积极从事情报合作。他们除了U-2高空侦察机的合作之外,还从人员代训、情报交换等方面加紧合作,图谋发展所谓的“敌后武力”。为了开辟派遣“情治”人员、发展“敌后武力”的基地,军事情报局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台北的“中美情报协调中心”,在大陆的一些周边国家搜罗华侨充当特工,进入大陆,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捣乱。同时,还利用香港警方政治部、移民局和国民党派驻香港的所谓“救济大陆难胞”的机构,强逼由大陆前往香港的正常移民,非法入境者及所谓“难民”等提供大陆各地的情况,甚至连到各驻港使领馆申请出境探亲的华侨眷属,也要遭盘问和询讯大陆各地的情况。他们还用金钱收买大陆的各种出版物、照片、电影底片、用过的民航机票、车票、船票和购买商品的各种发票等等,一一高价收买,尔后逐张逐件、逐字逐句加以细微的分析,研究寻找所需的情报材料,还在香港大帽山顶设立“中国广播收听站”,录取大陆各省市的广播内容,从中寻觅情报。此外,他们还曾利用西藏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和他的弟弟嘉乐顿珠一伙、西康黑河土司苏永和,以及青海军阀马步芳、马继援一伙的残部,在西南边境地区制造多起所谓“敌后武力叛乱事件”。当然,这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美台断交至台岛实行“政治革新”之前,强化海外基地,为策进对大陆的“政治作战”而积极培养大陆“情报细胞”。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冰释,美台密月结束。至此,台湾上空更是阴云四起,凝聚不散。为改变“国际孤儿”窘境,台湾当局不得不转向所谓“独立自主”的外交体制,妄图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来寻求台湾的“偏安拒和”,籍以造成海峡两岸长久的分离状态。进入80年代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大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后,海内外掀起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浪潮,强烈地冲击了台湾当局的僵化政策,当权者都意识到必须走“政治革新”之路。自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实行“全面革新”以来,台湾当局在大陆政策上亦作出某些松动。这样,海峡两岸局势相对平稳。
由于两岸关系日趋缓和,台军方已奉命不得掀起紧张局势,因而,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几乎已不再派遣专业人员进入大陆,以免这种人被捕,造成两岸军事关系紧张。实际上,试图在大陆发展“敌后武力”的作法,几乎全无效果,甚至完全没有意义,因此,这种发展“敌后武力”的动作已告停止。对大陆的“情治”活动,主要是强化“海外基地”,吸收大陆上人作为“情报细胞”。据悉,军事情报局在差不多的国家都建有这种据点。
由于特工这个伴随统治者应运而生的产物,无论客观形势如何瞬息万变,其誓为其主的属性不会改变。因而在海峡两岸未统一,台湾“情治”工作在严密控制岛内局势的同时,将为当局“坚持一个中国”“中国必将统一”的历史抉择尽其职责。
台湾的决策者们与大陆有着难以割舍的骨肉情缘,同为炎黄子孙,人心思“统”,人心思“安”,人心思祖国统一、强盛,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因此,作为台湾当权者工具之一的“情治”系统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将可能做出一些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善事。人们所熟悉的资深国民党员陈立夫先生既然已开先河,那些仍在“情治”系统服务的后来人,纷至仿效也势在情理之中。
注释:
①④龙中天:《蒋经国在台湾》第18、4页,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
②江南:《蒋经国传》第232页。
③转引自《金陵时报》1993年5月22日。
⑤《中央日报》1960年10月3日。
⑥宋平:《蒋介石生平》第57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7辑第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