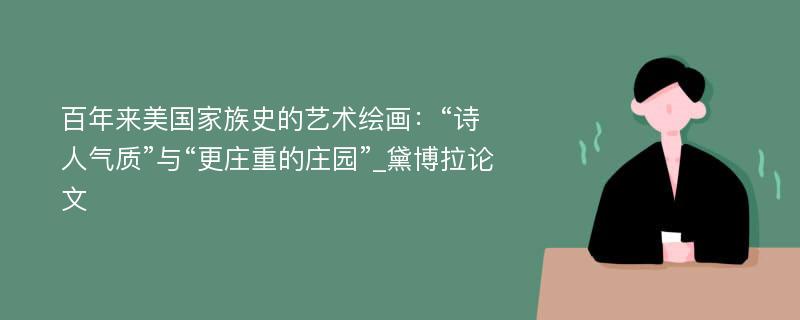
美国百年家族史的艺术画卷——《诗人的气质》与《更庄严的大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卷论文,美国论文,庄严论文,诗人论文,气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尤金·奥尼尔酝酿着他一生中最为庞大和野心勃勃的创作计划,“这是由七个剧本组成的组剧——一个超过了一百年的一个家族在物质、心理、精神上的历史”。奥尼尔在1935年给莱昂·米尔拉斯的书信中,提到了该剧的主题是“一个自我放弃占有的占有者们的故事”。(注:转引自(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廷、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28页。)1936年,奥尼尔在给兰纳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我对每个剧本的剧情是不是对国家的成长具有意义一点也不在乎。只要剧中情节对美国的家族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发展史具有意义就行了。这个组剧就是这样一部家族史。这些剧本是美国人的占有欲和实利主义的异乎寻常的例子和象征。”(注:转引自(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廷、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67页。)它将通过新英格兰人哈福德与爱尔兰移民洛迪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勾勒出19世纪美国文化变迁、政治发展和经济成长的历史画卷。按照奥尼尔的设想,这个组剧将连续演出,具备类似《战争与和平》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雄阔庄严的史诗风格和悲剧震撼力。1931年奥尼尔为这个组剧第三部作品,描写哈福德家族第三代的四兄弟乘坐快帆船前往加州的经历,构想了别致的剧名:《南回归线的无风时期》。在这以后,奥尼尔的创作精力凝聚在《悲悼》、《无穷的岁月》、《啊,荒野》三剧中,直到1935年,奥尼尔才开始认真地考虑这组历史剧的写作。
根据奥尼尔的工作日记,这七个剧本分为《诗人的气质》,描写了西蒙·哈福德与萨拉·梅洛迪的爱情以及萨拉父亲科的荒唐故事;《更庄严的大厦》叙述萨拉与西蒙婚后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西蒙的母亲戴博拉复杂邪恶的感情纠葛;《南回归线的无风时期》,主角是西蒙的长子伊桑,一个热衷于航海的青年。“整个剧本的情节发生在准备绕过合恩角航行的快速帆船上,结束在上海布朗开的膳食公寓里”;(注:转引自(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廷、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37页。)《财富叫人受不了》,描写西蒙的次子沃尔夫成为一个精明强干、声名显赫的银行家的全过程;《除了荣誉外别无所失》的中心人物则是西蒙那个一心想入主白宫的三子霍尼,他最终成了美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操纵铁路的人》则描写哈福德兄弟中的老小乔纳森如愿以偿,成为铁路业的巨子;《自我放弃占有的占有者们的没落》正如剧名显示的那样,准备交待哈福德家族的崩溃和最后结局。奥尼尔在设想这一组剧的内容和结构时,激动不已,曾在后来的岁月里,把它扩充到十一剧,打算一直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的哈福德家族历史。由于战争、疾病和生活变故等因素的干扰,奥尼尔最终并没有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写出来的稿本也多被他焚毁。在作者逝世后,只有《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两剧的打字稿以及《南回归线的无风时期》剧本提纲幸存于世。(注:《更庄严的大厦》的存世具有戏剧性。奥尼尔在该剧稿本里夹一张纸条:“未完成作品。我死后,此稿必须毁掉。”但奥尼尔1951年移居波士顿时,却无意中把稿本误装入耶鲁大学奥尼尔作品收藏馆的一个材料箱里。1957年,由奥尼尔妻子卡洛塔授权,瑞典导演耶鲁夫把它删节译成瑞典文,并搬上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参见《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第452页。)
二
四幕剧《诗人的气质》(A Touch of the Poet)初稿于1931年,是一部具有崇高的悲剧风格,又表现出情节剧明显特征的作品,按照奥尼尔研究专家弗洛伊德的评价,该剧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足以与《送冰的人来了》和《长日入夜行》两部杰作媲美。(注:参见《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第450页。)
该剧故事背景为1828年7月间波士顿城外的梅洛迪小客店。店主是爱尔兰移民科,一个在酒精和自恋幻影中生活的自命不凡的前英国龙骑兵少校。科本出身微贱,父亲靠开黑店,放高利贷而暴发,把科送到都柏林贵族学校,“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来证明他的儿子有资格跟任何一位绅士的儿子平起平坐”。不幸的是,科不仅保留了爱尔兰下层人好勇斗狠的性格,还沾染了贵族纨绔子弟寻花问柳、虚荣放纵的习气。科从军后,在西班牙战场上因作战英勇而得到晋升。但在一次与西班牙贵族夫人偷情中被抓获,又在决斗中杀死了她的丈夫,被革除军籍,从此便开始走下坡路。先是把老爹遗产挥霍一空,卖掉象征其社会地位的城堡,接着又因未婚先孕,被迫娶了庄园农夫女儿诺拉。移民美国后,在精明的新英格兰居民的花言巧语下,科把所有积蓄投资到铁路上去,血本无归,只剩下这家小客店和几百亩荒芜无用的林地。然而,科并没有正视已然陷入贫困的窘境,仍是孤傲地、我行我素地按照贵族生活方式来装饰自己。他奴役般地驱使妻子诺拉、女儿萨拉辛苦劳作,从不过问客店经营状况,整天穿着“英国贵族穿的那种价格昂贵、做工精致的老式服装”,骑着那匹宁可让妻女冻饿,也不亏待的良种母马,气宇轩昂地在街上缓行;他杯不离手,动辄高吟拜伦勋爵华美傲慢的诗篇,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不仅对爱尔兰贫贱老乡嗤之以鼻,对那些把他排斥在社交圈之外的美国地方新贵,也同样鄙视憎恨。在作者笔下,这是一个滑稽可笑而又令人同情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时代落伍者形象。
贯穿《诗人的气质》全剧的冲突,表现为带有农民习气的爱尔兰移民家族与以社会主流派自居的新英格兰绅士家族之间的冲突。它是通过萨拉与当地贵族哈福德儿子西蒙之间的爱情波折展开的。二十岁的萨拉,秀丽健美,“身上有一种混合气质,既有所谓的贵族气质,也有通常的农民特征。”她对父亲科的感情很复杂,崇拜他的高贵仪表,却憎恨他的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的沦落与无休止的劳役,反而磨砺了萨拉的渴望出人头地、跻身富人行列的决心。当她在林地小屋邂逅了西蒙后,立即察觉到这是解救自己出苦海的良机,便不惜一切代价地网罗住这个贵族青年的心。西蒙在剧中并没出场,他是一个“天生的梦想者”,一个被清高古怪的母亲黛博拉培养成怀抱着社会均富理想的诗人。西蒙在哈佛大学毕业后,自我放逐,打算写一部谴责功利主义的书。不料生病,住进梅洛迪客店,并堕入爱河。黛博拉偷偷来探视儿子,却激起了科的骑士殷勤和情场故技,造成极大难堪。这时哈福德的律师上门找到科,提出中止萨拉与西蒙的接触,代价是三千美元,但科的一家必须远离此地,最好搬到“西部去。——譬如说,俄亥俄州”。这种无耻无礼的要求激怒了科,他带着表弟克雷根冲出门,要求哈福德公开道歉,否则就决斗,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绅士风度。
全剧的高潮是第四幕,梅洛迪父女采取截然不同的讨取公道的方式,因而也获得两种结局。科在哈福德府上不仅没见到那个羞辱他的新英格兰暴发户,反而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拖到街心痛殴一顿。这个打击终于使科从愚昧的贵族白日梦中醒来,认清自己不过是贫困潦倒的爱尔兰贱民后代。于是科打死了那匹象征绅士幻影的纯种马,埋葬了那套曾带来荣誉和痛苦的少校军服,心甘情愿地以真面目回到酒吧间那些粗俗低贱的爱尔兰伙伴中去。萨拉曾竭力劝阻父亲徒取其辱的冲动,在心酸无奈之际,她毅然走进西蒙的客厅,用少女的贞洁征服了那座以傲慢与偏见为特征的贵族城堡,正象她向母亲发誓的那样:“我已经想好了一切计划,决不能让他这样疯疯癫癫地毁掉我的生活。我要让他看看,我也会玩弄绅士荣誉这种鬼把戏!”
弗洛伊德曾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奥尼尔在剧中描述的早期美国的族群冲突:“该剧探讨了爱尔兰移民在一个新国家里所面对的种种内心沮丧和悲剧。科在他那既是诗人又是庄稼汉的心灵里进行战斗,每一个19世纪初在一片陌生的国土上寻求保存他们的尊严和特性的爱尔兰移民都进行过。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因为他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和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他被打败了,受到了屈辱。他的梦想粉碎了,诗人毁灭了,只剩下那个爱尔兰庄稼汉。”(注:《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第449页。)那么,科的梦想是什么呢?是尊严与体面,优雅与风流。显然,在新英格兰这块冷酷势利的土地上这一切是绝对得不到的。且不说他的金钱已耗尽,又是移居他乡的爱尔兰后裔。更重要的是,那个崇尚勇敢与诗情的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庸俗贪婪、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风尚。科除了用绅士的面具武装自己,用贵族的花环陶醉自己,用逃避酒乡、沉湎回忆去消遣自己以外,他是毫无出路的。奥尼尔为这个唐·吉珂德式的悲剧人物设计了具有讽意的外貌和一些情节动作。首先,这个腰杆笔挺,颇有军人风度的前龙骑兵少将,力大如牛,有庄稼汉那种生气勃勃的活力。只有那张脸露出狂欢放荡的恶果——破了相。那张脸一度非常英俊,带有满不在乎的傲慢神情,如今还算漂亮,就象愤怒的拜伦式的英雄人物的脸庞那样,鼻梁端正,性感的嘴唇边上挂着盛气凌人而鄙夷不屑的神情,面色苍白,两颊塌陷,铁灰色头发浓密而卷曲,脸上还明显有一种由于自尊心受到屈辱而沮丧的神态。“其次,科最心爱的服装是那套惠灵顿龙骑兵团少校军官鲜艳的红色军装,每当重要的日子,比如塔拉韦拉战役纪念日,科都要穿上它,这时,他显得特别英俊高贵——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光彩夺目的罗曼蒂克人物。”除了那匹良种马外,科的生活舞台是客厅里那面镶在墙壁上的镜子。他欣赏自己,爱怜自己,仿佛要透过镜子去抓住那永逝不返的辉煌与荣耀。第三,除了决斗、酗酒、不过问世间琐事外,最能体现科的诗人气质和贵族情调的细节,是他在剧中反复背诵的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那段诗篇,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这已是沦落尘埃的科“可以用来找回自豪感,为自己一生辩护的咒语”——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生也没有爱过我/它的恶臭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注:译文依照杨熙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上海译文出版社。)无疑,科这种藐视现实、自我放逐和孤傲不羁、长歌当哭的感情特征,实际是奥尼尔——这个以爱尔兰后裔为荣的作者,对先辈们既爱又憎的复杂情怀的表现,为他们所吟唱的一首挽歌。第四,在布景道具上,还有一个最能体现科分裂性格的设计,即那扇隔在酒吧与客厅之间的大门。前来乡村小客店买醉的全是些出卖体力的下等人,其中又以爱尔兰移民居多,尽管科在内心深处更喜爱这些粗鄙的老乡,但面子上却摆出不屑为伍的傲慢神色,绝对不允许他们穿过大门进入客厅。客厅成为科保持贵族体面的最后一块领地。在全剧结束时,科终于冲开了那扇大门,汇入了那原本属于他的人群中,伴随着醉汉们的欢呼声和爱尔兰风笛的音乐声,科刻意营造的贵族幻影打碎了,自哀自怜的诗人死去了,他以一个庄稼汉的本来面目走进了现实世界。
《诗人的气质》是一部现实主义剧作,在艺术结构上采用双线并进的方法,爱尔兰移民与美国地方保守主义势力的冲突、理想主义与丑陋现实的冲突交揉在科与哈福德家族、科与女儿萨拉的双重对抗中。在场面的安排上,冷热交替,明暗搭配,高潮迭起,引人入胜,表现了作者娴熟高超的编剧技巧。正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它在美国戏剧史上应占令人尊敬的地位。
三
《更庄严的大厦》(More Stately Mansions),1958年10月在纽约上演,共284场,1977年重演,共141场。它的故事衔接于《诗人的气质》的尾声,幕启时是四年以后的1832年。该剧通过西蒙、萨拉和黛博拉三人错综复杂、疯狂病态的互相折磨与斗争,展现了哈福德家族物质上的盛衰史和精神崩溃的可怕历程。奥尼尔曾严厉指责美国人因崇尚实利主义将受到惩罚:“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曾沿着同样的自私、贪婪的道路走过来。我们谈论着美国梦,那……不过是物质东西的梦罢了。……人们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我们——我们大家——会有足够的理智懂得人的幸福的整个秘密能概括在连小孩也能懂的话里。那是什么话呢?‘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益处呢?’”(注:转引自(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廷、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38页。)最后这句引自《圣经》的话,揭示了《更庄严的大厦》的主题。
在《诗人的气质》的最后一场里,萨拉的父亲科曾预言女儿和西蒙结婚后,终有一天,“她会住进新英格兰佬的一座跟城堡一般大的大厦里,周围是座大庄园,有一片庄严的林地,绿油油柔软的草地和一个湖泊。”雄心勃勃的萨拉显然以一个占有者的姿态出现在这个剧本里,贪婪和狡猾驱使着她攫取一个又一个财富,她不仅很快改造了具有浪漫气质和纤弱性格的西蒙,使他放弃社会改良的乌托邦理想,成为一个精明残忍的赚钱机器,而且在与黛博拉争夺对西蒙的感情归属和哈福德家族财产控制权的拼搏中,也大获全胜。萨拉用少女的贞洁换取了进入哈福德家族的门票后,情况并不妙。老哈福德由于西蒙在婚姻上的背叛而震怒,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将其赶出家门。西蒙和萨拉靠黛博拉暗地里给的二千元钱,开始艰难的创业发展,不久便在棉纱业中崭露头角。患难与共的冒险和休戚相关的利益关系为他俩的感情生活增添了新鲜刺激的成分。很快地,他们遇到新的机缘:老哈福德由于投机生意失败导致公司濒临倒闭,在临终前遗言让西蒙接管公司;而黛博拉希望能从萨拉手中夺回宝贝儿子西蒙,也鼓励西蒙重返家族,因此心甘情愿地无偿转让她名下的产业:哈福德大厦,唯一的条件是让她能自由地和孙子们生活在一起。几年以后,在西蒙的领导下,哈福德公司起死回生,生意蒸蒸日上,成为一个横跨棉纺、运输、金融等行业的产业集团,西蒙也被誉为商界的拿破仑。
然而,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西蒙带来预期的快乐,反而使他陷入感情苦恼之中。西蒙是《更庄严的大厦》中塑造最成功的性格分裂、行为乖张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既有父亲血液里对金钱的天生贪婪,对商业交易本能敏感,对操纵驾驭人事的特殊才能,以及对荣誉和精神的传统追求等素质;也顽强地存在着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浪漫诗情、肉欲迷恋、神经质的幻觉和逃避现实的心理潜意识。西蒙既摆脱不了对黛博拉的恋母情结,又抗拒不了对萨拉肉体的渴求。然而,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他发现自己逐步被排斥在家庭之外,黛博拉与萨拉由互相仇视转变成亲密无间,她们自自失去特征,变成“母亲”与“妻子”的合体。妒火与邪恶在西蒙胸中燃烧,他刻意地挑起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让贪婪和情欲再次占据萨拉的心灵,以情妇和秘密合伙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司。西蒙开出的价格是:“你可以从我手中得到整个儿公司,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这当然是靠你一点一点把它赚到手!”萨拉因此堕落成一个不顾廉耻的荡妇淫娃和心狠手辣的商界女强人。而西蒙又与母亲达成一种精神上的契约:每天傍晚来到后花园凉亭,重现孩提时代的情景,在母亲的呵护下,“把灵魂寄托在幻想上,寄托在欢乐的化装舞会、神话故事和持续虚张声势的浪漫诗歌上——回避生活、逃避生活、忘却生活,安宁地歇息。”这样,西蒙就象《奇异的插曲》中的尼娜一样,生活中有不同的异性适应着他不同层面的欲望。萨拉既是他的妻子,又扮演妓女角色;黛博拉不仅是他的母亲,还是“恢复他灵魂”的祭师和满足他精神爱恋的对象。
《更庄严的大厦》的结局具有宿命色彩。萨拉和黛博拉象两只母狼一样撕吵恶斗,两败俱伤;西蒙的严重心灵分裂和双重生活模式,导致了最后的精神崩溃。萨拉首先从这场残酷的斗争中觉醒过来。她发现,纵然自己达到了父亲预言的建立更庄严大厦的物质目的,在精神和感情上则会一无所有。她把公司机密透露给竞争对手,亲手毁坏了哈福德庞大的产业;然后又跪在黛博拉的面前。请求饶恕与怜悯,最后带着痴狂的西蒙和孩子们回到农场小屋去。黛博拉无法承受自己是残害儿子元凶之一的事实,她关闭了花园小屋的门——把自己永远地幽闭在意迷情乱的幻想世界里。该剧还有一个尾声:一年以后,农妇装束的萨拉和神智清醒的西蒙承认过去的一切如同噩梦,只有农场和爱情才是真实可信的。萨拉鼓励西蒙继续写作那本研究社会均富理想的著作。
美国学者认为,《更庄严的大厦》在揭示组剧“一个自我放弃占有的占有者们的故事”的主题方面,有着特殊价值。毁灭性的贪婪促使人为了物质的占有而出卖灵魂,这使它又成为痛苦和悲剧的渊薮。另一个方面,该剧还进一步揭示了作者性格中某些隐秘的成份以及他与母亲的关系,对他们研究奥尼尔的创作历程是有帮助的。在艺术上,《更庄严的大厦》存在明显的缺陷。四幕九场外加一尾声,结构过于冗长,情节拖沓重复,人物间对话缺乏个性,有时人物行动也使观众感到突兀和不合理。1967年,何塞·金特罗把该剧大加删节后,缩成一个演足三小时的演出本,又特邀英格丽·褒曼饰演黛博拉,在纽约和洛杉矶上演,共演出142场,却遭到批评界的一致非难,甚至称它是“一片废墟,一个依照受尽糟蹋的蓝图修造的伟大建筑的空壳”。(注:转引自(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廷、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54页。)最近的重演,是1981年在纽约的爱尔兰反抗剧院,反应亦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