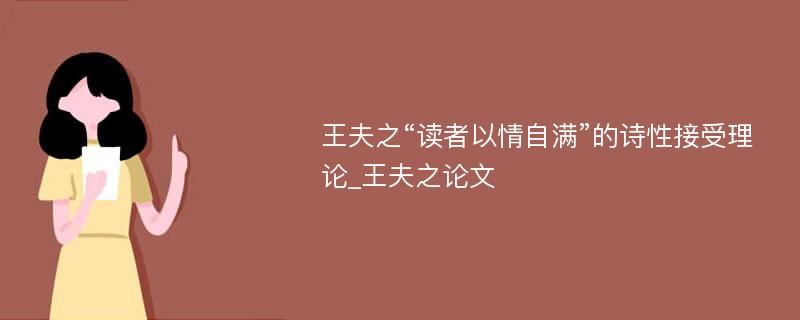
王夫之“读者以情自得”的诗歌接受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得论文,诗歌论文,以情论文,读者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王夫之诗歌接受理论的首要一个方面就是对读者在诗歌接受活动中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强调,这集中体现在他在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传统命题所作的具有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上: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注:《诗译》“二”条。)。王夫之对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说所作出的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其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于他打破了将“兴观群怨”四者割裂开来的传统看法而“以兴、观、群、怨四者的联系、转化论诗”(注:戴洪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这种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因为王夫之明确地对经学家将“兴观群怨”机械地割裂开来的作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意见:“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条。)但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王夫之为什么能够突破传统成见而以兴观群怨四者的联系、转化论诗?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王夫之把读者纳入理论考察的视野之内,对读者在诗歌接受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予以高度的重视,这就是他在上引这段话里所提出的“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理论命题。当然,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说并非完全无视读者,也不是完全不重视文学的社会效果和读者的反应。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它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读者应该如何“接受”文学作品对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说那里,读者实际上仍然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文学活动的中心仍然还在作家和作品方面。但是王夫之提出的“读者以情自得”的理论命题就不同了,它实际上把读者置于文学活动的主体地位,允许和承认读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来阐释和评价作品的权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夫之提出的“读者以情自得”说就决不是一时的兴发之言,而是一个表达他诗歌接受理论思想的重要的理论命题。
“读者以情自得”作为王夫之提出的一个诗歌接受理论的命题,其基本含义就是指读者在文学接受和欣赏的过程中,可以不必囿于以某诗为“兴”某诗为“观”的成见,而应该根据自己的情绪心态来自由地感受和触摸作品,从而对作品的审美蕴涵和美学功能作出自己的领悟和理解,王夫之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这一理论命题:“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于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注:《诗译》“二”条。)本来,按《毛诗序》的看法,《关雎》是一首通过起兴来颂美“后妃之德”的诗歌,但是齐、鲁、韩三家诗却认为是对周康王的晏朝荒政进行讽谏和规劝之作,这说明“于所兴而可观”。“于谟”句则见于《大雅·抑》,其本义是客观叙述统治者将国家的政策法令随时召告天下的事情而读者由此可以考见政治得失,所以王夫之称之为“观也”。但东晋的谢安却称赏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可以用来增其遐心,这则说明“于所观而可兴”。在王夫之看来,读者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存在,恰恰相反,他们的文学阅读活动是一种主体性的能动的参与行为。“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文学接受活动就是这样一种读者与作品本文之间相互沟通、遇合、触发与逗引的过程,它决不像人们以往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是读者被动接受作品“影响”的过程。为什么同一首诗,有的读者认为“可以兴”,而有的读者又认为“可以观”呢?在王夫之看来,这是由于不同的读者在思想性格、生活经验、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人情之游也无涯”。所以面对同一首诗,读者欣赏和接受的侧重点可能不完全相同,所引起的想象、联想和共鸣也不会完全一样,在思想上获得的感受和启示也会有相当的差异,这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各以其情遇”。
王夫之提出的“读者以情自得”的理论命题还包含有更深一层的要义:读者对作品的艺术再创造是诗歌意义和价值得以最后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说:
其情真者,其言恻,其志婉者,其意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故为文即事,顺理诠定,不取形似舛戾之说,亦令读者泳失以遇于意言之表,得其低徊沈郁之心焉(注:《楚辞通释》卷二《九歌》。)。在王夫之看来,高明的诗作者并不用包括议论在内的明言之理将自己的怀抱直接宣露出来,因为“议论入诗,自成背戾”(注:《古诗评选》卷四张载《招隐》评语。)。真正懂得艺术规律的诗人常常是在对真情实感的叙写之中(“为文即事”)自然含蓄地融入社会人生之理(“顺理诠定”),而读者自能在对作品的涵泳玩索中透过言意之表去最终领悟作品所传达的深刻蕴义。所以王夫之实际上是在强调,只有当读者积极主动地介入并作出创造性的接受之后,一篇作品的意义才能最终完成,他这种思想无疑具有接受理论方法论的意义。
2
尽管王夫之“以情自得”的理论命题高扬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读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力,但是他并没有走极端,把读者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而是认为,“以情自得”归根到底要受到作品客观内涵的制约和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感受、理解和创造性的发挥总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可以任意为之的。
王夫之在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批评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哀乐的情感本来就藏在人们的内心,只不过因为音乐和声的触发而表现出来,因而音乐本身与哀乐的情感无关。嵇康曾以人们在听哀、乐性质不同的乐曲的时候并未改变自己原有的情感这种现象为例来证明他的理论观点:“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歌,或听歌而感。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声音之无常哉?”(注:嵇康:《声无哀乐论》。)王夫之则认为,嵇康所举的例子只是反映了音乐接受和欣赏活动中“事与物不相称,物与情不相准”这种特殊的情况,而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这个样子,因此不应该由此而否认听者的情感反映与音乐的情感内涵之间的因果联系。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像嵇康那样完全否定音乐本身蕴涵的情感内容,否定音乐的情感内涵与听者的情感反映之间的内在联系,那就好像“云移日蔽,而疑日之无固明也”。所以他得出结论:“然则‘准水’之乐,其音自乐,听其声者自悲,两无相与,而乐不见功,乐奚害于其心之忧,忧奚害于其乐之和哉?……故君子之贵夫乐也,非贵其中出也,贵其外动而生中也。”这也就是说,音乐的接受和欣赏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运动,哀乐之情的产生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并非完全出自听者的内心而与音乐无关。说得具体一些,听者在接受和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所以会产生哀乐之情,是因为首先是蕴涵着哀乐之情的音乐打动了听者(“外动”),然后才引发听者相应的情感和情绪(“生中”)。总之,在王夫之看来,音乐接受和欣赏中的“以情自得”是要受到音乐本身的情感内涵的制约和影响的,那种以为听者可以“坦任其情,而忽于物理之贞胜”(注:引文均见《诗广传》卷三《小雅》“四四”条。),即把自己的感情任意地强加在音乐作品之上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说王夫之以上所论还限于音乐接受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时候,他则着重探讨了有关诗歌接受的问题。他在评论前人的诗歌作品时说:“盖意伏象外,随所至而与俱流。虽令寻行墨者不测其绪,要非如苏子瞻所云:‘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也。唯有定质,故可无定文。”(注:《古诗评选》卷一《秋胡行》评语。)王夫之认为,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其思想意蕴并不是用语言形象直接呈现给读者的,而是借助比兴、象征等方式暗示出来的,所以对于读者来说,是“意伏象外”,它有待于读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想象、联想的心理功能对之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充实。因此,对于具有“意伏象外”特点的诗歌作品,那些蹩脚的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寻行墨者”感到“不测其绪”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尽管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蕴往往“意伏象外”,难以捕捉,但并不等于说它是无法把握的。恰恰相反,它在“无定文”的表面现象之下暗藏着“有定质”。这个“定质”是什么呢?王夫之认为就是“情”,他在许多地方讲到这个“情”字:
《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著(注:《古诗评选》卷四《古诗十九首》评语。)。
古之为诗者,原立于博通四达之途,以一性一情周人情物理之变,而得其妙是故学焉而所益者无涯也(注:《四书训义》卷二十一。)。在王夫之看来,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可能直接叙写的是诗人自己独特的情绪感受,但是他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己的情感和情绪之上,而是要借此传达出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情绪,如王夫之所说的“以一性一情周人情物理之变”和“该情一切”,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定质”。这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上看的,如果再从表现形态上看,文学作品的“定质”则又有另一种特点:“古人于此,乍一寻之,如蝶无定宿,亦无定飞,乃往复百歧,总为情止,卷舒独立,情依以生。”(注:《古诗评选》卷四。)这也就是说,尽管诗人在作品中运用的表现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传达和表现诗人的情感即王夫之所说的“总为情止”,由此可见作为文学作品“定质”的情感是贯穿于作品的始终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王夫之才强调,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以情自得”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是应该牢牢抓住文学作品的“定质”,在作品所表现的情感、情绪的阈限内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记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尝记庚午除夜,兄(王介之)侍先妣拜影堂后,独行步廊下,悲咏“长安一片月”之诗,宛转欷虚,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谓。及后思之,孺慕之情,同于思妇,当起必发,有不自知者存也(注:《姜斋文集》卷二《石崖先生传略》。)。李白的《子夜吴歌》本来写的是思妇对于征戍的丈夫的怀念,而王夫之的哥哥却借这首诗来抒发自己对于先辈的哀思,这看起来似乎离开了原作的思想意蕴,王夫之所以起初感到不可理解,就因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及至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孺慕之情,同于思妇,当其必发,有不自知者存也。”这即是说,尽管李白写的是“思妇之情”(也即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孤栖忆远之情”(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四”条。)),而王夫之的哥哥借以表达的是却是“孺慕之情”,在具体的情感内涵上二者有相当的差异,但在情感的大致指向上二者又是是完全相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夫之的哥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对李白的《子夜吴歌》作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并没有违背原作的情感指向,像这样的“以情自得”自然要受到王夫之的肯定。
然而在古代诗歌接受史上,存在着一种片面夸大读者解读权力的倾向,这就是某些说诗人所热衷的“索隐”批评。这种“索隐”批评最大的特点就是千篇一律地以政治讽喻的代码来肢解文学作品,“把一篇篇作品分割成许多独立的符码单元,把一个兴象、一个喻体等价地置换成一个政治客体、政治意念”(注: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如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终南山》,全诗以绚烂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终南山磅礴雄浑的气势和朦胧迷幻的神韵,这明显是一首“模山范水”之作,然而却有说诗者认为此诗“皆讥时宰”,并竭力从诗中寻求政治讽喻的微言大义:“‘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言势位盘据朝野也。‘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言徒有表而无内也。‘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言恩泽偏也。‘欲投人住宿,隔水问樵夫’,言畏祸深也。”(注: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又如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有人作出这样的解说:“池塘者,泉川潴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记,一虫鸣则一候变;今日变鸣禽者,候将变也。”(注:见陈应行《咏窗杂录》,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像这样完全离开作品的客观内涵用政治讽喻的方法对作品进行恣意的曲解,必然要把文学接受活动引入歧途。王夫之对这种寻求政治隐射的解诗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右丞《终南山》非有所为岂可不以此咏终南也?宋人不知比赋,句句为之牵合,乃章淳一派舞文陷人机智。谢客‘池塘生春草’是何等语,亦坐以讥刺,瞎尽古今人眼孔,除真有眼人迎眸不乱耳。”王夫之还结合对杜甫《野望》这首诗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以寻求政治影射为务的“索隐”批评的态度:“如此作(案指杜甫的《野望》)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俗目不知,见其有叶落、日沉、独鹤、昏鸦之语,辄妄臆其有国君危、贤人隐、奸邪盛之意。审尔则何处更有杜陵邪!”(注:《唐诗评选》卷三杜甫《野望》评语。)这样一来,王夫之就把他自己提出的“读者以其情而自得”的诗歌接受理论与寻求政治影射的“索隐”批评彻底划清了界限,按照王夫之提出的理论原则,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接受就要像他对杜甫《野望》的解读那样,完全摒弃“索隐”批评一味在作品中寻求政治讽喻代码的做法,而从作品本身提供的艺术形象入手,然后在此基础上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发挥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能力,从而对作品作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王夫之“读者以情自得”的诗歌接受理论原则的全部要义之所在。
3
王夫之提出的“以情自得”的理论命题不仅是对读者在诗歌接受活动中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张扬,而且也是对读者能够创造性地鉴赏和解读作品所达到的极高境界的一种理论描述。因此,读者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以情自得”,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王夫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
从客观条件方面看,王夫之认为作为接受对象的诗歌作品必须具有深沉丰瞻的思想蕴涵,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经得起读者反复的咀嚼、揣摩和品味,才能引发读者无尽的联想和多重的理解,也才能真正使读者做到“以情自得”。王夫之曾提出“诗无达志”的命题:“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故曰:诗无达志。”(注:《唐诗评选》卷四杨巨源《长安春游》评语。)所谓“诗无达志”,其实就是说诗的意蕴具有某种丰富性、多义性和未定性,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某一种固定的意义去限定它,这实际上就为读诗者“以情自得”地去解读作品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基础。王夫之在评论一些诗歌的时候常常赞扬那些好诗“宽于用意”(注:《唐诗评选》卷四杜甫《九月蓝田宴崔氏庄》评语。),“绝不欲关人意”(注:《明诗评选》卷四石宝《秋夜》评语。),“寄意在有无之间”(注:《古诗评选》卷五江淹《效阮公诗》评语。),“无托者,正可令人有托也”(注:《明诗评选》卷八袁宏道《柳枝》评语。),就是强调诗歌思想蕴涵的这种丰富性、多义性和未定性的特点。文学作品如果具有了这个特点,就可以“广通诸情”,自然引发读者的多重感受;而从读者方面来说,则可“以情自得”,对作品作出带有自己个性特征的理解。梁简文帝萧纲有一首《春江曲》:“客行只念路,相争渡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这首小诗以对比的手法叙写诗人在春江边的见闻及感受:一边是行色匆匆竞相争渡的过客,一边则是摇手拭泪的旁观者。这幅春江即景是如实地传达诗人一时的审美感兴,还是要表现诗人对于人生的大彻大悟?看来这两种蕴义都有,王夫之就明确地持这种看法,他说:“偶尔得此,亏他好手写出。情真事真,斯可博譬广引。古今名利场中一往迷情,俱以此当清夜钟声也。”(注:《古诗评选》卷三简文帝《春江曲》评语。)在王夫之看来,梁简文帝的这首小诗表面上写的仅仅是诗人对渡口的瞬间感受,似乎没有什么深义,但由于它传达的“真”情和“真”事在思想蕴涵上带有某种宽泛性,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博譬广引”的巨大空间,比如读者就可以把这首诗作为向那些在名利场中迷恋忘返的人们敲响的夜半警钟,应该说王夫之的这一理解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与此相反,对于那些思想蕴涵单薄、言尽意穷、不能引发读者无尽想象和思索的作品,王夫之则持否定态度。我们看他对汉代和魏晋以后无题古诗的评价:
魏晋以下人,诗不著题则不知所谓,倘知所谓则一往意尽。唯汉人不然。如此诗(案指“桔柚垂花实”)一行入比,反复倾倒,文外隐而文内自显,可抒独思,可授众感。鲍照、李白间庶几焉,遂擅俊逸之称(注:《古诗评选》卷四。)。为什么王夫之对汉诗和魏晋以下的诗褒贬不同,就因为前者内涵丰富,意蕴无穷,尽管它抒发的是一己的感受(“抒独思”),但却可以引发众多读者多重的想象和思索(“授众感”),读者可以真正做到“以情自得”;而后者则由于缺乏蕴涵让人一览无余(“一往意尽”),不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启发和思考,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恐怕再高明的接受者和鉴赏者也无法做到“以情自得”。
读者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以情自得”,除了要求作为接受客体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深沉丰瞻的思想蕴涵以外,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自身也应该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和条件,王夫之对此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
其一,读者应该具有艺术的同感力。王夫之所说的艺术的同感力,实际上就是读者在接受和欣赏诗歌作品时能够设身处地地把自己置身于诗人当时境地,去全身心全人格地感受、体验和把捉诗人情感和意绪的能力。王夫之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以诗解诗”,而不是“以学究之陋解诗”(注:《诗译》“一0”条。)。 他在另外的地方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注:《诗译》“一”条。)。王夫之还结合鉴赏的实际来具体阐述说明这一点:
“欲投人住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诗。尝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次亦情中景也(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六”条。)。在王夫之看来,所引王维和杜甫的诗句是诗人在某种现实情境的自然感发中产生的,因此读者只有化身为诗人进入作品所描绘的艺术情境之中并设身处地作审美体验,作品所描绘的艺术形象才能够生动鲜活地涌现出来,读者也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其二,读者还应该具有艺术想象力。诗歌创作需要想象,这是中国古代诗论家的共识,王夫之也持同样的态度,如他用“善于取影”来称赞王昌龄的《少年行》,就是因为这首诗比较好地运用了艺术想象(注:《诗译》“五”条。案王昌龄《少年行》,《万首唐人绝句》及《全唐诗》诗题均作《青楼曲》。)。但王夫之也同样强调读者在诗歌接受活动中需要艺术想象,他在对《诗经·小雅·出车》的评论中表达了这一思想: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建旌旗,举矛戟,车马喧阗,凯乐竞奏之下,仓庚何能不惊飞,而尚闻其喈喈?六师在道,虽阅无忧,采蘩之妇亦何事暴面于三军之侧邪?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喜,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注:《诗译》“五”条。)。王夫之的这段议论是针对训诂家的有关解说而发的,如孔颖达《毛诗正义》在解读此诗时,一会儿说“此序其归来之事,陈戍卒之辞”,把此诗看作是以出征将士的口吻对凯旋归来场面所进行的实写;一会儿又觉得与“赫赫南仲”一语相抵牾,所以又说:“赫赫南仲,则非将帅自言也。”这样一来,一首本来蕴涵无尽的情趣和意味的佳作,却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索然寡味,这显然是解读者缺乏艺术想象力、全然“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所带来的恶果。王夫之对《出车》诗的解读所以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在于他在遵循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艺术的想象力。王夫之认为,这首诗并没有实写归师凯旋的热烈场面,也没有正面去写戍归的丈夫与妻子相聚时欣喜若狂的情景,而是把征夫渴望团聚的那种期盼之情融化在想象和联想之中:征夫在归途中“遥想”妻子即将面临凯旋场面的欣喜心情,“赫赫南仲”更是征夫想象妻子为自己的赫赫战功而欢欣鼓舞的境况。如果说《出车》一诗把征夫与妻子两情相依的实景化为想象中的虚景从而为读者留下一个可以进行再创造的艺术空间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取影”的话,那么王夫之作为高明的读者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对作品作出富有审美情趣的解说我们亦可以称之为“影中取影”(注:王夫之“影中取影”的本意是指诗歌创作中的想象,我们借用来指诗歌接受过程中读者对作品所进行的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想象。)。毫无疑问,像王夫之这样细致入微地体味作品、充分挖掘作品所蕴涵的审美旨趣,真正做到“以其情而自得”,没有“影中取影”即艺术想象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
收稿日期:1999—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