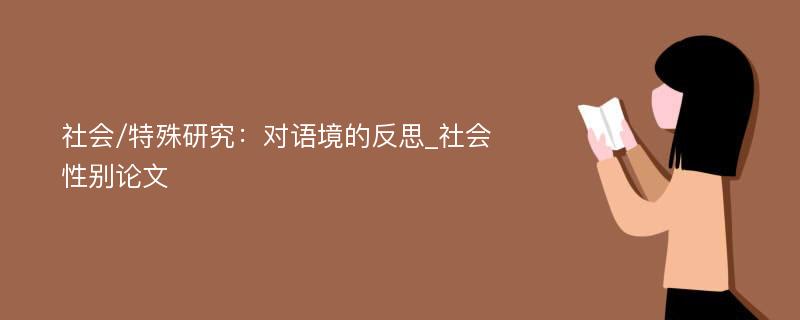
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脉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脉络里面对某些特定问题而设想出来的解决/解释。不同领域、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知识形式,而学术研究必然包含了对自身知识来源和状态的反思。对自己手里知识工具的历史脉络有所认识,方能觉悟自己的知识特质和局限。
在稳定而历史悠久的学术领域里,主导的知识体系以及相配搭的世界观往往构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知识状态,约束着亚流知识的成形和扩散。不过,任何知识体系也必然有其无力解释或根本熟视无睹的已存在或发展中的异状(anamoly)。当新的社会现实与竞逐、新的学术生产体制及其正规化的措施使得异状越来越凸显,主流知识体系遭遇解释危机,新的理论和解释有机会被尝试时,知识的典范革命便有可能发生。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因此以“典范更替”(paradigm shift)概念来说明过去从未想过的新视角和知识进路如何浮现,如何使既存的事物在新的典范之下形成不一样的认知,使新的观察和知识得以被看见而更进一步发展稳固新的典范②。当然,重点不是哪个知识或视角才正确,而是透过典范更替来反思我们想当然的知识是如何被特定视角和方法学生产出来的,我们所倚赖的思考框架如何阻碍了新视角、新知识的生产。
这篇文章的标题选用“社会性/别”(gender/sexuality)而非“社会性别”(gender),正是要借着两者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转折,显示“社会性别”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理论发展固然是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别构成”得以被凸显,然而最近20年“社会性”(sexuality)③在全球学界的快速理论发展也已经形成另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构成”成为当代的重要知识生产进路。本文使用“社会性/别”作为核心概念,一方面是要标记台湾在此领域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特殊理论洞见④,另一方面则是要抗拒线性思考,希望同时关注社会性别、社会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如阶级、族群、年龄、身体等)的复杂关连。这些关连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任何单一排他的关注都将形成严重的盲点,甚至现实的恶果⑤。回顾“社会性/别”在美国和中国台湾作为一个研究路数的发展路径和转折,将可帮助我们参照那些形塑并影响这个领域的多重脉络因素。
这个领域的典范更替其实明显可见于英语相关辞义的转变与语词的密集使用(或被冷落)。二十世纪中期以前,gender完全没有今日的“社会性/别”含义,它只是语言文法中用来区分字词“种类”的概念,也就是分析语言如何指涉事物有其天生内在的特质从而反映了社会区别(不见得仅止于阴性阳性之分);而十九世纪以来主要在生物学、性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使用的sex才是指涉(生理)“性别区分”的主要词语⑥。有研究者透过对1945年到2001年之间的期刊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sex和gender的出现场域、频率、和意义都有了明显的变化⑦,其中的转折关键被认定是性学家John Money对gen-der所赋予的新意义和用途。Money曾经说明把gender一词从文法领域引入性学领域,主要是为了描述那些外观上看起来是男或女但是性器官却天生暧昧因而无法实践其生理性别应有之“性别角色”(genderrole)的人⑧。在这里,gender指男性或女性在社会互动中应有的常规表现。不过,1950年代当时尚未兴起妇女运动,John Money的用法也只被一些心理学论文沿用在专业领域里描述那些“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个人(阴阳人、变性者、扮装者、同性恋、娘娘腔少年以及阳刚女孩)”⑨。换句话说,gender后来广泛为人所知的“社会性别”意义其实源自那些明显偏离性别规范的人,正是这些偏离的主体突出了社会性别对主体的形塑(失败)。
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妇女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gender越来越有了“社会性别”的含义,也越来越预设了性别不平等。妇女运动以sex discrimination(也就是“建基于生理性别的歧视”)强力批判女性所承受的歧视与限制,并且将John Money针对性别异类的gender概念转化,用来凸显社会文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对于生理女性的调教与规范如何压抑和限制了女性的人生选择和发展。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随着学院内外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述耕耘和理论发展,gender一词超越了原先主要出现的语言或医学心理领域,大量出现在读者群更宽广的人文社会领域期刊中,在意义上也专注于指涉那些“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和选择”⑩,甚至后来在通俗论述中全面取代sex而成为标记性别差异的字眼。值得注意的是,当年Money在描述“性别角色”的含义时除了提到性别区分,也特别提到性别角色“包含了(但不仅限于)性(sexuality),也就是情欲(eroticism)”(11);然而后来女性主义引用gender来谈性别角色时却略过了性别角色与情欲之间的内在关连,只强调环境、社会、心理对男女心理和行为差异的影响。
此刻,性别不平等的认知框架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有关社会性别的唯一思考可能。这个对“性”的漠视迟早在日益蓬勃发展的性文化中激化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对立,这也是后来“社会性”(sexuality)成为新显学的伏笔。
运动思潮的学院化
无可否认,有关“社会性别”的学术研究起自1960、1970年代英美的妇女运动,妇运震荡最强烈的当然是有着知识和话语能力的年轻女性,因此高等教育所可能带来的意识觉醒就成了她们改造世界的开端。当时美国高教因美苏冷战竞争而正好持续大幅扩张(12),教育投资使得学生来源和性质都超越单一背景,差异的经验和知识激荡因而提供了反思的动力;再加上同时接合了反(越)战、(黑人)民权、妇女解放、性解放、迷幻药物解放、新左派等等新社会运动挑战常识、质疑权威的风潮,使得“自由”与“平权”逐渐成为当时反主流文化的主导氛围和意识。
年轻一代的学生于是在社运的呼召下集结,强烈要求高教提供新的、反映其社会经验与愿景的知识。经过社会运动的酝酿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的呼吁和抗争,1968年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在学生罢课五个月后终于同意设置了第一个以“种族”为核心概念的“黑裔研究”(Black Studies)课程,以补救过去对黑人及其文化、历史、利益的知识忽略和轻蔑。接着,其他类似的学程──包括非裔离散研究、西裔研究、美国原住民研究──也陆续诞生。1969年该校女性解放组织与教师和社群妇女合作,组织了“妇女研究临时委员会”,收集学生的联署签名,要求校方比照黑裔研究也成立妇女研究学程,校方善意回应,经过半年筹备,于1970年秋天正式成立全美第一个妇女研究学程,第一批课程包括11门课。1974年推出18学分的副修课程,1975年校方在文学院成立正式的妇女研究系,1983年开始颁授本科生学位,1996年开设硕士班。这个成立的模式和过程后来在无数高教脉络中复制,形成妇女研究的荣景。
从“妇女研究”在学院生根扩散开始,以女性作为知识和研究视角,聚焦并反映女性的社会位置和经验,可以说完成了一次典范更替,使得这个视角成为生产知识的有效路径。作为妇女运动的学术侧翼,妇女研究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政治驱力,以被压迫者翻身的强大目的性和正当性来开创学术。这个取向当然也直接影响其知识生产倾向、方法学选择、特殊洞见以及可能的局限。不过在这里需要先指出,当时人文社会领域的女教授们跨领域凑起妇女研究学程,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妇女”,还没有以“性别”为范畴来思考社会,因此早期妇女研究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向。第一,挖掘并整理女性的知识前行者和女性历史,建立女性经典作为竞逐的知识传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历史研究,以及对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翻译和引介,这两人的论述也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文献。第二,女教授学者们用女性角度重新阅读各种文本与文化再现,揭露其中的性别权力政治与性别盲点,形成女性主义批判的传统,开辟广大的学域和无尽的文本供学者和学生们分析。这些开疆辟土的工作是早年妇女研究教室内最常见的意识觉醒活动,也是非常有力的批判工具,但是因为妇女研究的知识生产往往从性别二元出发,预设了以男性为参照点和区隔的对象,致力于显示社会文化对性别的建构如何形成清晰的男女高低强弱的权力分配,这种知识方法因而很容易被批评为预设立场、视野狭隘、意识形态挂帅。另外,性别二分关注的是男与女的区别和不平等,在团结自己人的目的之下,视野轴线沿着生理二分(同时异性恋)延伸,两性各自的内部差异因而很难浮上台面,就连gender概念原来的跨性别源头也往往被略过,反而简化了性别的多元现实。
早期妇女研究的认同政治出身以及论述形式(“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在上述学术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经验取向”的知识方法,但是困扰的是,妇女研究的名称假设其学术研究的对象、执行研究的主体以及研究视角都必须以(生理)女性为本,这样的思考也使得妇女研究逐步陷入盲点和困境。可是作为学术研究,妇女研究仍然必须面对学院环境的特殊要求和挑战,而不能只以认同和身份的特权视角回避理论的要求和挑战。1980年代美国高教的专业化加速,理论的转向(the turn to theory)使得人文社会各领域都快速发展文本分析、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族群理论、主体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知识生产路径。在性别疆域外缘稍晚出现的新兴同性恋研究、跨性别研究、性研究、身体理论、后人类研究等学术领域打从一开始便有机会趋向关注理论和复杂性,这也使得妇女研究的“经验研究”路数在接合这些理论的时候显得需要更多摸索磨合。毕竟,妇女研究积累的知识如果只切片看女性的历史和社会存在,在学院内的立足便显得偏颇;要加强理论性,就必须超越主体经验,进入抽象层次,以避免自己所生产的知识被局部化、边陲化。面对这个变化发展,妇女研究于是更多的投入“社会性别”(gender)这个知识和理论的概念,当成重要的理论发展方向,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热烈讨论“妇女研究”是否应该直接改名为“性别研究”以强化学术形象。当时,反对者认为把妇女研究改名为性别研究就是从妇女议题撤退,放弃妇女运动辛苦建立的特有视角;但是也有人认为妇女研究当初就是为了避免被说是预设立场而放弃了旗帜鲜明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研究”,现在用性别研究来取代妇女研究也没什么不可,不但可以扩大研究版图,还可以争取更多男性加入这个领域。然而这个命名争议尚未尘埃落定,新的理论发展又进入眼帘。
学术研究的理论化往往在争议和矛盾中得到极大动力长足发展,也因此可能促成新典范思考的成熟发展。1980年代前后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拥抱正面看待情欲议题,愉虐恋(SM)女同志团体坚拒以女性主义的性别权力两极分析作为理解情欲互动的唯一视角,因而与反性的女性主义者进行激烈的“女性主义性辩论”(feminist sex debates)(13),也大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的性论述。当时许多肯定情欲的女性主义者和性激进分子都认同女同志愉虐恋的自由立场,放弃被良妇心态笼罩的女性主义,校园里也开始有大批女性主义者离开妇女研究学程(14)。然而主流女性主义者仍然日益倾向以立法管制社会的性实践作为运动目标,以Catherine MacKinnon和Andrea Dworkin为首的女性主义者因此追求在法律和论述上把“性”等同性别歧视,把“色情”等同性暴力,企图形成对性实践与性信息极为不友善的环境。与此同时,艾滋危机固然挫败了彼时蓬勃发展的同性恋运动与社群,却也更刺激了同性恋的激进思考与抗争策略,在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后结构、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之下,与性激进女性主义(feminist sex radicals)合流,形成积极抵抗“性别唯一”(gender-only)思考框架并且正面肯定“社会性”(sexuality)的酷儿路线。“社会性”的相关研究也在这个争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为显学。
典范的再次更替
20世纪可以说是“性”的世纪,因为“性”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关切的重心。“性”的行为、言语、图像、感觉、欲望、身份认同,以及各种规范“性”的法律政策道德规训也不断浮现,促使“性”成为人们焦虑和愉悦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性主体群体被压迫和寻求政治解放的焦点。19世纪主导“性”思考和言论的知识体系主要是性学。目前,医疗的、生物的、行为科学的、心理学的性分析架构或许仍然构成最主要的顺口语言和理解方式,然而权力的、关系的、身体的、再现的、感情的、差异的、社会运动的语言也随着现代社会的多方变化和发展不断衍生,加入性领域的论述争战。
将社会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思考从1990年代末期起大幅推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就是福柯,他提醒性研究必须试图了解“性”是如何透过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象征的、地域的、法律的、政治的力道和脉络而逐步成为一个可供观察、可供解释、可供管理的对象;不同历史时期的性社会(权力)布局(sexual deployment)和性另类的构思与实践(alternative sexualities)因此都是当代性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性研究不但要包含目前性社会学对主体的性欲望和性愉悦、性行为和性互动、性认同和性价值的认知外,同时更需要检视这个学术专业的研究和概念范畴自身是如何形成、性的知识和教育如何转化成为常识和建制、集体的性社群及其文化如何浮现积累、性运组织及其论述如何形成争战等等。这些理论资源如果接合上同性恋运动与女性主义性运的能量,就更加推动对“社会性”的研究发展。
“社会性”(sexuality)在强烈竞争的美国高教学术圈中快速发展扩散,对社会性别的既有学域建制也造成冲击。学术的发展和师资的渐次换血促使美国许多高等教育名校历史悠久的妇女研究学程开始辩论是否应该重新命名,在新的名称上则倾向淡化“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的领衔,甚至连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也被视为不足以涵盖这个领域的学术视角,而必须在正式名称中包含“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以宣示本身在研究教学进路上的转向(15)。这当然是个很有深意的动作:它不但表达了学术研究的转向已经重大到不得不正式更名的地步,更透过正式的重新命名来宣示一个新的、超越“唯(生理)妇女/唯(生理)女性”的研究眼界。2002年美国名校康乃尔(Cornell)大学坦承,时代和学术的变迁已经使得妇女研究不敷所需:
妇女研究过去或许是个很好用的名称,然而现在她已经不符合我们系所的特色了。因为“妇女研究”暗示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一个统一的认知,这样的单一认知恐怕会排挤目前教学和课程的重要焦点:例如各种多元的性,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酷儿以及其他激进的性;多重性别;性别、种族、阶级、族群及其他相互建构的社会差异范畴以及跨国面向的女性主义、性别与性。(16)
妇女研究的师资最终合议把成立了30年的“妇女研究学程”改名为“女性主义、性别与性研究学程”,以便“转向研究性别与性和其他权力及不平等之间的复杂纠葛”(17)。换句话说,正因为妇女研究已经形成的狭隘视角排挤了目前很重要的新兴议题和理论,如果要进一步跟上学术研究和社会变迁的脚步,就必须用正式更名来打开局面,跟上潮流。同样的更名行动也发生在其他许多重要大学的校园内,基本上都是舍弃原先“妇女研究”的单一视角,积极的引入“性研究”的重要洞见。2004年,耶鲁(Yale)大学也把“妇女及性别研究学程”改名为“妇女、性别、性研究学程”,并且宣称只有正式在名称上标明“性研究”才能表示“同时研究性别与性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18)。
名称的更动其实反映了理论上的新进路,目前的研究倾向主要从各种社会因素的“交集/交会”(intersectionality)入手,聚焦于各种社会动态因素(例如年龄、阶级、族群、性、性别、国籍、种族、宗教和性认同)之间已经形成的、正在发展中的各种纠葛交会。
中国台湾经验与性/别研究的兴起
如上所述,美国“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最新的典范更替主要呈现方式是透过改名把“社会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加入列举的视野版图,以强化本身学术单位的可欲与吸引力。中国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也发生了类似的典范更替,但是却更为明确地把性别、性、其他社会差异一举融合在新创的中文名词“性/别”里(下详),以便在一片主流化的趋势中宣示一个边缘的、激进的抵抗立场。另外,如果说美国的典范更替主要由同性恋运动的发展促成(包括以女同性恋为主体与主流女性主义进行性辩论),那么中国台湾的典范更替可以说主要由(以异性恋为主的)女性情欲辩论带动,这也使得中国台湾的“性/别研究”除了推动同性恋研究、酷儿研究之外,更能清晰的与妇女运动和主流女性主义所代表的性守成力道持续鏖战,也因而更能洞悉近期性别政治趋向主流化的新权力布局以及其对性主体的冲击。
1980年代中国台湾逐渐开始积累的社会性别观点主要围绕着女性在婚姻内的处境,例如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家事和照顾工作的分工、离婚的困难和污名、家暴的难言与伤害等等,这些关注当然反映了妇女运动的良妇特质和情感取向,也使得婚姻和家庭成为妇女运动最深层的关切。然而在这个良妇视野以外,世界已经有了剧烈的转变。1960至1970年代中国台湾以纺织和加工制造业带动经济成长,构成新劳动力的大量女性劳工得以离开父权家庭,进入工厂聚集的都会卫星城镇,性自主因而有了契机;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则在此时开发新的消费与欲望动力,以西方青年文化、摇滚音乐与舞蹈来解放中国台湾年轻人的身体情欲;随着个体经济实力成长,婚姻也不再是女人的唯一前程而越来越成为人生选项之一而非必然,即使晚婚也使得性脱出婚姻的桎梏。来到1980年代,许多单身女性已具体实践了性关系的重大解放。(19)
然而性的公共论述仍集中于传统对女性的警示与谴责,性议题仍是由医学和公卫领域主导,以犯罪、偏差、卖淫、出轨、疾病等等面貌研究或报导,性主体仍然被病理化、病态化、道德化。即使1994年针对女性情欲解放形成了热烈辩论,1995年台大女生集体看黄片事件引发了社会争议,良妇女性主义团体在这些和性相关的议题上好像都只能在性别权力不平等的框架下提出批判,同时严厉排挤另辟蹊径的女性主义性论述,结果反而为保守禁色立场背书。为了开发更开阔的女性主义性立场,“中央大学”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1995年10月成立了“性/别研究室”,不但凸显性不能被性别笼罩,不能被性别不平等全然决定,也以阶级、族群、年龄、性别等社会“差异”或“别”(differences)来结合同性恋等“性”(sexualities)议题,以关照这些轴线之错综复杂纠葛。“性/别”之间的斜线不但表明了人类情欲的多元差异(性中有别),也展现性别和性之内各种可能的暧昧复杂与分裂不稳定。
这个新的女性主义性/别论述很快就与主流女性主义的性别立场对立起来。1997年台北公娼争取工作权的长期抗争中,良妇派与市长并肩推行废娼,性/别派则与公娼同一战线,维护女性性工作权,因而爆发女性主义分裂的公开化。双方的对垒从运动延烧到学术领域,1998年6位女性主义学者跨校整合提出有关性工作的研究计划,在台北公娼运动中活跃支持公娼的3位都没有通过审查。而且评审意见直接说:“本研究可以预见不仅不能发掘真相、建构可靠的知识,反会生产不可靠的东西,不唯无益于学术,更且可能产生误导社会的作用,因此不建议予以补助。”评审的主流路数不言而自明。在申覆后,有两位的申请通过,与公娼组织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仍然不通过。知识的典范更替显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已,另辟蹊径的研究路数总是会与原有典范形成(可能惨烈的)斗争。
这样的争战在进入21世纪后急速减少,主要原因是良妇女性主义者随着中国台湾政局的变化、政党政治的统治危机,逐渐被吸纳进入政府体制作为正当性的表彰,不但可以分包政府的各种计划,也分享极大的权力与资源。她们再也不需要搞运动,也不需要理会在体制外继续奋斗的不同立场女性主义者。同时,性别研究在三所大学成立了正式的相关系所(20),学术训练以性别视角为大宗,以平权为主轴,以替政府服务、协助治理为主要内容。2006年开始,中国台湾主流性别政治积极配合联合国“性别主流化”政策推广,以建立法制规章作为主要操作场域,协助建立严密管制和监控。性别平等成为政府施政的主轴,主要由良妇们主掌,急速上升成为占有道德高地的价值,在资源和正当性上大幅跃升;然而同时,性的各种实践、信息、再现则在性别平等、儿少保护的旗帜下(21),成为法律急切要管制、消除、惩罚的对象。
今日在中国台湾研究社会性别,主要的观察场域不再是最初妇女运动关切的日常生活、社会运动、文化现象、互动关系,而是行政、立法、社福,更是治理;最主要的知识工具不再是贴近生活质感的文化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而是统计学、政治学、法学。这个变化过程也构成了此刻性/别研究的重要洞见和批判对象。
每个社会有其独特的形构,也因此会形成极为不同的运动、论述、学术和典范(及其更替)。目前,中国台湾由于性/别运动与性/别研究的互相滋养以及言论相对开放,在论述和理论发展上暂有优势,性/别运动文化亦多多少少影响大陆性/别少数的文化(如语言命名)。然而,中国台湾内部的性保守势力透过民众对文明化和自我克制的渴望,往往使得法律的紧缩管制能够赢得保守的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妇女团体和主流女性主义者全力投入的性别治理也已成为国家政府管理人民的重要管道,性/别自由之危机日益明显。
相较于中国台湾,大陆的性革命也已经发生,边缘异类的性/别实践是否能够找到并得力于性/别解放的语言与文化(包括学术研究)以及沟通发声的开放语境,或者大陆会不会也和台湾一样在性别政治的操作下形成严密的性别治理──这些问题都是对于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高度关心的同行们需要持续观察的。宁应斌在论及两岸三地性/别发展时,曾经颇为乐观的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大陆本身的广大与多样以及文明现代性的不平衡发展:
中国大陆内部差异甚大,不但有未被中产文明化过程驯化的乡野朴鲁,也有极限体验的独特性癖或光怪陆离存在于社会深层,但是目前多数尚未能自傲现身,仅能含蓄自惭,在这方面,台湾的性/别异类则可以提供自我壮大的修辞话语与酷儿态度。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虽然有信息的检查与管制,但是许多在其他社会经过多年发展才锻炼出来的性/别修辞话语与政治态度,几乎同一时间都抵达了大陆,这诚然是后发的现代化特色。大陆性/别少数群体一方面具备同时涌到的话语资源和身份选择,另一方面则又因为检查管制而使得精英阶层无法发展能量,有时会阻碍这些话语资源与能量的向下渗透(因而无法帮忙壮大底层);却也有时会以“扭曲误解”的形式被下层阶级挪用改造,从而形成具有活力、突破现成分类的山寨身份(如伪娘);还有时反而给予性/别底层自我发展、自我定义、自我命名的契机,和上述山寨身份一样都形成了中国特色。(22)
或许,相对于中国台湾已经形成的从上而下的、柔软但无可商量的性别治理(23),抗拒文明现代性的单一和规训,维持中国大陆内部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呵护基层(特别是边缘)主体的自我培力,是必要的努力方向。
注释:
①本文初稿在2013年6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研习班中以演讲形式发表,现在再度改写后以论文形式发表。
②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③宁应斌教授于2009年第一届两岸三地性/别政治新局势会议中首度提出“社会性”、“生理性”、“社会性别”之三角用语,以对应英语的sexuality、sex、gender,作为两岸三地的共通理论语言。“社会性别”(gender)有别于“生理性(别)”(sex),生理性却无法决定“社会性别”;同样原理,“社会性”(sexuality)有别于“生理性”(sex),生理性也无法决定显然多样的“社会性”,两者之间同样有着复杂交错的关系。“社会性”一词强调“性(和性别一样)是一种社会建构”。参见宁应斌:《社会性(Sexuality)》,载何春蕤编:《连结性:两岸三地性/别新局》,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0,第3-14页。本刊本次专辑以“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为主题,我对最前面的这个“性”的理解就是此处所称的“社会性”。
④对于中国台湾的性解放运动发展和理论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宁应斌:《台湾性解放运动十年回顾:试论》,载何春蕤编:《转眼历史:两岸三地性运回顾》,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2,第365-393页。
⑤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作家Bell Hooks从1980年代便批判美国妇女运动对种族、阶级着力不足,她因此曾尖锐的质疑妇女运动所强调的性别平等:“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的阶级结构里,男人彼此也不是平等的,那么女人是要求跟谁平等呢?”毕竟,性别总是和其他的社会差异和力道纠结的,无法只从一条轴线(如性别)来分析社会或构思改变。谈平权的时候只想到性别,反而凸显了其他的社会差异已然被忽略,这在种族政治尖锐化的美国特别明显碍眼。Hooks后来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宰制体系相互勾联而形塑了现实,她因此创造了“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体制”(white-supremacist-capitalist-patriarchy)这个复合名词来强调许多力道是同时作用的,如果只关注一条轴线的运作就无法全面理解现实。这也是当代理论研究强调intersectionality的另一版本。可参看Hooks的访谈录像http://www.youtube.com/watch?v=zQUuHFKP-9s&hd=1.
⑥今日在许多英语系国家填写官方文件时仍然用sex(而非gender)来指涉性别。这使得跨性别主体不得不填写原来的生理性别,因而对照出与其社会性别的自我呈现有极大差异,也造成跨性别主体的生活困难。
⑦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在1900年至1964年之间最可能关切性别议题的婚姻家庭杂志中其实找不到任何一篇使用gender一词的文章(Udry,J.Richard,“The Nature of Gender,”Demography,31.1994(4)),然而1970到1980年代,gender却大量且广泛的出现在更多学术期刊中(Haig,David,“The Inexorable Rise of Gender and the Decline of Sex:Social Change in Academic Titles,1945-2001,”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3.2 (April 2004):pp.87-96)。在这里可以看到gender概念的学术化和稍后的普及化。
⑧⑨⑩(11)Haig,David,“The Inexorable Rise of Gender and the Decline of Sex:Social Change in Academic Titles,1945-2001,”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3.2 (April 2004):pp.87-96.
(12)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首枚人造卫星Sputnik进入太空绕行地球,美国大惊,艾森豪威尔随即签署《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Defense Education Act),投入大量经费强化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以加入冷战侧翼的太空竞逐。高教的大幅成长、民主化、及其对精英教育的冲击,形成了1960年代美国学运、民运快速发展的沃土。
(13)1980年代初期美国女性主义针对女同性恋性爱模式以及更广为大众所禁用的色情材料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禁色派(又称反性派)以性别二元的权力分布来阅读色情图像,认为色情就是性别压迫,拥性派则抗拒反性派的扫黄措施,主张女性情欲的能动性必须被认知。可参考Carole S.Vance,Pleasure and Danger: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Lisa Duggan and Nan D.Hunter,Sex Wars:Sexual Dissent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10th anniversary edition,2006.
(14)Janet Halley,Split Decisions: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P,2008,pp.114-118.
(15)著名的Ohio State University、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英国的York University等甚至已经设置了以sexuality studies为名的专属学程。
(16)(17)参见http://www.arts.cornell.edu/fgss/academics/index.html页面上Academics之下的Historical Note。
(18)Yale University于1979年成立的“妇女研究”学位学程,于1998年首度改名为“妇女与性别研究”学位学程,2004年再度改名为“妇女、性别与性研究”学位学程。这个改动过程充分地反映了学术领域内的发展方向。请见该校网页http://www.yale.edu/wgss/。
(19)中国台湾通俗作家苦苓1993年在《亲爱的别人的》(台北,太雅)一书中就曾以“单身公害”一词来批评这种不再封闭自身情欲甚至成为第三者的单身女性。1994年卡维波则以《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宣告了情欲领域的重大变化(卡维波:《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载何春蕤编:《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元尊远流,1997,第348-367页)。
(20)代表性/别研究立场的“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自2008年起年年提出成立研究所的申请,虽然有着极为优秀的学术表现,还是年年被搁置缓议,被剥夺再生产的管道。
(21)何春蕤:《台湾性别政治的年龄转向》,载何春蕤编:《转眼历史:两岸三地性运回顾》,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2,第261-263页。
(22)宁应斌:《中国转向之后的性/别研究》,载宁应斌编:《性地图景:两岸三地性/别气候》,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1,第iii-viii页。
(23)何春蕤:《性别治理与情感公民的形成》,载宁应斌编:《新道德主义:两岸三地性/别寻思》,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3,第211-2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