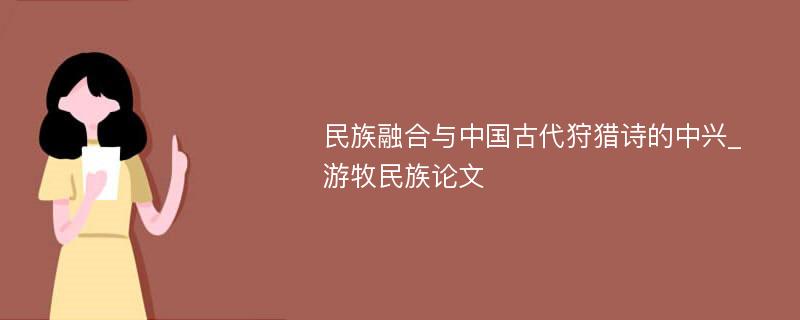
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狩猎诗的中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从汉魏至齐梁,是狩猎诗的消歇期,这和文学本身的分工有关,也是农业文明导致作家片面发展的结果。北朝民族融合使狩猎诗在《诗经》之后出现中兴局面,它的作者既有北朝本土文人,又有自南入北的王褒、庾信。北朝狩猎诗表现了游牧民族的风尚,把狩猎作为纯娱乐活动看待,但还缺少深刻的意蕴,猎手形象的个性不够突出。唐代真正实现了狩猎诗的中兴,注意对单独猎手的刻划,同时又流露出对时政的关心和参与,用政治功利对狩猎活动加以规范。狩猎诗从北朝到唐朝的演变过程,在辽金元到清代又再度重视。
关键词 民族融合 狩猎诗中兴 游牧文化 农业文明
狩猎最初是古代先民重要的谋生方式,是一种生产实践活动。中国古代狩猎诗产生甚早,相传作于黄帝时期的《弹歌》,叙述的就是制造弓箭、猎取野兽的情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中国古代狩猎诗经历了一个由昌盛到消歇、又再度中兴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农业文明使狩猎活动在生产实践中日益退居次要地位,而越来越变成一种消遣和娱乐,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而在游牧民族那里,狩猎却是人们重要的生产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依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在中国古代,一方面,农业文明使狩猎诗萎缩,另一方面,游牧文化又促进狩猎诗的产生和发展,不断为它注入生机和活力。中国古代经历了多次的民族融合,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反复地碰撞、吸纳,形成特殊的文化生态。正是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游猎诗得到中兴的契机,再度繁荣昌盛。
一
《诗经》时代是狩猎诗的兴盛期,今本《诗经》收录了十余首狩猎诗,分别见于《周南》、《召南》、《郑风》、《齐风》、《秦风》、《豳风》和《小雅》,覆盖的地域非常广阔,涉及到从天子、诸侯到士大夫、庶民各个阶层。除此之外,不少逸诗对狩猎活动也有所反映,相传作于周宣王时期的《石鼓诗》,就是叙述狩猎活动的作品,而且篇幅较长。先秦诗歌保存下来的数量有限,游猎诗占有相当比重,称那个时代是狩猎诗的兴盛期合乎历史实际。
秦代以后,作为严格意义的狩猎诗日趋减少,从汉魏以至南朝齐梁,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竟没有一首纯粹的狩猎诗,可以说是这类诗歌的消歇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受文学本身分工的制约,也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古代帝王有四时田狩之制,汉代许多大赋就是专门为此而作,还有的是把狩猎作为重要内容写入作品。天子狩猎是一项隆重的典礼,因此,汉代文人也就用最能体现皇家气派的大赋来表现它。久而久之,创作上形成一种定制,写帝王狩猎活动必用大赋,诗歌却派不上用场。汉代文学体裁之间的这种分工,作为历史的惯性在汉族王朝相沿不改,一直持续到南朝后期。这就是为什么从汉魏到齐梁,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许多狩猎赋,却见不到狩猎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狩猎是一项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活动,参加狩猎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武艺,尤其要长于骑射。然而,从两汉到齐梁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作家片面地向文的方面发展,对武艺越来越生疏。他们的兴趣不在狩猎上,而以琴棋书画为精神寄托。古代文士是诗歌创作的主体,既然他们不再是校猎场上的成员,所以,尽管出于润色鸿业的目的创作狩猎赋去歌颂帝王,但在表现他们自身的生活情趣时,却很少提到狩猎活动,不去创作狩猎诗。
汉魏齐梁文士绝大多数不再具备猎手的素质,但是,社会上的狩猎活动并没有灭绝,时常还可以见到。然而,农业文明和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抵触的,狩猎往往造成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有鉴于此,古代贤哲很早就对狩猎活动怀有高度警觉,批评那些沉湎于狩猎而难以自拔的人。《老子》第12章称:“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孟子·梁惠王下》亦云:“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古代贤哲把狩猎看作是追求耳目口腹之乐、摇荡心志的活动,认为它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很容易使人走入歧途。汉魏齐梁文人在这种观念熏陶下,往往对狩猎抱疏远态度,偶而创作这方面的作品,也要指出狩猎可能产生的危害。《全晋文》卷九十二收录了潘岳的《射雉赋》,序言称:“余徙家于琅琊,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肄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潘岳是受琅琊地方习俗的影响而从事狩猎活动,带有入乡随俗的性质,他又按照文学本身已经形成的分工,用赋这种体裁加以表现。结尾写道:“若乃耽盘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乐而无节,端操或亏。此则老氏所戒,君子不为。”潘岳虽然感受到了亲身参加狩猎的乐趣,但他又及时警告自己,不能流连忘返,而要有所节制。古代文人对狩猎活动的警惕心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因此,虽然社会上还存在狩猎活动,但激发不起文人的创作热情,这也造成汉魏齐梁狩猎诗的匮乏。
二
北朝是民族融合时期,北朝统治者有的是鲜卑族,有的是鲜卑化的汉人,代表的是游牧文化。游牧民族长于骑射,狩猎是他们经常从事的活动。
北朝狩猎活动勃起,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冲击下,原有的文学体裁之间的分工被打破,继《诗经》之后再度出现数量可观的狩猎诗,可以说是狩猎诗的中兴。
首先要提到的狩猎诗作者是高昂,他是东魏战将,鲜卑化的汉人。《北齐书·高昂传》记载,“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高昂少年时就以骑射为业,后来成了英勇善战的将领。《北齐诗》卷一收录了他的《征行诗》,全文如下:“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这首诗写的是典型的掠夺式的游牧生活,其中提到每天都要进行狩猎。高昂既是狩猎的亲身参加者,又是狩猎诗的创作者,这首诗尽管很简短,却写得热情洋溢,传达出了狩猎的乐趣。高昂的另一首《赠弟季式诗》也涉及到狩猎:“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高季式是高昂之弟,季式出任济州刺史,高昂劝酒作诗为他送行。高昂认为刺史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作为一名地方官,他可以悠闲自在地从事狩猎活动,不受任何限制。自己虽然是朝廷的司徒,但在这方面却无法和刺史相比。高昂的诗不仅表现了他对狩猎活动的热爱,从中也可以看出北朝盛行狩猎的社会风尚。高昂的这两首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狩猎诗中兴的开端。
狩猎风气弥漫于北朝,但是,这个时期创作狩猎诗的两名主将却是由南入北的王褒和庾信。王褒的狩猎诗现存二首,收录在《北周诗》卷一。庾信的狩猎诗现存六首,载于《北周诗》卷二和卷四。王、庾二人本是南朝著名文人,归附北朝以后,得到北周朝廷的器重,成为文学侍臣。他们经常陪驾出猎,有机会亲眼目睹北朝的狩猎场面,许多景观是在南朝见不到的,使他们产生一种新鲜感,激发起创作冲动。王庾二人狩猎诗的创作有的出自主动,更多的是应诏唱和之作。应诏唱和在时间上要求比较紧迫,不允许他们继续沿用大赋体制、从容不迫地进行创作。大赋耗时费力,难以速成,诗歌创作却相对容易,可以迅速拿出作品。王褒、庾信为应诏唱和而选择诗歌这种体裁,从而进一步打破了汉代形成的写狩猎必用赋体的传统,使狩猎诗出现中兴局面。
综观王褒、庾信的狩猎诗,它们虽然出自南人之手,但却表现了北方游牧文化的某些特点。
一是狩猎活动的普遍和频繁。王褒、庾信二人的狩猎诗,有的是跟随天子狩猎时所写,也有的是写朝臣的狩猎,庾信的《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诗》、《和宇文京兆游田诗》,都是属于后一类。北朝不但天子狩猎,朝臣也经常从事这项活动,对此,王褒、庾信的诗作了如实的反映,并且加以歌颂。北朝狩猎活动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并且非常频繁,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王褒的《九日从驾诗》写秋狩,《和张侍中看猎》写冬狩。庾信的狩猎诗有三篇明显是写冬狩,一篇写春狩。他的《咏画屏诗二十五首》内容庞杂,其中第十八首系狩猎题材,全诗如下:“将军息边务,校尉罢从戎。池台临戚里,弦管入新丰。浮云随走马,明月逐弯弓。比来多射猎,唯有上林中。”这首诗告诉我们,北朝将领经常开展狩猎活动,在时间上随意选择。高昂诗所说的“朝朝围山猎”,写的是部队出征途中的情况,庾信诗展示的则是军队将领闲暇时的狩猎活动,二者相互补充,全面地反映了北朝将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把狩猎活动列入重要日程的历史事实。
二是狩猎活动的纯娱乐性。汉魏齐梁的狩猎赋,通常都对帝王的狩猎活动加以粉饰,虽然其中不乏对畋猎之乐的描写,但又把它和某些庄严的目的联系起来,或称为了供祭祀,或云是在修武备,努力淡化狩猎活动的娱乐功能。北朝的狩猎诗则不同,这些作品不涉及政治功利,而是把狩猎当作纯粹的娱乐活动加以表现,显得真实直率。庾信《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有“山村落猎围”之语,狩猎是春日游山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消遣和享受。《和宇文京兆游田诗》写道:“小苑禁门开,长杨猎客来。悬知画眉罢,走马向章台。涧寒泉反缩,山晴云倒回。熊饥自舐掌,雁惊独衔枚。美酒余杭醉,芙蓉即奉杯。”长杨本是秦朝旧宫,至汉成为天子行宫,宫中有垂杨数亩,门曰射熊馆,系秦汉游猎之所。《汉书·张敞传》记载,“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抚。”章台是长安章台下街名,又是战国时秦渭南离宫台名,庾信诗中兼取二义。诗人运用秦汉典故,把京兆尹宇文氏的狩猎活动和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张敞的逸闻轶事联系起来。张敞在家为妻画眉,散朝后驱马过章台街,用扇子遮面,以免别人认出自己,显得悠闲自在。章台又是秦汉游猎的场所,诗中用以指代宇文氏的猎场。狩猎过程中用芙蓉杯饮美酒,其乐无比。游牧民族把狩猎当成确证自身的活动,虽然通过狩猎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提高了参加人员的武艺,但是,他们在从事这项活动时,并没有太多功利方面的考虑,没有和严肃的意义、崇高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而主要是体验到其中的乐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在自我实现的人那里,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工作与娱乐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他的工作就是娱乐,他的娱乐就是工作。”[①]用这段话来概括原始游牧民族的狩猎活动是满恰当的。北方游牧民族成员使游猎活动具有自我的性质,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游猎活动是他们内在价值的体现和化身,而不是要追求在狩猎之外的某种目的。王褒、庾信的狩猎诗展示了游牧文化的这种特征,读者看到的是娱乐和工作融为一体的生动画面,和高昂狩猎诗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王褒、庾信生于南朝,长于南朝,他们虽然在北朝文化的熏陶下创作出了一些反映游牧民族风尚的狩猎诗,但是,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他们这部分作品还缺少更加深刻的意蕴。王褒、庾信都是从欣赏的角度去描绘狩猎活动,他们虽然有时也奉陪出猎,但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出现,并没有跃马盘弓亲自从事狩猎。这样一来,他们对猎手精神风貌的展示有时就流于表面化,显得不够深入。其次,王褒、庾信诗中猎手的个性特征不够突出,相反,渲染狩猎队伍的整体阵容倒是比较充分。王褒、庾信很大程度上是用汉魏齐梁文人创作狩猎赋的笔法来写狩猎诗,用农业文明形成的素质来把自己和狩猎活动沟通,从而造成创作主体和表现对象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未能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三
中国古代诗歌在唐代进入鼎盛期,唐诗成为传统文化的瑰宝。古代狩猎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北朝开始中兴的,然而,狩猎诗中兴的真正实现却是在唐代完成的。唐代出现众多的诗歌流派,狩猎诗这个时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唐诗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
唐代继承了北朝民族融合的文化积淀,狩猎活动仍然比较频繁和普遍,狩猎诗也不断地产生出来,真正实现了这类诗歌的中兴。和北朝相比,唐朝的狩猎诗又有新的进步,弥补了王褒、庾信作品的某些不足。
唐朝有大量的观猎诗,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狩猎人员自己创作的诗篇,他们亲自射鸟击兽,又通过自己的诗歌对这种活动加以表现,给人一种亲切感。《全唐诗》卷一、卷三所收录的唐太宗《帝京篇》之三、《出猎》、《冬狩》、唐玄宗的《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都是狩猎活动的纪实之作。《通典》卷一三二《皇帝田狩》节对天子狩猎的细则有具体记载,唐太宗、玄宗都是亲自执弓,他们狩猎诗写的是亲身经历和感受。盛唐诗人韦应物的《射雉》也是写自己的狩猎活动,全诗如下:“走马上东冈,朝日照野田。野田双雉起,翻射斗回鞭。虽无百发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绣臆碎,头驰锦鞘悬。方将悦羁旅,非关学少年。叟弓一长啸,忆在灞城阡。”这首诗收录在《全唐诗》卷一九三,是韦应物壮年或老年时所作。韦应物系长安人,少年时以卫郎事唐明皇,晚年折节读书。韦应物武职出身,狩猎是他的本行,这首诗把作者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变化表现得细致入微,非常耐人寻味。他手执弓箭射雉完全是为了消愁解闷,用它来排遣旅居外地的苦闷。他不想效仿那些少年猎手,但此次射雉也使他回忆起青少年时期在长安的生活,诗中展现的跃马弯弓的自我形象,依然不减青少年时的英姿。韦应物既能搭弓射雉,又能动手写诗,这是王褒、庾信无法比拟的。经历北朝的民族融合,唐代产生出一大批文武兼备之士,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融汇。民族融合使唐代士人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相当一部分成为既是诗人又是射手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了诗歌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统一。
唐代的一些狩猎诗也写了盛大场面、整体阵容,这和北朝同类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唐代狩猎诗还注意对单独猎手的刻划,写出他们的个性,这在北朝狩猎诗中很难见到。韩愈的《雉带箭》一诗载于《全唐诗》卷三三八注云:“此愈佐张仆射于徐,从猎而作也。”张仆射名建封,这首诗着力刻划张建封的形象,没有渲染狩猎队伍的整体军容。在描写狩猎情景时,先是展现张建封充满自信的姿态,虽有猎物出现却不急于射击,以此引来众多的观众。接着写他精湛的射艺,在众人的注视下一箭中的,仰天大笑、踌躇满志,一片欢呼声中色彩斑斓的山雉带箭堕落在马前。杜牧的《赠猎骑》载于《全唐诗》卷五二四,是一首七言绝句:“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诗人笔下的猎手英姿飒爽,箭不虚发,通过描写他鸣鞭走马、翻身欲射的动作,诗人联想到他是怎样射落双雕,同时又为北去的大雁担心,劝猎人手下留情。至于点出射落的双雕“血尚新”更是传神之笔,暗示猎人连连得手,给人以鲜活之感。
唐代是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经历了充分的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这样一来,它的狩猎诗就难免留下农业文明的烙印,流露出对狩猎活动的警惕心理。作为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物,就是在狩猎诗中表现出对时政的关心和参与,用政治功利对狩猎活动加以规范和诱导。汉魏齐梁狩猎赋经常出现的那种倾向,在唐代狩猎诗中又再度复活。唐太宗《出猎》诗称:“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他申明自己狩猎的目的是为民除害,而不是贪图享受,否认狩猎是在追求娱乐。《冬狩》诗称:“心非洛汭逸,意在渭滨游。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唐太宗引述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以为戒鉴,用以提醒自己。《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代太康逸豫享乐,盘游无度,在洛水之滨畋猎,被有穷后羿所取代。其弟五人在洛涔避难,作《五子之歌》。歌中引用古训,把“外作禽荒”视为导致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禽荒,指没有节制地从事狩猎活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文王猎于渭滨,遇到了在那里隐居的高人吕尚。周文王把他立为太师,后来吕尚辅佐武王成就大业,创建周王朝。唐太宗表示,他要借狩猎的机会招揽贤臣,而不是像夏代太康那样沉湎于畋猎之中。在他看来,纵情游猎是不足取的,这种做法最终必定给人带来忧患。唐明皇《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在立意上和太宗的《冬狩》相类似,结尾写道:“既欣盈尺兆,复忆番溪便。岁丰将遇贤,俱荷皇天眷。”瑞雪兆丰年,唐明皇在义成狩猎时忽降大雪,他想起周文王狩猎遇吕尚的故事,又想到来年的丰收,心中无比高兴,认为这是皇天对自己的眷念。番溪,相传吕尚隐居之处,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地处渭水之滨。唐明皇也把狩猎说成是为了寻访贤人,是堂堂正正的大事,极力突出此项活动的政治价值。
唐朝天子的诗作把狩猎活动和严肃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唐代文士也大力宣扬狩猎活动要有经世致用的功能,不过,他们主要是把狩猎与习武挂钩,和天子诗作的联想角度有所不同。《全唐诗》卷二二○收录了杜甫的《冬狩行》,此诗先是描写梓州刺吏章彝冬狩场面,结尾部分写道:“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当时章彝兼侍御史留后东川,唐代宗为避吐蕃兵锋逃出长安,奔向陕州,诏召天下兵马,竟无一人响应。杜甫有感于此,故向章彝进言,希望他能把狩猎时显示出的军威用于疆场,协助朝廷安邦定国。杜甫这首诗写于危难之际,他劝狩猎的封疆大臣变猎禽为猎敌,可谓用心良苦。武元衡《幕中诸公有观猎之作因继之》一诗载于《全唐诗》卷三一七,是他任剑南节度使期间所作。从诗的题目可知,他是在许多幕僚写了观猎诗以后加以唱和。诗的前六句展示狩猎场面,结尾两句如下:“为报府中诸从事,燕然未勒莫论功。”汉代窦宪北征匈奴至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文人班固在那里撰文纪功,并命人刻于石上。武元衡身居重镇,手握兵权,他劝告幕僚不要为狩猎大唱赞歌,只有为国家消除战乱才有资格论功。
唐代的狩猎诗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功利紧密相联,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诗人的忧患意识加深,这种联系进一步强化。从本质上看,唐代狩猎诗重视政治功利的倾向,体现的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也是农业文明对游牧文化的同化,是把游牧文化形成的狩猎习俗努力纳入农业文明的轨道,服务于国家的政治。这样一来,唐代的狩猎诗就和汉魏齐梁的狩猎赋在思想倾向上有了相通之处。
四
中国古代狩猎诗的中兴始于北朝,到唐代就基本完成了。在此期间流传下来的狩猎诗基本都是产生于中土,反映的是中土狩猎场面,相反,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狩猎诗却非常罕见。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曾经反复多次进行,继南北朝之后,辽金元时期各民族再次经历了一次大的融合,反映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狩猎的诗篇也陆续见诸典籍,为古代狩猎诗增添了新的光彩。
赵延寿是没入辽国的汉人,耶律德光朝曾任丞相。《太平广记》卷二○○收录了他的一首失题狩猎诗,全文如下: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诗中提到的黄沙漫卷、大雪飞扬的景象,以及探水移帐、夜深生火等习俗,都是中土见不到的。狩猎者所处的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却感到乐趣无穷,除了狩猎放牧之外,他们没有更多的挂牵。游猎是他们的职业,也是生命的寄托,冰天雪地中鸟啄霜果、马畏冰河的场面,都显得富有诗意。据《太平广记》所载,此诗流播甚广,“南人闻者,往往传之。”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展示了大漠风情,再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故乡独特的狩猎生活画面。
《全辽文》卷十二引录姜夔《白石道人诗集上》记载的《契丹风土歌》,诗的后半部分如下:
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阜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韫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
原诗注:“都下闻萧总管自说其风土如此。”这首诗当是契丹族萧氏口述,姜夔笔录。尽管经历了一个转述过程,但作品依然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文化气息,而且近乎“原汁原味”。以上两首诗,一写春狩,一写冬猎,虽然季节不同,景物有别,但诗中的主人公都专注于狩猎,别无他虑。在这些狩猎者身上见不到对政治功利的牵挂,他们的内心是浑朴的,没有因权衡是非利害而产生的矛盾心态。北朝狩猎诗注重娱乐性的特征,在上述诗篇中同样可以见到,二者都保留了较多的游牧文化因素。
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土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农业文明的同化,狩猎诗从北朝到唐朝的中兴历程,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游牧文化融合于农业文明的发展态势。从辽金元到清代,北方游牧文化继续被中土农业文明所同化,因此,狩猎诗最终又恢复了唐代的风貌。建立大清帝国的满族非常重视狩猎活动,《日下旧闻考》卷七四所录乾隆四十七年御制《仲春幸南苑即事杂咏》诗自注:“予十二岁时,恭侍皇祖于南苑习围。盖我朝家法,最重骑射,无不自幼习劳。今每岁春间,仍命皇子、皇孙、皇曾孙辈学习行围,所宜万年遵守也。”直到乾隆朝,满清贵族仍然遵循祖宗法度,通过狩猎训练子孙的骑射技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是狩猎能手,据《清宫遗闻》卷一所载,康熙晚年曾对臣下说道:“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乾隆狩猎,也多有所获,他的狩猎活动从十二岁开始,一直到七十二岁还在南苑行围,并即事作诗。从这些活动来看,康熙、乾隆两位天子身体力行,继承了满族的游牧遗风,把狩猎当成人生一大乐事。可是,阅读他们的狩猎诗,又会发现他们受农业文明熏陶很深。《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四收录了康熙、乾隆多首狩猎诗。康熙《南苑行围》云:“苑中闻教阵,无事静论边。不废时苗典,思周天下先。”乾隆二十年御制《行围》称:“不废武还思谏猎,个中吾自有权衡。”康熙大帝狩猎时想到练兵习武,还想到不误农时。乾隆皇帝一方面要通过狩猎活动加强武备,同时又重温司马相如对汉武帝的讽谏,狩猎要适可而行又适可而止。康熙、乾隆的狩猎诗尚有游牧民族的流风遗韵,同时又打上了农业文明的印记,比较完满地体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和唐代天子的狩猎诗非常相近。总之,历史上每一次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土,都给狩猎诗的中兴提供契机,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又决定了狩猎诗演变的最终形态。
注释:
① [美]马斯洛:《超越性动机论——价值生命的生物基础》,引自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标签:游牧民族论文; 诗歌论文; 唐朝论文; 民族融合论文; 读书论文; 全唐诗论文; 南北朝论文; 庾信论文; 齐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