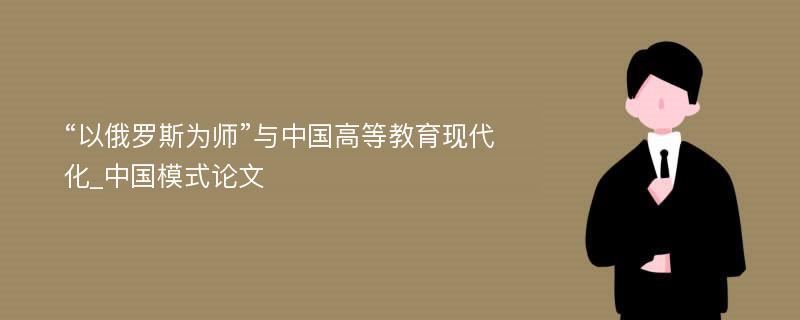
“以俄为师”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师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3)03-0034-03
一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发生在西欧,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所谓现代化,我们认为就是指“后发型”国家在受到“先发型”国家活动和榜样的刺激下所进行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与传统的“决裂”,而是与文化传统的互动。“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它的现代化过程必然要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与传统文化发生互动。”[1]然而,“后发型”社会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对外学习,事实上,现代化本身就带有对外学习的意思。所以,对外学习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例外,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以“早发内生型”的国家为蓝本。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了“超英赶美”,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与这场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是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首当其冲地成为这场对外学习的试验田,并很快成为这场对外学习的中心之一。因此,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学苏”可基本反映这场运动的大致情况。
二
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学苏”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忽视了这个环节,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多次高教改革。有人认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若干弊端就植根于这场学习运动之中,“‘以俄为师’的最大弊端在于形成了一套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结构,……我国以后进行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修正或重创新的教育体制和结构。”[2]也有人断言,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的‘以俄为师’。因为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3]。种种不同的观点向我们提出了究竟应该如何估价这次高等教育的对外学习。从总体上讲,高等教育的“以俄为师”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改革。应该说,这次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就高等教育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而言,“以俄为师”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其主要表现有三:1)“院系调整”初步改善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分布。高等教育机构在全国分布的合理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建国之初,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绝大部分高校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广大内地大学稀少[4]。而当时“院系调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高校布局不均衡的现象,并采取了迁移、新建、重组等手段对高校的地区分布进行了重新规划与调整,初步改变了高等教育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况。2)确立了“专业教育”的目标模式,改变了大学教育游离于经济生活之外的弊病。民国遗留下来的205所大学都是以美、德等国家的大学为样板的。西方大学所崇尚的“博雅教育”曾对我国大学教育影响很大,并一度形成了我国大学所开设的课程有点脱离中国实际,所建学科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联系不大的局面。“以俄为师”把这种学用脱节的“博雅教育”逐步改变成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学用结合的“专业教育”,确保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3)建立了严格的教学制度,保证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旧中国大学盛行英美等国家的松散的教学结构,引入“苏联模式”后,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施体系。课堂结构因此而变得十分严谨,教学过程也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操作规则。较之于旧中国大学松散的教学制度更有利于保证大学的教学质量。
然而,评价任何事物,我们都要用两个“焦点”看问题。今天当我们对“以俄为师”的高教改革进行反思时,既要看到其正面作用,更应看到其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好的方面看问题,对“以俄为师”的巨大负面影响缺乏深刻认识。事实上,“以俄为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其不良后果迄今都没有被完全消除。简而言之,“以俄为师”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教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专业设置重复,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为了与高度的计划经济相适应,我们仿效苏联划出相当一部分学校归专业部门管。其余的大学则一分为二,相当一部分学校归地方管,少数学校归教育部直管。由于中央各部委与地方各自为政,在专业设置上搞“小而全”,导致专业设置的低水平重复。而且由于专业设置直接与生产线相连,导致专业划分越来越细,造成毕业生对新的领域的不适应。其二,形成了过于功利化的工具价值取向的教育目标。由于我们片面强调把旧中国大学的“博雅教育”转变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把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使大学的教育功能出现紊乱。这主要表现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教育的文化功能则遭到极大的削弱,比如我们一度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只教俄语,不教英语。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把我国大学教育压得残缺不全,大学的超功利的人文精神被消磨殆尽,使大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三,形成单科院校占主体的格局,造成高等教育内部专业比例的严重失调。通过“院系调整”,我国综合性大学的数目大幅度减少,单科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其主要原因是我们不但将综合性大学进行分散调整,而且将工程学与基础学分离,造成文理分家、理工分家。1947年全国有综合性大学55年,工科院校18所,到1957年综合性大学减少到17所,工科院校则增加到44所[5]。不但如此,而且在专业的设置上,由于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导致工科专业的比重急剧上升,文、法、商等专业的比重却急剧下降。比如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47.6%,1957年则降至9.6%。1953年,在设置的215种专业中,工科占107种,而文科仅占19种[6]。专业比例的失调造成了文、法、商等方面的人才短缺。由此可见,“以俄为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并不全是积极的影响。相反,它的消极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全面学苏”更是对外学习中的一种异化形式,它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三
为什么会出现“全心全意学习苏联”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笔者认为“全面学苏”是必然性与偶然性机缘凑合的产物。作为“后发型”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必然会寻找学习的蓝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对外学习的过程。“西学东渐”运动曾促使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然而,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极端的敌视态度。因此,学习苏联在当时就成了惟一的选择。加之,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的确可以从苏联模式中找到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榜样。由此可见,学习苏联是种种政治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高等教育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政治、经济的“一边倒”决定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以俄为师”。正如朱九思先生所说的:“50年代全心全意学习苏联,主要是政治原因,在教育科学上没有任何根据。”
分析任何社会事务,都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一为原则分析,一为技术分析。原则分析解决“应不应该”的问题,技术分析解决“如何操作”的问题。虽然从原则层面来说,学习苏联模式有其必然性。苏联模式要学(原则层面),但并非一定要采取全盘照搬的方式进行(技术层面)。事实上,对学习苏联模式进行技术性分析可以突破历史决定论的藩篱,可以使我们从这段历史中挖掘出更宝贵的东西,使我们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教益。历史决定论本质上是一种宿命论,“它将历史发展的方向推给一个神秘的力量,从而剥落了一个社会对其成败得失的理性反省与义务承担。”[7]从技术层面分析历史,历史变得可以假设,它可增强我们对历史反思的力度。
人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得失最主要的成因是当事者的选择。实际上,从技术层面看,50年代学习苏联至少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学习方式。一种是把苏联模式神化,把苏联模式当教条全盘照搬照抄。另一种是将苏联模式当作一般创造物来学习,把苏联模式看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正确或固定不变的,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地进行学习。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有时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并付出截然不同的代价。事实上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显然,第一种学习方式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第二种学习方式所付出的代价。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我们恰恰选择了那种代价昂贵的学习方式——“全盘苏化”。在文化教育领域,我们扫荡传统文化,“倒向苏联”对苏联教育模式进行了完全的照搬。当时我们不论在观念上、体制上、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是对苏联教育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就照搬了诸如“院系调整,全盘苏化”、“重理轻文”、“强化专业教育”、“大批院校归专业部门”等一整套的苏式体制。而我国教育所固有的一些优良传统大都被抛弃,这就“完全打乱了原有大学大体上合理并与社会相适应的学科结构。”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硬被分解成单科性学院。又如我国向有私人办学的传统,解放前我国曾拥有一批办得较好的私立大学,但经过50年代的教育改革,私立高校几乎全部被取消。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当时不全面学习苏联,而遵照教育本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中国高等教育就不会还是现在这种状况,说不定早就产生了世界一流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甚至出现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假设。可是,在当时学习苏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当时谁也没有怀疑学习苏联有什么不好”(朱九思语)。历史证明我们为选择这种学习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一个弊端重重且影响深远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所形成的强大惯性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大大提高了教育改革的成本。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浪费在对这种体制的毫无意义的修修补补之上,严重地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四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以俄为师”,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这次学习不算成功,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至今尚在进行之中。总结“以俄为师”的经验教训,对现在所进行的对外学习(主要学习美国),对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将是十分有益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必须处理好“认同”与“适应”的关系。所谓“认同”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所谓“适应”就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既要认同又要适应。近代以来,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强调适应,对传统继承不够,认同太少。“全盘西化”、“全盘苏化”就是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对外来的文化缺乏选择的表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传统,恰恰相反,它正是在认同传统的基础上选择国外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当然认同也不能全面认同。
第二,必须处理好“学习”与“创新”的关系。对外学习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而要在消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然而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中,我们往往以学习的呼声冲淡创新的努力。照搬过多,创新不足。实际上,学习本身就是创新。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不完善性,我们不能将接受的东西作教条,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必然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每一次这样的结合,就是一次创新。正如罗素所说的,中西文化碰撞后将产生一个更伟大的文明。只有创造性的学习才能不被别人同化,也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第三,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并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本土化—国际化—本土化”的交互流动。“本土化”就是对输入的外来文化,不是简单的搬用,而是进行“嫁接”。把国外积极的文化,“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砧木上,使之在中国文化的主根上生根开花(涂又光语)。“国际化”即是指在学习国外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把自己独特的传统文明发扬与创新,输入世界。只有经由“本土化”达到“国际代”才会激活民族的整体创新能力,更快地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
第四,必须处理好“中庸”与“极端”的关系。“全盘学苏”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对“中庸”与“极端”关系问题的关注。任何国家选择现代化道路总是有代价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代价,理性的社会总在避免走极端,而致力于“中庸”之途。“‘中庸’的获得不是靠着消除‘极’的存在,而恰恰是通过对‘极’的价值的尊重和兼容。”[8]因此,对外学习,选择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不能只是一种主张,一个声音,而要充分保护各种不同观点、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同的思想往往能够拓宽决策的视野。只有不同的观点之间保持有必要的张力,才能避免对外学习中的“一边倒”,消除现代化进程中剧烈的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