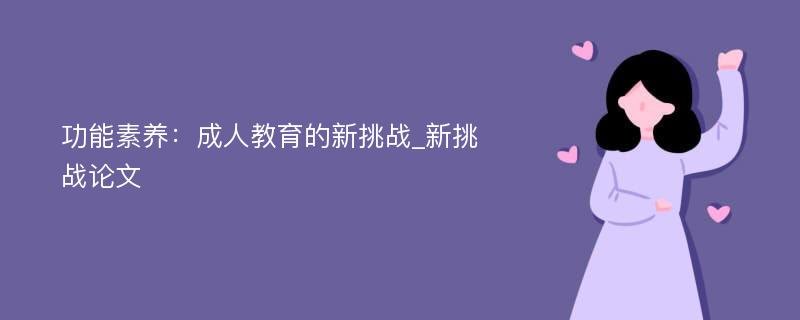
功能性扫盲:成人教育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扫盲论”及其研究
众所周知,文盲是发展的一大障碍。大力开展扫盲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发展,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重要教育课题之一。在古典的扫盲理论中是基于下述两个原理论述扫盲的价值的。其一是道德伦理原理——“扫盲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其二是社会发展原理——“扫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事实上,联合国自1945年创办以来,就是以这两个原理为指导理念的。这些本质性原理超越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是世界各国共通的、普遍的理论依据;是决定扫盲的教育政策及教育目标、内容的基本前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原理又是在多种多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解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各不相同的。这就造成了扫盲教育政策乃至教育目标的各具特色的差异。这个事实表明,“扫盲”的涵义只有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才能界定。社会、个人的需求变化了,其涵义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在国际教育界,晚近关于扫盲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大体可作如下分类:
第一,关于读写能力的研究。这是以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为中心展开的科际性研究,是关于识字的过程,读—说—写之间的关系,促进扫盲的环境、扫盲教学法等等的研究。
第二,扫盲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研究。在不同社会中扫盲是如何社会化的,如何比较文字文化与无文字文化,如何认识社会的扫盲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扫盲具有何等意义等等问题的研究。
第三,关于扫盲与技术关系的研究。在技术革新中社会所需要的功能性扫盲的涵义在不断变化,如何因应这种变化,机械的信息处理方式是如何影响人的思维,是否存在促进人的创造活动的技术学运用方法等等。
在这个背景下,“新扫盲论”(New Literacy)出现了。正如“新思维”(New Thinking)、“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之类的术语加上了“新”(New)给人以一种变革世界政治的框架和优先课题的印象那样,“新扫盲论”也有同样的鲜明性与刷新性。“新扫盲论”者围绕扫盲的价值、目标、范畴、程度的问题展开了种种的讨论,一般可以从下列五个论点加以琢磨:[2]
1.作为“双基”或“三基”的“基础性扫盲”。以“读写”或“读写算”作为最低限度的基本素养乃是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的。一般认为,“读写算”是构成今日扫盲教育的核心要素。
2.作为读写与一般知识、能力之统合的“功能性扫盲”。格雷贝尔斯基(O.Grebelsky)认为,这种扫盲涵括下列要项:(1)同日常生活上的知识、能力之统合;(2)同经济、社会发展手段、专门技术之统合;(3)相当于初等教育课程之学习的总体。
3.作为意识化的扫盲。这是弗雷勒(P.Freire)倡导的理论。主要着眼于不能读写者批判性地内省化,并且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状况加以变革的“自我教育力”。
4.作为高级认知特性的扫盲。所谓“高级认知特性”包括:(1)意义的理解;(2)语言的符号化;(3)图式的利用。这里的“图式”意指记忆所积累的知识的结构。(4)读解能力的理解与应用(元认知)。
5.社会背景中专门化的扫盲。构成扫盲的内容可以从特定社会生活中的特殊能力、知识这一视点加以界定。其概念正在扩充、深化。诸如科技性(含数学)扫盲、文化性(批判性)扫盲、经济性扫盲。而文化性扫盲又可分为三个范畴:功能性扫盲、文化性扫盲、批判性扫盲。这意味着,扫盲不仅在于“读语词”,而且还是一种“读世界”的努力。扫盲影响到个人如何理解世界。
由上可见,扫盲的目标、内容、范畴具有层级性。从最低水准的读写算基础,在能力、知识、态度、价值观的种种维度上,朝高级方向发展。这样,作为扫盲教育也可以划分为种种的阶段,例如,罗宾逊(A.H.Robinson)就把扫盲分成了这样五个阶段:完全文盲→低水准扫盲→局部性扫盲→可变性扫盲→完全扫盲。[3]
“新扫盲论”对传统的功能主义识字观持批判态度。“扫盲”(Iiteracy)这一术语系美国一家教育杂志于1883年率先提出的。原指“通过公共教育培养读写能力”。自那时以来,“扫盲”就是指“通过学校教育培养读写能力,并借助标准化的读写测验可以测得者”。近年来,脱盲与否,往往专门用五年级、八年级(初二)水准的阅读能力为基准加以衡量。随着信息化、国际化的进展,人际沟通愈益依存于文字以外的媒体,而且,从事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知识与信息处理能力也愈益多样。亦即扫盲的功能性要件扩大了对象并提高了要求。这样,“扫盲”概念的涵义是多方面的。诸如“信息扫盲”——信息社会中所要求的正确理解、判断并活用信息的能力;“电脑扫盲”——运用电脑的能力,乃至“乐曲扫盲”——读谱力、节律感;“视频信息扫盲”——从图像把握信息的能力;“公民扫盲”——人文素养以及多元文化理解力等等。这样,“新扫盲论”不同于传统的功能主义的识字观。它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哲学:从学习者的角度,把“读写”的涵义作为“自我发现、自我表现、人际关系的扩大”这一意义上加以重构了。[4]
二、国际通行的扫盲概念——功能性扫盲与扫盲教育政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倡导扫盲的先驱性概念的主导作用。现在,国际通行的旨在用于教育统计的“扫盲”的操作性定义,是1978年第20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通过的:[5]
●文盲(illiteracy):不能理解有关日常生活的简短文章且不能读写。
●扫盲(literacy):理解有关日常生活的简短文章并能读写。
●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不能从事其所属集团及社会需要读写能力的一切活动。
●功能性扫盲(functiona literacy):能从事所属集团及社会需要的读写能力的一切活动。
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手开展实验性世界扫盲计划(EWLP),率先推出了“功能性扫盲”的新概念,并在1965年伊朗德黑兰召开的“世界教育部长扫盲大会”上获得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8年)认为,“扫盲”的概念不应作过分狭窄的理解。不应限于读写的教学,还应包括专门性、技术性知识。这样才能促进成人更积极地参与公民生活。“功能性扫盲”不仅同基本的一般知识有关,而且应同职业训练、提高生产力、更积极地参与公民生活、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联系起来”。[6]显然,这个定义的特点是,主要限于职业能力的改善与一般职业指向的教育内容。支撑这种功能性扫盲计划的理论基础就是把教育视为经济投资的“人力资本论”。
不过,在整整10年后的1975年,关于实验性世界扫盲计划评价的专家会议召开,指出上述的突出技术性、经济性指向的功能性扫盲的定义仍然偏狭,并且推崇涵括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维度的一切侧面的新的“功能性扫盲”的定义。因此被称为“扫盲概念的转换期”。[7]
该会议作出的《波斯波利斯宣言》强调,这种概括化的“功能性扫盲”是“人的和谐发展及一切社会变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对比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盲状况后指出:“工业社会中的文盲状况恐怕是最困难的、多数场合是戏剧性的。在以口头交际占优势的文明中,文盲者不感到同周围环境的隔阂。而在技术发达的世界里,以书面语言的交际为前提,不能读解书写符号的人比之能读写的人,必然地处于劣势地位。当处理数字时,他们更加陷于窘迫的困境”。[9]尤其在发达国家,文盲概念从理论上说,作为传统定义的一般文盲,同意味着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读写算水准的功能性文盲,是不同的两种类型。“功能性扫盲”的范围与界限依存于国家的发展水准、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国家经济基础部门的复杂性。在一些国家里一般状况下被视为“功能性识字”的人,在另一些国家里也许被视为“功能性文盲”。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功能性扫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显示出愈益扩充的倾向。这是客观的、普遍的、历史的法则。莱文(K.Levine)指出,“应当改变视扫盲为某种统一的能力的观点。它是由多种层级构成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也必须作出总体的概括,把扫盲视为书面信息的获得与交换的熟练能力”。这样,对“功能性扫盲”可以作出概括的界定,这就是:“伴随读写的信息处理所必须的能力与信息的获得或对信息的存取所必须的能力”。[10]
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旨在教育资源的均等普及的“全民教育”的构想。接着,1990年在泰国的宗迪恩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全”,推广了“全民教育”的概念。这个概念提示了从现实出发作出的发展基础教育、完全普及初等教育及扫除成人文盲的统一的行动纲领。[11]
“新扫盲论”表明,在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各自的扫盲教育的任务。大体说来,发达国家的扫盲教育政策可列述如下三项内容:[12]⒈社会福利——旨在帮助不能读写的人在劳动市场获得更好的职位。⒉培育可雇用的公民——旨在培养可供雇用的、负责任的公民。⒊实用主义训练——旨在训练公民的意识、需求、资金导向一类的实用训练。发展中国家的扫盲教育政策同样不仅在于单纯地训练识字能力,而且以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为终级目标,扫盲被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一种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扫盲教育目的有其共同点,这就是以非就学的青壮年及未授完初等教育者为对象的识字能力、知识的教育为第一目标;追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第二目标;个人、集体、社会文化的发展是第三目标。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的扫盲计划的主要特点,开始侧重于读写算的基础性内容的要求,然后扩展为功能性内容的要求。[13]
三、世界扫盲运动与我国成人教育面临的课题
使国民掌握生活上基本的读写能力的教育谓之“扫盲教育”。这种教育不管学校内外,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也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当今世界,不能读写的文盲广泛存在。据国际统计资料,由于各国扫盲运动的进展,世界的文盲率从1970年代的32%下降为1985年的27.7%。但伴随人口的爆炸性增加,文盲的增长趋势依然不变。10年后的1995年全球文盲达9.6千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14]文盲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极为严重。另方面,发达国家的文盲问题也层出不穷,学校毕业后无法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功能性文盲”成为亟待克服的问题。美国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国家不仅每年有大量的高中辍学者,还有合法移民、非法移民、流亡者,都是构成文盲大军的基本成员。美国的“功能性文盲”占了美国人口总数的13%。[15]因此自1983年以来不得不开始了国家规模的扫盲运动。而联合国以1990年“国际扫盲年”为契机开展的扫盲运动则是国际教育界致力于扫盲的又一个明证。
列宁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6]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扫盲运动当作重要的国策实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展开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战后新中国的扫盲运动,都是世界扫盲运动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扫盲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17]从1949年至1991年的42年间,我国共计扫盲1.75亿人,使全国总人口的文盲率从80%以上下降到约15.88%。[18]我国扫盲运动的成就受到国际教育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四川省巴中县、吉林省、山东省五莲县、湖南省妇联、宁夏,分别获得“野间扫盲奖”、“野间扫盲荣誉奖”、“克鲁普斯卡娅扫盲奖”、“野间教育荣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扫盲表扬奖”。[19]不过,由于我国人口绝对数的增长,目前尚有青壮年文盲3500万。1995年6月6日,团中央、全国学联在北京市宣布“中国大中学生志愿者扫盲与科技文化服务行动”,已从当年暑假开始组织实施。一个全国规模的包括“功能性扫盲”在内的新的扫盲高潮已经到来。
我国扫盲运动面临两个严峻课题。
首先,我国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性文盲”的扫除任务尚待进一步落实。我国“个人脱盲标准”及“基本扫盲单位的标准”几经修订。“基础性扫盲”的个人脱盲标准是1953年11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制定的。它规定:“干部、工人一般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写200-300个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为认。识1000个常用字(1956年农民的识字量由1000字提高到1500字),大体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城市劳动人民应认识1500个常用字,阅读写作参照工人农民标准。”[20]
其次,针对我国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需求,需要把“功能性扫盲”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理应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应当说,上海市业已实施的以全民性、非营利性、自发性为其特征的“计算机等级考试”、“市民外语等级考试”,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的构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功能性扫盲”的时代要求,是值得称道的。不过,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市有必要也有可能制订并实施超越了诸如“90年代紧缺人才工程”的更为宏大的全方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素质的功能性扫盲计划。为此,就得展开“功能性文盲”问题的专题研究,从国际视野和国际大都市的要求的高度,明确“功能性扫盲”的概念,编制“功能性扫盲”的规划,设定“功能性扫盲”的标准及其课程,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又一个挑战。可以说,填补“功能性扫盲”教育的空白,已经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注释:
[1]卡塞勒斯(G.Carceles,1990)《世纪之交世界扫盲教育展望:到2000年实现全民扫盲的目标在统计上有可能吗》,载《比较教育评论》Vol,34,No,1,第4-20页。
[2]瓦格纳(D.A.Wagner,1990)《扫盲教育与研究:过去、现在、未来》,载《扫盲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3]罗宾逊(A.H.Robinson,1996)《为处境不利地位的成人提供基础教育》,载《理论与实践》,波士顿。
[4]阿普尔(M.W.Apple)、长尾彰夫、池田宽编(1993)《对学校文化的挑战》日本东信堂,第143页。
[5][9]中山玄三(1993)《扫盲教育》近代文艺社,第85-86页,第120页。
[6]林德(A.Lind)、约翰斯顿(A.Johnston)(1990):《第三世界国家的成人教育:对目标的回顾与策略》,瑞士国际发展局,斯德哥尔摩。
[7]巴塔依(L.Bataille,1976)《扫盲的转折点》,牛津大学出版社。
[8]查尔斯.赫梅尔(1983)《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王静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56页。
[10]莱文(K.Levine,1986)《文盲与非文盲的界定及其测量,扫盲的社会情境》伦敦罗特雷杰与凯根普出版社。
[11]世界全民教育大会(WCEFA,1990)《满足基本学习需求论:90年代新视野》,世界全民教育大会背景资料。
[12]利马格(L.Limage,1989)《欧洲与北美的成人扫盲教育与基础教育:从认识到行动》,选送第7届比较教育会议论文,蒙特利尔。
[13]格雷哈特(H.P.Gerhardt,1989)《为什么而扫盲:多元文化态度》,《展望》Vol,21No.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4]参见联合国人口基金1995年7月11日发表的《世界人口白皮书》。
[15][17][19][20]顾明远主编(1991)《教育大辞典》(卷3)第355、354、358、35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6]列宁(1920)《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选集》(1960)(卷4)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8]何东昌主编(1996)《当代中国教育》(上卷)第62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标签:新挑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