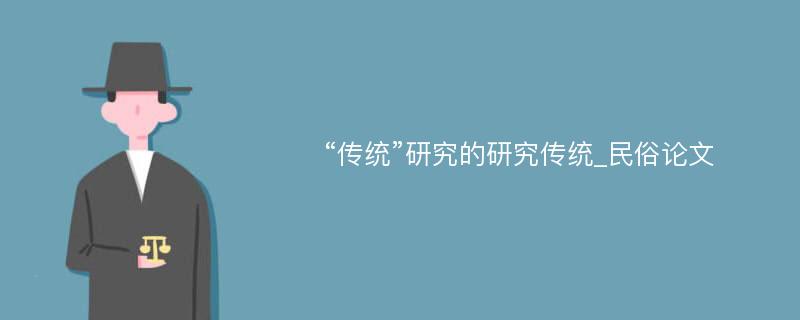
“传统”研究的研究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是民俗学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很久以来,“传统”只是民俗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民俗学的分析对象。民俗学借用“传统”来思考问题,却从来没有思考过“传统”这一问题。直到1983年,艾里克·霍布斯鲍姆与特里斯·兰格主编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出版以后,民俗学对于“传统”这一术语的质疑与反思才全面展开。
当然,“传统”并不是民俗学专有的分析工具,它也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核心词汇。在这两门学科当中,“传统”也是被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分析性“术语”而应用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思想的谱系当中。比如,在人类学当中,一条贯穿始终的研究理念是“我们”(欧洲人)对“他者”(欧洲之外的族群)的研究;在社会学当中,爱弥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麦克斯·韦伯、费迪南德·滕尼斯等都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一种是非工业的、强调不变的传统与集体规则的、面对面地交流的、亲近自然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自然地存在的,无反思性的,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灭亡听之任之;另一种是理性的、强调变迁的、重视契约关系的“现代社会”,这是一种被发明的社会,其中充斥着被发明的文化①。在不成文的学科定位当中,人类学研究“传统社会”,而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无论是作为理想的类型还是经验的概括,都是为了理解“现代社会”而存在的②。
20世纪下半叶,上述二元对立的社会理论模型受到了质疑。然而,即使如此,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在人类学界仍然十分流行。即使社会变迁已经发生了,但是,人类学家们仍然习惯性地去记录与研究“传统的形式”,固执地要研究原始的、本真的“传统”(比如本土的亲属关系、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对于“传统社会”中发生的变迁却视若无睹。这种研究理念无意之间与地方统治者及势力群体达成了合谋的关系,从理论上界定并强化了后者作为“传统的权威”的权力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类学家很少去反思“传统”这一概念在其学科当中的核心性与复杂性。
民俗学也关注“传统”,尤其是“口头传统”。区别于人类学的是,民俗学关注的是西方普通民众,而不是非西方的土著人。与人类学一样,民俗学也建构了“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民俗学的早期阶段,它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关注大众的遗留物的。然而,“较之人类学与社会学,民俗学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更加深重,更难看到现代生活中不断增长的理性以及传统社会的衰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理念使得民俗学家更难发现文化的转变与文化形成的混杂性”③。目前,绝大部分职业民俗学家们已经放弃了单线进化论的思想,但是,“传统”仍然是民俗学家界定自我学科认同的核心词汇。
“传统”的本质
既然民俗学是对“传统”的研究,是“传统”的科学,那么,在民俗学当中,“传统”指的是什么?换言之,“传统”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这里先从词典中关于“传统”的定义说起。在这些词典当中,“传统”的定义分别是:
一套信仰、习俗或者行为方式,它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当中存在了很长时间。(《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传承下来的言论、信仰或者代代相承的实践。(《牛津英语词典》)
在进化的社会态度、信仰、习俗与机制的巨大综合体中的文化连续性,它扎根于过去的经验,并对当下施加某种指导性的与指派性的影响。(《韦伯第三新国际词典》)
在上述定义当中,“传统”既指特定的信仰、习俗或者行为方式的“内容”本身,也指这些“内容”的传承“过程”。
然而,1846年,在W·J·汤普森提出“民俗”这一个术语的时候,他指的是“大众的古物”与“大众的文学”。在欧洲大陆的民俗学传统当中,民俗指的是“幸存物”或者“遗留物”。美国民俗学更新了欧洲“民俗”的意义,指向了“口头传统”。在北欧,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俗”仍然主要指的是“散文传统”。由此可见,在民俗学早期的观念当中,“传统”停留在过去,是一些古代的遗存,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无可避免其渐渐消亡的命运。因此,历久以来,民俗学似乎等同于“搜集”民俗古物的工作,其中暗含着“保护”的意思。这里所谓“搜集民俗”,显然指向了民俗传统的“内容”本身④。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雅克布·乔瑟菲(Jacobs Joseph)已经强调了“民俗”的社会的、心理的维度,既重视民俗的个体性特征,又重视其群体性特征;既强调民俗的时间的维度,又强调其空间的维度。他看到了“民俗”的传承的问题、文化的多层次性的问题,否定了文明的单线进化论。在他的观念当中,民俗的保存与传播方式以及内容本身都是“传统”,民俗学即是“传统”的科学,具体言之:
(1)民俗是连续地被更新与发明的,因此,民俗必然是不断更新的,为个体所模仿的。
(2)民众并不是社会的一个阶层,而是共享传统的一个群体,它可以属于任何阶层。
(3)传统并不是一个知识体。按照空间的与心理的模式,传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⑤
在雅克布·乔瑟菲看来,民俗与个体的需要、社会情境相关,于是民俗便摆脱了文化幸存主义理论的种族主义特征。在他的观念当中,传统既是被挑选的,也是被追随的;既是被创造的,也是承自往昔的。遗憾的是,雅克布·乔瑟菲的观点并没有引起民俗学家们足够的重视。
总之,在20世纪中期之前的民俗学传统当中,“传统”既指传承的“过程”,尤其是口头传承,又指传承的“内容”。由于受了科学主义研究思潮的挟持,传统的民俗学竭力要表现出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姿态,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传统在情感、学术、道德、政治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含义,片面地强调了“传统”的“内容”的固定性,而忽视了其“过程”当中复杂的“意义”生产。
介于“内容”与“过程”的观念之间,北欧民俗学家提出了作为“资源”的“传统”的概念。1981年,在第22届北欧民族学与民俗学大会上,他们提出了“传统”的三种定义:
(1)传统是在一个传承的、连续的过程中传递下来的某种东西。
(2)传统是文化被制造的原材料,它们被保存在民俗档案馆里。
(3)传统作为定性的标志,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表征(可能会基于社会成员的选择)。
在北欧学者的观念当中,传统既可以是祖先传下来的,也可以是从外界移入的。这些材料可能被贴上“传统”的标签,被相信传播了很久很久。因此,他们认为,对于“传统”应该采用宽泛的定义,应该包括特定群体过去与现在可资利用的所有材料。这样看来,“‘传统’就像一个仓库,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段,人们会利用某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等着被激活或者渐渐地被遗忘。这个仓库,不应该被描述为一个体系,其边界因进出这个群体的个体而变化,换言之,传统意味着潜力与资源,而非具体的、真实的文化”⑥。
然而,社会学家爱德华·西尔斯更强调“传统”作为“权威”的含义。他说,“在其纯粹的、最基本的意义上……传统……是从过去传承到现在的东西”,“传统被想当然地接受为唯一值得去做或者相信的合理的事情”⑦。也就是说,当人们声称某种知识是“传统”时,他不仅意味着这是一种集体的知识,也是群体的文化经典,同时意味着它是群体身体“认同”感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个体行为的文化“模式”⑧。
上述所有关于“传统”的本质的观点,都是从静态的观点出发论述的,它没有从“个体与传统”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传统”在静态的理论当中被固定化了,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方式。然而,这个所谓的“传统”是谁的“传统”呢?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传统”会持有相同的态度吗?⑨事实上,当人们说某种东西是“传统”时,更多地可能是一种“修辞”而不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受到了质疑。
“传统”的裂变
欧美社会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大规模扩张,引发了过去半个世纪当中全球范围内戏剧性的社会变迁,欧美民俗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不断变迁的过程当中,人们的传统与民俗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⑩比如,大型的音乐制作公司把某一特定的地方音乐包装加工之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甚至返回到其初始音乐的故乡时,哪个才是“传统”?对谁来说是“传统”?又比如,民俗学家们竭力要“搜集与保存”民俗传统,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搜集来的民俗材料“文本化”,然而存放在档案馆里,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些民俗传统仍将在它们生存的空间里被当地民众创造性地使用,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传统”呢?尤其是,当国际性的组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文化部门、地方群体与个人等参与搜集民俗传统时,谁来界定什么是“传统”,搜集哪些“传统”,排斥哪些“传统”等等问题使得关于“传统”的概念进一步复杂化了。总之,“传统”在面对政治行为、商业行为、学术行为时是如何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的呢?
面对上述现象,民俗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区分性的概念:
第一,“时间中的传统”与“空间中的传统”。前者指向了“本真的传统”的代代相承;后者指向了该传统在面对大众文化时,为广大地域中不同群体所接纳与实践的现实。这一区分提出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传统”还有“民众”的品质吗?还与“时间的延续”相关吗?(11)
第二,“本真的传统”与“民俗主义(Folklorismus)”或者“伪民俗(Fakelore)”。“本真的传统”认为“传统”具有固定不变的内核,这是民俗学的传统观念;“伪造传统”的思想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彼得·海因兹于1958年提出来的,后来,德国民俗学家汉斯·墨瑟尔于1962年进一步提出了“民俗主义”的概念(12)。在汉斯的分析当中,“民俗主义”至少具有三种类型:
(1)民间文化在其初始的地方语境之外表演。
(2)另一个社会阶层对大众母题的戏仿。
(3)出于不同目的,外在于任何已知的传统,特定的民俗被发明与创造。(13)
汉斯·墨瑟尔发现,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其民俗档案馆、民族旅游景点、民俗节日中到处充斥着被发明的民俗,尽管它们发明民俗与传统的意图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正是社会当中的上层阶级首先培育了“民俗主义”。理查德·道森稍后也提出了“伪民俗”这一概念(14),但是,与德国的民俗学者们不同,道森的概念显然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
第三,“死的传统”与“活的传统”。芬兰民俗学家培卡·拉卡森认为,那些储存在民俗档案馆里,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灭亡的、等候可能会有的回收利用与复兴的民俗材料可称之为“死的传统”;而“活的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活的、消极的传统”,他们储存在民众的记忆当中,但很不活跃,只能在特定的语境当中才可能被激活;另一种是“活的、积极的传统”,它们仍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被表演与交流,人们很难把它们跟大众文化、媒介知识、“半文学”的现象区分开来。拉卡森显然应用了瑞典民俗学家卡尔·威尔海姆·翁·西多关于“积极/消极的民俗”的理论遗产,但是,他的划分仅仅具有分类学的意义。
第四,民俗的“第一生命”与“第二生命”。劳里·杭柯把特定社区当中自然的、未受关注的民俗的存在视为民俗的“第一生命”;而随着对“传统”、社会与文化“认同”的意识的增长,民俗被搜集、记录、档案化、分析、编辑、出版,这就成为了民俗的“第二生命”。它们脱离了所属群体与特有的存在语境,对不属于其群体的其他人产生了影响。民俗旅游、民俗节日、民俗成为学校教育的素材、民间艺术成为高雅艺术的源泉等都属于民俗的“第二生命”。(15)
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则认为,民俗的第一生命与第二生命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它们不能被截然割裂开来,尽管有商业化与大众传媒的影响,民俗学家还是应该研究这一转变的过程及其功能。况且,民俗学家自身生产的民俗知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本真的民俗”与“民俗主义”对立起来,不可避免地会生产出更多的“民俗主义”。
第五,“民俗主义”与“今天的民俗”。匈牙利民俗学家威尔姆斯·威尔格特认为,“民俗主义”,确切地是指民俗现象在非民俗当中的传播。“民俗主义”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民俗”这一概念。但是,当调查了“旧有的”民俗在当今时代的遗存,人们就可以比较并清楚地区分“民俗主义”现象与民俗的“新”形式了。
此外,威尔姆斯·威尔格特认为,如果我们把“遗存”视为“今天的民俗”的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从事研究:第一,我们可以调查不变的遗存性因素(姓名学、神职体系、婚礼与丧礼中的仪式性的歌谣);第二,这些遗存性因素虽然继承下来了,但经验了相当大的功能性转变(节假习俗)。第三,“新的”现象(旅游主义、看电视、活动住房、私人博物馆与收藏、地方编年史与地方史俱乐部的活动等等)。因此,在他看来,广义的“今天的民俗”指的是任何口头的、非正式的、即兴的公共活动;而狭义的民俗指的是农民或工人的遗存的传统,即有迹可寻的民俗遗存。“渐变与转型”两种形式在民俗传统的存在过程中同时存在,需要民俗学家们仔细地予以区分。(16)
不难发现,民俗学家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的强调与排斥,显然涉及到了把乡村的民俗传统与象征“再情境化”到都市语境中的过程,这与20世纪“乡村与都市”间的互动有密切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一方面是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涌向农村寻找“失乐园”的潮流。正是频繁的社会流动与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民俗文化的剧变。
然而,显然,“民俗主义”并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既然如此,民俗学家似乎没有理由去鄙视“民俗主义”,相反,民俗学的任务似乎应该是发现“民俗主义”对于不同参与者的心理功能。正如赫尔曼·鲍辛格与林达·戴格所宣称的那样:“民俗与民俗主义经常是相互补充,相互交叠的;一个时代的民俗主义即是另一个时代的民俗。反之亦然。”“民俗总是被操纵的,民俗主义就是民俗,民俗自身携带了民俗主义的种子”(17)。关于“民俗主义”的讨论促使民俗学从“本质主义”的观念转向了“建构主义”的观念。
传统的建构
自《传统的发明》出版以来,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在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领域广泛流行着“建构主义”的思潮,“传统”不再被视为具有内在规定性与固定本质的“内容”,而是被视为一种“建构”(18)。在民俗学的建构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传统与民俗(包括“民俗主义”)都是以某种方式被建构的,虽然并非所有的建构行为都是有意为之的。当然,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乡村的民众,他们都不可能整体地“发明”传统的,他们只是连续不断地修正着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习俗的整体,并不是自在地存在于“那里”等待被发现的;“传统”是一种先在的模型,一方面形构着个体与群体的经验,另一方面又被个体与群体的经验所形构。“正如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说的那样,‘传统’具有反思的、连续地自我修正的本质,它是一种‘辩证的发明’。”(19)
民俗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民俗学界的常识,民俗被用于“民族一国家”的建构是民俗学关注的焦点。正如人类学家罗勃特·雷德菲尔德所告诫的那样,文明的特征最好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理解;结合艾里克·霍布斯鲍姆与特里斯·兰格对于“被发明的传统”(它们与过去的连续性是人为的)与“本真的传统”(古老的方式仍然存在,它们既不需要复活,也不需要被发明)的区分,以及对于“传统”(其目标与特征在于不变性)与“习俗”(并不排斥变革)的区分(20),可以更好地理解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目的而展开的民俗搜集运动。选择搜集哪些材料是由外在于民俗所在社区的群体或者个人决定的。正如斯图尔特·霍尔说所的那样,“在每一个时期,文化过程都涉及什么被纳入大传统,什么不被纳入的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料库,起着复制群体之间差异的功能,主导群体决定哪些东西是优秀的,值得保存与提炼的。特定民族的民族志项目与民族的建构相关,因为它意味着把差异化为统一,其表面的差异服务于标志潜在的统一”(21)。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的搜集与整理活动,显然是一种诗学与政治学的行为(22)。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一种文化——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但是,大部分人很难说清楚构成这种“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特征,正是民俗学家们发明了“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与遗产”。
同样,民俗传统还渐渐地被表征于地理位置当中,被用来激发思乡的情绪,被当作民间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民俗旅游作为民族国家展览的一种现代形式,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传统与遗产的政治对于理解各种社会群体、地方精英、国家机构之间关于“传统”的话语权的竞争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过程当中,历史学与民俗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是生产关于过去的知识的一种手段;遗产则是对那种知识的消费,“历史”与“遗产—传统”之间关系密切,通过“遗产—传统”,学者(作为有意义的过去的生产者)与遗产专家(作为传统的守护人)的合法性被建立起来了。除了学者与遗产守护者之外,普通民众也会参与到关于“传统—遗产”的话语生产活动当中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当中被不同的群体所建构与发明;在单一社会当中,‘传统’也可以以多种方式被表征。因此,传统不只是被‘发明’,也是被积极地竞争着的”(23)。在面向外来者的民俗旅游当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24)。
就“传统与个体”(25)之间的关系而言,正如亨利·格拉西所说“文化与传统是被有知识的个体所创造与发明的”(26)。这一论断所引出的问题是关于“传统”的本体论位置的三种可能性:
(1)传统是由社会当中的个体建构的。
(2)传统是由民俗学家建构的。
(3)在建构的行为之外,传统具有某些本真的特征存在。
显然,“传统”既意味着某些共享的、可反复展演的内容;也意味着与展演语境相关的精神、时空设置以及特定情绪。反言之,“在特定的社会互动之外,不存在所谓的传统歌谣,正是特定的社会互动关系,使它成为传统的”(27)。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讨论“个体与传统”的关系时,实验的民族志竭力倡导要创造一种新型的民族志文本,它要求把民俗的实践者与研究者的概念纳入一个共享的观念当中,这是一种“合作的民族志”,要求民俗学者不断地反思研究者的立场;对阐释的合法性予以澄清;并提供关于共享的理解的知识基础。“合作的民族志”是对传统的经验主义民俗学的突破,它质疑了研究者感官判断的权威性,反思了民俗传统可以被观察、可以被搜集、可以被记录的学科传统理念。事实上,在现代民俗学者看来,“民众知识专家(Folk-lorist)”所生产的所谓科学的知识,冷冰冰、硬邦邦,既不精确也不完整,与民众观念当中对于“传统”的理解相去甚远。“在实践的语境当中,‘传统’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逻辑的构成,而在于具体的含义。传统植根于特定的社区当中,植根于当下有意义的个人关系的网络当中”(28)。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存在于“表演”与“实践”当中,外在于“表演”与“实践”无所谓“传统”。
在“民族主义”、“民俗遗产”、“表演实践”的现象当中,民俗传统只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而不可能是民俗学家所宣称的“保护”的工作。“首先,那些被选中用以表征传统文化的元素被反复地‘去/再情境化’,最终被置于与其初始语境完全不同的情境当中;其次,这些被‘再情境化’的传统元素,对于研究者、手工艺人、舞蹈家、讲述者、表演者、观众、消费者以及一切参与民俗活动的人具有全新的意义,被重构、重新阐释为‘传统’,它们意味着民族认同。其本来的携带者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意识。第三,传统的发明是有选择性的,只有某些内容可以被选中代表传统的民族文化,其他的方面却被忽视与遗忘了”(29)。总之,被保留下来的“传统”是出于当时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家公开讨论“保护传统”的行为本身即是在“发明传统”。
“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矛盾之一是,文化保护不可避免地会改变、重构、发明其意在固定下来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无所谓“本真的”与“虚假的”,真与假的判断,只不过特定个体或者群体在特定社会立场之上的一种阐释。
正如西蒙·布鲁恩所说的那样,“传统既是可经验性地记录的文本,也是处于意识之外的笼统的力量、模式或者权威”(30)。“传统”存在于特定时空当中个体行为者的活动当中,这是“历史、权力、文化”相遇的地方。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当中,个人与群体关于“传统”的话语是其重要的象征性资本。声称拥护或者占有某种“传统”,就意味着与“过去”建立了联系,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权威感,意味占有了一种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在普通民众的话语当中,“传统”是一种指向过去的、统一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行为方式,“传统”本身具有“价值”的含义。传统主义者倾向于尊崇“传统”,而进步主义者大抵会抵制“传统”,但是,把这两种倾向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持任何一种社会立场的个体都会借助“传统”的资源进行社会互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学科的危机与反思之后,欧美民俗学并没有抛弃“传统”这一术语,而是对它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新的定义当中,“‘传统’成为大众文化的替代物。由于民俗学家总是对‘过去’十分敏感并总是习惯于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民俗学把学科的关注点从传统与习俗的连续性的考察转向了对共同体与认同的未来指向的‘动态关系’的考察”(31)。“实践”与“表演”指向的民俗学考察的是民俗与传统的呈现中的、动态的、创造性的过程,“传统”的“指导性”以及“传播性”的问题被有意地忽略了。在一个“建构主义”思潮横扫学界的时代,这种研究的范式正在引起民俗学家进一步的反思与讨论(32)。
注释:
①Jukka Siikala,Those Who Know:the Tumu Korero of the Cook Islands,FF Network,2009,p.5.
②安东尼·佩勒蒂认为:“没有现代媒介,现代性不可能表征非现代性,正是通过现代媒介,非现代的表征才变得现代化。换言之,被视为非现代的,在非现代的现代话语当中获得其意义。既然非现代性只能作为现代的他者才可以被讨论,那么,非现代性同时也是关于现代性的话语。”(Perttti J.Anttonen,1993,p.18.)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也是一门现代性的学科,只有“透过‘现代性’才能理解‘传统’”。
③Diarmuid O Giollain,"Tradition,Modern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Dynamics of Tradition:Perspectives on Oral Poetry and Folk Belief,edited by Lotte Tarkka,Studia Fennica,Folkloristica,2003,p.38.
④正是因为民俗学家们长期以来聚精会神地投身于民俗的“搜集与保护”工作当中,才会引发民俗学学科内外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学被学术界称为“半吊子的学问”或者“资料之学”,在某些国家,比如墨西哥,民俗学甚至没有合法的学术地位可言,民俗学界内部也因为缺乏“宏大的理论”而产生了普遍的学科危机感,从而迫使民俗学进入了反思的时代。相关论述可参看Kirshenblatt-Gimblett,Barbara."Folklore's Crisi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1,1998,p.281~327; Alan Dundes,"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8(470),AFS Invited Presidential Plenary Address,2004,pp.385~408.
⑤Jacobs,Joseph,"The Folk",Folk-Lore 4,1893,p.237.
⑥Lauri Honko,"Study on Tradi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Tradi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by Lauri Honko,Turku,Finland: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1988,p.10.
⑦Shils,Edward,Tra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3.
⑧Ben-Amos,Dan,"The Seven Strands of Tradition:Varieties in Its Meaning in American Folklore Studies".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1,1984,pp.97~131.丹·本-阿默斯的经典论文《传统的七条路径》总结了民俗学领域关于“传统”的七种观点,它们分别是“传统”作为“知识、经典、过程、资源库、文化、语言与表演”。本文以为,作为“资料库”的“传统”,内在地包括了作为“文化”与“语言”的意含。“传统”作为“表演”的观点在正文当中另有论述。关于丹·本-阿默斯的评论,参见Alan Gailey,"The Nature of Tradition",Folklore 100,1989,pp.143~161.
⑨Finnegan Ruth,"Tradition,But What Tradition,and For Whom?",Oral Tradition,6,1991,p.114.
⑩相关著作有Singer Milton,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s ,New York:Praeger,1972; Hermann Bausinger,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translated by Elke Dettm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 and Indianapolis,1990.鲍辛格早于《传统的发明》的作者艾里克·霍布斯鲍姆与特里斯·兰格提出,传统并不是一个文化给定的东西,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
(11)正如丹·本-阿默斯给“民俗”所下的定义,“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流”。这就意味着“民俗”可以是非传统的。“时间性”成了民俗学的沉重的包袱,它使得民俗学无法延伸到大众文化的研究当中,同时,它也与民俗学自身的存在前提相违背。
(12)威尔姆斯·威尔格特认为,“民俗主义”这一术语最早起源于法国学者保罗·西比里特(Paul Sebillot)。
(13)转引自Venetia J.Newall "The Adaptation of Folklore and Tradition(Folklorismus)",Folklore 98:1987,p.136.
(14)Dorson,Richard M,Folklore and Fakelore:Essays Toward a Discipline of Folk Stud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5)Lauri Honko,Possibilit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Safeguarding of Folklore,NIF,Vol 15(1),1987,pp.7~8.
(16)Vilmos Voigt,Today's Folklore:A Review in Contemporary Folklore and Culture Change,Edited by Irma-Riitta Jarvinen,Lansi-Savo Oy,Mikkeli,1986,pp.17~32.
(17)转引自Venetia J.Newall,"The Adaptation of Folklore and Tradition(Folklorismus)",Folklore 98,1987,p.147.简单地把新的民俗现象斥之为“伪民俗”或者“民俗主义”显然太简单化了,纵然民俗学家视之为伪造,但是,民众群体可能十分认同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俗学家有义务去研究这些“传统化”的行为。
(18)《传统的发明》中“发明”这一词汇显然不如“建构”一词更恰当,因为“建构”意味着一个更长久的、连续的、创造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当中,“传统的建构”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的过程,是“传统”的施行者与观察者互动性地建构的过程。
(19)Jocelyn S.Linnekin,"Defining Tradition:Variations on the Hawaiian Identity",American Ethnologist 10,1983,p.241.在作者的观念当中,所谓“传统”,就是一个挑选的过程,过去的内容被按照一种现代的意义予以修正与重新定义。传统是流动的,其内容是被每一代人定义的,其“无时间性”可以被情境化地建构。过去与现在时间与空间在这一概念当中倒塌了。
(20)Ronald L.Baker,"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in Folklore and Literature",Western Folklore 59,2000,p.107.这与民俗学家的观点不同,民俗学家认为,习俗是传统的,而传统一定是动态的。
(21)Hall,Stuart,"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Raphael Samuel(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236.
(22)Sabine Trebinjac,"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Musical Tradition in China",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5,2004,p.221.作者在研究了中国音乐传统之后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发明总是一再被重新发明,‘传统’在中国已经被‘国家传统主义’所取代,核心的权力机关总是在创造与调适着传统。”“在中国,人人都说整理后的音乐是典型的中国音乐,但是,这种‘家族的相似’包括了中国所有的音乐传统,经过了搜集者的模塑,只是国家传统主义的一部分”。因此,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与西方人的定义不同,作者建议代之以“国家传统主义”。关于美国民俗传统形成过程的描述,可参见Richard M.Dorson,"The Shaping of Folklore Tra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Folklore 78,1967,p.161~183.理查德·道森分析了移民与殖民的历史对于美国各族群民俗传统形成的影响。
(23)Paul Sant Cassia,"Tradition,Tourism and Memory in Mah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lnstitute 5,1999,p.259.仅仅关注文化精英的行为与动机会产生一种单一维度的仪式观点,从而忽视了传统在展演的过程当中,被社会其他成员转化的观点。Simon Coleman & John Elsner,"Tradition as Play:Pilgrimage to 'England's Nazareth",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 5,2004,p.284.类似的观点可见:Anna-Leena Siikala,"Tradition,locality and multicultural processes",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FFN 12,June:5~6),1994,pp.2~4;1997,pp.5~6.
(24)Dorota C.Starzecka,Review 1976,"Traditions in Transition:Culture Contact and Material Change",by L.E.Dawson,Man,11:1976,pp.627~628.外来的旅游者的喜好修正着地方群体的认同,这种被修正的认同正在朝着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性迈进。
(25)关于“个体与传统”之间关系的民俗学文献综述,可参考:Michael Owen Jones,"'Tradition' in Identity Discourses and an Individual's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Self",Western Folklore 59,2000,pp.115~141.
(26)Glassie,Henry,"Tradition",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08:1995,pp.395~412.格拉西把“传统”等同于“表演”,认为表演者处于责任的复杂纽带当中。在谈到“领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查尔斯·约翰·艾拉斯莫斯提倡一种“文化限制论”,遗憾的是他未能对这一观点进行细致的阐述。Charles John Erasmus."The Leader vs.Tradition:A Case Study",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4,1952,pp.168~178.
(27)McDonald,Barry,"Tradition as Personal Relationship",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10(435),1997,p.61.作者认的,传统的激发可能被互动关系当中的每个部分持续地协商,这样一来,个人表达的机会与变异(尤其是内容与语境)可以被看作内在于传统的过程当中。
(28)Anne Elise Thomas,"Practicing Tradition:History and Community in an Appalachian Dance Style",Western Folklore 60,2001,p.166.
(29)Handler,Richard,and Jocelyn Linnekin,"Tradition,Genuine or Spuriou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1984.p.279.
(30)Simon J.Bronner,"The Meaning of Tradition:An Introduction",Western Folklore 59(2)2000,p.97.
(31)Simon J.Bronner,"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radition:Folklore in the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Values",Western Folklore 59,2000,p.161.
(32)The eighth 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2010),After the New Folkloristics.http://www.folklorefellows.fi/summer/ffss_20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