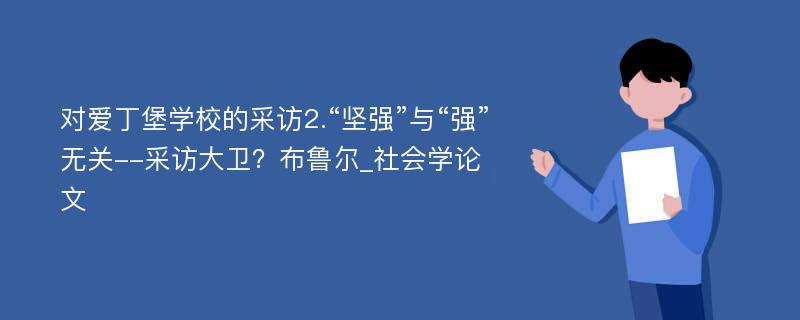
爱丁堡学派访谈录——2.“强”不强有关系——大卫#183;布鲁尔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丁堡论文,大卫论文,访谈录论文,学派论文,不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3)04-0004-09
在场人物:大卫·布鲁尔(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教授,以下简称“布”)
黄之栋(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博士,台湾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以下简称“黄”)
李正风(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李”)
缪航(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以下简称“缪”)
翻译团队:戴东源(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朱容萱(高雄餐旅大学应用英语系专案助理教授)
黄之栋(台湾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黄:我想请教关于有限论(finitism)的议题。请您为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有限论,并请告诉我们为什么它很重要?
布:首先,让我来谈一下有限论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经验论哲学家(empiricist philosophers),比如说英国的经验论者密尔(John Stuart Mill)。密尔认为,推论总是从特称(particular)到特称的。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就是有限论的核心。不过,有限论还有其他的来源。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依循(rule-following)的研究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来源。维特根斯坦展示了规则的依循是种一步步的渐进过程,而不是某种像是在已经事先决定好的预存轨道上运行的东西。赫茜(Mary Hesse)的研究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来源,特别是1974年那本《科学推论的结构》尤为重要。
如果要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有限论的基本想法的话,可以说:一个概念或一个字之前的应用并不能决定(或不能完全决定)这个概念或这个字之后的应用。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总是在问:为什么一个概念被用一种恰如其是的方式精确地应用着呢?这个概念被应用于此,也被应用于彼,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限论者会说,总是会有像这样的问题出现的,而那些分析概念应用的人(如科学史学家)就得去问这样的问题。在科学中,一个概念先前的应用与下次应用之间永远隔着各种条件、因果以及其他潜在的问题。不论这些概念是经验的概念(如“水”)、理论的概念(如“分子”),还是数学的概念(如“多面体”),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是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固定意义的东西。
以一些简单的非科学的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议题如此重要。假设某一政府与另一个政府签署了一份条约或是协定,最后却做了不符合条约内容的事情。这时缔约国会开始争论:哪些字是他们事前就同意会去做的;哪些字的意思又是在新的案例中不适用的。我最近记得有这么几个糟糕的案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美国是不“拷打”战俘的。“拷打”这个字在过去一般的应用里,是指有些人遭受到“拷”“打”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但美国政府却辩解,“拷打”这个字眼并不适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划出了新的类别与区分,然后说自己所做的只是“加强审问”而已。当然,很多其他政府也做过相同或类似的事。不过,在这个议题里,应该注意的要点是:之前“拷打”这个概念和意义几乎无法阻止现在拷打这件事情的发生。
有人可能会这么说吧,这些例子显示了人们后来的所作所为忽视或违背了他们当初处理与签署这些原则时的本来的意义。有限论的研究路径在解释像这样的案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则是更激进的。有限论者同意协定的“精神”以及该协定背后原本的涵义是可能会被违反的,但他们会进一步说,这类涵义不可能被体现在不变意义的字词或概念里。原因是,意义是无法被固定住的,意义永远是在新的局面中再次被创造出来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有限论者就得说,布什政府的谎言是可以被接受的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布什政府所作所为的强有力批判,不可能只从语言表达原则是否一致或是这些原则意义的概念论证中推导出来。
我把话题从科学岔得太开了,我得来谈谈为什么这类主题会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兴趣。我得再强调一下,有限论者“不”主张什么——有限论者不是在说科学是伴随着许多政治和交际手腕的坏信条而开展的。由这方面来看,过去我用来说明这个观点的例子或许正好都是些不幸的案例。对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而言,科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概念的变迁、调整、重新定义、重新分类以及协商等,在科学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且让我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谈谈这个问题。社会学家总是在寻找那些被称作“抉择点”的东西。每当科学家得决定要用这种还是那种方式来做事情的时候,社会学家或许也能贡献些什么,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抉择是这样的。这可以很容易从科学家考虑大型政策问题上看出来,譬如说,科学的预算应该花在基础粒子物理学研究上,还是该花在基因体学研究上呢?从中,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利益、惯例以及权力斗争可能会以某种社会学家可以阐明的方式进入到这些选择中。不过,有限论者会说,社会学的好奇心不仅是在处理像这类高层次的政策问题而已,这些问题延续到探索科学思考的细节中。事实上,同类的问题与同样的抉择出现在每次概念运用于某件事的时候,就是在这么小的范围里出现的。每次科学概念应用于具体事物时,所有概念的应用都牵扯了某种“政策”的意涵。也就是说,原则上概念的应用几乎毫无意外地会成为争论的标的。不但如此,在谈论这些隐含的政策时,原则上,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都能提出些有用的东西才是。
让我们思考下面的例子。假设某个科学家有了一个理论,然后用这个理论来预测;再假定这个预测好像是错的。这可能意谓着这个理论是错的;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也就是这个理论和理论中的概念是被以一种可以被挑战或改变的方式应用着。这个科学家或许会察觉到这么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可以调整该理论及理论中的几个概念,如此一来,理论就可以与数据相吻合了。这就是我方才所谓“抉择点”的一种——这个抉择点是物理学家迪昂(Pierre Duhem)著名的发现。迪昂证明了没有什么“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s)的存在,一个看似已经被驳倒的理论,理论上总还是能被救回来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迪昂的论证也可以被反过来操作。同样的想法显示了,一个看起来已经被驳倒的理论到最后却可能是正确的;这种想法同时却也证明了,一个看起来已经被证实的理论最后却可能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限论者会说,这类抉择是无所不在的了。在每一个概念应用的行为里,都隐然牵涉了抉择的元素,这是不同要素间互相权衡下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整个的科学知识都成为社会学感兴趣的潜在领域,这意谓着,社会学探究的某些陈旧的限制是不适当的。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声称:社会学家可以考察一些诸如大规模的科学政策决定,一旦政策决定了之后,接下来科学到底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就落在社会学所能说明的范围之外了——这些是行为中“纯粹”理性的东西,与社会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刚刚概述的论点就是为了说明,有限论揭露了哲学家的这些区分是相当不实际的。
哲学家还发展出了其他类似的论点。比如说,他们说一个概念必须得有一个定义。当然了,有些人比较喜炊这个定义,而有些人喜欢那个定义。哲学家会承认,定义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常规。不过他们会继续说,一旦科学家决定了这些概念的定义后,他们主张的真假就不再是社会的或约定成俗的问题了,有的只是这世界到底符不符合这些定义的问题——约定的常规、相对性及社会的关联性此时就不再扮演什么重大的角色了,这是哲学里非常普遍的态度。有限论者想尝试扭转这种立场,他们称,约定性或相对性的概念不只适用于论证一开始被赋予定义时那个知识的初始阶段而已。对于有限论者而言,没有人能经由决定或定义而固定住意义。可能发生的概念应用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且在在皆是,所以哲学家试图限制社会和常规的角色范围,是一种误导。
总而言之,有限论是一种关于意义的思考方式,它让那些社会学家研究且阐明的东西鲜明了起来;有限论是一种论证方式,可以用以反击许多设法使社会的角色尽可能地受限并隐形起来的哲学家。我觉得,有限论是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它引出了诸多关于知识和意义本质的深切问题。许多关于科学的讨论之所以仍停留在很肤浅的阶段,就是因为人们还没能充分思考意义和概念应用的本质。
还有一个维度是我还未提及的——为什么有限论会被叫做“有限论”呢?这牵涉到意义是如何被习得的。有限论者称,所有意义最终都是通过指出实例来学习、传播或沟通的。当孩童在学习“猫”这个字的时候,他的父母会指着猫说:“那是一只猫。”换句话说,概念是通过实例来获得意义的。当然,有时语词的定义是被给定的,比如说,“猫有四只脚、一条尾巴和几根胡须”。然而在某个定义中的字必须先被赋予一个意义,如此一来,人们才能再回到实例里来解释这些字。重点是,这些实例的数目一定是有限的。让我们把这种想法拿来对照一下哲学家所谈论的意义,哲学家并不否认实例的数目是有限的,但他们会说,实例会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概念,这些概念超越了原本的实例。或者就像哲学家所说的,被习得的意义是固定在可能事例的无限范围内的。哲学家会说,“猫”这个字指的是宇宙中曾经存在过或是以后会被叫做猫的所有的东西。落在这个概念无限类别内的东西,被称为是其“外延”。哲学家说,像“猫”(或“电子”“多面体”“+2”)这个概念就有一个本质上潜在的无限外延。他们会很坚持,这就是意义最核心且最重要的事实。有限论者则会说:“忘掉那些无限的外延,专注于那些数目有限的实例上吧!”这样你就会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接着你也会了解,为什么通过6个、7个或20个实例学到的概念永远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概念的使用者是如何得到第21个或第22个例子的呢?先前那些概念的应用本身并不决定这个概念接下来是如何被正确应用的。
所有事实都进入到概念是如何被应用的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人展现出一个概念的相同实例或例子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应用这个概念,因为他们从这些实例中萃取出了不同的东西。人们创造了不同的理解方式,或是把实例与不同的目的联结起来,抑或是把这些实例置于不同的背景框架中去。所有这些问题都密切地与“定义是基于有限数目的实例而来的”这个事实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知识社会学都是建立在所谓“有限论”的立场上。
黄:在您的书中,使用了“社会学的”有限论这个词,它似乎意味着还有“非社会学的”有限论。
布:我承认其他作者有时会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使用“有限论”这个字,或去指一些稍微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数学家对于什么是一个恰当的证明程序或什么是有意义的数学运算,有着不同的看法。有限论在这个脉络下有时是指:证明必然是一个数目有限的步骤。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与我使用的方式是类似的,并非完全一样,却是相似的。或许,当我谈到“社会学的”有限论时,它是被用以区辨社会学观点与这个早已存在的数学用法。
黄: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说也许有“非社会学的”有限论……
布:我有时会将有限论这个字与另一个字相联结,去指“意义有限论”(meaning-finitism),这是因为我想在意义的有限论与意义的决定论(determinism)之间做出区隔。意义决定论是那些认为你能够“固定住”某个意义这种想法的产物,我的立场是,意义决定论是错误的。意义决定论者认为,意义能够决定,比如说人在依循规则时的行为,这个规则的意义决定了后续规则依循行为的正确与否。我记得我曾做了这样的区隔。
黄:您提到“我们”发现了有限论,我猜您是在指巴恩斯或亨利(John Henry),您说的“我们”是指谁呢?
布:可以确定的是,巴恩斯与我都做了许多关于有限论的研究。巴恩斯做过一些既清晰又易于理解的研究,他真的做得非常好,那本阐释托马斯·库恩的书就非常棒。还有谁也采取了有限论观点呢?有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司德迪(Steve Sturdy)、库施(Martin Kusch)、马佐蒂(Massimo Mazzotti)。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也使用了这个观念且知道如何使用它。
黄:能否谈谈您与巴恩斯之间的异同?
布:我认为除了他比我聪明得多之外,我们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也许我们作品的风格有些许的不同吧——巴恩斯的思考是非常社会学式的,我的思考可能就比较属于哲学式的了。由于他研究中深厚的社会学洞见,我一直是他作品的仰慕者——虽说不是他所有的观点或意见我都同意,但他有着相当精辟推展论证的方法,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我很高兴地说,我们还是会花时间讨论。很棒的是,在离开这么久之后,他又回到爱丁堡来了。②
黄:说到您与巴恩斯,我想我们就得谈“强纲领”。在中国,我们倾向以“强纲领”这个大的架构来理解爱丁堡学派,您认为用这个词是个有意义的提法吗?
布:是的,我认为有意义。“爱丁堡学派”这个词用得很广,我认为这个词是很合适的。当然,它只是一种近似的提法,我们也应该留意很多有着多元见解和进路的人曾在不同时间在科学研究部待过。我们从未有某种“学派的路线”(party line),我希望将来也不会有。或许我也该说明一下,“爱丁堡学派”是其他人谈论我们时所给的标签,不是我们这群人自己会用的。科学研究部的人不是某天围坐在餐桌旁然后说:让我们称自己为“爱丁堡学派”吧!是我们发现其他人称我们为“爱丁堡学派”。
黄:您先前的访谈中也谈到强纲领,但那次您说:“‘我’基本上用这个词。”
布:我倾向用这个字眼,巴恩斯和夏平(Steven Shapin)过去没用、现在也不太用这个字眼,我不认为这个差异很重要。
黄:所以你们彼此的观念十分接近?
布:我想是的。我在1970年AI写作下这个纲领的时候,只是试图标示出一些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共通的意见与观念,不仅限于在爱丁堡的人。我引用并描述了相当多史学家当时所做的工作,试着搞清楚那些我认为隐含在诸多研究里的东西。我想我正确地标示出了一种广为流传的思考模式——这就是我所一认为的强纲领,也是我倾向思考它的方式,更是我爱丁堡的同事们思考它的方式。
有些圈外人似乎相信或是他们写得好像他们相信某人某天说:“喔!这边有个纲领,让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即刻遵循这个纲领来做些研究。”不是这样的,其实恰好相反。许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先有了研究的成果,然后我想:怎样才能将这成果刻画出来呢?其根本特征是什么?它假设的基础又是什么?纲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成果从纲领中产生出来。也许因为如此,“纲领”不是一个该被放在称号中的恰当字眼,因为它使人想到指导,而不是提炼和概括。我当时没想到这个问题,而现在要改名也为时过晚了。
黄:您能否为非专业的读者说明一下,为什么强纲领是“强的”?
布:在这个脉络里,强与弱之间的区分点在于,有些人说社会学家能合理地解释理性的背离或失败,但不能甚至不应该去尝试说明成功的理性思考——社会学家能够说明失败的观点或理论,但不能说明成功的观点或理论;社会学家可以解释错误,但不能说明知识——这就是我所谓的“弱纲领”。强纲领会说,社会学家不仅能在理解理性的背离中扮演一个相当的角色,也能在所谓的理性本身的理解上扮演相当的角色。不管是好科学,还是坏科学,都可以。批评者有时认为,“强”这个字眼在这里意谓着,遵循纲领的人相信“每种与知识有关的事都是纯粹社会学的”。这些批评者认为,一种“强的”社会学视角意谓着:没有什么心理学,没有什么生物学,也没有什么物质世界。这是错的,强与弱的对比并不意谓着提供一个选择:“所有事物都是社会学的”或“并非所有事物都是社会学的”——强与弱的区分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种区分不是如此运作的,很明显的是,因为把“每件事”都当成是社会学的这样的想法是很莫名其妙的,是非常前后不一致的。我们之所以有社会,是因为我们是一种特定的生物有机体;我们之所以是生物有机体,又是因为我们存活在物质环境里。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是社会学的。然而,人们在回应强纲领时,总是一再地把这种看法当成强纲领拥护者的主张。批评者说:“你难道不认为物质世界会与科学有某种关联吗?”我当然认为他们有关,打从一开始,我就把强纲领描绘成是建立在唯物论背景上的。
黄:您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及哲学这三个角度来阐释一下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成就吗?
布: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外加上历史,是能被诸如历史学家运用且一直以来都被持续利用着的资源。这三门学科与其说是强纲领的基础,倒不如说是可以被强纲领研究运用的资源。于我而言,被人要求来谈成就的问题是很为难的,因为这似乎是要自吹自擂一番。人是不应该自夸的。(笑)
请记住我方才说的:研究的工作并非依循着纲领而来,研究的工作早于纲领,而且仍持续进行着。但大体而言,研究的进行并不是因为学派的关系。当然,在擘画这个纲领的时候,我就试着界定出所谓的“佳作”来。也许真正该问的问题是:在研究传统的诸种成果中,哪些是我所认为的佳作呢?我认为答案是:一些很有洞察力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关于历史本质的研究,都已经有成果了。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现了现今的科学,以及过去曾有过的科学思维。我认为这些研究展现出了科学是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这些研究道出了科学是多么地仰赖偶然的发生。这些研究也道尽了要具体化一些简单的规则或是预测科学、谈论科学的走向,甚至去建议人们应该如何从事研究等是多么的不可能。
所以,也许这个传统最主要的一个成就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擘画科学政策时,得非常的小心。这几乎是在说:我们所尝试控制或规则化的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太多了。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就像个试着操纵一台非常复杂机器的人,对于转动这个把手或拉起那个操纵杆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有这么一丁点儿的想法。殊不知,这台机器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别太自信地认为当你拉起某个操纵杆,就可以预测到它会有怎样的影响。虽然你问我的是有关成就的问题,然而这其实是一件相当负面的事情。不过,了解知识的极限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这个世界上,众多问题的主要源头之一是我们太过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控制事物或是预测事情及人类行为的后果。我并不认为人们应该过于悲观或是认为所有的控制行为都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认为人们应该放弃。想要控制自己的文化和制度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更恰当的态度是在意识到困难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热切渴望,这比有一个建立在天真科学图像上的天真理论或天真政策要好得多了——这好像不算什么很伟大的成就?(笑)反倒比较像个负面的成就。
我也许真的应该试着说些比较正面的事。也许我应该说,这里最大的成就在于,它让我们更真实地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假使某人思索知识生活的品质后,他会知道,现在我们对自身认知的窘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也许无法马上就运用这项知识,但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应该肯定了解“我们的处境”与“我们是谁”等这些问题的价值——搞清楚我们现在身处的定位点这件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了,这几乎是种哲学的存在主义了。我现在说的是去领会人类现处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试着去领会人类所处情境的复杂面以及阴郁面中的可能性。没有比看着人们活在虚幻的世界里更糟糕的事情了,人们以肤浅且自以为是的信念来看待过去、未来、自己以及社会。有这么个比较实际的看法也许没什么好处,也可能没什么用。即使我们会因此而不愉快,但是了解这件事本身还是比较好的。
黄:可否请您谈谈您最近的研究?听说您不久要推出一本书。
布:真希望是“不久”之后!我快要完成一本有关空气力学史的书,③它已经花了我很长时间了。这本书之所以如此耗时,是因为它是本叙事非常细腻的书。这本书探讨有关“抬升”现象的理论,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的机翼能运作且让飞机在空中停留?对这个问题,英国和德国科学家有些争论,争论从1906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空气力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答案,而我就是研究这当中的见解分歧。我发现这场论争历经了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要到1926年战争过后,英德专家的意见才渐渐靠拢。我把这个研究拿来当作强纲领在知识社会学里的运用,我想知道这当中的分歧从何而来,又是什么让这个分歧延续下去的。这项研究牵涉到仔细地推敲科学家感兴趣的论据,研究还深入到一些数学的细节里。
黄:听起来这本书与科学史或争议史有关。
布:没错!的确如此。
黄:根据加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STS在美国的领军人物,主编了第二版STS手册)教授的看法,在科学史与科学研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鸿沟。她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如何来缩小这条鸿沟。您觉得有这么条鸿沟吗?
布:没有!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加萨诺夫教授提到,当科技与社会的研究者对科学史敞开心胸进行研究的时候,史学家们反倒是想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保持距离。这与我所经验的是不同的,我一直以来都发现,史学家对社会学的见解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的浑然合一,也许一点儿也不出人意料之外——因为我整个的研究生涯都是在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研究部度过的,这个研究部的首要成员中一直以来至少都有一位史学家,我的杰出同事们包括了夏平、亨利和司德迪等。从这个名单看来,我的经验与加萨诺夫教授讲座中所描述的情形是不一致的。她文章标题中“科技与社会和科学史研究可不可能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样的问题几乎没在我头脑中出现过。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两者是共同发展的,且已经好到把对方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地步了。只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回想麦肯齐对英国统计学史的研究,他的研究一开始是1970年代在科学研究部里的博士论文,然后在1981年出版成书,麦肯齐融合了历史研究与社会学及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我可以举出许多科学研究部之内或之外的例子,也可以引用伦敦、剑桥还有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运用了社会学的敏锐度并结合了详尽的历史研究来研究科学。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过去几年来,我相当荣幸地能在柏林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里钻研科学史。在那段工作期间,我也没遇到加萨诺夫教授所提到的抗拒。当然,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些不同看法的人,但就我看来,这整个环境似乎是开放的,而不是这么死脑筋的。
即使是对史学家最微不足道的指责,我也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会觉得有必要提出来。也许加萨诺夫教授在这些事情上的经验刚好与我的不同吧,也许英德的景象与美国的某些地区不同吧,我不得而知。如果说哪个学术领域本该接纳社会学观点却到最后一直没接纳,我会说是科学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史家。即使有一些醒目的特例,但一直以来这几乎成了惯例。这个阵营对社会学有着轻蔑的敌意,他们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去接纳知识社会学的研究。
李: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STS现状的?
布:这是个蛮难回答的问题。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对这方面的文献知识并不是很广,且我对现在这个领域正在发生的事也不是很熟悉。对于某些特定的领域,我有深入的了解,但不够广博。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相反地,这令我蛮羞愧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进行研究,我非常地沉迷于自己的研究,所以有很多事、很多我该看的书我都没看。所以我没什么自信能说我知道这个领域的现状。
当然,我对这个领域是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的,不过都是我个人非常主观的看法而已。我有这么个印象,就是说许多STS的人相信他们的研究进展已经超越了强纲领。他们觉得这个纲领在1970年代也许真的很有趣,但他们认为自己现在做的是些很不同或更有深度的或是说更有趣的事情。但我猜测真正的情形是,许多人发现强纲领太难了。我猜他们没给自己设下个严苛的目标。他们发现强纲领涉及到要找出因果解释,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些深奥的理由,好拒绝用因果的方式来思索科学和科学活动。他们运用了个存在已久的传统,即因果关系可以适用于物理科学,但社会科学关心的是意义、解释与理解。据此,研究科技与社会的学者应该使用解释或诠释学的方法,而不是因果的方法。
于我而言,这事实上就像是在对自己说:让日子过得简单点吧!在找到事情的起因之前,不要这么挣扎地研究了吧!让我们快速地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来展现解释的多样风貌。然后,就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老方法更胜一筹的新研究法。
我认为这是在规避那些最有深度且最有趣的问题。当察觉到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领域就不会再往前进了——我认为这个领域正在走回头路。当然,当某个人66岁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抱怨这样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我老了吧!
黄: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之前,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部的学生,我很想知道要如何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好个案研究呢?我们部里有个硕士程度的个案研究课,但到底该怎样选择一个好的个案来做研究呢?
布:我的回答可能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说笑。我会说:选一个你能找到的最小的课题。原因是,当你仔细地研究一个案例的时候,当你真的把显微镜都倒过来观察其中的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小议题都存在着许多的联结与隐射。看来很小的个案可能最后会变得很复杂,但至少你还有能力描述这个小议题。如果你一开始就选了个太大的,那么你永远都收不了尾,最后只能做一些普通又没有深度的评论。
虽说是要选个小的个案,但你也得选个自己可以确切地指出问题所在的案例。例如说,看看你是否可以找出争议在哪儿,但不见得要是个很大或很著名的见解分歧。顺便提一下,许多人误解了争议的有趣之处。他们认为科学里有许多的争议,但也有不那么有争议的。他们因此总结:如果你对争议感兴趣,就是对这之外的事不感兴趣,因为你只专注于几个特例上。但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错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之所以专注在争议上,是因为想了解当争议没有发生的时候,情形究竟是怎样的。
研究争议有助于我们看清知识形成的真相,即使这些真相在一些非争议的地方隐而未显,还是存在且关系重大的。那么,是怎样的真相呢?例如某些利益的运作,机构、学科与传统的影响等。所以,你可以找个你已经几乎确定一定有什么有趣之处或隐情的小争议来做研究。在科学里,小范围的争议随处可见。我正在研究的空气动力学就是一个小的争议研究,探讨空气通过机翼时的不同看法。就基础科学而言,这个研究的争议性虽无法比拟相对论、量子论或演化论,但一些令人惊奇的或是有深度的事情会从中跑出来。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遭遇到各式各样的事,这些事本身就使研究变得有趣。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厂必须生产很多飞机。这些都是原形机,但是有些工厂会大量生产,以备送往法国与荷兰的前线去。好了,有些制造商生产了这些飞机,然后政府派了监察员去监管。不用说也知道,这其中必然有很大的争议。监察员会说:不行!这品质太差!不够好。再做一次!然后制造商会说:这样太不切实际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做不到啦!这已经够好了!或者他们会说:这是你们政府的责任,不是我们制造商的责任。
当看到这项争议时,我马上就想到,某人可以写个这项研究的博士论文。他可以探讨这中间的利益纠葛,探讨这些利益的拉扯如何反映在评断木头的品质、金属的质量及做工的精细与否上——怎样的做工才能算是够格呢?他们用哪些证据来证明这个做工欠佳呢?
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理解有限论如此重要——你就不必非得找个爱因斯坦与波尔之间关于决定论这样的伟大争议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来研究。几乎日常生活中每个维度的小摩擦和问题,都可以找到好的题材来做个案研究。一直找下去,你就会找到的。(笑)
找一些这类小线索,然后往上追溯,跟着文末的参考文献走。你很快就会发现:原来有一个超乎想象的大争论在这儿。从一个小的注脚出发,接着就会变成四个注脚,然后就会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不久,你就有了争议研究的文献资料。有了20篇文献后,就可以踏上你的博士之路了。
黄:在我问最后的问题之前,在座的两位有什么后续的问题要问吗?
李:我想知道在您的强纲领建立之后,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布: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不知道当我说没有的时候,是该骄傲,还是该羞愧。
黄:但很多人说有限论是您思想中的一个转折,不知是否如此?
布:无疑的,它是个进展,是已完成研究中一个正在增长的领域。
李:已经深入地发展了吗?
布:我相信可以在我非常早期的作品中指出有限论的存在。然而无疑地,这个题目已日趋重要了。当然,它早已出现在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依循的分析里,即使那时没有真地使用有限论这个字眼,但那是一个有限论的分析。在强纲领的革创期即引进了的合理化的论述,就诉诸了维特根斯坦的规则依循分析。
许多评论家忽视了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在强纲领中所占的根本角色。当听到强纲领的支持者说:“社会的影响在科学里随处可见”,那些批评家认为,这只是一个武断的声称或是个非常愚蠢的概括。批评家想说的是,你也许会在科学的某些维度中发现社会的影响,但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有时候科学自行发展而没有受到社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是实在且谨慎的。
维特根斯坦有关规则依循的优势及重要性在于,他选了个似乎不会受到社会影响的例子,一个似乎完全取决于意义与逻辑性质的例子。来看看2、4、6、8、10这样规则依循的行为会有什么社会的影响?维特根斯坦说:让我们专注于这个例子。然后他解释人们是如何学会这个规则的。他研究说,如果有人无法学会这个规则,或是一开始就用非标准的方式来学习这个规则的话,那些信心满满的规则依循者或是老师会怎么说?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非常有说服力,他说明了你最终所拥有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影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想想老师可用的资源吧!他们会援用规则的意义或是试图鼓励学生在给予了有限的例子后,依循同样的方式继续推论下去。但是什么造就了“这个”规则的意义?是什么让这个规则沿着“相同”的方式推论下去?“相同”又是什么意思?在每种情况下,答案不是得以更多的例子来呈现,就是为了让人能够依循这个规则,而必须试着更具体地来解释某个规则。没错儿,一个要你依循规则的规则只是把你再带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最终,除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之外,老师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学生必须学会如何做得像老师一样,否则他们就是还不够格。我们现在所集体进行着的,就是在确认什么才算是一种合格的规则依循。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告诉你,我们过去所用的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有些哲学家建议,应该把纠缠着的推论与社会影响“拆解”开来。维特根斯坦则用了一个漂亮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譬如说,有个明晰且正确的推论在这儿。如果你把推论从社会影响中抽离,那么就什么也不剩了。就像一件毛衣,现在要将其从其编织中“拆解”开来——如果你试着这样做的话,那么最后你将一无所有,你不会有个什么更纯粹的衣服的形式,而是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例子的重点,旨在摧毁这种简单割裂推论与社会过程的想法。维特根斯坦让我们知道,你不可能在推论与社会影响之间划出界限或是“拆解”开来——因为这两件事情根本是同一件事。你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比这个更强的强纲领了。
黄:在座的各位,我可以请教最后一个问题了吗?我们决定要问每个受访者这个问题:科技与社会研究(STS)正在东亚蓬勃发展,您是否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以帮助我们建构自己的STS研究呢?
布:我感到无力胜任这个提供意见的角色,我想我最有把握说的都是一些很粗略的建议。比如,我希望你们不会再犯一些欧美之前且目前还在犯的错误;我建议多鼓励科学史研究以及有事实根据并关注因果性解释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无法给你们一个纲领或是科学政策,但可以提供探讨科学的资源。它们无法告诉你“把钱用在这个还是那个自然科学的领域上”,但是当你思索政策的时候,这些研究会是非常有用的。当你围坐在桌旁听取政策时,了解一下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颇有助益的——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训练可以帮助你更精准地察觉到私利与自利的意识形态。经由个案研究,你就会了解到这些东西。而且你很快就能与案例相联结。所以,我会说:多鼓励历史研究与因果解释的社会学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记得要把哲学家排除在外。(大家都笑了)
注释:
①本访谈录首刊于台湾《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0期第237-264页,其英文版Go Strong or Go Home:An Interview with David Bloor刊于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0年第3期第419-432页。
②巴里·巴恩斯教授2008年进入半退休状态,但他已搬回爱丁堡居住。
③布鲁尔教授所著The Enigma of the Aerofoil:Rival Theories in Aerodynamics,1909-1930一书已于201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