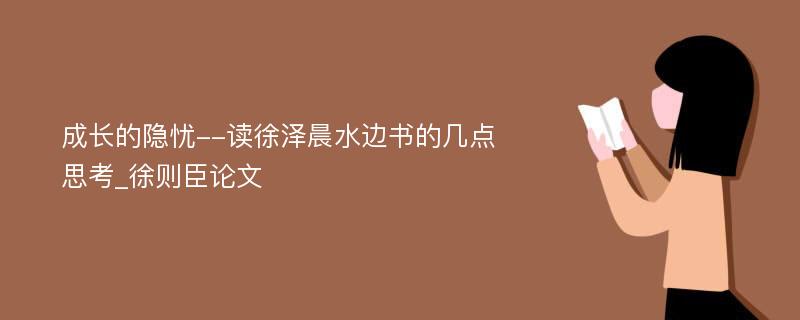
成长的隐痛——读徐则臣《水边书》的一些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痛论文,水边论文,随想论文,读徐则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是在火车上读完《水边书》的。那是深夜的硬座车厢,人满为患,灯光昏暗。大多数人睡去了,我还醒着。听着火车在旷野里奔驰,透过车窗放眼望去,只偶尔看见一两星灯光,冷冷地在夜色里浮动,我靠着窗读书,那灯光便一棱一棱地在书页上闪过,文字于明暗之中乍隐乍现。这时候,我正读到陈小多离家出走那一段儿。在旅途中读关于旅途的文字,特别的有感觉,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少年陈小多一个人走在荒野里的心情,瘦弱的他就在眼前,努力地迈着步子、挥着手臂。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十几岁时的自己。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唤起某些深藏在心中的记忆、痛苦、欢乐或者忧愁。虽然读者很少会和书中的人物有一模一样的经历,但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彼此相通的。事实上,离家出走、学武功等等这些“梦想”,是许多“70后”、“80后”男生们共同拥有过的,只是很少有人付诸行动,就如同童年的玩具,被我们扔在了某个犄角旮旯,在岁月中渐渐蒙尘。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人探讨过,为什么这两代的年轻人会有着这些共同的梦想。仅仅是因为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兴盛吗?还是说,离家出走、到远方去等等,本是无数代年轻人共有的“梦想”,到嵩山学武功,不过是这些“梦想”在某个特定时代下的变体?
回想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写离家出走的。余华和徐则臣同为江浙一带的作家,将他们的不同文本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
先看余华所写的离家出走。在“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我“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父亲说是要让“我”出门,因为“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这里面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首先是余华竭力渲染一种欢乐的氛围,给了这篇梦呓般的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小说一层明媚的色彩;其次是“我”的离家出走是在父亲的鼓励下进行的,严格说来,这甚至算不上离家出走。“我”离开家到远方去,并没有一种“断裂”感,至少,在感情上仍然有“家”在背后作为支撑。这两点在《水边书》里完全变了。陈小多的离家出走不再有梦幻般的愉悦色彩,也不再充满不确定性。他两次离家出走,目的都非常明确,都是为了到河南嵩山去学少林功夫。原因嘛,第一次是因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年龄,该硬的都得硬起来”;第二次是因为陈小多被学校里的斧头帮帮主狠揍了一顿。他走得好像很潇洒,尤其第二次,只给爸妈留了个纸条,纸条上写着:“爸妈,别找了,我没事。也别担心,又不是第一次。回来时我告诉你们。”这和余华笔下“我”离家出走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陈小多离家出走并非源于父辈的鼓励,而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一种“叛逆”行为;另一方面,偶一为之的叛逆行为,在陈小多这儿有了常态化的倾向。陈小多的离家出走,除了追寻梦想,还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意味,旅途中他才会常常觉得自己很“悲壮”。
“离家出走”更多的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离家出走,就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成长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和认知,“我”并没有预先对世界有多少想象和期待,所以,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显得特别广阔。到了《水边书》里的陈小多这儿,离家出走已经不大具备之前的象征意义了,这件事必须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功能或者目的,因为离家出走本身在他这儿几乎已经常态化了,不再能够表达“断裂”的姿态。必须有更加具体、有力的东西来承担“断裂”的表达。对陈小多来说,就是武功。只有学到了武功,他才能彻底摆脱自己的固有形象和命运,才能彻底和过去的自己断裂。因为目的明确,他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功利和狭小的。他离家出走的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只能是世界上很窄的一个方面——都是和武功相关的。世界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来说,犹如没有定型的自由漫流的水,对陈小多来说,已经是装在容器里有了一定形状的水了。我不由得想,这仅仅是两位写作者的区别,还是两部作品写作时代的区别呢?
陈小多离家出走,最终并未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终究没能到达嵩山,更没能学到武功。陈小多在突然决定回家后,走在路上有一段思考,“你看,会不会武功重要么?……有两下子的和没两下子的,结果都要置人于死地,他们比常人更不安全,还比如四大金刚和斧头帮,还有无数的这个帮那个派,又有几个终是与人为善的侠客?当然有,可是他看见的一跟功夫扯上关系怎么不是凶手就是帮凶呢?如果全练成了这样的人,他屁颠屁颠地跑到少林寺的意义何在?”陈小多离家出走后的整段行程,似乎不是为了抵达嵩山少林,而是为了抵达这样一个开悟的时刻。所谓开悟,就是要回到平常人的状态。这一代人实在有太多的人做过武侠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也没练成武功,武侠梦被他们不经意间丢下了,但陈小多是经过了一番磨砺和思索后才丢下的。对理想的舍弃,意味着另一种断裂。陈小多的离家出走,不仅仅是和“家”的断裂,也是和青春梦的断裂。
很多优秀的写作是对可能的生活进行叙述,而非对现实的生活进行叙述。也就是说,写作其实写的很可能是现实中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一个男孩儿为了武侠梦离家出走到嵩山少林去,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发生的,但确实在这一代无数年轻人的想象中发生过。徐则臣这么写,实际是对这一想法的一种想象。
徐则臣似乎很喜欢写漂泊的状态。或许是漂泊可以有无限多的可能吧。到目前为止,徐则臣的写作主要以京漂系列和花街系列为主。无论哪一系列,都有一些漂泊的人物,京漂系列尤为突出。
徐则臣写作的这两个系列,不禁让人想到苏童。苏童和徐则臣都是江苏人,有着比较相似的生活环境。这样两个人的写作,会有着什么样的异同?众所周知,苏童的写作主要由“枫杨树乡”系列和“香椿树街”系列构成。“香椿树街”系列和“花街”系列一样,都写的小镇,环境很有几分相似,比如,小桥流水都是镇上非常重要的景致。他们在类似的小镇上展开的故事,有时候也显出几分相似来。他们的另一部分写作就不同了,苏童写的是“枫杨树乡”,是乡间;徐则臣写的是京漂,是城市。都是写的农民,但苏童的农民还待在乡间,徐则臣的农民则跑到京城去了。在日益衰败的乡间和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其中的农民,内心里会有着怎样的异同?
综合起来,从书写的地域上来说,从苏童到徐则臣的写作可以这么概括:
乡村→小镇→城市
两位有代表性的江苏作家,一位是“60后”,一位是“70后”,他们所叙述的地方,刚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生命路径。
徐则臣和苏童的“亲近”也表现在了《水边书》这部作品里。这部作品,让我不由得想到了苏童2009年出版的新长篇《河岸》。单从题目上来看,“水边”和“河岸”,并没太大不同。所不同的是视角。在苏童那儿,是以船上人的视角来叙述“河岸”的,河岸是坚实的,河水意味着居无定所,意味着藏污纳垢,意味着被主流社会“流放”,船上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回到岸上。我曾写过一篇《河岸》的短评,其中有一段写道:“《河岸》有一个很清晰的叙事脉络,可以用两个动词概括:‘丧失’和‘寻找’。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用一句话概括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河岸》里的油坊镇和金雀河也构成了两个世界,关系上却不是这么回事,金雀河上的船民想上岸,油坊镇的人却不想到金雀河的船上。‘岸上就是比水上好。’船,成了浮动的流放地,背景是奔流不息的河水。河水(包括鱼)经常象征自由,但在《河岸》里,象征的首先是命运的波谲云诡。库文轩、库东亮和慧仙,他们在岸上丧失了某些东西之后,来到了波动不止的金雀河。他们三个人在河上对‘岸’的不同态度,构成了整部小说最主要的情节。”
在徐则臣这儿,是以岸上人的视角来叙述“水边”的,岸上的人对水始终是一个“看”的姿势,有着一点点好奇,还有一点点冷眼旁观。水给花街带来了不少不安定因素,“街顶头就是运河上著名的石码头,多少年来水上的男人上岸,都要在这里找点乐趣。……男人们哗啦啦都约好了似的在石码头上岸,就得有很多女人等在这里。本地的女人都被父母、丈夫和孩子看得死死的,只好由外地女人千里迢迢地赶来支援。所以说,在花街,即使缺了男人也不会缺外地女人。她们源源不断地来这里租房子。租房子的人都不打算久居,挣完了钱拍拍屁股就走”。为此,水在花街人眼中,就显得很复杂了。水不单单代表一种未知的生活、一个未知的世界,同样也有着苏童《河岸》里那一层意思,有一点暧昧,还有一点肮脏。
和《河岸》相同的,《水边书》里的几位主要人物都在追寻着某种东西。郑青蓝和姑姑(可能是郑青蓝的母亲)郑辛如来到花街,追寻的是正常的身份和正常的生活,这让她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郑青蓝和姑姑也是到花街租房的外地女人,也和水上来的男人们有着不清不楚的联系,她们的身份就不由得让人生疑。她们过去的经历在小说中一直没有清楚地交代,但可以隐约感觉得到,她们过去的生活经历了诸多坎坷。她们的过去一定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在花街住下了,还和水上的人保持着来往就是证明。她们到花街来,是为了脱离水的束缚,让一切重新开始的。花街并没有给她们这种机会。花街已经对外来女人有了固定的看法,她们便成了这种成见下的牺牲品。郑青蓝最终离开花街回到了水上。她在给陈小多的信里说,“我在水上漂游,远离花街和石码头,很好。……老是做梦,好像这些年的生活都是梦做出来的,我自己,原本就是待在船上”。郑青蓝离开后,郑辛如留在岸上独自守候,这让我想到那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们都是那样的倔强和绝望。曾经在学校表现优异、性格坚强的郑青蓝,仿佛被水吞噬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小说的结尾,陈小多看到一个蹲在船上往河里撒尿的女人,她回头看了一眼,陈小多忽然感觉到那就是郑青蓝,跳下车去追,却没能追上。“热蒸汽上升,置身阳光底下,十五米外的景物就虚虚飘飘,陈小多觉得她的红内裤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她低头弯腰推着摇篮车绕到货物的另一边,扎冲天小辫的小女孩搬着小板凳跟在她身后。”女人的形象突兀、强硬地嵌入了读者的视野,久久不能淡去。这人不知道是不是郑青蓝,正因为这不确定性,让人愈加为郑青蓝的命运担忧。对正常身份和生活的追寻,郑辛如留在在岸上,得到的是孤独和伤痛;郑青蓝又回到了水上,势必伴随着种种妥协。
陈小多所追寻的是武功,是个人生命力量的强大,最终失败了。陈小多的父亲陈医生追寻的是医好郑辛如的痒病,最终没能医好不说,自己也犯了痒病。——郑辛如的痒病是通过自残痊愈的。作者一再写到郑辛如的痒病,当然不是无意为之的。这种病痛很难被人理解,却又那么痛苦不堪,我把它理解成郑辛如非正常身份和生活的一个象征,要治愈就要自残。这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事儿。
徐则臣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斯文特拉说的:“一个作家必要为自己写一本成长的书。”《水边书》就是一本关乎成长的书。青春期的成长,将生命的美丽和疼痛以特别迅猛的方式表现出来。对成长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词汇就是“远方”,所以,崔健在80年代一次次唱响“远方”,所以余华要“十八岁出门远行”,所以苏童在《河岸》里一再提到那个叫做“幸福”的遥远小镇。徐则臣则让陈小多和郑青蓝都追寻远方而去,两人的不同在于,陈小多希望脱离走向远方凡俗人生,却最终回到了花街;郑青蓝希望在花街融入凡俗人生,却不得不到远方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似乎都是失败的。说到底,无论是郑辛如、郑青蓝还是陈医生、陈小多,他们追寻的,都是对个体生命的确认。他们的失败,构成了潜藏至深的生命隐痛。
当然,《水边书》并非简单地写了青春期的成长,还写了生命的可能和不可能、希望和绝望、散失和找寻。
2010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