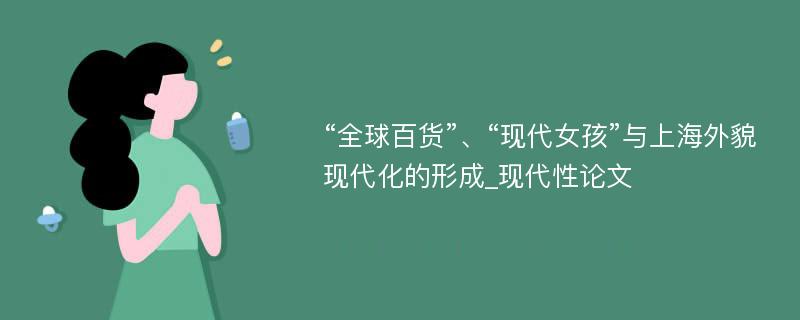
“环球百货”、“摩登女郎”与上海外观现代性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环球论文,摩登论文,上海论文,女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142-07
“线性时间进步观”通常被认为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性追求上的主要倾向,而世人对“线性时间”的认知、信仰包括“迷茫”很大程度是和视觉的震惊交织在一起的。本雅明曾以电影为例指出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给世界所带来的“震惊”,而在其后的“拱廊街计划”中,他则将造成现代人视觉震惊的根源推到了商品世界,尤其是它的展示和消费活动。德波、鲍德里亚等有关“景观社会”的分析,也都进一步指出了都市奇观与炫耀消费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百货公司使西方女性第一次可以不需要男性的陪同而自由地往来于街道商店,它因此被女性主义读解成是“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了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①她们并因此而发现了普通女性在不断推进的都市新奇观中的作用。这一切,在现代上海同样有着鲜明的表现——20世纪10—3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经销“环球百货”著名的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及其与此相关的“摩登女郎”。本文以此为线索,探讨现代上海炫耀性消费的发展和外观现代性的生成,及其与“线性时间进步观”的关系。
一、“环球百货”:视觉政体和炫耀消费
近代以来,上海的消费文化日趋繁盛,一首流行于晚清的竹枝词这样说道:“申江自是繁华地,岁岁更张岁岁新,解取及时行乐意,千金一刻莫因循。”②尤其是在有着“销金窟”之称的福州路上,茶园、酒楼、戏苑鳞次栉比。但上海的消费文化或商业形态进一步向“制度性”的以视觉为主导的炫耀性消费的发展,端赖于先施、永安等公司的创立。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籍广东的澳洲华侨马应彪、郭乐等人乘着西方各国忙于战事无暇中国市场的开拓,先后回国在上海南京路、近浙江路一带投资创立大型百货公司。1917年10月,马应彪的先施公司首先揭幕;翌年9月,郭乐的永安公司也随之开张。1926年和1936年,又有两家名为“新新”和“大新”的巨型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闪亮登场。
历史和文化评论家罗斯在谈到西方百货公司的兴起时指出,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某些变革,为当年巴黎在百货公司发展上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豪斯曼伯爵主持的市政工程改变了城市的街道,新修的路面和人行道让行人可以方便地行走和闲逛,并暂停脚步凝视商店的橱窗,玻璃和铸铁技术的发展使大片橱窗得以镶嵌在商店的正面,电气化则提升了隐藏于橱窗背后的奇观与戏剧性。④这也是先施、永安等公司出现的背景和呈现出的新气象。20世纪初,随着跑马场的几迁其址,南京路由东向西已经发展成了上海首屈一指的大马路,路面宽阔且定时洒扫,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也于1908年建成通车,日后先施、永安之所以选址于南京路西段,也是因为邻近的浙江路上有电车通往北火车站,能带来大量客流。无疑,道路交通的现代化为先施等公司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现代商业模式的引入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商业的形态。四大公司除了商场外,还设有酒家、旅馆、茶室、咖啡厅和游乐场等等,人们原本是来购物的,结果却进了一个吃喝玩乐无所不能的场所。新新公司里的“玻璃电台”和大新公司里的“自动扶梯”更是充分展现了电气化所导演的“戏剧性”。而从消费与视觉性关系的角度看,先施等公司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或创举,乃是在于建立了一种以“不二价”/“明码标价”为支柱的“视觉政体”,从而把商品的“可视性”和“炫耀感”抬升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以最先开张的先施、永安两公司为例。在“统销环球货、始创不二价”的经营方针下,先施在开张之日即已采购、经销各类商品逾万种,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陈列出来。偌大的、近万平方米的商场内,成千上万的商品被以明码标价的方式分门别类地陈列于“一目了然”的玻璃柜或展示架中。永安在同样规模和方式的展示外另开了上海大橱窗陈列的先河,在底层朝南京路的一面设了10个由进口大玻璃制成的嵌入式橱窗,此后,各大公司纷纷效仿,大橱窗陈列遂成为上海的街景和大商场的惯例之一。这样一些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展示方式,在现代上海的空间建构和消费发展中却未可小觑,不仅一举颠覆了传统的商业形态,且对社会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将各类商品“完美无缺”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仿佛“触手可及”,让商品的诱惑力和炫耀性令人“瞠目”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则将人们与所观看到的商品有效地隔离开来,原先可与卖家讨价还价的主动的言辞往返也被迫转化为“沉默”的观看,从而使人们“视”有余而“取”不足,进而萌生“必欲取之而后快”的愿望。以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的分析,这样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展示方式正是“商品拜物教”得以实现的机制之一,无数的“商品挂着,无拘无束地像最狂野的梦中意象那样呈现出来”⑤,有效地唤起了人们的视觉和对商品的欲望。
如果考虑到现代上海对“洋货”等外来奇观曾经不无“骇怪”,那么,这一方式对上海炫耀性消费发展的影响更值得注意了。由于上海的开埠伴随了坚船利炮的先导,其后大量涌入的新奇物品/“洋货”在中国的历史上却闻所未闻,世人于是在“奇技淫巧”的鄙夷之外也不无“骇怪”或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晚清妓女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了洋货的率先使用者;唯其如此,洋货使用的“合法性”更成了问题。先施“始创”的“不二价”则将人们的“骇怪”有效地化解于对“科学”与“诚信”的信仰中。所谓“明码标价”,即一切商品都首先是“看得见”的,而不是如传统商业那样越是贵重的物品越是深藏不露;不仅如此,它还同时意味着所有的成本和利润都经过了科学精确的核算,从而具有足够的诚信或合理性。先施的店名也是取自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公司“Bon Marché”表示经营信条的“Sincere”(诚信)的译音。如此,通过对“科学”和“诚信”的强调,洋货的“他者性”便被大大“降低”了,或者说已被成功地“去魅”。与此同时,先施、永安还对“洋货”进行了重新的命名,将其改换成了“环球百货”。原因无他,只因以“线性时间进步”的观念看,不仅“科学管理”下的“诚信”是“时间进步”的象征或体现,欧美为代表的“环球”及其物品本身即意味了先进和文明。
这便解释了四大公司的“环球百货”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为什么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来自“环球”的品牌,时新的款式和“科学”的定价,使购买者顿时产生了“合潮流”/“有身份”的感觉。四大公司还纷纷发明了向富裕有“信誉”的顾客发放可以赊账的购物折子和用汽车接送它的特选顾客等方法,进一步宣示了“环球百货”及其使用者的“非同凡响”。在这样的策略引导下,不仅上层阶级唯先施、永安等公司的“环球百货”为“尚”,一般大众也紧随其后,成了它们忠实的“拥趸”,其逻辑恰如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说:“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穿到最下阶层。结果是,每个阶级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级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⑥
二、女性的“合法”空间和“摩登女郎”的产生
四大公司的视觉政体和“环球百货”无疑在上海炫耀性消费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海派小说家如下的描写则告诉我们,普通都市女性同样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或者说,正是由于她们的加入,四大公司才成为上海最具人气的消费空间:
“倷个个啥辰光买格?”……“是公司里买的。”那回答在不熟悉这种情形的人听来也许会以为它是一句隐语……而那问者却不会不熟悉这种情形的,因此她一听就知道那所被说到的公司就是三公司之一——她们把先施、永安和新新合称为三公司……只要是说是从公司购的,就知道它有公司的货品地位。
小说名曰《三公司》⑦,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其时大新公司尚没有开张,故称“三公司”。而早在19世纪末,上海女性“冲出闺阁”介入公共空间和消费的愿望已经十分强烈,《吴友如画宝》中一幅数名闺阁女子手持望远镜遥望租界的情景便生动地传达了这一信息。⑧上海女性的“不安于室”其实要更早于此。民国的建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为女性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但1924年的北京戏园里仍是男女分座的,某晚瞿秋白请刚从沪到京的丁玲看陈德霖出演的京剧,丁玲因哀伤挚友的早逝无心看戏,写了一个字条请茶房递过去便不辞而别了。⑨
女性之所以被排除在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或被区隔开来,以女性主义的看法,在于历史上女性的活动通常被限定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女性的“越界”/对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的涉足通常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在现代都市的初兴之时,尤其是百货公司出现之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能在城市中自由移动的“公共女人”大都是妓女。晚清上海虽然普通女性的行为准则也已有所松动,但转型时期的混杂却引发了人们更多地对于“危险的女性”或“女性的危险”的担忧,普通的良家妇女如何“安全/合法”地置身于公共空间,仍然是个问题。
先施、永安的出现则为破除这一“僵局”提供了条件。它们的宽畅明亮和“明码标价”等等的经营方式,无不表明这是一个“童叟无欺”、当然也包括妇女在内的“安全”同时也是充分“合法化”的空间,普通女性在其中的活动并不会有伤大雅。于是,大量的都市女性开始往来于街道和“公司”之间,并构成了四大公司本身的景观之一。1928年《上海漫画》上一幅题为“秋冬之衣”⑩的漫画几乎“纪实”地描绘了这一状况:秋冬之际,忙着换季(装)的都市女性摩肩接踵地在“公司”的楼道里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这一景况的出现其实和百货公司所允诺的“随意浏览”有更大的关联:“头一遭,过路行人可以不负购买义务地随意进入店家。”(11)一般认为,19世纪中期诞生于巴黎的“Bon Marché”是“随意浏览”的始作俑者,先施等公司显然仿效了这一方式。可以“只看不买”,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在其间的逗留时间,本雅明认为,购物活动中这种由随意的“闲逛”而引发的人际间的“摩擦”与“交流”,能够于无意间将消费的场所演变为社会空间,而以左拉在《妇女乐园》中的描述,“随意浏览”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针对女性而设计的性别化的商业体制,根本上是为了“诱惑”女性而促使交易的成功:
女人乃是交易之中心。她们要被引诱、诱导与迷惑。她们被特价商品吸引,被标价的纯粹数字所震慑。最初她们以家庭主妇的身份被诉求征服,接着被新潮的喜好牵着走……(12)
事实上,四大公司在提供女性“合法”空间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促进”消费的使命,恰如女性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功能在于挪用并保存她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或享受的价值与商品;她替他们的劳动提供了一剂解药和一个目的”。(13)在现代上海,“随意浏览”的另一个结果则是促使了“摩登女郎”的产生。1934年《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绘现代中国的都会女性:
现代中国的摩登姑娘,太太们,哪一个不是成了洋货商店的好主顾,从头发丝尖儿起,至高跟皮鞋底的最末一英寸止,差不多除了她们固有的中华血统的皮肉之外,全都装饰着舶来的服用品。(14)
四大公司无疑为“摩登姑娘,太太们”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流行的标杆。换言之,如果说明码标价和随意浏览构成了四大公司“视觉政体”的核心,那么它们也同时造就了一种踵事增华的新的女性形象和气质。早在1928年,《华北捷报》上已有了关于“中国的奇装异服的轻浮女子”的报道,她们“穿着半洋化,短发……短裙……脂粉脸”(15),而到了1930年代,描眉,画眼,烫发,抹口红,身穿改良旗袍或其他各式时装,足登丝袜和高跟鞋,则构成了“摩登姑娘,太太们”的“经典”形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四大公司提供了女性自由行走的合法性,以往“养在深闺”消息闭塞的她们在成为“摩登”代表的同时,且广泛地出现于公共场合,构成了都市潮起潮落人群的一部分,其之于都市,已“一如飞鸟游鱼之于自然”,进而将“环球百货”所宣扬或表征的“摩登”更为广泛地播撒开来。
三、时间、空间与性别:上海外观现代性的生成和紧张
“现代性世界是一个最终由商品生产、流通和交换的支配地位造就的幻想和假象世界”(16),就现代上海而言,“环球百货”和“摩登女郎”无疑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环节。如果说前者构成了现代上海商品世界的主体,那么后者同样参与了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上海外观现代性的生成。而这一过程与它们对炫耀性消费的推进并不能分开。
首先,“环球百货”、“摩登女郎”所形构和表征的炫耀性消费提升了表面印象在现代上海的重要性。“表面印象重要性的增加,这也是现代性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上海开埠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流动,加上“转型”造成的“礼崩乐坏”,使得传统由稳固的地理所属和血缘关系为依据的身份认知已经变得不再有效。“环球百货”则以其使用价值和文化符号并举的双重功能提供了人们于一个新的变动不居的环境里身份重建的可能。而四大公司大量展示的本身亦同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大量展示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外观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世人对事物的认知也越来越“依赖”于“目之所见”。1935年的一幅《想象型之都市女性之新妆》(18)的漫画夸张而不失真实地凸显了这一变化。画面上一“摩登女郎”造型夸张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而男性则被描绘/比喻成了匍匐于女郎新妆之下地位卑微的小乌龟。女性的“新妆”之所以会引起人们有关男性地位跌落的联想,除了漫画家的夸张外,也是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社会认知方式的改变,原本居于卑位的女性有可能借自我包装/外观的改变而获得发展的机遇。“外观”于是变得不仅仅是外观,而成了机会的凭证和社会竞争的资本。这一变化的意义当然不仅是它为女性的社会“晋升”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运行方式的出现:即个人的身份和发展机遇可以通过外表的修饰而获得,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帮助了人们的身份“重建”和社会流动。
其次,“环球百货”和“摩登女郎”有力地参与了都市的“印象整饰”或景观生产。外滩的万国建筑、汽车轮船和霓虹装饰历来是上海都市景观的典型代表,茅盾的《子夜》开场便以外滩为背景,从薄雾笼罩的外白渡桥、1930年的雪铁笼汽车和闪射着赤光绿焰的霓虹管广告,一路描写到南京路、河南路口抛球场一带“高耸碧霄”的摩天楼……如果说凡此等等的新景观宣告了“现代性的来临”,那么身穿“外国轻绡”、香气扑鼻的“摩登女郎”从一开始就与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并直接促使了来自乡下的“封建僵尸”的命归西天。随着情节的开展,行走于大饭店交易所的她们且制造出了更富视觉刺激的马路戏剧:有“西洋美人”之称的摩登女郎刘玉英,一次“像被风卷去了似的直扑过马路”后,在外滩华懋饭店前的石台阶上和一西装男子迎面相撞,其开叉极高的旗袍被风吹起后,旋即卷进了男子的手杖。而在“新感觉派”小说家的笔下,“摩登女郎”更多地被和八汽缸的汽车、骆驼牌香烟、咖啡的幽香、舞厅的灯光和上了白漆的行道树“混合”在一起,成为都市律动不可或缺的因素。有意味的是,如果说至此为止,“摩登女郎”还是行走于摩天楼下,那么,到了30年代中期,随着先施、永安等集聚的南京路西端日益成为上海的地标,“摩登女郎”已经被置于都市的高空,和夜空中的先施、永安、新新公司壮丽的大楼景观并列在一起。1926年,南京路上首次出现了“皇家牌打字机”吊灯广告,先施公司立即跟进,将霓虹店招悬挂到了公司大楼的顶端;不久,永安公司的楼顶上也闪烁起红色的英文字样“Wing On”和绿色的中文“永安”,新新公司的霓虹装饰更是后来居上。这一景况很快被与“摩登女郎”结合起来,成为上海“印象整饰”的新篇章。1934年出品的电影《神女》中,我们看到,当银幕上出现了被璀灿的霓虹装饰着的先施、永安和新新公司的大楼建筑时,阮玲玉扮演的性感而“巧笑倩兮”的“神女”的身姿面影也叠加其上,构成了“上海繁华”的象征或人们想象中的上海“应有”的景象。如果说建筑是都市最为重要的语汇之一,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现代都市的建筑已经和女性性特征的叙述化无法分离了”。(19)
四大公司及其相伴而生的“摩登女郎”无疑对上海的都市感性和外观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促使上海从历史上一个“文物寂寂”的“弹丸蕞尔之地”一跃而为远东第一都市或世界第六大城市。但与其说“环球百货”、“摩登女郎”是上海外观现代性生产的主导力量,毋宁说上海的外观现代性生成于现代中国对“线性时间”的强烈追求。外观现代性既是空间的呈现,同时是时间的概念,现代上海对“时间进步”的认知可以说是从空间/视觉的震惊开始的。开埠后大量涌入的“洋货”和外来奇观在让人们感到深深的震惊的同时,也“直观”地体悟到了西方世界的“先进”和“老中国”在时间上的“滞后”,从而激起了对“时间进步”的急追。在这一过程中,先施、永安无疑居功厥伟,它们不仅前所未有地重塑了人们的视觉,而且在“外观”和“时间”之间建立起了牢固而重要的联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的外观现代性日渐生成。“表面印象”在现代上海之所以至关紧要,除了它是个人在匿名社会里必要的标注外,也是因为它的“瞬间”变化有利于人们对“时间进步”的及时跟进。“摩登女郎”的香氛薄衫、炫奇斗异虽然极大地挑战了社会成规,但因为其中所蕴涵的时间意识也在其时的上海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快速发展中,时间无疑成了价值的主要参数,上海的外观现代性也因此而呈现出超常的“求新求变”和更易速率,往往“三数年间”或“转瞬”之间已“有如隔代”。诚然,“摩登女郎”的“以时为尚”也表现出某种时尚固有的“循环往复”的趋向,如旗袍在30年代的忽长忽短,但现代上海的时尚系统总体上可以用“与时俱进”、“虎跃过往”来概括。“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20)这样一种对“时间”的急迫追求也渗透和表现在四大公司的形成及命名中。1926年登场的新新公司以“日新又新”为宗旨,而1936年开张的大新公司则以最“大”之“新”为标榜。事实上,现代风格的大楼建筑等等也再一次刷新了现代上海的外观现代性。
吊诡的是,现代上海此类对“时间进步”的追求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焦虑。面对上海开埠后尤其是20世纪都市化加剧以来的变化,人们一方面感叹着上海“在念(廿)多个周年这进展的过程也就够瞧呢”,“什么皇后号总统号……一船船把许许多多的物质文明都装到上海来啦,看看摩天大楼一天天如年龄般愈长愈高了”;(21)同时则疑惑着:“虽说上海的地面是我们中国的,但有一寸土真正是中国同胞的吗?”(22)在1933年新中华杂志社发起的“上海的将来”的征文讨论中,更有论者不留情地说,上海应当全然“没有将来”,“上海如不能走向健康的繁荣,毋宁走向痛快的毁灭”,上海的霓虹灯必须被死亡吞灭,“墨墨的浓云”将笼罩城市。(23)事实上,上海自开埠以来,其“将来”和外观的变化就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有意味的是,正当“上海繁华”或“一种新都市文化”的形成已成不争事实之际,出现了不若“毁灭”的呼声。显然,如果说日趋发展的外观现代性表明了上海在“线性时间进步”追求上的成就,并使它远比马尼拉、加尔各答等城市更有都市的感性,那么现代上海触目皆是的异国情调、景致和风物,以及“分裂”的一市三政的空间格局,也同时凸显了中国主权的缺损和屈辱。
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也是权力争斗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现代上海不断发生的空间和景观的变化或外观现代性的演进,无疑和殖民势力的影响有关。换言之,如果说“线性时间进步观”成功地带动了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和都市化的进程,那么也为它的殖民扩张提供了想象的基础。而作为殖民扩张对象或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其对“线性时间进步”的追求则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时空的紧张或两难。当“线性时间进步观”在现代上海衍化为一系列的包括四大公司和“摩登女郎”在内的“新都市文化”或景象之时,上海顷刻间与世界的“先进文明”接上了关系,获得了“时间进步”的正值;与此同时,其显而易见的外来性则也触目地提醒了主权的暧昧,加剧了人们空间感受的复杂性。这一“紧张”且因为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在30年代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呈现出来。1929年,世界爆发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美各国包括日本为摆脱危机加紧了向中国的商品倾销,造成了中国连年不断攀升的入超;“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令困顿中的民族工业再一次遭受了重创。这一系列的变故无疑加剧了人们“亡国”的焦虑,而关税和主权的不自主不完整,则使国人在频繁严重的变故面前几乎没有切实的应对之道。于是,和历史上不少困厄的时刻相同,性别政治登上了前台。其时,上海发生了普遍的“女性嫌恶症”,尤其是在1933年开始的“国货年”运动中,“摩登女郎”遭到了严厉的谴责,被认为毋庸置疑地“犯有卖国的嫌疑”(24),因为“除了她们的肉体是从母胎带来的国货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无一不是外国货。(25)而在1934年蒋介石亲自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摩登女郎”的“衣长袖短”之所以被纳入了国家管制的范围(26),也是因为在当政者看来,除了她们的奇装异服必将造成严重的“风化”问题之外,其对外货的追捧也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主权。
莫尔维曾将叙事性电影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主动的/男性观看和被动的/女性被看之间的分裂,而女性在成为男性“视觉快感”客体的同时,也诱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女性的性差异所暗示的“阉割”焦虑;而男性摆脱这一焦虑的途径通常有两条,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对“女性”这一“有罪的对象的贬斥、惩罚或拯救来加以平衡”。(27)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摆脱”焦虑的方式。面对无法改变的“入超”和国土丧失等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其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同样采取了对“女性”/“摩登女郎”这一“有罪对象”的贬斥、放逐来“平衡”。不同的是,如果说经典的叙事性电影凭借这一方式有效地帮助男性个体在潜意识层次上摆脱了“阉割的焦虑”,那么,现代上海对“摩登女郎”的控诉并未能真正有效地缓解民族现实的危机包括社会的焦虑,反倒是更为强烈地凸显了危机的“存在”和进一步的临近。1936年,一幅《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28)的漫画以戏剧化的手法描画、想象了未来女性成为上海统治力量的状况,她们将“从裸腿露肩的装扮进化到全体公开”,只是在“重要部分”系了一丝细带,而男性却仍然穿着传统的裤子,被解放了的她们称作“封建余孽”。考虑到时距上海沦为孤岛不足一年,这一“风光的狂测”无疑折射了更多国族的焦虑,或者说乃是变局将临之际空气中愈益弥漫的“惘惘的威胁”及现实矛盾在社会心理中的“变异”。漫画呈现给人们的似乎只是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未来上海的两性关系图,而“进化”、“封建余孽”等等的字眼却透露出其中深蕴着的有关时间、空间的焦虑与迷茫。
总之,如果说,“线性时间进步观”主导了现代上海外观现代性的生成,那么,形成于20世纪10-30年代、以经销“环球百货”著名的先施等四大公司及其相伴而生的“摩登女郎”则有力地参与了这一进程。先施等公司在以“科学性”、“视觉化”和“随意浏览”等方式打造现代观览型的商业形态或“视觉政体”的同时,也形塑了一种踵事增华的女性形象,造成了她们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大量出现。“环球百货”、“摩登女郎”提升了“表面印象”在现代上海的重要性,帮助了人们的身份重建和社会流动,并构成了都市“印象整饰”和景观生产的重要部分。上海外观现代性超常的“求新求变”和更易速率,在促使上海一跃而为远东第一都市或世界级城市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持续不断地焦虑和普遍的“女性嫌恶症”。性别政治的介入复杂化了现代上海的面目,同时凸显了现代中国或上海在“线性时间进步”追求中的时空紧张。“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形式。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属于都市和在都市中形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达的在场。”(29)作为城市的文化资本之一,现代上海的外观现代性包括其内在的紧张无疑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复兴。其对“老上海”的执著寻找和“重构”,似乎着意的是重现当年的都市感性和景观,其潜在的心理却是对曾经“失落”或“断裂”的时间的重拾,包括以“上海小姐”、“上海的金枝玉叶”为中心的文学描写热的形成及其所引发的争议(30),无不显示出时间、空间和性别在新时代里新一轮的交错和复杂。
注释:
①[美]米卡·娜娃:《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18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②袁祖志:《续沪北竹枝词》,见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③上海有百货公司并非自先施、永安起,20世纪初,南京路近外滩一带已有福利、汇司等数家外商经营的百货公司,但这些外商百货公司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中国人服务,很少有中国人前去购物。
④[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第218页,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⑤转引自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的碎片》,第322—3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⑥[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64页,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⑦作者林微音。
⑧见《视远惟明》,周慕桥(1868-1922)绘。
⑨王增如、刘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第2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⑩叶浅予:《秋冬之衣》,载《上海漫画》,第13期,1928-11-10。
(11)(13)[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第161、219页。
(12)转引自张小虹:《在百货公司遇见狼》,第167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
(14)导溱文:《摩登妇女,觉悟吧》,载《报》,1934-08-02。
(15)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第2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的碎片》,第360页。
(17)[美]米卡·娜佳:《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见《消费文化读本》,第183页。
(18)张英超:《想象型之都市女性之新妆》,载《现象》,1935(2)。
(19)[美]玛丽·安·多恩:《跨语境下的女性面孔、城市风景和现代性》,见《聚焦女性:性别与华语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张爱玲:《更衣记》。
(21)《上海礼赞》,载《现代》,第11期,1935-11-01。
(22)(23)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44、33、4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
(24)画舫:《鸣鼓攻“摩登”》,载《红玫瑰》,6卷32期,1930-12-21。
(25)《生活》,2卷42期,1927-08-21。
(26)1934年6月,江西省据蒋介石手令率先出台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
(27)[英]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见《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8)张文元:《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载《时代漫画》,1936(30)。
(29)[英]托马斯·班特尔:《当代都市与现代性问题》,见《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0)见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