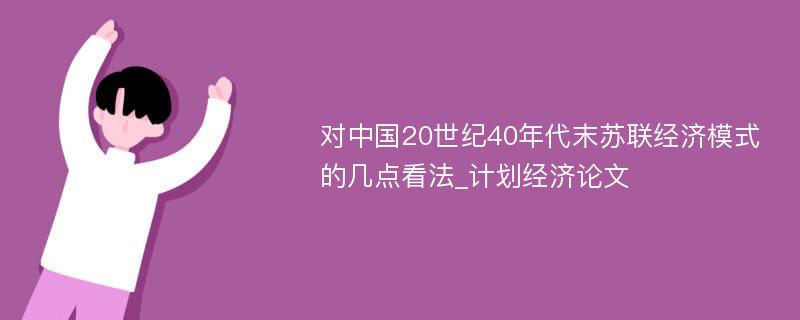
194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若干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学界论文,中国论文,后期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4-0095-05
20世纪前半期的苏联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与经济状况时刻在世人的瞩目之下,以自由主义者为主要构成的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40年代自由主义者最向往的制度选择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合而为一,政治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古老话题,而经济民主则是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凸现的一个新内容。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竭力推崇的理想制度,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成为自由主义者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参照。本文主要阐述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对苏联经济状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认识和看法。
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中国知识界认知和评价社会主义的重要指标之一。40年代末期,苏联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取得了可观的建设成就,这一点被自由主义者普遍认可。浙江大学法学系教授严仁赓的说法颇有代表性:“资本主义制度耗费了一二百年所取得的成就,她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已赶过半程。若不是这次大战折磨她,说不定她今日已经追上了农工各业最先进的国家了。不独生产事业,其它部门哪一门她没有超速度的进步?我们没有替苏联吹嘘的必要,这本是大家熟知的事实。”[1](pp5-8)
对苏联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状况予以系统和详细介绍的是任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著名教授吴景超,他运用社会学的比较方式,从美苏对比的角度展示苏联的经济建设成就。吴景超认为,从人口方面看,最能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是人口的职业分布情况。苏联经过大规模的工业化,职业分配出现了良好的变化,统计资料表明:“初级职业中人口的百分数,有显著的减少,而其它职业中人口的百分数,亦有显著的加增,这是苏联大规模工业化的最好象征。”[2](pp3-5)关于农业,吴氏认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的建立是苏联农业最有价值的改革,并由此取得了农业技术改良和机械化推广的良好成效。至于工业,始终是苏联建设的重点,建国以来苏联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生产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贸易上,苏联以国营商业为主,集体农民仍保留着自由市场性质的农贸市场,消费物资则采用供给制和价格制结合的方式,保证了人民的基本需求。
吴景超在肯定苏联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他认为,在农业方面,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太少,负担过重,租税高达农民所得(包括实物与货币)的35%-40%,“由此可见,苏联农民的负担,是很重的。他们的牺牲,是促成苏联工业化的主要因素。我们希望苏联工业化的结果,在将来,也可以给苏联的农民分享,像美国的农民,得到美国工业化的好处一样”[3](pp4-7)。就工业言,苏联工人的生产效率始终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产品性质方面美苏差别最大。苏联偏重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比例之高世界罕见:“这种牺牲目前的享受,以加速资本的形成,恐怕只有集权国家里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生产,才办得到。”[4](pp3-7)而美国大部分是用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差异,是影响目前两国人民生活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4](pp3-7)。至于消费,总体上看苏联的消费物资仍然短缺,使其商业劳务的质量不如他国,“这种现象,在消费物资不能大量供给之前,是无法改进的”[5](pp6-8)。
吴景超对苏联经济状况的介绍和分析是根据的,他运用了苏联官方以及西方学界的大量数据材料,系统地对苏联经济取得的成绩与问题给予评说,并由此引发了对美苏两国经济制度的思考:“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最时髦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最后也许要引用这一类的研究结果来下公平的判断。”[4](pp5-7)
吴景超的思考反映了4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状态。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给予了颇多的关注与讨论,本人曾有专文对此进行过分析[6]。有相当多的学者对计划经济充满热情,比如著名学者张东荪、政治学者吴恩裕、经济学者陈振汉、负生(笔名)等,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为样板的。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苏联取得建设成就的核心所在。
在上述学者看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生产的高效率。张东荪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说近百年来欧洲社会主义试验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革命后能使生产增长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产降低则必会被反革命所推翻。“苏联的经过尤为明显:革命之初的战时共产制就因为不能满足增产的要求以至维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为新经济政策。如新经济政策永久下去,则革命虽成而社会主义却失败了,幸而有计划经济,可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乃得到新的生路”[7](pp3-5)。张东荪强调,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的所有制下都可运用,但只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计划经济才具有进步性,这是苏联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的贡献。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增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7](pp3-5)张东荪还认为,苏联的经验对于落后国家尤为适用。陈振汉也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效率角度提出,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下,计划当局仍能够根据所谓价格的变数作用(parametric function)把生产资源派分到各种生产事业里去,并能达到与理想的价格制度媲美的效率。从实践看,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证明,做到供求平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pp5-7)。总之,这些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重要建设成就,计划经济功不可没。
当然,有的学者如前面提到的吴景超,在对苏联的计划经济给与肯定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估计这一体制的局限的。吴景超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局限之一是在生产目的方面存在问题。吴景超引用斯大林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六项基本任务:“在这六个基本任务中,我们以为最后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国防能力的任务,乃是苏联推行计划经济的中心动机。”[9](pp22-34)显然,提高国防能力的最好手段就是采取计划经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革命的远大抱负,势必使苏联将提高国防能力视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计划经济也会长期存在。换句话说,苏联计划经济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工具,首先要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标。“在苏联草拟五年计划的时候,是否把这一点列为主要目标呢?我们不能说苏联政府完全忽略了这一目标,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不以这个目标为最重要,也没有把这一个目标首先提出来考虑”[9](pp22-34)。
吴景超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所以在苏联还没有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生活程度低下的国家,人民的初步要求仅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苏联的设计机关,过去对于人民需要的解决,所致力的,也只限于这方面”。[9](pp22-34)但基本需求之上,人类更高层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无穷尽的,而且主观成分极强,这便超出了计划经济所能达到的能力:“苏联将近两亿人民的主观要求,决非少数设计者所能窥其全豹。目前苏联设计者,对于人民需要的供给,还是停留在基本需要的满足一个阶段,还没有进到文化需要的满足那个进一步的阶段。假如有一天,苏联走上了第二阶段,我很怀疑,计划经济是否能胜此重任。”[9](pp22-34)
可以看出,吴景超并不笼统地看待苏联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生产能力,而是注重考察生产力的提高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生活不同方面的需要。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在对苏联计划经济多有赞美的潮流中,保持着特有的理性和清醒,并主张只有市场经济与价格机构才是经济制度唯一的理想选择。
在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各种好评中,最为大家称道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平等。一般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从而铲除了剥削存在的社会基础,贫富悬殊现象不复发生,经济平等的理想初步实现。“我们知道苏联是经济最平等的国家。土地、资本和工业完全国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民没有冻馁的危险,没有失业的恐惧,经济问题有了合理的解决”[10](pp5)。调整社会经济制度,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扩展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这就是所谓经济的民主。在这方面,苏联1917的革命和苏联将近三十年在这方面的努力,成绩特别多”[11](p75)。比较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苏联的成就更加突出,学者郑林庄概括说:“自一九二九年发生世界经济大恐慌以后,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普遍地受到打击,到处都闹着‘物价暴跌、生产停顿、失业日众,民生益困’的病象。当时唯一一个未受影响的国家,只有一个立国不久而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那里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享受,虽然还有许多地方,仍然赶不上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她们的人民大体都能安居乐业,而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12](pp9-10)经济上贫富悬殊缩小、人民安居乐业的苏联,受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普遍推崇,并成为他们理想中的“经济民主”的重要样板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中间依然有人对苏联的经济平等给予了分析和质疑。首先是如何理解经济平等。张东荪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它所能做到的平等也只是消灭剥削,至于完全的经济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3](pp3-5)。吴景超对经济平等的分析,特别强调了人们容易忽视的经济权力问题。他认为在苏联公有制的情形下,私人对资本没有所有权,但这些财产的使用权却掌握在若干人手中,其集中的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于是“在苏联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于在美国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资本家。……在苏联,得罪了政府,还有什么别的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余万方里的苏联领土之内,他有何处可以成家立业呢?苏联国内政治权与经济权的集中,是苏联人民的最大不幸”[14](pp4-6)。吴景超完全同意英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希克斯对经济权力的论述,即权力不平等的危害胜于收入的不平等,也就是说,真正的经济平等是不能将经济权力的平等排除在外的。在他看来,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政府可以控制人民的一切,这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极大威胁,绝不值得效仿,与吴景超有相同看法的还有北京大学的青年经济学教授蒋硕杰等。
其次,苏联现实的收入状况是否真的平等,这还是个问题。这方面有详细分析的仍是吴景超。一是收入的来源。苏联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理应无财产收入,但私人所得,可以储蓄或购买国家公债,获得利息。不过苏联的利息数量不大,在现行体制下,该收入也不可能转为资本,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根本不同。二是收入的数量是否悬殊。劳务所得是苏联人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所以工资或薪水的差别最能反映经济平等的状况。“最可注意的一点,是苏联的工作者,虽然都拿薪水或工资,但最高的薪水,与最低的工资,中间隔着相当的距离,有与日俱增之势-[15](pp19-20)。根据苏联30年代末期规定的工资上限与下限,“苏联最高的薪水,超过最低的工资约十八倍。最近有人估计,两端收入的比例,已经变为二十比一”[15](pp19-20)。如果连同奖金合计,一位经理与普通工人的差距有130余倍。“这一类的统计,可以表示苏联贫富距离,正在扩张中”[15](pp19-20)。
根据比较分析,吴景超认为,英美贫富间的距离的确大于苏联,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有一点是饶有兴味的,就是英美贫富间的距离,近年来正走着与苏联相反的趋势,换句话说,英美贫富间的距离,正在缩短的过程中”[15](pp19-20)这种反方向的趋势演化“能否使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下,贫富距离的程度,趋于一致呢?这是一个极有兴味的问题,但只有将来的事实,可以回答”[15](pp19-20)。暂且不论吴氏关于趋同的判断是否准确,重要的是他对苏联经济平等的分析颇具说服力,其结论也基本符合我们后来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尤其是他对经济权力的关注切中要害。实际上,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是导致现实经济状况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20世纪前半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强调平等的学说,获得了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普遍的好感。他们高度关注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并对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平等多有赞许,表现出对经济民主的强烈向往。第二,部分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经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和实际状况的不平等,此种清醒和理智十分可贵。实际上,这些自由主义者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分析,体现着他们对理想经济体制的特有认知,在他们看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的结合,乃是保证民主政治和社会活力的最佳制度选择。第三,自由主义者普遍对苏联的政治体制持否定态度,这也是他们更衷情于战后西欧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缘由所在。
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张东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