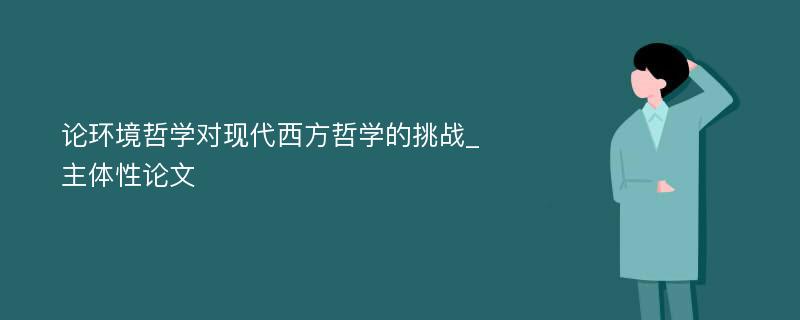
论环境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环境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哲学提出了若干颠覆性的命题,从而对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提出了挑战。环境哲学要求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摒弃现代哲学的许多成见。固守着现代哲学的成见不仅难以避免种种理论上的谬误,还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
1 拒斥僵硬的主客二分
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人是主体,非人的一切皆为客体。人的主体性被愚蠢地夸大了。主体是自主、自足、自为的存在者,或如海德格尔所言,“主体自为地就是主体”[1],客体则只是无自主性、无灵性的死物或物理实体。主体可认识、分析、解剖、操纵、控制客体。对于虔信上帝的西方中世纪人来说,上帝才是绝对主体,而人只是上帝的创造物(creature)。但“上帝死了”之后,“人起立而入于他的本质的主体性中”[2],当人成了惟一的主体时,便有了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
自培根和笛卡尔之后,“‘我’(ego)就成了一般主体(subjectum),也就是说,主体成了自我意识。主体的主体性取决于自我意识的确定性”[3]。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黑格尔又说,认识了的必然和能动的实践便是自由。于是,人的主体性或自由就体现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非人存在物的控制和征服。
既然只有人具有主体性,一切非人存在物皆无主体性,那便意味着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和权利,一切非人存在物皆无内在价值和权利。
然而,这些信念都只是现代性的成见。实际上,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相对的,主体性是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人并不是惟一的主体,也不是最高主体;作为“存在之大全”的自然才是最高主体,而且是绝对主体;非人存在物也具有主体性,从而亦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权利[4]。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就包含着关于自然之主体性的思想,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在马克思眼中,自然界不仅仅是客体,她也是主体。只是自然的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人的主体性。不可把大自然理解为一个巨灵,即一个具有人的重识的无限实体,那样就会坠入神秘主义。自然的主体性植根于它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无限性,自然“作为基础把一切聚集于自身”,除了“上帝”没有任何存在者具有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说自然是无限的,既指它时空上的无限,又指它具有无限复杂性,或指它内蕴无穷奥秘。这种自然是形上学意义上的自然,既不可等同于地球,也不可等同于现代宇宙学所说的产生于“大爆炸”的宇宙[6],更不可等同于自然物。
非人事物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一位植物学家曾指出:一切植物都有主体性,人类总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利用植物,其实植物也利用人类[7]。动物更有主体性。美国学者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说得好:“重新发现我们与周围实在的关系,首先在于认识到人类周围并不只是一堆客体,而是一群主体”[8]。
我们不必像海德格尔那样完全抛弃主客体的区分,但必须重新理解主体性,并重新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1)主体性可简括为事物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凡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事物都有主体性。具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事物都能在具体环境中进行不同程度的创造,从而取得一定水平的适应环境的主动性和主导性。
(2)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在世界万物中,作为“存在之大全”的自然具有最高的主体性,自然的主体性是绝对的主体性。在地球上,人类具有最高程度的主体性,动物次之,植物又次之,如此等等。
2 承认自然和自然物的价值
保留了主体性、主体、客体概念,环境哲学可帮助澄清价值论中的许多混乱,清楚地定义价值、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等重要概念。价值或者是主体的目的,或者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或属性。内在价值就是主体的纯粹目的,即不作为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的目的,如幸福之于人,生命之于一切生物。内在价值直接发源于主体的主体性。工具价值则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或属性,如金钱之于人,水之于动植物。工具价值产生于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根据这里的内在价值定义,所有的生物至少都有一种内在价值——生命(动物还能追求另一种内在价值——快乐)。
有了以上的价值论,环境哲学就可以正确地理解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的价值关系。
现代人混淆了自然和自然物(或自然系统),这是个严重的错误!环境哲学要求严格区分自然与自然物。自然物是具体的,可被科学所认知的,而自然是超验的,只能通过哲学之思去体悟[9]。科学思维使人们只见经验的东西,不见超验的东西。人类征服了许多自然物,便误以为征服了自然。
自然是人类须对之心存敬畏的终极实在,而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人类既无能力保护自然,也无能力征服自然。人类可对生态系统有所损益,但不可能对大自然有所损益。地球和大阳系迟早都会消亡,人类当然也会消亡。如利奥塔所说的,“人类的死亡已嵌入了人类的精神生命”,“地球一消失,思维就停止”[10]。但又如恩格斯所言:“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11]。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若努力遵循生态学规律,就不至于在不该灭亡的时候灭亡,若仍像目前这样破坏生态平衡,就可能在不该灭亡的时候灭亡。而人类是否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自毁,并不影响无限大自然的“永恒的循环”[12]。所以,为说话方便,我们可以说保护自然或破坏自然,但确切地说,人类既无能力保护自然,也无能力破坏自然。
但人类确实破坏了生态系统。人类过度砍伐了森林,过度开发了荒野和湿地,过度挤占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人类也有能力去保护生态系统。但最好的保护办法并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抑制贪欲,不再挤占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不再污染环境。因为自然生态系统有其循环再生能力[13],只要人类不去干预它,它就能保持动态平衡。可见,最好的维护生态平衡的方式是遵循着生态学规律去生产和消费,自觉加入地球生态系统的再生循环。
我们既不必像彼特·辛格所告诫的那样都做素食者,也不必像某些毫无心肝的商人那样完全漠视生物的价值和权利。我们倒是应该接受利奥波德整体主义的道德标准:凡有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都是错的[14]。在自然界,捕食与被捕食关系是自然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当被捕食者的数量严重减少时,便会抑制捕食者的繁殖,从而为被捕食者的繁殖生长提供条件,这样就能恢复二者之间种群数量的平衡。现代人类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和保健学)无止境地增加了人口,商业无止境地刺激着人们的贪欲,以至于过度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大量物种的灭绝。根本错误不在人类的饮食习惯。如果不该吃动物,也就不该吃植物,因为植物也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但如果什么都不吃就只能饿死。正确的态度是,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这里的“应该”不能只由人类武断地决定,人类须倾听自然的言说,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是该吃的,什么是不该吃的。生态学能告诉我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整体主义似乎会把我们引向汤姆·里根(Tom Regan)所反对的“环境法西斯主义”[15]。根据整体主义原则,一切都得服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如果一个物种繁殖过快,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有权消灭该物种的部分个体,以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已繁殖过多,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所以,应该消灭一部分人类!这是骇人听闻的结论!但实际上,整体主义哲学没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承认非人自然物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但并不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同等的主体性,所以也不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利。人除了生命权以外,还享有财产权、名誉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在地球上,人类因为具有最高的主体性而创造了文化,从而才享有这么多的权利。即财产权、名誉权等是文化所赋予个人的权利。我们不认为所有的非人自然物都和人一样享有这些权利,但认为所有的生物至少都享有种的生存权,而种的生存权是自然所赋予每一物种的权利。因为人类是惟一能认知生态学规律的物种,所以人类可以根据生态学规律去调节其他物种的种群数量。
我们不可能像尊重每个个人的人权一样尊重每一个生物个体的权利,如果这样做,那便连打死一只苍蝇也是如同杀死一个人一样的罪过。每个个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权)是现代文化赋予个人的权利,而非人物种不属于文化共同体。我们只能以服从生态规律的方式尊重生命共同体中诸物种的生存权利。之所以可以这样,就因为我们的主体性比其他物种的主体性高,我们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而它们没有。但在人类共同体内部,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同类。长期以来我们违背了生态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地球上人口过多,人已严重侵占了其他生物的栖息地。但只能通过教育、协商、计划生育和普及生态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我们中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有权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宣称某一部分人可以继续生存,而其他人都必须死,以便保持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
这么说丝毫也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超越生态规律。我们永远也不可忘记,人类虽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最高存在者,但不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者,自然之剑永远高悬于人类头上。人类作为地球上惟一具有生态意识的物种应在生态系统中主持公道。这决不意指人类就是自然的主宰。能在宇宙间主持公道的不是人类,而是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大自然。人类若不能很好地在生态系统中主持公道,如像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样,根本不考虑其他存在者本身的价值和利益,只关心人类自身的利益,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大自然以其客观规律(包括生态规律)为权威律令:人类如果不尊重非人生命的生存权利,也会失去自己的生存权利。如果说在文化共同体中个人的权利是由法律保障的,那么在大自然中物种的生存权则是由自然规律保障的。暴徒对无辜者行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人类对其他物种不公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在地球共同体中,人类若不能在诸生物物种中主持公道,而一任自己的贪欲膨胀,便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人类共同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蔑视人权而猎杀人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但至高无上的大自然有权决定是否让人类继续生存在地球上。
可见,如果我们能辩证地理解主体与客体、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并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之上还有无限的大自然,便既可坚持整体主义立场,又不走向“环境法西斯主义”。
3 消解事实与价值的二分
环境哲学不认为道德规范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也不认为道德规范只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约定;不承认事实与价值、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截然二分,也不承认什么“自然主义谬误”。因为环境哲学恰恰要用现代生态学的规律去支持环境道德规范。事实与价值(或描述性话语与评价性话语)的二分是现代哲学一个教条,环境哲学要求废除这一教条。普特南曾系统地论证了事实与价值、合理性(rationality)与价值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普特南看来,“每一个事实都渗透着价值,而我们的每一种价值都负载着某种事实”,事实和价值通过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框架而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之中[16]。但普特南因坚持内在实在论而难以摆脱主观主义,他对事实-价值二分的消解使事实和价值判断都封闭于人类的语言框架之内。
环境哲学可以吸取普特南的正确观点:在人类语言框架中,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所以,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必须用我们重新阐释的主体论去摆脱主观主义的束缚。不能认为人类语言是个封闭的系统,不能认为人永远都只跟人交流,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物乃至于自然也处于交流过程中。人际交流是人的本真生存状态,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的交流也是。但现代性遮蔽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认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只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是主体,自然和自然物只是客体。这样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交流关系,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只是认知关系,或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如果认识到我们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和它们交流,甚至和它们交朋友。有一位叫蒂皮的法国小女孩讲述了自己和各种动物交朋友的许多趣事,她说:“我会跟动物说话”。可见,人可以与动物交流。可能有人说,这只是一个孩子的天真。但孩子的天真有时正是发现真理的条件。“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不正是惟一说出真理的人吗?现代人被现代性蒙蔽得太厉害了,他们反而发现不了天真的孩子所能发现的真理。如果我们能承认非人自然物的主体性,就能把儒学所极重视的推己及人的良知用于非人主体,即站在非人主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或如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一样思考”[17],从而能摆脱主观主义。如果我们能“像山一样思考”,就不仅能发现关于非人自然事物的事实,而且能理解它们的价值。若能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用关于自然和自然事物的事实去论证关于价值的命题。
4 倾听自然的言说,培养“生态良知”
现代哲学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这也是个错误的成见。语言不过就是主体交流用的有规则的符号体系。动物学家认为,动物也有其语言,只是没有人类的语言复杂。自然科学已充分表明大自然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大自然无时不在透露各种各样的信息。大自然按其自身规律所透露的信息难道不就是她自己的语言吗?大自然的语言远比人类语言复杂、深奥!
现代人的狂妄一则表现为对自然主体性的否认,一则表现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极度乐观。人们认为自然客体的奥秘是不变的,人类知识越进步,未为人知的奥秘就越少。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任何困难都可以通过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可以在宇宙中为所欲为。这是十分愚蠢的狂妄。实际上,大自然是无限的。大自然永远孕化着无穷奥秘。人类在不断地发现和创造,大自然也在不断地创造,孙悟空永远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无论人类知识进步到什么程度,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匿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大自然是我们应永远对之保持敬畏之情的终极实在,是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绝对主体。我们只能通过自然科学去窥见大自然的部分奥秘,而决不可能把握大自然的全部奥秘。
现代人在认识自然物方面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远比在认识自己方面花费得多。但不能说现代人一直在倾听自然的言说。为什么?就因为现代科学一直没有把自然和自然物当作主体,而只当作客体。现代人认识自然不是为了理解自然和顺从自然,而是为了“指挥自然”或征服自然。什么叫“倾听自然的言说”?满怀敬畏之情地探究自然奥秘就是倾听自然的言说!倾听自然的言说是为了理解自然,顺从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倾听自然的言说就是追求真理。真理就是客体的本真显现或主体的真诚言说。但每个人的真诚言说并不就构成客观真理。真理的客观性是通过主体间的交流而达到的。真诚的人们在心灵洞开的交流中所达成的共识便是相对真理。但人类为了发现真理,不能只注意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还必须与自然物交流。与自然物交流便是倾听自然的言说。
现代人割断了与终极实在的联系,因而再也无法体验人类的集体罪恶。在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人们因为信仰上帝而有体验人类集体罪恶的参照系,上帝曾因为人类的集体堕落而降罪于人类,并以“大洪水”惩罚人类。在现代文化场中,人就是上帝,人间的法就是最高法,绝大多数人拥护的就是正确的、道德的。只有像希特勒和本·拉登那样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滥杀无辜)才是有罪的,无害于人的就是无罪的。人类长期以来为满足贪欲而破坏地球,虐杀各种动物,灭绝无数物种,人们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更没有什么罪恶感,因为这些事情是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做的。在忘却了终极实在的生存状态中,人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无法纠正集体错误。在征服自然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只会不断地从技术错误和认知错误中汲取教训,以改进技术、扩充知识,再更有效率地征服自然事物。人们无暇反思:人类是不是在集体堕落?
实际上,人既已超然于其他动物之上,就不应只一味追求物质丰富,而应在满足生物性需要的基础上追求精神超越。
现代化的一大成就是在物质生产上保证了人的生物性需要的充分满足,但资本主义文化却用其整个符号系统诱导了人类的集体堕落,即用纯外在的物质符号系统去表征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以及所消费的商品的档次,从而使人们完全不能领会内在精神超越的价值。现代性激励人们无止境地追逐财富,无止境地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本是有限的,例如,每个人只能吃那么多食物;只需要穿那么多衣服;只需要住那么多房屋;……但现代文化使人们对物质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生物性需要,原因在于它使人们把占有和消费尽可能多、尽可能高档次的物品当作人生的最高意义,这才使人们对物质的需要趋于无限。
人本该在精神超越中追求无限,但现代文化却激励人们在物欲满足中追求无限,绝大多数人以物欲满足为最高价值,这便是人类的集体堕落。人类所面临的潜在战争危险和生态危机皆与这种集体堕落密切相关。人类为什么消除不了战争?就因为集体堕落。资本主义是争富斗强的,为争夺资源、财富和市场,民族国家之间不免发生战争。人类为什么在已面临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仍不肯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就因为集体堕落。若不能从集体堕落中自拔,人类就难逃巨大的劫难。
为从集体堕落中自拔,人类需要一次良心的革命和伦理学范式的转换,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环境哲学可促成伦理学范式的转换,可以培养人的生态良知,因为环境哲学能促成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换,能消解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
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界,我们就能明白,道德关怀不应只限于人,还应扩及一切生命。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界,人类才能从愚蠢的骄傲中清醒过来,明白人类并不是上帝,人类也不可能通过文化的历史积累而历史地逼近上帝的全智全能,并进而由当代科学所提供的材料,经过哲学反思而认识到大自然就是人类所绝对依赖的终极实在。
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伦理学即可从实证科学中寻求理论根据,从而使人类的道德话语摆脱其纯粹主观的形式。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哲学伦理学即可与实证科学通畅地对话。但哲学伦理学不必认为实证科学就是终极权威。实际上,实证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只是哲学伦理学理解终极实在——大自然——的中介。经过这一中介,伦理学便可重新寻找其真理之根。这样的伦理学才可能引导人类生活于真理之中。而现代伦理学因为不再触及终极实在,从而封闭于人类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这便使现代人一方面表现出征服自然的狂妄,一方面深陷虚无主义的荒谬之中。
环境哲学将力倡一次“良心的革命”。良心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培养的。良心就是人根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判断善恶是非进而做出行动选择的能力,有良心的人就是能分辨善恶是非且择善而行的人。无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无从形成人的良心(并不排斥个人对先在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进行反思和批判)。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良心。现代文化培养了现代人的良心,这种良心只表现为对人权的尊重,而难以表现为对自然事物的关爱。在现代文化场中,有良心的人们无时不在对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进行战争。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界,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我们就可以重新陶冶良心。既然并非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我们就不仅应善待同类,也应善待一切生物。既然道德话语不是纯主观的感情表达,价值与事实互相包含,我们就应努力通过自然科学中介,而把伦理学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确立起觉察集体堕落的参照系。有了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就会明白,对待自然事物也有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算,对自然事物怎么做都行。我们不仅应对人讲良心,对自然事物也应讲良心。良心不是纯主观的,良心不仅依赖于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标准,而且依赖于人类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在我们准备实施大型工程之前,不仅应询问公众同意不同意,还应该询问自然允许不允许。
有了这样的良心,我们就不会认为,是否普遍奉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只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事情。历代都有人穷奢极欲,但在传统社会只有少数人可以这样。大自然能宽容少数人的过错,但不能宽容人类的集体堕落。今天的地球已有60亿人口,地球凡能供人居住的地方都已住满了人。在现代性的指引下,这些人都希望有汽车、洋房,都希望成为比尔·盖茨。如果我们能培养出新的良心,就该叩问大自然允许不允许人类集体过这样的生活。
面对环境哲学的挑战,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哲学须有一次根本性的转向。
收稿日期:2003-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