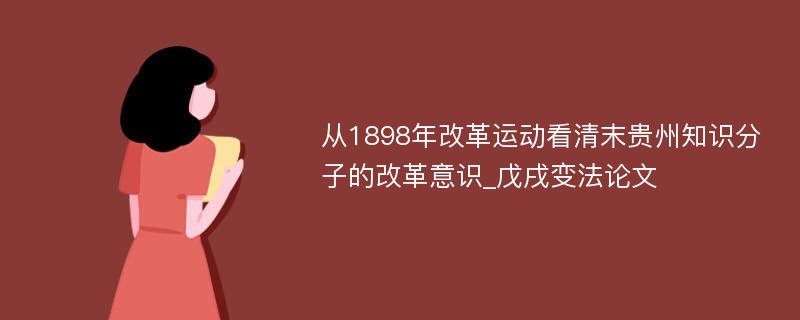
从戊戌变法看晚清贵州知识分子的变革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晚清论文,贵州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百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当年,贵州人士曾积极参加戊戌变法的有关活动,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行省众多应试举人进行“公车上书”时,其中就有贵州举人。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参加聚议的1300多人后“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数百人遂取回知单,实际签名者只603人, 贵州举人则有95人, 占此总数的1/6,在18行省中为第二多者;1898年,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时,该组织先后召开过三次会议,其中一次在北京贵州会馆举行,这也表明该组织得到贵州在京人士的支持,或有他们参与;其时任礼部尚书的贵州人李端棻是朝廷中唯一的“言新政”的二品大员,他曾荐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18位维新人士入朝,变法时期,他又在康、梁与光绪皇帝之间的联系起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贵州人士在北京曾经参与戊戌维新运动。不仅如此,变法维新的影响也传入贵州,就在1898年初,湘人吴嘉瑞到贞丰百层任厘金总办时,曾与杨虚绍发起组织“仁学会”,该会以文昌宫为会址,“每夜由吴杨共选一讲演题目,或国防时事,或国内政治”,抨击时政,鼓吹变法,入会青年知识分子多达30余人;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改贵州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招贵阳、贵筑及省内各属高材生40人,除教授经、史之外,并授天算、格致等新学。
尽管当时贵州人士中不乏上述趋时者,在办新学堂方面且得风气之先,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重要一页的戊戌变法对贵州所产生的影响,与当时贵州人士的参与程度似不成比例。95名贵州举人在北京“公车上书”时是那样的热血沸腾,义无反顾,为什么回到贵州后却未曾奔走呼喊,进一步扩散变法维新思想,是不能耶?抑或是不为耶?我以为,由此作进一步的探析,了解戊戌维新运动在贵州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不仅是研究戊戌变法运动之所需,而且对于认识贵州社会近代化历程何以起步既慢、进展甚缓,亦有帮助。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贵州人,特别是大众情绪的主要代表者知识分子们,是从爱国救亡的层面去认同和参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在他们之中尚无学习西方,突破儒家思想模式、解放思想、进行文化启蒙的认识和先行者。这是因为,当时的贵州社会不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贵州社会经济中虽然有商品经济在滋生和发展,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东南沿海和周边地区都要落后,而进入晚清以后,封建统治制度日益腐朽衰败,但封建剥削却不断加重。其时,封建政府的田赋、征派、税、捐、差徭等有增而无减,即以田赋为例,嘉庆年间,田赋随征耗羡,每正赋1两,带征银10—15分, 正赋米每石带征耗米10—15升,到清末时,因各地官吏任意增加征收数额,“正银1 两”竟“收至10两以上”。至于以“踩戥、踢斛、样盘、零尖”、“地盘米”、“看谷费”、“风车谷”等名目的浮收、勒折等更层出不穷,其数额较前期和前朝增加数倍。田赋之外,更有苛繁的捐税和徭役负担,而各地地主则通过畸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等疯狂榨取农民的血汗,正是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广大贵州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他们一年辛劳却不能求得温饱,常常“至食草根、木皮”,“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有的人甚至“田园卖尽,始而鬻卖屋宇,继而鬻卖男女”,“更有逃亡故绝”者,他们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更无力扩大再生产,致使直至清末及此后很长时期贵州农业经济长期在低水平状态中徘徊。
咸同年间长达18年的社会剧烈震荡,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对贵州各族农民的血腥镇压,使贵州社会经济一度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全省死于战乱者在200万人以上,而咸丰元年(1851)时, 全省丁口总数仅为544万人,人口的剧减表明劳动力损失巨大, 战火还造成老百姓房屋被毁,财产、粮食、牲畜、工具被洗劫一空。战乱之后,贵州农村虽有复苏,但经此破坏进一步拉大了与沿海及发达地区的差距,造成了直至清末、贵州的支柱经济仍旧是农业经济,仍未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的状况。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贵州所造成的影响也与沿海地区不尽相同,贵州人士虽有因列强侵略造成的屈辱感和承担赔款的经济重负,但其大多数人并不曾有过列强坚船利炮的实际感觉;洋纱洋布虽畅销于贵州的一些农村市场,但有清一代,洋人未曾在贵州城镇办过一家工厂、也不曾划分出一块租界,只在边远的铜仁万山、梵净山等处开办了数家矿业公司。因此,贵州人感受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19世纪80年代在贵州兴办的全国第一个“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青溪铁厂,其机器设备购自英国,还聘请了外籍工程师,但主持人潘露不是贵州人,技师、工匠系从江浙聘来,潘露不幸“积劳病故”后,贵州竟找不到精通西学的干员以接任其职。而该厂从一开始就因设计规划存在问题陷入“亏折”的困境,此后更因管理不善而终于倒闭。因此,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并未起到示范的作用,相反只能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时期的贵州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感受十分有限,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认识更加肤浅。当时,开始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只有经世学堂的40名学生,他们所学的近代科学知识也只是初级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时贵州尚未派人游学国外(直到1905年前后,贵州官费、公费资送留学日本学生54人、自费生10人),而此前贵州人士走出国门并带回国外印象造成影响者,也只有黎庶昌等数人;贞丰仁学会成员在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的黔西南,其所议论的国际时事和“西儒学说”,难免不是皮毛之见;至于当时追随西方传教士的贵州教徒多系农村妇女和社会下层人士,她们只是盲从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没有对包括天主教教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刻的领悟,更谈不上是西方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就是将上述几种人都算作是西方文化的接受人和传播者,其总数也不过数百人而已。对于一个户籍口数多达500余万,交通不便、 信息传播不灵的内陆省份而言,无论怎样看,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远未达到广泛传播的程度。
然而,当时的贵州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情绪,正处于对现实严重不满,要求变革现实的状况之中。这是由于面临内外交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压榨剥削之时,已不顾惜中小地主阶层了。咸同年间,因苛捐杂税而家贫甚至破产的人家中就有中小乡绅,还有许多“文绅系牢发一尺,武绅坐狱面深墨”,而郑珍之类的地主知识分子正因为感受过官吏催逼的情景和实际苦痛,才能写下’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雷声不住哭声起……长官切齿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银”这样的诗句来。更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对外的一系列失败,再到咸同年间贵州地方各族农民的大起义,使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洞悉清朝统治者腐朽无能,感觉到封建中央政权再不能维护和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饱受过咸同社会动乱期间出生入死、流离失所的苦痛、不安和恐惧的贵州知识分子,他们油然而生末世之感、乱世之痛,尤有拨乱反正、改变现状的紧迫感,这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贵州地方中下层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包括戊戌变法运动的原因。
可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所依据的仍旧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幻想用重建纲常伦理道德,清除贪官污吏,革新弊政,再现一个贤君明臣在位、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孔孟之道,经济生活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以清末贵州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和他们最崇拜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例:在清末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之时,郑珍却感到忧虑,感到不满,他甚至认为世风的变化、外国的入侵都缘于此,为此慨叹到:“入时闻言者道苏货、广货相诧极矣。十年来乃盛尚洋货,非自洋来者不贵异。今日英吉利即洋货所由来者也,其于中国何如耶?自去年扰秽海疆,至今大半年,积半天下兵力而犹未荡涤,是何由致之?”他反对开发地下矿藏,除了有对矿工的同情之心外,还耽心“山川精英之意,毕终于五金矣”。并从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出发主张“孔孟固应避钱神”。他极力推崇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认为这才是治理天下之根本:“学术正,天下乱,犹得持正者以治之;至学术亦乱,而治具且失矣。”他还提出求“真知”的问题,指出“事必求是,言必求诚”,特别强调知与行的结合,而他的知与行都是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准则,而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他极力推崇的理想模式是“农勤女纺织,商贩不远鬻。僻社萃廉秀,星居藩果竹。……叟或不识城,儿不识摴鞠”的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社会。莫友芝对于西方物质文化很厌恶,从儒家的“夷夏之辨”观点出发,他不仅反对外国侵略者,而且反对外国的科学技术,他曾写诗称:“海夷非族类,猾夏恣狂狡。机变绝耻心,奇淫售穷巧。”为此,他对洋务运动也不感兴趣。他和郑珍一样,主张靠儒家的“圣道”来拯救人心,挽救危机:“定乱视人心,惟正除百扰”,要求学习诵读经史诸子之书,明义利之辩,“安于贫”。他所向往和经常歌咏的隐居生活和世外桃源,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比较郑珍、莫友芝二人宦途蹉跎的境遇,黎庶昌稍有作为,他因经办洋务并走出国门周游欧洲、在日本任公使,不仅对西洋物质文化有丰富感性认识,而且对西方的议会制度、艺术、教育、社会风情等也有一定的了解,在光绪十年(1884)向朝廷所进《敬陈管见折》中,他还提出“稍稍酌用西法”,实行变法的主张,且具体建议火车宜及早兴办;京师宜修治街道;商务宜重加保护……等。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政治思想等均不曾超越儒家思想的范畴。他追求的是以忠信仁义为立身,进而“仁民爱物”,“明德新民”,“齐之以礼”“博施众庶”,以达到“国治而天下平”、“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即使到了国外,他虽然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但他是从儒学的角度去认同西方文化的,他不仅称“西人立法施度,往往与儒暗合”;并认为西方民主政治、议会制度等,“颇与三代大同”;他甚至引儒家经典以证天文、勾股、重力之学,以及“园囿之观”、“与百姓同乐,同好货好色”等,即寻找儒学与西方自然科学、民情风俗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他主张以儒学去融汇“西学”。为了实践他的这种认识,在日期间,他致力搜求散见于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并“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刻印出版《古逸丛书》;此外,潜心读书治学,计编纂有《续古文辞类纂》,收集整理出几部有关乡邦文化的著作,如《全黔国故颂》、《黔文粹》、《奬牁故事》;《黎氏家集》等,多属国学、地方文化之类;他还和日本朝野人士进行交流,但这种文化交流主要基于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对此,他曾慨叹:“在东西洋日久,愈信孔孟之学为可行”,和他往还的日本文士,或与他诗酒唱酬,或讨论汉学兴废;或切磋对儒学的见解;或与日本医学探讨道家三宝之说、《灵素》经之要旨,等等。正是由于对日本有关人士对儒学的认同估价过高,黎庶昌认为“轻视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主张与日本联合对付西方列强,为此上书清廷,建议修订一个亲密往来互助条约,其结果是,出乎他的意料,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了侵华的甲午之战,主战派中即有当年与黎交往甚密者,为此,他因精神受到刺激而神智恍忽。其实,最令人遗憾的事还在于,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他没有像同时代的严复那样,致力于介绍西方科学文化。
戊戌变法时期,贵州的知识分子关于改革现实的认识,并未超过郑、莫、黎的程度,就一般人而言,尚等而下之,其他,就更是远远不及了。这种状况造成了“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虽因对现实不满而有自发的改革需求与愤然参与,然而此后,因思想滞后,并未真正接受维新思想,就再无或很少对维新派的施为作出积极的反应了。相反, 直至1902年李端棻被赦回筑受聘主持贵州经世学堂时, 当他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将卢梭与孟子、孔子相提并论,不仅学生“哗以为怪”,社会上亦议论纷纷,诽谤之词,恐吓小诗也广为流传,迫使他任教不及一年便离开学堂。我认为,这不仅是保守派使然,也反映当时贵州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态。而这种思想状况便造成了戊戌变法时期,贵州人士因其一度参与而声名卓著,然而实际的反应却非常微弱,特别是戊戌变法运动所推动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在贵州影响不大,收效甚微。
在贵州近代历史上,贵州知识分子曾多次表现其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可贵精神,也多次表现出于新事物认识不足、缺乏后劲的思想缺陷。这也正是贵州人亟欲抓住历史机遇而终未抓住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