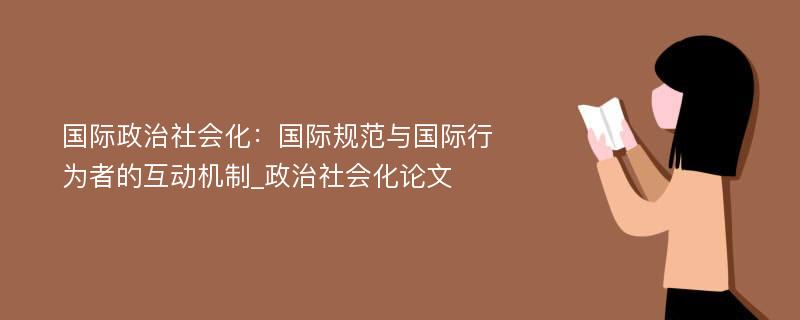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互动论文,机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4)10-0012-11 随着国际政治一体化程度加深,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治理成为学界公认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不二选择。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①。可以说,国际规范和制度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它们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国际行为体如何应对,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国际政治社会学将政治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解释主权国家与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互动关系,将主权国家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比作国内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认为“国家如个人一样,内化由其相互作用的组织所描绘的行为类型和角色期望”②,从而形成国际政治社会化理论,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日趋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重要议题,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③目前,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失规范,国际关系学者在“规范内化”、“国家社会化”、“国际社会化”、“国际化”、“民主化的国际影响因素”④、“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⑤等概念中讨论国际政治社会化问题时,术语不一,概念差异较大,理论阐释多样。概括起来,学者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解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国际规范的内化。有的学者从国际规范内化的角度解释国际政治社会化,认为其是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是“引导一个国家将国际环境所建构的观念与规范予以内化的过程”⑥。内化是使国际社会所主张的价值观念、规范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权国家自身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并成为国际行为体按照“适当性逻辑”遵从新的规范。⑦因此,内化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成为现实的必然途径。 二是国际社会的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组织、霸权国家以及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以国际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对主权国家进行示范和教育的过程。正如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Checkel)认为,社会化是使行为体接受既定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⑧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国家“传授”官僚机构创新理念中的作用进行研究,认为国家的创新观念是源于外部的国际组织,而非国家自身或内部的其他机制。⑨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通过教化机制“改变客体对其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定义”⑩。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社会化被用作对“流氓国家”的再教育机制,(11)也是国际组织塑造和管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机制。在对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非政府组织往往扮演了一个诱导型和批评型教师的角色,国家在其教化下,通过被动型学习而融入新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中。(12)这种观点强调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把其认可的价值、规范以及“适当行为”作为全球治理规范,传授给其成员或追随国,以维系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延续。教化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本质,但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行为体的教化和主权国家对国际规范内化的统一。只有通过主权国家的学习、内化,国际规范才能被国家吸收和转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国际社会化。因此,以国际社会为中心的教化理论有失偏颇。 三是主权国家的学习。这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规范和观念从一个行为体移植到另一行为体的学习过程”(13)。“国际社会的教化观”提出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棘手问题,即如何理解具有自主性的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时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理论也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非是被动的,而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主权国家显然不是被动的受化者。国家本身的能力、态度等在国际社会互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制约因素。因此,这一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否定了霸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强调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使用“国家社会化”和“国家国际化”的概念,前者表示“凭借国家之间所酝酿的观念或规范,通过互惠、模仿、游说和建立信任的方式进行互动,最终达成规范的内化,建构出国家间学习的模式,从而推动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制度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运作”(14);后者“是国家从游离于国际体系逐渐向国际社会正常成员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为体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渐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学习他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了解他国对本国的判断、评价与态度,形成相对完整的自我判断与自我评价,逐渐认知自己的身份和利益”。(15)这意味着行为体的国际融入。(16)可见,“国家社会化”、“国家国际化”注重以心理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学习观,更加强调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在其融入国际社会和推动全球治理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国家自身对学习模式和过程的控制。 四是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这种观点不再拘泥于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孰轻孰重的争论,而是从更宏观的文化角度来讨论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机制。如佟德志等人认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社会化是指“国际政治主体由于相互之间的影响而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它本质上是各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过程”(17)。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也指出,虽然各国的国内文化可能存在着“文明的冲突”,但“国家体系仍然可以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影响到体系内成员的行为”(18)。国际体系处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的混合状态,这就决定了体系内的国家会以敌人、对手或朋友的立场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国际政治社会化就是国家通过强迫、利己或确定合法性的途径内化这些文化。这种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脱离了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和安全的强调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机制的强调,转而关注国际规范和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过程,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探究国际体系文化在国际体系结构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和内化只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行为体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讨论主权国家身份认同和偏好的形成和改变,以及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产生、扩散、遵守和改变的过程。因此,“国际体系文化传播”为理解国际政治社会化设定了文化范围,但又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其全部内涵。 五是个体公民的国际化。有学者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国际化场域对微观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如莉丝柏特·霍克(Liesbet Hooghe)的研究强调,公民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经历可能会使“个人改变其偏好和对既定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认同以与国际组织规范相协调”(19)。对此,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是关于“何时、通过何种手段、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哪些人获得了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知识或信条、观点、态度、价值观、行为意图和行为类型,以及这些认知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国际及国内政治系统的影响如何”(20)。根据卡伊·奥尔德森(Kai Alderson)的观点,个体学习并内化国际规范、政府行为遵从特定国际规范(即政治内化),以及国际规范内化为国家法律制度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三个不具有时序性的过程。(21)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个体公民的国际化是政治个体的国际经验对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过程,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路径,其与以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宏观路径相区别。 综上,本文把国际政治社会化定义为:在国际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行为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互动过程中接受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教化,学习和内化国际体系的文化、价值观、规范和制度,形成新的国际身份和利益认同,并进而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辩证过程;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体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机制,是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机制,是全球治理规范的形成和传播机制。 二、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1)国际规范内化与国家行为外化。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规范内化和主权国家行为外化的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内化是国际规范在各种国际行为主体内部的社会化机制,其结果是重塑主权国家内部精英、民众的价值观念,改革其政治制度的过程。通过内化,国际规范不断融入主权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文化中,成为稳定的国际体系文化。外化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规范的现实化过程,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改变其国际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在新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主权国家作为政治社会化主体,影响或教化其他国家。因此,内化是外化的基础,是国际化的前提,但内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社会化的完成,“外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方式和目的,只有在外化的过程中,人类才能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22)。 (2)主权国家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建构主义者把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行为体看成是一对互动的概念。一方面,国际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学习和内化国际价值,遵守国际规范,形成国际社会认可的身份,从而被国际社会共同体所接纳,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国家的国际社会化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受化国又具有独立于国际社会的自主性,这表现在:第一,通过参与国际活动,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影响国际规范的扩散,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规范和制度。现有的研究强调,作为施化者的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其观念也处于变动之中,很多新观念是从成员国或依附国的观念中上传的,是“相互学习、适应和促进的过程”(23)。第二,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主权国家能够根据需要、目标和自我取向,主动地选择国际规范的内容、内化程度及方式。在考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时,有学者指出传统社会化理论所推崇的“教”与“学”的模式,不能揭示作为施化者的霸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与作为受化者的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特征;在不平等的传授—学习关系中,面对国际组织居高临下的知识传授,国家更多的是“适应”,而不是真正的“学习”。因此,有必要依据“参与实践”理论,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建立起联盟实践解释模式,即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24) (3)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由于在国际交往中国际行为体间不断互动,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化始终贯穿于国际体系的形成、扩散、变化之中,贯穿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形成、发展以及对国际事务认知的变化之中。但由于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其外部生存空间的不断改变,以及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调整,国际政治社会化又会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在研究国际人权规范如何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时指出,政治社会化包括了三个阶段:工具性适应和战略讨价还价阶段;道德意识上升、争议、对话和说服阶段;标志着社会化过程结束的制度化和惯习化阶段。(25)唐贤兴也认为,在国家对外开放的不同阶段,物质资源(如资本和技术)、精神资源(如国家声誉和形象)以及制度资源(如参与国际组织、学习国际制度规范等)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中国对外开放第一个阶段是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第二个阶段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了国家学习和适应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建构的过程。(26) (4)社会化结果的同质性和国家性。国际行为体既包括主权国家,又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在同一国际体系之下的国际行为主体,必然受到相同或相似的国际规范的约束和教化,因此能够形成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于是这种国际政治社会化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即社会经济制度的同质化,(27)有助于产生集体认同和全球治理的共识价值。同时,由于单个主权国家在内化国际规范时,必然与其自身的利益、需要以及发展阶段相一致,这导致不同国家对于相同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形式与方法不同。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主权国家的能力、制度结构及其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有区别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导致了不同国家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千差万别。另外,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并进,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是时空维度交叉互动的统一过程。(28)在此过程中,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缺乏有效的协调和一致性,(29)这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复杂性。因此,从国际体系角度看,主权国家的国家性是国际体系发展的必然。国际政治社会化会产生国际规范的内化,但规范的内化并不是行为的顺从。社会学最新的理论发展表明,社会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同质化,而强调社会复制、顺从和限制个体行为动力的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会导致“过度社会化”(30)。即使在经济领域,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给很多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政策“趋同化”压力,但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供国家调整其国内经济。(31)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提出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是观察国际政治的新视角和窗口,其强调外部因素重塑了国家身份的内部构成并限制国家行为,是对政治发展“内生论”(32)的否定。但国际政治社会化并不排斥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国际社会化绝不是将外来的规范通过直接方式强加给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同质化一定得支配多元化,而是分析在何种环境下国际社会化的机制能真正发挥影响”(33)。 (5)社会化与反社会化并存。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于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接受国可能进行文化移入(学习)或文化抵抗两种基本反应,(34)这就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不仅仅是国际规范的内化和主权国家的学习,而不可避免充满着反复性,甚至出现逆社会化或反社会化现象。(35)其表现在人们对建立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念的拒斥,以及国家行为与主流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等的背离。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由于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是“西方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不是相异文化体系冲突的成就”,(36)而且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认知差异产生了“文明的冲突”,这使全球治理价值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反社会化成为一种常在现象,也提出了全球治理价值层面普世性的匮乏问题。尽管国际政治反社会化有可能通过“不适当”的行动来否定旧的不合理的国际规范,从而产生超越既有规范的新规范,成为创造新的全球治理规范的途径。(37)然而,由于更多的国际政治反社会化反映的是地方性知识,或是不适当的社会化机制引起受化者的感性排斥,对主流全球治理价值拒斥和背离行为对全球治理及主权国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反社会化问题应得到重视。 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持下,全球治理规范和观念迅速扩散到世界,各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实践的推广者都加速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国内拓展。(38)国际政治社会化正是全球治理理念向国内拓展的过程,国家自身的利益考量和国情、国内各方的反应都决定了国家对国际政治社会化或反社会化的态度,决定了国家接受和内化全球治理规范和价值的速度。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如何在维护自身主权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进程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问题。因此,有选择地接受全球治理规范,并对其进行修正和改造,使之与国内治理协调,不失为一种良策。 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机制 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社会化如何实现?国际行为体在传播、教授或内化国际规范时采用何种实践类型或机制?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化机制包括“新行为体的模仿、国际制度为国家提供社会认同;权力和物质利益为社会化提供刺激”(39)。对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不同理论流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现实主义学派在霍布斯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行为的外部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从而限制和塑造着系统内行为体的行为。(40)也就是说,在社会结构/体系的自动制约中,通过理性主义的算计以及对既有制度惩戒机制的畏惧而产生对行为的约束。现实主义者是最低程度的社会化者,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施化者只是受化者的外部结构,其寻求最小化介入受化国家的社会化,受化国对施化者规范的遵从主要依赖于这些行为者的“自社会化”,而受化者也旨在确保以最小国内改变来获取施化者的肯定和奖励。(41)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着各国通过模仿和学习他国成功的实践,改变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地,促进了国家间的趋同,(42)这就是新现实主义学派所主张的系统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在洛克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会产生改变国内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推力,如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三原则”对有意加入欧盟的原东欧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制度变革压力。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模仿和学习进行规则的适应和规避,并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甚至国内制度结构。但新自由制度主义仍建立于理性主义的因果逻辑之上,认为影响国内制度变革的多边制度和约束性条款“是有报偿的,遵守这些条款能带来好处”(43)。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提倡者,其将国际政治社会化产生的起源置于三个前提之上:一是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二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由国际体系建构而成;三是体系理论的范畴应包括国家间的互动。(44)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通过创建共享的意义而非限制行为而发生作用。(45)在此,国际规范的传播并不主要依赖于改变主权国家内部政策和体制的回报结构来影响国家行为,而是在全球治理和各种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改变主权国家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认同。国际社会结构不仅约束行为体的行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认同”(46),进而约束和影响着行为体倾向于合作或暴力的行为选择。 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国际体系结构的教育、制裁和说服是学界共同关注的社会化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分为利益导向型和规范导向型,则前者是基于理性算计的因果逻辑的制裁机制,包括经济制裁、外交援助、军事支持、国际市场权力;后者包括基于论证逻辑的教育和说服机制,这些机制“涉及在缺乏公开的物质或精神强制的情况下,行为体对因果关系分析和认同的思想、观念、态度的变化”(47)。在此,国家对规范的遵从和内化不是出于最大功利考虑,而是认为这是“适当”的行为,这些国际规范重塑了国家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 关于规范导向或利益导向的社会化,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依次出现的,在功利的理性发挥作用之前,规范先确定了国家的利益所在。(48)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和自利是人类(以及国家)行为的相对原因,(49)这两种方式相互强化且很难理清。理性主义者认为,当说服者可以提供实质性的胡萝卜或大棒时,说服才更有可能成功。(50)朱迪思·凯利(Judith Kelly)在研究欧盟制度对东欧国家国内政策的影响时,比较了传统理性选择机制如成员条件性与社会化机制之间的区别,提出条件性激发了行为改变,而社会化机制只是引导行为。(51)另一些建构主义者强调,“说服”包括不同的机制,不会对对方进行强制动员,也不利用直接的物质利益诱导对方进行改革。相反,他们会提供一套行为规范作为“适当行为”,而忽略对采取这种行动的国际激励。(52)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在批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西方制度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中指出,国际制度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一定通过增强政府间协作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实现,但可以通过参与共同体构建的社会化实践来改变主体间的知识,并重塑身份和利益。(53)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是“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附带在以资本输出、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之中,经济全球化为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重要途径”(54)。 而无论是说服、诈骗、争议或羞辱机制,其发生作用都需要一定的条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Kupchan)对历史案例的研究发现:第一,社会化发生的时机和程度高度依赖于霸权国宣传其国际秩序理念的努力,也依赖于次级国家再造及重新确定国内政治合法性的紧迫性;第二,社会化主要是针对精英而非大众,那些对国家行为有重要影响的规范必须得到精英群体的支持;第三,社会化的发生主要通过外部引入或内部再造,而规范劝说并不能引发社会化过程,只有与其物质刺激结合或通过直接干涉来强加这些规范时,次级国家中的精英才开始相信霸权国所阐述的规范和价值。(55)可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能否成功,一与推动国际规范社会化的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密切相关,在国际社会中强大的行为体更有能力通过各种社会化机制推行国际规范;二与被传播的国际规范的性质相关,一般认为根据全球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原则确立的规范更易于传播;三与受化国接受规范的意愿和进行国际社会化的紧迫性相关。(56) 四、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实现的文化因素,其通过多种机制的互动,在国际行为体之中传播国际文化和规范、教导主权国家、维持国际体系和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包括: (1)传播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文化。国际规范(包括国际法、国际惯例、国际机制、国际共识)是政治社会化的传播内容,国际秩序和体系的维持和变革通过国际社会化机制得以实现。首先,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传播国际规范和价值的完整结构,并以国际交流的方式实现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在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凭借一定的传播手段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民众传播一定的观念和规范,教导其国际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实现了国际规范的传播和变迁,推动国际规范的形成、扩散和改变。国际政治社会化通过国际规范在水平方向上的扩散,使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或国际组织获得其他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同和遵从。其次,由于国际政治社会化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外化过程中,作为政治信息的传播者进入传播过程,能够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内化过程,从而培养新的国际规范载体。 (2)塑造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其一,国际政治社会化可以促进国际观念的形成。通过教化使主权国家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引导国家形成一定的观念性认同,“观念性认同是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融合,涉及身份、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57),进而确立有助于全球治理的国家身份。其二,国际政治社会化训练国际交往技能,通过训练主权国家进行国际交流的技能,从而使国家获得参与国际政治生活的一般知识,掌握常规的参与技术和技巧。其三,积累国际参与经验。国际政治行为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外化过程,主权国家一方面根据参与政治生活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矫正自己的参与行为;另一方面又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加深对国际体系的了解,从而进行再政治社会化。正如政治社会化旨在通过塑造个体的政治人格而促进其政治参与以及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对政治秩序的遵守,国际政治社会化也在于重塑主权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改变其不利于国际秩序的行为,促进国际合作。 (3)维护和变革国际体系结构。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者则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提出国际无政府状态存在着三种文化体系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进而向康德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58)然而,由于文化的自我再造性,以及基于国际体系文化变迁的国际体系物质结构的变化是缓慢的,以国际体系文化为内容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维持国际体系和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功能。另外,主权国家在学习和内化国际规范的实践活动中,会加入自己的诠释从而产生新的国际规范;这些新的规范在国际互动中通过政治社会化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因而具有更新和变革既有国际规范和体系结构的功能。 (4)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全球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其强调治理的多中心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全球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59)。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上建立共同的价值和观念,进而使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以此来推动治理规制的实践”(60)。由于全球治理的文化基础是一套符合全体人类利益的全球伦理,因此必然要求在文化选择上超越霸权国家的主导,任何国家的单边主义都会面临巨大的文化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全球“底线价值”(61)的传播和内化的过程。成功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可以促进集体观念和知识认同,形成和传播全球治理规则和价值观念,从而为提升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主观性基础;另一方面,有效的全球治理实践有助于规范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式,传播国际体系文化。 五、国际政治社会化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家在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中展开实践互动的过程和必然结果,包括了国家的国际化以及全球治理规范的形成和内化。(62)国际政治社会化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在于,在国际政治一体化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和受体,势必需要重新确定自身的身份认同,建构新的国际角色。 在全球治理兴起之时,国际政治社会化越来越偏离现实主义的霸权主导论,更多的学者和国家开始关注中等强国在人类安全、人道主义救援、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所发挥的领导者角色。(63)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对国际政治社会化和国际规范的态度经历了“从早期的消极反应,到后来的坚持抵抗,再到今天的主动介入;从被迫接受外部制订的条件,到艰难探索学习适应国际规则之道,甚至尝试把自己的理念与动议加入到人类进步的议程”(64)。其角色经历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拒斥者、受化者以及施化者的变化。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全球治理领域出现诸多包容式改进的困难,中国提出的共生性秩序观、包容性结构正成为一种国际规范,在国际社会传播和践行。(65)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有学者指出,外援在中国产生了双向的“学习过程”:中国接受援助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了解国际规则、融入国际体制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国通过消化吸收西方发展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的发展道路对援助方的援助政策和措施产生了反作用力,甚至发展出国际援助的“中国方式”(66),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地区性组织的肯定,扩大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67) 全球治理的实际进程存在着摩擦与合作、学习与排斥的复杂矛盾。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作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施化者的反社会化表现。其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既有缘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而导致的误判与摩擦,又有我们的外宣缺乏说服力而造成中外解释上的差异与冲突,还有来自我方某些具体制度和做法不合乎国际通用规范而带来的问题。(68)面对反政治社会化,中国应提高自身应对非主流国际规范的能力,提升国际公关能力和说服能力,利用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机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理论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作为,减少西方舆论的误解和偏见。同时,在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新形势下,中国在积极参与和平调解、安全对话、冲突解决以及社会经济重建的过程中,也要以“文化先行”,(69)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与思想之光,创造性地介入全球治理,提高中国在全球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杠杆作用。另外,由于反社会化与社会化的机制密切相关,减少中国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的反社会化问题,还需要“在参与必要的全球治理和增强中国国际介入力度的场合,必须牢记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等对外交往理念,必须谨慎地处理涉及他国主权、尊严和其他权益的事宜”(70)。 总之,中国作为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应创造性介入全球治理过程,明确基本的参与原则及自身角色的定位与调整。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务实,并利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和器物层面加强对国际规范的掌握甚至主导,不断提升中国在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动议权和提升制订规则的能力,将自身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基于责任、合作、和谐与共赢的新价值整合到全球治理议程,促进全球治理观念和知识创新、机制改革和内容调整,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六、结语 “如果说物质性增长塑造的是一个国家制度化的骨架与血肉之躯,那么社会化成长塑造的则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与灵魂。”(71)国家的社会性和国际政治一体化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必然性。与国际政治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相伴随的是全球公共事务的复杂多样性和相互交织性,以及全球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这迫使各种行为体超越主权和国家的有形疆界,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模式。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兴起与国际政治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都要求重新审视国际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意义,重新思考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国际政治社会化理论为研究全球治理、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行为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全面、深刻地认识国际制度规范的内化机制以及国际行为体对国际一体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仍将是国际关系学者需进一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收稿日期:2014-04-21;修订日期:2014-07-22。 注释: ①俞可平著:《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②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7-8. ③袁正清著:《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④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第165-177页。 ⑤刘兴华:“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全球/国际治理的另一种说法,参见[法]让—马克·柯伊考:“国际组织与国际合法性:制约、问题与可能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年第4期,第3-33页。 ⑥Frank Schimmelfenning,"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6,No.1,2000,pp.111-112. ⑦Alexandra Gheciu,"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Autumn 2005,pp.973-1012. ⑧Jeffrey T.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ernational and Framewor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Autumn 2005,pp.801-826. ⑨Martha Finnemor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Teachers of Norms: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Science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4,Autumn 1993,pp.565-597. ⑩Ibid⑤. (11)Alexander George,Bridging the Gap: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93. (12)刘贞晔:“国家的社会化、非政府组织及其理论解释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第26-31页;钟龙彪:“国家社会化:国际关系的一项研究议程”,《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5-137页;刘兴华:“试析国家社会化的演进”,《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71-81页。 (13)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Summer 1990,pp.283-315. (14)黄黎洪:“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6期,第5-13页。 (15)唐贤兴:“对外开放与中国的国际化和制度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9期,第64-69页。 (16)Alice D.Ba,"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The Pacific Review,Vol.19,No.2,June 2006,p.158. (17)佟德志、苟轶:“文化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以新自由主义为个案分析西方政治文明扩张的模式”,《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62-65页。 (1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53页。 (19)Liesbet Hooghe,"Several Roads lead to International Norms,But Few via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Autumm 2005,pp.861-898. (20)苗红娜:“欧美政治社会化研究五十年述评”,《理论界》,2009年10月,第209-212页。 (21)Kai Alderson,"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3,Jul.2001,pp.415-433. (22)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8-26页。 (23)沈骥如:“中国与APEC的相互适应及APEC的未来”;宋泓:“中国与WTO:一个相互学习、适应和促进的过程”,载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16页。 (24)吴文成:“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第30-48页;朱立群:“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第13-29页。 (25)Thomas Risse and Kathryn Sikkink,"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Introduction",in T.Risse,K.Sikkink,eds.,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5-6. (26)唐贤兴:“对外开放与中国的国际化和制度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9期,第64-69页。 (27)Fred Halliday,"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Homogeneity:Burke,Marx,Fukuyama",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1,1992,pp.435-461. (28)凌志云:“试析国际政治社会化”,《文史博览》,2008年第3期,第36-37页。 (29)"Report of Secretary of the 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System-wide Coherence:Delivering as One",http://www.un.org/events/panel/resounds/.../HLP-SWC-FinalReport.pdf. (30)Dennis R.Wrong,"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ivew,Vol.26,1961,p.192. (31)[加]安东尼·希拉:“国家参与的管制博弈——以部门政策应对全球化”,载于[加]马乔里·格里芬·科恩、斯蒂芬·麦克布莱德编,段保良译:《全球化动荡》,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32)“内生论”认为国家发展源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认为国内经济的现代化使个人获得理性价值,使国家转向官僚主义类型,使国际体系变得更加同质化并趋于和平。 (33)黄黎洪:“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6期,第5-13页。 (34)[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著,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9页。 (35)郭树勇:“论国际政治社会化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第8-14页。 (36)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7)林永亮:“全球治理的规范缺失与规范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 (38)刘兴华:“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吴志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向度与气候变化治理”,《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9)P.A.Beck and M.K.Jennings,"Family Traditions,Political Periods,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san Orientations",Journal of Politics,Vol.53,1991,pp.742-763. (40)[美]肯尼恩·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1页。 (41)Frank Schimmelfennig,"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6,No,1,2000,pp.109-139. (42)[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9页。 (43)Philippe C.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 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in Laurence Whitehead,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6-54. (44)[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45)Friedrich Kratochwil and J.G.Ruggi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The State of the Art on the Art of the St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1986,p.767. (46)[美]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2页。 (47)李海龙:“论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一个社会交往视角下的分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83-90页。 (48)Peter J.Katzenstain,Robert O.Keohane and S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1998,p.681. (49)Jon Elster,The Cement of Society,Cambridge Univevsity Press,1989,pp.150-151.James G.March and John P.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Free Press,1989,p.23. (50)Frank Schimmelfennig,"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Membership Incentives,Party Constellations,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Autumn 2005,pp.827-860. (51)Judith Kelley,"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3,Summer 2004,pp.425-457. (52)Joseph Jupille,James A.Caporeso and Jeffrey T.Checkel,"Integrating Institutions:Rationalism,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6,No.1,2003,pp.7-40. (53)Emanuel Adler,"Seeds of Peaceful Change:The OSCE's 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d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9-160. (54)佟德志、苟轶:“文化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以新自由主义为个案分析西方政治文明扩张的模式”,《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62-65页。 (55)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Summer 1990,pp.283-315. (56)方长平:“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第62-67页。 (57)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5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59)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编:《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60)石晨霞:“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第18-28页。 (61)“底线价值”既是各种价值体系、价值观念、价值主张、价值传统都可能认可的价值,也可以是理想价值、制度价值和生活价值共同实践的价值规范。它是人类之构成人类活动的不可突破的底线原则,源自于人类活动的共同结构、相似经历和应付环境的共同处境。参见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12页。“开放的‘类的共同体’和‘包容他者’的价值共识应该成为全球公共规则和社会规范的价值判断标准,成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依据的价值基础,同时还应当成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准则。”参见蔡拓、吴娟:“试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34-40页。 (62)郭树勇把国际政治社会化概括为:一是众多的民族国家加入到一种国际制度文化中去;二是一种新兴的国际政治文化不断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三是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中强权政治的色彩越来越少,不断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乃至康德文化过渡,体现一种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参见郭树勇著:《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63)唐纲:“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8期,第40-48页;[加]安德鲁·F.库珀、[波]阿加塔·安特科维茨著,史明涛、马骏译:《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4)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65)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 (66)其主要特征是中国的发展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且“避开了善治和人权附加条件”。Stephen Marks,"Introduction",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eds.,African Perspective on China in Africa,Fahamu,2007,pp.6-7. (67)杜旸:“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90-99页。 (68)同(64)。 (69)刘海方:“文化先行——关于中国与非洲发展合作的文化思考”,载李安山、安春英、李忠人主编:《中非关系与当代世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2008年版,第322-349页。 (70)同(64),第90页。 (71)郭树勇著:《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标签:政治社会化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