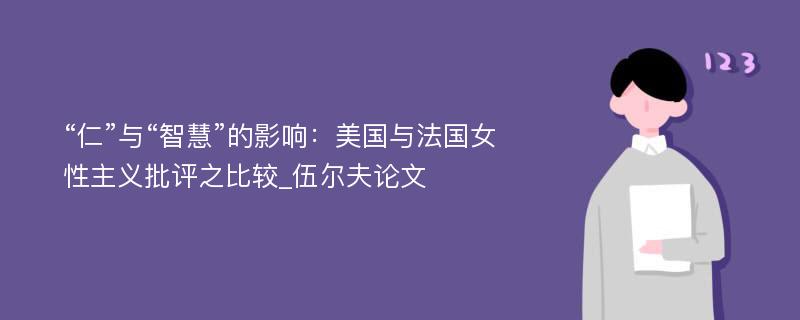
“仁”与“智”的撞击——美、法女权主义批评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法女权主义批评存在着差异,这是许多批评大家所承认的。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批评方法、取势、理论的借重、文学观等方面。总括起来,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是政治的,经验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寻求单一的女性主体,而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则是理论的,心理分析和解构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肯定多元女性主体。
一、政治的、经济主义的与理论的、心理分析和解构的
可以说,自觉的女权主义批评始于政治运动。肖沃尔特明确指出:妇女真正将自己视作女权主义批评家,是在“革命的”1968年之后。[1]在几千年的人类文学史中,作为“半边天”的妇女不能占得一席之地,只可隐约地见到几个影子,这是不公正的。即使初略地考察一下小说的起源,也可发现小说的兴起原有妇女的一份功劳。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对妇女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妇女一开始便与感伤小说(小说雏形之一种)发生了联系,她们或是作者或是读者。当时在法国,人们认为妇女是爱情的权威,而爱情这情感在法国小说传统中起了“主导作用”。(如约翰逊所云:“小说是个故事,一般说的是爱情。”)英国也出现了大量由妇女创作、阅读的感伤小说,尤其是在18世纪。[2]实际上,从1660到1880年,发表的英文小说由妇女创作的占了三分之一。在十八世纪末,女小说家竟居支配地位,创作的小说“更胜一筹”。[3]
面对文学中的这种男权统治,广大知识女性在6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批判。在美国,反映这时期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典型代表是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1970)。米勒特在书中用“父权统治”一词来描述造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父权统治将女人置于男人之下,或视女人劣于男人。米勒特称这种以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来实施性角色行为是“性政治”。她认为性政治是父权统治的支柱,提出“需要改变整个世界,必须向所有建立的标准挑战”。[4]可以说,《性政治》是部女权主义政治纲领。
60年代的其他女权主义著作,如贝蒂·弗里艾登的《女性的神秘》(1963),玛丽·爱尔曼的《思考妇女》(1968),埃鲁·菲杰斯的《父权观念》(1970)以及杰曼思·格里尔的《女太监》(1970),都可以说是妇女运动的产物。和米勒特一样,他们都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弗里艾登和格里尔侧重分析妇女杂志中的妇女形象,虽然缺乏米勒特那样的理论,但因其文章通俗,故在鼓励“提高意识”中起了“重要作用”。[5]
“提高意识”可视为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于60年代末,由激进女权主义者发起。其口号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6]女权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提出“提高意识”,乃是因为她们认为父权统治的作用虽比比皆是,但多数妇女却未必能看得清楚。因此,要使妇女能意识到男性统治的作用,妇女就须有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这便是“提高意识”。“提高意识”就是提高人的认识(awareness),看清先前很少注意或完全忽视的男性统治的事实,把先前只在无意识层次所知觉和理解的东西推进意识层里。“提高意识”的关键作用,是使妇女将个人经验与政治含义联系起来。妇女习惯把自己的痛苦与苦难视为个人的不幸,但若在小组中(一般为12人)互叙苦楚与凄凉,这些痛苦与苦难就可能落入一种模式,虽有不同却折射出妇女生活的共同特征。这样,妇女就会认识到个人的不幸就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了,而可能是社会问题,因而也是政治问题。因此,“提高意识”实为女权主义者将批评直接挂钩于政治的表现。
时至7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仍未脱离“妇女形象分析”模式。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埃伦·莫艾斯的《文学妇女》(1976),以及吉尔伯特和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都带有这种模式的痕迹。若说她们与米勒特有何区别,主要差异之一是在分析妇女形象时,后者侧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而前者侧重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此外,米勒特在《性政治》中表现出的如火山般的勇气与热情,虽与6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的磅礴气势相吻合,但她的谴责或许多于冷静的思考与批评。相形之下,肖沃而特、吉尔伯特和格巴就沉稳得多,分析似较精辟。肖氏划分的“女性”、“女权”“女人”三阶段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她痛斥传统文学史将女作家缩减到几个影子的错误做法,认为妇女确有“自己的文学”。但是,无论是米勒特还是肖沃尔特,是莫艾斯还是吉尔伯特和格巴,其批评方法都是“在批评阅读中用妇女经验来分析妇女形象”。为此,凯尼恩干脆称这种方式为美国式女权主义批评方式,并明确指出其“内在的弱点是它假定了小说与自传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7]
在法国,情形却大相经庭。法国女权主义者很少将女权主义批评与政治直接挂钩。其出版的著作,专论女作家的甚少,亦不怎么分析、比较妇女形象。她们认为“美国的”(有时称作“英美的”)女权主义批评是“幼稚的”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其理论肤浅。鲁思维思曾注意到,“在法国圈子里,‘英国的’是一贬义词。”[8]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对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拉康式的新心理分析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切。这可能与法国的具体国情有关。
其一,有些法国妇女组织在一建立时便与心理分析发生了联系。1968年的五月革命,使法国妇女有了第一次政治觉醒,至当年秋出现了几个激进的妇女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心理分析与政治”(psychet po),中坚人物是安托万内特·富格和埃莱娜·西苏,财神爷是西尔维亚·鲍森纳。该组织一开始就与心理分析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们说:“现有的讨论性欲的唯一话语就是心理分析话语。”[9]
其二,1968年后,巴黎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心理分析热。依据谢丽·特克尔所见,法国出现心理分析文化是在革命左派崩溃后。“人们……现在转向心理分析思想,以求解释所发生的事情。”[10]70年代初,拉康作了一系列讲座,其方式和影响可谓前所未有。或许正是拉康的心理分析促使法国女权主义运动由具体的政治目标转向更抽象的女性理论化。
其三,从历史上说,法国妇女的创作传统比英美弱。英国19世纪就有妇女创作传统,有些女作家已进入文学神殿(如奥斯汀,勃氏姐妹,艾略特)。美国19世纪也出现女作家作品列入畅销书的现象(虽受到男性同行的贬低但却不可忽视)。法国在本世纪前半叶未曾见有杰出的女作家,没有伍尔夫,没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西蒙·德·鲍娃成就虽显赫,但她在《第二性》中却悲伤妇女作品(包括她自己的)没有真正的放肆胆量,就毅力和自信来说,较之斯泰因逊色得多。再者,法国的妇女运动与美国的亦有不同,法国妇女直到1946年还无选举权。这些历史上的原因,迫使法国女权主义者去利用刚在法国出现的拉康式心理分析和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可以说,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在时间上是与它们同步的。
法国女权主义自视“清高”,不屑于美国女权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法国的四大女权主义批评家克丽斯蒂娃、伊丽嘉蕾、西苏和莫娃虽都承认妇女要有实际政治运动,但其思维却主要停留在心理文学试验领域。克丽斯蒂娃认为在文本中超越象征便意味政治反抗。西苏坚持主体性改造必须先于社会改造。事实上西苏反对将女权主义看作与男人的运动相似,认为追求权力实际是模仿而不是超越阳物中心秩序。伊丽嘉蕾也认为妇女必须能欣赏自己作为女人的快乐,应把此快乐看作女性自我意识的起点。莫娃意识在理论上与西苏和伊丽嘉蕾有所对立,提出从政治上解构“妇女”一词本身,但在创造什么样的女性本体问题上,她却想到女性同性恋,并创造了女同性恋史诗《女游击队员》。实际上,莫娃在想象性文本的创作中,对形式和主题的关注与这几位有许多相同之处。
法国女权主义热衷于批评理论,为此人们有时用“法国性”(Frenchness)来指称它的这一特点。构成这种“法国性”的是新心理分析学说和后解构主义理论。安·罗莎琳德·琼斯在《刻画女子气质:法国女性理论》一文中,归纳了四种法国女权主义批评模式:1.解构主义;2.聆听沉默;3.解码女性符号;4.文体政治。[11]实际上这四种模式都逃不出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的范畴,都是运用这两种理论围绕着语言这一核心,来批评阳物中心论。
二、现实主义的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
美、法女权主义者在文学观点上也存在着分歧。
美国女权主义者相信语言能反映现实,因此她们热衷于“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现实主义”女性人物描写,崇尚作为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米勒特在《性政治》中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时,理论的立足点就是语言对应于现实,人物对应于作家。她忽略了文学作品的虚构本质,为此受到科拉·凯普兰的批评。凯氏指责她将作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等同起来,把小说人物读作真实的历史人物,视文学一向为作者意识的有意识表述。[12]吉伯尔特和格巴也有这种倾向。[13]
肖沃尔特也未摆脱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其一,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她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现实主义作品里。其二,她提出的“雌性批评”(gynocriticism)的基础,是假定文本与生活不可分割,二者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依据玛丽·伊格尔顿的见解,“雌性批评阅读最流行的读法是从现实到作者到读者再到现实:在作者的文本中有一作者理解并真实描写的客观现实;读者欣赏文本的可靠性,并将它联系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14]
法国女权主义者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的意义不能确定,它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现实只是一种“虚构物”。针对雌性批评,法国女权主义者阿莉丝·加丁恩提出“女性分析”(gynesis)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女人即女性藉以被发现和表达的过程。玛丽·伊格尔顿就雌性批评和女性分析了精辟的比较和分析,并认为它们各自反映了英美和法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区别。[15]我们试将这些区别列表如下:
雌性批评
1.相信作为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关注“生活之真”;
2.相信可以控制作者;
3.女性经验是真实的试金石
4.作者、人物、读者可在女性意义的探索中结成同盟;
5.强调“妇女”,视其为真实的生物实体;
6.解放即是发现人的真实自我。
女性分析
1.坚持现实是一“虚构物”,关注本文意义的自由玩弄;
2.作者已死;文本万岁;读者万岁;
3.不追求女性经验叙述,强调女性欲望;
4.不特别强调女性作者和女性人物,崇尚先锋派叙述结构;
5.强调“女人”,视其为一“写作效果”而不是一个人;
6.解放是放弃一个(人的)真实自我。
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美、法女权主义者“不是相互对话,而是各说各的一套”。
在讨论这二者的区别时,似应提及肖沃尔特和莫娃在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时的分岐,因为伊格尔顿认为二者的分歧“可看作一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间的争论。”[16]
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仅讨论了妇女成为作家的物质条件,而且也讨论了其心理条件。她认为心灵像身体一样,也有两个性别,心灵的正常和舒适状态是最有益于创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灵中的男女性两个方面是“和睦相处的”。她说:“在男人的心灵中,男人管束女人;在女人的心灵中,女人统辖男人。正常和舒适状态存在之时,亦是二者和睦相处、精神互相合作之时。如果一方为男人,心灵的女人部分必须仍有作用;而一个女人也必须与她身上的男人交合。”[17]伍尔夫由此得出结论: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颗双性同体心灵。她认为莎士比亚是这样的,济慈、斯泰因、库伯、柯勒律治也是。”人必须是女化的男性(woman—manly)或男化的女性(man—womanly)。”[18]
肖沃尔特对伍尔夫的这种雌雄同体见解不满。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她用一章的篇幅来陈述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伍尔夫的见解是种逃避主义,不足以解决性政治问题。她说:“雌雄同体是帮助她逃避她自己的痛苦女性、使她能扼杀和压抑其愤怒和抱负的神话。”[19]“双性同体心灵……是理想艺术家的乌托邦投影。”[20]此外,肖沃尔特对伍尔夫在书中运用的创作技巧(重复,夸张,滑稽模仿,怪诞,多重视角)亦大为不然,视此书“极端的非人格”,“躲躲闪闪,戏语连篇”,尽和读者“玩游戏”。
然而莫娃的见解却与肖沃尔特的迥然有异。莫娃认为肖沃尔特之所以对此不以为然,乃是因为她觉得“伍尔夫的作品不断地逃避批评家的观点,总是拒绝固定在一个统一的视角上”,“相信文本应该反映作者的经验,而且读者越感到经验真实,文本就越有价值”。[21]莫娃觉得肖沃尔特的这些观点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的表现,而这便意味着肖氏未能看清传统人文主义“事实上是父权意识的一部分,在其中心,立着一个天衣无缝的统一自我——无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这自我通常被称作‘男人’……这个统一自我,事实上是阳物自我。”[22]显然,莫娃是从另一角度解读伍尔夫的。
首先,莫娃认为伍尔夫实践的是“一种我们可称作‘解构’的创作形式”。在这种实践中,伍尔夫“揭露了语言拒绝固定于底层的基本意义”。因此伍尔夫文本的飘忽不定,视角的重叠多变,均可看作,“抛弃了支撑父权意识的形而上唯实论”。[23]显而易见,莫娃的这种解读方式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具体运用。德里达把语言的构成看作是意义的无穷迟延,把对意义的基本绝对稳定的追求视作形而上学。既然能指可自由玩弄,意义就不可能有最终的统一。
其次,莫娃认为伍尔夫怀疑人文主义的本体观。她列举两个事实来说明伍尔夫在本体观上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响。一是伍尔夫夫妇创办的出版社出版过弗氏的著作,一是1939年弗氏到伦敦时,伍尔夫去拜会过他。同时,莫娃引证克丽斯蒂娃的理论,来说明伍尔夫拒绝所谓理性的或说合逻辑的创作形式乃是对象征语言的“突破”,而她的雌雄同体观则旨在解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由此可见,莫娃的解读方式是完全对立于肖沃尔特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肖沃尔特发现瑕疵的地方莫娃却发现了优点;肖沃尔特看作回避公开作出政治承诺的东西莫娃却视为革命实践的潜能;肖沃尔特相信伍尔夫多重人格的运用意味着拒绝面对现实,而莫娃却欢迎伍尔夫乐于彻底破坏一元自我观即西方男权人文主义的中心观念。”[24]
关于美、法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学观上的分歧,吉伯尔特和格巴在《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一文中亦有论述。[25]她们以“镜”与“妖”来分别比拟美、法女权主义批评。她们认为高举“镜子”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是理性的,依赖着“经验主义”,“常常根据文学‘是客观和事件的反映’这种假设来工作,其所提出的工程“无论怎样都具有政治性,所以它们有时也并非完美无缺”,这是“因为当描述的镜子变成了规定行动的工具之时,……批评家能在镜中看到的只是她所想看到的东西。”而实践女妖艺术的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的假设与镜子派批评家迥然不同。她们“更激进、更浪漫”,“不认为阐释文学文本是批评家应参与的政治活动”,主张“文学不是经验的再现”。她们崇尚女性欲望,视欲望为力量的源泉和分析的主题。为了把“女性”从父权制束缚中解脱出来,她们提出“女性写作”(西苏语)或“女性语言”(伊丽嘉蕾语)或“诗歌语言革命”(克丽斯蒂娃语),将女性主体性置于文本、性欲或符号序中。
三、寻求单一女性主体与肯定多元妇性主体
何谓女性本体(identity)?它存于何处?对于这些问题,美、法女权主义者往往因其所立的角度不同而得出的答案亦有异。
寻求本体,实际就是解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就是寻求主体(subject)。那么主体是什么呢?
在哲学的认识论中,主体被看作现象客体的对立面,是感觉或意识之总和。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知觉、认识都取决于主体,因而客观世界的意义也依赖于主体。因此,主体成了构成现象世界的复杂而又统一的场所。这里,主体与客体并存,但主体却又是一,是客体的操纵者,是意义与行为的发生地。这是一个独尊的、统一的单一主体。这是种人文主义主体观。当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时,他运用的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的见解,把本体和存在(being)视作个人存在的相互依赖的因素,将个人视作意义之源的统一控制中心。
但还有一种主体性见解。它与上述的人文主义主体观相对立;它解除个人(或说主体)中心,因它否认个人先于语言而存在并把握着语言,相反却认为主体乃因语言而确立。因此在这种主体性见解中,主体是一构造物(made),没有中心,可被改造;它不稳定,是一失去中心的主体(decentered subject)。例如,在拉康的分析中,主体的形成要经历几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婴儿不分自我与其他,这是拉康称作“想象的”存在状态,没有中心自我,不区别主体与客体。第二阶段是“镜子”阶段。婴儿在此阶段仍处于这种“想象的”存在阶段,但已开始将某一整体(unity)投进镜子(不必为真实的镜子)中破碎的自我意象,制造了一个“自我”。当婴儿见到镜中的映象时,他或她就意识到注视的“我”与被注视的“我”间存在一种分裂,因为映出的他(other)看起来有个整体并能控制自己,而注视的“我”却没有。但他或她见到的意象仍部分是想象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婴儿进入语言的阶段。婴儿一旦进入语言便确定其在象征序的主体位置。在这个序里,主体既在语言中产生同时又受制于(subjected)先于其存在的象征法律。由于主体是在语言中产生的,所以它既依赖于(在镜子阶段实现的自我和其他的)差异,又依赖于进入语言内的“我”的位置。所以拉康认为主体概念是通过“我”与“非我”的区分产生的。拉康在这三阶段中划分的想象序和象征序,对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影响极大,尤其是对克丽斯蒂娃。
从整体上看,美国女权主义所持有的是人文主义的主体观。在讨论女性主体性时,她们强调妇女经验和女体主体。一方面,她们猛烈地抨击男性文学标准,认为它既拒绝又不能表现妇女经验;另一方面,她们又崇尚妇女作品,认为妇女作品至少是表现或探索女性经验和本体的场所。长期以来,妇女不仅在政治、经济而且在语言、文学领域受男性剥削、压迫,被男性客体化、边缘化。妇女要抵御这种剥削、压迫和边缘化,要改变自己无史、被湮没的现象,就要确立自己的本体。为此女权主义批评家做了两方面的工作:1.要求建立妇女文学传统以填补父权传统和历史的缺口;2.鼓励妇女积极利用当今的社会结构以确保新发掘的妇女传统不仅能延续不已而且能对父权结构产生持续影响。[26]可以说,米勒特、肖沃尔特、吉尔伯特和格巴所做的工作都属这个范围。她们似乎想说明:女性经验等同于女性本体,或者女性主体对位于女性经验。她们的推理似乎很简单:女性无史(即看不见,无本体),要建立女性历史就要强调女性经验,因为女性经验是男性所没有的,是男性无法表现的,是被男性歪曲、压制的,所以稳定了女性经验就稳定了一个空间,一个女性可立于其中的空间,一个女性主体藉以栖居的空间。
法国女权主义者所持有的是上述的第二种主体观。她们认为女性主体是变化的,不连贯、不稳定和不统一的,妇女要肯定女性本体首先需要具体研究产生本体意识的特定条件以及确立主体的种种基本条件。而她们切入问题的角度主要是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
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基础是构造了一个幻想的至尊主体,把男人理想化。哲学伊始,人类就把自己视作认识论的中心参照点,而认识论就是建立在一套等级对立之上的。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男人向来居于受崇地位,男人与自我、主体、出场、法律相同一,女人却处于劣势,与其他、缺场、混乱相同一。解构主义旨在暴露和解构这种对立,视解构这种形而上逻辑为其最终目的。我们前面提到的四位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都受到拉康的心理分析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影响,尤其是西苏、伊丽嘉蕾和克丽斯蒂娃。她们提出一个理想王国,一个太初女性空间,这空间与母亲之声联结在一起,脱离了象征序、性别角色、其他性和父亲法律。西苏就相信这个理想王国因有母亲之声而成了一切女性创作的源泉,为此她发布“女性写作”宣言《美杜莎的笑》,号召妇女用“身体”写作,表现女性力比多和无意识。在《出击》一文中西苏直接运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批评男尊女卑的二元对立。她说:“哲学、文学、阳物中心主义之间存在一内在联系。哲学本身即以贬低女人开始。将女性秩序置于男性秩序之下,似乎是这部机器运转的条件。”[27]她认为男人也有女性气质,女人也有男性气质,所以“差异自然不能依据社会确定的性别来划分。”[28]“差异最为明显的地方是性快乐层次。”[29]因此要解构阳物中心主义就要有一真正的性欲解放,即改变妇女与自己身体以及男人身体的关系,落实到文学上,就是要创作女性文本。
伊丽嘉蕾也描写这种乌托邦式的女性空间。她企图通过解构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力倡女子气质这一修辞范畴而非“自然”范畴,来创造一种女性语言。在《窥见另一妇女》一书中,她提出什么是女子气质问题。她认为弗洛伊德在分析“她如何诞生”时把妇女当作“其他”,当作一个有别于正常“主体”的异体。伊丽嘉蕾指出弗氏的主体观包含的思想是女子气质只可在俄狄浦斯阶段见到,在此之前任何“主体”都是男性的。她戏谑地问:弗洛伊德怎么没想到子宫妒忌或乳房妒忌?[30]在她看来,男性话语范围里不会有女性主体,因为这种话语像男性性欲一样,是线性的,单一的,不能具体表现女子气质。女人若在这样的话语中说话,要么是跟着男人鹦鹉学舌,要么只作为一个没有具相的“主体”。因此,女人要讲话,要改变父权制,必须先有自己的具体本体感。就此,伊丽嘉蕾提出这本体可以从身体的具性中获取。显然,伊丽嘉蕾将女性本体放在女性身体的具性即女性性欲里。
克丽斯蒂娃就是这一乌托邦空间说得更清楚。她明确将它定在想象序即符号序里。这是她扩展拉康的象征序的区别的结果。克丽斯蒂娃认为象征序将阳物视作父权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律统治了人类社会。想象序却是母亲序(她称之为符号序),联结于儿童全身流动的口腔、肛门驱力。这些驱力的冲动都聚集在她称作“考拉”的地方。当后来因阉割情结使然,儿童确定其在象征序中的位置时,考拉内的东西受到压抑,但其影响却可通过节奏、声调等在语言话语中辨析出来。这些驱力像语言,但还未整理成语言。它们是“符号”材料,要让这材料成为“象征的”,必须要使它们稳定,而这就涉及压抑这些流动的、有节奏的驱力。由于这些心理和生理驱力是在俄狄浦斯情结前产生的,所以它们与母亲的身体有联系,故而“符号的”就必然与女性身体发生联系,而“象征的”则与父亲法律发生关系。这样,女人便成了“其他”,立于象征序之外;她成了先于话语的沉默。另一方面,由于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儿童没有性别意识,所以“符号的”又不为女人所独有。克丽斯蒂娃分析了先锋派作家,认为他们进入的是符号序,洛特雷阿蒙和马拉梅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构成了一个“革命性的”创作形式。[31]这种现代主义诗歌因其承转意外,断行少句,不落俗套,缺乏逻辑结构而威胁着“讲话人”与读者的统一主体性,“主体”便不再被看作是意义之源,因而可能“扩散”,不具统一性。因此可以说,克丽斯蒂娃将女性本体放在符号序里,并将先锋派式的文本视作其具体表现方式。
综述三位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主体在法国女权主义者眼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位置,而且由于这位置是由语言(或文本)构成的,故而它是不稳定的,非统一的。
谢莉尔·B·托斯尼曾将女权主义批评比喻为“花被褥”。[32]构成这“花被褥”的是批评方法上的多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黑人的,女同性恋的……美法女权主义批评只不过是其中之两元,所以它们间的分歧是在摧毁父权统治的大前提下批评方法、切入问题的角度以及借鉴的理论的不同而已,不足为怪。女权主义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权主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正因为是前所未有,它才没有现成的理论与方法可直接运用于自己的目的;它需要“拿来”并加以鉴别,这是一个摸索着前进的过程。美、法女权主义批评存在的分歧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镜”未必能照出全貌,“妖”亦未必能惑人耳目。它们各有所见与未所见,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者的分歧是仁与智的分歧,二者的撞击是仁与智的撞击。这种撞击不会消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相反却只会增长其生命力。“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注释:
[1]伊莱恩·肖沃尔特:《女权主义和文学》,载彼特·科利尔等主编:《当今文学理论》,政体出版社1990版,179页。
[2]德博拉·卡梅伦主编:《女权主义的语言批评》,Routledge,1990,44页。
[3]德博拉·卡梅伦主编:《女权主义的语言批评》,Routledge,1990,52页。
[4]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2页。
[5]玛吉·汉姆:《女权主义批评:作为当代批评家的妇女》,圣马丁出版社1986年版,28-33页。
[6]参见赫斯特·艾森斯坦:《当代女权思潮》,G.K.Hall & Co.,1983,35页。
[7]盖尔加·凯尼恩:《描写妇女:当代妇女小说家》,冥王星出版社1991年版,5页。
[8]伊莱恩·肖沃尔特:《女权主义和文学》,载彼特·科利尔等主编:《当今文学理论》,政体出版社1990版,181页。
[9]伊莱恩·肖沃尔特:《女权主义和文学》,载彼特·科利尔等主编:《当今文学理论》,政体出版社1990版,184页。
[10]伊莱恩·肖沃尔特:《女权主义和文学》,载彼特·科利尔等主编:《当今文学理论》,政体出版社1990版,185页。
[11]载盖尔·格林等主编:《制造差异:女权主义文学批评》,Methuen,1985,96-106页。
[12]见科拉·凯普兰:《激进女权主义和文学:重新思考米勒特的性政治》,载伊格尔顿论文集,157-170页。
[13]玛吉·汉姆:《女权主义批评:作为当代批评家的妇女》,圣马丁出版社1986年版,62页。
[14]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9页。
[15]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9-11页。
[16]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11页。
[17]罗伯特·康·戴维斯等主编:《当代批评与理论》,朗曼出版社1989年版,616页。
[18]罗伯特·康·戴维斯等主编:《当代批评与理论》,朗曼出版社1989年版,619页。
[19]伊格尔顿论文集,25页。
[20]伊格尔顿论文集,30-31页。
[21]托里尔·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载伊格尔顿论文集,39-40页。
[22]托里尔·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载伊格尔顿论文集,43页。
[23]托里尔·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载伊格尔顿论文集,44页。
[24]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18页。
[25]拉夫尔·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177-209页。
[26]见鲍尔·史密斯:《洞察主体》,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35页。
[27]戴维·洛奇:《现代批评与理论》,朗曼出版社1988年版,289,291页。
[28]戴维·洛奇:《现代批评与理论》,朗曼出版社1988年版,289,291页。
[29]戴维·洛奇:《现代批评与理论》,朗曼出版社1988年版,289,291页。
[30]见鲍尔·史密斯:《洞察主体》,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42页。
[31]托里尔·莫娃:《性欲/文本政治》,载伊格尔顿论文集,45页。
[32]谢莉·B·托斯尼:《批评的花被褥》,载阿特金斯主编:《当代文学理论》,麦克米兰出版社1989年版,180-191页。
